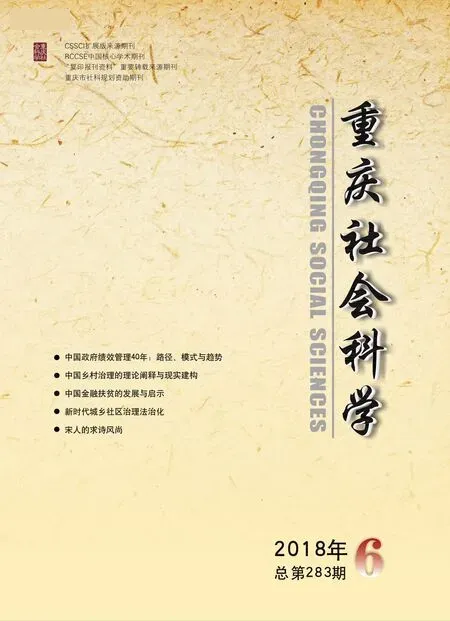乌江流域黔东北地区土司时期教育述略
金子求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乌江流域历史上远离中原,山高峡深,虽早与中原即有往来,然自秦汉至宋元的千余年间,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一直落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嘉靖十四年(1535年)贵州开科乡试,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儒教方兴,人文日盛。主要就乌江流域黔东北民族地区土司时期教育发展作一略述。
一、黔东北地区行政吏治的演变
黔东北地区为土家族聚居地。早在秦汉时期,黔东北地区就与中原王朝互通往来。元代建立土司制度后,中央政府对此民族地区逐步采取“土流并治”的办法,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土流并治就是在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流官与土官并存,以流官治“编户”,以土官治“土民”[1]63。土流并治是中国封建王朝借以实现对民族地区统治的基本策略。土司制度是自秦汉以来,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羁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的行政吏治变革。中央王朝对黔东北地区“土流并治”的吏治模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我国西南地区自古就部族众多,属东方典型的多民族地区。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将巴蜀之外的西南少数民族统称之为西南夷,“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2]2281。自秦汉始,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即有往来。公元前219年,封建政府就在黔东北地区石阡县设置郡县,“其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置夜郎于今县境西部,属象郡”[3]。“秦伐楚遂以为黔中郡地,汉为西南夷地。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以是地分属牂牁、夜郎、武陵三郡[4]7。”思南,谓之“黔中郡”“武陵郡”等。汉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年),汉武帝派鄱阳县令唐蒙为中郎将,“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2]2283。
隋文帝开皇元年,授田宗显“黔中太守知黔州事,民夷率服”。其后,宗显四世孙田克昌,“涉巴峡,卜筑思州,以父功授义军兵马使,后遂世有兹土”[5]161。田氏作为黔东北大姓的统治地位得到确立。唐朝统一边疆后,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设置羁縻府、州、县856个,任用各少数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等官职,世袭其职,世长其民。唐代在贵州乌江以北设置中央直接控制户籍、田亩的经制州,在乌江以南设置羁縻州。唐贞观四年(630年)置思州(今沿河、思南、印江一带)。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思州土著首领,蕃部长田佑恭入朝乞求归附,宋朝廷以其地置思州,管辖今思南、德江、沿河、务川等县境,并命佑恭“知思州事”。此后,田氏世领其地。
宋、元交替,土司制度逐步形成。元朝中央政府在湖广、四川、云南等地设置土司、土官,任命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地方各级官吏,如设置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诸司及土知府、土知县等官职。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6]2308。元政府在民族地区“达鲁花赤长官、长官、副长官”皆“参用其土人为之”[6]2318。元朝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土司任命制度,如诰敕、印章、虎符、承袭、升迁惩处等,“宣慰使司秩从二品,每司宣慰使三员,从二品;同知一员,从三品;副使一员,正四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兼架阁管勾一员,正九品”[6]2308。土司制度有助于中央政令在西南边疆的推行。民族地方土官在维持一方秩序的同时,负责地方岁赋的征收、纳贡、派兵从征、修筑道路、设立驿站、屯田垦殖等。至元十四年(1277年),田景贤以地降元,授思州军民宣抚使。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省宣慰司降为思州军民安抚司,后改为思州军民宣抚司。思州政权在明正德年间被改为思南、思州两宣慰司,辖39个长官司,如黔东北沿河祐溪长官司、水德江长官司和蛮夷长官司、思南宣慰司直属地、印江思邛江长官司和郎溪蛮夷长官司、江口省溪、提溪长官司等。清道光《思南府续志》载:“隨府司朗溪正司,皆少师子礼,公支裔也。其由开疆授职世袭者蛮彝(夷)正司安氏、朗溪副司任氏,肇于宋沿河祐溪正司张氏、副司冉氏;安化属土县丞张氏、土主簿杨氏、印江属土县丞张氏,肇于元;安化土巡检陆氏,肇於明。盖自明田宣慰罢后,迄我朝各司率先归附”。[5]1661365年,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杨琛向朱元璋交附元授宣慰使诰身,田仁智遂为明朝廷授宣慰使。其后继由田大雅、田宗鼎承袭。同年,思州宣抚使田仁厚遣使归附明朝。朱元璋命改思州宣抚司为思州宣慰司,田仁厚为宣慰使,后继田弘正、田琛承袭。明永乐九年(1411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和思州宣慰使田琛为争夺朱砂矿井爆发战争。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朱棣趁解决田氏二土司相互攻杀之机,废除思南、思州二土司,“分思州、思南地,更置州县”,将两宣慰司管辖的39个长官司改置思州、石阡、新化、思南、镇远、铜仁、乌罗、黎平八府。明政府在贵州废除土司的同时,设承宣布政使司,派遣流官治理思州、石阡、镇远等府。明朝在广西、贵州等地州县授“纳土归附”的土官以世袭知州,并“设流官吏目佐之”[7]。
土司制度在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方面显现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但其弊端日益显露。清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谕令四川、陕西、云南、贵州等省督抚提镇:“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於所属土民,多端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8]清政府在大肆开拓“苗疆”的同时,大规模改土归流。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上奏朝廷《改土归流疏》:“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雍正十三年(1735年)始,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黔东北土司势力大为削弱。但清代改土归流仍不彻底,土司残余仍旧保留。鄂尔泰《正疆界定流土疏》中说:“旨至苗民管辖一事,臣查土司改流,原属正务,但有应改者,有不应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应改而不得不缓改者;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审时度势,顺情得理,庶先无成心,而有济公事。若不论有无过犯,一概勒令改流,无论不足以服人,兼恐即无以善后。如果相安在‘土’,原无异于在‘流’。如不相安在‘流’,亦无异于在‘土’也。 ”[9]黔东北沿河祐溪正副长官司、郎溪正副长官司、印江土县丞、石阡府属省溪正副长官司、提溪正副长官司等土司在清代仍得以延续,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消除。
二、黔东北土司时期教育状况
秦汉设置郡县,隋唐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羁縻州县,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的羁縻制度至元代形成完整的土司制度。明清政府逐渐施行改土归流,对民族地方施以土流并治。历代统治者对边疆少数民族加强管辖的同时,亦注重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文治教化,以达“教化安边”之效。如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播州土司杨粲,南宋宁宗嘉泰初年承袭播州安抚使职后,修造儒学、琳宫、梵刹等,建学养士,推崇儒学,制定《家训十条》:“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候、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10]54元朝建立土司制度的同时,在黔东北地区提倡尊孔崇儒,传播程朱理学,并广设学校,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亦在土司地区建立儒学,令土司子弟入学习礼,并允许土司子弟入国子监。《明史》选举志载:“云南、四川皆有土官生。”[11]1677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诏诸土司皆立儒学”[12],使明代土司教育一时兴盛。1644年清军入关后定都北京,清初统治者十分重视兴文教对政权的巩固作用,“世祖勘定天下,命赈助贫生,优免在学生员,官给廪饩”。顺治七年(1650年),世宗汲取明末战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阙焉未讲”之教训,明确提出:“帝王敷治,文教为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并令礼部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士子,研修理学、道德、典故诸书,“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13]3114。历代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文治教化,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和文化繁荣。土司时期,乌江流域黔东北地区各类学校渐增,人才辈出。
(一)兴儒学
所谓学校,一曰国学,二曰府、州、县学。地方官学即为儒学,或称乡学、学宫。秦汉以来,历代统治者皆重视儒学教育。学校教育发展至明代,其体系日臻完备。“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 ”[11]1686明政府规定:“科举必由学校。 ”[11]1675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宗学、武学、医学、阴阳学等;地方官学亦较健全。鉴于元代学校教育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又明政权初建,“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立”,朱元璋极为重视文教,“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11]1686。洪武二年(1369年),明政府遂向全国发布兴学令,“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其后,明政府大兴学校,并配备健全的官职体系,给以优厚的教职待遇:“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由于政府的重视,明初官学呈现前所未有之盛世,“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11]1686。
明朝令边疆土官设儒学,如宣慰司学、安抚司和长官司学等。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太祖谕礼部:“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14]监察御史裴丞相奏请“四川贵、播二州,湖广思南、思州宣慰使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皆“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永乐五年(1407年),思南、思州宣慰使司学建成。思南宣慰使司儒学是黔东北地区第一所官学。此外黔东北地区还有郎溪司、蛮夷司、沿河司学等少数民族地方官学。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南、思州二宣慰使被革职后所设思南、思州二府,后司学改为府学。思南府学在府治东北,宣慰田氏旧宅。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自河东宣慰学迁建。成化年间,知府王南增建,后经多次修缮,“正德二年,知府宁阅修。嘉靖年间,知府李文敏、张镖洪价先后修葺。隆庆六年知府田稔更葺之……”[15]159此前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朝廷增设石阡府学,后经成化十六年(1480年)、万历十八年(1590年)间多次修缮。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知府郭原宾又建“敬一亭”于尊经阁后旁,并建崇圣祠、名宦乡贤二祠[15]160。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知府周骥建铜仁府学。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巡抚王燕题设,知县王原修建铜仁县学[15]160-161。万历年间,邑人御史萧重圣疏请设印江县学,明末毁于战乱,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始得重建。康熙三十八年,巡抚王燕题请设学,知县姚夔建安化县学。雍正五年(1727年)知县蒋燧重修[15]160。至此,乌江流域黔东北地区府、州、县学日臻完备。
清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同样注重文治教化。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贵州巡抚赵廷臣疏言:“贵州古称鬼方,自城市外,四顾皆苗。其贵阳以东,苗为夥,而铜苗、九股为悍……专事斗杀,驭之甚难。”[16]“父子兄弟群处,强凌弱,众暴寡,绝无先王礼义之教,其由来旧矣。故驭苗者,往往急则用威,威激而叛;缓则用恩,恩滥而骄。”[17]鉴于此,赵廷臣向清廷建议:“乘此遐荒初辟,首明教化以端本……今后土官应袭,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者,听补廪、科贡,与汉民一体仕进。使明知礼义之为利,则儒教日兴而悍俗渐变矣。”[17]其进谏获朝廷议准,清廷遂令地方官查苗民中稍通文理者,开送学道考试,择其优者量取,送附近府、州、县、卫学肄业。就地方官学的教授内容而言,府、州、县学主要向土司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使其濡染华夏礼仪,以行礼乐教化之责。同时,官学也是师生祭孔、奏乐、习礼之处所。明初政府规定,府、州、县学专习经书,以礼、乐、射、御、书、数等科为主。清代官学主要传习《御纂经解》《性理》《诗》《古文辞》及校订《十三经》《二十二史》《三通》、《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等儒家经典或宋明理学。康熙年间,《圣谕十六条》为各类学校读本。雍正后,清廷在土司、土民子弟中传授《圣谕广训》,课以经书,使土官土民渐知礼仪,以图教化安边之用。
(二)设书院
书院是唐宋至明清时期兴起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起初多为文人学士藏书、讲学之所,后来渐渐发展成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1]67。历代“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13]3119。宋代书院一时兴盛,据统计,宋代共建有书院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18]。清代各地所设书院尤多,“各省学校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19]411。
与府、州、县学等官学相比,书院更注重学术造诣。其教职多由“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品行方正,学问博通,素为士林所推重者”[19]412担任。各书院长则由地方官绅自行延访品学兼优者担任。各书院院长任上须延请品端学裕之人充任教职。
乌江流域自南宋时期就开始出现书院。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绍庆府治彭水县(今贵州省沿河县)境,建有銮塘书院和竹溪书院,此系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最早的书院。乌江流域书院虽初创较早,但因地处西南边陲,交通阻隔,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书院发展一度缓慢。自南宋绍兴年间初办书院始,至元末,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书院不过3所。明代历时270余年间,乌江流域书院共12所。但在历代中央政权推动下,民族地方文人学士捐资兴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书院亦逐渐兴盛。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石阡府始建镇东书院,隆庆六年(1572年)该府又建明德书院。清初统治者为加强思想控制,以防“地方游士无行之徒空谈废业”,顺治朝大兴儒学的同时禁止地方士人私设书院。至康熙后,地方书院则又日渐勃兴。雍正时期,政府从政策和经费上扶持地方书院发展。清政府设“捐输局”加强对地方书院的管理,并从经费上资助书院事业。《清文献通考》卷七十载:“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政府经费的资助主要用途一是教职员的“修金、薪膳、聘仪、节仪、程仪、开馆折席费”;二是行政人员的薪水,如“斋长津贴、礼房纸张费、官师课午膳茶水费、官师课卷费、看司工食费、资卷费”;三是用于生童的“膏火、奖赏、宾兴”;四是用于书院的祭祀活动费,如“开馆祭先师、丁祭、礼生衣资、香油”[20]。清代政府政策和财力上的支持促进了民间书院的勃兴。至康熙年间,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书院一时兴盛,共达致9所,雍正年间又修办3所,乾隆年间19所,嘉庆年间7所,道光时期修办3所,咸丰年间创办1所,同治年间7所,光绪年间则又修建 15 所,共达 77 所书院[21]200-201。
黔东北地区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增设印江龙津书院,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增设德江文思书院[1]68。黔东北地区书院亦得益于民间地方望族有识之士资助。明清时期思南府还建有“斗坤”“为仁”“中和”三书院。其中,斗坤书院位于思南府万胜山顶,系明隆庆年间佥事周以鲁建。为仁书院位于思南府真武观内,明代知府田稔、推官伍佽与郡人李渭均在此讲学[22]。中和书院系思南同知陈以耀兴建于明万历辛亥年 (1611年)。道光年间思南府周、黄两姓捐资兴建凤鸣书院。同治元年(1862年),思南府邑绅冯谦臣创建修文书院。
(三)办社学和义学
黔东北地区土司时期的基础教育主要包括社学和义学。社学是封建地方政府官办的进行儿童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学校。社学始创于元代。元制五十户为一社,每社均设一所学校,令土民子弟农闲时入学,授之儒家经典。乌江流域黔东北地区的社学始创于明代。明初朱元璋诏令地方政府建立社学。永乐以后,中央政府严令乌江流域各地长官司在治所及村寨人口密集处兴建社学,令土司及族属子弟入学习礼。弘治贵州志言:“贵州始有学,盖洪武二十六年也”,“太祖皇帝不鄙夷,其民既设贵州宣慰使司抚治之,又欲使皆复于善,设立学校以教焉”[4]19。此举激发了民族子弟入学的积极性,促成民族地方社学渐兴,“各建室十余间,聚子弟教之”,一时间“闾里文化,勃然兴起”[4]20。嘉靖、万历年间,随着贵州开科乡试后科举制度影响日盛,乌江流域石阡府、思南府及府属朗溪、蛮夷、水德江、沿河等长官司辖地及务川、印江两县均大兴社学。嘉靖十年(1531年),印江知县严阶在县城太阳山麓最早建立社学。
清顺治九年(1652年),朝廷议准:“每乡置社学一区,择文行优者充社师,免其差徭,量给廪饩。凡近乡子弟十二岁以上令入学。”[13]3119顺治十五年(1658年)又规定:“土司子弟,有向化愿学者,令立学一所。行地方官取文理明通者一人,充为教读,以司训督,岁给饩银八两,膏火银二十四两,地方官动正项支给。 ”[23]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清廷认为各地社学“近多冒滥”[23]。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遂在各地改设义学。乾隆十六年(1751年),贵州布政使温福认为,黔省苗民之所以反抗官府起事,苗地社学遍立是其中重要起因,“无知愚苗,开其智巧,将必奸诈百出”[24],遂上奏清廷密饬地方官逐步裁革社学。此后,黔东北地区社学逐渐为清廷裁革,此后私塾和义学兴起。
义学主要为孤寒子弟及土司应袭子弟而设。清初,京师五城各立一所义学,后各省府、州、县多设义学,“教孤寒生童,或苗、蛮、黎、瑶子弟秀巽者。规制简略,可无述也”[13]3119。黔省义学始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巡抚于准题请各府州县置立,“俾土苗子弟入学肄业”[25],故朝廷议准黔省各府州县设义学,“将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俟袭替。其族属人等,并苗民子弟愿入学者,亦令送学。该府州县复设训导,躬亲教谕”[23]。雍正八年(1730年),总督鄂尔泰、巡抚张广泗、学政晏斯盛题请设古州等处义学,“化导苗民子弟,其课读塾师,准于附近州县,选择老成谨慎、文品兼优之生员,前往教导”[24]。义学的教学内容一方面是识字教学,令生童学习《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幼学琼林》《千家诗》《圣谕广训》等。另一方面则是令生童学习儒家经典,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春秋》等[21]192。清代康雍乾时期,黔东北义学兴盛,主要有思南府安化县、印江县、婺川县义学,石阡府龙泉县义学,思州府玉屏县、青溪县义学及铜仁府铜仁县义学等。自雍正朝推行改土归流后在黔东北地区广设义学,义学教育对平民子弟起到了“识字明理”“人心向学”的作用。
三、黔东北土司时期教育的影响
秦汉以来,中原地区与西南边疆民族地方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逐步加深。至元代,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明清政府施行土流并治的行政吏治变革,加强对少数民族地方的管辖。同时,历代中原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兴儒学,设立书院,创办社学和义学,振兴民族文化教育,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明进步,加强了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稳定和文化繁荣。就乌江流域黔东北地区而言,土司时期教育的兴盛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土司时期少数民族科举人才辈出
由于儒学、书院和义学普及,土官、土民及其子弟深受汉文化的儒家价值观浸染,少数民族地区人文精神得以提升。黔东北文人学士开始传习儒家经典,通过科举入仕,人才辈出。贵州在明代建省后的百余年间,仍然没有独立举办的乡试。历代贵州学人只能就试云南、四川、湖广,往试者多因路途遥远,不习水土,十病其九,只得作罢,严重导致科举人才的埋没。明嘉靖九年(1530年),黔东北思南府人田秋向朝廷上书《开贤科以宏文教疏》,奏请明政府应允贵州开科乡试。嘉靖十四年(1535年),明朝廷允准贵州开设科场。1537年,贵州首次乡试在贵阳举行,结束了贵州无科场的历史。贵州开设乡试后,明清两代黔东北地区产生了大批的科举人才,如思南共397名举人,其中38名考中进士;石阡21人中进士,120人中举。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石阡府成世瑄、张海澜、徐培琛三人同时考中进士,被誉为“贵州三杰”,一时间“十里三进士,隔墙两翰林”在黔地传为佳话[1]72。
(二)兴文教,变夷风
土司时期儒学教育的兴盛有助于推动民族地区形成“人心向学”,重视文教的良好社会风气,起到了“兴文教,变夷风”[26]的作用。元明清三代,黔东北儒学渐兴,少数民族文人学士或著书立说,或立馆讲学,促进了社会文明进步和文化繁荣。如明代著名理学名臣,思南府水德司人李渭先后著有《先行录问答》三卷、《大儒治规》三卷、《简记》三卷及《诗文》三卷等,其丰富的理学成就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繁荣功不可没。黔东北地区土司时期官学、书院及义学共同构成的民族地方教育体系在历史发展中将中原文明的思想观念、文化理念引入,强化了儒家文化在民族地方的影响。以土司时期官学教育为例,黔东北地区各府、州、县学教授内容多为儒家经典,以经、史、子、集和八股文为内容,科举取士,其生徒为博取功名而刻苦诵研儒家经典,推动了儒学在民族地方的传承。书院教育虽相对独立于科举制体系之外,但至明清后期,尤清代政府将书院纳入其行政管辖,书院教育逐渐走向官学化,客观上促进了儒家文化在民族地方的勃兴。
(三)教化安边,促进统一
从文化教育的政治功能看,土司时期儒学的推行,起到了“教化安边”的作用,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办学校,令土司子弟诵读儒家经典,使其深谙华夏礼仪,并养成忠君尽孝意识,有利于维护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秩序。如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播州土司杨粲即告诫子弟:“吾家自唐守播,累世恪守忠节。吾老矣!勉继吾志,勿堕家声,世世子孙,不离忠孝二字。”[10]78中原王朝在民族地区通过科举取士,将包括贫寒子弟在内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选拔到各级政权机构,打破了黔东北地区长期由地方土司豪强把持政权的历史,改变了民族地区权力阶层的文化构成。地方统治者文化素质的提高,有效维护中央政权对民族地区的管辖,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
(四)黔东北地区土司时期教育发展对当代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土司时期中央王朝重视民族地方文化教育,尽管是出于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但历代封建政府对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视和政策支持是推动民族地方教育兴盛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对民族地方本土人才的培养和重视。如黔东北历史上,被誉为“贵州科举之父”的田秋和“阳明理学”名臣李渭等一批地方政治、文化精英为家乡教育疾呼,并以自身丰富的文化成就推动了地方文化发展。田秋不仅对明代贵州开科乡试有功,且为鼓励和支持平民学子应试,他首倡地方绅士捐买卷田。李渭晚年辞官还乡后,在思南府城北建“中和书院”讲学,兴学黔中,致黔东北一时文风昌盛。在清代黔东北地区还有德江田氏、思南冉氏、沿河王藩及石阡徐培琛等文化精英各领风骚。正是诸如此类“乡贤”人物在民族地方文化教育发展进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导向和推动作用,培育“新乡贤文化”亦是当今民族地方文化教育和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
[1]罗中玺、田永国.乌江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以黔东北地区为个案[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石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石阡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1.
[4]沈庠,赵瓒.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M].贵阳:贵州省图书馆影印本,2010.
[5]夏修恕等修,萧琯等纂.思南府续志·秩官门:卷五[M].贵阳:贵州省图书馆据四川省图书馆藏道光二十一年刻本复制油印本,1966.
[6]宋濂等.元史·百官志七:卷九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
[7]苏濬.土司志[M],粤西文载:卷十二[M]//粤西通载:第四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37.
[8]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1985:326.
[9]鄂尔泰.正疆界定流土疏·雍正六年[G]//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兵政十七蛮防上:卷八十六.清道光七年刻本.
[10]遵义市文化局.遵义地区文物志[Z].遵义:遵义地区文物管委会,1984.
[11]张廷玉等.明史·选举一:卷六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G].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511.
[13]赵尔巽等.清史稿·选举志一:卷一百零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4]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九·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壬申条[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3476.
[15]贵州通志:卷九·学校·乾隆六年刊本[M].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159,160,160-161,160.
[16]赵尔巽等.清史稿·列传六十赵廷臣:卷二百七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030.
[17]清实录·世祖实录:卷一二六[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978.
[18]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53.
[19]清会典事例·礼部·学校·各省书院:卷三九五[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
[20]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406.
[21]李良品,彭福荣,崔莉等.乌江流域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22]贵州通志:卷九·书院·乾隆六年刊本[M].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163.
[23]清会典事例·礼部·学校·各省义学:卷三九六[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417.
[24]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三九五[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21.
[25]贵州通志:卷九·义学·乾隆六年刊本[M].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68:164.
[26]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