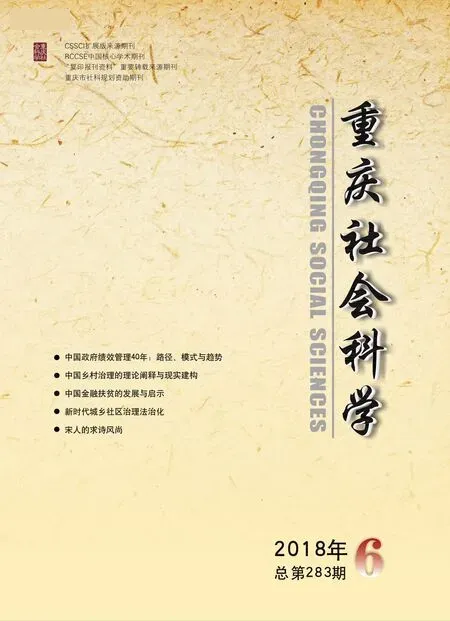宋人的求诗风尚
左福生 陈 忻
(1.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2.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求诗即指请求他人作诗、赐诗,与“求字”“求画”的旨趣类似。向他人求诗现象在唐人的交往中已初显端倪,如唐刘商诗《殷秀才求诗》就表明此诗乃应求而作。不过,唐人求诗尚不常见,而求诗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习尚,则无疑是始于宋代,几乎形成无人不求诗、无事不求诗的文化景象。求诗风尚促使诗歌创作由原来的诗人主体分化出自我抒写和应求而作两种路径,这不是创作主体位移的浅层问题,而是关涉诗歌的文体功能衍变及其抒写方式的转换等若干方面。同时,也反映出诗歌在宋代的人际交往中所承担的现实作用及宋代政治文化、人文心理等对诗歌创作的深层影响。
一、求诗风尚的体现
“求诗”一词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东汉经学家何休注《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颂声作矣”句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1]所谓“使之民间求诗”,是指统治者为察风俗人情,知施政之得失而派人搜集民间歌谣,也叫采风、采诗。另外,求诗还有“寻觅诗材”的意思,如陆游《别王伯高》诗:“倾家酿酒犹嫌少,入海求诗未厌深。”[2]952不过,本文拟探讨的“求诗”内涵与此二意不同,而是专指向他人请求作诗、赐诗的一种文化行为。
宋人的求诗意向有多种表达,从大量宋代文献及诗文中发现,除“求诗”这一用语外,乞诗、索诗、觅诗和要诗等诸词都是表达此诉求的同义语。此外,宋人还偶用“丐诗”等,以下主要针对前五者加以举证论述。
(一)求诗
宋人用“求诗”来表达请人作诗最为常见,如《容斋随笔》“题咏绝唱”条写道:“钱伸仲大夫于锡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先人已有卜筑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垄在其上,名曰‘望云’;种桃数百千株名曰‘芳美’;凿地涌泉,或以为与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诗于一时名流……”[3]洪迈所述的是钱大夫在庄园中建成四座新亭,并请当时名流题诗颂美。文中所谓“求诗”,就是请他人作诗之意,这一表述在宋诗中极为常见,出现于诗题的有:文彦博《子山朝奉倅汝阴过洛访别求诗》,陆游《杜敬叔寓僧舍开轩松下以虚濑名之来求诗》,范成大《程助教远饯求诗》,周必大《青衣道人罗尚简论予命宜退不宜进甚契鄙心连日求诗为赋一首》等。以上诗人们在题目上透露出自己是受人求取而创作的信息。此外,求诗信息也常常在诗句中体现,如:“从事滁阳去,寄音苦求诗。”[4]“疏轩以睡名,从我远求诗”。[5]“去年清富屡求诗,今日凭阑约翠微”[6]34377“来从千里求诗去,愧我全无一句工。 ”[6]40011;“来翁摊纸要求诗,犹胜儿童弱弄嬉。”[6]40133有苦求者,有远道求者,乃至千里来求者,有求一次不得而屡求者,还有带着纸墨登门而求者,这些描述把宋人为求得一诗而不辞千里、苦心讨求、反复絮念的情态毕现于纸上。
(二)乞诗
《广韵·迄韵》曰:“乞,求也。”乞诗与求诗在请求他人作诗、赐诗意向上基本无别。如南宋赵蕃《日者张一麟求诗谩与二绝句》其一云“家徒四壁将何赠,乞与两诗赊卦钱”,诗题言“求诗”,诗中则说“乞与”,可见二者不分彼此。宋人诗题也屡用“乞诗”,如:宋祁《王秀才贽赋乞诗为别归毗陵》,王安石《宝应二三进士见送乞诗》,彭汝砺《睦仲乞诗用其韵谢之》等。在诗中透露乞诗意向的也很常见,如释德洪《留题三峰壁间》云:“庵头禅翁头雪白,麻衣草履提筇策……粥罢收盂知我去,殷勤乞与题诗句。 ”[6]15061又如(王禹偁《送冯尊师》)“今说东南行,问我坚乞诗。 ”[6]671从以上诗句中,我们同样能感受到乞诗者的殷切之意,如“殷勤乞”“坚乞”等都为反复求取。
(三)索诗
宋人话语中的索诗有体现自上而下的索取之意,如:“景德中,夏英公初授馆职,时方早秋,上夕宴后庭,酒酣,遽命中使诣公索新词。”[7]4850这里“索新词”是代表皇帝的旨意,是受“命”来取要的,不容违抗,故此类“索诗”与本文求诗性质有别,不纳入细论。索诗也有求取诗篇的意思。如:周必大《慧海大师日智索诗》,王十朋《薛师约抚干召饭于圆通寺主僧瀹茗索诗》,索诗者都为僧人,索诗对象是周必大、王十朋等官员,可想而知此处索诗必定与前文“遽命中使诣公索新词”有明显之别。另如:李之仪 《春日同梁十四宴李公昭朝霞阁侍儿舞梁州曲彻客有以润罗为赠公昭命玉杯满酌酬之又以金钟邀儿相属既釂出乌丝栏索诗》,此诗题所述宛曲多折,其大意是侍儿向与宴的宾客李之仪请诗,这与白居易《卢侍御小伎乞诗座上留赠》及道潜访苏轼于徐州轼使营伎戏求诗于潜的情况类似。从中反映出唐宋时期文人士夫宴饮的文化特色,其中侍从婢女不仅以其歌舞伎艺为客人助兴,还通过求诗、索诗等方式把宴会气氛推向高潮。
(四)觅诗
觅,一般释作寻觅、找寻,“觅诗”义可作两解,一为寻找、搜寻诗材或诗思,这是一种文学创作的主观行为。如,杨万里《走笔和张功父玉照堂十绝》其二云:“年年春信遣人疑,赚出诗人枉觅诗。”[6]26355陆游《弋阳县驿》:“大雨山中采药回,丫头岩畔觅诗来。”[2]932杨、陆诗中的“觅诗”都是寻觅、搜求诗材或诗思的意思,与本文所论之求诗风尚非同一范畴。不过,在宋人的视域里,“觅诗”内涵已突破诗人自我外求的局限,而大量地转为他者向诗人求取诗作的一种意向性祈请,与上文之求诗、乞诗和索诗的趣味趋于一致。如,陆游《法云孚上座求诗》:“堪笑山僧能好事,乞碑才去觅诗来。”[2]4253诗人将“乞碑”与“觅诗”对举,显然,乞与觅作为外求的意义十分接近乃至相同,且此诗题为“求诗”,更加证实了求诗与觅诗的一致性。另如王当《何源秀才为予画山水图觅诗》,张孝祥《黄龙侍者本高觅诗》等,其“觅诗”都表示请人作诗或赐诗。
(五)要诗
“要”字在古汉语里表“求”意较为常见。如,朱熹对《孟子·公孙丑上》“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中之“要”注作“要,求”[8]。如此,宋人说“要诗”是不是“求诗”呢?我们可通过具体的诗例来考查。如,吕本中《尤美轩在玉山县小叶村喻子才作尉时名之取欧阳文忠公醉翁亭记所谓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者后数年旧轩既毁复作寺僧移轩山下汪圣锡要诗叙本末因成数句寄之》,此诗长题大意是汪圣锡为新建的尤美轩向吕本中请诗以纪,与李纲《吕元直得书天台郭外治园林作退老堂求诗为赋两章》及司马光《聂著作三舅谪官长沙作耐辱亭书来索诗》为异曲同工。王安石《纯甫出释惠崇画要予作诗》,此诗题在“要”与“诗”之间嵌入“予作”二字,这恰恰暗示了求诗的本意,“要予作诗”当解为“请求我作诗”,明显有“求”的意味。另如释居简《严山人饷蒲萄浆》:“凉州亦有杨州鹤,惆怅山人只要诗。”尤其范成大《大雪送炭与芥隐》颇有意味,其云:“无因同拨地炉灰,想见柴荆晚未开。不是雪中须送炭,聊装风景要诗来。”[9]求诗者为顺利获诗,故借雪中送炭而求,颇有主动讨好之意,生动展示其求诗的微妙策略。
二、求诗主体的广泛性
诗为儒者事,但在宋代社会中,求诗者却绝不限于儒者,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及时代风气的熏染,求诗之风涉及宋代不同文化层次的“社会人”。若从身份来区分,主要有以下几类群体。
(一)文人士大夫
宋代文人士大夫属于文化阶层内的求诗者,如吴处厚《青箱杂记》:“夏文庄公竦幼负才藻,超迈不群……公举制科,庭对策罢,方出殿门,遇杨徽之,见其年少,遽邀与语曰:‘老夫他则不知,唯喜吟咏。愿丐贤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不识可否?’公援笔欣然曰:‘殿上衮衣明日月,砚中旗影动龙蛇。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杨公叹服数四,曰:‘真将相器也。’”[10]此中杨徽向夏竦“丐”诗,场合是在制科庭对后,体现了文人的共同趣尚。对此,魏泰《东轩笔录》中记道:“夏郑公竦以父殁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读书,攻为诗……后数年,举制科,对策廷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阅人多矣,视贤良,他日必贵,乞一诗以志今日之事。’因以吴绫手巾展于前,郑公乘兴题曰:‘帘内衮衣明黼黻,殿前旗斾杂龙蛇。纵横落笔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是年制册高等。”[11]此记只说求诗人乃老宦者,但特别点明 “以吴绫手巾展于前”的具体方式,突出求诗者热切诚恳的姿态。对同一事件,南宋陈鹄还进行了评述:“然不若前诗用字之工。所谓宦者以吴绫手巾求诗,想必有此。至今殿试唱名,宦者例求三名诗,但句语少有工者,诗亦不足重矣。”[7]4846他特意指出宋代殿试唱名时形成“宦者例求三名诗”的惯例,此尚自北宋初年发端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时间跨度之长、风气蔓延之盛,可谓文人求诗的典范习尚。
(二)方外之士
宋代佛教得到长足发展,僧人队伍不断壮大,在求诗群体中,僧人占有极大比例。如:释德洪的《巴川衲子求诗》《隐山照上人求诗》,陆游《小僧乞诗》,王洋《化僧求诗往宣城》《僧求诗往平江》,李之仪《德山方老退院索诗送行即席口占》,孔武仲《维那观师以偈示余求诗为赠因成两绝句》,晁公休《夏日过庄严寺寺僧索诗为留三绝拉舍弟同赋》,张侃《象山住持僧于修求诗戏题五十六字》,张孝祥《黄龙侍者本高觅诗》。求诗僧人有普通衲子小僧、过路化僧、侍者、住持僧,以及将退隐的老方丈等,几乎遍及释门各阶层。
宋人的诗文作品中有许多反映方外人热衷于向文士求取诗作的现象。如苏轼《自记庐山诗》中写道:“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开先寺主求诗,为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2]东坡此行本“不欲作诗”,但求诗僧俗络绎不绝,最后还是破戒写下多首。
方外群体中的道士也常有求诗表现,如:孔平仲《黄道士求诗戏为口号赠之》,胡宗师《题双流保国观古柏》云:“求诗道士心弥坚,试听一诵工曹诗。”
(三)侍从人员
宋代社会的底层群体,如马倌车夫、侍儿婢女等也是求诗者,在此姑以“侍从人员”作泛称。这一群体有相应的人身依附性,求诗之举常受主人的命使和安排,且多发生在宴会场合。另如朱淑真《会魏夫人席上命小鬟妙舞曲终求诗于予以飞雪满群山为韵作五绝》。又如:“曾诚存之,元符间任馆职,尝与同舍诸公饮王诜都尉家。有侍儿辈侍香求诗求字者,以烟浓近侍香为韵。存之得浓字,赋诗云:‘俯仰佳人看墨踪,和研亲炷宝熏浓。诗情过笔当千里,妙思凝香欲万重。山盎泄云倾白酒,越罗沾露浥黄封。从来粉黛宜灯烛,妙手凭谁写醉容。’”[13]曾诚的应作则明显表现调和游戏的意味。以上求诗者或为官伎或作侍儿,她们所求一般是代表主人的意思,体现特定的侑酒娱乐性质。
(四)外邦使节
宋人的求诗风尚还影响了与之往来的番邦邻国,如洪皓的《春使留金金臣悟室求诗口占漫答》,反映的是南宋使金文臣受金国馆臣求诗而作的事实;而受汉文化影响甚深的那些日本、高丽来客也常向宋人发出求诗之请。如释慧开《日本觉心禅人远来炷香请教求诗迅笔赠之》;又如《耆旧续闻》“熙宁中,高丽遣使入贡,且求王平甫学士京师题咏。有旨令权知开封府元厚之内翰抄录以赐。厚之自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诗戏之曰:‘谁使诗仙来凤沼?欲传贾客过鸡林。’”[7]4846这些求诗现象反映出在宋代文化的辐射影响下,邻国异族对汉诗的崇奉与热爱。
以上主要从身份角度分述了几类求诗主体,若从年龄、职业等方面来说,求诗者的层次性则显得更为复杂。有向人求诗的老翁,如陈着《戴仲伦求诗》:“来翁摊纸要求诗,犹胜儿童弱弄嬉。”有小孩求诗,如曾丰《应童子科欧阳文成觅诗漫以塞责》:“身躯眇小胆气大,齿发幼艾言语苍。”释德洪《童子名道员年五岁余不茹荤随母往来禅林旦夕稍长即与落髪觅诗作此授之》;有生员和秀才,如释宝昙《府学二生求诗》,卲雍《答宁秀才求诗吟》;还有萍水相逢的坐客向人求诗,如释德洪《临川康乐亭碾茶观女优拨琵琶坐客索诗》;就连那些掐命看相的江湖人士也常常向人求诗,如张镃《相士陈邦彦觅诗》,陈着《赠医相者赵月堂》云:“去年相访无一辞,忽焉而去岂其欺。今年重来又默默,问之不答惟求诗。汝袖医手缄相口,却要我开诗口落汝手。”赵蕃《日者张一麟求诗谩与二绝句》等。更有甚者,连村夫野老也学会求诗,如陈起《旧题隐者壁一绝》云:“总道村居无外事,有人庭下索诗逋。”另如,陆文圭《宿黄村土人索诗》。
从以上所述求诗者的复杂身份见出,求诗风气所及之社会阶层极为广泛,几可以“无人不求诗”来概括其实况。
三、求诗的缘起与方式
宋人求诗之盛已如上述,他们为何热衷于此,且通常是以哪些方式相求?下文从求诗缘起和求诗方式两方面做进一步分析和论述。
(一)求诗的缘起
宋人求诗大致可分交际性求诗和实用性求诗两个方面。相对而言,前者淡化求诗的功利色彩,求写双方不是简单的施受关系,彼此间有着情感交流与关怀需要;而实用性求诗则强化诗作的现实功能,求诗者希望借他人之笔对日常情事做一番渲染点缀,寄寓了求者对诗的纪事性期待。
宋代主流文化是趋雅避俗的,宋人尤其是知识阶层在交往中比较注重文饰,求诗正是他们在人际交往中体现的一种雅化趣尚和诗意表达,一般无明显的功利性。如:曾巩《恩藏主送古梅求诗》云:“折得前村雪里枝,殷勤来聘老夫诗。”黄庭坚《王才元舍人许牡丹求诗》云:“闻道潜溪千叶紫,主人不剪要题诗。欲搜佳句恐春老,试遣七言赊一枝。”求诗者借送梅与牡丹这类雅物来换取诗歌,主客之间或“聘”或“赊”,在彼此满足中颇见情致和雅趣。黄庭坚《贾天锡惠宝熏乞诗予以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十字作诗报之》,“宝熏”是用来熏香和取暖的炉子,为士夫阶层的日用之物。为体现礼尚往来,黄庭坚一口气写了十首诗以“报之”,这些行为反映出宋人求诗中对礼节的自觉遵守,双方是一种互敬互惠的赠予,有利于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王之道《赠坚上人》诗,题下诗人特注曰:“坚上人以竹斋居士所赠《岷峩图诗》来求鄙句,为赋之,继其韵也。”[6]21079诗中写道:“师诚乞诗我丐画,不然无用徒相煎。”诗人受求写诗,于是乘机向来者“丐画”,有互求的交际性,彼此都出于对艺术的赏爱,不显鄙俗。即便是涉及日常物用的求诗,也很见生活趣味和人情友善,如苏轼诗《明日复以大鱼为馈重二十斤且求诗故复戏之》。从题中“馈”与“戏”两个互动性词中,我们分明感受到的不是鱼的实用价值,而是二者在交往中流露的友情和兴味。宋人通过求诗,把生活中的日用琐事进行了诗化的涵养和提升,在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交往中,进行情谊的沟通和意趣的传达。
此中最见情感性的应属赠别性求诗。何谓赠别求诗?简言之,即二者于分别之时,其一方请求另一方写诗相赠。这与一般的赠别诗不同,是经“求”而赠,求诗者一般是即将远去者,如贬官、赴任官、致仕官、邂逅而别的友人、拟退的寺院住持等。如王安石《次韵陆定远以谪往来求诗》:“牢落何由共一樽,相望空复叹芝焚。济时尚负生平学,慰我应多别后文。可但风流追甫白,由来家世出机云。行吟强欲偷新格,自笑安能到万分。”[5]847诗中流露出二人相互勉励、彼此留恋的深切情意。苏轼的《王颐赴建州钱监求诗及草书》,向东坡求诗求字的王颐是将远赴福建之建州任钱监的官员;张耒《王子开朝散早年以疾病谢事还江阴求诗为别三首》,向张耒求诗的王子开则是因去官归乡而相请;汪藻《东安许明府同里之亲任满回家求诗为别即席赋此兼简熊使君》,许明府向汪藻求诗则是因官期任满将别。
实用性求诗多指为具体情事而向人请诗,其突出功能是志新庆喜、装点生活。如对新居落成、斋室取名、亲人生日等这些喜庆之事,宋人多会请人借题发挥,作诗讴歌,或是记其过程,或是渲染其意义,尽管其用处依然是精神层面的,但此类求诗总归有一定的实用指向。如:李纲《吕元直得书天台郭外治园林作退老堂求诗为赋两章》,曾几《李商叟秀才求斋名于王元渤以养源名之求诗》,周必大《安福宗子师共兄弟五人作慈顺堂养母求诗》,舒邦佐《戴氏楼名折桂来觅诗赋二十八字》,等等。或楼堂落成求诗,或为轩室取名而觅索,求者刻意追求一种诗意的感受与记忆,以表达祝颂和点缀的目的。
在庆寿、生日等事宜上宋人也屡屡求诗。有为母祝寿而求,如叶适的《詹鲁山解元以寿母求诗》;有为子生日而求,如陈着的《王得淦次子侑生日求诗》。宋人将“佳会寄诗以亲”的雅尚推而吉事求诗以庆,求诗行为显示出鲜明的人伦烙印,饱含着亲情的关怀。而这种关怀甚至延伸至于逝者,即为死者求诗,以饰其终。如周必大《陈君举示张孝恺行状且求诗孝恺尝摄令华亭有善状》,戴复古《黎明府见示令叔显谟开国墓志求诗为赋三首》等。此外,还有人生前为自己营造墓舍而求诗,如陆游《姜总管自筑墓舍名茧庵求诗》等,显示出求诗习俗的在现实生活中无所不及的渗透力。
宋人求诗还与其他艺术创作相互生发交融,为画求诗正是这一审美趣尚衍生的结果。如:周必大《刘讷画庐陵三老图求诗》,陆游《谢君寄一犁春雨图求诗为作绝句二首》。张弋《赠沈庄可》云:“问遍菊名因作谱,画将兰本要求诗。”宋人深谙一人难胜诗画兼善之理,于是他们就理性地选择分工,将作画和题诗的任务分而合之,这一风气对题画诗的独立发展及其艺术水平的提升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
宋人求诗还涉及一些极为细微和琐碎之事。如释德洪《郭佑之太尉试新龙团索诗》,“龙团”是一种贡茶,连喝茶这样的平常事也求人题诗,真可谓生活处处不离诗。再如:陈文蔚《傅材甫窗前白月桂开材甫索诗戏作》,释德洪《宗公以兰见遗风叶萧散兰芽并茁一干双花斗开宗以为瑞乞诗记其事》,慕容彦逢《友人有小石数颗以余酷爱将辍惠佳者唯求一诗赋以赠之》。这些仅为兰桂花开、辍惠小石的琐事求诗,充分体现出宋人体察入微的生活态度,以至于他们入梦时都有索诗、作诗的事发生,如苏轼《数日前梦一僧出二镜求诗僧以镜置日中其影甚异其一如芭蕉其一如莲花梦中与作诗》。对宋人如此频繁的求诗现象,以“无事不求诗”来形容似无夸张之嫌。
(二)求诗的方式
宋人求诗有其约定俗成的范式,主要表现为口头求诗、以信求诗、以诗求诗三方面,其各自表现如下。
一是口头求诗,也可称作当面求诗。求诗者与诗人同时在场,如宴饮席间求诗,即属此类。另如求诗者亲自登门求取也为此类常态,如:惠洪《余将北游留海昏而馀佑禅者自靖安来觅诗》云:“入门一调笑,如获璧与珪。问来何所欲,雅意在诗词。”[14]另如:释德洪《龙安送宗上人游东吴》之“牵衣觅诗亦不恶,怪君儿戏忘髭须”,周必大《青衣道人罗尚简论予命宜退不宜进甚契鄙心连日求诗为赋一首》,陆游《蜀僧宗杰来乞诗三日不去作长句送之》等,“牵衣觅诗”“连日求诗”“乞诗三日不去”等,都属于当面发生的行为。
二是以信求诗。宋人在“千里来求诗”的劳苦之外,还借助书信往来以达成远程的求赠交流。如王安石《寄题睡轩》写道:“疏轩以睡名,从我远求诗。”即说明寄受双方存在的距离感。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也是如此:“书来乞诗要自写,为把栗尾书溪藤。”[15]溪藤指剡溪纸,此代指书信。另如:戴表元《道衡书寄求诗》,赵蕃《刘伯山书来云有施主为造一亭刘子澄名曰竹溪索诗为赋二首》,韩淲《元默书来作溪翁亭成且索诗因寄四章》等,“书来”“书寄”之语都是远道以信相求的体现。至若楼钥《代仲舅尚书赋江山得助楼》诗写道:“几番贻书来索诗,只许归田为君赋。”[6]29404说明以信索诗也有类似口头求诗那样须反复求取的情况。
三是以诗求诗。宋人还把求诗意向借诗以传达,在诗中向对方委婉而求,显得颇为雅致。如北宋赵抃《和诗僧栖诘求诗》云:“蟠龙僧胆大如斗,直以诗求蜀守诗。”[6]4224以诗求诗还促成酬唱的发生,即赠诗者会袭用求诗之原韵来作复,如:姜特立《和赵太中觅诗》,华镇《钱秀才索诗用韵酬之》,彭汝砺《睦仲乞诗用其韵谢之》,王之道《赠坚上人》诗注曰:“坚上人以竹斋居士所赠《岷峩图诗》来求鄙句,为赋之,继其韵也。”这些应求诗都做到了依韵复诗的特点,体现了宋人唱和诗普遍遵循的体式。
四、求诗之风与宋人文化心理及以诗代文倾向
宋人求诗风尚的极盛有其多方面成因,其中宋代政治文化的转型及在此文化作用下的士人心理嬗变,以及宋代文体功能的演变等是决定此风炽盛的主要因素。
(一)宋代政治文化转型与士人文化心理之变
一种习尚的形成必有其社会文化根源,宋人求诗风尚的炽盛既是传统风习延续发展的表现,同时,也与宋代的政治文化及人文心理有密切关联。宋代文化教育迈越往代,文化阶层得到充分扩展,宋人的整体文化修养普遍提升,这有效地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和受众群体的壮大。加之宋代统治者偃武佑文,尊儒崇道,施行文治,造就了宋人趋于含蓄而内敛的性格。在人际交往中宋人避俗趋雅,注重文饰,诗歌成为他们情感传达和思想交流的有效手段,表现出彬彬之礼和温文之雅。
宋人性格的内敛和含蓄进而影响其心理的敏感与细腻。敏感则易为外事触动并产生反应;细腻则感知精微,对细小之物都会留心或产生审美感受,这正是宋人对一花一石的新变和特异有惊喜、生好感,并求人题诗的内在原因。
严耕望先生对唐人诗学发达之因曾做了如下总结:“唐代诗学发达,文人对于一切事物喜欢以诗篇发之,朋友通讯,更是经常以诗代文。”[16]其实用这句话来概括宋人求诗之热也是颇为精准和恰当的。相对于唐人而言,宋人对生活中的经历见闻更加用心,探奇和追问的倾向更显突出,对现实诸现象既勤于探本溯源,分析原委,且习于将之与社会人生相联系,掘发其哲理意味和现实意义。“玩赏与研究之兴味与智力活动本身之创造性,有机交织,此即宋人生活形态与精神又一特征。”[17]
(二)文体功能演变下的以诗代文倾向
宋人的探究兴趣和关注热情,于宋代的杂论文发展中有较明显的体现。曾枣庄先生所著《宋文通论》中,其杂论文种类分为建筑物记、学记、山水记和书画记四大项[18],其中仅建筑物记就涉及楼、台、亭、阁、堂、斋、轩、室、院、祠、堤、桥、井、磨、寺观、园林、厅壁等17个小类,足见宋人记文取材之广泛及其对生活情事关注之深细。其实,宋人杂记文中还有一类别具风味的选材,即记日常见闻事物者,如欧阳修的《菱溪石记》、赵汝回的《小石记》、曹愿长的《同心一会记》、潘华的《梦鱼记》、邹浩的《梅花记》、苏轼的《牡丹记叙》、王庠的《雅州蒙顶茶记》等。虽然曾著中未专门列出,但此类记文似乎更能反映宋人“玩赏与研究之兴味”。推而观之,宋人求诗与此兴味颇有相通,即寻求诗文来记录和描述赏心之事。他们常用“求诗以纪”等话语来表达求诗之目的,这一点我们可从众多应求而作的诗中见其端倪。如苏轼《杨康功有石状如醉道士为赋此诗》云:“求诗纪其异,本末得细剖。”[15]1375诗人对“求诗纪其异”的动机心领神会,于是循其意图而对奇石大作文章,以排律体式着重对奇石的成因和来源做深入探究与追述,直到“本末得细剖”才罢休,在“玩赏与研究”中表露了求写双方的探奇之趣。至如司马光的《晋康陈生家世以孝悌闻有异木连理生其庭郡欲旌表其门不果王禹玉为之求诗于朝之士大夫以纪之》,吕本中的《尤美轩在玉山县小叶村喻子才作尉时名之取欧阳文忠公醉翁亭记所谓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者后数年旧轩既毁复作寺僧移轩山下汪圣锡要诗叙本末因成数句寄之》,释德洪《宗公以兰见遗风叶萧散兰芽并茁一干双花斗开宗以为瑞乞诗记其事》,李之仪《清凉寺觉海召饭出数帖相示览之怆然求诗为记》等,诗题所标示的“求诗……以纪之”“要诗叙本末”“乞诗记其事”“求诗为记”等等,都有鲜明的叙事需求和倾向。为实现这一目的,诗人在操作上就必须侧重于对事情物理做来龙去脉的叙述与论析,这既给求者留下确切可感的追忆之据,也为诗人的纵笔书写展开发挥的空间。
宋人的求“记”心理与此时的文体发展走向是很有关联的。吴承学先生指出:“《文苑英华》等宋人总集与《文选》相比,明显多出传、记二体。在《文选》产生的时代及此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叙事与述人的功能基本是由史传来完成的,所以只有少数文体如碑文涉及叙事与述人的功能。但是从唐宋古文兴盛以后,出现文史合流的倾向。文章学内部越来越重视叙事性,叙事性文章也大为增多。具体反映到文体上,便是记体与传体的高度繁荣。”[19]
吴先生的表述无疑是合乎事实的,上文关于宋代记体文的丰富性足以反映其繁荣局面。记、传体的繁荣无形中也影响到诗歌的笔法,具体表现为诗歌中叙事、述人、铭物的成分受到一定强化。诗歌在许多方面与记文并驾齐驱,如在对亭台楼阁的叙写上,诗歌和记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艺术效果上都是足可比肩的。而在日常交往中,诗歌还以其创作便捷、形式自由、抒情性强等优点得到求诗者的青睐,成为取代记文之首选。如上文求诗所涉的人情事理,宋人每每舍文而用诗,以兼顾其纪事和抒情的双重需要。当然,此中也不排除诗的即兴性和高雅性诸因素。“以诗代文”倾向还可从应求而作的篇幅体量上获得一定的印证,即诗人为了达到叙事周圆、详备切意的目的,往往作洋洋大篇,极尽渲染,在诗题上每以“作长句”“作长篇”“赋长句”相标榜,或一篇不能尽意而连写多首以达情,如李纲《吕元直得书天台郭外治园林作退老堂求诗为赋两章》,韩淲《元默书来作溪翁亭成且索诗因寄四章》等。这也见出,在以诗代文的实践中,诗人为适应和对接文所书写的内容而做出的努力。
五、求诗风尚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宋人求诗而使人际关系趋于温雅和谐,其日常情事借诗的浸润而富有意蕴。求诗之风在改善宋人生活品位的同时,对诗歌创作也构成潜在的双重影响。
(一)正面作用
求诗有其可取之一面,它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契机,促进了文学与生活的互动,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及表达形式。有些求诗的时机契入得当,能有效地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写出平时苦思而不得的好作品。如道潜在徐州席上的应机之作就深得时人的赞许,曾产生“一坐大惊,自是名闻海内”[20]的风靡效应。苏轼庐山之行,应僧人之求而写《题西林壁》,该诗融景致与哲理于一体,妙趣横生,令人涵咏不尽,成为古今绝调。可见,求诗不仅考验了诗人的应机构思能力,也确为诗界奉献了相应精品和创作经验。
(二)负面效应
求诗对诗歌创作及其规律也有不利影响,传统诗学强调诗言志,作为吟咏性情的手段,“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1]所发出的吟唱最为切情。刘勰言:“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1]其应“感”主体指向的是诗人自身。显然,在缘情机制下,诗人自我抒怀是其主要动机,其性情抒写是明朗的。但是,在应求而作的机制下,诗人成了他者的代言人,为迎合他者之趣,在落笔时无可避免地要揣摩求诗者的感受,诗情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则因此而受到干涉乃至冲击。
概括来说,求诗风气对诗歌创作的负面效应主要有三:其一是违背了诗人的创作激情。如梅尧臣 《方在许昌幕内弟滁州谢判官有书邀余诗送近闻欧阳永叔移守此郡为我寄声也》云:“从事滁阳去,寄音苦求诗。吾诗固少爱,唯尔太守知。不敢辄所拒,勉勉作此辞。”诗人在“寄音苦求”之下复诗,“勉勉作此辞”中既含有礼节性的谦逊,也吐露诗人难以推脱的苦衷。再如,韩驹《孙朝散母封彭城郡君赐霞帔以诗贺之》则道:“从予乞诗费雕镌,借君诗囊为君编,那知又有南陔篇。”[6]16581写出诗思不畅、费尽雕镌的窘状,最后不得已而借对方的诗料来编排,其应酬编造之状可以想见。难怪王质在《和李无变求诗》中叹道:“十年惨淡经营处,一点青萤灯火知。平日诗从天外得,只今天外总无诗。”[6]28862其二是敷衍搪塞之习的蔓延。由于情感的疏离,应请的被动仓促,而诗人又碍于情面,不宜拒绝,于是出现游戏笔墨的草率应酬。如:强至的《月卿大师以书抵予言到自永嘉今将还杭因索诗送行聊书短章塞来请之勤》,曾丰的《应童子科欧阳文成觅诗漫以塞责》等,诗人竟把“塞来请之勤”“塞责”置于题中,丝毫不掩内心的抵制搪塞之绪,故此类诗难免为文造情、以文害情之弊。其三是产生不少庸陋之作。求诗的随机性,写诗的即时性,回复的应酬性,这些因素决定了求诗之风也是促成庸诗、恶诗的有力推手。如,李光《稚山运使作斋名藏晖且觅诗久不能成今兹以大农召行有日因成鄙句并以送行》,诗人在久难成诗的焦虑下,只得以鄙句相送。北宋诗人吴奎曾形象道出此应请创作的尴尬,他在《游云门寺留题灵运上人房》一诗中写道:“禅师索题诗,捉笔事冥搜。欲速驰思远,顷刻历九州。象外有真物,惝怳难为求。徒形陈熟言,羞涩为尔留。”[6]4448诗人受禅师索求,尽管其极力“精鹜八极,心游万仞”,仍无所遂心,只好人云亦云,凑点陈言俗语以对,羞愧之情自难掩抑。宋人方回对此感触颇深,其《复如严陵就省先墓》诗道出了被求者的普遍心声:“一僧独沾醉,座间具纸笔。索诗苦不已,佳句岂易得!”[6]41490好诗是灵感和性情的自然流露,应求而作,往往“佳句”难得。
尽管求诗之风给诗歌创作造成了诸多干扰和冲击,但这一习尚对宋人的诗意交往颇有促进,并强化了诗歌作为公共社会关系的润滑剂功能,有着深刻的文化史和风俗史意义。它涉及文学生成机制中的多个环节,为后人思考有宋一代诗歌繁荣之因提供了生动依据和有益参照,值得学界的研究。
[1]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六[M].文渊阁四库全书.
[2]陆游.剑南诗稿校注:第1册[M].钱仲联,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洪迈.容斋随笔[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449.
[4]梅尧臣.梅尧臣编年校注[M].朱东润,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16.
[5]王安石.王荆公诗笺注:上[M].李壁,笺注,高克勤,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傅璇琮,等.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7]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九/[G].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朱熹.朱子全书:第 6 册[M].朱杰人,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89.
[9]范成大.范石湖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40.
[10]吴处厚.青箱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48.
[11]魏泰.东轩笔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20.
[12]苏轼.苏轼文集:第 5 册[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2165.
[13]张邦基.墨庄漫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185.
[14]释惠洪.注石门文字禅:卷四[M].释廓门贯彻,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255.
[15]苏轼.苏轼诗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16]严耕望.治史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135.
[17]胡晓明.尚意的诗学和宋代人文精神[J].文学遗产,1991(2):79-91.
[18]曾枣庄.宋文通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658-735.
[19]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321.
[20]魏庆之.诗人玉屑: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7:638.
[21]刘勰.文心雕龙注释[M].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