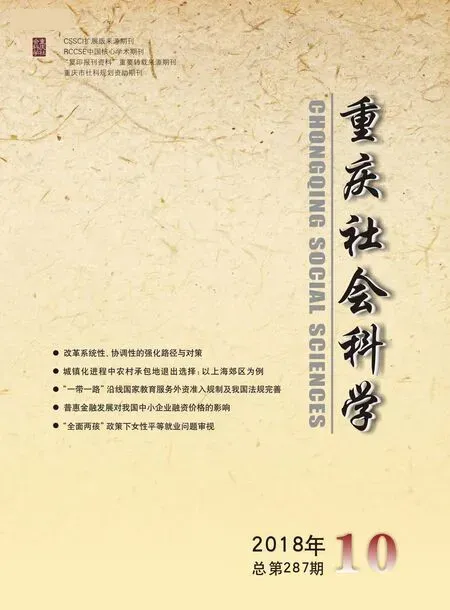唐甄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谭利思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4)
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是清初四川籍的一位思想家、政论家。他的儒学思想独树一帜,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他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关切民生,提出高薪养廉、藏富于民等观点。唐甄的伦理思想依托于他的“天之道故平”的道体观,提倡平等,强调责任,这些不仅有别于传统儒学伦理思想,更对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儒家伦理思想
伦理学是西方学科分类思想下形成的一门学科,它是一门关于道德的科学,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研究道德原则、道德规范,故伦理学又可称为道德学[1]2。我国使用“伦理学”一词是由日语翻译过来的。日本学者在翻译英文ethics时借用了汉语的“伦理”二字,将它译为“伦理学”。伦理学是一个学科概念,有其完整的知识结构和范畴体系。伦理思想则是指对道德问题的思考。本文考察唐甄伦理思想,尤其是对儒家传统的道德问题的思考。首先梳理一下儒家语境下“伦理”和“道德”的概念的来源、内涵和关系以及儒家学者对哪些道德问题进行了思考。
(一)伦理与道德
“伦理”即人伦之理,此二字最早出自《礼记·乐记》所称:“乐者,通伦理者也”[2]125,泛指伦类条理。 徐慎《说文解字》里则认为“伦,从人,辈也,明道也;理,从玉,治玉也”,就是说“伦”可是人与人之间不同辈分的关系,“理”则可以理解为处理人与人之间行为的准则。《左传·文公十八年》提出了五种人际关系及其准则,称为“五教”,“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弟”[3]116。《中庸》也提出五种人际关系,即“五伦”,“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4]28,并将这五种人际关系称为“天下之达道也”。 《孟子·滕文公上》又云,“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4]259。朱子继承了孟子之五伦说,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将它们称为“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这里的“亲”“义”“别”“序”“信”就是用来处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和“朋友”的原则和规范。在儒家学者这里,“伦理”即“伦常之理”,指人际关系中所共守的规范。
在先秦儒家典籍中“道”“德”最初并未连用,也是两个概念。“道”本意是人行之路,后引申为人类行为应当遵守的原则以及支配自然和人类生活的规律。“德”是指有所“得”,偏重于人在实行“道”的过程中内心所得,心中得“道”,并保持它、遵循它就是“德”。也就是说,“道”是最高原则,“德”是原则的实际体现。“道”是抽象的,“德”是具体的。《中庸》中说“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3]35,唯有“至德”才能呈现“道”。“道”“德”二字连用首见于《周易·说卦》,“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荀子·劝学篇》中也有“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5]6。就是说道德可以指人们的道德品质、道德境界和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伦理”和“道德”两个概念的基本含义是相似的,伦理思想包含了道德观念和伦理学说。只不过道德侧重于人们之间实际的道德观念、规范标准即道德品质,伦理学说侧重于关于这种行为和人伦关系的理论。伦理侧重“人伦之理”,道德则侧重“人伦之理”之所“得”。故“伦理”多指“应然的人际关系及其法则”,而道德则多指“实然的道德现象”[6]6。
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包括儒家伦理思想在内)主要讨论了八个问题,分别是:人性问题;道德的最高原则与规范问题;礼义与衣食的问题,即道德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义利”“理欲”问题;“力命”“义命”的问题;“志功”问题,即动机与效果的问题;道德在天地之间的意义,即伦理学与本体论的关系;修养方法问题[1]9。儒家伦理尤其注重人性论、人际关系及法则(即五伦关系)和义利-理欲问题的讨论。
(二)先秦至宋明儒家伦理思想概述
先秦时期的儒家伦理思想由孔子创立,孟子继承和发扬,荀子可看作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总结者。这一时期的儒家伦理思想就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孔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忠、信、孝、悌、恭、宽、敏、惠为具体的道德条目。在义利观方面,孔子重视道德义务,轻视功利目的,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究“君子义以为上”。但是孔子并不绝对排斥“利”,指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4]194。对待个人物质利益,孔子主张“取之有道”,反对见利忘义。理欲观方面,《礼记·乐记》中提出天理人欲的概念:“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2]126《礼记·礼运》篇还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2]78,可以说先秦儒家对人的欲望是承认的。但是,先秦儒家基本都认为“欲”不能纵,要寡欲。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孔子并没有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为五伦,但是提出在君臣关系上要“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4]66,“以道事君,不可则止”[4]128;家庭关系中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4]49,孝悌则是“仁”之本。与人相处要“信”,因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4]59,还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166,进而可以“修己以安人”[4]159、“安百姓”[4]159、“博施于民,而能济众”[4]91。
孟子上承孔子,具体提出“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八个道德规范。人性论上,他认为人性本善,仁义礼智是人所固有,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特质。义利观上,孟子也主张重义轻利。对待个人欲望,孟子主张养心而“寡欲”。孟子明确提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关系,并为这如何处理则五伦关系提出了亲、义、别、序、信的规范。在君臣关系上,孟子特别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4]290。
荀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他的性恶论。荀子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生之所以然谓之性”[5]319,若顺从,此自然属性必定产生“恶”,所以荀子特别重视外在“礼”对人行为的规范和教化作用,只有这样人才能化性起伪。荀子之“礼”具有典章制度、礼仪标准和道德规范等多重含义,是治国之本。义利观上,荀子主张先义后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5]32。荀子也不否认个人利益,“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但是“利”要服从“义”的原则:“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5]414对于个人欲望,荀子提出“以道节欲”。荀子将人际关系分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认为这几对关系“与天地通理,与万世通久”[5]104。君臣关系上,荀子认为臣的重要作用是以德辅君,他认为“大忠”之臣应“以德覆君而化之”[5]187;以德行感动君王是次忠;犯言直谏则是下忠[5]187。
汉代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论为前提,认为道德标准、伦理秩序受天命、天志决定。他用阴阳五行说论证阳尊阴卑,提出“三纲”理论,并用仁义礼智信配五行,将此五德称为“五常”。“三纲”确立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等级秩序,君、父、夫是主导地位,臣、子、妇是从属地位。“五常”则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人性论方面,董仲舒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并提出了性分为上中下三等的“性三品”论。义利观上,董仲舒虽然提出义利两养,承认义之于心、利之于身都重要:“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人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7]248但是,在他看来“仁人”的标准依然是“义”而不是“利”,他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对后世儒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明两代是儒家伦理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都肯定仁义礼智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人性论方面,宋儒二程、朱熹都继承了张载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说法,持性二元论。天地之性是理是纯粹至善,气质之性是理气结合清浊昏明不同,有善有恶。宋儒从二程开始特别注重义利之辨,宋儒的义利之辨有时候也是“理欲”之辨。北宋周敦颐提出“主静无欲”,张载主张“寡欲”,二程则将理欲完全对立,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必须消灭人心才能保存道心。朱子论义利之辨时,也主张“义”为先,也严辨“天理人欲”,认为这两者是对立的,学者须革尽人欲而复天理。但是,朱子同时也认为满足人基本生活需要的欲望是符合天理的,超过一定限度的欲望才是人欲。在讨论与“天理人欲”密切相关的人心、道心之间的关系时,他认为人心和人身是共在的,不可能消灭人心只保留道心的,若人心为道心所节制,那么人心也是道心:“若说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两个心。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8]2010,“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饥寒痛痒,此人心也。恻隐、羞恶、是非、辞让,此道心也。虽上智亦同”[8]1487,“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8]1487,“如饥食渴饮之类,虽小人不能无道心,如恻隐之心是”[8]2011。朱子认为人只有“一个心”,天理本明,只是物欲蒙蔽了人心,如果在心体上时时用“工夫”与人欲作斗争,就会摆脱人欲,心之本体就可以恢复清澈明净。
象山先生虽然在理论体系和求学方法上和朱子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在义利之辨上与朱子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象山先生认为道、理、公、义是一致的:“私意与公理,利欲与道义,其势不两立。”[9]184王阳明心学中,“心”“良知”“性”“理”名异实同,良知是至善的,有善有恶则是良知之发用。阳明在理欲之辨上继承了朱子,认为工夫就在于去人欲、存天理。
二、唐甄伦理思想
唐甄的伦理思想与他的道体论一脉相承,贯彻了“天之道故平”的理念,故唐甄的伦理思想有着鲜明的平等思想的特色。唐甄还十分强调君主对国家、丈夫对家庭应有一定的责任,他对人正常想“养身”“存身”的欲望做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全民适当谋利过上富足的生活恰恰是国之“大利”。
(一)人性论
唐甄在心性论上是宗孟、法王的,提出“执良知以为枢”,故在人性善恶上是主张性善论的。但是,在性德的划分上唐甄依然秉持了儒家的性三品论,认为人的德性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德者少,凶德者少,中德者恒多。中德者,道之善则善,道之不善则不善,唯凶德不移。”[10]110还说:“凡人之性,上者有义无利,其次见利思义,其下见利忘义。上下少而次者多,厚其禄,所以兴义也。上者不德而忠,其次德而后忠,其下虽德不忠。上下少而次者多,厚其禄,所以劝忠也。兴义劝忠,所以厚民生也。”[10]185上、下两头的都少,但是中间的居多。中间这部分人心体与圣人一样,只是心体不彻:“杂以嗜好,拘于礼义”[10]14,心体不能充而已,中德者导之善则善,导之不善则不善,所以需要上德者先觉觉后觉,先进带后进。众人只能通过“学”和“自修”来达到即性而善的目的,同时教化也显得特别重要。
唐甄又把“上德者”按照他们的“外王”功绩分为三种:上圣者就是即性而善之人,他们能凭借自己的性德、运用自己的性才于治世辅助明君,使得“上下和易,老幼饱暖,养生送死无憾”[10]12。上圣者于乱世不仅可以“定乱除暴安百姓”[10]6,还能引导“中德之人”向善,让他们做到“见利思义”,可以“善污世”,可以“化狙为良,柔雄为雌,而天下可定”[10]11,这些外在之“用”,是“儒之为贵者”[10]12。 次圣者只能保全自己于“污世”,只能“动于遇而善”,这些人若“得君就功”,也能“匡世治民”,但是也会“暴白藏墨,使民形牿情散”[10]25,但天下只能“小治”不能“大治”。 而再下之的就只能避世了,唐甄认为“凡物之生,必有其用”,“贤而不致于用,吾见其不瓦砾若也”[10]128,所以唐甄认为贤者若要避世,是没有明君而不能见用,是不得已而为之。若有明君,贤者还要隐于山林的话就是“视民如蛙鳖”[10]128,就十分的不应该了。
(二)五伦观
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早在孔子时期,夫妇关系并没有列入五伦。《中庸》中将五伦视为“天下之达道”,顺序是: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孟子将父子关系置于五伦关系之首,认为“事亲,事之本也”,“亲亲,仁也”。到了荀子,又将五伦关系排序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君臣关系排在了首位,夫妇关系排了兄弟关系之后。而荀子的五伦关系排位一直被后来儒家学者所沿用。
唐甄对五伦关系的重新阐释,首先表现在重新设置五伦的关系以及调整其顺序:“昔者高子常问于我矣,曰:‘君父之重,人皆知矣。若兄弟、若妻、若子,平居奉之,及难免之,其后先轻重若何也?’曰:‘昔也吾尝慎思之矣,差之为五等:一曰君、父母,次二曰兄弟,次三曰妻,次四曰子、兄弟之子,次五曰朋友。子权之焉!”[10]105从唐甄慎重考虑后调整的五伦关系的次序,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出现了“母亲”,“母亲”还和君主、父亲一同被排在了第一位;“妻”的重要性被排在了第三位,排在“子”以及家族“兄弟之子”的前面,而原来的夫妇一伦是排在父子、兄弟关系之后的。通过这种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唐甄对女性地位提高的愿望,期冀君臣、男女之间能够平等相待、相互尊重。
不仅如此,唐甄在《潜书·明悌》篇中明确提出重新阐释、重构传统五伦关系。“明悌”就是申明悌道。唐甄认为五伦中的“兄弟”一伦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悌”不能为世人博取“显名”。世人好名,“忠”的名声容易显、大,所以世人只讲“忠”,少言“孝”,不言“悌”:“人莫为之,亦莫言之。梯道之绝也,盖已久于斯焉矣!”[10]104但是五伦中“兄弟”关系又十分重要:“江汉源而海委,孝悌源而忠委。”[10]104孟子称赞孝道可以解忧:“美色、富贵不足解忧,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4]303而唐甄认为“兄弟”才可以解忧:“美色、富贵不足解忧,惟顺于兄弟可以解忧。”[10]105所以唐甄要重新建立“悌道”。悌道的最高标准是“杀之而不怨”,这个本来是事君、事父之道,但唐甄认为也应推之而及兄弟之间的“悌”道:“昔者象欲杀舜,舜则富贵之。富贵奚足云乎?象忧舜亦忧,象喜舜亦喜。是道也,舜事瞽瞍之道也,人所难能也。舜则施之于弟,且施之杀己之弟”[10]105,兄弟之间应该同忧同喜,守望相助,兄弟相处最高境界就是“杀之而不怨”,如舜对象,即便象要杀舜,但是舜对象不怨不恨依然“富贵之”。
唐甄还把“悌”扩大到了姊妹之间。他批评世人“姊妹既嫁,蔑焉忘之”,而孔子及其弟子的做法是:“昔者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子曰:‘奚为弗除也?’曰:‘吾鲜兄弟而弗忍除也。’夫子亦尝有姊之丧矣,与弟子立而拱尚右也,弟子不知其故,子曰:‘我尚右者,以我有姊之丧也。’由斯观之,可知悌矣。”[10]106唐甄极力将“不忍人之心”推用到姊妹关系上,姊妹与兄弟一样都是手足之亲,人们对手足之丧的悲戚、不舍的情怀是一样的,故“悌道”同样适用于姊妹之间,对于家里的姊妹同样要恭敬友善、相爱相助。这是对儒家原有“悌道”的突破,从中可以看出唐甄提倡的男女平等的思想。
唐甄还用“天地之道故平”的天道观阐释“君臣”与“夫妇”两伦的关系,主张君臣之间有权利、有责任,而丈夫对妻子、对家庭同样有责任,反对君尊臣卑、夫尊妇卑。
“君臣”关系中,唐甄认为天道强调“平等”,君臣间也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况且君主也是人,而人与人是一样的,“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皆人也”[10]94,“人我一情,本无众异”[10]28,故君臣之间应该是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然而,现实中君臣关系却日益异化,君的地位越来越高以至于不再履行其在家庭、朝廷中的责任:“为上易骄,为下易谀,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是以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之不类于我”[10]94,久而久之君主之尊“如在天上”,如“土神”,不仅君主与自己的父母妻子之间都是“朝见有时”“进御有时”,臣对君更是战战兢兢,跪拜应对,不敢仰视。君主在家中不尽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骨肉之间,骄亢袭成”[10]94,结果就会“馋人间之,废嗣废后,易于反掌,不和于家,乱之本也”[10]94;君主在朝中不尽责任就会导致“大权下移”,权臣嬖侍弄权亡国。君主一定要通过“近人”“与民同情”的方法来“抑尊”,在家里将自己看作与普通人一样有孝父母、亲妻子、慈爱幼儿的责任,在朝中平等对待自己的臣子。
君臣平等体现在君与臣都有各自享有各自的权利,也各自须得尽到自己的责任。臣尽己奉君,恪尽职守;君也要以礼待臣,谦逊处下,体恤臣民。唐甄尤其强调重视君主尽到自己的责任,以此来调节君臣关系,期待建立君臣对等权利和义务关系,改进君臣相处模式,更好地治理国家,为民谋利。一个明德之君的责任包括“以天下为身”,爱惜天下犹如爱惜自己的生命:“以为我实民之父母,民实我之男女,惟恐其衣食不足,居处不安,日夜念之不忘。”[10]259唯能如此,君子才能牧养天下子民,让他们安居乐业。明德之君生活上应崇尚朴素:“卑前殿,陋后宫,布衣蔬食,陶器素舆”[10]259,要“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10]143,唯能如此,君主才能寡欲浚心,不横征暴敛,对百姓不过分“虐取”,让他们可以修生养息;明德之君还须以礼待臣,用贤臣、畏“直臣”、擅“处下”。贤臣为君主之股肱,帮君主治天下;直臣有如良医,直臣之言有如良药,可以时刻纠正君主的行为;而君主擅“处下”,天下之善则能归之,反而成就了君主之“尊”,若君傲慢,不能下于臣,则为“君亢”。“君亢,则臣不竭忠,民不爱上。”[10]107若君能明德,臣能尽忠,那么君臣同心,治世可期。
在传统五伦中的“夫妇”一伦关系中,唐甄特别强调改善女性的地位,反对男尊女卑,他从男女平等的角度提出“备孝”,即完备孝道。他不满儒家伦理语境中的“孝”仅适用于父系家长,他认为此行为准则亦适用于母系家长。
首先,从“本”上说,从人类的来源来说,女子在人类社会繁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女子出嫁“为人母,于是乃有父子焉,乃有君臣焉”[10]107,“人若无妻,子孙何以出?家何以成?帑则熟寄?居则孰铺?出则孰守? ”[10]107其次,从“言乎其所生”的角度来说“男女,一也;男之子,女之子,亦一也”[10]102,男性女性都是生命,是同等重要的。再次,女性对家庭、社会的贡献不亚于男性。女子少时貌好,嫁人后“执蚕绩、功针缕、治酒醴、调燔炙”,年老后“长子孙、训妇女”[10]105。基于此,唐甄批判了当时礼制和服制上对女性的歧视,认为女子在家与出嫁都应该一视同仁,对待本姓长辈与外姓长辈都要同等重视与尊重:“父之父母,母之父母,亦一也……女子在室于父母,出嫁于父母,岂有异乎?”[10]103因为父母之恩对于女子来说一样的厚重,“恩不以服薄”。他还强调“父母一也”“男女一也”其实也是孔子的教诲:“及读《春秋》书杞伯姬来朝其子,其斯义夫?盖妇人归宁,细事也;孺子无知,手挈之而来,尤细事也。于来可勿书,况其子乎?惟诸侯来,曰朝。朝,大礼也,以加诸孺子,重其义也。仲尼欲教天下之人,爱其母之所从出如祖父母,爱其女所出如其孙,故特起朝子之文以见义也。”[10]102“及读《春秋》书纪季姜归于京师,其斯义也夫?夫诸侯且不称字矣,王后之尊,同于天子,乃称字乎?称字,所以申父母之尊也。父母之尊,不降于天子,岂降于舅姑?仲尼恐为人妇者习焉而忘其情,尊舅姑、降父母,近舅姑、远父母,亲舅姑、疏父母,故特起王后称字之文以见义也。”[10]103唐甄从《春秋》中孔子用“朝”杞伯姬携子的“归宁”以及对周恒王王后称其“字”的做法来说明孔子对出嫁女子、以及外姓长辈是一样尊敬的,因为“朝”是用形容“诸侯”的朝见,而“称字”是天子才有的待遇。
正是有了“男女一也”的意识,所以在夫妇关系上唐甄强调男女平等,他对当时女性是十分同情的,明确声称他“尤恤女”:“君不善于臣,臣犹得免焉;父不善于子,子犹得免焉;主不善于仆,仆犹得免焉。至于妻,无所逃之矣。”[10]108他批评世人家庭生活中不公正对待自己的妻子,认为世人爱其妻“甚下于其兄弟”,这些人平时多“好交好游,或月不归,或岁不归,或屡岁不归。归则出之日多,入之日少,入则朋来之时多,见妻之时少……欢于友而愠于妻,逆意于外而作色于内”[10]110,“入室而逞于妻”,“暴其妻,屈于外而威于内,忍于仆而逞于内,以妻为迁怒之地”[10]107,久而久之夫妇之间如仇人一般,毁了夫妇这一伦关系。
唐甄认为夫妇关系中,“夫”对待妻子的态度和处理事情的方法至关重要。首先,唐甄认为夫妇之道就是“相下之道”,“夫之下于妻者,德也”[10]107。 如果“夫”没有这个德性就是“夫亢”,会引起“门内不和,家道不成”[10]107,而“不和于家,乱之本也”,最终家必丧。其次,唐甄还提出夫妇之道在于“平”和“恕”。唐甄从天道出发,认为天之生物有厚有薄,而君子要做到“嘉美而矜恶”来平之。而“恕”则是君子处世的“大枢”,五伦关系、百姓相处都是以“恕”为基础。“行恕”首先开始于夫妻之间,恕于妻才能推而恕于人。若妻都不能恕,而能恕于人,一定是因为利益关系相互讨好巴结而已,不是真的能“恕于人”。最后,唐甄认为夫妇之间还应该是言语上“敬且和”,世人应该做到妻忧我亦忧,妻喜我亦喜,这样才能做到尽夫妇之伦。
朋友一伦是儒家五伦关系中的横向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交友的原则,例如交友要志同道合,“毋友不如己者”,还有就是要友直、友谅、友多闻、友可以辅仁。而友偏辟、友善柔、友便佞则是有损自己德行的。
唐甄的交友的观点更多是从生活窘迫的底层士人角度,讨论取友、交友之道。他在这一伦的关系中仍然提倡“平恕”之道。“平”,就是要平等待人,朋友之间无论穷、达,人格上是平等的。平常朋友之间难免有施受之举,君子“惠人”时,首先要注意态度上不能轻慢,要舍弃“骄吝”,不能“共揖不失,其睹若无;问答不失,其语若忘”[10]113。朋友之道,还有赖于“恕”,唐甄提出朋友之交当学会“异位而处”,推己及人,“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10]112,取友要“不僭不贼,鲜不为则”。
综上,唐甄五伦观不仅改变了之前五伦排列的顺序,把父母提高到同君同等的地位、把悌道也在排序中做了提升,更是对悌道的内容做了补充,把“悌”道由兄弟之间的行为准则扩大到了姊妹之间。唐甄还用“平恕”之道重新阐释“君臣”“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君”应该“抑尊”处下、“与民同情”才能建立健康的君臣关系,这是君的责任。而夫妇之道在于“夫”能够“下于妻”“恤女”,最后丈夫做到对妻子“忧其所忧,喜其所喜”。朋友一伦中,唐甄主张“异位而处”,救朋友之急时要注意“惠之不慢”,平等待人。可以看出唐甄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责任十分重要。
(三)义利之辨
儒家传统的义利观中的“义”“利”之别泾渭分明,“义”往往与“利”对举。而在唐甄的“义”和“利”不再是截然二分的两个对立面。唐甄《潜书·食难》篇中有客人从“义利之辨”角度,问唐甄为何从事牙商:“吾尝闻先生与人言学,内制心,外制行,先明义利之辨,此吾所心服者。民之为道,士为贵,农次之,惟贾为下。贾为下者,为其为利也。是故君子不言货币,不问赢绌。一涉于此,谓之贾风,必深耻之。夫贾为下,牙为尤下,先生为之,无乃近于利乎?”[10]120这段文字其实就是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的观点,客人讥笑他作为一个读圣贤书、中过举人、在朝廷当过官的人,却为了蝇头小利沦落市井为牙商。唐甄通过反驳这个观点阐明了他自己的义利观。
首先,唐甄将“道”引入义利之辨,他说:“万物之生,毕生皆利,没而后已,莫能穷之者。若或穷之,非生道矣。”[10]75万物生生不息的过程就是利己、利他的过程,这是万物之“生”道。道如此,人也不例外,人的出生以及后来在社会上从事的各行各业都是既利己又利他的,人的本性中就包含有“为利”之属性,人类出于本能为了生存、发展就必须做有“利”己的事情,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利”的因素是人类社会最初的发展动力。所以,为了自己和家人能更好地生存而去“谋利”,看上去是“利”实则是“义”:“天下岂有无故而可以死者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所以成义也,生为重矣。今欲假布粟于亲戚而不可得,假束稿于邻里而不可得,或得担粟于朋友而不可为常。一旦无米无稿,不能出户,岂有款门而救之者!吾虽不贵、不高、不贤,亦父母之身也,其不可以饿死也明矣。今者贾客满堂,酒脯在厨,日得微利以活家人,妻奴相保,居于市廛,日食不匮,此救死也。”[10]119
唐甄从尊重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肯定生命的可贵。伯夷叔齐之不食周粟之“义”一直为儒家学者所称颂。但是,像唐甄这样境遇窘迫、求借无门的时候,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不得不从事“低贱”的职业养活家人,让他们免遭饿死之命运,守护生命的尊严就是“义”。这是唐甄对儒家之核心概念“义”的新解读。所以他感叹“天下岂有无故可以死者哉!”世人须得辨明“生”和“所以生”,“死”和“其所不死”。以道谋财,进而“存身”“养身”并不是耻辱的事情:“苟非仕而得禄,及公卿敬礼而周之,其下耕贾而得之,则财无可求之道,求之必谓小人之为矣。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10]125君子求财之道无非有三:俸禄、公卿周济、耕贾辛劳所得。在市为贾虽为“下”,但仍然是取财之道。这种尊重生命、不因职业的“低贱”而辱没生命的做法就是“义”。
他提出百姓“衣食足”、安居乐业是“礼义廉耻”之基础,也是社会最终之“利”。以“富民”“养民”为目的政事措施都可以看作“义”。“尧舜”之治不在于其“德治”而在于其“耕耨桑蚕”“鸡豚狗彘”上,让百姓生活富足是德行教化可以施行的前提条件:“衣食足而知廉耻,廉耻而尚礼义,而治化大行矣”[10]259,“节之立不立,由于食之足不足。食之于人,岂不重乎”[10]125,“尧舜之治无他,耕耨是也,桑蚕是也,鸡豚狗彘是也。百姓既是,不思犯乱,而后风化可施,赏罚可行”[10]14。庶民百姓只有丰衣足食了,才会老有所依,幼有所养,才不会犯上作乱引起社会动荡,百姓们“养生丧死无憾”才能够进一步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社会才能大治,从这个角度义利不是对立的,个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是同构的,是相互成就的。
(四)理欲之分
明末清初之际社会的巨变、经济的发展、西学的介绍都使得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道德观根基发生了动摇,一批思想家开始对“人欲”的合理性加以肯定并进行论证,唐甄也是其中之一。
唐甄的理欲观中,“欲”有“天下之欲”和“个人之欲”之分,前者唐甄又称之为“众欲”,就是指一郡一邑甚至天下百姓“之言”“之智”(即一方百姓所共同主张、欲望),唐甄认为为政者要善于“从人”,听从一方百姓之所“欲”,以“天下之欲行事,何事不达! ”[10]195唐甄的“众欲”与王夫之的“公欲”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认为百姓们共同期望的就是合理的,故“众欲不可拂也”[10]195。
唐甄将个人私欲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随着人的血气之身而自然产生的生存欲望,以及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情绪,是人的本能,例如,蔬食之士闻馨,自然会慕鼎肉;徒步之士见高车,自然会感于累而心生羡慕之情;遇威,自然心生畏惧;遇侮,自然心生愤怒:“轻富贵,安贫贱,勿易言也。果能若此,此为圣之基也。人皆曰‘我轻富贵,我安贫贱’,皆自欺也,即非自欺,不必其不动也,蔬食之士,不慕鼎肉,不能闻馨而不动于嗜;徒步之士,不慕高车,不能见乘而不感于劳。故夫不慕富贵者则有之矣,见富贵而不动者,吾未之见也。威不惧,侮不怒,尤未易言也。当义不辟死,当辱不与校,固有之矣。遇威、侮而不变于色、不动于心者,吾未之见也。布与缎同暖,菜与肉同饱。暖必缎,为人也;饱必肉,从嗜也。 ”[10]78这个层次的欲望主要是为了“养身”“存身”。
第二个层次的“欲望”,唐甄称之为“奢欲”,是指人若过于沉溺第一个层次的自然欲望而导致心的放逸,就会不择手段地求显身、尊身和肥身。第一个层次的“欲”是人为了能够生存自然而起之欲,但是若听任这种气血之欲膨胀、发展就会滞于物,成为嗜欲。“奢欲”才有对治的必要。对“嗜欲”加以对治才能达到“见富贵而不慕、遇威侮而不动心”的境界,进而才能舍身而取义,是圣人之基。
唐甄认为第一个层次的“私欲”是合天理的,因为人有“身”。“身”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第一必要条件。丰衣足食是君子求道、守节等德性追求的首要条件,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养其体气,固其寿命,是力学、修身、建业之所先也”[10]246,“夫荆士、骆子之不能守其节者,食不足也。殷子之能守其节者,食足也。节之立不立,由于食之足不足”[10]125。“冻饿逼矣,不可以言礼;考妣馁矣,不可以言孝;先泽斩矣,不可以言传。于斯讲学,何学可讲?于斯进德,何德可进?必使不陷于死、不绝于先、有继于后,此三者,正所以讲学也,正所以进德也。 ”[10]116在唐甄看来“力学”“修身”“建业”“言礼”“言孝”等种种社会行为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个体“身之所存”。
君子之“身”不仅对自己很重要,对家人、国家也重要。君子爱惜己身,义激气愤、解带自觉、暴虎冯河等使自己生命陷于险地之事不是君子所为。对家庭,君子要用正当的手段去谋食,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富足的生活。只有家庭富足,才能祭祀祖先使“不绝于先”,才能抚育后代使“有继于后”,这本身就是“为学进德”。基于此,唐甄认为他自己为了“存身”在市井中为贾就不是辱身,真正的辱身是不择手段求显身、尊身和肥身。对国家,唐甄抨击了明末腐儒们“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作风。唐甄提出君子应该惜命,有四不死:“权奸擅命,天子敛手,欲救而逆之,如冶炉燎羽耳,当是之时,君子不死;朋党相訾,有伏戎焉,自贤而非人,自白而浊人,祸不移影,当是之时,君子不死也;兴废用舍,非所以安危者则不争,抗言争之,或以激怒,当是之时,君子不死也;大命既倾,人不能支,君死矣,国亡矣,非其股肱之佐、守疆之重臣,而委身殉之,则过矣,当是之时,君子不死也”[10]247,权奸当道,天子昏庸,君子若犯言直谏,甚至以死报国实则是自轻自贱的行为。“君子之道,先爱其身,不立乱朝,不事暗君。屈身以从小人,固可丑也;杀身以殉小人,亦自轻也。是故义有所不立,勇有所不为,忠有所不致。《诗》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言有所待也,君子爱身之谓也。”[10]72但是唐甄却认为有三种情况,君子殉身报国就是“大义”:第一殉身可以定大乱;第二殉身可以使国存;第三殉身可以使君安,这时候君子应该毫不犹豫地“舍生取义”,是谓死得其所。
所以,对于“欲望”,唐甄主张须“得其正而安之,不得其正则弃之,是为君子。得其正而溺之,不得其正而强遂之,是为鄙夫。人所欲者,食、色、衣、处是也”[10]130,唐甄反对把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起来,他批判禁欲。所谓“正”就是符合天理,符合天理之人欲才是可以追求的,人类通过正当手段改善自己基本的生活条件、状况是无可厚非的,是与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之“大利”一致的,得欲之正,才能安之。而所谓“安之”就是以正当手段实现自己的欲望,不损害他人和社会整体利益,否则即便是“羊豕之味”也是“豢我”,“貂狐之衣”也是“束我”,使我蒙羞而已。感物而动的“欲”如果不加节制就是“不得其正”,唐甄肯定人内在之五情“思、气、味、饮、色”是本在的,但是不能过度,过则有疾,过度纵欲溺心坑命、害身,“思淫心疾,气淫肝疾,味淫脾疾,饮淫肺疾,色淫肾疾。此五者,内自贼者也”[10]257,危害极大,世人不得不警惕。
三、唐甄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出挖掘、阐发、赋予、运用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价值,以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为全世界的华人找到共同的“精神家园”。诚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为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伦理”即为我国传统文化其较显著的特征也是其核心内容[11]31。重新审视、研究、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思想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学者们重要的任务。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严辨义利和理欲,这些思想资源对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都有重要的意义。唐甄是明末清初儒家思想家,这一时期思想家们亲历王朝更迭,目睹王学之流弊,在社会巨变的背景下,清初儒家学者们对前朝的心性学开始反思,纷纷对宋明理学提出新的阐释,唐甄也是如此。
唐甄伦理思想人性论中坚持了“性三品”论的观点,将人分为上德者、中德者和凶德者三类,认为上德者应该多多树立事功以“除暴安百姓”并积极导人向善。中下德之人可以通过受教育、勤学习来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慢慢成长为有德新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唐甄提倡平等、责任以及推己及人等原则。唐甄认为君臣之间、夫妇、朋友之间应该平等相处。君臣、夫妇相互之间既有权利也有责任,君主要以“天下为身”,爱惜自己的子民,不能铺张浪费,要以礼待臣,谦逊处下;男子在家庭生活中要平等对待自己的妻子,言语要和气,还要以道谋财,养活家人,而家里的子嗣无论男女都应该有平等的待遇。义利、理欲之辨中,唐甄对百姓为了富足的生活而逐利的行为,持肯定的态度,并且认为只有人人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德行教化才成为可能,但是他反对过分逐利,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危害社会整体利益,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牺牲个人生命报效国家。唐甄反对过度的“奢欲”,奉行俭朴。所有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人际关系的建设,以及如何处理个人私欲与国家集体利益的关系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然,唐甄的思想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只要我们能紧随时代的步伐,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可以去其糟粕,取其精髓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