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维亚·乔迈银幕动画:法国动画电影的现实指涉与人文蕴藉
20世纪80年代后,以“沃尔特·迪斯尼动画工作室(Walt Disney Animation Studios)”为代表的美国动画电影,集巨大的人力物力,一部部兼具商业性和娱乐性的动画电影接连问世,在主流电影界最受追捧。以“吉卜力工作室”为代表的日本动画电影老少咸宜,牢牢锁定着亚太市场。相比之下,西欧动画电影则显得黯然失色。实际上,西欧动画电影不仅起步早,艺术性上也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其中以法国最具代表性。
“现代动画之父”——法国人埃米尔·科尔于1906年首次运用摄影停格技术拍摄了动画短片《幻影集》,拉开了法国动画电影的序幕。在这之后,法国动画电影一发不可收拾,尤其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动漫产业发展的浪潮下,法国动画电影进入了新的黄金时期,即使是在金融危机较为严重的2008年,仍达到了1.52亿欧元的产值,位列世界三大动画大国。自《青蛙的预言》(2003)问世后,几乎每年都有影片获得主流电影奖提名,其中由西维亚·乔迈担任导演的两部作品——《疯狂约会美丽都》(2003)和《魔术师》(2009)最具特色。
西维亚·乔迈(Sylvain Chom)是法国电影导演、演员,1963年出生,青年时期系统学习了漫画和剧本创作。在充分的前期积累下,1998年开始从事动画电影创作。乔迈是典型的厚积薄发型的导演,20年间只创作了《老妇与鸽》《疯狂约会美丽都》和《魔术师》3部影片,每一部都技惊四座,收获了奥斯卡、凯撒奖和安妮奖等国际大奖的提名或授奖。西维亚·乔迈的成功既是自身努力的结果,也离不开法国动画电影长期以来的熏染。在《疯狂约会美丽都》和《魔术师》两部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法国动画电影一贯的平民视角和人文关怀。
一、西维亚·乔迈动画电影的平民情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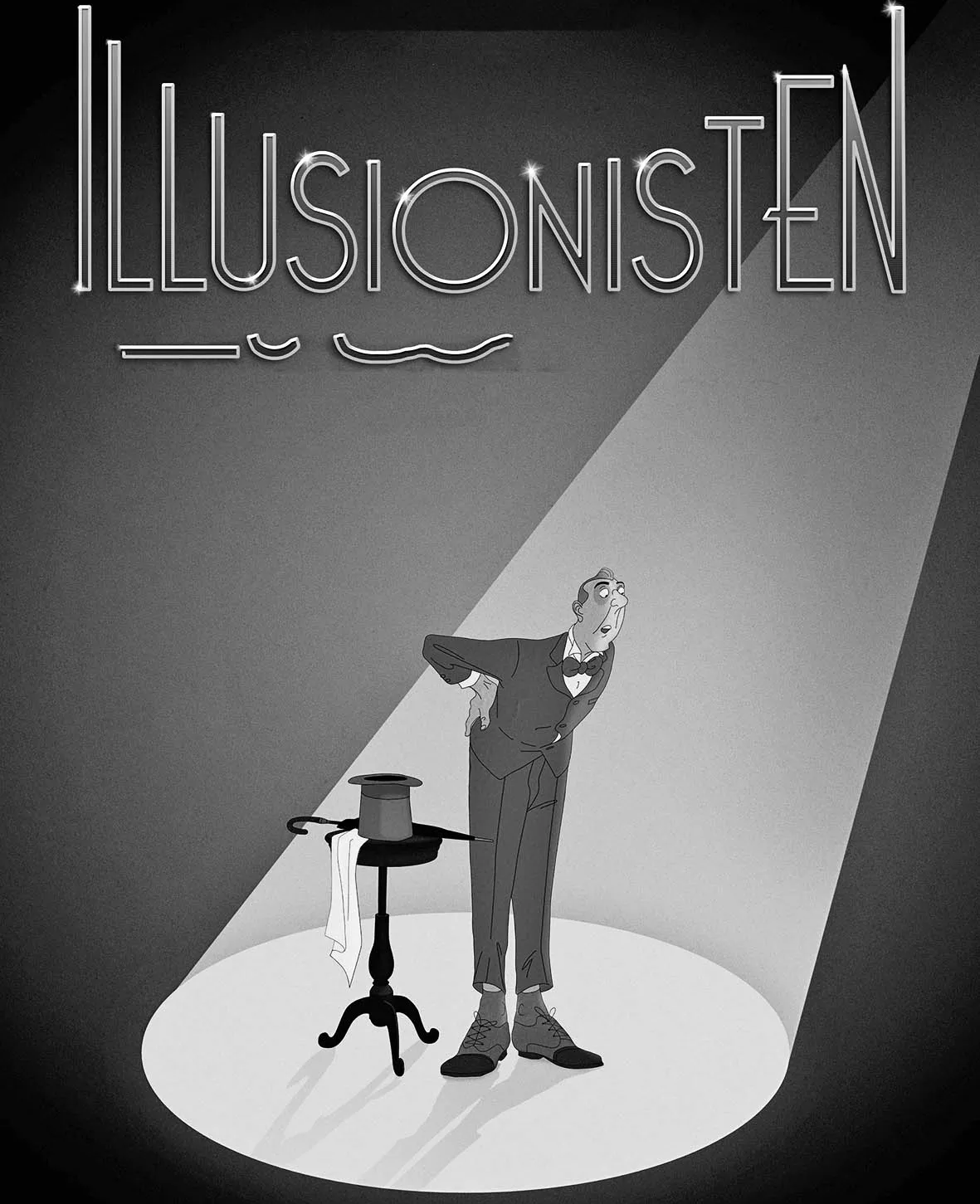
动画电影《魔术师》海报
迪士尼动画电影一向营造一个美丽的梦幻世界,宣扬英雄主义和梦想,每一部电影都是主人公的成长史。白雪公主、长发公主等近二十位自带公主光环的女主角自不必说,梅莉达(Merida)、木兰、贝儿(Belle)、安娜(Anna)等出身平凡的女性,其人生经历也带有传奇色彩。总而言之,在英雄主义和梦想的旗帜下,电影中的人物和故事严重脱离了现实。法国电影却与此相反,对平民的关注是法国电影历来的传统,来自真实的生活的平民小人物是大银幕的主角,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真实自然、亲切生动。这种平民化传统使得法国电影呈现出一种与现实的贴合感,充满生活的黏性与质感。这里,既包含对小人物的生活化的刻画,又囊括了对小人物的褒贬,寄寓着创作者对人性、对美丑的价值认同或批判,这是完全不同于好莱坞式的英雄大片中二元对立模式的一种影像传达。
乔迈的影片即以普通平民为主,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形象饱满的小人物。与此同时,乔迈又是个漫画家,他将原本扁平化的角色的性格同形象一起进行了夸大、突出,赋予平凡角色以饱满的性格,充满了幽默感。这些小人物身上既有值得褒扬的优点,也有着难以修缮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缺点,人物显得圆融立体,令观者常能联想起身边的某一些人。《疯狂约会美丽都》的主人公均来自社会底层:小男孩查宾自幼父母双亡,而且有自闭症,和他相依为命的奶奶身体残疾行动不便,他的狗布鲁诺则是不至从何处捡来的流浪狗。另一方面,成年后的查宾是一个双腿粗壮、腰腹纤细的“螳螂相”人物;奶奶戴着昏黄的眼镜,身材矮小且是长短脚,但聪明能干、性格坚毅,对孙子充满关爱;布鲁诺也始终对主人不离不弃。当观众的视角随着奶奶转移到美丽都(Hollyfood,影射好莱坞)时,发现这里的人扭着因过度肥胖而显得畸形夸张的身体;黑帮打手身材高大、黑色装扮,像是移动的扑克牌;还有尖酸刻薄的汉堡店女招待、奴颜婢膝的餐厅服务员等等,这些简化的形象取材于现实生活,但个性鲜明,甚至带有社会符号化特征,能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魔术师》则直接取材于20世纪初法国导演雅克·塔蒂,作为喜剧大师的塔蒂曾有一个私生女,二人素未谋面,被弃少女童年在孤儿院抚养长大,成年后曾尝试与已成名的父亲保持少量通信往来。为保护父亲的声誉,女儿一直未公开自己的身份,但塔蒂深埋于心的愧疚却时时不能消散。心怀负罪感的塔蒂借此创作了《魔术师》的故事。2010年,西维亚·乔迈在偶然得到剧本,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于是,以此为蓝本,将其拍摄成一部淡淡的、苦涩的动画电影。在影片中,雅克·塔蒂不再是大师,而是一个落魄的老年魔术师,私生女变成了一个可怜、单纯的小姑娘,所有的故事就在这些普通人中间展开。
从平民视角出发,自然不会有那些拯救世界的大英雄以及“公主和王子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这种程式化的圆满结局。西维亚·乔迈关注平民的同时,对浸泡在物质文化下的粗鄙与浮躁进行了反省和批判。这一创作视角来源于导演乔迈对现实主义原则的遵循。在动画电影的具体表达上,乔迈从视听表现、人物塑造、环境描写等各个角度进行精雕细琢,力图能丰富动画的表达主题与表现形式。
《疯狂约会美丽都》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残缺的家庭,这种残酷的现实较之迪士尼的“公主系列”,更接近其实生活本身,其中的“美丽都”影射的就是以好莱坞为标志的现代美国。在西维亚·乔迈的镜头里,美国文化并不值得崇拜,它缺乏人情味、黑手党盛行,当查宾的奶奶远涉重洋来到美丽都时,码头上有一尊自由女神像,只见雕像奇胖无比,不是手举火炬的形象,而是一手托着汉堡包,一手高擎冰淇淋;美丽都的富人们体态臃肿,而被贵妇人们当赚钱工具的男人们精瘦无比,这种巨大的差异暗合了现今美国社会审美畸形、唯钱是问的现实。《魔术师》中的老年魔术师为求生存,如同丧家之犬一般辗转于各地,在遇到纯真的小姑娘时,生活仿佛有了一丝慰藉,但当小姑娘长大成人后,那种被抛弃的感觉再一次向老魔术师袭来,最终他仍然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就像现实社会中的许多孤独的老年人一样。
在商业动画居主导地位的形势下,西维亚·乔迈关注小人物,关注在社会底层生活的人们,他以独特的视角使自己的影片具有鲜明的特色。
二、西维亚·乔迈动画电影中的人文关怀
著名艺术理论家弗雷德里克·透纳(Frederick J.Turner)曾指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必然要有实质内容,不论在认识上还是感情上都能给人以启迪。”其所说的“实质内容”,即是指作品的主题。毫无疑问,西维亚·乔迈的电影有着丰富的“实质内容”,他擅长于平民化的视角下,用朴素的、纯粹的故事向观众传达普遍但深刻的主题,如亲情、友情、爱情。小人物质朴而真实的情感性表达,是乔迈动画电影的一大标识。乔迈自幼由祖母抚养长大,这使得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主人公都是乐观开朗的老婆婆,每一部作品里都寄托了对无私亲情的讴歌。《疯狂约会美丽都》讲的是祖孙情,影片的故事很简单,主线就是奶奶营救自己的孙子查宾。主角苏珊凭借着对孙子的爱,让她不畏艰险,历经磨难地找到了孙子,并且将其从魔爪中解救出来。影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这种淡淡的温暖用奇特的动画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十分精道和微妙。在影片结尾,乔迈深情地打上了“献给我的父母”字样。如同其色调一样温暖,是这部影片给人最直接的审美体验。《魔术师》中老魔术师一次次的心力交瘁,只不过是不愿意看到爱丽丝的天真被残酷的现实所污染,当穷尽一切后,看到爱丽丝和她的白马王子悠闲散步,他终于放弃了魔术,独自一人踏上了漂泊的路。身为魔术师,他更像是一位父亲。现实生活中的“魔术师们”也大抵如此——从小到大,父亲为自己的孩子奉献出时间、心血,却装出轻描淡写的样子,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欲望的膨胀,父亲逐渐力不从心,面对孩子们的疑问,只有识相地选择离开,和电影中的老魔术师如出一辙。也许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神奇的“魔法”。
亲情之外,对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反思是西维亚·乔迈电影的另一主题。现代化的机械式、工业式、快餐式都是乔迈讨伐的对象。《疯狂约会美丽都》中的狗布鲁诺,因为小时候尾巴被玩具火车碾过而留下了对火车的恐惧,每当有火车或是列车经过,它都会不由自主地狂吠,以至于在梦中布鲁诺身边的查宾成了一台蒸汽机,这使得布鲁诺惊慌失措;当它乘着蒸汽机从自家窗户前经过,而在窗内则是那些列车中的乘客对着它狂吠,角色完全颠倒。美丽都中黑帮们的赌博工具,是一台类似跑步机前端加了一个屏幕的机器,查宾就这样看着眼前虚拟的景象,永无停歇地骑着自行车。这一切就像是工业化下人类丧失个性的缩影,我们沉溺于虚拟的影像,什么事情都是那么高效、快速,快得让我们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幸好,查宾对梦想的追逐和执着、奶奶的爱与勇敢,都是对这个物欲世界的反省和自救。一系列现代化的机械符号,乔迈将其与人物的情感或情绪反应相联系,彰显出了现代符号统摄下的人类生存环境的异化,是之于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侵蚀下人际关系嬗变的反思与批判。
乔迈注重向受众传达电影的主题,他从喜剧大师雅克·塔蒂的默片等传统创作中汲取灵感,用质朴的方手法来尽可能完美地体现自己的银幕构想,其电影中平民化的文化视角、细腻温暖的情感表达以及对旧时光的缅怀,令人印象深刻,带有浓郁的人文关怀。
三、法国动画电影前瞻及其启示
法国动画电影善于“用极简的方式打造了一个极动人的亲情故事,在极度抽象的画而下却蕴含养感动”。早在1979年,法国动画大师保罗·格里莫制作的《国王与小鸟》就借牧羊女和扫烟囱的小伙子与假国王之间的三角恋情纠纷,展现了下层人民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推翻强权的统治阶级统治的过程。21世纪后,兼具商业性和艺术性的作品层出不穷,《我在伊朗长大》 (又名《茉莉人生》)获2007年各大影展中大放异彩,影片讲述了伊朗一位普通的小姑娘玛嘉(Marjane)的成长经历,并贯穿着东西文化冲突。影片没有用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他国,没有将欧洲描述成梦想中的天堂,而展现了一个存在无法生存残酷现实的真实欧洲。《小王子》(2015)精准地传达出回归真我、守护人性的追求:现实世界是冰冷、灰暗的大人世界,是被权力、金钱、劳动所捆绑的社会;小王子象征着每个人本来的那颗赤子之心,在这无比复杂的社会中如何做好自己,如何不受外界邪恶事物的影响,内心的小王子起着关键作用。此后,诸如《西葫芦的生活》(2016)和《了不起的菲丽西》(2017)等则把目光投向孤儿院里的孩子们,展现其追逐亲情、友情和梦想的坎坷历程。放眼未来,对平凡人物的刻画和对人间温情的展现,将一直是法国动画电影的主流和特色。
法国动画电影的成功,在某些方面于中国的动画电影有重要的的借鉴意义。首先,要善于挖掘本民族的文化宝藏,而不是一味奉行“拿来主义”。中国动画电影在很长一段时期被国人亲切地称为“美术片”,1949年以后的中国动画,代表性的作品如《大闹天宫》《天书奇谭》《牧笛》《山水情》《南郭先生》等等,在内容上均以传统的中国文化题材为基础,大多取材于古代传说和文学经典中与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如孝悌、友爱、坚韧不拔等相契合的内容,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具有极高的标识度,因此获得了极高的荣誉。20世纪90年代至今,大量国外动画系列剧和连续剧的引入,中国动画开始尝试与国际接轨,这一时期的中国动画题材更加多元化,但精品佳作始终不多。如今,我们强调“文化自信”,电影创作也应有自信!“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能真正通向文化自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构建的丰富而强大的文化是中国动画电影可以去汲取、去深挖、去重构的丰厚养料,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的动画电影只有在基于民族文化个性的基础上,才能为赢得世界的瞩目打开大门。也就是说,只有重视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使用,中国动画电影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世界影坛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主题的浅薄也是中国动画电影缺乏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中国动画电影大多过分重视作品的单一功能而忽略作品的综合表现力,电影表达的主题缺乏普遍性和深刻性。而今作为观影主力军的年轻观众,他们思维活跃、好奇心强,重视说教、主题浅薄的作品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观影需求,他们更多地希望能看到一些贴近自己生活、反映他们思想情趣的动画“新”故事。因此,中国动画电影应从根本创作上转型,以制作主题鲜明、老少咸宜的作品为目标,发展自己的“国民动画”。此外,“一个好的电影作品是一个作者风格昭著的作品,作品艺术性的衡量标准即是作品中作者个人风格化的程度”。动画电影导演应该形成自己的风格,无论是语言、形式还是叙事。观照西维亚·乔迈的动画电影可以发现,他的电影表达已形成了个人特色,如在视觉表达上,乔迈往往采用复古式的影像,从而能唤起观众的怀旧情怀;在听觉表达上,乔迈并不倾注于丰富的台词,反而是减少了人物对白,有一种默片式的效果,但其间强化的人物表演以及适当的音效或音乐,却能够使观众充分地感受到人物的内心情感或情绪波动,叙事与抒情并不因对白的少量而减色。乔迈这种有意留白的表达方式,反而使观者更注重画面和演员的表演,加大了影像表达与观众感受之间的张力。这无疑是一种乔迈式的个性表达。中国动画电影若能从以上三方面加以完善,即丰富的民族性塑造、深刻多元的主题挖掘、个体化风格的突显,只有这三者实现恰切的融合,才有可能跻身于世界动画电影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