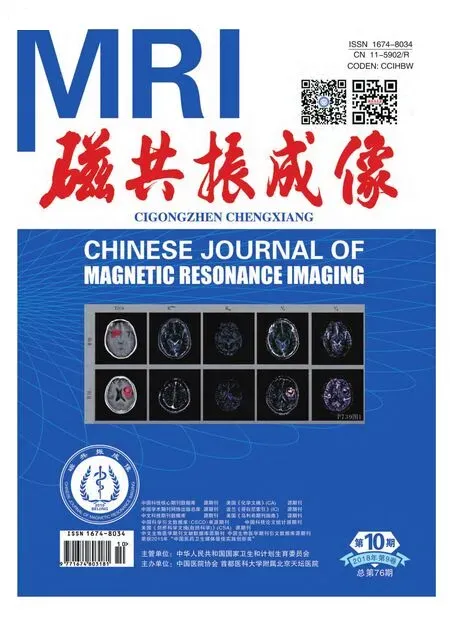脑胶质瘤MRI影像基因组学研究进展
王佳,胡粟,胡春洪
脑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最常见的原发性肿瘤,约占所有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27%,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的80%[1]。近年来,肿瘤诊断正从组织学层面转向分子遗传学层面。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分级标准修改版[2]仍将脑胶质瘤分为Ⅰ~Ⅳ级,但首次将基因型纳入脑肿瘤的诊断中,并根据分子特征对肿瘤进行分型,如异柠檬酸脱氢酶基因(isocitrate dehydrogenase,IDH)突变状态将组织学上相似的弥漫性胶质瘤划分为基因和临床表现上截然不同的亚型,伴IDH野生型肿瘤更具有侵袭性和基因异质性,无论其WHO等级如何。TP53和1p/19q状态在IDH突变型星形细胞瘤和少突细胞瘤中的意义也逐渐获得认可[3]。这都改变了长久以来基于光镜的组织学分类准则,增加了临床诊断的客观性,对指导个体化治疗和预后评价具有重大意义。
相较于组织学分类,基因可能是与治疗和预后相关的一些分子标志物改变的更为关键的预测因子。一些分子遗传学标志物(包括IDH1/2突变、TP53突变、MGMT启动子甲基化、1p/19q共缺失等)在肿瘤发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不断涌现的磁共振成像和图像分析技术,不仅提供了非侵袭性的诊断和评估肿瘤的方法,并且提供了实验室检查无法得到的瘤周区域特征以及瘤体内部的基因异质性[4-5],从而让临床工作者获得更为全面的肿瘤信息。本文将从几种常见的胶质瘤基因分子标志物方面就胶质瘤影像基因组学研究进展予以综述。
1 MRI成像评估IDH基因突变
IDH基因突变是胶质瘤发生过程中的早期事件,由Parons等[6]于2008年首先报道,主要发生在低级别胶质瘤和继发性胶质母细胞瘤中。后续研究发现,IDH突变型胶质瘤患者的预后明显好于野生型患者,提示IDH基因突变对胶质瘤患者诊断及预后有重要的临床预测价值[7]。IDH1基因突变使IDH与底物结合能力下降,突变型IDH1与野生型竞争底物形成二聚体造成α-KG含量下降,细胞缺氧诱导因子(hypoxia-mducible factor,HIF)稳定性增加,HIF信号通路激活,最终导致肿瘤的发生。
有文献报道了磁共振解剖成像对不同IDH基因型胶质瘤生长特点的分析。Qi等[8]发现IDH突变型胶质瘤患者生存期的延长主要是与肿瘤的位置和MRI特征所对应的低度侵袭性的生物学行为有关。突变型肿瘤在常规MRI上主要位于一侧脑叶,如额叶、颞叶或者小脑,而极少位于间脑或脑干,并且更倾向于单侧生长,边缘清晰锐利,密度均一,增强几乎无强化。
目前,国内外对于IDH1基因的非侵袭性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建立在IDH1基因突变可使三羧酸循环中间物α-酮戊二酸(α-ketoglutarate,α-KG)转变为2-羟基戊二酸(2-hydroxyglutarate,2-HG)的理论基础上的。由于IDH1基因突变造成的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NADPH)依赖性还原反应被催化,使得α-KG 变成2-HG。肿瘤细胞内过量2-HG累积的影响尚不完全明确,但众多研究者的成果表明,2-HG在改变IDH突变型肿瘤的基因及代谢图谱进而促使细胞增殖和恶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IDH突变型胶质瘤内2-HG浓度范围为5~35 mmol/L,而在体磁共振波谱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MRS)检测代谢物的灵敏度阈值约为1 mmol/L,并且在正常脑组织中不存在2-HG浓度背景[9]。因此,理论上MRS成像可实现在体评估2-HG的水平。但2-HG波谱易与谷氨酸和谷氨酰胺等代谢峰重叠,传统的1D-MRS很难实现对2-HG的检测。研究人员通过改良2D-MRS成像参数及波谱解析技术,解决了波谱重叠问题,成功实现了2-HG的在体评估[10]。
尽管多数研究者认为2-HG是一种理想的评估IDH突变的标志物,并且MRS十分适用于2-HG的非侵袭性研究,然而一方面由于耗时过长,操作复杂等原因,MRS并不是临床常规使用的成像技术,另一方面其技术本身仍存在局限性。既往文献报道的MRS对于不同级别胶质瘤的IDH1基因诊断的截断值不尽相同,同时,2-HG的检测效果还受到肿瘤体积的影响,对于体积小于3.4 ml的肿瘤,MRS的灵敏度仅有8%[11]。
部分学者转向第2种方法即多模态影像分析技术。IDH基因的突变改变了IDH与底物的亲和力,导致三羧酸循环能量代谢异常,从而使肿瘤微结构和代谢产物发生改变。多模态MRI通过分析与这些微结构和代谢改变相关的定量或半定量影像特征以达到在体无创评价胶质瘤IDH基因表型的目的。Kickingereder等[12]证明IDH基因突变对HIF-1α和血管生成等生物学功能的抑制作用。因此,IDH1/2突变型患者相对脑血容量较野生型患者下降,提示突变型肿瘤细胞增殖程度低,新生血管生成少,与其较好的预后相一致。Eichinger等[13]依靠肿瘤体积和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纹理信息预测WHO Ⅱ和Ⅲ级胶质瘤的IDH基因状态。他们建立的一模型在实验组和验证组中的精确度分别达到了92%和95%。Zhang等[14]从T1WI、T2WI、T1WI增强和ADC图中提取的2970个影像特征与临床数据整合产生的模型在实验组和验证组中也分别达到了86%和89%的准确度,其中预测价值最高的是患者年龄、参数强度、纹理和形态特征。Yamashita等[15]从TIWI增强和DWI图像中选取了6种参数,在这6种参数值中绝对脑血容量(cerebral blood volume,CBV)、相对CBV、坏死面积、增强病变中跨层坏死面积百分比在突变型和野生型IDH肿瘤中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74~0.87。
总之,目前无创检测肿瘤IDH状态的方法中应用广泛的是通过MRS技术来探测由IDH基因突变所导致的2-HG累积,但是IDH基因突变引发的代谢和微结构的改变为多参数DWI,灌注加权成像(perfusion-weighted imaging,PWI)和血氧水平依赖等获得反映肿瘤细胞密度、微血管密度、血管通透性及氧代谢等影像标记提供了分子学和病理学基础。多模态影像分析因大量定量/半定量特征的优点在IDH研究中可获得进一步应用。
2 MRI成像评估染色体1p/19q共缺失
1p/19q共缺失是指1号染色体短臂(1p)和19号长臂(19q)同时缺失。目前研究认为1p/19q共缺失与少突胶质细胞瘤高度相关,是其诊断性分子标志物[16]。2016年,WHO分型指出1p/19q共缺失与IDH1基因突变可共同作为少突及星形胶质细胞瘤进一步分类的重要分子标准。1p/19q相关基因的丢失使得其他抑癌基因、癌基因或耐药基因发生激活或者功能下降,从而使伴1p/19q共缺失型少突胶质细胞瘤通常对放化疗更为敏感,预后更为良好。
研究表明,少突胶质细胞瘤发生部位与1p/19q共缺失状态存在一定关系,额叶和枕叶多为共缺失型而岛叶和颞叶多为非缺失型[17]。Zlatescu等[18]在间变性少突胶质瘤患者群体中得出同样的结论,并且他们发现共缺失型往往具有双边生长的特点。对此,研究人员认为癌基因转变事件仅仅发生在特定细胞来源或脑区域时才会有效,从而使得不同前体细胞来源的肿瘤表现出不同的影像学和病理学特点。少突胶质瘤MRI图像特征同样与1p/19q共缺失状态存在一定关系。共缺失型肿瘤T1WI和T2WI信号较混杂,边缘模糊[19]。Jenkinson等[20]对33例少突胶质细胞瘤患者及53例星形细胞瘤患者肿瘤生长特征和基因型与MRI表现的研究表明,浸润性生长在1p/19q未缺失型胶质瘤中更为常见。同时,1p/19q未缺失型与共缺失型肿瘤相比,肿瘤边缘更为光滑或锐利,但不同基因型瘤体细胞结构的影像学边缘并无明显差异。
文献报道的1p/19q共缺失状态与灌注和扩散成像参数之间的关系尚存争议。有研究[21]表明1p/19q共缺失型肿瘤rCBV值更高,将ROC曲线阈值设为1.59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92%和76%。与1p/19q未缺失型伴低rCBV值和1p/19q共缺失型伴高rCBV值相比,1p/19q未缺失型伴高rCBV值的胶质瘤患者预后更差。该作者的另一项研究[22]表明,1p/19q未缺失型肿瘤的最大ADC值及ADC直方图更高。然而Fellah等[23]认为1p/19q未缺失型和共缺失型肿瘤的DWI、PWI及MRS表现并无显著差异,但他们发现结合MRS,共缺失状态可有效判断低级别少突胶质细胞瘤的间变性,在不伴共缺失的胶质瘤患者中,Cho/Cr>2.4往往与间变的出现有关。相反,在伴共缺失的肿瘤患者中,当Cho/Cr>2.4时没有观察到间变性。
有学者通过对常规MRI图像的纹理分析等方法来预测1p/19q 状态。Zhou等[24]发现由T1WI、T2WI、T2 FLAIR以及T1WI增强序列所获得的MRI纹理特征对165例低级别星形细胞瘤和少突胶质瘤的共缺失状态预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达到0.90%和89%。Rui等[25]基于T2 FLAIR的纹理分析也证实了少突胶质细胞瘤、IDH突变和共缺失之间影像特征的联系。
尽管在各型胶质瘤中的诊断作用并不完全一致,但共缺失状态却是评估放化疗效果的有力指标。研究证实,对比增强和瘤周水肿等影像学特征可有效预测伴共缺失型间变性少突胶质瘤的预后[26]。临床试验也证实伴共缺失型间变性胶质瘤患者在接受了放疗和或烷化剂化疗后的生存期更长[27]。
3 MRI成像评估TP53突变
TP53为肿瘤抑制基因,其编码产物为P53蛋白,后者通过转录调节下游的靶基因而发挥调节细胞周期阻滞、诱导细胞凋亡、抑制血管生成、调节能量代谢作用,从而阻止DNA损伤和有丝分裂后异常染色体分布细胞的存活,抑制肿瘤形成、生长[28]。TP53基因突变发生在胶质瘤形成早期,阳性率达到了47.5%,且与肿瘤的恶变进程有关,高级别胶质瘤的阳性率显著高于低级别胶质瘤[29]。
TP53基因突变与特定肿瘤解剖位置有一定的相关性。突变型低级别胶质瘤多位于双侧颞叶和岛叶,而野生型肿瘤多位于额叶。这一解剖位置的特异性对肿瘤的预后可能也有影响,左内颞叶和右前颞叶与P53的高表达高度相关,而位于这些区域的肿瘤的无进展生存期明显差于其他区域[30]。但突变型高级别胶质瘤多发生在侧脑室前角周围额叶区[31]。
不同的微血管密集度导致的水肿程度在MRI上表现为T2WI信号的差异。周东海等[32]分析了星形细胞瘤瘤周水肿MRI评分与肿瘤组织P53蛋白的相关性。他们发现随着瘤周水肿MRI评分的增高,P53阳性细胞率亦随之增加,因此MRI瘤周水肿表现可反映肿瘤组织P53蛋白的表达程度。Li等[33]从常规MRI图像中提取影像组学数据建立的模型对低级别胶质瘤的TP53状态的预测精确度达到了80%和70.7%,较单个影像特征的预测效果有明显优势。这些研究结果都符合TP53突变型肿瘤具有更高的微血管计数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过表达的病理学特征。
4 MRI成像评估MGMT启动子甲基化
MGMT是一种DNA修复蛋白,可移除DNA上鸟嘌呤氧6位点致突变的烷基加合物,使受损的鸟嘌呤恢复,从而能够保护细胞免受烷化剂的损伤。因此,MGMT的高表达会影响烷化剂的疗效,这也是细胞对烷化剂类药物产生耐药的分子基础。甲基化状态有助于预测肿瘤治疗效果,但是关于MGMT在脑胶质瘤中的阳性表达与肿瘤病理的关系仍有争议。Yuan等[34]认为高级别胶质瘤中MGMT的阳性率显著低于低级别胶质瘤,另一部分学者得到相反的结果[35]。
文献报道了常规影像特征如肿瘤位置、体积、增强、侵袭及水肿对MGMT甲基化的预测价值,但尚未达成共识。Kor fiatis等[36]认为MGMT甲基化状态与肿瘤的大小无明显相关性,而与肿瘤的发生部位相关。甲基化肿瘤多发生于左额叶,未甲基化肿瘤多发于颞枕叶。Ellingson等[37]认为MGMT启动子甲基化型胶质瘤通常位于左半球,未甲基化型多位于右半球。他们还观察到了甲基化和未甲基化肿瘤的T2 FLAIR高信号容积具有显著差异,甲基化肿瘤容积明显小于未甲基化,而两者的对比增强体积却无明显差异,说明甲基化肿瘤的水肿程度要小于未甲基化肿瘤。
MGMT甲基化肿瘤具有较为一致的扩散特点,其ADC值、ADC比值及最小ADC值较非甲基化肿瘤大,提示甲基化肿瘤更高的异质性和较低的细胞结构性[38-39]。Han等[40]的研究不仅表明ADC值比rCBV值对MGMT甲基化状态的预测价值更高,并且联合肿瘤位置与囊变特征可获得更高的AUC。Kanas等[41]使用MRI 3D容积模型对胶质母细胞瘤的MGMT甲基化状态预测精确度达到了73.6%,其中水肿/坏死容积比、肿瘤/坏死容积比、水肿容积和肿瘤分布及增强特点的预测价值最高。Han等[42]使用胶质母细胞瘤患者的轴向MRI图像构建了卷积神经网络结构来预测MGMT甲基化状态,为进一步了解胶质母细胞瘤中MGMT甲基化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以上结果说明,尽管MGMT启动子甲基化在增强化疗敏感性方面的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但MGMT状态与胶质瘤MRI成像特点关系的研究还不足,各作者的结果往往不一,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5 MRI成像评估其他分子遗传改变
目前还有许多与胶质瘤相关的基因及其分子标志物被相继发现并获得研究。ATRX基因突变通过端粒替代延长机制参与胶质瘤的发生,其缺失通常与IDH基因突变联合发生而与1p/19q 共缺失拮抗发生,其突变状态可通过动脉自旋标记成像加以分辨[43]。EGFR过表达可促使肿瘤细胞恶性侵袭。研究认为动脉自旋标记成像获得的脑血流量图与EGFR变体III状态具有相关性[44],中位相对脑血容量、最大肿瘤血流量和相对肿瘤血流量都与EGFR表达呈显著正相关。基于体素的影像组学分析对EGFR表达状态的预测准确度达到了90%[45]。
6 小结
影像基因组学是联合应用新型MRI成像和数据分析技术来判断影像特征与不同分子表型之间的关系,可对胶质瘤特异性分子遗传学变异进行更为深入地分析。胶质瘤分子遗传学特性与多种影像技术的结合将是未来胶质瘤分子诊断与治疗的必然趋势。关于胶质瘤的影像基因组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尚存在一些局限性,如病例数少,多为回顾性研究,基因样本与影像指标不能一一对应,多采用常规MRI序列等。尽管已经确定了大量有潜在价值的影像基因组学生物标志物,但由于不同的仪器获得的影像特征的一致性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需要未来进行更加广泛的多中心验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