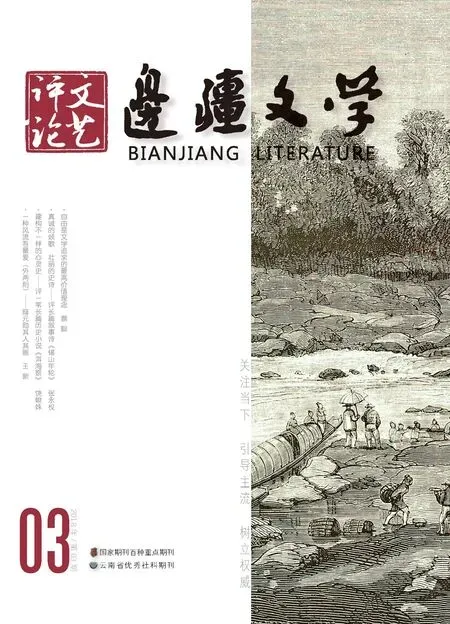一种风流吾最爱(外两则)
——寇元勋其人其画
王 新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形容的也许正是寇元勋这种人。
一派空明,一袭诗意,然而尚需一脉古意,方足当之。
四十年来,寇元勋守在云南花木葱茏的一隅,安静地喝茶,吃饭,伺候着笔下那些莺莺燕燕、花花草草,不哗众,不取宠,把日子过得风流自赏。
尽管如此,寇元勋其人其画,绝对让人眼前一亮,过目入心。
寇元勋相貌高古,其人身材伟岸,乱发当风,声若洪钟,像极江湖山林间啸傲杀伐的好汉,然则其开口一笑,便灿若罗汉,憨憨然,淳淳然,真非尘俗间人物也。
寇元勋有茶癖,有美食癖。一遇美食,便可为之生,为之死,为之“上穷碧落下黄泉”,其罹患痛风顽疾多年,本当粗茶淡饭,但他从不以为意,经常忘乎所以,扪腹大啖,啖得酣畅淋漓,啖得怡然自若。
熟悉魏晋风流的人都知道,这样有深癖者,往往有深情。
寇元勋擅卜算。
寇元勋还爱唱歌,吼一曲《沧海一声笑》,“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实在是唱得苍凉旷落,孤独雄浑。
当然,绝大多数时候,寇元勋把这一襟深情,都轻轻收敛住了,化为其笔下花草与烟云。
近年来,寇元勋笔下出现了一系列花草古僧形象,多破笔枯笔,萧然草草,水渍墨晕,纵横挥洒,随抹随写,随写随生,在花意盎然中映现古淡僧影,极富高古旷逸之致。此种合花鸟画与人物画而为之的手腕,在当今国画界,北方有李世南,南方则有寇元勋,然则前者苦涩,后者枯淡,前者紧致,后者松灵。

寇元勋 梅花道人,2015
寇元勋的松灵,还体现在近年花鸟画创作的新变中。寇元勋实在能画一手纯正的文人笔墨,观其早年富有代表性的兰竹石图,以书法写之,以诗文润之,以豪气振之,竹清,兰幽,石丑,画面清雅劲秀;后又以云南民族佳人风物入画,细笔袅袅,计白当黑,略施颜色,与水墨相融,自得明丽风致。

寇元勋 独立枝头,2017
当然,看得出来,从早期至今天,跃动在寇元勋笔尖的豪纵之气,无一日减之;近年来,其创作更是顺乎天性,不再刻意追求笔墨书写,让豪纵与疏野结合,与古淡结合,与婉秀结合;藉水法带动,墨撞色,色撞墨,水墨色流溢、渍染、晕化,再以松灵的用笔,“池塘生春草”般随势成之,点线面穿插对比,水墨色呼应重叠,果黄花红,披美缤纷,鲜妍而雅淡;画中花鸟虫鱼,或发呆,或雀跃,或嘤鸣,似与不似,抽象与具象,有笔墨,有构成,有情味,既传统,也现代。尤为重要者,寇元勋似乎越来越不着意于画,笔墨越来越放松,越来越空灵,这是真正大写意渐臻于老境的标志。这样松灵的笔墨,这样老辣自由的境界,在艺术史上,中国唯有黄宾虹、西方唯有伦勃朗,得之。
寇元勋显然是走上了一条人迹罕至的林中路。
诗人弗罗斯特说,“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轻声叹息把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了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寇元勋应该有弗罗斯特同样的惆怅与孤独。
据说,某一天,寇元勋正盯着墙上自画的一个扇面,扇面上一只垂首兀立的黑色乌鸦,凝神黯然。一非专业老师路过,十分很好奇:一只黑乌鸦,有什么好看的呢?
寇元勋十分严肃地说:
“这是一只孤独的乌鸦!这只乌鸦就是我!”
可见, 寇元勋有酝酿在骨子里的孤独,这种孤独也是魏晋名士骨子里的孤独。
此品玲珑有暗香——汪硕画评
汪硕是我读研时“睡在我下铺的兄弟”,山东人,体格粗壮,赤膊,短裤,经常作白痴状,朝着我喊:“嘿,新哥!”
当时我就想,这么粗放的人,能画什么画呢?
及至后来,我溜到他的工作室,一瞄,大吃一惊:雅致婉丽,一派江南!

汪硕 寒山,30-40cm,2016年
我开始对他的创作留意起来。
这个五大三粗的小伙的才情,体现在他的安静,体现在他对色彩细腻锐敏的自如拿捏上。三年中,除了谈恋爱,绝大多数时候,他都安静地坐在画布前,旁若无人,一抹一擦,一点一线,慢慢吞吞地经营着他那些风景小品。尤其其小品色彩,画不盈尺,极少的几种颜色,但每一种颜色,皆能开拓与幻化出无数的变奏,细腻,精致,余音袅袅。
这一可贵的色彩天分与教养,他一直自觉保持在其多年创作中。观其近作《雪景寒林》系列,以蓝色与白色为主题色调,浅蓝、湖蓝、靛蓝,洁白、银白、灰白,结合空间、形状、线条、笔触,渍染刮擦,呼应厮磨,画得清华明洁,极有古典风调。除了细腻温润,尤其《寒山》一画,把绿色画得苍翠沉雄,有了人书俱老的力量。这是不凡的长进。
实际上,西方古典油画正统,也讲求单色专精,画家应充分发掘与其天性相亲的、每一种色彩表现的所有可能性,开拓画幅披美缤纷的“主题色”变奏,达·芬奇、伦勃朗、终生能使用得完全得心应手的色彩也就两三个,两三个,在创造者手腕下,便会风华无限。汪硕多年最喜、最擅绿色、蓝色、白色、黄色;此四色,也许,他使用得还不那么完全得心应手,好在他堂堂乎其正,走在了艺术的坦荡正途。

汪硕 雪景寒林2,90-120cm,2017年
追根溯源,汪硕良好的色彩教养,得益于海派油画传统。纵览新中国艺术史,能在铺天盖地的灰调子、红光亮中,自始至终固执地画出明丽温润的色彩,唯有林风眠、刘海粟、吴大羽直至当代的俞晓夫、邱瑞敏、黄阿忠的海派传统,这一传统基本是印象派在东方的承传与变奏。汪硕的老师是海上油画名家黄阿忠教授,他自然而幸福地接续了这一学脉。
汪硕的画,还追求谨严的构成感,这也是塞尚以来的现代绘画传统,当然也是乃师黄阿忠所擅之胜场。汪硕放弃了过于呆板的空间透视,而注重在压缩得紧致的平面中,通过线、面的构成,将五音繁会的色彩锁缚、搭配,从而让画面变得安静,精致,富有现代感。其《平行的风景》系列,将蓝、绿色块平行切割,排比,几何化的近景田园与有机化的远山,巧妙搭配,造成一种梦寐如幻的现代感,整个画面风格已经逸出了其惯常的古典情味,这是其创作另外的一种有益尝试。他的诸多静物系列作品,皆不出这一努力范畴。
随手翻过其“夕照千山的山林晚景,”进入到“绿意盎然的盛夏田园”,宋人苏舜钦诗句“秋色入林红黯淡,日光穿竹翠玲珑 ” ,蓦然闪现,前句讲调子,层次丰富无际,后句讲光色,精致亮丽。我想,这句诗也正好符合汪硕的油画格调,符合他的审美情怀。在观念化、物质化、机械化横行的当代艺术风潮里,汪硕的这种细腻,这种精致,这种安静,无疑皆是值得褒扬的创造美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宝贵的玲珑“暗香”。
然而,作为兄长,作为艺术的同道,我还是要提醒汪硕,他在一门心思精研乃师黄阿忠先生的油画精义时,千万不要忘记其师右手油画、左手国画,其油画上有着国画水墨渍染的空灵与自由,所以能风标独秀。汪硕的创造,若能欣然会此,多一些放手的书写,多一些抖落过于认真后的松灵, 必然后有更可期待的进境。
期待一个更加妩媚,更加松灵的大汉!

全显光 钟馗1,2016
磅礴天地的自在与孤独——读全显光的钟馗
“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说的是大自在,也是大孤独。
在我的导师王洪义教授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我师祖全显光先生的钟馗,想到的正是庄子的这句话。
猛厉恣肆的自在,睥睨旷古的孤独。
王洪义老师跟我说,他一直缺乏勇气在公开的媒体上谈论全显光先生,“因为我的老师显然是一流的,我却连二流也够不上,如果斗胆自报出身,其实是有辱师尊的。”
这令我十分震惊,要知道,王洪义老师在上海滩的艺术圈子中,也算声名赫赫。那次,他还告诉我,全先生脾气很大。
这,我不奇怪:才气大的人,脾气往往也大,比如章太炎,比如陈独秀。
恰恰相反,他一点也没有脾气。我第一次见到全显光先生,双手一握,那种糙重的感觉,是农民的双手,朴厚极了。
但那双大得吓人的眼睛,像极了他笔下的钟馗。
79岁的老人,一口气跟我聊了6个小时。没有废话,全是关于艺术的要言妙道。
我这次明白,黄宾虹与伦勃朗在高处相通;全氏钟馗性感而傲慢的胡茬与胸毛,正是来自二者的“重叠”画法。全显光先生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德国莱比锡书籍与版画艺术学院留学7年,他专业为版画,但同时在沃尔特·门泽工作室学油画,与老莱比锡画派大师海森克、新莱比锡画派林克是同学,在门泽指导下,他遍临莱比锡博物馆伦勃朗真迹,伦勃朗油画中数百次“重叠”所形成的浑厚华滋之精义,其由此心会。
他同样终生精研黄宾虹的笔墨“重叠”。
他的钟馗艺术,只是其艺术创造极小的一部分,在国、油、版、雕诸领域,他都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凡创造;更蔚为大观的是,他的“德国式”体大思精的基础教育体系。
我在硕士论文答辩会上,一展示我关于全显光先生的研究,艺术学大家潘耀昌先生、卢辅圣先生双双颔首。
我的这篇论文后来获得了上海市优秀学位论文,是当年美术学专业唯一论文。
毕业后,我回到云南大学教书。我极力邀请他来云南讲学,因为他是昆明人。
他来了。我陪他到故居一游,他忽然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终生爱画钟馗吗?”我当然不知道。
他长叹一声,“小时候家里穷,穷到有时候,到老鼠洞里去掏米粒吃。逼得没有办法,为了讨生活,过年,就去学画门神钟馗。有时候,当有人买了,还说‘好’,我就十分激动,要知道这可是晦暗生活里的一星阳光啊!”
自然,他的钟馗,带上了特别馥郁的民间味儿。
他对民间情味与智慧毕生深赏。他成熟时的钟馗,上半身是伦勃朗画法,保持立体层次,细腻丰富,下半身则完全舍弃立体刻画,十分肯定地走向线条书写,走向灵活多样的线条穿插与构成,完全平面化,俨然剪纸。无需奇怪,这是他向民间剪纸艺术的虔诚致敬。
民间艺术带给他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深藏民间的那种无法掩抑的猛厉生动。我们知道,中国绘画讲气韵生动,但北宋之后,在文人艺术中,气韵生动,日益精致,乃至沦为疲弱。只有在民间才存留了真正元气淋漓的大生动。
全氏钟馗慑服心旌的生动,就来自这里。
更有意思的是,无意间,在他的怀表盖里,我发现了他的钟馗,油画所画,神采照人,我惊呆了,问他,“这么小,怎么画成的?”他笑笑,“凭手感,闭眼画的。”
人书俱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庄子笔下的解牛庖丁,或解衣般礴者,大概类此。
而且后来在他沈阳的家里,我见识了他的丈二钟馗。
正所谓小不盈尺,大可全壁,全氏钟馗,有执扇,有仗剑,或顶立,或偃卧,可醉酒,可簪花,雄厚处逼人,妩媚间动人。
尤其85岁以后,其钟馗又为之一变:中国画而深求油画风调,在挤压得极薄的平面中,通过百多次用笔、用墨、用水,反复重叠,实现丰富已极、细腻已极的“微差”塑造,且不掩脏、乱、犷、砺,霜皮龙鳞,老辣恣肆。
为什么他如此情牵钟馗呢?联系钟馗作为一介书生怀才沦落继而在鬼蜮振起的故事,再看看全先生的人生:他虽然是鲁迅美术学院的知名教授,然而,在苏式主流美术一统天下的日子里,他命途坎坷:调工作几番不成,工作室随意被取缔,批斗,抄家,排挤,样样遭逢,艰难备尝,但他隐忍默守,埋头苦干,以才华与气质,书写不屈与愤怒。读其钟馗,他的苍凉勃郁心境,可见一斑。

全显光 钟馗2,2016
除了愤怒,钟馗正是一种磅礴天地的自在与孤独。
今年86岁的全显光先生,人前人后,哪怕在毛头小子面前,都依然保持着十分的谦卑,看过他的大量钟馗后,唯有我知道:他的轻蔑、傲岸与雄心。
(作者系美术学硕士,思想史博士生,现为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