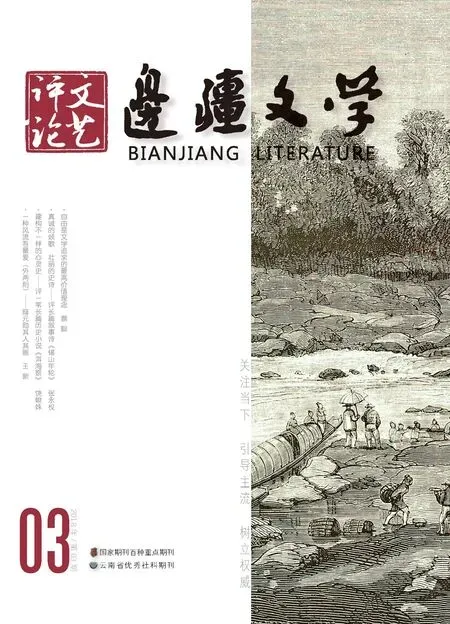自由是文学追求的最高价值理念
蔡 毅
在考虑文学价值系统的建构时,必须将自由、自由思想、自由精神和自由创作作为最重要的内容提出来研究,并将其作为支持并统领一切的最高价值理念,贯彻在文学创作和价值建构的所有活动中。因为自由既是从事一切活动的必要元素,最基本的条件,又是搞好一切最根本的思想原则、精神保证。陈寅恪先生曾大力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标举“无自由之思想便无优美之文学”,因为它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
什么是自由呢?自由是对限制的否定。自由便是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心意进行活动、思考和选择的权力,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这首先是由于人的生命的本质就是自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出“人本自由”的命题,他说:“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因为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面临着无数的机会与选择、变动与坚守,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人是自己思想和行为的主人。启蒙思想家卢梭更提出了“人是生而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天生本性,是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天赋人权。倘若放弃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是放弃自己的义务。马克思也专门指出:“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人的本质特征便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若无自由,人便不复为人,或成为奴隶,或成为工具,都会丧失人之为人的资格,成为行尸走肉。萨特曾大声宣称,人就是自由,人存在的本质就在于他的自由。“人首先就是一个过着自己独特生活的计划,而不是一片青苔、一堆垃圾或一朵菜花。”没有任何东西能对人的命运进行预先的安排或规定,人只是循自己的计划而成的东西,只是他自己行为的总和。
其次,自由是人的精神活动的本质,是人类精神存在的天然属性。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过:“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精神的特权”,是“伟大的天赋特权”,是“理性的晨光所赐的自然礼物”。因为只有自由,人才能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从而也才能知道什么样的道路才真正适合自己。自由既是人类生命存在的形式,也是人类生命力的升华,精神的一切属性都是由于自由才得以存在和发展,没有自由,精神便无立足之地和生存之家,自然也谈不上任何的发展。人类精神的自由,并不是动物式的蒙昧无知或随心所欲,而是理智状态下的心志自主,是在各种关系中最高程度的自觉适应。人之所以优于动物,正是由于人具有动物所不具有的思想、精神和理性。这思想精神会引导人去追求自由,提高与扩大自己生命的质量与内容,向着使自己生活得诗意而又神圣的境界发展。无论思想或是精神,随心所欲自由流动,无拘无束自主选择是它最根本的状态,也是其追求的唯一真理。
再次,自由是人类崇尚和追求的宝贵价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最有名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便表述了人之自由是高于生命和爱情的崇高价值,它值得每个人舍生忘死去争取、维护和捍卫,而决不放弃的坚定信念,因为没有自由对人来说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惨烈的可悲。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中,主张人类社会本来就应该是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争取人的解放,就是争取自由的人的本质的复归。他认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在这个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主张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要建立人世间的“自由王国”。恩格斯也说过:“人类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他们显然都是把自由当作最高的价值目标倾尽毕生精力来追求。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说:“进步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是自由”。因为一部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人越来越从各种桎梏中挣脱出来,走向自由幸福的历史。人类的发展也雄辩地证明,人只有在不受限制的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他的创造力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也才能完全激发调动出来,贡献于社会和国家。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结语中所说:“自由并非通往某个高尚目标的手段,自由乃最高尚的目标。”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又说:“自由不只是许多价值中的一个价值,而且还是所有其他个人价值的渊源和必要条件。”高度肯定自由乃是价值中的价值!基于以上理由,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显而易见,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其他杰出的思想家,他们都十分注重自由,一直把自由放在显著的地位,因为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是人类的最高追求,自由属于人类共有和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黑格尔说得好:“世界史就是人们自由意识的进步。”
说了那么多,无非是想说自由是一种可贵的生命源泉和精神动力,也是一个现代重要的价值理念,它体现了自由权利和自由意志的诉求,关乎着人的本质及价值理想的实现。在任何时代,只要思想是自由的,人类就会取得较大较快的进步;如果思想是不自由的,人类就会停滞,甚或退步。自由关乎思考,关乎创造,关乎价值。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无不渴望和期盼着自由,更多更大的自由。任何一个人都应当高度重视心灵与行动的自由。
折回到文学来说,文学是一方自由驰骋之地,自由是文学高贵的品质,是文学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法宝。有了自由的心灵与自由的创作,作家艺术家才能超越狭隘现实的束缚,摆脱经验与既往思维方式的拘囿,八方驰骋,往来古今,让思绪在广阔的时空中流动,调动全部的知识、才华、见识和想象,去构思与创建新颖奇妙的组合,创造出具有崭新品质和意蕴的作品。
众所周知,共和国建立之前,我们还有《我们在太行山上》的歌词:“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的表达,但越到后来,自由却被视为伪善有害的东西,被丑化排斥,打压封杀,严加管束禁止。使得自由或被当作是十恶不赦、离经叛道的思想,视若洪水猛兽;或被打入资产阶级的罪恶范畴,视为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使“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统统变成一种罪名,致使自由在中国一度成为一种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
改革开放扫荡了限制人们思想行动的陈腐教条,砸碎了许多捆绑在人们身上的枷锁,使我们国家在走向强大富裕的同时,也锻铸了相对成熟的头脑和宽广的胸怀,自由思想和创造不再是动辄得咎的罪过,反成为人人欣羡的可贵品质。近年来党和政府更是把自由作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大力倡导推广,让人从中看到时代、社会的根本变化与进步。今天的社会环境比之过去已有翻天覆地的极大改善,但距离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状况,仍有很大差距。需要每一个人继续努力,千方百计去争取自由更大更快的发展。这只消提两个问题,如我们的创作真的能冲破意识形态、时代风潮、世俗舆论的藩篱,无所畏惧,解放思想,尽情写作了吗?真的能不畏权势,不为经济利益,不为流行趣味和读者好恶诱导,而完全打开自我,真诚写作了吗?谁也不敢做完全肯定的回答。由此可见,我们对自由之路的探寻依然是任重而道远,需要加倍努力的。
文学是自由思想自由创作的一方独特领域,文艺创作是个人创造力的扩张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历史已证明,什么时候能做到真正彻底的自由,文学就能够大放光彩,吐露芬芳。什么时候文学失去自由,它必定就会枝残叶凋,萎靡不振。所以对文学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考虑如何创造各种条件,保证文学创作的自由和生存自由。
欲实现创作自由,从外部环境来说,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和行政规定一直到相关部门、相关人员都必须创造宽容宽松、自由活泼的环境空气,促使自由的降生。个人自由的政策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少限制,多支持,不干涉,放手让作家艺术家去进行各种探索试验,尽心竭力去展现个人的所思所想,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智慧与创造本领。
从内部环境来说,心灵的真正自由解放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自由。让思想、情感和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许多写作者企盼的境界。心灵的自由不是上帝的恩赐,不是他人的赏予,而是内心的自觉与开悟。唯有内心真正感觉到来自外界的限制是必须破除的,来自自我的限定是必须冲毁的,从而放开手脚,目空一切,法自我出,才能实现内心的自由。这就需要打破他人设置的“思维牢笼”“政治铁屋”,逃离个人洞穴、自我困局,永远葆有一颗向往自由之心,听从自由信念的呼唤,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自己做自己的上帝。若能做到这些,即使在恶劣环境中也能保持内心的自由。若做不到这些,即使锦衣玉食,生活优裕,内心也可能是僵冻枯萎的。
生命的本质就是自由,卢梭说:“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前句话是理想,后句话却是现实。现实是大多数人总不免被许多有形无形的绳索七缠八绕,重重捆缚。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生命中的各种束缚,或无力反抗被迫顺从,或无奈而日趋消沉麻木,或习焉不察久居不觉。作家艺术家却天生敏感,天性爱自由,他们都懂得自由是文学的天性,是创造的前提。没有自由意志与自主选择,谈何自由创造?所以他们必须做自由的倡导者、实行者与引路人。
自由是相对不自由而言的。什么是自由呢?自由其实就是按照个人的心愿,尽情尽兴地活动与表现。自由是人的天性与本性。自由是人对自己的价值和幸福的最高理解,自由是人格的崇高敬意。人生活于世,一切言行都应从自己的天性本性出发,从与人利益的相关性出发。凡符合人的天性本性的就是正当的,不符合人的天性本性的就是不正当的。韩少功说:“在相同条件下做出相同的选择,是限定而不是自由。只有在相同的条件下做出不同的选择,在一切条件都驱使你这样而你偏偏可以那样,在你敢于蔑视一切似乎不可抗拒的法则,在你可以违背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常规逆势而动不可为而为的时候,人才确证自己的选择权利,才有了自由……自由常常表现为把自己逼入绝境,表现为对利诱这些词义的熠熠利诱无动于衷。”这是自由的一种境况。
让心灵和自己所有的感觉器官都处于一种自由开放的状态,让如约而至的灵感给创作带来意外的惊喜。“灵魂是一只鸟/它热爱自由”。只要作家自身所有的生命感觉永远处于纯净鲜活的姿态,创作灵感就一定会源源不断。这又是自由的另一种境况。自由的状态是多种多样的。自由是文学追求的目标与理想境界。
什么是不自由?外在的限制就不用说了,内心的各种条条框框、观念误区会对自我形成束缚、限制、压抑,那就是不自由。它们会使作家艺术家由于害怕惹麻烦,吃官司,害怕读者对号入座,怕舆论批评,于是根本就谈不上真正的打开自我,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反而处处受制于环境、道德以及内心对自我的约束,小心翼翼畏首畏尾,不敢对世界提出质疑,对人事提出抗辩,不敢对成规冒犯,样样都按规定的来,从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就需要打破外界加诸自身的各种束缚,突破传统的、道德的、甚至包括写作惯例的约束限制。一切的创造,不光需要尽情尽性,而且需要一种“神圣的疯狂”,即超越理性的冲动恣肆,使个人能量和创造力得到极大的舒张释放,让个体摆脱具体的禁锢,在有限的经验中体悟到无限,体会到个人的渺小与伟大崇高,才可望打破陈规陋习的束缚,获得新的飞腾和进步。
强调自由便根本不用担心自己所写是否合别人的意,是否会引起麻烦,招致灾祸,要敢于在一个强大的气场里写出自己内心的东西,说出真正想说的话。面对任何情形,无论是顺境逆境、掌声或嘘声都不能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失去自我,而要养成自由思考写作的习惯,这才可望能打开堵塞的阀门,放出清流,真正进入自由创作的天地,让思想无疆界,精神无羁绊,才是创造者每天应当努力并践行的准则。
必须警惕各种可能出现的“画地为牢”。这“牢”或是别人所设,或是自己所设,但只要有“牢”,大脑就被套上枷锁。每个作家在思考写作时都不免会自我设限、自我规约,以使自己的写作更符合潮流和文学惯例。大多数作家都不敢,也不愿去做个“不合时宜”者。因为在某些方面吃过亏,或看见别人吃了亏。还有是因自己冲不破某些障碍,便认可障碍的存在,不敢再去触碰它。更多的则是某种套路写顺了,尝到甜头,就沿着这套路滑行,不思改进,不再进行新的试验探索,于是也就丧失了自由。写作本是为了自由自在,可写着写着一不留神就为自己套上了枷锁,浑身只剩下了拘束和不自在,这是不少写作者的悲剧。
美国哲学家莫里斯说:“敌人在我们自己里面,而我们的力量也在我们自己身上。”卡夫卡说:“我头脑中有个阔广的世界。但是如何解放我并解放它,而又不致粉身碎骨呢。宁可粉身碎骨一千次,也强于将它留在或埋葬在我心中。我就是为这个而生存在世上的,我对此完全明白。”他们都强调自己是自己的救星,自己如何冲破一切障碍,最大限度地张扬个性,发挥个人全部的积极性创造性,使生命价值最大化,就是最重要的事。在现今这个价值往往是由经济法则决定的社会中,精神和灵魂的自由对于每一个人都尤显重要。因为唯有精神、灵魂保持自由,思想、行为和人的一切活动才能独立自主、活泼不羁,才能超越普通为生存而挣扎的实在世界,向着永恒而美好的理想世界、价值世界奔赴。既不向庸常琐碎的生活现实妥协,也不盲目信从流行的意识形态和日常经验,而是将自我的所有正能量统统释放。创作需要自我解放,写作须要绝大的自信,对自由表达的确信和坚信。自由表达的冲动越大,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空间就越大。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既不要让虚荣心、胆怯的焦虑来折磨我们,也不服从规定动作,不按照既定方针“作茧自缚”,时时要以超脱或超越的心态进行跨界、越轨——颠覆式创造,以一种自由、自然、自在的心态从事创作。写作最高的,也是最美的姿态就是自由。只有精神自由的人,才可能写出好文章和大文章。
自由是文学生长的土壤,也是文学得以生存的阳光雨露。自由是一种至善的境界,因为它除了把人带入理想的美的境界别无所求。“只有自由,才能幸福;只有勇敢,才能自由。”伯里克利的演说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而不褪色,至今依旧响亮。自由也是文学价值建构的最高目标,即把自由当作目的,在一切的文学活动都运用自己的理性,贯彻自由呼吸、自由思考、自由行动的原则,让自由的光辉照耀文字、人心和书本,反对和清除一切妨碍自由之物,使之朝着有利于自由的方向演进。创作的生命、本质是自由,所以自由精神必须从始至终陪伴在我们周围。帮助我们真正无所顾忌地秉笔直书,自由自在地坦陈己见,写出的文字完全听从内心的声音。当然,达到这些目标并不容易,它需要我们终生与身体中那个怯懦和懒惰的“我”进行不屈不挠地搏斗,需要我们怀抱陈寅恪先生那种“思想之不自由,毋宁死耳”的勇敢决绝,用自己的奋斗去争取自由更大范围的扩张与更大程度地实现。
当今中国正在进行全面的深化改革,改革需要自由和创新的思想作动力,文学正是社会思想库发源滥觞之所在,文学应当成为启发创新思想的自由土壤。因此我们期望通过对自由精神、自由创造的大力呼唤,催生更多集时代性、思想性、艺术性、创造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反映当代中国人的审美追求,给人们带来精神的洗礼、情感的愉悦和心灵的提升。

马祥和 国画 秋声
【注释】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207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3页。
[3]《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95出版。
[7]约翰·密尔:《论自由》第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出版。
[8]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第4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9]韩少功:《人在江湖》第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
[10]李瑛:《灵魂是一只鸟》(组诗),见2015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11]卡夫卡:《卡夫卡散文》第208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4年度西部项目(14XZW04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