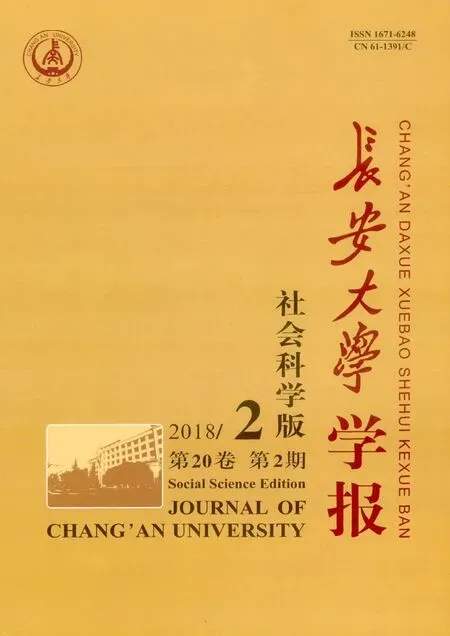黄陵、新郑和缙云黄帝公祭再探讨
李桂民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黄帝作为古史传说时代的重要人物,被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 从古至今广受尊崇。对于黄帝的祭祀,起源于先秦时期,至今仍有多地定期举行黄帝祭祀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河南省新郑市黄帝故里和浙江省缙云县黄帝祠举办的黄帝祭祀活动。
黄帝族是中国上古时期的著名部族,黄帝部族日后的分化和迁徙,致使全国多地至今仍有黄帝传说流传,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就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1]因此,全国各地的黄帝纪念性建筑,是黄帝尊崇观念的物化形式。
祭祀为“五礼”之一,祭祀在古代社会占有重要地位,《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2]对于黄帝的祭祀可分为公祭和民祭,公祭活动尤以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和浙江缙云三地影响最大。本文主要围绕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和浙江缙云三地黄帝公祭谈谈看法,一方面增强公众对于黄帝祭祀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利于黄帝祭祀活动的健康发展,不当之处,请前贤硕儒不吝教之。
一、黄帝国祭之争和陕西黄帝陵祭祀黄帝的优势
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和浙江缙云的黄帝公祭活动,都已经办出了影响,其中祭祀历史最长的是陕西省黄陵县的黄帝祭祀。就这三地的黄帝遗迹而言,陕西黄陵县有黄帝陵,河南新郑为黄帝故里,浙江缙云则为黄帝祠。黄陵、新郑和缙云三地的黄帝祭祀活动已经各自举行多年,起初三者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冲突,甚至还出现了黄帝生于河南、葬于陕西的说法。可见,陕西对于河南等地新兴的黄帝祭祀活动开始并没有反对,只不过随着河南新郑黄帝祭祀影响的日益扩大,河南新郑寻求把黄帝故里祭祀典礼上升到国祭,一些学者为这种愿求积极寻找历史根据,撰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后,方在陕西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2015年9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国家拜祭体现时代创造力——“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与国家文化建设”研讨纪要》,同版还刊发了许嘉璐的《把拜祭黄帝上升到国家级拜祭》、李学勤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特点》、李伯谦的《祭拜黄帝要达成共识》和刘庆柱的《国祭也是祭国》等文章,提出把每年农历三月三日举办的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由省部级主办升格为国家祭拜的建议。《光明日报》组织的这期文章,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河南省政协联合主办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与国家文化建设”专家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和会议纪要,在这次会议上,许嘉璐做了建议把拜祭黄帝上升为国家级祭祀的专题演讲,李学勤认为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上升到国家主办是“实至名归、水到渠成”,李伯谦也提出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上升到国家主办是“历史必然”[3-6]。
2015年11月9日,《光明日报》又刊发了许嘉璐《国家祭拜的力量》的文章[7],这篇文章是其在2015年4月20日第九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的主旨发言,尽管这篇文章早于“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与国家文化建设”专家研讨会发言,但由于发表较晚,可以看作是对在河南新郑进行国祭观点的重申。
在河南新郑举行国祭黄帝的观点经《光明日报》正式发表后,在陕的一些学者撰写文章与之商榷,不过这些文章大多以网络形式发表。在反对在河南国祭黄帝的文章中,有代表性的是方光华的《对黄帝的国家祭典到底应该在哪里》文章[8],反对“拜庙不拜陵”的主张。从相关争论可以看出,“拜庙不拜陵”这种说法并不能成为拜祭黄帝应在新郑的理由,因为今天陕西的黄帝公祭亦属于庙祭,尽管历史上的陕西省黄陵县的祭祀黄帝活动是陵祭。事实上,就庙祭和陵祭的关系而言,并不是庙祭优于陵祭,而是庙祭较陵祭方便,历史上庙祭始终没有完全取代陵祭[9]。
关于黄帝国祭之争,是在河南和陕西之间展开的。尽管许嘉璐的文章提议把河南新郑的拜祖大典升格为国家主办,并没有要求废除其他地方的祭祀,但由于挑战了陕西黄帝陵的历史地位,因此,在陕西引起了强烈反对。综观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和浙江缙云三地黄帝公祭,陕西黄陵县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黄帝陵祭祀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其陵庙并存更能满足民众祭祀和寻根冀求。陕西的黄帝陵被列入祀典较早,“唐代宗大历五年接受了鄜坊节度使臧希让‘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方飨祭,列于祀典’的建议,自此,黄帝陵庙致祭被正式纳入官方祭典”[10]。明清以来更是形成了定期致祭的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陕西省率先于1955年开始对黄帝进行祭祀,除了1964到1979年祭祀停办外,长期保持了祭祀黄帝的传统。黄帝陵古墓葬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黄帝陵题词和做出重要指示,黄帝陵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价值日益增强。为了能够更好体现祭祀的庄严、肃穆气氛,从1999年开始,陕西公祭黄帝大典改在轩辕庙举行,祭祀大殿建成后又改为在祭祀大殿前举行。在祭祖大典结束以后,再去拜谒黄帝陵,能较好满足慎终追远、缅怀先祖的精神需求,这一点是其他地方黄帝祭祀所无法比拟的。
第二,清明节祭祖更符合广大民众缅怀始祖的风俗习惯。清明节祭祀是宗族中具有代表性的仪式,是时至今日仍盛行的风俗,陕西黄陵的黄帝公祭活动定在清明节举行,意义正在于此。从三地公祭的时间选择看,黄陵祭祀选在清明,新郑拜祭黄帝大典时间定在每年的农历三月三日,浙江缙云的公祭时间则选在每年的重阳节,缙云的清明节祭祀黄帝则属于民祭。河南新郑和浙江缙云之所以不在清明节祭祀黄帝,主要原因在于清明节一般是墓祭,由于两地没有黄帝陵墓,因此,都没有选择在清明节举行公祭黄帝活动。农历的三月三是上巳节,“上巳节是民间禁忌与古老的‘袚’祭仪式相结合的产物。它是民间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上巳节又不断发展变化。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巳节已由祓除不祥的巫术仪式演变为曲水流觞、走马步射、欢会游春的民俗节日。节日内涵也由宗教娱神向娱人和自娱转变。至唐代,民间节俗上升为官方礼仪,成为雅俗共赏的盛大节日。宋以后,上巳节渐趋衰落,逐步退出人们的生活,只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尚有部分留存。”[11]可见,上巳节并不是专门祭祀黄帝的节日,选择三月三进行祭祀的原因,据说这一天是黄帝诞日。黄帝诞日之说,缺乏可靠依据,晚清时期曾经出现过黄帝纪年,不过,黄帝纪年是一个政治学或文化学意义上的概念,其政治象征意义大于年代意义[12]。黄帝纪年由于各有所宗,造成一定混乱,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电令各省废除黄帝纪年,而采用公历。浙江缙云从1998年起,对黄帝进行春秋两祭,其把每年的重阳节作为公祭黄帝的时间,而和陕西黄陵把重阳节作为民祭不同。从当前的民俗可以看出,清明节祭祖更为符合中国人的认知和习惯。
第三,陕西的黄帝公祭活动起步早、规格高。历史上的黄帝陵墓并非一处,黄帝祠庙也分布于各地,桥山黄帝陵在中国古代就得到官方认可,赵世超认为:“历代王朝用规范礼制的办法确定下来的陵庙祭祀地点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因而也具有唯一性。”[13]不过,明清以来的这种唯一性在当代不再唯一,出现了多地祭祀黄帝的现象。新中国建立以后,陕西最早开始祭祀黄帝,开始于1955年,河南新郑的拜祖活动开始于1992年,三地当中,浙江缙云开始祭祀黄帝的时间最晚,从1998年才开始黄帝祭拜活动。从祭祀黄帝规格上看,陕西黄帝陵黄帝祭祀的主祭人是省长或副省长或省人大副主任,后来主祭人一般由省长担任,也就是说陕西省黄陵县的黄帝公祭活动一直由陕西省主办。为了办好黄帝祭祀典礼,陕西省还于1996年专门设立了陕西省清明公祭轩辕黄帝陵典礼筹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后更名为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简称陕西祭陵办。河南省新郑市的拜祖活动不仅起步晚,祭祀规格也不如陕西,后来改为省里主办后,才逐渐办出了影响。黄陵、新郑和缙云三地中,浙江缙云的祭祀规格最低,还没有升格到省级层面。需要指出的是,黄陵、新郑和缙云的黄帝祭典都先后进入国家非物质遗产目录,具体来说,2006年黄陵黄帝陵祭典进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新郑黄帝祭典进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2011年5月,“缙云轩辕祭典”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从非遗名录看,黄陵、新郑和缙云三地的黄帝祭典的地位要以陕西黄帝陵祭典地位最高。对于黄帝祭典,陕西和河南都有升格为由国家主办的提议,由于目前学术界关于黄帝的争论较大,这种提议短时间内不会实现,不过,陕西黄帝陵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作用,其价值在当代社会会日益凸显。
二、黄帝公祭祭典仪程及其祭祀的现实意义
礼在中国古代,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正如《左传》所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4]在正常情况下,礼仪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仪式表演,尽管今天的礼已经不复像古代那样重要。约翰·费斯克认为:“仪式就是组织化的象征活动与典礼活动,用以界定和表现特殊的时刻、事件和变化所包含的社会与文化意味。”[15]詹姆斯·W·凯瑞把传播分类为传播传递观和传播仪式观,认为:“如果传播的传递观其核心在于讯息在地理上的拓展(以控制为目的),那么传播的仪式观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16]就黄帝祭典的传播来看,其传播兼具讯息和仪式的双重意义,而且两者从来也不是互相排斥的。
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和浙江缙云的黄帝大典都经过专门设计,并在举办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目前,三地祭典先后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或扩展名录,也是全国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的祭祀活动,表明三地的黄帝祭典在仪程上开始固定下来。黄帝祭祀,并不仅仅是一次追思先人的行为,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黄帝代表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肇始,对于人文始祖黄帝的认同,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只有站在这个立场上来看待黄帝祭祀,才能真正理解黄帝祭典所蕴含的仪式传播意义。
从陕西省黄陵、河南省新郑和浙江省缙云三地的祭祀开始时间看,三地都选择了9:50这个时间节点,以取“九五之尊”之意。皇帝又称“九五之尊”,其由来有不同说法,一说是九是最高阳数,五居正中,以此象征帝王权威;另一说认为源自《易经》乾卦九五爻,此爻爻辞最好,以此形容帝王之相;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九五:“两字应是源自华夏远古时代的“九部”“九州”“九井”“九门”和“五帝”以及与五帝相应的“五方神庙”[17]。祭祀黄帝时间取“九五之尊”之意,就说明是把黄帝作为中国上古时期的杰出首领来祭祀。在各地黄帝祭文中也可以看出,称颂的主要是黄帝作为“人文初祖”的历史功绩,祭祀黄帝实际上是通过对中华民族根的追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当代的黄帝祭祀中祭祀的权力象征和宗教意义淡化,祭典各项仪程主要展现了中华民族对黄帝的尊崇之情。从具体祭祀仪程看,陕西黄帝祭典主要有七项程序,即全体肃立、击鼓鸣钟、敬献花篮、恭读祭文、向黄帝像三鞠躬礼、乐舞告祭、瞻仰祭祀大殿并拜谒黄帝陵。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仪程有九项,分别是盛世礼炮、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行施拜礼、恭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敬拜、祈福中华、天地人和。浙江缙云重阳节公祭程序包括击鼓撞钟、敬上高香、敬献花篮、主祭就位、敬献供品、敬献美酒、恭读祭文、行鞠躬礼、乐舞告祭等九项仪程。从各项仪程看,整个祭典设计突出了对黄帝之“敬”,祭典要表达的不是人伦之孝,而是对于黄帝开创中华文明历史功绩的缅怀和尊崇之情。因此,不能把黄帝的祭祀看成是汉族人对自己祖先的祭祀,当代祭祀的黄帝,不是一个血缘上的祖先,而是一种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既可以理解成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象征,也可以看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祭典所要表达和彰显的是“敬”,正是这种“敬”的意识贯穿了祭典的始终。通过祭典,无论是仪式的参与者还是观礼者,都进入典礼庄严肃穆的氛围,在祭典中得到灵魂的洗礼和思想的升华。
黄帝祭典除了上述功能以外,还具有展现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绩、增强海内外华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祭礼设计富有象征意义,如陕西黄陵和浙江缙云的黄帝祭典的击鼓,击鼓34咚,象征全国3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鸣钟9响,代表中华民族最高礼数,浙江缙云击鼓也黄陵一样,鸣钟则为15响,代表全世界15亿炎黄子孙。黄帝祭典的祭文,陕西黄陵、河南新郑、浙江缙云并不统一,而且没有固定格式,内容也不相同。不过,祭文除了表达追思以外,还展现了当代社会的建设成果,对于当代社会的展现,不仅是为了告慰“人文初祖”黄帝,同时亦具有现实功用。如陕西省黄陵县2002年清明节公祭黄帝祭文中说:“爰及当代,经济建设,纲举目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法制,民主兴邦;以德治国,刑仁俭让;中华振兴,蒸蒸日上。旋看花开南国,特区建设硕果累累;更听浪激北疆,西部开发众志昂昂。举国安定,尧天溢采;山川秀美,舜帝流芳。国逢盛世,民富小康;中国特色,港澳回归,一国两制携手并航;惟盼金瓯无缺,海峡子孙一脉炎黄。”在祭文中,不仅歌颂了当代取得的伟大成绩,还表达了今后的发展愿景和盼望海峡两岸统一的心声,祭文接着说:“展望全球,风云激荡,和平发展乃时代主流,富民强国系民族希望。强国为本,仍当抓紧机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富民为先,尤须面对挑战,落实三个代表思想。冀我全民,愿我全党,唯法是依,唯德是昌,反贪拒腐,清正贞刚,与时俱进,求新开创,五星红旗,万世永扬!”[18]这里无需再过多摘录祭文的内容,可以说,黄陵、新郑和缙云黄帝祭典的祭文内容尽管文字内容不同,但是其精神主旨是一致的,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祭典的现实功用。
三、黄帝祭典的设计原则和需要完善之处
综观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和浙江缙云三地的黄帝拜祭大典,可以看到,黄帝祭典逐渐规范。近年的祭典和早年相比,有了显著进步,从仪式上看,黄帝祭典属于古今、礼乐相结合的产物。黄陵、新郑和缙云都没有照搬古礼,体现了礼的损益原则,可以说,三地祭礼各具特色。不过,在参加了黄帝祭典以后,感觉祭典并非完美无缺,尚存在进一步完善空间。
第一,在祭典过程中如何更好体现参与性,需要祭典筹办和组织者进一步考虑。加强黄帝祭典的参与性,就是不能把方队代表或现场群众仅仅视为观礼者,方队代表一般是由社会各界的代表组成,到场群众人数一般也有限制,如何体现祭典的广泛有序参与性,需要纳入筹办者考虑范围。对于有的地方的祭祀方队,需要加强组织和管理,在祭典正式开始半小时前就应该到达指定位置,排好队伍。尽管在直播的时候方队不是重点,并不需要全时呈现在画面当中,但是在现场的人却能感受这种无序。除了祭祀方队外,还有到现场的群众,陕西黄帝陵一般是通过手拉手的人墙把祭祀方队和观礼群众隔开。前些年的黄陵祭典,是在祭典结束后才让群众进入轩辕庙,所以现场秩序较好,近年为了更好体现祭祀黄帝的广泛性,没有错时安排祭祀方队和当地群众的进入,由于祭祀方队人员从西安赶来,时间上不够充裕,在进入轩辕庙时已经是人山人海,祭祀方队的队形被冲散,到达祭祀地点时已经没有时间整齐队伍,给人一种无序之感。其他地方的祭祀也存在这种问题,由于沦为看客,现场随意走动、喧哗、拍照的现象普遍存在。浙江缙云曾有群众上香环节,但由于组织不善,效果也差强人意,环聚两边的观礼群众的秩序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二,要专门创作祭祀用乐,音乐要优美典雅、打动人心,力争创作出广泛流传的音乐作品。在祭祀用乐方面,近年陕西、河南公祭黄帝大典都曾设计过专门的音乐,这是值得肯定的,浙江缙云由于不是由省主办,在祭祀用乐等方面尚存在提高之处。许多祭祀用乐的设计,尽管表现和歌颂了黄帝的功绩,不过在音乐的构思上并没有更多考虑如何打动人心、把在现场之人真正带入祭祀仪式的氛围,如果从这些方面来衡量,各地祭祀用乐明显存在不足。当然,要达到上述效果,也许不只是音乐可以胜任,还需要考虑建筑、雕塑因素及其祭典各个环节的精益求精。虽说如此,也不能因此放松对祭祀用乐的要求,在祭祀过程中,音乐是决定祭祀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浙江缙云传说是黄帝飞升之地,其祭祀用乐曾经用过梵音歌曲,现场云雾缭绕,在音乐使用上随意性较强。
黄帝大典祭祀用乐从随意选择到创作专门用乐,这是黄帝祭典规范化的表现,我们常常把祭祀用乐称之为背景音乐,实际上就存在对祭祀用乐重视不够的问题。对于祭祀用乐的重要性,荀子《荀子·乐论》就曾有过论述,认为音乐能达到“感人深”“使人心庄”的目的[19],而这正是祭典所要达到的效果。张岂之指出:“在祭祀人文初祖的新礼中,一定要配合乐曲。乐曲是抒发人的感情,是心灵美化的艺术力量。世界上精致的、成熟的宗教,都有其独特感人的音乐做支撑。祭陵活动不是宗教活动,更不能离开优秀歌曲做铺垫。”[20]毫无疑问,优秀的音乐作品不仅能够提高祭祀的品位,而且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弘扬。
第三,黄帝祭祀中的乐舞献祭等与时俱进,提倡乐舞献祭穿现代服装。尽管黄陵、新郑、缙云的黄帝祭典先后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或扩展名录,毕竟黄帝祭典并不是古礼在当代的延续,因此,没必要在祭典设计上过多考虑古礼古乐。礼的根本原则是因时损益,所以在中国古代,每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往往都要制礼作乐,不同的时代理应有不同时代之礼。黄帝公祭基本采用了穿现代服装祭祀,古装仅仅保留在乐舞献祭部分,有无必要一定使用古式旌旗幢幡和服装,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不过,既然采用了现代服装祭祀,就有必要一改彻底,使祭祀体现时代特点,不然,难免给人一种时空穿越之感。
在公祭活动中,有的地方不能正确对待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的服装,祭祀中过于强调汉服,这种做法有些不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服装,不同时期各有特点,先秦服装古朴敦厚、秦汉服装雄健庄重、隋唐服装华丽清新、宋代服装质朴典雅、明朝服装繁丽华美和清新纤巧、现代服装洒脱开放与自由前卫等,一个时代的服装是政治结构、经济制度和社会风尚的反映[21]。虽然平原生活的人对山新奇,看惯了高楼大厦的人偏爱古代建筑,今人对于古代的服装难免会有所偏爱,只不过服装的变迁有其时代的合理性,现代的新服装,如借鉴了古代服装元素的现代服装,没必要称之为新汉服,可以归到现代服装的行列。众所周知,出于节俭办祭典的目的,许多地方的乐舞献祭者服装往往是循环使用的,循环使用总比租用服装要好,市场上有的古装由于质量低劣,毫无档次,实在影响祭典效果。不过,为了更好体现时代性,乐舞献祭者的服装还是穿现代服装为好,因为这是当代的黄帝祭祀,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祭祀方式。
另外,撰写的黄帝祭文要不拘一格,鼓励创新,创作出引起共鸣的优秀祭文。从创作的黄帝祭典祭文看,一般不采用现代演讲文体格式,而采用四字一句的《诗经》体,或不拘体例,由于讲求对仗,读起来铿锵有力,富有气势。从众多成功之作看,往往不囿于某种固定模式,古代祭文语言形式千变万化,“或用韵,或无韵;或骚体,或骈体;或四言,或五言,或六言,或杂言,可谓千姿百态”[22]。为了提高祭文质量,祭祀大典祭文有时请专人撰写,或者向海内外公开征集,都是值得提倡的做法。刘勰曾提出应用文“或全任质素,或杂用文绮”[23],考虑到恭读的祭文不太适合书面书言,必须考虑祭文的可理解性,让听众不知所云的一篇祭文,不利于有效交流情感和宣传鼓动,也难以引起公众共鸣。
四、结语
陕西省黄陵、河南省新郑和浙江省缙云的黄帝公祭大典,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完善,日益走向规范化,与三地的民祭相比,更好地体现了文明新风尚,彰显了祭祀的“志意思慕之情”,是值得肯定的。从黄陵、新郑和缙云三地黄帝祭典的历史和现状看,陕西省黄陵县的黄帝大典不仅历史悠久、起步早、规格高,而且具有其他地方祭祀所无法比拟的优势。陵庙一体的墓制,保存较好的历代祭祀遗迹,以及“黄帝死,葬桥山”的历史记载,使得陕西黄陵县成为闻名海内外的拜谒始祖之地。
河南新郑因为历史上黄帝居有熊的记载,被称之为黄帝故里,自1992年以来,黄帝故里拜谒大典逐渐办出了影响,成为中国北方地区黄帝祭祀的中心之一。浙江缙云的鼎湖山,传说是黄帝飞升之地,缙云黄帝祭祀采用一年两祭方式,其中每年九月九日的重阳节祭祀属于公祭,是中国南方地区祭祀黄帝的中心。
在中国古代,对于黄帝是没有争议的,古史辨派兴起以后,其疑古观点使得一部分人在思想上陷入迷茫。有的学者认为将来的考古学也不能完全证明传说时代,如果既不能证有又不能证无,那么武断地认为传说时代的东西都不可信、把传说人物都归结为神,这种认识逻辑未免不妥。不过,令人欣慰地看到,山西的陶寺遗址尽管没有文字资料,学界却在其归属上达成了广泛共识,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没有文字,包括黄帝在内的古史传说决不是面壁虚造,其包含的真实素材会被越来越多的认识。
就黄帝祭祀大典而言,不同于对血缘祖先的祭祀,黄帝作为“人文初祖”受到当代人的祭祀,既有慎终追远、缅怀先祖的原因,更有着促进海峡两岸早日一统的美好愿景。黄帝祭祀大典经过多年的发展,仪程日益规范和固定化,但在祭祀用乐、乐舞献祭者服装和祭文撰写方面都有进一步完善空间。在黄帝祭祀上,没必要过多拘泥于古礼古乐,只有建立符合时代特点的祭典礼仪,才能更好地发挥黄帝祭祀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 许嘉璐.把拜祭黄帝上升为国家级拜祭[N].光明日报,2015-09-07(16).
[4] 李学勤.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特点[N].光明日报,2015-09-07(16).
[5] 李伯谦.拜祭黄帝要达成共识[N].光明日报,2015-09-07(16).
[6] 刘庆柱.国祭也是祭国[N].光明日报,2015-09-07(16).
[7] 许嘉璐.国家拜祭的力量[N].光明日报,2015-11-09(16).
[8] 方光华.对黄帝的国家祭奠到底应该在哪里[J].华夏文化,2015(4):4-5.
[9] 李桂民.“古不墓祭”再思考[N].光明日报,2016-07-11(16).
[10] 李桂民.黄帝史实与崇拜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1] 贾艳红.上巳节考论[M].齐鲁学刊,2015(1):59-63.
[12] 陈希亮.《辛亥革命后的黄帝纪年》指误[J].南京社会科学,2006(4):78-80.
[13] 赵世超.黄帝陵所在地之我见[M].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5,23.
[1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5] 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16] 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仪式和社会”论文集[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7] 韩湖初.我国古代“九”“五”的丰富文化意蕴——并谈皇帝为什么又称“九五之尊”[J].湘南学院学报,2014(1):33-37.
[18] 刘宝才,何炳武.黄帝陵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19]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0] 张岂之.心祭重于形祭[C]//黄帝陵基金会.黄帝祭祀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1-5.
[21] 王鸣.中国服装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22] 莫恒全.应用写作并不一概拒绝文学手法——刘勰哀祭文写作理论的启示[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21-125.
[23] 刘勰.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