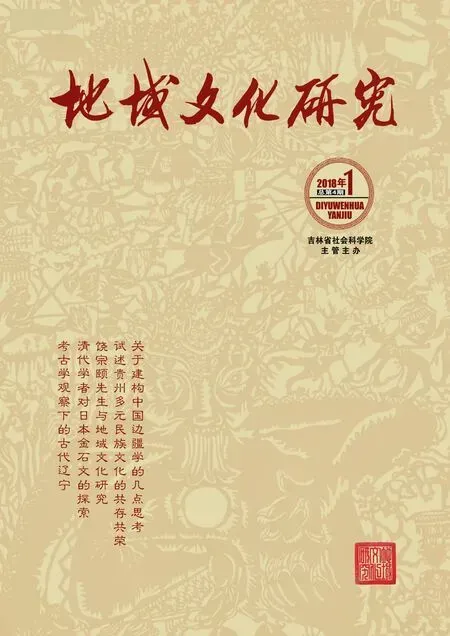钱山漾文化与“徐中舒之问”
李学功
2016丙申年,对于钱山漾文化而言,是一个颇不寻常的年份。它既是新中国建立后浙江省文管会对钱山漾遗址(图一)进行首次系统、科学考古发掘60周年,也是钱山漾文化的发现者慎微之先生诞辰120周年。为此,中国先秦史学会在南太湖之畔的钱山漾文化发现地——浙江省湖州市,与湖州师范学院联袂举办了“首届‘丝绸之源·太湖文明’全国学术研讨会”以为纪念。1934年,青年学者慎微之①按,慎微之先生在发现钱山漾文化后,对文物考古痴心未改,自1955年至1971年间,遍访吴兴范围内的文物遗存,曾写下多达10万字的考古日记,当地乡民喻之为“拎竹篮子的石头博士”。在其家乡浙江潞村第一次采集到石刀、石锛、石镰、石镞等石器“共300余件”②慎微之:《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吴越文化论丛》,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221页。,由此揭开了钱山漾文化的神秘面纱。

图一 钱山漾遗址鸟瞰
说到钱山漾文化,不能不提及1958年绢片、丝带、丝线的发现。此亦说明湖州与丝绸有着特殊的缘分。从唐宋的贡丝,到有清一代皇帝的龙袍,从首届伦敦世博会金奖的“辑里湖丝”,到以湖商“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①按,以“象”“牛”“狗”,乃至“虎”“羊”名状的富商之家,晚清之时颇流行于江浙一带,而尤以浙江南浔所传民谚为胜。朱从亮《南浔文献新志纪余》引徐珂《可言》有谓:“南浔镇之丝商,同光之繁富,甲于浙中,数富室者有‘五虎、六羊、八牯牛、七十二只焦黄狗’之喻”。参见《南浔文献新志纪馀》(未刊本)2001年,第53页。关于“象、牛、狗”的资产评判标准,较权威的说法约略有二:一、刘大钧、李植泉《吴兴农村经济》谓,100万以上为象,50万以上不超过百万为牛,30万以上不超过50万为狗。参见林黎元《南浔史略(初稿)》,上海:文瑞印书馆,1939年,第124页;二、据民国时期曾担任南浔中学校长的林黎元先生的看法,资产500万以上为象,100万以上为牛,10万以上为狗。参见林黎元《南浔史略(初稿)》(未刊本)卷5。为代表的丝业帝国,丝绸在湖州的文化和产业历史上曾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湖州因丝而兴盛,在中国古代及至近代的丝路贸易活动中,作为丝绸原料的重要产地,堪谓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由此出发,研究探讨钱山漾丝绸文化自有着不同一般的凡响和意义。
寻检钱山漾文化从发现到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80多年的历程,不难看出,学界对钱山漾文化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
一、发现、认识与命名
钱山漾遗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城南7公里的一座古村落——潞村。这里位于太湖流域的冲积平原,河道密布,是典型的江南水乡。1934年,任教于沪江大学的慎微之暑期回乡,时值大旱,钱山漾水位落至1857年以来之最低点,有三分之二面积干涸见底。于是慎微之“乘此良机,冒暑拾集石器,不经发掘,即能获得大量石器”②慎微之:《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吴越文化论丛》,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218页。。所得石器,“经考古学家苏惠培氏、安特荪博士、格拉汉博士、张凤博士及卫聚贤先生等加以鉴定……就时代言之,有属于旧石器时代者,有属于新石器时代者”③慎微之:《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吴越文化论丛》,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222页。。1937年,慎微之将研究心得——《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一文刊布于《吴越文化论丛》。在是文中,他一面批判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一面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学术判断:第一,钱山漾遗址处于旧石器时代;第二,提出了人类进化中的“湖州人”假说;第三,中国文化起于东南江海之交。④慎微之:《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源》,《吴越文化论丛》,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224、231、232页。
今天来看慎微之先生的认识和判断,有着历史和时代因素的局限,但其对江南上古历史与文化的重新认识,确乎具有先行者的卓识与洞见。众所周知,中华文明起源于“满天星斗说”如今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不唯如此,随着浙江境内上山遗址、跨湖桥遗址、河姆渡遗址、马家浜遗址、菘泽遗址、良渚遗址、钱山漾遗址等的发现,江南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面貌和地位,亦逐渐为世人所认知和重估。
就钱山漾文化而言,1956年开始的发掘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自此,钱山漾遗址考古步入了系统、科学的发掘阶段。这一次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在遗址的南北两端共挖探方10个,发掘面积390.5㎡。对于中国丝绸文明的历史而言,1958年则更是值得铭记的时刻。1958年2月至3月,考古工作者在钱山漾遗址的北部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共挖探方13个,总面积为341㎡。正是在这次发掘中,发现了一批盛在竹筐内的丝织品,包括绢片、丝带和丝线等。据《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第二次发掘时,在探坑22出土不少丝麻织品。麻织品有麻布残片、细麻绳。丝织品有绢片、丝带(图二)、丝线等。大部分都保存在一个竹筐里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经浙江省纺织科学研究所和浙江丝绸工学院多次验证鉴定,原料是家蚕丝,绢片是“由长茧丝不加捻并合成丝线做经纬线,交织而成的平纹织物”,“证实钱山漾出土的丝织物是由桑蚕丝原料织成的”。②浙江丝绸工学院徐辉等:《对钱山漾出土丝织品的验证》,《丝绸》1981年第2期。

图二 2005年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出土的丝带
对钱山漾的考古发现,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一文中提到:
就纺织技术来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Bombyxmori)和织造丝绸的国家,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据说发现了一个“半割”的蚕茧,“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后来有许多人便认为这证明当时已有了养蚕业。其实,这个发现是很靠不住的,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根据我们的发掘经验,在华北黄土地带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层中,蚕丝这种质料的东西是不可能保存得那么完好的;而新石器时代又有什么锋利的刃器可以剪割或切割蚕茧,并且使之有“极平直”的边缘呢?如果说是蚕蛾钻穿所致,但蚕蛾钻出前要分泌一种淡黄色的液体以溶解丝胶,茧上留有痕迹,极易识别,也不会形成“极平直”的割痕。因此,我们不能根据这个靠不住的“孤证”来断定仰韶文化已有养蚕业。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一批盛在竹筐中的丝织品,包括绢片、丝带和丝线等。经鉴定,原料是家蚕丝,绢片是平纹组织,经纬密度每厘米48根。这遗址紧靠河流,文化层深处低于水平面,夹杂有断断续续的灰白色淤土,所以动植物纤维容易保存。③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
众所周知,关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是否出现养蚕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翻检曾主持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工作的李济先生当年所撰之《西阴村发掘》报告,可以看到李济先生的严谨和审慎。对西阴村发现的“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李济先生称之为“最有趣的一个发现”④李济:《西阴村发掘》,《李济文集》卷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8页。,但亦认为:“假如我们根据这个性质未十分定的一个孤证来推定中国新石器时代蚕业的存在,我们就未免近于‘妄’了。”①李济:《西阴村发掘》,《李济文集》卷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
迄至20世纪80年代,夏鼐先生《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一文中继续坚持了“中国最早的丝织品,是1958年在浙江省吴兴县钱山漾遗址中所发现的……丝织品、绢片丝带”②夏鼐:《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8页、第70页注①。这一认识。
考上古夏商周早期国家的历史,史籍文献谈到当时的贡赋之法,曾有“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③《孟子·滕文公上》,《诸子集成》(1),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197页。的说法。翻检《尚书·禹贡》亦有“震泽底(致)定……厥贡……厥篚织贝”的记载。按,“篚”“匪”之义,《说文》解作“筐”。《广韵》释作竹器。方曰“筐”,圆曰“篚”。由史籍记载观诸考古发现,显然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织品盛在竹筐之中,可谓文献有据,渊源有自。
随着学界对钱山漾遗址内涵认识的渐趋深化,2005年和2008年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联合湖州市博物馆对钱山漾遗址先后进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发掘。这两次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明确了钱山漾遗址的年代晚于良渚文化。不唯如此,2005年3月至6月考古工作者在钱山漾遗址的第三次发掘中,在编号为H108的灰坑内首次发现了时间上属于马桥文化层的丝带,在编号为T0901、T0902、T0903的剖面第9层发现了钱山漾文化一期的麻葛类编织物和较多竹编物④丁品等:《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5日,第1版;丁品:《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7期。。
我们知道,学术界对钱山漾遗址及其文化属性的认识,是伴随着考古工作和文献解读工作中认识的不断深化而逐步解惑释疑的。这从慎微之对钱山漾遗址的旧石器时代判断,到钱山漾遗址为良渚文化的认识;从重新认知钱山漾遗址内涵的独特性到提出良渚文化钱山漾类型;再到分析厘辨钱山漾文化属性⑤按,钱山漾遗址出土的鱼鳍足鼎有别于良渚文化,系该文化具有标识意义的器物。,进而提出钱山漾文化新概念。一种科学求真、理性思考的精神始终贯穿其间。2006年,考古学家张忠培在“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上即提出钱山漾一期文化可正式名之为“钱山漾文化”。⑥张忠培:《解惑与求真——在“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的讲话》,《南方文物》2006(4)。2014年,在“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暨钱山漾遗址学术研讨会”上,张忠培、李伯谦等与会专家学者再次确认了关于“钱山漾文化”的看法,认为“钱山漾一期文化遗存”作为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已经比较清晰,文化面貌独特并有充分的考古地层学证据,将“钱山漾一期文化遗存”名之为“钱山漾文化”可谓实至名归⑦丁品:《钱山漾遗址与钱山漾文化》,参见浙江文物网电子刊物《浙江文物》2014年第6期。。
二、“徐中舒之问”与太湖文明再认识
论及越文化,一般总不脱春秋时代的越国,诸多史家并视浙江绍兴为越文化的“龙兴之地”。关于越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人也多视越为“断发文身”的荒服之地。史学宗师徐中舒先生曾有一问:“要是吴越的文化真很低,怎么能骤然兴起并与中原争霸呢?”要回答徐中舒之问,必须借重考古新发现与研究的新成果。不妨这样说,太湖流域之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钱山漾文化皆可视作先越文化,是越文化的“龙兴”源头所在,并奠立了越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过去,人们一谈及湖州所处之浙西(钱塘江以西地区,今指浙北),常谓为“吴根越角”,其实就早期历史的实相而言,称“越根吴角”似更恰切。就此出发,钱山漾文化确乎值得再探讨、再认识。
翻检《左传》《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有一个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即春秋间吴与越的冲突、交战主要是沿太湖一线展开,如发生在前510年、前496年的两次檇李之战和前494年的夫椒之战(一称五湖之战)、前478年的笠泽之战等。檇李即今浙江嘉兴西南,五湖即太湖,夫椒即今太湖中之洞庭山,笠泽在今江苏吴江一带。说明有“五湖”之称的太湖,当是春秋时期吴越交兵所在,南太湖流域当属越的势力范围。如此,亦可看出,曾以太湖流域为核心带的先越区域文化——钱山漾文化,在其形成、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与良渚文化等确乎充当了涵化、孕育越文化的母体角色,从而使得太湖流域成为越文化的滥觞、龙兴之地。
《国语·越语上》载:
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今绍兴诸暨),北至于御儿(今嘉兴桐乡),东至于鄞(今宁波鄞县),西至于姑蔑(今衢州龙游)。①《国语·越语上》,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70页。
由此不难看出,越文化初兴地确在浙江北部太湖以南流域,并与钱山漾文化(图三)之核心带正相吻合。对此,著名历史学家童书业先生则有着更进一步的“大胆”推断:
《左氏》哀元年传云:“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夫椒为今太湖中山(《越语下》:“战于五湖,不胜,棲于会稽。”“五湖”即太湖,则夫椒为太湖中山当可信),所谓“五湖”,盖即吴越之交界。越败于夫椒而吴遂得入越都,则越都必离太湖不远,不当在今绍兴。……(自楚灭越后,越裔南迁,故有越都绍兴之说)。……越都固在太湖流域。②童书业:《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1、232、234页。
童书业先生上述关于越都所在的议论,确乎是个大胆的推断。这是因为,无论《史记》《越绝书》还是《吴越春秋》等均言越都在绍兴。对此,童先生亦言,自己的说法,“还是证据甚不够之假定”③童书业:《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4页。。童先生对越都之所而发的议论,仍有待考古发掘的进一步说明。在此,笔者所关注的是,童先生对吴越地理区域的探究。为方便讨论,不妨再引述如下:

图三 钱山漾遗址地理位置图
我读《国语·吴语》而发生怀疑,《吴语》载越王勾践袭吴之役云:“吴王夫差……会晋公午于黄池,于是越王勾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沂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勾践乃率中军沂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说“沂淮以绝吴路”,“沂江以袭吴”,察其辞意,似吴都在淮南长江之附近,不然,何以用师辽远如此?……我又读《越语》,云:“夫吴之与越也,仇雠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上)“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下)则吴越“三江环之”,均为临近太湖之国。……我们的假定,春秋末吴都江北扬州附近,越在太湖流域。①童书业:《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0页、第231页、第233页。
童先生对吴越区位的思考,对我们启示良多②实际上,即便是吴之所在,学界也有颇为不同的认识。如对周之太伯奔吴,也有东吴、西吴、北吴等不同说法。参见叶文宪《吴国历史与吴文化探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8页。。联系到良渚文化和钱山漾文化等文化的地理分布,颇有意趣。目今所见,以良渚文化论,其分布的范围北抵江苏的扬州、海安一带,南入浙江的宁(波)绍(兴)平原,东及舟山群岛,西达江苏的宁(南京)镇(江)地区,其中心区域主要在太湖流域③林华东:《浙江史前文化的两朵金花——河姆渡和良渚文化》,《文史知识》1996年第10期;并见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0页。安志敏先生在为《良渚文化研究》所作序中认为,良渚文化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南限迄于浙南,东到海滨并远达舟山群岛,同时还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江西、广东的若干史前遗存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对于良渚文化分布的范围,也有学者表达出不同认识,如认为宁绍平原不属于良渚文化范畴,认为宁镇地区的史前文化第四期属于江南新石器文化区系等。参见牟永抗《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魏正谨《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与分期》,《考古》1983年第3期。。考古发现之良渚文化活动半径与童先生所论之吴越,特别是越的活动范围大致契合。2003年至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浙北长兴鼻子山、安吉龙山均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越国贵族大墓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2005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安吉笔架山发现了颇为密集的春秋战国越人古墓群及一座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城遗址。这些发现可以说是继绍兴印山越国王陵之后浙江越文化考古新的重要成果。其中,长兴鼻子山“墓外陪葬器物坑的发现在浙江尚属首次,是越国墓葬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与突破”⑤陈元甫:《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新纪元》,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7页。。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大墓,其木椁“在形制上与绍兴印山越国王陵木椁相同”⑥陈元甫:《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新纪元》,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不唯如此,2007年,考古工作者对德清火烧山原始青瓷窑址的发掘,揭示出这是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纯烧原始青瓷的窑址。窑址“出土了大批包括卣、鼎、簋在内的仿青铜礼器产品,为江南大型土墩墓随葬的同类器物找到了原产地”⑦曹锦炎:《〈浙江考古新纪元〉导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新纪元》,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愚以为,德清窑仿青铜礼器产品的发现和太湖流域越人石室土墩墓⑧据叶文宪先生分析,石室土墩墓可看作是越人、越文化颇具典型意义的特征。在德清独仓山与南王山,考古工作者发现有6座石室土墩墓。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独仓山与南王山》,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等墓葬的发现,正在一步步揭开太湖流域与越文化崛起关系之谜。上述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浙北太湖流域是越文化萌蘖之根系所在。如此,将钱山漾文化、良渚文化等视作先越文化,在地域范围上应无大的问题。
当然,沿着童先生之说所启示的方向思考,并不意味着童先生所提出的假说没有问题。问题之一,如果说吴都在江北,那么其与无锡发现的阖闾故城、苏州乃吴之姑苏所在等问题如何释解、圆通?这需要进一步的历史文献与实证资料的解读,以说明曾经发生的人口与文化的传播、流动及其带来的文化记忆的变迁;问题之二,考古界对春秋战国及其前后时段的发掘更多的尚处于“点”的解剖,若想复原先秦时代这一区域的整体面貌仍需假以更多的时日,而且这个问题的解决,其本身就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面向理想的现实魔方。
笔者浅见,包括钱山漾文化在内的先越文化存在一个与其他文化的此消彼长以及相对疏离、渐趋聚合的状态与阶段。钱山漾文化的延展和后来在太湖之地的逐渐消遁,既反映出黄河流域文化对淮河、长江流域文化的扩张、影响,也表明吴文化与越文化的碰撞、交集及越地文化在族的迁徙和文化传播浪潮中的形态嬗变。①在笔者看来吴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当更深,印迹亦更为明显。而这也恰恰说明华夏文明的形成,确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远古时代族群的分分合合,各地方文化的差异离合,当是一种常态②说到区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离合”问题,早期巴蜀文化与中国的两大河——长江、黄河流域主流文化的疏离较为明显,且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离”的文化差异性特征。春秋战国以降,巴蜀文化开始步入文化整合的过渡时期,其文化特征才较多地显示出与中原文化、楚文化等“合”的一面。而吴越文化则与巴蜀文化不同,其“合”的成分与意识相对较浓。限于篇幅,这里只交待一下观点,待另文论之。。当然,无论怎样改变,区域文化的基本精神却仍如屈原“九歌”中的魂魄一般,“虽九死其犹未悔”。众所周知,越文化以好剑轻死、厥性轻扬而著称。《越绝书》即称:“锐兵任死,越之常性”③《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8页。。明《(万历)湖州府志》引《晋志》云:“江南气劲,厥性轻扬”。及至东汉末、三国争雄时,世人谈及江南之地仍谓之:“江南精兵,北土所难,欲以十卒当东一人”。凡此,亦说明时空的跨越消解不了文化的生命力,区域文化的耐应力和持续张力远比人们想象的顽强得多和复杂得多。
综上所论,尽管在钱山漾文化的认知上,史学与考古学互有歧见,尽管对越文化初兴地的认识也还只是一个开始,但并不妨碍历史学借鉴考古学的成果构建新的古史体系,不妨碍我们将钱山漾文化遗址目作先越部族时代重要的文化聚落群,不妨碍史学放宽研究的视野去找寻越文化在历史的原野留下的芳迹和支点。事实是,在今天想要探究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时代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只能根据考古发现进行研究,而考古学确乎“有能力研究发生在数百年或数千年前的历史过程,以重现并检验某一时刻曾存在于世上但现在已消失了的各种文化类型的全貌”④乔纳森·哈斯:《史前国家的演进》,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5页。。一如王家范先生所论:“考古事业的大发展,使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古书里提到的‘方国’或‘方邦’,正从地底慢慢涌出”⑤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32页。。而钱山漾文化无疑正是一个文明破晓前夜“从地底慢慢涌出”的部族时代丝绸文明的突出代表,太湖流域无疑应视作越文化初起、勃兴的重要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