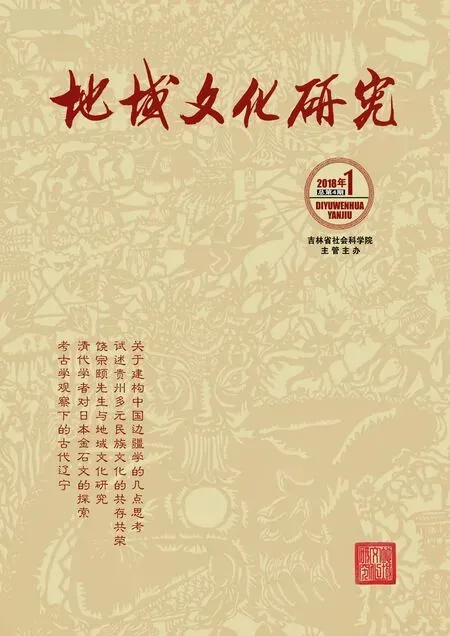“张献忠与四川”史籍鉴析
胡昭曦
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2016年度至2017年度考古发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给历史研究以很大的帮助和启迪,特别是为明代社会历史、“张献忠与四川”等史实的相互印证和综合研究,提供了数量巨大、品类多样的实物资料,有助于对有关历史文献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辨析、考证与鉴别。笔者拟将近年来“张献忠与四川”研究引用较多的历史文献加以鉴析,俾能同考古资料更好结合,以求历史真实。
一、近年来引用较多的历史文献
近年来,“张献忠与四川”研究引用较多的历史文献中,有一书名标为《张献忠剿四川实录》的汇编校点本(以下简称校点本),包括《张献忠陷庐州记》《滟滪囊》《蜀难叙略》《蜀碧》《蜀警录》《蜀龟鉴》《蜀破镜》《荒书》八种书(其中七本书见下表)。对此校点本,一种意见认为,汇集了一些有助研究的史籍,应当对其内容仔细分析,认真考订,以证史实;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些书是“较为可靠的原始资料”,属于“实录”。①该书把一些史籍集中汇编,加以校点出版,给读者带来方便,故引用者较多;而其书名“实录”,也使有的读者把它们看作实录而加以引用。例如有著述写道:这些书“作者都是亲历了明末清初四川战乱的当事人,其纪事本于亲历见闻,应视为较为可靠的原始资料。这些实录都记载了张献忠肆意杀人、焚毀成都城市的暴行”。

表1 有关记叙张献忠在四川活动的七本书概况表①②
上列各书,被称之为野史,③校点本所选各书均据丛书《中国野史集成》(《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编,缪钺、胡昭曦、林万清主编,陈力常务副主编)第29—30册,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影印版;《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22册,巴蜀书社2000年影印版;校点本《中国野史集粹》(陈力主编)第2册,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传统四部分类大都属史部杂史。从编纂情况而言,表列七本书大体可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作者的亲历与见闻。《蜀难叙略》《荒书》《蜀警录》属此类。
崇祯十五年(1642),太仓(今属江苏苏州)人沈荀蔚随赴任华阳县令的父亲沈云祚到四川。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其父被张献忠农民军执杀于成都,“荀蔚方八岁,与母、妹及舅张仕伟逃匿邛州、洪雅山谷间,数遭劫夺。至雅州,父友监军道范文苂见而怜之,送居乾坝,而檄士伟署洪雅县事。未几士伟卒,土酋葛祐明作乱,复入八面山中潜匿不出”。到顺治十二年(1655)前后,沈荀蔚(时年约十八九岁)“以眉州籍应试补诸生”。他自八岁至十八九岁随全家逃匿于川西南山谷间约10年以上,乃“于帖括之暇,或追惟(忆)往事,或搜集遣闻(蒐集遗闻)”,④本文所引七本书所据皆自校点本。校点本底本皆影印古籍,然在整理排印中,于变换字体、版式和标点时还存在少数问题,笔者在这些地方用其他版本核校并用圆括号标注,供读者并参。查乾隆道光间长塘鲍氏刻本(中国丛书库),“追惟往事”作“追忆往事”;此本及《中国野史集成》底本“搜集遣闻”,作“蒐集遗闻”。期于可信,咸笔之于书。“自兹以后,凡耳目所及,日附益之……总目之曰《蜀难叙略》。”⑤沈荀蔚:《蜀难叙略》引言;同治《苏州府志》卷112《流寓·沈荀蔚》;民国《吴县志》第76上。
《荒书》作者是新繁(今属四川新都)人费密。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军陷成都(费密时年20岁①同治《新繁县志》卷11《文苑·费密传》。),顺治二年(1645)费密从家中出走,辗转于彭县山中,又在什邡高定关组织武装抗击张献忠军,然后只身去云南,探望任昆明县知县的父亲费经虞并将其接回。途中,被镇守嘉定(今四川乐山)的明将杨展任用为中书舍人、都御史,顺治五年(1648)屯田于荥经瓦屋山。顺治九年(1652),“归新繁,旧宅已为灰烬,乃北行至陕西沔县,因家焉”。后奉父至扬州“卜居野田村,闭户著书”。②民国《新繁县志》卷8《费密传》。他从顺治二年(1645)至九年(1652)的七八年间,辗转于川西山中和川滇道上,《荒书》是他“就愚闻见,采而纪之”③费密:《荒书·自序》。的著作。
《蜀警录》(原名《纪乱》《蜀乱》,又名《欧阳氏遗书》)。约于康熙八年(1669)成书。④刘景伯:《蜀龟鉴》卷7《明兵部郎中欧阳直传》。作者欧阳直(1620—?),⑤欧阳直:《蜀警录》云,“余生于万历四十八年”,即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有文章说其生年为1621年,此从《蜀警录》所记。广安州(今四川广安)人,⑥据《蜀龟鉴·明兵部郎中欧阳直传》。民国《乐山县志》卷11下称“渠县人”,或因幼时由其嫂傅氏“携归宕渠母家养之,十七岁回原籍”(《蜀警录·自纪》);嘉庆《四川通志》卷184《经籍志》作“嘉定州人”,或因作过南明嘉定知县,后入杨展幕,乃流寓嘉州(今四川乐山)。崇祯十五年(1642)22岁时补郡庠生。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军入蜀,被执,在骁骑营受“检验”,曾被“发光禄寺给养”,“历七月而三易”。顺治二年(1645)三月,营将刘进忠叛献,走秦陇,“乃乘间计脱归……尽括诸藏蓄浮家东下”⑦《蜀龟鉴·凡例》说,欧阳直“以顺治三年被俘献营三年,献诛乃得逸”不确。在张献忠军营实为七个月,即自崇祯十七年(1644)七、八月至次年三月。。途中又被执于摇天动、黄龙武装,辗转营中二年,复乘机逃至定远(今武胜),明将曾英置之幕中,旋授安居令。顺治四年(1647)二月,被清军俘,置为椽曹,数月后脱去,“窜匿荆棘间”。夏,至嘉定,入明将杨展幕中。顺治八年(1651)刘文秀率军取川,召直供事中书科,随营入滇,历礼部主事、兵部郎中、翰林院检讨等职。清兵入滇,南明亡。直从此以馆为家,教书著述为业。⑧《蜀警录·自纪》。从其经历看,欧阳直在张献忠军骁骑营七个月;逃出后被执于摇黄部历时两年,所记此前三年事多与张献忠直接相关,于成都较详。此后所记乃作者流徙川南、云南的经历以及张献忠余部、残明官员在云贵一带的活动,清军攻取川滇的简况等,有亲身经历,也有得自传闻。
这类书的共同特点是:第一,作者的父辈和家庭都被张献忠军直接打击,作者本人不同时段不同程度,亲身经历了明末清初四川地区的社会动乱,所记不乏亲历亲闻资料,包括张献忠军、摇黄武装、川滇南明军、吴三桂军攻四川、入川清军和地方武装等。第二,作者当时对所在地区的见闻的记述,较之转手再录者,有较多的第一手资料。第三,这些著述内容中还有大量传闻,纵使是亲历亲见,也存在局限。可见,这一类书虽是研究“张献忠与四川”的重要历史文献,但还不是“实录”,作者于此也说得很清楚,如费密在《荒书》引论所说:“一方大事,而杂书所纪,流传讹谬……道听途说,多没其实。询问当时在事故老,采各州郡实历舆论,阅岁既久,合取而著焉。然不敢尽谓全获也。未详与差错者,恐亦尚有,而大端则在此矣。”
第二类,采辑与编纂。《滟滪囊》《蜀碧》《蜀龟鉴》《蜀破镜》属此类。其共同主要特点如下。
(一)编者均非张献忠在四川时期的亲历者,成书时间迟。《滟滪囊》是明末清初通江人李馥荣编辑、康雍年间嘉川(今四川旺苍)人刘承莆(字尧草)做了大量参订,①《中国野史集成》底本双流黄氏济忠堂本。最后于雍正元年(1723)成书,距崇祯十七年(1644)已近80年。未见李馥荣亲历明末清初战乱的记载。《蜀碧》“编述”者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县)人彭遵泗,约出生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之后,②彭遵泗之兄彭端淑约生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则彭遵泗出生在此之后。乾隆二年(1737)进士。此书编成于乾隆十年(1745),距崇祯十七年(1644)已一百年。《蜀龟鉴》是四川内江人刘景伯辑。刘曾任新都教谕,③民国《内江县志》卷2《选举》、卷3《官达》。咸丰四年(1854)在新都学署中编成此书,④《蜀龟鉴·序》距崇祯十七年(1644)已210年。《蜀破镜》,署名孙錤撰。其“前言”又作“孙澍撰”。⑤参该书胡淦“前言”。孙錤,郫县(今成都郫都区)人。其弟孙澍,咸丰五年(1855)举人,曾任綦江县教谕,告归后,“与錤著书不辍”,兄弟共同辑刊《古棠书屋辑刊》(内收《蜀破镜》)。⑥孙钅其:《蜀破镜》胡淦“前言”;同治《郫县志》卷28《儒林》;杨钟义撰:《雪桥诗话三集》卷12。《蜀破镜》成书约在咸丰年间,距崇祯十七年(1644)亦已200年以上。
(二)采辑引录编纂而成,总体上不是第一手资料。这类书的篇幅均在约2万字以上,最多约7.5万字。
《滟滪囊》,约3.5万字。李馥荣撰,刘承莆补订。所记自崇祯四年(1631)⑦《滟滪囊》刘承莆《原序》说,“始崇祯六年,讫康熙二年”,检视內容记事,实起于“崇祯四年(1631)辛未”。用道光二十七年(1847)退思轩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校核。至康熙二十年(1681,刘补写了康熙六年至康熙二十年事),共51年事。先是李馥荣之子将此书稿托请刘承莆“笔削以公诸世”,并称“此先大人苦心数十年所采辑而成焉者”。刘“就其中记叙,采之风闻,或名实非据;得诸称述,或详略非宜”,“详加讨论,宛为修饰,务俾质而不俗,简而能该”。⑧刘承莆:《滟滪囊·原序》。全书共5卷,第1—4卷多为张献忠及摇天动、黄龙事,第五卷主要记吴三桂、王屏藩事,与张献忠无直接关系。卷尾、节尾加了一些“刘尧草曰”。
阿强天不怕地不怕,可就是怕狗怕得厉害,他说:“还是你自己牵出来吧。”不一会儿,狗就被牵了出来,男子再三表示歉意后牵着狼狗下了楼。阿强这才嘘了口气,他在门外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信封。他回到屋里,忽然见到桌上又是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阿强先生,这次我又偷了你的电视遥控器,三个回合我都赢了,看来你这个防盗大王也不过如此。江城神偷。”
《蜀碧》,约3万字,记事起崇祯元年(1628),讫康熙二年(1663),共约35年事。编者彭遵泗于《自序》写道,“余儿时稔闻遗老聚谈事。比长,博采群书并蜀乘所载当时忠臣烈士、节女义夫可印证者,汇为《蜀碧》一编”。该书记事多据旧述和传闻,收录了张献忠据蜀的记述,据卷首列出书目,其引录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纪本末》《绥寇纪略》《寄园寄所寄》《荒书》《蜀通志》《邛州志》《见闻录》等25种。卷1署题“丹溪生彭遵泗磬泉编述”。⑨用清道光中金山钱氏据借月山房汇钞刊版重编增刊本(中国丛书库)《蜀碧》校核。
《蜀龟鉴》,约7万字,仿《春秋》体例。起嘉靖三年(1524),至康熙二十年(1681)而止,共150余年。所涉地域包括许多省份,而重点在四川。辑书很多,编纂而成,编者写道,同辈遂劝予将《欧阳遗书》《滟滪囊》辑为一书,“爰遍阅诸纪”,包括《荒书》《蜀破镜》《蜀碧》《蜀难叙略》等,加以合并删润而成。①《蜀龟鉴·凡例》卷首署题“内江刘景伯石溪居士辑”。此书有大量的编者论说,在编年叙事的卷帙中,几乎每页都能看到编者系于某时某事的“论”“赞”,用以阐发编者观点、议论,也有少数补充资料或考辨、置问。此书实为一本编年史籍。
《蜀破镜》全书约2万字,起崇祯元年(1628),迄于康熙四年(1665),叙事共约37年,为编年体,分为5卷。卷1署题作“蜀郫孙錤野史述”。多采他书而成,主要是《荒书》《蜀碧》,还有《明史》《蜀明诗》《井蛙杂记》《毛西河文集》《明史稿》《绥寇纪略》《大清一统志》等,编者在“后序”中说:“予于暇日采甲申事表而出之”,胡淦“前言”云:“是书……详张献忠川西之乱,依据新繁费此度密《荒书》、丹棱彭磬泉《蜀碧》而成”。其内容叙事较略,多在系时叙事间表出人物简介,包括各方军队官兵、各地官吏、儒生及妇女等。
(三)对引用史料或采编故事基本不注出处,内容互证不确处亦多。四本书分别完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之后近80年、100年、210年、200年,均为辑编而成,但只见《蜀龟鉴》有很少数所引书名的夹注,且所注未详是否原文和所在卷帙。其他三书,则于个别行文或按语中偶见所据。《蜀碧》为作者综合直叙,其引书出注只见“《长祥记》”“《寄园寄圻(所)寄》”二处。《蜀破镜》卷3注引也只有10余条,多为短注,其中长者2条。至于各书之间或本书之内,亦存在不少内容牴悟、互证乏确和存疑待考之处。如《蜀碧》于顺治三年(1646)三月纪述:“贼分道捜杀四路遗民……蜀民于此真无孑遗矣”,又于当年十一月纪述:“或云,贼欲屠保宁府属,神僧破山为民请命。”“破山破戒尝噉犬豕肉,贼因免之”。
虽然上述两类史书都存在局限和一些问题,但其作者或编者倾注了很大的心力,保留下来不少有价值的资料,是我们研究“张献忠与四川”及相关历史问题的重要史籍,然而确乎不能视为“实录”。
所谓“实录”,即忠实的记录。讲求“直书”“信史”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直书”就是“实录”。班固写道:“自刘向、扬雄博览群书,皆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实录。”②《汉书》卷62《司马迁传·赞》。上列第一类书中,作者的亲历亲见和经过考证的确切史实,均属“直书”即“实录”范畴,但是大量内容皆采自传闻,且未作细考,所以《荒书》写道“不敢尽谓全获也。未详与差错者,恐亦尚有”。因此这类书就其整体而言,不好称为“实录”。至于第二类书,更不待言了。
我国史学著作中,实录是编年类体裁,其中以官修为主且形成制度。金毓黻先生写道:“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自汉以来更修起居注,以举记言记事之职……迨唐以后,则每帝崩殂后,必由继嗣之君敕修实录,沿为定例……实录之体,略如荀悦《汉纪》,为编年史之一种,即于一帝崩殂后,取其起居注、日录、时政记等记注之作,年经月纬,汇而成编。”③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5-96页、第100页。纵使是官修,且取记、注之材,然而因当时政局氛围、修纂者的政治见解与历史观的不同,同一皇帝的实录也会有很大区别,著者如《宋神宗实录》,由于当政者对熙丰变法(一般称王安石变法)的不同评价和派别对立,曾数次编修。宋哲宗时高太后行“元祐更化”,首修《宋神宗实录》(被称为墨本),借以诋毀新法,恢复旧制。哲宗亲政即“绍述新政”,欲复熙丰新法,乃重修《宋神宗实录》(用朱笔删添修改,称朱本)。宋高宗宣称“朕最爱元祐”,提倡恢复“祖宗之制”,又再次重修《宋神宗实录》。这就是李心传所谓:“此盖史官各以私意去取,指为报复之资”。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1,绍兴七年六月丙申。参见胡昭曦:《〈宋神宗实录〉及其朱墨本辑佚简论》,《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1期;收入《胡昭曦宋史论集》,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样,实录只是一种史体之称了,要讲求信史,还须再编,正如宋孝宗时史官李焘所说:“缘正史当据实录,又缘实录往往差误,史官自合旁采异闻,考验增损。”②《宋会要辑稿·职官》第6册18至5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校点本,第3508页。
二、有关记述须要细致辨析考订
以上七书,均为研究张献忠与四川的重要史籍,但由于所据纷繁复杂,取舍不一,仁智各见,须要细致辨析考订,以厘清史实,探求真相。试举二例。
(一)关于彭山江口沉银
“水锢”之称,《蜀难叙略》于顺治三年(1646)载:“其所聚金银,以千余人运之江干,三月始毕……于江底作大穴,投以金银,而杀运夫于上。后覆以土,仍决江流,复故道。”江干,未明指何江之干。《蜀碧》称之“锢金”,且明言在锦江,“将所余蜀府金银铸饼及瑶宝等物,用法移锦江,锢其流,穿穴数仞实之……名曰‘锢金’。”《蜀龟鉴》顺治三年五月同此载,并云:“测江水浅处开支流,如筑决河法,水涸掘大穴,投以木鞘,杀运夫而实以土,乃决江流,复故道。”《蜀破镜》则称为“水藏”,亦云在锦江,顺治三年(1646)八月“张献忠将前自江口败回所余蜀府金宝,用法移锦江,锢其流,穿穴数仞填之,下土石并凿工掩筑,然后决堤放流,名曰‘水藏’。”
彭山江口沉银。或云张献忠主动沉银,《荒书》载:顺治三年(1646)正月,“献忠尽括四川金银作鞘注。彭山县江[畔](口)③“彭山县江[畔]杨展先锋”,“畔”字为校点本补入,用方括号标出。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荒书》,文字为“彭山县江杨展先锋”,亦于“江”后缺字。“畔”字补作“口”字似更贴切。杨展先锋见贼焚舟,不知为金银也。其后渔人得之,展始取以养兵,故上南为饶。”《蜀警录》载:“金银山积,收齐装以本(木)鞘箱笼,载以数十巨舰,令水军都督押赴彭山之江口沉诸河。”④《蜀警录》顺治二年(1645)八月前纪事(八月张献忠弃成都北去),《中国野史集成》底本错刻“木”为“本”,迳改。《后鉴录》载:张献忠“命刘文秀捆数年所掠珍宝兼金,装巨舰百余,赴彭山县江口沉之,而歼驾船卒于水。后为杨展所泅取,以赈川南,即是物也。”或云张献忠兵败被焚舟沉银。《蜀龟鉴》载:顺治三年(1646)六月,“明副将杨展大败献于江口。献率劲兵十数万、金宝数千艘……展逆于彭山江口,纵火焚其舟……展取所遗金宝益军储,富强甲诸将。居民时于江口获木鞘全银。”《蜀破镜》于顺治三年(1646)载,“秋七月,张献忠闻杨展兵执甚盛,大惧,率兵三十余万,载金宝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胜负……展闻,以兵逆于彭山之江口,大战,顺风纵火烧贼舟无算,士卒辎重丧亡略尽,复奔还成都。”
又有记叙说沉银地点在新津江口。《蜀难叙略》:“其所聚金银……后续有所得,俱刳木成鞘,运至新津江口,载以千余艘,将为顺流,计至巫峡投之。”《蜀龟鉴》同此。《蜀难叙略》云:顺治三年(1646)“七月,逆以川北民未尽屠,且欲诱杀进忠,乃烧其财负(货)①《中国野史集成》底本此字上半部分缺,据长塘鲍氏刊本订补。舟楫于新津,拔营而北。”关于张献忠军撤向川北,《蜀碧》载:“献自江口败还,势不振。又闻王祥、曾英近资、简,决走川北。”②《蜀碧》卷3。
以上只是列举各书载叙淆混之一斑。它们记叙的不足和局限较多,或一事互异,或自相抵牾,或有不经之语,或存夸大之说,甚至所谈无稽。这就必须具客观史识,全面分析,仔细辨判,力求佐证,期达信实。
(二)关于张献忠军在四川杀人数
笔者与许多近人著述相同,认为张献忠军曾在四川杀人,而且存在扩大化等乱杀情况,被杀者数量亦大。然而对《明史》及有的史籍所载张献忠在四川“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之说持以否定,认为显系夸张甚至荒诞。长时间以来,不少著者也在辨析探究其杀人总数和有关问题,但尚无公认符合历史实际的结果。这又表明了对以上七书必须辨析考订。下面就本文所涉史籍所载列表于下。

表2 部分史籍所载张献忠军杀四川人数列表 单位:余万
毛奇龄(1623—1716)曾于康熙年间参加修纂《明史》,他曾在其著《后鉴录》中撰写张献忠生平事迹,此文对《明史·张献忠传》或有影响,二者有一些明显契同之处,《明史》所载“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或即参据《后鉴录》或冯甦《见闻随笔》。
关于“六万万”记载之荒诞,学界已有许多讨论,本文不赘。近见有著述另辟蹊径,用一种新的意见诠释《明史》“六万万”之说,即:“万万为亿的计数法,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确定下来,而此前古人的计数方法‘6万万’应为60万。”③转引自“今日头条”骊姐的人类学之眼:《一场关于张献忠屠蜀的大辩论,正反双方谁更靠谱?》,2017年4月15日。按此即指古人计数是以十万为亿。这种说法是论者鉴析史载的又一探索之举,但其稽据不全面,结论亦值得考虑。
《明史》所谓“万万”指的是什么数量?该书多次提到“万万”,如“万万岁”“万万世”“万万计”“万万里”“数万万”等,“六万万”之数或即毛奇龄记叙四路杀人总共69,948余万之约数。上列各书中,万、十万、百万、千万之区别和十进位计算法明显,四路总和为数万万,即数“亿”。这种区别和计算法在《明史》中是统一的,即“亿”乃由“千万”进位,如《历志》载:“气应……积三亿七千六百一十九万九千七百七十五分”,“转应……共得三亿七千六百三十二万九千九百八十分”。①(清)张廷玉:《明史》卷35《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86页。《明史》所谓“万万”,不是“十万”而是“亿”,则明白无疑。
所记张献忠军杀人“六万万”,明显荒诞,不足为据。要探求其确,殊多困难,然如上述多设方法,或可接近史实。也再次表明,对上述七书不可视为“实录”,必须多方考证仔细辨别,冀求得见历史之本来面目。
史观(史识)和原始资料(史底)是研究历史的两个最基本条件,重视原始资料,并加以鉴别考订,从中探索历史真相和文化内涵,是我国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蒙文通先生曾指出:“最直接的原始资料,这就是宋人叫的史底,是最可宝贵的东西”,“史料是构成历史的基石,而史料的来源则是多方面的……矛盾的材料,总须等到解决才可使用……许多野史记载的不同,都应当先研究作者是何种人,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解决了这些问题,才可以少些错误。总之,时代稍后的历史记载可信的成分就减少了一些,最初的史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②蒙文通:《从〈采石瓜洲毙亮记〉看宋代野史中的新闻报道》,《蒙文通全集》第2册《史学甄微》,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对于本文所涉七本史书,还需厘清资料的原始性、了解作者编者的写作意图、解释其引用和论述的矛盾处,充分发挥历史文献探索历史真相的作用。与此同时,还需着力搜集像《圣教入川记》《五马先生纪年》③1979年,笔者在位于成都市和平街的四川省图书馆古籍特藏部查阅资料时,承该部沙铭璞先生介绍,得见简阳人傅迪吉(1627—1696)撰写的《五马先生纪年》道光二年(1822)、光绪三年(1877)两个抄本,记录了他七十年的亲身经历(包括投附张献忠军)和见闻。在取得省图书馆同意后,经与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袁庭栋先生相商,将其与古洛东著《圣教入川记》(该书大量篇幅叙述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在张献忠军中的亲历与当时见闻),合为一书加以出版。笔者对此二书进行了标点校订,撰写了“出版说明”,并委托学生在重庆调查了古洛东和原印行此书的圣家书局情况。四川人民出版社由袁先生担任责任编辑于1981年4月出版。那样的“最初的史底”(同样须要细致辨析考订),以扩大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
进一步研究“张献忠与四川”的历史,要继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也要更加讲求研究方法。综合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要求史学工作者做好历史文献的考辨和相互印证,与此同时,将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社会调查和实地考察等相结合,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结合,拓展视野,扩充资料,进行多学科多方位多层次的综合研究,用经过辨析考订的多种证据弄清历史的真面目。④参见胡昭曦《综合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4日学术版。对上列七本历史著作的初步剖析,展示出现在张献忠研究文献方面,还要大力发掘新的资料和扩大资料面;而彭山江口沉银考古的硕果,为张献忠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将它们进行深入的综合研究,将会带来研究工作的新突破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