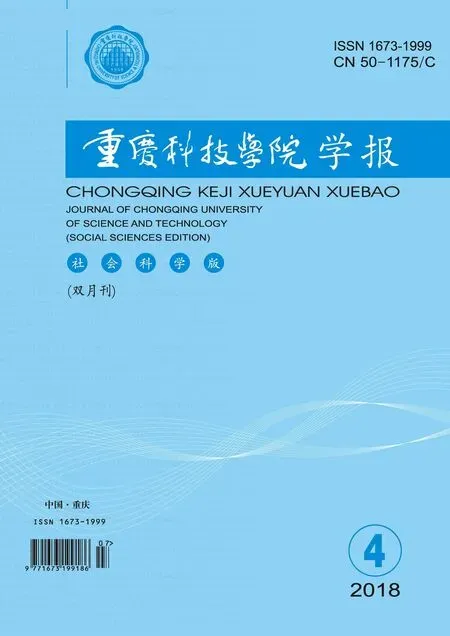论伦理学视域下的学校道德空间重构
程淑华
20世纪中期,米歇尔·福柯、亨利·列斐伏尔、齐格蒙特·鲍曼、安东尼·吉登斯等思想大师都从空间的角度研究社会问题,西方社会学研究开始了空间转向。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空间也成了道德研究的独特视角。从空间的角度看,道德空间是学校空间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学校道德空间是一个意义之域,它是学校成员的心灵安顿之所。我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伦理型社会。在伦理文化的浸润下,学校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道德空间。然而,随着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结构性转型,伦理日渐失落曾有的本真意义且有无序发展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校道德空间的弱化。
一、道德空间的涵义及价值
(一)道德空间的涵义
从哲学上看,道德没有自身独立存在的感性空间域(物理空间),而是存在或渗透于政治、经济等一切现实自由意志的实践领域。因此,严格来说并没有独立的道德空间,我们所能经验的仅是物理空间。人是社会性存在,所以人存在的物理空间又是个社会空间。人的活动具有认知、道德和审美3个基本向度,社会空间也由认知空间、美学空间和道德空间组成,三者相互交叠、相互作用。正如格奥尔格·齐美尔所言,空间从根本上讲只不过是心灵的一种活动,只不过是人类把本身不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感官意向结合为一些统一的观点的方式[1]。空间为人所创造,如果人的活动除认知和审美之外,还鲜明地具有道德的要素,就如同将道德作为填充物不断填入所存在的物理空间,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就具有道德的内涵,就有道德空间的存在。
从心理场论的解释范式来看,道德空间就是道德主体置身其中的价值场域。作为一个价值场域,道德空间中含有特定的伦理精神、善恶的评价标准以及具体的道德规范,它们维系着道德空间的存在。道德空间为道德主体所建构,也为道德主体而存在。不同的道德主体建构不同的道德空间。从规范伦理学角度来看,道德主体可以分为个体和社会。相应的,道德空间也可以分为个体道德空间和社会伦理空间。个体道德空间是个体的价值场域,是个体的心灵空间,是由个体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等整合而成的价值系统。社会伦理空间是个体存在的外部的价值场域,它“是指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正当性的,是由构成社会伦理空间的诸多块块所依据的不同的社会伦理规范建构起来的,是通过不同领域的社会成员遵守该领域的道德规范实现的”[2]。个体道德空间与社会伦理空间相辅相成、相互建构。个休道德空间的形成除了源自个体的道德反思,还有社会伦理的浸染和教化;而社会伦理空间是由个体在不断扩大共识、践履社会伦理规范的基础上形成的。
(二)道德空间的价值
道德不仅是人应然的存在方式,更是人智慧的存在方式。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论语·里仁》),无论是“仁者”还是“智者”,都选择“仁”的生活方式。根据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等人的思想,道德就是“恰当的做”。这“恰当的做”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而成为万物之灵。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认为,道德就是人的本能,正如人们厌恶令人恶心的东西,或害怕从高空坠落一样。在我国古代汉语中,道德即得“道”,也就是“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可见,道德的形成除了依赖个体的自我反省和端正心性,还需要在一定的道德空间中与他人进行伦理互动。查尔斯·泰勒还分析了道德空间之于个体品德建构的本体论意义。在他看来,只有在道德空间这个框架中才能知道“我是谁”,才能实现自我认同。“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赞同或反对什么。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3]个体知道“我是谁”就有了道德上的方向感,有了道德方向感的确认就能够明辨是非、对错,对什么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等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道德方向感缺失,则会手足无措,如同迷路。由道德之于人的作用、道德空间之于道德的作用可知,道德空间之于人具有本体论价值。
二、伦理部分失序与学校道德空间的弱化
随着社会的结构性变革,我国的社会伦理正处于部分失序的状态。一方面,曾有的伦理秩序已经松动或者趋于终结。儒家伦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遭到重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又被当作革命道德的对立面而被抛弃,这使得我国伦理的谱系失去了应有的连续性。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建立起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伦理秩序,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较为有益的精神条件。但这种伦理秩序的基础主要是战时的革命道德和领袖权威,而不是依靠道德文化本身的创建方式来实现的。这种伦理秩序因过于理想化且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也逐渐遭到弃绝。另一方面,与我国政治民主制度及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个体自由、平等、尊严为核心的伦理秩序,尚未真正确立。社会伦理是学校赖以存在的价值场域。社会伦理秩序稳定,学校道德空间也会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社会伦理失序,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学校道德空间的弱化,甚至完全拆除。
(一)空间冲突导致学校道德空间弱化
学校空间由认知空间、道德空间和审美空间组成,三者相互叠合、相互冲突,而且冲突几乎无处不在。总体而言,“认知分隔的空间和美学分隔的空间对道德空间都不热情相待”[4]212。认知空间强调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和客观性,它创造了距离;审美空间遵循娱乐和审美原则,追求感官上的刺激;道德空间遵循的是良心原则,它不仅超拔于规则和客观性之上,而且视娱乐价值为自己的敌人。在当前社会伦理部分失序的背景下,学校三个空间的冲突更为频繁和激烈,认知空间和审美空间严重挤占道德空间。
传统道德文化断裂,物质主义侵袭,导致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严重僭越。学校人际交往的基础通常不是情感和责任,而是冰冷的规则;人际交往的目标不是追求“个体善”及“共同善”,而是在欲望“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利益交换。认知空间的扩张拉大了学校成员间的距离(特别是心灵距离),它使得学校成员间往往是“相处”的关系,而远未达到“相遇”“相依”的程度。“相处”是一种话题式关系,它由话题赋予。手头的话题和限于此时此地的“专门”的兴趣,产生和限制着交往双方的相关性。自我不愿意在相处中展开超过话题的内容,他者也不强调手头话题允许之外的内容[5]。自我与他者的相遇具有原初的伦理性,是伦理发生的前提。而认知空间的扩张如果使人成了“没有联系的人”,学校空间也就失去了它的伦理内涵。
审美空间的扩张,使人沉溺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感官刺激,追求新颖、惊奇,甚至是神秘、恐怖。拒绝崇高,将一切都当作嬉戏、嘲弄甚至是解构的对象。适度追求感官享受并不一定导致学校道德空间的弱化,但过度的感官欲望一定是弱化和解构道德空间的力量。“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章句下》)过度的感官欲望,必然导致内心的迷失。
(二)理性化原则损伤人的道德本性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伦理逐渐取代传统美德伦理的主导地位。制度伦理强调通过制度和规则来规约社会成员在公共领域中的交往行为。在这种背景下,学校的理性化特征也愈来愈突出。理性化有益于学校的有序运行,但它也是拆除学校道德空间的内在因素。
当前,我国学校运行的各个层面和环节都强烈体现着理性化原则。在办学目标上过度追求效率,使师生成了实现学校组织目标的“工具”,而不是使其以主体的姿态开创属于他们自己的“可能生活”。在管理方式上,通常将师生视为“工具人”和“经济人”,这样的人性假设导致 “信任网络”在学校的严重匮乏。管理不是基于对师生的道德信任,通常是依赖严密的制度及规则体系对学校成员进行规约和控制。必须借助严密的科层体制及技术理性才能实现制度的规约作用,这就导致学校管理过于强调领导权威和科层建制。“当人的本性(厌憎杀戮、不倾向于暴力、害怕负罪感、害怕对不道德行为负责)遭遇到文明的产物当中最备受珍视的实际效率,即遭遇到其技术、选择的理性标准、思想和行动服从于经济与效能的倾向的时候,就暴露出了它的不足与脆弱。”[6]学校成员并非自甘于道德上的平庸和沉沦,学校的功利取向、严密的科层体制及“技艺”式管理损伤了道德自抑机制,致使他们通常难以凭借本有的道德良知去进行各种实践。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服从就变成了最高的美德。
(三)角色变化导致教师道德权威旁落
在传统社会,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联系。知识可以为权力的合法性及有效性进行辩护,权力可以凭借自身的运作抬升知识的地位。知识分子被赋予了唯一的正确性和道德权威性,能够以理性代言人的身份进行伦理立法。随着传统社会的终结,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知识分子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拥有者,而且他们的知识难以对世界提供唯一的“确定性”解释。权力与知识之间的联系也不再那样紧密。知识分子的角色由立法者变为阐释者,道德权威性旁落。阐释者的主要职能,如鲍曼所言,在于“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形成解释性话语”,“促进自主性的共同参与者之间的交往”,“防止交往活动中发生意义的曲解”,“深入到相异之知识系统中,维持两个相异系统之间的微妙平衡”[7]。
在学校中,教师群体难以充当道德权威,教师中的精英分子也难以成为伦理上的立法者。作为阐释者的教师,在学校道德生活中实质上没有什么权力,他们不能发号施令,只能说服和诱导。在“多元主义”及“后喻文化”的时代背景中,教师的阐释也常常难以得到学生的认同。教师失去了其道德上的权威地位。教师道德权威的旁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主、平等、自由等伦理价值的实现,但同时会加剧学校“多元主义”的发展,从而使学校的道德空间不再如同传统社会中那样稳固。
三、学校道德空间的重构
社会伦理的部分失序导致学校道德空间的弱化甚至拆除,但道德空间的拆除并不意味着道德在学校的终结。道德是伦理上的造诣。伦理是“客观法”,道德是“主观法”。客观性的伦理内化为个体的操守和自觉行动,就沉淀为个体的道德。学校道德空间的重构要置于伦理学视域,以校园伦理秩序的重建为切入点。
(一)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学校道德空间的重构需要社会为其提供优良的伦理背景,而在教育系统中,教师的主导作用是重要的重构力量。教师道德权威的旁落不能成为放弃教师主导作用的理由,相反,应当加强这种主导作用。
首先,教师要深刻体认伦理的本真意义,这是主导道德空间重构的观念前提。伦理(ethics)最早在古希腊语中是指人的住所、居留地,这实质上蕴含了伦理的本真意义。也就是说,伦理是对存在的观照,它使人以道德的方式去存在,从而获得安身立命之所。当前,伦理对存在的意义观照就是使人的理性、情感、意志等全面、和谐发展,从而以整全的样式去存在。体认了伦理的本真意义,才能从观照存在的角度引领校园伦理秩序的重建,进而使师生的实践活动同时具有认知、道德、审美的因素,促进道德空间的重构。
其次,教师要明晰校园伦理重建的基本向度。其一,传统伦理中的一些伦理原则及规范,如责任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体、相互敬重等等,有助于使个体与伦理实体(家庭、国家)形成紧密的伦理关联,从而成为一个伦理的存在。黑格尔说过,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伦理就是个别性的人作为家庭成员或民族公民而存在,伦理行为就是个体作为家庭成员和民族公民而行动。”[8]我国的一些传统伦理契合伦理的本质。校园伦理的重建,不能对我国传统伦理进行全盘否定或摒弃,而要对其进行现代续接和创造性转化。其二,正如艾伦·沃尔夫所言,我们必须作为我们自己的道德代理人去行动[4]36。随着社会的现代性发展,传统的法典式的伦理已失去它的存在基础,而现代国家和现代市场作为道德代理人又无力使现代人步出道德的困境。因此,伦理秩序的重建就要诉诸个体的道德自治。这就需要以个体间的伦理协商和重叠共识作为伦理重建的重点。我们需要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积极借鉴人类现代生活的道德经验,包括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等积极的伦理资源。
最后,教师要以优良伦理进行人格的自觉建构。“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荀子·修身》)教师能否主导学校道德空间的重构,关键不在于他们是否被制度赋予道德权威的地位,而在于他们能否将优良伦理自觉地内化为自身之“善”。实质上,教师主要是凭借自身的人格力量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孔子周游列国十几载,学生一路跟随,不离不弃。这不是因为孔子具有道德权威的地位,没有制度赋予他道德权威的地位。“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孔子具有学生所敬仰的伟大的人格力量。
(二)坚持以正义和责任为价值基础
正义与责任是学校道德空间重构所需要的价值基础。
俄国伦理学家克鲁泡特金说过,没有正义,便没有道德。正义是古今中外社会伦理的基本理念。在我国传统伦理中,正义主要指个体美德。“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现代伦理中的正义,除了指向个人美德这个维度,还指向社会生活的伦理正义,如社会在基本制度上的安排、对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正义之所以是现代伦理建构的基础,主要是因为它是社会成员能够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基本原则,它保证社会成员有序参与社会生活。伦理正义所要求的是对他者的基本正直,而不是较高程度的和非平等基础上的让渡或牺牲。因此,它具有“底线伦理”的特点,具有普遍的价值有效性。学校道德空间的重构,必须基于正义这一基本的价值。学校公共生活当然也需要传统的美德伦理,但它只能作为倡导的内容,而不应成为对学校成员的基本要求。学校公共生活是一种制度生活,每个成员的行动均以制度为依据,根据制度行使其权力,并且承担与权力相应的义务。因此,学校需要在“无知之幕”的原初状态下,将权利向每个成员平等地开放,让每个人都有选择和被选择的自由。同时,学校的制度安排在保证“平等自由”这一原则的优先地位之外,还应当遵循“差别原则”,让那些不利处境中的弱势成员成为最大受惠者。
学校道德空间的重构还需要以责任作为其基础性价值。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遇是道德的原初场景,是道德自我的摇篮和发源地。自我不仅要与亲近的他者相遇,还要与陌生的他者相遇,而陌生的他者会令人产生不同程度的“蛋白质恐惧症”[7]。这就需要以包容的心态,将陌生的他者转化为“邻居”。道德责任不同于理智,它没有根基和原因,也没有决定因素。它是“本我第一位的实在,是社会之起点而非社会产品”[4]16。 因此,在学校空间中,每个成员不仅追求与他者的相遇,还要为他者负责。对他者负责,首先需要我们在道德上为自己的无知负责。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今时代,学校成员特别是管理者及教师,不仅要有理念与信仰上的高尚,还要时刻预防自己的行为给学生造成伤害,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负责。除此之外,还需要以“恻隐之情”面对他者的“脆弱性”,激活自身本有的道德良知,从而充分为他者负责。
(三)使学生成为道德空间重构的主体
学生一方面在道德空间中成长,一方面应以道德主体的姿态对道德空间施加积极的影响。这样,学校道德空间才能保持相对稳定,同时还能不断发展。
要使学生成为学校道德空间重构的主体,首先要对学生的良善本性及道德禀赋怀有高度自信。学生固有良善的本性,有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其次,要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并引导学生进行自觉的选择。学校要制定一定的规则,但不能追求在约束学生方面的无微不至,否则就可能压制学生的道德冲动。要弱化理性化的管理方式,赋予学生自主安排生活的权力。英国伦理学家亨利·莫尔说过,伦理学是幸福生活之术。道德的终极目的是使道德主体过上“美好”和“善好”的生活。教师要引导学生理解何谓幸福生活、如何才能过上一种幸福的生活,帮助学生养成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的良好习惯。再次,不能以说教和强制的方式使学生接受道德规则。说教和强制所建构的道德空间,表面看起来可能稳固,但它缺少坚实的根基,且是一个封闭的道德空间。因此,需要提升学生的实践理性,教师应当提供经验指导,存养、扩充学生本有的性善端。这样,学生才能不断体认自己的本性及目的,从而以能动的道德主体的姿态,对道德空间进行创造性的建构。
[1]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M].林荣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92.
[2]龚长宇,晁乐红.道德空间界说[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5).
[3]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37.
[4]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5]曹永国.师生关系:从相处到相依[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17).
[6]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8.
[7]龚长宇,郑杭生.道德空间的拆除与重建:鲍曼后现代道德社会学思想探析[J].河北学刊,2014(1).
[8]樊浩.“伦”的传统及其“终结”与“后伦理时代”: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对话与互释[J].哲学研究,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