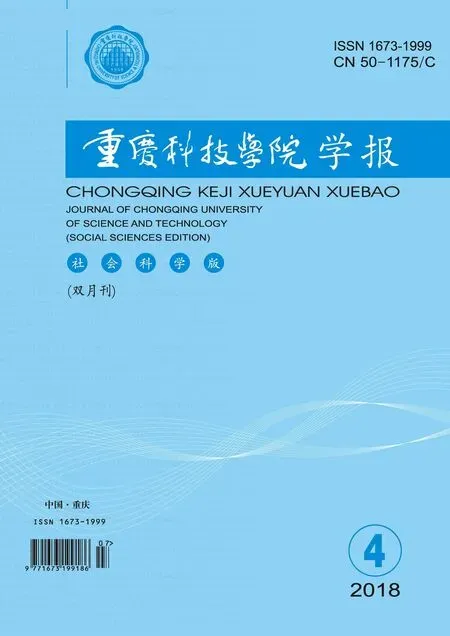论郁达夫笔下的上海空间意义生产
何琛,段小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魔都”“东方巴黎”的别称,人口稠密,商业繁荣。商埠和各通商口岸的开辟,各国租界的划定以及外国文化的侵入,使其成为了一座殖民色彩极为浓郁的现代都市。旅居上海的作家对这座城市的情感不可谓不复杂,发诸笔端便有了文学中样态纷呈的上海形象。文学作品中的城市空间是一种渗透着作家主观情感体验,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想象空间。
郁达夫作品中的上海书写真实再现了上海都市华美靡丽的现代化气息;同时,他将描写的触角延伸到这浮华煌丽背后的暗淡角落,显得感伤而又落寞。
一、都市公共空间:街道、马路、外滩和戏园
街道和马路的书写在郁氏小说中占据重要地位。街道很好地体现了城市的流动性和混乱性特征,是城市别于乡村的主要空间特征之一。街道串联起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构筑起城市的整体框架,宽阔的马路和纵横交错的内街小巷将城市连接为一个整体,人群在道路上移动的同时观察着城市[1]39。
《烟影》中,文朴寓所附近的街巷里,天空中起了寒风……吹起了些泊拉丹奴斯的败叶和几阵灰土来,文朴的心里,不知不觉的感着了一种日暮的悲哀[2]308。“寒风”“败叶”“灰土”“日暮”等意象构筑起一幅萧索的上海街景。街道上,放学回家的小孩和行色匆匆往家赶的工人勾起了他的无限乡愁,“破旧的书籍”“嘈杂的市声”使他“不住地回忆到少年时候的他故里的景象上去”。街道延伸的远方便是阔别已久的故乡,上海对他而言不过是个“过场”,只有少年时候的故乡才是他心灵的归宿。
小说《落日》中,Y和C立在摩天的W公司的屋顶上,环顾上海全市的烟景溶解在金黄色的残阳光里。马路上,人类、车马如同虫蚁一般,簇在十字路口蠕动。市廛的嚣声断断续续传过来,凉风拂面,带有使人落泪的一种哀意。主人公居高临下,“上海全市的烟景”尽揽于眼底。“金黄色的残阳”,“同虫蚁一般”,“蠕动”的人类群和车马,喧嚣的“市廛”等空间意象,看似开阔富有动感,但这一切热闹都与他们无关。他们立在高处俯瞰城市,拉开了与城市内部的距离,“在而不属”是他们与这座城市关系的真实写照。因而游戏场传来“煞尾的中国乐器声”和“听众的哄笑声”时,落寞之感便袭上心头了。这繁华的都市如梦一般,美好却虚幻。
与街道和马路一样,作为上海最繁华地带的外滩,在郁氏小说里同样呈现出一派静寞。小说《茫茫夜》中,“静寂的黄埔滩上,一个行人也没有。街灯的灰白的光线,散射在苍茫的夜色里……黄浦江中停着的船上,时有一声船板和货物相击的声音传来,和远远不知从何处来的汽车车轮声合在一处,更加形容得这初秋深夜的黄埔滩上的寂寞”[2]100。 “灰白的光线”“苍茫的夜色”“黄浦江中停着的船”等空间意象冷清冰凉,与上海外滩常见的明丽动人景象大异其趣。黄浦江滩的夜景褪去华丽的外衣,凄清迷离,目睹这一切的主人公心中充斥着一种幻灭感,觉得将亡未亡的中国,将灭未灭的人类,茫茫的长夜,耿耿的秋星,都是伤心的种子[2]105。
除了街道、马路、外滩等室外公共空间之外,“戏园”这一室内公共空间也常常充当了郁氏小说的叙事场景。小说《落日》中,Y和C在某个星期六赶上K舞台去听戏,戏园里的人都是些穿着轻软的衣服的贵公子和富家的妻女。戏园作为有钱人的娱乐场所,其权力主体是那些来自上海社会上层阶级的“贵公子”和“富家妻女”,Y和C的出现,显然与这里格格不入。“Y心里顿时起了一种被威胁的恐惧,好像是闯入了不该来的地方的样子”[2]267。对 Y 来说,戏园早已失去了其固有的消遣和娱乐功能,生产出的是一种莫名的压迫感和恐惧感。戏园在他们心里不过是权力场域的象征,虽能短暂地享受到感官上的欢娱,然而在精神上却始终无法与之契合,他们终究难以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
上海都市公共空间在作家笔下,显然绝非机械化的客观再现,而是自由化的主观呈现。外在都市空间与人物内在心理空间交融混合,互为映衬,营造出一种感伤的情绪氛围,建构起一个洋溢着颓废美的文学场域。
二、都市边缘空间:贫民区里的亭子间
亭子间要算是上海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了。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2m左右,面积6~7m2,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不少作家有过住亭子间的经历,他们的作品叙事也多会涉及亭子间生活。
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关于贫民区有一段这样的描写:“邓脱路的这几排房子……只有一丈几尺高。我住的楼上的那间房间,更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楼板上伸一伸懒腰,两只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顶穿通的……黑沉沉的这层楼上,本来只有猫额那样大,房主人却把它隔成了两间小房”[2]248。20 年代的上海,要数闸北地区的番瓜弄、沪西曹家渡、徐家汇、老城南市区沿码头一带和外白渡桥北堍的杨树浦区域的贫民区条件最差。居住者多为产业工人,小买卖贩子和低级从业者等。房屋除了用来遮风挡雨,也体现着居住者的身份与地位,它既可以作为夸耀的资本存在,也可能是无奈境遇的写照。小说中“我”寄居的亭子间,表征着“我”在上海的窘迫处境,成了“我”作为底层知识分子的一个身份标签。
居室作为一种人化的空间形式,深刻表征着人的意识,承载着人的喜怒哀乐,脾气与性情。小说中的“我”与陈二妹分住在只一墙之隔的两间逼仄的亭子间中。陈二妹坚强善良,同情并照顾着落难于贫民区的“我”,让“我”得以暂避来自社会的冷漠与压迫。对“我”来说,逼仄的亭子间不再是单纯的容身之所,也成了心灵的休养栖息之地,
亭子间在小说叙事中,不光是故事展开的场景,它还以一种破陋的形象驻留于上海繁华都市中,从侧面反映出整个上海城市空间的异质性与多元性,给我们观照上海提供了新的维度。它揭示出上海底层居民生存的日常性和真实生存状态。对贫民区和亭子间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愿意接近社会底层的情感倾向。
三、都市空间的“漫游者”
都市“漫游者”是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市“漫游者”滥觞于本雅明笔下的波德莱尔,这里的游荡者不愿放弃雅士们悠闲之乐的生活,追求的是一种悠然自得,一种我行我素,而非机械呆板的城市经验,而郁氏笔下的游荡者则迫于经济的困窘与生存空间的逼仄,不得不到马路或公园流浪。
小说《落日》中,Y流落上海。由于没有职业,如何消磨无聊的白昼便成了他的“一个天大的问题”。他所居住的上海贫民窟的那间同鼠穴似的屋顶房间并不适合用来打发他的无聊。于是,他一天到晚“尽伏在电车头上的玻璃窗里随电车跑来跑去,在那里看如流水似的往后退去的两旁的街市;有时候看街市看得厌烦了,他就把目光转到同座的西洋女子或中国女子的腰上,肩上,胸部,后部,脚肚,脚尖上去”[2]263。过了几天,他觉得电车上的买票者和查票者记熟了他的面貌,老对他放奇异的眼光,便不敢再坐电车而改坐人力车了,“有几次无缘无故的跑上火车站上去”,有时他还在半夜里“雇了人力车跑上黄埔滩的各轮船公司的码头上,走上灯火辉煌,旅人嘈杂的将离岸的船上去”[2]263。 后来他怕人力车夫也认得他,就直接改作了徒步旅行,或在白天或在晚上,穿行于城市的马路上。“街道是重要的连接点,连接着繁华外在的都市奇观和世俗庸常的日常生活。”[1]43
Y由于失业造成的空虚感无处发泄,只好通过闲逛来打发掉心中的无聊与苦闷,逃避琐碎的生活烦恼。他与街道上的陌生人(电车上的买票者或查票者,西洋女子或中国女子、人力车夫等)之间存在一种“互看”关系。他在看别人的同时也被别人看,这诱发了他担心被别人认出的惶恐心理。在他用尽所有的金钱后,“白天热闹的马路两旁的样子间,他不敢再去一间一间的看了,因为正当他在看的一瞬间,心里若感得有一个人的眼光在疑他作小偷窃贼……”于是“他的徒步旅行,白天就在僻静的地方举行,晚上必等大家睡静的时候,方敢上马路上去”[2]264。 漫游在减轻他的空虚感时,又在无形中加剧了他的恐慌心理,显示出他自卑与多疑的性格。在失去金钱这一重要精神依托后,他心里的安全感极度缺乏。上海都市丰富的物质生活与文明程度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渴望享受这些物质文明,同时也体验到一种“都市边缘人”的羞怯感,处境甚是尴尬。
小说《血泪》中,“我”因缺路费回家,只得流落上海街头。“白天我每到外白渡桥的公园里去看那些西洋的小孩儿游玩,到了晚上,在四马路大马路的最热闹的地方走来走去的走一回,就择了清净简便的地方睡一忽。”[2]195这里,作为公共空间的马路所体现出的“私人化”意义更为明显,它既是“我”消遣与排忧的场所,还兼有“卧室”的功能。
在《茑萝行》中,“我”是一个混迹上海,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的游民,“在烈日蒸照,灰土很多的上海市街中,整日的空跑了半个多月”。“我于这样的晚上,不是往黄浦江边去徘徊,便是一个人跑上法国公园的草地上去呆坐……一个人看看天上悠久的星河,听听远远从那公园的跳舞室里飞过来的舞曲的琴音,老有放声痛哭的时候……有时候哭得倦了,我也曾在那公园的草地上露宿过的”[2]237。在社会里饱尝辛酸、四处碰壁的“我”,内心郁结的苦闷唯有寄予这不谙人事的都市景观与自然景观中。
对于这些都市“漫游者”来说,街道、马路等公共空间在他们那里获得了“私人化”的意义。他们从街道、马路的漫游中,在街道和马路所框定的都市空间中寻求私人感官与精神上的满足,在都市中行走是他们与城市保持亲密接触的最可靠最直接的办法,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他们被城市所冷落的命运,他们始终是上海这个金刚石库里微不足道的一粒尘埃。在阅尽城市的繁华后,他们只能在内心深处哀叹着自己的不幸。上海不是他们的天堂,而是销金的魔窟,他们在这暗晦的、浑浊的都市空间里步履维艰,颓然度日。都市社会空间的异质性与悖谬性带给他们精神上的困厄与挣扎。尽管他们可以自由熟练地穿越上海的街道、马路、巷子、公园等各个空间,但他们在精神上仍然无法真正融入都市的内部结构,与这个城市之间发生了明显的错位。
四、都市空间体验下作家的身份认同危机
存在需要领会,空间也需要领会,人正是存在与空间的领会者。“属人的生存性空间,是一个充满意义追求、充满感性经验、充满情感体验、充满精神超越、充满生命关怀的个性化差异世界”。“都市空间作为现代生存体验的基本形式,决定了都市人的生存空间体验,同时也决定着文学艺术家的生存空间体验,构成文学的内在生命意蕴”[3]156。郁达夫与其小说中的都市“漫游者”开掘出属于自我的生命体验空间。
归国之初,寄居上海的作者境遇窘迫。他在自叙传小说《茑萝行》中感叹道,“一踏上了上海的岸,生计问题就逼紧到我的眼前来”[2]234,“一下子就把这位得到经济学学士学位的、已经出版了小说集《沉沦》的作家挤入了底层”。他感叹自己竟成了一个“社会的牢笼里碰撞的求生者”,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4]118,颇具自嘲意味,在无形中模糊甚至掩盖了自己留日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他改变了以往生活的空间环境(上海之外的空间环境),进入到新的空间环境(上海租界)中时,随之而来的忧伤和落寞的情感里,蕴藏着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
当他以一种楔入的姿态进入上海,直接面对来自租界现实的剧烈冲撞和城市空间的挤压时,文化身份建构的焦虑感无时无刻不困扰着他。“漂泊在租界中的知识分子受到几种文化在场的制约,尤其是西方殖民文化的在场、现代都市文化的在场、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场和乡土文化的在场,这几种在场文化对知识分子交互进行‘嬉戏’,造成了租界中文人文化身份的‘不纯’,投机、颓废、放荡和漂泊感构成了租界文人的精神气质。”[5]135殖民体验、都市现代性体验以及原有的故土乡村体验交织杂糅在一起,一度引起作者内心的恐慌与不安,造成自身精神归属感的缺失与身份意识的迷茫。租界生活的殖民体验给了他弱国子民的悲哀,摩登与繁华的都市让他时时联想到自己是个外来的“乡下人”,卖文为生的尴尬处境使他常以“贩卖知识的商人”自嘲。生活于上海都市空间中,他是孤独的,这种孤独同时也表现为一种无依的漂泊感。反映到小说叙事中,就是“家”的意象的缺席。家是构成一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家所延伸出的表征意义代表了一种温馨、安适与幸福。“家”概念的缺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作家对于都市化上海的游离感,而造成作家的这种游离感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其心理上的无家可归感,这也导致他在身份认同上的茫然与焦虑,显现出了郁达夫惯有的卑弱心态。
[1]焦雨虹.消费文化与都市表达:当代都市小说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2]郁达夫.郁达夫选集: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域中的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王观泉.颓废中隐现辉煌:郁达夫[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5]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