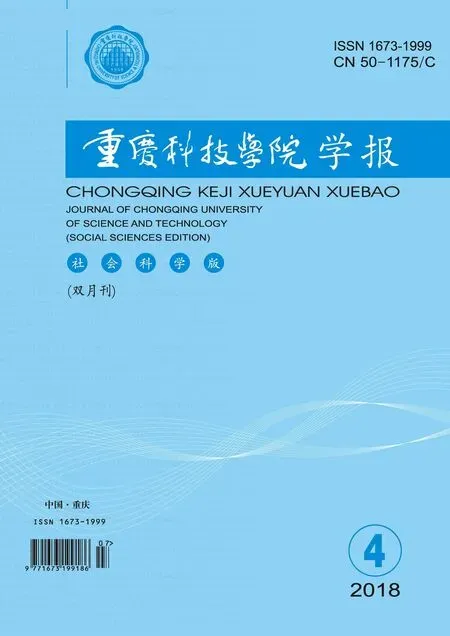非裔美国人的狂欢之旅:疯癫美学下的莫里森三部曲
朱晓丽
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爵士乐》《天堂》,因时间、内容上的连贯性而被归结为三部曲,更因系统刻画了一群狂欢中的疯癫人物而堪称三部曲之狂欢化经典。三部曲自问世以来引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潮,有研究者集中关注单一作品的内容和写作风格,但是,在疯癫美学观照下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系统研究莫里森三部曲的却不多。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由狂欢节、狂欢式和狂欢化三要素构成。狂欢节逐渐演化成圣诞节和集市等。狂欢式是狂欢节上加冕和脱冕等一切仪式的总称,具有全民性和动态性,带有狂欢化色彩的疯癫者也参与其中并体验狂欢式的世界。当狂欢式升格为文学语言时就形成了狂欢化。狂欢化处在动态的建构中,消解了疯癫与理性、神圣与粗鄙、黑与白等的二元对立。疯癫与狂欢密不可分,疯癫是内容和表象,狂欢是形式和释放,本质都旨在颠覆。巴赫金推崇的“怪诞”美与福柯倡导的“疯癫”美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旨在突出疯癫的边缘视角而体验相对化的、狂欢化的世界。因此,在疯癫美学观照下,三部曲也就具备了为非裔美国人开启一场狂欢之旅的可能性。
一、“疯癫语体”的狂欢化叙述
疯癫者以“不可靠叙事者”身份参与到叙事中,使文本具有了不确定性的艺术张力,其跳跃性思维和非理性语言决定了文本在叙述语体上呈现出诗化与粗鄙化并置的特征,契合了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要理解疯癫,需要诗人的才华”[1],因为疯癫者的精神紊乱导致其叙述杂乱琐碎,并有意使用狂欢广场上的粗言俗语使叙事呈现出语体粗鄙化的特点。疯癫者异化的才华也让他们常使用诗歌的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法凸显文本语言诗化的特色。因此,三部曲正是奔走在这两种极端语体中的代表。小说中的疯癫者借助两种语体的并置共存,在钟摆式的狂欢中完成了加冕和脱冕的仪式,解构了权威。
《宠儿》的疯癫叙事具有典型的诗化特征:隐喻性、象征性、多重视角性。《宠儿》的狂欢化底蕴决定了疯癫者被脱冕的命运,在语体上表现出粗鄙和插科打诨。“甜蜜之家”里充斥着饥饿的意象,富含隐喻的诗意。奴隶们忍受着身心的双重饥饿;塞丝被迫与母亲分离,饱受对母爱的饥渴;在124号房子里,贝比临死前对颜色极其饥渴;丹芙与世隔绝数年后,对人际交往充满饥渴。塞丝疯狂出逃途中,借白人姑娘之口将其背上的鞭痕描述成一棵枝繁叶茂的樱桃树,象征着塞丝和树一样有着获得新生的能力。塞丝弑婴事件通过奴隶主、贝比和黑人邻居的多重视角叙述给读者,虽杂乱无章却震撼人心,凸显了奴隶制下黑人对主流霸权的抗争精神,实现了对疯癫者的加冕。宠儿的疯癫也通过不同视角被展现出来:塞丝眼中的她有着婴儿的外形和对自己母爱的疯狂渴求;保罗·D眼中的她在厨房里叙述自己身世时内容不连贯,语法不规则,在意识流中流露出粗鄙化的倾向。然而,宠儿的鬼魂是黑人群体的梦魇,最终逃不过被驱赶、被脱冕的宿命。
《爵士乐》疯癫叙事的诗化特征在于:声音多元化、隐喻性、音乐性。狂欢广场上爵士乐即兴演奏的特点决定了小说呈非线型叙述,语体也出现了偏离现象。不同疯癫者叙述的多声交融构成了文本的声音多元化。开端的叙述者就是一个不可靠的大都市旁观者,她介绍维奥莱特的语言呈即兴碎片式,具有杜撰编造的嫌疑。号称权威的小说家暴露自己虚构枪杀案的印痕,并且常对自我叙述加以评判。人物名字富含隐喻含义:乔的姓为特雷斯,隐喻着自己就是父母消失时留下的痕迹;维奥莱特的名字与暴力同音,隐喻着其成年时的疯癫。小说章节间均以一页空白隔开,仿效了爵士乐演奏的形式。开端似是爵士乐长号和小号的合奏,急促奏响了乔夫妇与第三者间的乐章。后半部乔和多卡丝的个人独白正如爵士乐的独奏,充满韵律。主人公们在奏响爵士乐的广场上狂欢并被加冕。小说大量使用临造词,如“下流的音乐”等,使叙述简洁有力,还有意把相悖的词拼贴在一起,构成矛盾修饰,如黑人由于大都市迷乱生活的“鼓舞”才北上。矛盾的语言揭示了黑人迷失自我的苦闷,使他们集体被脱冕。
《天堂》疯癫叙事的诗化特征也很明显:黑人性、指涉性、魔幻性。疯癫者的在场导致小说叙事呈现出记忆碎片拼贴组合的特色,小说结尾也呈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故事发生的中心地是鲁比镇,这个纯黑人小镇遵循越黑越美的原则,但也警醒黑人们不要落入黑人种族主义的泥潭。小说构建了一个丰富的人物指涉体系:黑人祖先撒迦利亚以《圣经》人物为原型;黑人帕拉斯以希腊女神雅典娜为原型;康瑟蕾塔则以基督教中的耶稣为原型。小说中魔幻神话与美国现实融为一体,富含审美意象:撒迦利亚带领黑人们在“神秘人”指引下来到黑文镇;康瑟蕾塔具有“迈步进入人体”的魔法,黑人们在保持“黑人性”的狂欢中得到了临时加冕。小说叙述的故事被切割成碎片并分散到不同时间里交叉拼贴进行:黑人男性袭击修道院的暴力狂欢事件打开了叙事的闸门,接下来小说一一讲述修道院中5名女性癫狂的故事,在叙述过程中穿插了鲁比镇和修道院里的事。当讲完这些故事后,小说又折返继续完成开篇尚未结束的讲述。结尾并未交代小镇的前途和遭屠杀的修道院女性的去处,具有开放性,也让黑人们再次被脱冕。
二、“疯癫意象”的狂欢化戏仿
三部曲都选择了疯癫者作为叙事者,因为疯癫隐喻着边缘人对理性的正统文化和权威的主流社会的质疑和否定,“能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彻悟状态中”[2]。疯癫意象成为了三部曲解构主流叙事的有力武器,具有了“戏仿”的反讽戏谑的狂欢化功能。“戏仿”亦称“戏拟”或“讽拟”,基于文本互文性,以嬉笑怒骂的狂欢式语言对经典作品中人物形象、主题、历史情节等进行模仿重构,有意戏谑消解叙事陈规和传统话语,达到关怀和批判现实的讽刺目的。正如巴赫金所说,一切重要的讽拟,都总具有讽刺性;而一切重要的讽刺,又总与讽拟和谐戏过时的体裁、风格和语言结合在一起[3]。
《宠儿》里疯癫意象主要对经典文学中的人物主题、神话和历史情节进行了反讽式戏仿。宠儿和塞丝都是疯癫的黑人女性,她们的名字分别源自《圣经》和埃及神话,但均具有反讽性。上帝把自己庇护下的子民称作宠儿,小说中的宠儿并未得到宠爱,幼年时被母亲弑杀,当其鬼魂回来霸占母爱时又被黑人群体赶走,所以,她的名字讽刺抨击了奴隶制的罪恶。埃及神话里的魔鬼寨兹杀害了亲哥哥,是个负面形象。小说里塞丝疯狂弑杀女儿,貌似残忍但却揭露了奴隶所遭受的非人迫害。塞丝弑婴的主题戏仿了西方经典文学中的杀婴母题,也与希腊神话中美狄亚的故事产生互文性。美狄亚为心上人弑杀了亲哥哥和亲生孩子。塞丝因奴隶主追捕和黑人邻居嫉妒而癫狂杀子,虽仍是杀婴主题,但却颠覆了情节和导火索,借此反讽白人的霸权和黑人的不团结。塞丝逃离“甜蜜之家”的情节源自《圣经》里伊甸园的故事。伊甸园里硕果累累,亚当和夏娃幸福生活着。“甜蜜之家”里,奴隶主加纳先生给予黑奴们一定自由,但其伪善随着学校老师的到来而暴露出来,塞丝的拼死逃离讽刺了南方种植园隐藏在甜蜜后的严重种族压迫和歧视。
《爵士乐》里疯癫意象则对《圣经》中的场景情节、人物原型以及西方通俗小说中的侦探小说模式进行了反讽式戏仿。伊甸园里树木成荫,亚当和夏娃安宁的生活着。与伊甸园相似,小说中乔痴狂寻母的林中木槿花盛开,乔陶醉于这片乐土,然而,乔在这片乐园中觅母不得,白人掌控了南方,最终烧毁了乔的家园和这片林子。这种戏仿讽刺了主流霸权和黑人的闭塞。《圣经》里,撒旦原是上帝宠信的六翼天使,由于嫉妒上帝,他反叛上帝并引诱亚当夏娃吃下禁果,终堕落成魔鬼。小说里多卡丝被戏拟为女版撒旦,年幼时目睹父母在种族冲突中丧生的经历导致她成年后反叛堕落,她引诱有妇之夫乔成功后即将其抛弃。当乔疯狂枪杀她后,同胞之爱让她宁死也不指认乔。与撒旦不同的是,她是善恶的结合体,揭露了种族冲突对黑人身心的迫害。侦探小说常以一个悬案作为开端,叙述过程中采用多种侦破手段逐渐揭开谜底。《爵士乐》开端以一个枪杀案埋下伏笔,后通过维奥莱特层层追踪线索直至结尾交代真相。与传统侦探小说不同的是,《爵士乐》还运用了疯癫叙事的策略,从而反讽颠覆了白人主流文学的宏大叙事。
《天堂》里疯癫意象对《圣经》里的天堂场景、人物原型和美国社会里的白人种族主义进行了戏仿。《圣经》里,天堂是上帝所在之处,耶稣的信徒死后便可以进入这样的圣所,人们与上帝快乐同在。小说中的黑人鲁比镇花团锦簇,夜不闭户,貌似伊甸园,然而,祥和之下隐藏着性别和种族的歧视。这样的戏仿反讽揭示了黑人天堂的乌托邦性质。在基督教里,亚伯拉罕为向上帝表忠心欲杀死爱子,被上帝制止后抓来一只无辜的公羊,把它作为替代品燔祭给上帝。小说里修道院本是一个女性天堂,鲁比镇上的黑人男性把小镇家园衰落归咎为修道院女性的邪恶,把她们当替罪羊,于是暴力袭击了她们,小说借戏拟警醒黑人们反思和批判自身的问题。在美国现代社会中,白人处于霸权地位,他们歧视黑人肤色,推行白人种族主义,使黑人饱尝奴役和屈辱,导致了频繁的种族冲突。在黑人小镇上,黑人们推崇黑人种族主义,信奉越黑越高贵的原则,歧视和隔离浅肤色黑人,导致了黑人群体的四分五裂和小镇的分崩离析。黑人种族主义是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反讽式戏仿,影射并辛辣讽刺了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血统优越论。
三、“疯癫审美”的狂欢化表征
疯癫文学中的人物被赋予了特殊的美学,表征为精神癫狂、异化和狂欢。疯癫叙事的不确定性也使文本自我否定和前后相悖,呈现出矛盾美,建构了多元化的审美样态,体现了一定的审美价值:对理性和人性的映射、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对正统权威的颠覆。这与狂欢化理论的美学内涵不谋而合,因为狂欢化叙事的叙述者常是疯傻之人,他们滑稽粗俗的经验世界赋予了文本美学特质,透露出一定的审美内涵:对人性和自由平等的肯定、对生命更替价值的昭示、对世俗和霸权的解构,其美学表征为痴傻、怪诞和佯狂。因此,疯癫审美和狂欢审美相互交融,共同体验了陌生化的审美感受,同时具有了狂欢化表征,并在三部曲中大放异彩。
《宠儿》疯癫审美的狂欢化表征在于:怪诞美、意识流美和魔幻美。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怪诞具有未完成性和动态性,既含有恐惧神秘感,也含有崇高优美感。鬼魂宠儿外表畸形,行为癫狂,她的纠缠让塞丝无法走出奴隶制的阴霾。然而,她出现在狂欢节时分,具有狂欢式的怪诞,从而使黑人群体的恐惧厌恶转变为短暂的快乐。宠儿、塞丝和丹芙将结冰的小河和124号房子变成女性的狂欢场,她们大笑着溜冰和缝衣做饭,暂时获得新生,凸显了姐妹情谊的审美张力。作为一种美学视野的拓展,意识流用时间蒙太奇和自由联想等手法取代了传统宏大叙事,凸现了边缘性审美体验。小说中,1873年的“现在”和奴隶制的“过去”在塞丝意识流动中自由跳跃,不时中断交汇,呈现出时间狂欢的蒙太奇之美。当母女3人在林间空地上狂欢时,塞丝的意识以其所在时空为辐射场,自由联想到有关奴隶制的一系列经历,呈现出动态的伞状美。作为审美的载体,魔幻意象是神话传说和历史现实的结合体,创造了奇特的审美效果。鬼魂宠儿是核心的魔幻意象,她从水中走出,有着多重身份的神秘之美:抑或是塞丝弑杀的女儿,抑或是奴隶主残害的黑奴冤魂,在虚实狂欢中营造了小说的魔幻色彩和审美魅力。
《爵士乐》疯癫审美的狂欢化表征为:音韵美、悲剧美和百纳被审美。相同或相近音素的重复成对出现构成了语言和谐共振的音韵美。小说的语言效仿了爵士乐音效和节奏,糅合了头韵、拟声叠词、逗号和重复段等手法,增加了爵士乐的音质感,打破了语言粗俗与高雅的界限,在狂欢中展现了音韵美。在美学范畴内,悲剧美是由小说中的悲剧情节和精神升华为艺术而创造出的一种特殊美,其本质是爱中实现自我救赎。《爵士乐》中暴力、杀戮等血腥的狂欢情节具有悲剧性,但也净化和救赎了主人公的灵魂,促进了黑人群体的和谐团结,从而超越了传统的悲惨,获得了精神愉悦的美感。百纳被是用不同图案的碎布缝制而成的唯美艺术品。在小说中,缝制百纳被的聚会跨越了种族和肤色,促进了姐妹情谊,具有美学价值。《爵士乐》中随处可见的身体、精神、家庭碎片在聚会的狂欢中被缝制成一个整体,弥合了断裂的过去和现在,凸显了百衲被特质。
《天堂》疯癫审美的狂欢化表征体现在:色彩美、身体美和劳动美。色彩的审美力量在于以绘画映现和象征意蕴的方式营造了崇高或粗鄙的意境,从而产生美感联想。小说中有意使纯黑、浅黑和白色并置以形成强烈跳跃对比,缔造了越黑越美的意境。浓烈的黑色象征了非洲传统,从边缘来到狂欢场的中心,凸显了黑人美学的核心。作为审美的主体和对象,身体在审美实践中感知和体验崇高之美,是对精神的内省关照。小说中,修道院女性身心因长期被奴役变得异化,为了恢复身体的内在本质,院长康妮引导不同肤色的女人们躺在地板上,用彩笔刻画下身体的轮廓及更细致的部位。她们在欣赏身体美的同时大声讲述各自的噩梦,从而在语言的狂欢中实现了灵肉合一。劳动在动态的层面上创造了实用价值,有用即美,可以给人带来愉悦的美。小说里的劳动狂欢场景体现了女性自力更生的精神,康妮和玛维斯一起剥核桃时通过优雅的手把抽象的美转化为物质的美,凸显了劳动美。
三部曲中的非裔美国人在狂欢节上扮演傻瓜和疯子,借用圣愚形象来颠覆正统,构建边缘世界的合理性和审美性,通过交替和变更、死亡和新生的狂欢化精神,在解构权威的狂欢之旅中实现了加冕和脱冕,使文本的疯癫叙事呈现出浓烈的狂欢化色彩。正如福柯所说,在闹剧和傻瓜剧,愚人和白痴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它不再是司空见惯地站在一边的可笑配角,而是作为真理的卫士,走入了舞台的中央[4]。
[1]米歇尔·福柯.福柯集[M].杜小真,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7.
[2]苏珊·桑塔.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35.
[3]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M].白春仁,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1
[4]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