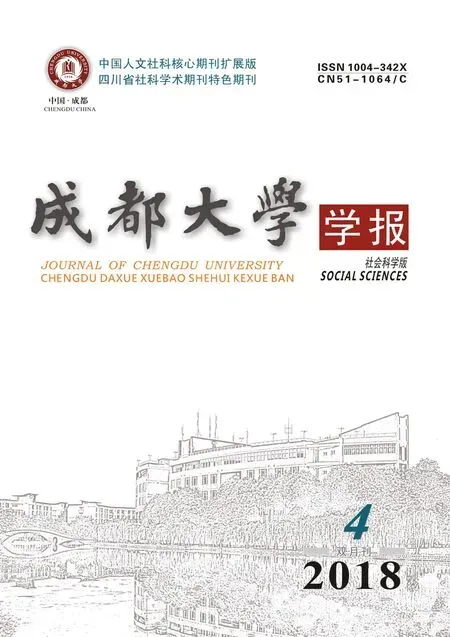英语世界对老舍小说的男性气质研究*
续 静
(成都大学 师范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男性气质研究是伴随20世纪初女权运动所强调的女性气质一同兴起的研究角度,只是似乎易因女性主义的标出性而被淹没了声音。它与性别政治、身份认同等术语紧密相连,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形成有体系的研究门类。英语世界学者雷金庆(Cam Louie)的英语长文《现代世界的中国男性化建构——以老舍小说〈二马〉为例》、专著《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及陈慧敏(Wei-ming Chen)英语专著《“笔”或“剑”:短篇小说中的“文”、“武”理想冲突》各自梳理了中国自古以来对男性气质的理解、建构与想象,充分论证了老舍小说中对传统男性气质被解构及寻找重新建构途径的严肃思索过程及观点。尽管20世纪之交出现许多不同的男性化理想,但西方文化对男性身份的影响是基本而持久的。东西方接触是否有意义地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化理想?如果是,这种新形象是如何整合传统与西方性别架构的?老舍在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时表现出怎样的复杂心态,进行过怎样曲折艰苦的探索?在整个20世纪中国男性气质论中老舍贡献了什么?这是研究者想要探究的问题。
一、“文武”的双重建构——老舍小说对中国男性气质的界定
康奈尔、梅瑟施米特等“支配性男性气质”概念(hegemonic masculinity)提供了社会学意义方面的研究理论。男性气质是在社会文化特定社会机制下形成的;男性群体对自己的社会主流定位在文化史及文学史上一直是发展演变并多样的,因而是复杂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总会有某种或某几种主要的特质被不断强调并相对固定下来。老舍小说最突出的文化价值之一就是它们较大程度上复现着传统中国文化的诸种习俗和风貌,其中包括对传统男性气质最基本最到位的理解。雷金庆将“文武”解释为“文化修养和勇武之气”[1]。陈慧敏界定“文”“武”为“笔”和“剑”:“文”是用“笔”的人,“文人”, 与民间文学相联系,具有体弱、多思、少行、理论重于实践等特征;“武”是用“剑”的人,行动的人,与军营文学相联系,具有体格健硕、勇力过人、实践重于理论等特征。[2]英语世界学者与国内学者一样,都发现中国男性气质理论基础在老舍的小说中被明确定义为“文武”。文武特征被看作中国男性特有的。“文”与“武”,传统男权社会对以主人翁姿态崭露头角的男性群体的政治、伦理要求,也是对一种至高人文理想的提炼。从孔子开始,教育上对“文治”与“武功”的要求日渐分离。“文武双全”自然是最高理想,然则将二者之一发展到极致都不失为真汉子。毕竟文人士大夫和武将的身份几乎不可能全然长久地集于一身。尽管老舍“文”的形象具有压倒性,这由其气质和从文之路决定,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老舍小说既有文化批判及对文人命运的忧思(如《大悲寺外》、《牺牲》、《新韩穆烈德》、《离婚》等),又关注传统武艺、武魂的没落和英雄的人格力量(如《断魂枪》、《黑白李》、《老字号》、《八太爷》等)。诸般事实展示出老舍以“文”为主对“文武”的重视和追求。
“文武”与阶级、种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雷金庆关注“文武”作为中国男性气质的引导力量如何被建构及其在西方文化被引入时发生了何种转换。他发现老舍在《二马》中花大量篇幅描述英国华工和中国文人留学生的差异。20世纪初中国受教育阶层的男性身份曾受到威胁,不仅仅是被西方价值观念袭击,同时更被国内逐渐有话语权的女性和劳动阶层的男性所威胁。雷金庆论文是少有深入挖掘马则仁形象的英文文章,剖析其类似孔乙己的迂阔文人特质。但他忽略了马则仁曾接受英语教育的背景。马则仁同饱读诗书希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孔乙己不同,他厌烦读书,也没能培养起读书的品位。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做官,曾想通过娶政府官员女儿达到做官的目的。他看不起商人,李子荣请辞时又觉得给他丢脸。他还刻意按照英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行动。马则仁的处世态度是对中国世俗哲学的着意张扬。多数评论如王德威认为马威是爱国和悲剧的。马威同父亲意识之间的疏离确证了李欧梵关于这一代人的经典研究。李指出,到1920年代为止,“新”文人开始与传统旧文人产生分裂,他列举了八种当时与“现代”相关的流行思想。李子荣们摒弃了整个文武理想,开心于体力劳动,争取商业学位。他既非资产阶级也不是共产主义者;老舍对他的态度有褒有贬,有对失去根性呆板青年的惋惜,也有对行动务实者的赞赏。雷金庆认为“马威就是老舍心目中理想的男性”的说法并不客观。老舍的理想青年该是不逃跑的浪漫马威和有头脑与行动力的李子荣的综合体。20世纪之交中国知识分子要求重塑自己身份的强烈渴望,来自于士大夫时代终结的逼迫和对西方知识分子自由姿态的向往。文武之道已然破碎,但是年轻学者抱着它们对现代世界依然有用的想法视图将其拼贴起来,并利用达尔文“进化论”作为青年今胜昔的理论依据,以积极学习西方知识理念作为实现重塑的手段。雷金庆独辟蹊径,研究了没有文化的华工、普通女性与留洋知识分子之间形成的对话与冲突,从这个罅隙考察转型时期中国男性气质的复杂性及男性知识分子的尴尬精神处境。精英男性已经率先体察到由阶级、种族差异而造成的处境转变,自觉要求调适身份,其建构新气质的反思与挣扎、得意与失败生动地被老舍捕捉并描绘出来,并以一种谨慎的怀疑主义予以审视和批判。“文”与“武”是传统文化赋予中国男性气质的底色,它通常是有所偏重的,然而在20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身上发现了兼具二者的雄心壮志,尽管实践过程是沉浮不定的。
二、“文武”的消长——老舍思想的矛盾与求索
陈慧敏认为老舍的68个中短篇小说集中体现出他作为文人却在动荡混乱的革命年代产生的对“文”与“武”迥异身份的双重向往及对民族精神建构过程中男性气质要求的冲突,并认为对这种几乎是二元对立境界的追求及受挫调适的动态人格冲突过程构成老舍小说的一种精神魅力。《小铃儿》是老舍“武”情结的萌芽,抗战短篇小说反映出投笔从戎的理想,直到《恋》才对“文”予以重新肯定。[5]老舍潜意识里曾渴望弃“文”从“武”,二者冲突构成其许多小说的一种张力。幽默则成为调节冲突紧张感的自我解脱之道。老舍有时痛恨自己的文人身份,是由于他深切了解乱世中文人的脆弱特质与无法一展长才的无奈心境;同时又明知“武”的某些手段和理念已经成为过去,无论是刺杀政客失败的李景纯还是习得一身好武艺的拳师沙子龙都失去了那个“侠”的时代。童年时为父报仇的想法,到抗战时期演变为抵御外敌、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老舍的爱国抗战小说中“武”的思想上升到重要位置,甚至以民间艺人的身份投身抗战宣传,实践“武”的理想。陈慧敏的研究为我们重估老舍抗战时期的文艺提供了新的突破口,如果是“文武”理想齐头并进并在战时有个应激权重的话,那么老舍抗战时期的很多创作现象和小说特征就比较易于理解了。而且其中大部分论点显然站得住脚,比如老舍思想中“侠”的一面,那强烈的爱憎、除暴安良的理想,使他与许多士大夫文人区别开来,呈现出更阳刚的男性气质。任何一种创作行为都不可能只为一种力量所促成,而这种二元模式的引入有助于梳理老舍多阶段小说创作的思想演变主线,尽管它并不完备。顺着这条线走下去,可以对建国后甚至文革时期老舍的创作心理进行大胆假设和求证。比如,老舍之死是否有“文武"理想覆灭的原因?而这理想已经内化为他骨血的一部分。这个话题和其他的一些命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老舍与中国革命,老舍爱国主义的演变过程,老舍怀疑主义的思想路径,老舍整个创作生涯的几次大转变,老舍幽默的演变过程等等。继续挖下去就会发现,同其他英语世界的动态研究一样,“文武”观的演进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要解剖老舍创作思想的肌理,它仅提供了一个起步的平台。
老舍“文武”思想的消长是中国整体文化环境变动下文武消长思想史的一部分。雷金庆在《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这部英文专著中论证了中国男性气质建构从“阴阳”发轫,到孔孟学派对“文”的推崇、后世“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对“文人”的偏爱,再到元明时期“文”被置于边缘地位,“五四”和八十年代“文”的集中被重视,勾勒了一条中国社会“文武观”发展的曲线。老舍的男性气质观在这条历史线索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横向比较的话,老舍自觉对民国文化转型期男人尤其是文人的角色转变进行了深沉思考,并将其纳入全球化的语境中予以观照;对男性气质的反思是鲁迅开创的启蒙的现实主义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类似的文本有鲁迅《孤独者》、郁达夫《沉沦》、钱钟书《围城》、王蒙《活动变人形》等,而老舍出于对“侠文化”的偏爱及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更希望知识分子向前走一步,突破几千年来传统的“文人”柔弱素质,摆脱“重文轻武”“重文轻商”的观念,追求“文武双全”的理想,使自己更丰厚和硬朗起来。从纵向看,老舍的“文武观”在发展中仍倾向于强调“文人”传统,带有明显的儒家印记。对于具体如何实现“文武”结合,使民族气质中增添一份雄强和理性的力量,他的探索如同沈从文、莫言这些“乡土”作家一样还处在理论探讨的阶段,呈现出矛盾和理想主义的图景。
三、“文武”视野与两性关系中的男性——老舍的个性理解
老舍认为社会转型期的男性气质很重要地体现在两性关系中,这种对两性关系的探讨和独特反思贯穿于他整个小说创作生涯。儒家价值观崩塌、男女平等观念出现对男女关系和男性气质形成强烈冲击。首先,爱情是文人颠覆旧秩序展现男性气质的重要场域。正如李欧梵所说,对文人来说,爱情已经成为新式道德的一个象征,轻而易举地取代了传统礼仪中仰赖于外界的约束。[6]这才有了《离婚》、《二马》、《骆驼祥子》等对男性在两性关系中的行为要求。他既看到男性在勇于冲破封建束缚、张扬自我意识方面是新式爱情的自觉追求者,又要求男性尤其是青年男性从小我的情爱中走出来,在特殊的革命历史时期勤奋务实、学好知识、报效祖国。从《老张的哲学》开始,他探讨不合规矩的爱情是男性气质自我强化的表现,同时爱情不是男性气质建构的必要条件,甚至有时是种消极因素;他如同质疑盲目的学生运动一样质疑着所谓自由恋爱。老舍很少细腻地描写恋爱,尤其是鲜少塑造为了爱情舍弃一切的男性形象。他笔下的硬汉居多。其次,老舍意识到男性气质开始在与女性气质这个新参照物的映衬下折射出别样的意义。在民国时期,传统中只有男人可以把握的文武观念被新女性挑战了。女性在传统中国社会被阻拦在“文武”领域之外,转型期至少在观念上为他们进入“文武”的话语场进行权力争夺提供了观念上的准备。此时的男性气质无疑备受挑战,虎妞、温都母女就是挑战者。虎妞代表着男女关系中主动权的互换,而温都母女则代表跨种族的罗曼史对中国男性的魅惑及对男性身份的压迫。二马父子是受过中国式教育的文人,而温都太太和女儿按照英国标准只是中下层,结果是二马被质疑、被抛弃。在批判传统男性气质被固守而造成悲剧的同时,《猫城记》中老舍刻画了一类受过教育的女性:肤浅,爱打扮,模仿外国潮流,丢失了持家能力也并未获得新的美德。可见老舍认为无论是男性气质中过时的一面还是刚建构的女性气质中不理智的一面都值得被抛弃,这种扬弃的态度实质是老舍对儒家文化的态度。
陈慧敏认为老舍早期小说中关于女性及男女关系的思考经常以某种幽默方式表达出来,《爱的小鬼》《同盟》就是如此,揶揄那些永远无法理解喜欢的女性及成为失败情人的男性。[7]这反映出传统男性气质中自私、自我、粗糙的一面,同时也许证明老舍作为男性的气质中缺失的一块。基于老舍骨子里的传统意识,他很少表现浪漫爱情和将爱情理想化,多从性、经济关系、两性战争、性别政治等角度来刻画两性,叙述者多采用男性声音和视角。王德威却认为阶级和种族可能导致草率肤浅的结论,特别在使用爱情和性作为小说的工具来呈现时。[8]这不无道理。外国男人同外国女人一样被排除在传统中国人对于男性气质的考虑之外。老舍使小说里的英国人空洞如伊牧师,大嗓门如醉汉亚历山大,自私如恶霸保罗。种种迹象表明老舍很不认同中国男性照着西方男性的样子来重构自己,也没有找到更理想的参照物。老舍对女性的塑造流于简单的二分法而缺乏更饱满细腻的魅力,传统的和现代的女性被区别对待,老舍更倾向于支持前者。而《二马》塑造的温都母女因为种族突出的需要而被粗暴处理了。老舍小说中的两性书写是“五四”作家中的个案,他反对无头脑的男女解放,反而表现出一种如托尔斯泰一般的保守性;倾向欣赏贤妻良母式的女性,而对所谓新女性有一种隐性怀疑。这说明老舍并没有做好准备要男性在家庭关系中也来一场大变革,而家庭中的男性言说远非《离婚》题材能穷尽的;一接触到新式爱情、婚姻中的男性这个话题,老舍的反应不是回避就是相对潦草地去表现,都说明老舍不擅长以女性为参照物来反思和表现男性。
总之,老舍小说对于中国男性气质重构的现代性反思是个与性别、种族、阶级、民族国家相联系的宏大命题。男性气质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同样文学作品中的男性气质观念也是一种建构,与具体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9]老舍心中一直有“文武双全”的自我要求和崇高理想,这导致他在一生的创作和社会实践活动中不间断地进行身份试错,造成他个人追求及小说内涵中对“文”和“武”气质的轮动强调,反映出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和身份焦虑。他在小说中实践着对中国现代男性气质的构想,认为理想的男性气质是既要继承儒家传统文化赋予的道德伦理内涵,又要勇于突破,比如过于文质及脱离实际,比如避世或不中不西。他更不认为西方的男性气质是中国男性要学习的榜样,尤其反感取其皮毛的虚荣做派,对待西方的男性气质及后面才出现的女性气质这类参照物还是抱一种慎重的态度为好。当代社会对“男性气质”的世俗和形而上意义的关注更密切,中国社会男性“雌化”和女性 “雄化”成为一种显见的现状;对男性气质重构的忧虑从民国时期就开始了,老舍及“新儒学”的思想者们有个共同点,都在为立足传统文化对民族性格的现代性建构做出理论探索,而精英知识分子如何发声并传达给大众、影响大众则是一个沉重的实践命题。英语世界的学者对老舍男性气质观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仍有可商榷之处,比如将对男性气质的追求及英雄气概的自我把握与“厌女症”等现代术语臆想性地联系起来就易流入主观性太强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