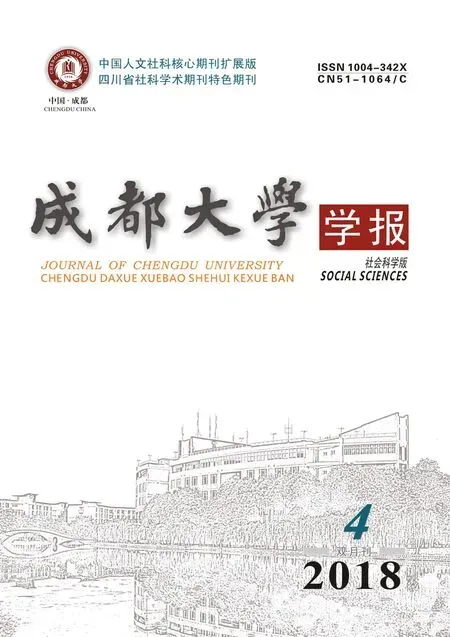解读《卑劣的灵魂》中的环境种族主义
李润润 李 伟
(安徽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00)
在美国当代印第安人作家中,美国本土裔女作家琳达·霍根颇有建树,她的作品大多围绕美国本土族裔奇卡索部落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风土人情而展开。除了作家的身份,霍根还是一个十足的环保主义者。通过她的作品,作家呼吁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与其他印第安作家相比,霍根不论是在诗歌、小说还是在散文创作中都更加集中关注一个凸显的主题——环境,以美国印第安居民所特有的传统文化视角对于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变迁进行鞭挞,对于印第安居民在此过程中的惨痛经历进行回顾,在对历史的再阐释和对殖民暴力的控诉中强调其社会和政治的诉求。
霍根在1990年推出的小说《卑劣的灵魂》一经出版就受到极大的关注。《洛杉矶时报》发表的书评认为这部作品堪称“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就如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和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用魔法师的目光考虑他们的政治史,琳达·霍根则通过奇事和魔幻审视某些血腥的美国真相”。
目前国内对琳达·霍根的作品研究比较有限,对于《卑劣的灵魂》这部作品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路洁和邹惠玲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将霍根的两部作品《北极光》和《卑劣的灵魂》结合起来从而“再现了白人统治与压榨下印第安人水深火热的处境和白人与印第安人水火不相容的伦理选择”[1]。唐建南和刘凯菁从后殖民生态的角度“揭露西方霸权主义者的卑劣灵魂”[2]。在此研究基础之上,本文将从环境种族主义的视角解读《卑劣的灵魂》,将印第安人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与种族主义联系起来。由于美国白人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对石油进行肆意开采以及对土地的不合理利用,从而给印第安人带来了环境和精神上的双重危机。在这场面对环境非正义行为的运动中,印第安人不仅依靠自己的绵薄之力奋起应战,还尽力将自己的生态思想传递给白人,借此希望美国白人能够反思一下自身的环境种族主义行为。
一、《卑劣的灵魂》中的环境种族主义行为
霍根从小就目睹了身边的印第安人因为身份差异而不得不面对的社会变迁与动荡。她从小成长的印第安人世界俄克拉荷马与印白混居的丹佛市为她提供了一个既单纯又复杂的文化大背景,一方面她可以去体会淳朴的印第安人灵学思想传统,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适应不断变更的混杂的社会洪流的影响。这些关于种族问题的矛盾和冲突在《卑劣的灵魂》这部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该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历史事实为原型,以印第安人保留地上突然被发掘的石油而引发的一系列凶杀案为主要故事背景。琳达·霍根在文学作品中将故事发生的地点移至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一个名叫瓦托纳(Watona)的印第安小镇。小镇上印第安居民的生活因为突然被发现的丰富的石油资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些石油资源对印第安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突然发现的石油资源让小镇上的居民接二连三地死亡或失踪。小镇居民格雷斯·布兰科特(Grace Blanket) 根据道斯法案获得了160英亩干旱的砂石地。这些土地一开始因为贫瘠被称为“不毛之地”(The Barren Land)。后来在这片被人抛弃的土地上却因为意外发现了石油而变成一块“贵族之地”(The Baron Land)。然而不幸的是,因为土地下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一夜暴富的格雷斯却被残忍地杀害了。“然后在光天化日下,一声枪响打破了空气的沉寂……那两个男人把格雷斯的尸体放在他们中间,好像她只是一个星期日外出的女朋友。”[3]14不仅如此,死亡的阴影还蔓延至她的女儿、妹妹、妹夫等所有可能获得土地继承权的亲人们。事实上,围绕这笔巨大的石油财富,已先后有近20人莫名地死亡或失踪。可以说,对于印第安人而言,巨大的石油财富并没有为族人带来幸福的生活,而是一切灾难的开始。
其次,除了笼罩在小镇上的死亡阴影之外,镇上印第安居民的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自从美国白人在瓦托纳小镇上开采石油之后,曾经生机勃勃的土地变得满目疮痍。印第安人每天不得不面对和忍受小镇周围土地上因为石油开采而被挖掘的一个个黑洞。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全非,他们栖息的土地变得伤痕累累,曾经茂密的森林变成了一片焦黑的荒山秃岭,野生动物也在逐渐濒临灭绝。在小说中,霍根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白人对待地球母亲的残忍方式,他们贪婪地想要榨取这片土地上的最后一滴石油。“一阵爆炸声把他们震得站起来了,使他们完全清醒了。它摇晃着大地,好像它被分开了。”[3]75
二、“环境种族主义"行为背后的原因
“20世纪以来,维护环境正义活动中,人们越发注意到一个事实:在不同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少数族裔社区以及社会弱势人群,正在不公正地成为有毒垃圾、空气污染、水污染、各种军事武器试验所导致的环境灾难的受害者。”美国基督教教会联合会在1987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上将上述环境种族歧视现象命名为“环境种族主义”。
在《卑劣的灵魂》这部作品中,为什么以格雷斯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人群没有享受到财富带来的福祉,反而成为财富的受害者?为什么石油资源给他们带来的只有数不清的磨难和死亡呢?为什么受伤害的一直都是印第安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印第安人正在不公正地沦为白人发展经济所导致的环境灾难的最大受害者。作为一部围绕石油而展开杀戮史实为背景的故事,作品中的白人出于贪婪疯狂掠夺和占有印第安人土地下的石油资源。地底下被发现的丰富石油资源让白人在巨大的财富面前利益熏心、草菅人命。让人感到更愤怒的是,这凶残的明目张胆的罪行却无法在联邦法律的框架中得以申诉和惩处。上述种族歧视现象就是典型的“环境种族正义”。美国政府一直以来所宣扬的公正与民主,在印第安人所面临的环境问题面前,根本就是一个幌子。霍根通过文学之笔真实地再现了这段暴力的罪恶历史。她指责美国白人的环境种族非正义行为造成的不公使当地的环境日益恶化,使印第安人的幸福生活遭到了严重的威胁。通过对印第安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生态灾难的描写,霍根有力地控诉了白人社会的环境种族非正义行为。
霍根不仅仅是在为她的同胞所遭受的残害讨回公道,更是为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战。一开始,美国白人为了发展自身的经济将印第安人强行迁移至被白人嫌弃的贫瘠的土地上生活。然而当这片土地上发现了石油之后,印第安人又一次遭受了迫害。不仅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印第安人再次遭到挤压、驱逐甚至失去生命,甚至连这片土地也成为被无情掠夺的最大受害者。借用小说中印第安人牧师乔·比利(Joe Billy)的话,这不仅仅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场人与自然之间的战争。“他们在向大地挑战,他们烧毁了我们的森林和玉米地……”[3]14
三、如何面对环境种族主义行为
霍根在小说中讲述了白人和印第安人围绕石油资源而展开斗争的故事。“印第安人的世界正在与白人的世界相互撞击”[3]13。小镇上的每一个印第安人在这个相互撞击的过程中都遭遇了物质和精神上的不公。当财富从贫穷的印第安人的家园转移到相对富裕的白人手中时,正义遭受到了损害。那么在这场对抗白人贪欲的斗争中,印第安人该如何实现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身份构建呢?
首先,小镇上的印第安居民要切实做到保护好脚下的这片土地。对于印第安人而言,土地绝不仅仅是用于开发从而获取利益的工具,它更是承载所有生命的载体,是所有生命的源泉。“这是印第安人的土地。这是我们的宝贝,是我们的领土。"[3]310以格雷克劳德(Graycloud family)一家人为代表的小镇印第安人民众都清楚地知道谁是杀害格雷斯等人的元凶,也知道在美国现有的法律体制下,利令智昏的白人并不会为他们伸张正义。所以在这场保护族人权利和对抗白人贪欲的斗争中,只有保护好脚下的这片土地,才能保全族人,才能阻止更多的罪恶。正如基尔·霍布森(Geary Hobson)在《被记住的土地》(The Remembered Earth,1980)的前言中写道:“遗产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土地,土地就是遗产。通过记住这些——人民、大地、过去——的关系,我们重申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延续的力量。……‘人民'和‘土地’是无法区分,不可分割的。”[5]
其次,印第安人可以借助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帮助族人度过这场危机。在远离小镇的某个僻静之处生活着一群古老的族人。因为他们隐居在山上,所以被小镇上的印第安居民尊称为“山人”(The Hill People)。尽管生活在别处,山上的古老族人却一直默默地关注瓦托纳小镇上的情况、关心格雷克劳德等印第安居民的安危并指导他们与白人作斗争。可以说,“山人”担当着小镇居民精神领袖的角色,指引着他们回归传统,实现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身份构建。“在山人古老的居住地弥漫着一种不同的安宁,那里如此宁静,它深深地浸入大地火红的骨架中。”[3]253他们在这场保卫大地的战争中伸张了正义,也最终引导白人重新认识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印第安老人米卡尔·霍斯通过书写《霍斯福音》来传递印第安人的精神信仰。他说道:“《圣经》满是错误,我想我会校正它,例如,它何处提及所有的生物都平等合一?”[3]273于他而言,书写更像是一种救赎的行为。霍斯的书写行为在为族人传承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给白人以警醒和启示。可以说,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印第安人的心灵指南,也是指引白人行为的精神向导。它教导人们“尊崇天空父亲和大地母亲,照看所有的一切……与大地温和共存……向大地祈祷,修复身心,恢复表达,重塑灵魂,使之与自然和宇宙和谐共处……”[3]361
再次,在这场面对环境非正义行为的运动中,印第安人不仅依靠自己的绵薄之力奋起应战,还尽力将自己的生态思想传递给其他人。在小说中,克里族人牧师乔·比利(Joe Billy)和警探斯泰斯·雷德·霍克(Stace Red Hawk)的思想变化彰显了印第安文化的精神影响力。
作为精神世界的导师,克里族人牧师乔·比利摒弃了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试图接受印第安传统文化中关于“万物合一”的灵学思想。通过这些方式,他最终保全大地免遭涂炭,保护族人免遭杀戮。年轻时的乔·比利赢得白人女子玛莎的芳心。从神学院毕业回到家乡后,他立志拯救和服务于他自己的印第安乡民。在小镇上的浸礼会教堂里,乔对他的教众们宣讲着神的旨意。然而白人与印第安人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激烈冲突让他逐渐意识到:在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中,白人的上帝已经无法再给印第安人信众带来心灵上的慰藉。白人在探测石油时打井爆破的声音将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大地撕裂。最后,连比利牧师自己都不再相信自己的布道。“那是我向别人许下的诺言,当他们在世的日子结束时,他们将进入天堂的黄金世界。我觉得自己像个伪君子。”[3]261他认识到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与印第安人的大地伦理思想的背道而驰。最终,乔·比利和他的白人妻子一同选择摒弃基督教的上帝,走向印第安“山人”的世界。
来自华盛顿的警探斯泰斯·雷德·霍克是另外一个深受印第安文化影响的例子。他同情印第安人的处境,一开始他希望用强大的联邦法律为他们伸张正义。但是,他亲眼目睹了联邦政府对于印第安人的冷漠态度。这一切让他意识到所谓强大公正的联邦法律并不能保证印第安人的安宁,更无法保护这片土地免遭白人的侵害。所以他最终放弃了政府的工作,选择信奉印第安人的传统。“他感受到了大地的灵魂……他感受到了河流的美丽和力量,他变得头脑清醒,他确信为政府工作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有时斯泰斯认为人们已经走入绝境,但有时他又知道未来是一片开阔地,他必须找到新路穿过它。”[3]248
四、结语
美国教授乔治·廷克曾说,“现代社会的生态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式、欧化的改变造成的,它逐渐突出个人而贬低共同利益,对于自治、自主、长久存在的原住民群体缺乏政治上、经济上的尊敬和理论上的认同。”[6]现代人的盲目自大更是加剧了这种生态的恶化。这种盲目自大体现在对于地球的无止境的征服,对于资源的无穷探索和贪婪占有,对于欲望的无法扼制等等。所有这一切终将造成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对立,产生各种生态危机。面对这样的现状,霍根在小说中通过历史再叙的手法既描述了印第安人所遭受的不公,又彰显了印第安人对于人类与土地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信仰所能激发的生命力。作为印第安少数族裔的一员,霍根亲自经历了印第安人所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这种不公平不公正行为在《卑劣的灵魂》中得到了充分反映。通过反复讲述各种环境种族主义行为,她积极地为印第安群体发声,呼吁并寻求环境和社会正义。“她崇尚弥合与补救,竭力传达生态保护思想,希望用文学打动心灵,改变精神状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