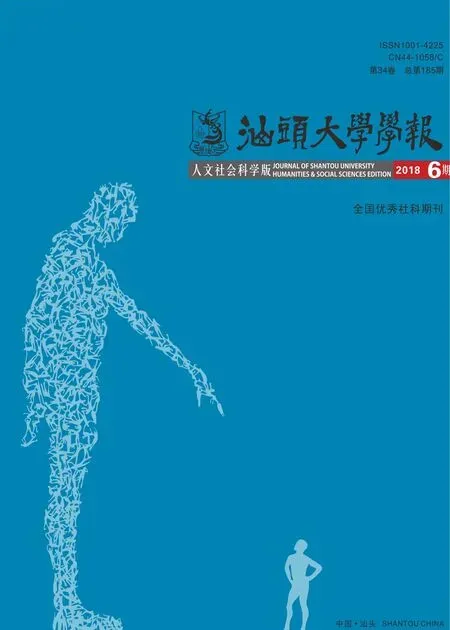“感觉到了作为人的伟大”
——纪念王富仁老师
旷新年
(清华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083)
听到王富仁老师离世的消息,十分意外与震惊,心中作痛。距离如此之近,又是如此之远;如此之远,又是如此之近。尽管王富仁老师是哺育了我、有恩于我的前辈,尽管我们有过不少交集;然而,由于我画地自狱,几乎从未有过通常意义上的交接。我从来不敢打扰任何人,甚至最好的朋友也长期不通音讯,与学界没有任何交际,更不敢让自已的文字污人眼目。
我上大学的那一年——1980年,萨特逝世,一个时代结束了。罗伯·格里耶说:“应当说所有的革命经历都事与愿违。人们反抗过北美帝国主义,却在西贡和柬埔寨让北越帝国主义取得了政权。同样,满怀热忱的共产主义者们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不过助长了苏维埃帝国主义的发展。所有的革命经历都事与愿违,也就是说都以斯大林主义告终。古巴和越南就是近例。现在我们看到什么?波兰工人阶级全体起来反抗曾是世界希望的阶级。一切都事与愿违。发展事与愿违。反殖民化事与愿违。历史事与愿违。萨特一生所坚持的那种良好意识,我觉得其他人再也不会有了。他作为资产阶级的愧疚意识,是他作为革命者的良好意识。他的愧疚意识造就了他的良好意识,使他能够无所不言。”[1]与萨特“能够无所不言”不同,鲁迅陷于无法言说的困境:“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2]自从上大学以后,我便落入了鲁迅这种无法言说和“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的状态。[3]
1989年,我入读研究生,成为了现代文学的一名学徒。那个时代的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都不可能错过王富仁老师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这本书和钱理群老师的《心灵的探寻》不仅是鲁迅研究划时代的著作,而且也是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纪念碑。
自我读研究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渐渐生变。今天,许多人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历史慢慢颠倒过来,价值纷纷颠倒过来,一切的一切都翻了个个。白的变成了黑的,黑的变成了白的。比起沧海桑田的社会巨变来,现代文学的变化只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我们这几十年遭遇的变化可能超过了有文字记述以来的几千年。对于我这样与世隔绝、孤陋寡闻的农民来说,真是“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产业化,学术行政化与买办化结伴而行,齐头并进。学界头面人物或以衙门自许,或挟洋以自重。“矫枉必须过正”是中国祖传的思想秘方,“深刻的片面”是新时期传销的学术秘诀,因此,旋转木马就可以称得上中国顶格的学术了。
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即便以鲁迅研究为业的学者,也开始贬低鲁迅。在他们看来,比起世界文学大师来,鲁迅矮了一截。后来,鲁迅研究慢慢地由学术研究变成了学术流言,鲁迅流言专家成为了鲁迅研究专家。由于历史的变化与时代的颠倒,自由、平等、民主这些价值遭到了时髦学术与权威学者的嘲笑、诋毁、攻击,成为了耻辱的印记,昔日的“民族魂”鲁迅今天人人得而诛之,正人君子甚至恨不能“斩草除根”“除恶务尽”。
这个时代,文人学士将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做成了招牌,悬在胸前,口中念念有词。他们将陈寅恪语录做成了学界的时尚,当成了提高身份的时装,就像时髦女性的LV和富二代的法拉利。然而,陈寅恪声明:“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4]陈寅恪并非像时髦的文人学士那样自命为西崽洋奴,奉北美扶桑为正朔。
在这个时髦、颠倒的时代里,王富仁老师依然固守着五四的精神价值,坚守着鲁迅的思想立场。他不愿意违背自已的良知,保持着自已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守护民族的灵魂。鲁迅是民族魂,而王富仁老师则以鲁迅的生命为自已的生命。于是,他遭遇了和鲁迅同样的命运,成为了堂吉诃德,成为了落伍的象征,成了被嘲笑的对象,成为了集矢之异端。在势力面前,良知多么渺小;在流行面前,思想多么无力。这种艰难和困境并不是今天的学者才遇到。王富仁老师在今天的遭遇,他那孤独的身影,令人想起鲁迅曾经的处境——“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王富仁老师是当代对鲁迅最深刻、最生动,也是最好的诠释。在我们的时代里,王富仁老师的形象与鲁迅的形象重叠在一起了。他不势利,不从众,要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一个有良心、有灵魂、有担当的人。
作为现代文学的学徒,我一直将1789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作为我的价值防线。王富仁老师必定也有他的防线。我想,在心底里,他是将自已作为五四的托命之人,在艰难时刻守护着五四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的价值。王富仁老师强调做人,人的尊严,人的良知,人的信念。在他这里,为学与做人、学术与生命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学术不是名片,乃至不仅仅是纯粹的研究,而是生命的升华,人生的提炼,人格的完成。王富仁老师以自已的生命和学术践行了五四的价值。他用生命雕塑了五四。他是五四的化身,是自由和平等的化身。在他的身上,既有不可亵渎的庄严,又有众生平等的包容。他既令人景仰,又可以亲近。
张爱玲是中国新文学作家中作品被翻译成外语最多的作家。①庄信正《张爱玲致庄信正》(1966-10-19)注解:“张爱玲一九六九年所写履历中提到那时TheRice-SproutSong已被译成二十三种语文,NakedEarth也有十几种译文。”庄信正编注《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16页。《秧歌》被翻译成了23种语言,不仅使鲁迅,而且足以使任何一位汉语作家黯然失色。然而,这并非因为夏志清所吹嘘的什么张爱玲的文学成就,而是因为美国金多,并且显示了美国的宣传机器是多么强大,冷战文学的战线是多么漫长。不少人绘声绘色地描述过老舍、沈从文怎样错过了诺贝尔文学奖,却没有听说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翻译成了23种语言的张爱玲错过了诺贝尔文学奖,甚至国际上从未有人认真将张爱玲与纯文学联系起来。这并不令人意外。可见诺贝尔文学奖还没有那么低级、无聊。因此,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张爱玲神话以及张爱玲与鲁迅评价的颠倒耐人寻味。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直言不讳,亚洲只有两位作家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这就是泰戈尔和鲁迅。
当鲁迅逝世的时候,人民尊奉他为“民族魂”。当时有四万万五千万之众的中国,日寇如入无人之境。用陈寅恪的说法,“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②吴宓所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陈寅恪的谈话,见《吴宓日记》第6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168页。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政府、军队、知识界充满了蔑视,他们可以轻侮中国的一切。然而,在鲁迅的身上,他们感到了不可征服的力量。通过亲近鲁迅,日本学者增田涉“感觉到了作为人的伟大”。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5]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将成为历史定论。在鲁迅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纯粹的人性、淳美的人生。
在抗日战争中,为学界所瞩目与期待的历史学家张荫麟不幸英年早逝,成为学界最大的损失。史学大师陈寅恪对他的赞誉,早已为常人所知:“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6]张荫麟难得将眼光投向当代文学,全集仅有三文涉及当代文学。1929年,针对《真善美》杂志的“女作家专号”,他写了《所谓“中国女作家”》一文,忍不住对“言作家而特标女子,而必冠以作者之照像,岂其以‘一样的眼眉腰,在万千形质中偏偏生得那般软美’欤?”以及“中国所谓‘名士’,每好捧场一二‘才女’,或收罗若干‘女弟子’以为娱”的恶俗加以针砭。[7]1933年,当他听到“不卖女字”的著名左翼作家丁玲被国民党政府绑架遭遇不测,义愤填膺写下了《悼丁玲》一文。①鲁迅也因此写了《悼丁君》一诗:“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见《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153页。第三篇关于当代文学的文字是鲁迅论。1934年,鲁迅的杂文集《南腔北调集》出版,他写了书评《读〈南腔北调集〉》。他说,“为求名副其实,此文当题为《〈南腔北调集〉颂》。”实质上,这也并非一篇《〈南腔北调集〉颂》,而是一部《鲁迅颂》:“先颂周先生。他可以算得当今国内最富人性的文人了。自然人有许多种。周先生不就铸造过‘第三种人’的名词么?但我所指的是那种见着光明峻美敢于尽情赞叹,见着丑恶黑暗敢于尽情诅咒的人;是那种堂堂赳赳,贫贱不能转移,威武不能屈服的人。”“周先生本来可作‘吾道中人’。古董他是好玩的,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已成了一部标准的著作。只要他肯略为守雌守默,他尽可以加入那些坐包车,食大菜,每星期几次念念讲义,开开玩笑便拿几百块钱一个月的群体中,而成为其中的凤毛麟角。然而他现今却是绅士们戟指而詈的匪徒,海上颠沛流离的文丐。他投稿要隐姓换名,他的书没有体面的书店肯替出版。人性的确是足以累人,大丈夫的确是不容易做的。‘伤屯悼屈只此身,嗟时之人我所羞!’读周先生的书每每使我不寐。”“然而周先生可以自慰的,他已为一切感觉敏锐而未为豢养所糟蹋的青年们所向往。这种青年的向背也许不足以卜一个文人的前途,却断然足以卜一个文人所依附的正义的命运。自人类有主义以来,这条公理未曾碰过例外。当周先生的杂感被绅士们鄙弃的时候,颇有人誉他为先驱者,我还有点怀疑。但自从他公开地转向以来,这种称誉他确足以当之无愧。最难得的是当许多比他更先的先驱者早已被动地缄口无声,或自动地改变了口号的时候,他才唱着‘南腔北调’,来守着一株叶落枝摧的孤树,作秋后的鸣蝉。但夏天迟早会再出现的。而一个光明的‘苛士’,当屯否晦塞的时候,正需一个‘斵轮老手’来撑持。假如钳制和老年不足以销尽他创造的生机,那么,我敢预言,在未来十年的中国文坛上,他要占最重要的地位的。”[8]张荫麟的鲁迅论不仅充分显示了他史学大家的非凡眼光,而且是高贵心灵的共鸣,是最纯粹的人性的感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经过一个世纪的进化,“女作家”已经进化成为了“美女作家”。对中国文学这样一种进化方式,作为史学大家的张萌麟恐怕要跌破眼镜了。
当一个人越接近纯粹的生命,越接近真理的时候,也就越接近鲁迅,就像闻一多那样。1944年,闻一多在《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痛切深刻地检讨了自己,毫无保留地颂扬了鲁迅:“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他对帝国主义,对买办大亨,对当权人物,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宁可流亡受苦,也不妥协。鲁迅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伟大的作品,和他这种高尚的人格是分不开的,学习鲁迅,我想先得学习他这种高尚的人格。”“有人不喜欢鲁迅,他不让别人喜欢,因为嫌他说话讨厌,所以不准提到鲁迅的名字。也有人不喜欢鲁迅,倒愿意常常提到鲁迅的名字,是为了骂骂鲁迅。因为,据说当时一旦鲁迅回骂就可以出名。现在,也可以对某些人表明自己的‘忠诚’。前者可谓之反动,后者只好叫做无耻了。其实,反动和无耻本来也是分不开的。”“除了这样两种人,也还有一种自命清高的人,就像我自己这样的一批人。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人自称‘京派’的学者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的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上的。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那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9]
鲁迅远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能够衡量的。他是文化巨人,是当之无愧的民族灵魂。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鲁迅,就没有现代文学。或者说,没有鲁迅,中国新文学就会黯淡无光。鲁迅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鲁迅不仅是中国的灵魂,而且也是亚洲的灵魂,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灵魂,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灵魂。
鲁迅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高高在上把自已当成了主子,像胡适那样打着“宽容”的官腔,有着“光明所到,黑暗自消”的法力;而是因为他彻底认清了自已奴隶的地位和身份,并且坚定地站在奴隶们的立场上。晚年,他培养了萧军、萧红、叶紫等著名青年作家,编辑了有名的“奴隶丛书”。他感叹,从前是满清的奴隶,后来成了民国的奴隶。他把周起应称为“奴隶总管”,因此,也是周起应、狄克们的奴隶。但是,他是奴隶,却不是奴才。
曾经某个短暂的瞬间,鲁迅受到圣旨的庇护,《鲁迅全集》像《四书五经》一般神圣。然而,王富仁老师知道,在大伪的时代里,吃鲁迅教的徒众,就像吃基督教的徒众一样,只是势利之徒、乌合之众。在势力消散以后,徒众也会一哄而散。在王富仁老师这里,鲁迅的伟大,并不是势力的伟大,而是精神的伟大。也只有在势力消散以后,才得见真的信仰。
鲁迅一个“爬”字和一个“踹”字,深刻而生动地概括了中国的广大众生相。在我看来,许多所谓学者名流仅仅用鲁迅的这两个字就可以概括净尽,最多再加上一个“装”字。王富仁老师是一个很不像“大师”的学者,是学界中难得一见的敞亮的人物。与王富仁老师在一起,就像在乡亲中间一样无拘无束,从来不会感觉到心累,更不会像在“大师”们面前一样起鸡皮疙瘩。今天在每一个暴发户的大门上都悬着“皇家”“御用”或者“贵族”“精英”的标牌,他们对于自由、民主、平等有多少敌意、仇恨、污蔑,就有多少丑恶、肮脏、腐败。
王富仁老师是鲁迅的守灵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的守夜人。王富仁老师的离去,使得现代文学界愈加萧条和空虚,并且意味着与我们血肉相联的一个时代的真正远去。
王富仁老师是当代最朴素的一位学者,平凡中寓着伟大,在这个泡沫的时代里格外宝贵。有同学为王富仁老师愤愤不平,他甚至自责起自已无意识的势利来:比起那些位居权位、呼朋引类、呼风唤雨、俨然大师的人物来,王富仁老师的成就远远被低估了。然而,这难道不正是真正的学者与纸糊的学者之间的区别吗?难道不是独战众数的孤独者的宿命吗?
孟子有言:“无恒产者无恒心。”长期以来,中国的“读书人”常常处于物质破产的边缘,因此,也经常处于精神破产的边缘。历史学家吕思勉认为,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尤其因为缺乏经济基础,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所谓读书人,仁甚少,智甚少,勇甚少。[10]然而,只要不肮脏、不污浊、不下作,不阴暗、不虚伪、不委琐、不趋炎附势、不装腔作势,便都可喜、可爱、可亲、可师、可友。当我看到有所谓作家由替汉奸汪精卫辩护而辱及三百多年前抵抗异族入侵、死不瞑目的英灵,真不知今世何世。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在古典文学专业,诋毁民族英烈,歌颂汉奸的“贡献”,认为舍生取义毁灭了文化,当汉奸保存了文化,将汉奸视为文化传承的介体,成为了学术新潮。如果是这样的话,文天祥、陆秀夫岂不成了中国文化的罪人,而洪承畴、周作人则成了中国文化的功臣?呜呼!假如所谓文化竟然只能是下流的、禽兽不如的汉奸文化的话,我宁可没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