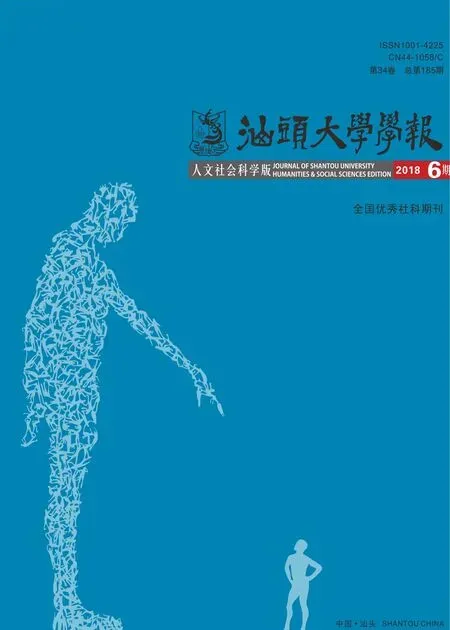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与学术生成
——王富仁先生新国学研究管窥
张艳艳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前 言
在《中国文化的守夜人》自序中,王富仁先生谈及其深耕鲁迅文本世界的体验:“鲁迅是一个醒着的人,感觉中国还有一个醒着的人,我心里多少感觉踏实些,即使对现实的世界仍然是迷蒙的,仍然少了些恐惧感。”[1]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表述之前有一段与之呼应的个人情感流露的话:“记得小时候和母亲住在农村一座黑乎乎的土屋中,睡梦中醒来,见母亲还坐在我的身边,心里就感到很踏实,很安全,若是发现身边没有一个醒着的人,心里马上就恐怖起来。”[1]母亲之于孩童的情感慰藉、鲁迅之于学者的心理力量,并置同构,彰显出王富仁先生学术生成的底色:从生命自身出发。可以说,基于生命体验的学术生成在王富仁先生的鲁迅研究中是一以贯之的,也是其整个学术研究的基底。钱理群先生讲:“其内在的精神,即学术研究的生命特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读者之间的‘生命的交融’,是具有普遍性的,至少是构成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派别,我称为‘生命学派’的基本特征。而富仁正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最重要的代表之一。”[2]王富仁先生的学术研究往往浩荡之气充塞,思想的激情携着巨大的撼动力冲击着读者的心灵世界,带来强烈的共振互鸣效应,感人深、发人省。知己所言,即是此意。学问与生命的交融状态,令多少学子同道豁然,在为数可观的纪念文章里都有所显现,李怡教授说得痛快:“他使我的生命展开了”[3],真是心有戚戚焉。
一
新国学研究亦是建立在此“生命的交融”基础上的,王富仁先生说:“新国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与我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的体验有直接关系的。”[4]对于20世纪以降的中国现当代学术生态,王富仁先生处身其中是有着深切的体认的,基于此深切体认,王富仁先生切中肯綮:“在当前,有很多对中国现当代学术的反思和批评,但我认为,归宿感的危机和由此而来的自我意识形式的混乱则是影响中国学术继续发展的关键因素。”[5]就学术生成的两个面向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而言,研究者的自我认知是学术生成的机枢所在。新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共同体,即包含这一内在的问题视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与身份认同的问题。只有透析现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混乱与认同危机的内在质里,才有可能讨论中国学术共同体的良性生长。
基于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宏阔又缜密的耙梳,王富仁先生彰明了学术认知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角色认同的两种主要误区,一种是将学术卷裹进政治权力之中,丧失了学术的本体性与独立性。一种则将学术活动的价值评判权利让渡出去,以西方文化为评判尺牍,丧失了中国学术的本位意识。
对于前一种,就其质里而言又有两个形态,一种形态是试图以“政统”控制“道统”,实现政治话语对学术话语的主动掌控,王富仁先生称之为“政治主体性的越界”。[5]不仅严重扰乱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实质上对政体本身也带来负面影响,晚近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即是如此。“从形式上,以‘革命’的名义对中国现代学院文化和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批判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实质上,却将政治的权力大量引进了文化的关系之中,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之间的平等竞争关系,紊乱了中国文化内部的秩序,使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5]另一种形态是知识分子自我角色认知上混同“道统”与“政统”,王富仁先生将其追溯到孟子以“帝王师”自居的角色认同开启的儒家知识分子传统,“从孟子开始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产生的关于‘王者之师’的梦想,实际都是虚幻不实的,都是在‘教’与‘学’的观念发生分裂之后在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头脑里产生的错觉。”[6]这种知识分子自我精英化及其变形自古典时期绵延到现代,看似匡世救民,实则“在更多的情况下倒是使自己更严重地丧失了独立性”,[6]沦为被政治空间束缚住的臣僚型知识分子。就具体呈现而言,两种形态往往有机缠绕在一起,共同导致学术独立性与本体性的丧失。
对于后一种,在晚清以降的近现代学术史上尤为显著,近现代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国族诉求中,渐趋以西方欧美文化为圭臬,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断裂感,另一方面以“西化”格义中国文化也终将是疏离的,在导致知识分子归属感缺失的同时,实质上带来中国学术的民族本位性的缺失。在王富仁先生看来,晚清洋务派在“中-西”“体-用”的学术框架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以中学的体统和西学的用,在道-器一体关系中其实是错位的,在学术本位意义上是失败的。就二三十年代的西化派与80年代改革开放学术复苏以来的“西学热”而言,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在“中-西”“传统-现代”并置的二元分立的学术框架中展开的,用王富仁先生的话来说,他们承续的是“传统的今文学派和西方的进化论结合而成的学术传统”,但是学术研究立场则挪移向西学为体,以西方文化为现代化、世界化的价值准绳评判文化、中国与世界,终将导致学术研究主体意识与民族本位的双重沦丧。
二
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角色认同与学术生成内在危机的洞悉,是王富仁先生提倡新国学观念的文化语境;对学术独立性与研究者主体意识的昌明则是其新国学研究展开的前提,由此我们进一步阐释新国学作为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内在构成。借用王富仁先生的话:“学术是一种参与”,[5]就是参与什么与怎样参与的问题。
“参与什么”勾勒新国学研究的学术谱系,谱系的明晰基于历史的梳理。《新国学研究论纲》可谓王富仁先生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凝结。
王富仁先生将现代文化分为三种形态,分别是现代革命文化、现代学院文化、现代社会文化。它们的差异并不来自于研究对象或者知识领域的差异,而是基于中国新文化在革新传统文化的共同基础上不同的演化方向。这样的划分方式包含王富仁先生一个极其深刻的洞见,即其对于学术的理解:“我们所说的学术,实际上有两个并不完全相同的层面:其一是知识的层面(包括现实经验和已有的理论知识两类),其二是主体精神的层面。”[5]不是研究者的具体研究对象,也不是研究者所掌握的理论,而是研究者的主体精神决定着学术的方向与特质。革命文化“主张的是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思想革命”[5],在学术与社会政治关系格局中展开;学院文化“主张的则主要是科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思想革命”[5],在导师与学生的学术传承格局中展开;社会文化“主张的是国民精神发展意义上的思想革命”[5],在个人与社会的心灵沟通关系中展开。非常清楚,三者作为文化,是思想革命,而非其他。尤其是对于革命文化的理解,革命并非学术,但是革命过程产生的文化同时反过来影响革命则是学术的构成部分,将革命作为政治话语、革命文化作为学术话语的清晰区隔在20世纪文化语境中无疑是意义深重的见地。一方面彰显了学术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另一方面也深化了对20世纪学术谱系的全面理解。尽管王富仁先生在个人的学术气质上更加服膺鲁迅,却认定:“比鲁迅更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与发展的是胡适。”[5]伴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来的学院文化更加代表现代学术的独立性,职业化、专门化的现代知识分子更代表一般性的研究者的形态。
静止地来看,这三种文化形态是分途发展起来、彼此差异,甚至是充满矛盾的;动态地来看,它们相互之间又是彼此碰撞、交错相生的。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量的社会知识分子向革命文化方向转化,深刻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形成。同时就一种文化方向而言,其内部也不是一元静止的,而是多元交会、相对相生、不断生成发展着的。“在学院文化中,也不仅仅停留在传统派和西化派的分化趋势中,西化派和西化派,传统派和传统派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分化。”[5]就西化派与新儒家学派的关系来说,恰恰是西化派的西化立场激发了现代新儒家的民族文化本位意识,促使其更为自觉、深入地阐发中国文化的特质与根性。这个由不同文化构成的现代中国学术谱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一个生成态的文化结构体,在这个意义上,王富仁先生捻出其称谓——“新国学”。
更进一步来看,近现代学术的建构尤其是“五四”新文化的发展与传统构成怎样的关系?
传统与现代、新文化与旧文化是一种断裂关系吗?刘勇教授认为王富仁先生重构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7]传统是活在当下的,传统进入现代学者的视域并因其诠释而葆有活力并成为现代学术的有机部分,这是一个“生成-积淀”“积淀-生成”[5]的持续动态过程。在表面的革新与断裂之下,王富仁先生勾勒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融变新生的内在勾连关系,见出学术生长自身的因革损益。“我认为,迄今为止中国近现代文化真正有实质意义的发展,都是通过重新回归传统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5]“实际上,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都是由我们所谓的‘旧文化’与我们所谓的‘新文化’在交叉、交织、纠缠、相互转化、相互过渡而又对峙、对立、对抗中构成的一个充满张力关系的文化格局”。[5]以鲁迅先生为例,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柱力量,就其学术气质与学术传统而言,实则“与从古文学派发展而来的章太炎的国学传统有着一脉相承的连带关系”。[5]王富仁先生梳理了近现代学术建构起来的三个学术传统:“其一是主要继承着中国古代主流正统文化命脉——名义上是儒家文化传统,实际上主要是宋明理学传统——的学术传统”;其二是继承着今文学派传统的中国近现代进化论学术传统;“其三则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在古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学传统。这三种学术传统实际影响着具体的文化形态,晚清洋务派、复古派、现代革命文化及其变体虽然立场不同,但就其主体意识而言,其实都秉持着儒家正统文化传统。当然三种学术传统与具体的文化形态并不仅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鲁迅先生的情况便是如此,章太炎的学术首先从古典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主体精神的养分,而这个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养分又滋养其在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过程中生成中国现代学术之重要一种“国学”,再进而,其所发展的现代国学传统又构成了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支柱的鲁迅学术志业的底色。学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承传代续、融变新生由此可见一斑。
承上所述,我们来理解王富仁先生对这个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谱系的称谓“新国学”:“参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存在与发展的中国学术整体就视为我们的‘国学’”,[5]它“不是规定性的,而是构成性的”,[5]“这种横向构成的‘国学’却同时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动态过程。”[5]这个学术有机整一体,“它就是我们中国学术的‘道’体。”[5]可见新国学作为观念是与王富仁先生打破学派壁垒、兼容并包的文化史观相携而生的。
王富仁先生的文化史观打破中-西、传统-现代二元框架,甚至不应有文理二元壁垒,打通学术形态既有的时空结构隔断,坚守建立中国学术的使命感并辅以持之以恒的切实努力。其将中国文化看成是生成态的文化时空结构,传统在现代学术格局中的因革损益,异质文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吸收吐纳;作为学理知识是多元的,作为现代中国学术自我养成的资源又是融通的;根本的关切点在于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即如何整合生成葆有个体性的、彰显民族意识的、共同促进人类良性未来的学术力量。新国学观念的提出源于近现代学术的演变轨迹与谱系格局,在这个意味上讲,是对于既有学术史的实况描述。当然王富仁先生对于构成这个学术整体的不同学术传统是有自己的评价的,但是这个评价并不影响其将它们全部纳入新国学这一动态学术共同体的范围里边来。就这一层来说,新国学是描述性的,是对近现代以降以至未来所有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描述性界定。当然新国学研究又不只是描述性的,在兼容并包的文化史观之下,王富仁先生个人又是有所甄认的,以学院派的、职业化知识分子的现实角色,持守学术本位的参与立场,在“个人-社会”的学术框架之下,以生命体验做底,对社会始终葆有关切,构筑其学术生成。在怎样参与的问题上,王富仁先生倡导的学术特质是清晰而鲜明的。
三
怎样参与?以学术的方式参与,或者说是以学术为本位的参与。对于学术的本质与角色、知识分子的本质与角色,王富仁先生都做了清晰界定:“全人类的以及一个民族的学术不论怎样定义,它起到的都是理性地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作用。”[5]“构成学术事业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对本民族社会实践关系的一种关切。”[5]“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就是在这种对民族现实实践关系的关怀中自然形成的,就是在对自我独立思想和见解的意义和价值的明确意识中自然生成的。”[5]明确知识分子与其学术志业的本分与职守,对知识分子来说,言说即行动,在学术关系中实现其对社会实践的关切,既是对学术独立性、本体性的坚守,又是其实现社会情怀的得当方式。从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来讲,就是立足于生命体验自身的个体性与独立性、彰显国族情怀与使命感,促进人类整体的互通性与超越性。王富仁先生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与学术生成与之两相符契。《新国学论纲》举起纲,经典现代文学研究与轴心时代诸子思想阐释张其目,纲举目张,堪为典范。
从生命体验出发,坚守学术的个体性与独立性,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两个主体的平等对话与心灵沟通之间展开的学术研究是王富仁先生新国学研究的首要特质。这里边其实有一个研究姿态的问题,即对研究对象本位性、尤其是文本本位性的尊重。其一贯强调,阅读鲁迅,“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还原式的阅读不仅是回到作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分子自身,更是要回到他们的文本世界中去理解他们。而“文本存在于语境之中”,[8]也要回到他们所存身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去理解他们。王富仁先生的鲁迅研究自始至终都贯注这一基本立场,要理解鲁迅独立、立人的思想革命,只有在三者一体呼应的结构关系中理解。鲁迅、鲁迅的文本世界与其存身的社会文化语境构成着整体性的内在互文关系,“离开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整体发展这一基点,鲁迅的整体思想都将成为一种荒谬。”[9]对孔子思想的阐释亦然,如对“孝”“丧礼”以及《乡党》篇孔子践礼行为的解读,都放到孔子言论所从出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甚至具体的言说对象中来理解,还原被神圣化而趋于刻板与教条的孔子思想以灵动的学术原发生命力。
“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知识结构,同时也是一个整体的心灵结构”。[6]作为知识分子的王富仁以其心灵结构召唤出这一悠长、深远的中国知识分子学术人格的传统谱系。从孔子到孟子、从章太炎到鲁迅,从生命的内在体验出发,以独立不倚的主体精神在整个文化传统中汲取力量、创发独立的学术思想。在王富仁先生看来,孔子思想都来自“学以成己”,对具体生命的关切,即从内心感受出发,实现个体生命自我发展的最高境界。“从‘学’到‘仁’是孔子自我成长和发展的过程,是孔子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的根本原因,”[10]这富有“主体性的学”[10]所实现的生命圆成状态从自身生命出发,在“个人-社会”的格局中,无挂碍的会通自我与他人,作为生命最高境界的“仁”,“实际是从个体人内在精神中产生的对人类、人类社会的整体关怀。”[10]而孟子思想的重要面向更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彰显上。“他又讲‘恒心’、‘不动心’,讲‘养勇’,讲‘志’,讲‘气’,讲‘知言’,讲‘浩然之气’,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知识分子人格的修养展开的。我称之为孟子的‘知识分子人格论’。”[6]章太炎的学术之独立与创新亦不在于研究对象之独立或创新,而是章太炎作为研究主体之“独立不倚的主体精神”,以此开出国学研究,成就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部分、甚至重构学术传统,成为传统富有活力新质素。在这个意味上,鲁迅承续了章太炎的这一学术传统,独立、立人,从具体的、现实的人,“从人的生命以及人的生命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角度”,[11]以文学实现其思想革命,同时赓续着自古及今的这一整个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传统。“假若说鲁迅思想是中国现代社会的立人思想,孔子思想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立人思想。”[6]我们看到,传统中国的“士”与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学术人格上的认同、承续与持守。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富有主体间性的心灵沟通与对话中彼此敞开,也因此富有个人创造性的学术不断生成,并进入整个中国学术的洪流,甚至构筑其真正的中流砥柱,在重构传统文化的同时成为传统自身。
同时我们看到,王富仁先生在勾勒这个学术传统的时候,在知识分子角色认同与学术生成上与之有深深的认同感。实际上,王富仁先生作为知识分子和其学术研究也早已嵌入这一传统之中,并成为其有机的一分子。其实其最初的学术发声便满溢这一特质,1984年写就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从思想革命的角度非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重新阐释鲁迅思想,将学术研究从与政治话语同构的格局中析出,摆脱固有的外在的价值准地束缚,以自身生命内在的独特体验与独立理解来解读,一时振聋发聩。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从其早年深耕的现代文学领域到晚年对轴心时代诸子经典的阐释,都是对此一以贯之地深入践行。
建构现代中国民族学术,彰显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独立意识与本位意识是王富仁先生倡导新国学研究的第二个核心要义。这既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境遇有关,又与当代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认同息息相关,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强调现当代中国学术生成的民族本位意识有其迫切性。新国学的边界是“通过‘民族语言’和‘国家’这两个构成性因素”[5]界定的。族裔、国家(包括地缘)、语言与学术,个中关系当然复杂深邃,我们试图讨论王富仁的两个主导看法。
一个看法,“民族语言是构成一个民族学术整体中的关键因素”。[5]“语言对于一个民族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有自己共同的语言,就有这个民族的共同体”;[5]1对民族与语言的相生相伴关系的理解与安德森有异曲同工的旨趣:“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12],学术当然是以语言文字的方式存在,显然,在全球化语境中,以民族语言存在的民族学术的本位意识正当性甚至是无需论证的。但是必须厘清的是,王富仁对于民族语言与民族学术本位意识的强调并不是在排他性甚至霸权化的方向上存在的,他特别提出一个概念:“越际学术现象”[5]。举个例子,林语堂大量英文写就的著作算不算民族学术的整体,就我们的理解来说:算。从王富仁先生提出这个问题的文化语境中看,对于世界多种语言与多元文化的译介、交流他是肯定的,对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研究、交流他也是肯定的,对于民族语言与民族学术的坚守更直接的驱动力是抵制欧美文化霸权化甚至一元化倾向。所以总体来看,民族、语言、民族学术的这个整体既是稳定的,又是开放的。
另一个看法,个人的学术语言与民族语言构成的民族学术的关系。我们用赛义德的一段话把王富仁先生贯注在整个新国学研究中的这个看法讲得更显性一点:“知识分子应该使用一个民族的语言,不只是为了方便、熟悉这些明显的理由,也是因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希望赋予那种语言一种特殊的声音、特别的腔调、一己的看法。”[13]王富仁先生对于胡适与现代中国学术关系的评价实际上暗合了这个观念,白话文运动,不仅是在个人的学术话语的意义上丰富、推进了民族学术,更是在群落意义上,直接带来了现代中国民族学术话语的崭新生态,从文言到白话文,实现的是民族学术语言的重构与新生,更是民族学术的融变新生。
最后,新国学的学术生成如何既是个人的、又是民族的、同时又是人类整体的?如果从人性的内在生命的基点来理解,三者的关系就是内在一体的。在孔子那里,个人-社会的学术框架内蕴着孔子的天下观,从内在心灵感受出发,“学以成仁”是“出于对人类社会的普遍的关心”[5]。在鲁迅那里,个人的主体性问题与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重建问题都是在整个人类文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5],三者是一体同构的。钱理群先生曾提到有些学者的疑虑,[14]全球化的语境中,如果从一元、排他、霸权化的倾向性来理解这个人类学术的整体,这个疑虑就会加大。如果从多元、兼容、丰富性的倾向性上理解人类学术的整体,就是许多文化中的许多共同构成着人类文明的整体,而非天选之民、最好的或者更好的几个构成着这个整体,这个疑虑就可以冰释,在我们看来,王富仁先生对于人类学术整体的这个理解属于后者。
结 语
由问学的职分上来说,“新国学”令人在学术谱系与自我定位上保持清晰、自省。对于生命的尊重,基础得是自我尊重,才谈得上是对他人的尊重,扩而言之,社群、国族认同上的自我尊重,继之而来的是人类共通性上的彼此尊重,以此带来人类整体的更自由、美好方向上的可能性。这是以生命体验做底的、经由理性自觉的考辨、始终保持批判性的学术立场可能辟出的道路。
纵观王富仁先生的学术研究,在研究格局上,其做了纵深、宏阔的推进;就学术精神而言,却是一以贯之地坚守;纠合两者,可以说王富仁先生的鲁迅研究始终是其新国学研究的主核,鲁迅精神可谓传统中国士之道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涅槃重生。独立、立人,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王富仁先生的自我认同与学术生成与之同声共气。
故此,我们将王富仁先生送给鲁迅的话送给富仁先生:
“他返回了个人,返回了个人存在的小空间,返回了个人存在的那个‘现在’,那个时间上的一刹那,但他却以这种方式,进入了整个世界,进入了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时间隧道。”[15]
“他永远站立在他用自己的生命为自己开辟的那个时间和空间的结构之中。”[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