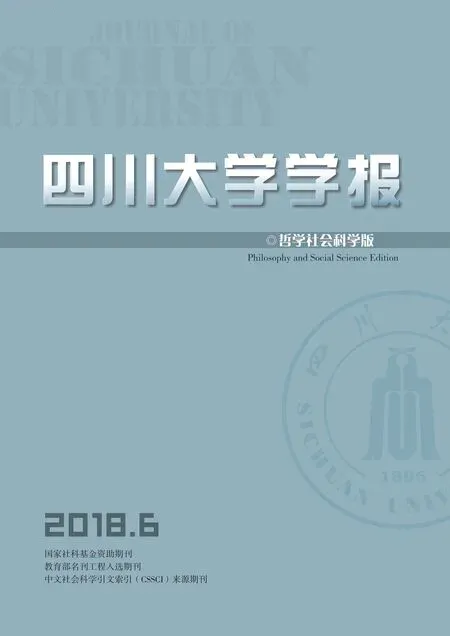特色小镇:思想流变及本质特征
,,
引 言
特色小镇建设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随着国家战略部署的推进,我国已将特色小镇的培育与建设视为治理“城市病”的一种有效方式。*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城市开发》 2017年第8期。在此之前,西方学术界已经以田园城市理论为切入,就如何培育新型城镇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部分探讨因被落实到市镇运动中,因此在英美世界中一般也被称为“新镇计划”。*Frederic J. Osborn and Arnold Whittick, New Towns: Their Origins, Achievements and Progress,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pp.21.“新镇计划”是特色小镇建设的思想源头之一,它因埃比尼泽·霍华德在莱奇沃思(Letchworth)和韦林(Welwyn)的实践而逐渐为世人所熟知,并且因为美国建筑规划师克莱伦斯·斯坦和刘易斯·芒福德的引介而蜚声全球。特色小镇一词,其词汇上限是城市。作为城乡关系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对此问题的考察,可以追溯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简·雅各布斯在评述中指出,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带有显著的乌托邦情结,它所呈现的城市形式是一个“相对自足的孤岛”。*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6页。克里斯顿森的评价亦显示,在霍华德的城市理论中充斥着“协调”、“抑制”和“自足”这三个关键词。*Carol A. Christensen, The American Garden City and the New Towns Movement, Ann Arbor. UMl Research Press, 1986, pp.6-7.显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构想是理想化的,他将对理想城市的追求落实到对城市形态的设计上,虽然带有显著的乌托邦色彩,但却打开了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想先河。作为一种在地化的尝试,特色小镇建设在中国正处于起步阶段,其历史环境与客观条件同“新镇计划”有很多的区别,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探索性。目前大量的分析虽然将指导思想追溯到了霍华德,并以霍氏对社会城市的构想作为特色小镇的思想之源,但对理论本身的把握并不透彻。为深化学术界对特色小镇建设的理解和把握,有必要对其思想流变和本质特征进行一番详尽的梳理,以适应科研和实践的需求。
一、肇始:乌托邦梦想与理想城市
(一)城市是第一个乌托邦
芒福德在梳理城市发展史时指出:“城市是第一个乌托邦”,人们对理想城市的追求与乌托邦梦想相伴始终。[注]Lewis Mumford, “Utopia, the City and the Machine,” Daedalus, Vol.94, No.2, 1965, pp.271-292.据已有研究显示,这里包含着至少3层意思:其一,理想的城市是对未来世界的一种预测,理想一词既是对现实人居环境的一种批判,同时也指向了对美好国度的一种向往。理想带有显著的乌托邦成分,但是乌托邦并不等同于幻想,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一个对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它的核心是批判,批判现实中不合理的东西,并为之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注]Carol A. Christensen, The American Garden City and the New Towns Movement, Michigan: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86, pp.3-4.其二,乌托邦梦想通常被赋予一种独特的城市形态,它是理想的,同时也是连接现实与未来的。[注]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在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上,从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工程师维特鲁威,到现代主义时期的霍华德和勒·柯布西耶,众多的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学家留下了大量关于理想城市的构想。这些构想有已经实现的,也有众多中道夭折的。除对现代规划仍富有启示外,它们所突出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在于:乌托邦梦想对于理想城市的想象始终伴随着现实的城市,同时又与现实的城市状态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其三,乌托邦梦想通常是通过对理想城市的设计来使之形象化的,[注]翟辉:《香格里拉·乌托邦·理想城——香格里拉地区人居环境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年,第68页。理想之城并非是一个局限于规划图纸或是文学语言的表述,相反,它不但具有明显的实践要求,而且在外在表现上,它的提出通常是与社会变革的设想紧密相连的,每一种形态的理想之城都内在地包含着一些对社会发展现实的思考。大量的实践证据也表明,理想的城市与人的发展乃是一种生命的共同体。[注]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张兆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6页。
(二)理想城市的萌芽
词源上,英文中城市(city)一词源于希腊文的城邦(polis)和拉丁文的城市(civitas)。据伊顿在《理想城市》一书中的考证,希腊语中的polis和拉丁语中的civitas具有同义性。[注]Ruth Eaton, Ideal Cities: Utopianism and the (Un)Built Environment,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2, pp.11-12.这些通过构筑城墙而围起来的地方,既是物理空间,也是政治实体。作为城市(city)一词的起源,这些运作在共同的政治、宗教制度和法规下的部落联盟,是当今城镇结构的最早形态。在西方语境中,“理想城市”的英文表述是“Ideal City”,这个词通常也被译为是“Utopia”,翻译成中文便是乌托邦或是理想城。它的英文译法有两种:“Outopia”和“Eutopia”。构词上,ou源自希腊文中表示否定的词ouk,eu在希腊文中则是有美好和完美的意思,topia源于希腊语topos,在希腊文中表示“地方”(place)。组合起来,分别是“乌(无)有之乡”(Outopia=Ou+topos)和“理想之国”(Eutopia=Eu+topos)。[注]刘琰:《中国现代理想城市的构建与探索》,《城市发展研究》2013年第11期。16世纪时,托马斯·莫尔在游记体小说《乌托邦》中,结合以上两个词义的希腊文拼合成了一个新的词汇“Utopia”——既是福地乐土(Eutopia),也是一个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乌有之乡(Outopia)。莫尔用这个词来指代他所设想的那个完美的国度及其所代表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就这一点上讲,理想城市中的“理想”一词,无论就其形容词还是名词的意思来说,都是指那些存在于想象而非现实中的城市,它们近乎于完美,以至于与之相关的规划实践实际上都是在试图极力向它靠近。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托马斯·莫尔不但创造“Utopia”一词,使得乌托邦文学盛行于世,而且带来了城市规划思想与社会变革理论的一种革新,他的乌托邦小说“描绘了一个存在于世间的理想城邦,人间伊甸园”,这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中来世天国观念与古希腊神话中理想的人间城邦的结合。[注]Frank E. Manuel and Fritzie P. Manuel,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4.由此产生的影响,不但促成了人们对于完美城市的理想和渴望,而且还使得建设人间伊甸园成为城市建造的一大目的。人们对理想城市的追求,不但是城,同时也是镇,镇是城市化进程的一种中间形态。特色小镇的建设与培育说到底,仍是一个关于理想城市与城市乌托邦梦想的议题。反传统城市与小镇情结的交织,这是自霍华德以来的城市规划思想突出表现出的一种内在特质。
(三)理想城市与乌托邦
人们对理想城市的追求带有显著的乌托邦色彩。对此问题的思考甚至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巨擘柏拉图,他对理想国(TheRepublic)的叙述被认为是现代城市规划思想与乌托邦思想的源头。[注]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第8页。柯林·罗在《拼贴城市》一书中曾将乌托邦依其形式概括为两类:一是经典的乌托邦(Classical Utopia),起始于柏拉图而衰落于中世纪,在文艺复兴时期表现为对形体上可见的“理想城市”的追求;其次是行动派的乌托邦(Activist Utopia),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主张普遍的道德和社会的公正,将建筑的具象化“作为一种清晰的社会变革的工具”。柯林·罗批判后者,并且指出,经典的乌托邦是由普遍理性精神和公平思想所激发的理念式的城市想象,这种理念上的城市,从根本上讲“是由希伯来式的启示录和柏拉图式的宇宙观组合而成的”。[注]柯林·罗、弗瑞德·科特:《拼贴城市》,童明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13-14页。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文化中关于理想城市想象的源头,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理想城邦的理念而非其具体形态,由此引出的乃是对于城市的发展及其未来的批判。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对理想的城市形态进行描绘的典范。小说中的城市是以伦敦为原型写作的,它的首都亚马乌罗提城(Amaurote)不但与伦敦的地理特点相似,同时有着许多当时欧洲城市的影子。[注]Brian R. Goodey, “Mapping ‘Utopia’: A Comment on the Geography of Sir Thomas More,” Geographical Review, Vol.60, No.1, 1970, pp.15-30.它像伦敦一样位于潮水河畔,同时又有着与当时的伦敦迥然不同的风景。在托马斯·莫尔的设想中,亚马乌罗提城位于乌托邦岛的中心,是54个城镇之一。这些城镇相隔不超过24英里,彼此分离,却又相互联系。这些理想中的城市以绿带作为彼此的界限,同时每一个也被竞相修葺得有如花园,法律甚至规定每个居民必须在乡村里住上两年。[注]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345页。彼时的伦敦,建制与莫尔笔下的乌托邦岛相似,拥有53个郡和一个伦敦城。然而发展情况却不令人满意,甚至与乌托邦岛有着相反的境遇。[注]John Guy, Tudor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12.通过以上对比不难看出,在托马斯·莫尔的笔下,乌托邦岛实际上有着非常清晰的现实指向。他的小说《乌托邦》开启了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先河,其批判既是针对产生英国社会弊端的种种根源的抨击和讽刺,也是对一个完美社会的期盼和想象。在其强烈的反传统城市的背后,潜藏着对理想城市的追求。他尝试用具体的城市形态来描绘理想的城市,对柏拉图等学者的城市批判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深刻地影响到了自霍华德以来的人本主义规划大师对理想城市的想象。
二、流变: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紧凑型城市
(一)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被认为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开端。他将带有乌托邦气息的新的城镇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此之后城市规划才广为人知。[注]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第16页。在题为田园城市的书中,霍华德借助三磁铁理论(three magnets diagram)描述了他对于理想城市的想象,这种想象开启了现代城市发展的母题,同时也被认为是指导特色小镇建设的理论源头。[注]张鸿雁:《论特色小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中国名城》2017年第1期。他的讨论将柏拉图式的理想结合到19世纪英国城市发展的现实背景中来,叙述了一种兼具城乡优点的新型城镇化模式,这一模式带有浓烈的反传统城市倾向和小镇情结。他主张:理想的城市应当有其自足性,不应无限制地扩张;每座城镇都有自己的乡村地带,他们以绿带作为城市的界限,随时间的推移,形成彼此独立却又相互连接的城市群;城市的内部分布有绿地,这些绿地在空间上相互联系,并且交织成网。就以上文字可以看到,霍华德对田园城市的叙述,带有显著的乌托邦色彩,既直接承袭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对理想的城市形态的想象,又与柏拉图对理想国中“正义之城”的描述密切相关。以致该书在初版中的题名是《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注]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译序第18、1-2页。反映了作者希望以此推动社会改革的愿望。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是理想小镇的主要原型。他将田园城市作为社会城市的一个局部试验点,最终目的是要形成一个“城市—乡村”一体化发展的田园城市群——社会城市。田园城市的根本特征不在于田园,而是城乡一体。所谓“城乡一体”,并非是乡村的城市化,或是城市的乡村化。相反,它倒是在要求实现“城与乡的联姻”(a marriage of town and country),将城市与乡村的优点结合起来,让人们在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而不失田园景致。[注]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译序第6-9页。在要求产业配置、基础设施、交通环境等向现代城市看齐的同时,田园城市的设想要求城市的发展要限制其规模,并保留永久性的绿地。城市化的过程是一种能量聚集,它将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等高密度地聚集到地域中心,并有不断持续的倾向。由此产生的问题,既有城市的无序扩张造成的恶性增值,也有类郊区化进程的加剧带来的城市环境的去自然化。勒·柯布西耶将之喻为是“近于麻风病似的蔓延”。[注]勒·柯布西耶:《人类三大聚居地规划》,刘佳燕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为根治这一弊病,霍华德在田园城市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城市的构想。其根本目的是试图以田园城市群内城镇数量的增加来取代单个城市规模的无限扩大。这种浓郁的反传统城市倾向具有显著的小城镇情结,以至于芒福德在1946年《明日的田园城市》的第四版导言中,仍然盛赞这一理论“让人们在返回地面后,得以居住在最美好的地方(田园城市)。”[注]Lewis Mumford, “The Garden City Idea and Modern Planning,” In Larice M. & McDonald E, ed., The Urban Design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Urban Reader Series, 2006, pp.43-53.
社会城市是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的核心。它所设想的城市空间结构,摆脱了就城市而论城市的陈腐观念,创造性地将城乡问题作为城市改进的一个统一问题来进行处理,极大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对此,芒福德的评价是:“如果需要什么东西来证实霍华德思想的高瞻远瞩,那么,仅书中‘社会城市’一章就够了。”[注]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532页。社会城市是霍华德发展田园城市的最终目标,这种布局思想直接影响到了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方向。他所定义的田园,不是城郊,而是城郊的对立物。由此产生的城市,也不是乡村避难所,而是一种生动而完整的城市生活。他曾断言,一旦这种改造完成,人们便可以重返故土。[注]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译序第10页。
需要指出的是,由田园城市发展出社会城市,这种带有先驱性的城市模式不仅是受乌托邦小说的激发而产生的,[注]Robert Beevers, The Garden City Utopia: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Ebenezer Howar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8, p.27.而且其浓郁的乌托邦色彩也决定了这种被理想化的城市原型,在具体实施上存在一定的困难。然而并不妨碍后世的城市规划学家对田园城市理论的吸收和喜爱。应当予以指出的是,霍华德所提出的田园城市构想,它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拥有花园和绿地。它与传统城市的发展思路全然不同的创新之处在于:它试图在抑制与协调的基础上,通过对一个组合体的合理运用,将错综复杂的情况加以有序化的处理,进而以内聚和有机生长的形式遏制当代城市扩张力量的惯性。[注]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第381-382页。它的布局目标,不是要消除城乡关系的二元对立,使城市从属于乡村或是使乡村从属于城市,而是要以一种“城乡联姻”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取代传统模式下的城市生长方式,从而化解因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和乡村人口的不断流失所引起的社会问题。[注]Frederic J. Osborn and Arnold Whittick, New Towns: Their Origins, Achievements and Progress,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pp.33-34.它所定义的田园城市虽然是反传统城市的,但是仍旧带有显著的工业主义色彩。它所主张的以田园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空间形态,不仅是工业背景下理想小镇的原型,而且还为理想城市的建设确立了几条最为基本的标准——除要求以快速交通对各田园城市进行网状链接外,还创造性地提出要对城市进行功能的分区,这种分区既是位于城市内部的,同时也存在于各田园城市之间。内聚与统筹是社会城市的核心要义。
霍华德将对理想城市的想象落实到对土地的使用与规范上,试图通过对土地功能的设置与限定来实现城乡统筹和城市生长的有序性。在霍华德看来,田园城市背景下的城乡关系不再是分工与协作,而是融合,融合的目的为的是将二者的优点结合到一起。以更通俗的话来理解即是:城与乡的差别不再是地域的区分,而是不同区域所显示出的不同性格特征。这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构想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是人口的分流与城市规模的限制,而且还要求用明确的产业分工和向先进城市看齐的基础设置配置,以此来满足人们对高质量的居住生活的需求。[注]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第12页。以此为基础,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分析框架基本定型。
(二)紧凑型城市的发展
建设紧凑型城市(Compact City)是在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城市发展理念。理论框架上,基本保持了霍华德对田园城市和社会城市的构想,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成分。比较典型的思想有四个,代表了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四个方向。
1.光辉之城
勒·柯布西耶的“光辉之城”(Radiant City)主张从功能城市(Functional City)的角度用紧凑性的规划来解决城市的发展问题。痴迷于秩序和统一性的勒·柯布西耶,既对霍华德的城市发展理念表示支持,同时也认为“田园城市不过是前机器时代的一个迷梦”,无视了机器时代的潜力与风险。[注]勒·柯布西耶:《光辉的城市》,金秋野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94页。他坚信,现代技术的应用和工业的创造力必然促使城市集聚,集聚才有活力。在此基础上,勒·柯布西耶提出了建设现代城市的四个原则:用摩天大厦和高密度的建筑实现市中心的扩容和土地的解放、释放出来的土地用于增大建筑间距及布局更多的城市绿地和公共空间、对交通工具进行了分类进而建立立体化的交通系统、对城市功能进行分区,以便用宽阔笔直的方格路网来降低因通勤带来的拥堵。如此,便可以得到一个“垂直耸立于阳光与空气之中,且绽放着绚丽光芒的城市”。[注]勒·柯布西耶:《明日之城市》,李浩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260页。显然,勒·柯布西耶的“光辉之城”既是乌托邦的,也是反乌托邦的。它的突出贡献在于:在高度工业化的背景下,展现了田园城市的一种垂直分布。
2.有机分散
伊里尔·沙里宁的“有机分散”(Organic Decentralization)与勒·柯布西耶所主张的高度集中不同,芬兰建筑师沙里宁从生物的生长现象中受到启示,认为城市的结构要符合人类聚居的天性,既要便于共同的社会生活,又不应与自然分离。[注]伊里尔·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顾启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第33-56页。城市应围绕其功能着意经营,使之密不致拥挤,疏不失繁华。在避免城市的中心地区过度集中的同时,将城市的功能进行合理的分散,并依照生活和工作的需要对“经常活动”的区域进行集中的布置;对于“偶然活动”的场所,沙里宁的主张是做分散的布置,但不必拘泥于一定的位置。经常活动的区域需要将交通量减少到最低程度,在步行为主的同时,应尽量降低对机械化交通工具的使用;往返于偶然活动的场所,可以使用快速通道进行连接。沙里宁的主张具有很强的田园城市色彩,他认为城市组织机能的瘫痪,根本原因在于内部秩序的臃肿和不合理块体不断凝聚。要扭转这一趋势,需要对城市的形体进行重塑,将无序的集中转变为有序的分散。依沙里宁的构想,当这一改造完成,现代城市的衰退即能被制止,恢复合理秩序的城市既符合人类对于工作与交往的需求,又不脱离自然,分散的结果使得人们得以居住在一个城乡优点兼备的环境中。
3.广亩城市
赖特的“广亩城市”(Broadacre City)是分散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反对集体主义的他主张将城市分散到农村去,形成一种“没有城市的城市”。理想的状态是:每户拥有一英亩的田地足够生产蔬菜和粮食;居住区之间以高速公路进行连接;公共设施沿着公路进行布置,并以汽车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注]George Fred Keck, “Reviewed Work(s): The Disappearing City by Frank Lloyd Wright,” The Journal of Land &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 No.2, 1933, pp.215-216.相比于勒·柯布西耶,赖特的广亩城市理想性更为浓厚。他所主张的城市具有很强的反城市性,一种完全分散的城镇化布局形式被他所推崇,最终形成的实际上是一种水平分布的田园城市,集低密度和现代性于一体。追求人与环境的相对和谐,是广亩城市的一大特质。它摒弃了传统城市的所有结构,主张大城市应当让其自行消失,良好的城镇形态不是城市与乡村的折中方案,而是应当真正地融入到自然乡土之中。
4.拼贴城市
柯林·罗的“拼贴城市”(Collage City),主张用织补的方式来激发城市的活力。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与大部分的城市规划学家不同,柯林·罗和简·雅各布斯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关注并不止步于田园城市,而是将人的多元需要纳入了城市的个性。分散与集中从整体上规定了城市的发展框架,柯林·罗等所着眼的恰是以上分析鲜有着墨的部分——城市的形态与地方个性。一座城市要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布局对于现代性的响应,更应着眼于人的需求。织补破碎的城市肌理,是激发城市活力与多样性的关键。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开创了一个对现代城市规划进行反思的时代。她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一套用于缝合城市空间的策略: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基础上,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用以满足人们对于交往和空间多样性的需要。[注]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第165页。小而灵活的规划(little vital plan)是简·雅各布斯和柯林·罗所推崇的。《拼贴城市》中,城市为生活服务与其人性化的本质,被柯林·罗表达得淋漓尽致——拼贴中的城市反对大拆大建,在保障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时强调了历史与文脉的重要性,力图在现代城市的理想中实现传统与现代、永恒与偶发、秩序和非秩序的共存。[注]柯林·罗、弗瑞德·科特:《拼贴城市》,引言第6-8页。显然,拼贴城市的目标并非是要着眼于通过对城市形态的一次性规划,一劳永逸地解决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它的落脚点是动态的,希望通过对城市活力与多样性的把握,为城市的自我更新留下可能。
以上是自霍华德以来城市规划理论的几个典型代表。他们大多以霍华德对田园城市和社会城市的构想为图底,在各国的“新镇计划”中得到进一步的检验和完善。实践证明,上述理论各有得失,在实际操作中并不以孤立的形式存在。它们以恩温的“卫星城镇”(Satellite Town)理论作为协调,在功能互补中形成统一,[注]Mervyn Miller, “The Elusive Green Background: Raymond Unwin and the Greater London Regional Plan,” Planning Perspectives, Vol.4, No.1, 1989, pp.15-44.所呈现的不仅是对于理想城市的多种想象,更是建设特色小镇的理论之源。
三、特色小镇的本质特征
对城市恶性增值的忧思,是促成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大部分的分析是将研究的重点放置在对城乡问题的解决上,并试图通过对城市形态的探索,在满足现代性需求的基础上实现对城市无序化增值的有效遏制;然而依旧可以看到,他们所呈现的城市形式实际上是带有浓烈的小镇情结的。因为城市的发展必须被控制在一定的生长边界内,因此它所表现出的城市特质,不仅是界限清晰的,而且是能够自足的。自足的意思并不指向于封闭,而是要求形成一种内生的活力。这种活力,不仅要让人们在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而不失其田园景致,同时它也对城市功能的实现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完整且合理的城市,在区域内必须同时兼有且足以能满足四种功能——居住、工作、休闲娱乐和交通,才不至于需要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持续分化来满足城市扩张的需要。[注]Gideon S. Golany, New-town Plann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New York: Wiley, 1976, p.22.当城市的恶性增值被制止,在体积和容量上有所收敛的现代都市的宜居性将进一步凸显。与此相适应,作为分流结果的“新镇”,不但较大地缓解了发展大型城市的压力,而且使得使用城镇群数量的增加来取代单体城市的无限扩大成为可能。因此,仅就城市增值和对治理城乡问题而言,发展特色小镇不但是适应现代性和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同时也是调整已有城乡空间布局的一个切入点。它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将对理想城市的追求落实到了更小的范围内,更是为城市的再次发展留足了空间。
大量的实践证据显示,单体城市的过度增长在不断侵蚀城乡界限的同时,也使得城乡之间脆弱的平衡不断走向坍塌和崩溃。作为代价,不稳定的城乡界限虽然为中心城市的快速增长提供了一条很好的发展道路,但是仅依靠自身容纳能力的扩大来实现大城市的诸多功能,显然并非明智之举。急剧增长的城市规模牺牲了近郊地区的优越性,看似已经城市化,但解决办法却是暂时的且代价昂贵。为遏制城市边界的外溢与其负面效果,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构想,这是发展社会城市的“局部实验”,同时也是指导新镇计划和特色小镇建设的思想纲要。从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到,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虽然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革,但在总体上仍旧具有非常显著的城市边界意识和浓郁的小型城镇倾向,这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构想所奠定出的思想基调。就城市群之间的布局形式来看,总体上也深受社会城市这一构想的影响。
小而精,这是发展特色小镇的一个典型特征。所谓“镇”,并不在于与现代城市相对,相反,它是内在发展中兼具城市与乡村的优点。它是为安排健康的生活而设计的城市,“小”仅是其形容词,其核心要义在于要控制城市的规模和有明晰的城市界限,这里的界限既是城与城之间的,也是城与乡之间的。“镇”是其限定词,是针对已经形成的大中型城市而言的,以“镇”相称的目的,为的是在限制城市发展规模的基础上令其尺寸与需要相匹配。特色小镇并不排斥现代化,甚至对现代化的社会供给有着更高的要求。此外,特色小镇中的“镇”实际上是一个介于大城市与乡村间的居间概念,与传统观念不同,它的指向并非只是行政上的建制镇(designated town),更是以特色镇(characteristic town)为特征的城镇发展。它的最终结果可以是一个建制镇内多个特色镇的并荣,也可以是单个特色镇与建制镇的高度融合。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后一种情况似乎更受国内实践者的青睐。
四、特色小镇建设的几点思考
特色小镇的建设是理想城市的一种实践状态,小而精是其外部特征,其生命力与魅力的关键在于“特色”,在地化的特色与人性化设计的结合是其本质特征。就学理关系而言,特色小镇的独特性首先来自于三点:一是区别于传统城市的布局形式。承袭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而来,在要求每一城市要控制好城市规模与边界的同时,坚持用城镇群数量的增加来取代单体城市的无限扩大;二是产业集聚的思想。用特色主导产业来避免小镇的同质化,是保持持续生命力的关键,惟有产业上先“立得住”,新的城镇才不至于因为就业前景的衰败而丧失其吸引力。产业特色和产业竞争力是各小镇相互区别的关键,它们惟有分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并在城市功能上实现有机互补,才有各自可以维系城市边界的可能。既有的城市经验显示,城市边界的无序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已有的城市边界不足以容纳产业链发展的需要,因此才需要向外扩张。可见,一个边界清晰的城市必然是一个产业及其价值链集聚的城市。只有经济基础上实现自足,区别与容纳才成为可能;三是生产生活的高度结合。建设特色小镇的初衷,为的是疏解大中城市的压力以及引导新的城市增长极,宜居性与宜业性的融合是其内在要求,这种要求与之前的工业城市相比有着根本性的进步。虽然直接承袭了霍华德对于田园城市的想象,但是仍旧需要指出,特色小镇成败的关键在于“分流”。当小镇所能提供的生产生活条件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预期和需要时,被分流出的过溢人口又将向大中型城市进行回流。显然,特色小镇的建设不能只是偏重于住房和就业,它必须以其融合性在兼顾城乡优点的同时,满足人们对现代生活的客观需要。综上所述,特色小镇之“特”,第一表现特征为:在规模适中且边界清晰的城镇范围内,拥有内聚的城市生长力。
除保持了田园城市的基本特征外,勒·柯布西耶的“光辉之城”等也为特色小镇的建设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城镇原型。这些原型虽极具理想化,但是其中不乏切中要害之处。如前所述,特色小镇的实质实际上是兼具城乡优点的小型城镇群,它的布局形式严守着霍华德对于社会城市的构想,既要求各城市之间以高速通道进行连接,同时也指出惟有边界清晰,城市的规模增值才可能得到遏制。小而灵活的规划是特色小镇的第二特征。因为“小”,所以必须围绕其功能精心布局。在满足日常需要的同时,要使之密不致于拥挤,疏不失其繁华。优化生态与传承人文是支撑特色小镇能够产生自我更新能力的关键要素,必须将城市与人视为生命的共同体,小而灵活的规划才有存在的可能。需要注意的是,特色小镇虽然是以“镇”为名,但它本身并不是反城市化的。不但没有反城市的倾向,而且还对基础设施的配备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需要向现代城市看齐,同时还要求在小而精的规划范围内实现城乡优点的兼具和文脉的延续。它的布局目标,不是要消除城乡关系的二元对立,使城市从属于乡村或是使乡村从属于城市,而是要以一种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取代传统模式下的城市生长方式,从而化解因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和乡村人口的不断流失所引起的社会问题。
创造和引导新的经济增长极是特色小镇建设的第三个特征。它的着眼点在于产业,需要通过精准的定位,在全产业链的集聚上做足文章。借用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的描述来说,即要寻找到一种新的方法,令它产生的磁力能够将人民吸引过去。[注]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第6页。显然,建设全产业链是一种最为切近的方式。它以支撑特色产业的发展为基础,将全生产要素按价值链的关系聚集到特定区域内,并以功能链的结构进行连接,其实质是要在可控的城市增长边界内,用优势产业的集聚来保持内聚的城市生长力。以上是各特色小镇得以相互区别的关键,同时也是维系其竞争力的根本所在。惟有在产业上先“立得住”,特色小镇才可能创造出新的城市增长极,进而避免衰败。这既是它应有的形象特征,同时也是其命脉所在。研究者们需要看到,特色小镇之“特”,不仅是城市发展思路和布局形式的新颖,更为关键的是,这类小镇在策划之初即具有明确的产业布局思想。以产业进行驱动、在“特色”上下足功夫、对接优质市场,这是创造和引导新的城市增长极的关键,同时也是支撑特色小镇使命的关键。
依托特色产业建成有生命力的本地社区,这是特色小镇建设思想的元发点,同时也是形成城镇内聚力的必要约束。因为落脚点和归宿在于“人”,因此过度偏重经济诉求,实际上会将特色小镇建设逐渐引入深渊。应当看到的是,特色小镇的“小”,不仅是要为进一步的城市化留足空间,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在要求是要在对田园景致的保持中,满足人们对于现代生活的需要。这里的需要不仅是住房和就业,更有文化的需求和邻里交往。一言以蔽之,特色小镇的“小”实际上是要求建成兼具城乡优点的“城市综合体”。它的“小”是相较于传统城市而言的,并非是指其规模或容量明显劣于现代城市,而是说它的生长边界是清晰且可控的,同时在该地域范围内,单体城市的无序扩张与恶性增值被以有序化发展的田园城市群所取代。以上便是特色小镇的规划特征。应当看到,此处的“镇”实际上是一个相对于单体城市的小型城市群,它以社区和邻里为基本单位,发展的方向是形成多个相互联系且富有生命力的城市综合体。单体城市的弊病被兼具城乡优点的小型城市群所取代,这是特色小镇的建成目标,同时也是其内在机理和规划基础。如何建成具有生命力的本地社区,这是直接影响特色小镇建设成败的关键所在。与此相适应的是,研究者们需要在规划图纸之外,将积淀在地域风物中的地方个性充分发挥出来,使城市既是宜居宜业的,也是内聚、文化、生态以及现代的。
规划者们需要看到,特色小镇的建设思想虽然始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但建成一个兼具城乡优点的小型城市群并无一个固定或既成的模板可以参照。“特色”一词,不仅表明此处的城镇形态是有别于传统城市的,而且说明这种在地化的“特色”是可以通过科学的论证和规划进行引导和布局的。特色之“镇”,既是从地方文化中成长起来并与之融合的,同时也是科技和现代的。在此,田园城市的构想与其说是为现代城市的发展绘制出了一种理想的城镇范式,毋宁说一种兼具城乡优点的城镇布局形式作为一种规划的方法论被它所提倡。特色小镇的建设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当前,大部分的实践者已经将特色小镇的分析目光由“构建田园城市”逐渐细化到了产业布局和城镇形态上,作为问题的延伸,分析者们需要看到,影响特色小镇建设成败的关键其实还是在于“人”。以人为中心,依托特色产业和地方性,建成具有生命力的本地社区,这是特色小镇建设思想的元发点。提倡小而精的城市,目的是为了创造和引导新的城市增长极、实现乡村振兴以及提供更好的服务于人们生活的要求。
五、结语与展望
特色小镇是一个介于大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居间概念,它的实质是以“特色镇”为特征的城镇发展。特色小镇的建设表面上看,是在探索一种新型的城镇化道路,但是其实质却是反传统城市的,它的建设目标不是要在与乡村对立的一极找出城市化的另外一种形态,而是要在建设与尝试中破解城乡关系的二元对立。它所设想的城市是亦城亦乡(town-country),既要求城市与乡村将其优点融合,同时,城乡需要依其功能定位以特色主导产业为基础进行归位。在此背景下,城与乡的联系不再是调和,而是融合;城与乡的差别不再是地域的区分,而是不同区域所显示出的不同性格特征。分析者们需要注意到,特色小镇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是面向城市的,同时也是面向乡村的,不可孤立而言。它所倡导的城市,是一个兼容了城乡优点且设置了明确的城市增长边界的城市。城与乡的一体化发展,所要解决的不仅是落后的乡村面貌,还要避开因传统城市的无序扩张与恶性增值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城市病。此处所坚持的“特色镇”既是城市也是乡村,它所倡导的生活和服务供给并不是现代城市的对立。需要看到,本文虽然以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为核心,对特色小镇的思想流变及其本质特征等进行了追溯,但问题并未因此而结束。作为一个颇具实践性的话题,特色小镇的建设正如其缘起所示,不仅有着乌托邦色彩同时是对理想城市的一种现代追求,对它的思考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探索性,需要研究者们在实践工作中进一步细化和深入。
特色小镇虽以“镇”为名,但其实质却是一个生长边界清晰且产业链及其价值链集聚的城市。它将城市与乡村的优点,在培育优质的特色产业的基础上结合起来,最终的发展结果不仅优质的乡镇文化传统得以保留,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全域的城市化(overall urbanization)在破除了城乡关系的二元对立之后,得以在广阔的乡村背景中建立起来。在此,城与乡的差异不再是传统城乡结构下发展程度和社会服务供给的区别,而是不同区域的地格特征在产业分工上所展现出的地理性格的差异,一种共享的城市化在区域内被倡导和实现。许多分析关注到了特色小镇在提供现代生活上的作用,但是也应当警醒,特色小镇的根本特征不在于城市化,而是城乡一体。城乡一体的最终目标,不是城市的乡村化或是乡村的城市化,而是要使这个以特色产业为基本支撑的小镇成为“一个适宜现在和未来生活的城镇”。
特色小镇的建设中心在于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对特色小镇在具体实践中可能过度偏重于经济诉求的一种控制。拼贴城市的分析表明,城市的内生活力在于其多样性。[注]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第165-166页。就特色小镇而言,以人为本既是保障其城市活力与多样性的源泉,同时也是开展小镇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人与城市是生命的共同体,这句话要求特色小镇在规划与实践当中需要满足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以避免传统模式下的衰败,以产业为支撑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条件于人们的生活和环境。概括起来即:精研定位、明确功能;在传承和发展历史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于地方性,实现特色产业与地理性格特征的融合;保持特色产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的诗意栖居”既是特色小镇建设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其归宿。大量的实践证据表明,一座拥有持久生命力的城市,不仅要在产业布局和服务供给上对现代性进行响应,更应着眼于人的各种需求,使城市切实成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本地社区。
最后,特色小镇的独特魅力是源自历史和生活积淀的地域风物。小镇与小镇之间区别不仅是产业定位与培育上的差异,同时也是地方特色之间的差异。这一特质决定了特色小镇的建设仅凭借“移植”和“嫁接”的思路是无法完成,需要精研定位,在对接优质市场上下足功夫。重视地域风物与长效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精研产业定位的基础,同时也是影响特色小镇营运成败的关键。特色产业同地域风物的融合不可能一蹴而就,重建设、轻运营易导致产业与地方性的脱嵌,使特色小镇名存实亡。就定义上看,建成后的特色小镇应当是宜居、宜业、宜游以及生态的,当前有些观念片面地将特色小镇在经济开发的视域下简单等同于产业小镇或是文旅小镇,狭隘了特色小镇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重要性,这是值得学术界警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