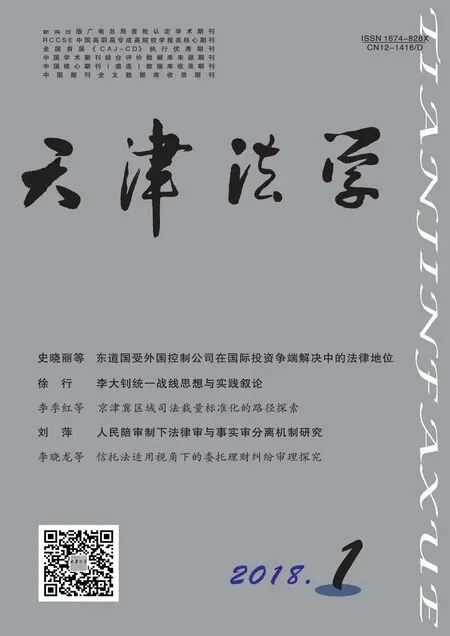伪造签名型假按揭合同的效力认定和责任承担
——某银行诉胡某、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审视和评析
李 硕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研究室,天津 300204)
【案例要旨】
开发商为套取银行资金,伪造他人签字,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应认为被冒名人与银行未达成借款和抵押合意,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未成立,银行无权要求被冒名人承担还本付息义务。抵押预告登记能排斥义务人的妨害债权请求权的处分行为,具有合同保全功能,但不等同于正式抵押登记,当事人主张依据抵押预告登记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不应予以支持。法院经审理查明的法律关系与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应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坚持原诉讼请求的,法院应按照原诉讼请求进行审理;经审理,认为当事人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的,应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案情简介】
原告某银行诉称,2004年3月22日,原告与被告胡某签订“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及“个人住房借款抵押合同”,约定:被告胡某向原告借款50万元用于购买房产。原告与被告胡某签订了“个人住房借款抵押合同”,约定被告胡某所购房产提供担保。此外,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原告签订“商品房按揭合作协议”约定,在未取得房屋他项权证之前,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对被告胡某的欠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按约定将贷款打入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账户,被告胡某未按期还本服息。因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起诉,请求被告胡某偿还原告借款本息,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并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胡某辩称,房产虽预告登记在胡某名下,但经笔迹鉴定,借款合同不是胡某本人签字,未支付购房款、偿还贷款和实际居住。即使原告提供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也不能减轻银行的审查义务,被告胡某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辩称,涉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非胡某本人签字。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亦不是胡某本人所签,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为筹集资金,冒用胡某的身份证件办理贷款,首付款和前期的还款均由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办理。
经审理查明,2004年3月22日,原告与签字姓名为“胡某”的人签订“个人住房借款合同”“个人住房借款抵押合同”。借款合同约定,“胡某”向原告借款50万元用于购买房产,贷款期限自2004年3月22日至2014年3月21日。抵押合同约定,“胡某”以所购房屋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双方办理抵押预告登记。天津市某区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证明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为原告与被告“胡某”所签,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此外,原告与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按揭合作协议”,约定,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为胡某的借款提供阶段性连带保证责任。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将款项打入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账户。经对胡某笔迹鉴定,“个人住房借款合同”及“个人住房借款抵押合同”中“胡某”的字迹均非被告胡某本人所签。而后,法院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原告依然坚持诉请。经法院调查得知位于涉案房产由案外人郑某实际居住十余年,且与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付清房屋全款。
【法院判决】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认为,涉诉的“个人住房借款合同”非被告胡某本人所签,双方未达成借款合意,原告与被告胡某之间自始未发生借款合同关系,因此,原告诉请被告胡某偿还借款本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要求对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一节,因“个人住房借款合同”“个人住房借款抵押合同”不是被告胡某本人所签,合同并未真实成立,那么基于该合同办理的抵押预告登记也不应发生效力,且抵押预告登记并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原告不能对抵押物优先受偿。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请,虽然原告与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存在相关约定,但是债的担保具有从属性,担保之债从属于被担保的主债,主债不成立,担保之债也不能发生效力。本案被担保的主债没有真实发生,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担保之债也不能发生法律效力,被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综上,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某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原、被告均未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法律解析】
(一)伪造签名假按揭案件司法处理乱象
司法案件是社会的晴雨表,伪造签名假按揭案件的发生与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制度密不可分。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是指开发商将尚未竣工的商品房预先出售给购房者,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交付商品房并转移所有权,购房者支付首期价款,剩余购房款因购房者将未取得所有权的商品房抵押给银行作为担保,由银行代为支付,具有房地产抵押和分期付款双重功能。根据类型化分析,假按揭案件根据借款人签名是否为本人所签、房产是否真实存在、有无真实购房行为以及交易价格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分为五种情形:签字真实、房产不存在的“真人假房型”;签字真实、房产存在、无真实购房合意的“真人真房型”;签字虚假、房产存在、无真实购房合意的“假人真房型”;签字虚假、房产不存在的“假人假房型”;签字真实、房产存在、价格非本意的“真房假价型”。本文探讨的伪造签名型假按揭属于“假人真房型”,系指开发商为套取银行贷款,伪造购房申请人签字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且为该笔借款提供阶段性保证担保,并以尚未竣工的商品房作为抵押,办理抵押预告登记。
司法实践中伪造签名的假按揭案件如何裁判观点不一,目前主要有三种裁判路径:一是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因当事人未达成合意而未成立,抵押预告登记因其从属性而未生效,法官应予以释明,当事人拒不变更诉请的,法院的审理限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之内,若证据不足,应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二是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因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无效,抵押预告登记因银行不具有善意不具有优先受偿效力,直接认定开发商和银行成立事实借款合同关系,判决由开发商承担还本付息义务。三是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因欺诈而可撤销,抵押预告登记不同于抵押登记不具有优先受偿效力,法院应释明当事人变更诉请,当事人坚持不变更诉请的直接按法院查明不当得利判决。
经对本案法律关系进行全面梳理,共涉及四重合同关系(房屋买卖关系、借款合同关系、保证合同关系、抵押合同关系)和两重物权或准物权变动关系(房屋所有权的转移、抵押预告登记的设定),其中借款合同关系是第一性的法律关系,即主法律关系。本案审理须一一回答以下五个难题: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的效力,保证合同的效力,抵押预告登记的效力,法院是否可以不经释明直接判决,当事人拒不变更诉请的司法处理。对于上述五个问题,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声音,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亦非鲜见。

图1本案焦点问题的实践观点
(二)伪造签字合同的效力认定
实务界对伪造签字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的效力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一是合同未成立说,认为合同系双方法律行为,其成立的前提是存在合意,伪造签字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欠缺一方意思表示,未达成合意,故合同不成立;二是合同无效说,认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签字非本人所为,其意思表示不真实,故为无效合同;三是合同可撤销说,认为开发商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银行因虚假信息陷入错误违背其真意,构成欺诈,故为可撤销合同;四是合同效力待定说,认为开发商以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却未获得授权,构成无权代理,为效力待定合同。
对于伪造合同的效力,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合同未成立说。合同成立的要件包括要约、承诺,核心要件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伪造签字的合同欠缺一方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32条的规定,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时成立,伪造签字合同欠缺真正一方当事人的签字,合同未成立。合同无效说、可撤销说、效力待定说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失当。一是,合同无效说虽注意到签订合同非被冒名人的真意,但合同无效着眼于法律判断,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根源于内容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伪造签字的合同并非从内容上加以考量,仅是欠缺意思表示,与意思表示不真实抑或存在瑕疵迥异,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前提是存在意思表示,伪造签字合同认定为无效存在法理障碍。二是,合同可撤销说关注点集中于银行系在第三方的欺诈下作出意思表示,存在瑕疵,但有舍本逐末之嫌,合同成立是事实判断,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合同成立为合同生效的前置阶段,合同的效力是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还是有效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伪造签字合同一方当事人意思表示欠缺,探寻是否构成欺诈已无意义。三是,合同效力待定说着眼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签订合同,却未深入了解代理制度的精髓,无权代理是双方当事人知悉代理事实,而伪造签名的合同当事人并不了解存在代理事实,客观上无实施代理事实,主观上亦无将代理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也不符合隐名代理的构成要件,不构成无权代理。
本案中伪造签字的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未成立。这是因为胡某并不知晓借款购房情况,合同中有关“胡某”的签名均非胡某本人所写,合同欠缺其意思表示,并且胡某未实际取得款项,所涉款项直接划入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账户,由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实际使用并偿还款项,胡某亦未实际居住涉诉房产,故本案借款合同的真实借款人并非胡某,某银行与胡某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不成立,某银行无权要求胡某承担还款责任。抵押合同亦非胡某本人所签,胡某与某银行未形成设定抵押预告登记的合意,因此抵押合同未成立。担保之债具有从属性,借款合同未成立,保证合同也就不发生效力,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无需承担阶段性保证责任。
银行在发放贷款和进行抵押预告登记时存在过失,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不能代替银行的审查义务。银行作为专业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应遵守金融管理机构的贷款管理规定以及合理的商业准则,谨慎勤勉经营,在资信调查、文件审核、现场考察、资力评估、信息甄别等方面履行谨慎审查义务,按照《贷款通则》第37条和《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13条、第14条和第15条等的规定,在发放贷款和接受抵押前应对借款人和抵押物进行尽职调查,在签署抵押合同及办理抵押预告登记过程中核对当事人身份,落实“面签制度”“双人谈话制度”等,才能认定银行为善意无过失。公证书不能替代银行贷款审查义务,若银行未经核查,完全信赖公证书的内容,即应承担公证失实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三)抵押预告登记的效果厘定
抵押预告登记效力如何?银行能否享有优先受偿权?这是审理本案又需解决的难题。
鉴于担保物权具有从属性,借款合同作为主合同未成立,抵押预告登记也将不发生效力。虽然法律关于合同未成立对抵押预告登记效力的影响的规定有限,通过《物权法》第20条第2款和《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5条中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我们对其立法精神可见一斑,债权消灭,预告登记失效。预告登记的前提是债权请求权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债权一旦消灭或自始不存在,预告登记也就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
抵押预告登记是否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根据《物权法》第180条和第187条的规定,以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进行抵押的,抵押权自登记时成立。商品房预售抵押属于在建建筑物抵押,抵押权成立,抵押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二是抵押预告登记不同于能产生支配效力的抵押登记,是对将来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请求权,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本文同意第二种观点。抵押预告登记不属于在建建筑物抵押,后者一般是开发商在销售前为融资办理的抵押,而非购房人。抵押预告登记与抵押登记在法律效力上存在明显区分,抵押预告登记属于预备登记,是抵押登记的准备阶段,《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规定,以未来物预购的商品房设立抵押的,待商品房竣工后,还应当办理新的房屋抵押登记。抵押预告登记旨在合同请求权与物权之间建立有利于债权人的权利纽带,保障债权请求权的实现,降低交易风险,保护交易安全,具有权利保全效力、顺位保全效力和破产保护效力等[1]。虽然抵押预告登记通过公示,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债权的相对性,成为具有对抗第三人效力的特殊债权[2],产生溢出效应,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法律并未将抵押预告登记界定为物权,其本质依然为债权,难免受到债之关系的各种抗辩,如买受人未完全履行付款义务,出卖人享有抗辩权,买受人可能无法取得预售房产所有权等。抵押预告登记介于债权与物权之间,根据《物权法》第20条的规定,具有办理抵押登记条件三个月内而未办理的,抵押预告登记失效。从债权实现角度看,预售商品房尚未完全竣工,不具有可流通性,不能强制执行,无法成为优先受偿的标的物[3]。最高人民法院在厦门明瑞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晋江市陈埭苏厝强达鞋塑服装厂、苏奋强等借款合同纠纷案①中,亦认为在建房屋抵押预告登记并不产生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从拍卖在建房屋的价款中优先受偿的法律后果,只是用以约束债务人以将来建成房屋作为抵押标的物。
具体到本案,虽然原告某银行与签名为“胡某”的订立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预告登记,但抵押预告登记所担保的是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借款合同未成立,抵押预告登记亦不发生效力。且抵押预告登记不具有支配利益,不能据此将其等同于抵押登记,某银行对涉诉房产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法官释明权的边界确定
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未成立后,本案如何裁判?是径行按法院查明的法律关系裁判?抑或应向原告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如果原告拒不变更诉讼请求法院又该如何处理?实务界有四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为更直观的了解实务现状,笔者特搜集相关案例进行解构研析。
1.法院不具有释明的义务,直接按查明的法律关系裁判,径行判决开发商和银行之间存在事实借款合同关系。如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无锡汇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陆梅芳、崔阳、陆三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惠山支行(以下简称“惠山中行”)、无锡富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民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②,因惠山中行提供的贷款进入富民公司账户,由富民公司取得并支配使用,富民公司也实际向惠山中行偿还了部分本息,且富民公司在本案诉讼中也愿意继续履行还款义务,故法院认定惠山中行与富民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借款关系,从而直接判决富民公司偿还借款本息。
2.法院应行使释明权,当事人拒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法院直接按审理查明的法律关系作出判决。如池某铭诉孟某民间借贷关系案[4],原告池某铭以民间借贷关系提起诉讼,法院查明属于不当得利纠纷,经释明,原告池某铭坚持原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此案的主要观点和理由中认为“按照不当得利和民间借贷审理的结果并无差别,不会影响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基于诉讼经济的原则,避免当事人重新起诉,可按照民间借贷关系案件处理”。根据诉讼经济原则,此案法院可以直接按审理查明的法律关系判决,以节约司法成本,实现诉讼效益最大化。
3.法院具有释明义务,当事人拒不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应进行实体审理,否则违反处分原则,同时为防止一事不再理,应以原告不具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或被告不适格等为由,从程序上裁定驳回起诉。如北京华润置地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新中实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海南中实(集团)有限公司房地产项目权益纠纷案③,一审法院释明原告变更诉清后,当事人依然主张原诉讼请求,法院按查明法律关系直接判决。二审时,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当事人坚持原诉请的情况下,法院不应作出实体判决,一审法院径行对原告未主张的法律关系予以裁判,既替原告行使了起诉权利,又剥夺了被告的抗辩权利,违反了法定程序。
4.法院具有释明义务,当事人坚持原诉请的,基于“不告不理”原则和法院居中裁判立场,法院应严格按照原告的诉请进行审理,如原告证据不足则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大庆开发区吉大油脂有限公司与大庆石油管理局、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④为此观点提供了有力佐证,法院认为当事人拒不变更原诉请,经实体审理又证据不足的,法院应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所受损失原告可另行主张。
经过严密的理论分析,笔者同意第四种观点,具体理由如下:一是,释明权是法官的职权、职责和义务,兼具强制性和裁量性,“系指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为明确作为案件裁判基础的事实关系与法律关系,采用发问、提醒、告知、指导等方式,促使当事人准确、完整地陈述事实、提供证据和发表辩论的活动”[5]。释明权起源于德国,属于法院诉讼指挥权的范畴,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包括诉讼请求、事实主张、证据和法律观点的释明,“被理解为包括职权探知主义审理在内的法院的一个旨在谋求审理充实化、促进化及公平审理实质化的手段”[6]。法律关系的性质判断属于法官的职权判断,鉴于请求权竞合问题,法律关系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诉讼请求的变更,并不绝对同步,为保障当事人正当的程序性辩论权,释明要件应采法律关系性质变更必要说[7]。法官释明有利于弥补绝对当事人主义模式导致实质不公平的弊端,吸取职权主义的精华,建立起法官和当事人相互对话、沟通的渠道,使裁判更容易被当事人和社会所理解与接纳,促进息诉服判、“案结事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立有序的诉讼攻防关系,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提升司法公信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⑤和第35条⑥明确规定了法官的释明义务。法院在释明时应严格把握释明的范围、阶段、对象和方式,注重规范性、针对性和中立性,不可怠于释明,亦不可过度释明,避免当事人诉讼地位失衡现象的发生,若释明不当,属于程序违法,当事人有权提出异议或在判决后上诉。法院不经释明直接裁判突破当事人辩论意见和证据的束缚,会导致法律适用突袭,损害当事人的处分权,剥夺对方当事人的抗辩权,使辩论原则形同虚设[8];二是,在当事人拒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应坚持有限介入和中立原则,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和处分权,将法院的裁判权限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之内,而非按法院查明法律关系判决。法官的释明权并不是没有界限的,其边界为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法官行使释明权要保持谦抑性,把握好“度”。“法官应当帮助当事人作出正确的决定,但不应当代替当事人作出决定,不能让法官的理智取代当事人的意志”[9]。此外,法院在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亦应保障对方当事人的辩论权,究其原因在于变更诉请极有可能导致裁判结果的变化,必须为对方当事人提供充分发表意见的平台,否则可能因违反辩论原则导致程序的重大瑕疵或违法。在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法院应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这是因为裁定驳回起诉主要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和第111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着眼于程序性事项,而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是法官进行实体判断,对诉讼请求作出的否定性评价。
本案中,原告某银行主张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成立,并以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为基础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胡某偿还本息,被告某房地产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并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但经法院查明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因欠缺胡某签字未成立,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并不存在,原告诉请依据的请求权基础发生变化,由此导致诉讼请求亦须变更。为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在法院查明合同未成立后,应释明原告某银行变更诉讼请求。原告拒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法院应根据“不告不理”原则、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原则,在原告诉讼请求范围内进行审理。原告某银行提供的证据无法支持其诉讼请求,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因此法院应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某银行可另案以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为被告提起不当得利之诉,矫正欠缺法律关系的财产转移,取除“受益人”无法律上原因而受的利益[10]。
注 释:
①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766号民事裁定书。
②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抗字第67号民事判决书。
③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一终字第107号民事裁定书。
④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终字第148号民事判决书。
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
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1]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384.
[2]杨立新,宋志红.预告登记的性质、效力和范围探索[J].法学杂志,2006,(4):34.
[3]常鹏翱.预售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的法律效力[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6):89.
[4]杜万华.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147-151.
[5]熊跃敏.民事诉讼中法院释明的实证分析——以释明范围为中心的考察[J].中国法学,2010,(5):133.
[6](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314.
[7]曹云吉.释明权行使的要件及效果论—对《证据规定》第 35 条的规范分析[J].当代法学,2016,(6):119.
[8]贺小荣,王松.法院释明权的方法及其合理限制[A].黄松有.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97.
[9](德)鲁道夫.瓦塞尔曼.从辩论主义到合作主义[A].(德)米夏埃尔.施蒂尔纳.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C].赵秀举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380.
[10]王泽鉴.不当得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