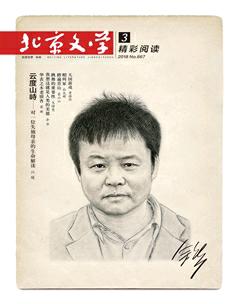大杂院里的往事
晚菘
其实大院儿里住着,最让人怀念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股热乎劲儿。一个院儿的邻居住得都像亲人。出了院门,整条胡同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碰见谁都会笑嘻嘻地打个招呼,问一句,“您吃了吗?”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居无定所,到处借宿,住的都是破宿舍和筒子楼,基本没啥好地儿。后来租房住,搬来搬去的,一不留神就把北京城四个角儿都住遍了。当时心里想,啥时候能在故宫旁边住几天,在中央城区睡一下,那该是何等的荣光。
没承想,还真让我给睡着了。
那年的秋天,我们告别了青龙桥菜地旁的房子。房东二哥帮着找了辆货车,我们收拾了半天,破杯子烂碗,啥都不舍得扔,堆了小半车家当,然后带着二哥二嫂的祝福,风风光光地进了城。
那时四环还没修,“城”的概念是二环以里,货车晚上8点以后才让进城。我们在西直门外猫了一会儿,赶8点整开上二环,晃晃悠悠快9点才到新家外头。新租的房子在北京饭店向北不远的磁器库胡同北巷,明朝时宫里在这儿堆放过瓷器。胡同南头向西走几步,有座普度寺,明代叫东苑,是太子住的地方,清初成了铁帽子亲王多尔衮的府邸,后来才改成了大庙。再往西,就是故宫了。所以,说我们和皇帝是邻居,也不算吹牛。
这是一处大杂院。院门朝东,外头就是胡同。院子是瘦长的一溜,南北走向,很窄,住人的屋子都靠西,隔着一条步道,东墙下挤满了高矮参差的厨房和杂物间。我们把头儿,住北房。门口有一处凹进去的空间,我们拿它做了厨房,立上一架灶台,炒锅一口,蒸锅一口,连门儿都没有,就用块塑料布一苫。穷家也得先把日子过起来。
搬家那天也是惊心动魄。因为胡同太窄,货车开不进去,只能停在胡同口外的大街上,二三百米的距离,背扛肩挎,一趟一趟搬吧。这一通闹哄哄,院儿里竟没半个人出来瞧一眼的。搬完快10点,招呼大家吃完饭,回来已经11点多了。一推门,嘿,打里面锁上了。拍了半天门,没人搭理。我这暴脾气!爷可是交了租子的,我就不信进不去了。情急之下,突然想起一句话来,狗急跳墙。对!垫上几块砖头我就翻上院墙,底下黑咕隆咚的啥也瞅不见,一闭眼跳下去,落地就踩倒了一个硬家伙,“叮了咣啷” 滚好远,一摸索,好像是个垃圾桶。从里头把院门打开,女朋友探进头来,小声嘟囔了一句,“这都住了些啥人啊?”
管他呢。收拾铺盖,先睡觉,这一天累的。我俩把床板搭上,铺好垫子褥子,都没顾上洗漱,就躺下了。半夜迷迷糊糊翻了个身,就听“咣当”一声,耳边响起一记炸雷,撕裂了黑夜,也把我俩炸蒙了。回过神儿来,已经在地上了,原来是床板没搭严实,塌下来了。又起来重新搭好,接着睡下,这才到天亮。后来隔壁胖婶儿告诉我们,我们搬来的第二天,她就和李奶奶一阵儿嘀咕。李奶奶说,这户人家不简单,是厉害人物,咱们可别惹。我们就这么立了威,直到搬走,大家都对我们客客气气的。当然,后来是处出了感情。
胖婶儿是高久雷蒙制衣厂的下岗工人,她说算是内退。她老头儿张叔是裕龙大酒店的厨子,据说炒得一手好菜,可除了酱爆鸭丝,我们就没见过他在家里做过饭。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去王府井西头儿的一家烤鸭店买鸭架子,两块钱一只外卖,便宜到难以置信。买回来撕巴撕巴就一盘子鸭肉,张叔要是在家,就会用葱丝和甜面酱给我们酱爆着吃,香极了。
张叔性子好,从来不和胖婶儿拌嘴,就是总开玩笑挤对胖婶儿爱犯迷糊。其实他说得倒也没错。有天下午,我们出门回来,见胖婶儿一个人在家门口低头呆立着,好像午睡才起来,还没醒透,但看上去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嗯……好像肚子比平时大了好多。再一细看,哈哈,原来是裤子穿反了,屁股跑到前面,鼓了一个大包。她低着脑袋,估计也正琢磨这事儿呢。看见我们笑,她这才反应过来,哎哟一声,红着脸儿闪进屋里,乐得我们肚子疼。
住在院子南头儿的李奶奶就从不犯迷糊,可她都快80了。李奶奶总戴着一副老式黑边眼镜,镜片得有瓶子底那么厚,头发一丝不苟,油亮油亮的,看上去既精明又利索。她是天津人,老了才搬来和儿子住,妞妞是她的孙女,那时才上小学。我们都喜欢妞妞。她梳着两条小辫儿,总是咧着大嘴笑,啥时候都那么开心。我们有时会和她在胡同口一起玩一会儿,踢毽子啊、蹦蹦杆儿啊、跳格子啊,每次妞妞都拽着不让我们走。我们偶尔会给她补补课,带着她做作业。李奶奶瞧见了,准会洗俩大苹果,或者拿点儿什么别的吃食,塞我们手里,并不多說话。有一年夏天晚上,我们正做着饭,就见李奶奶从对面儿端着个盘子,急匆匆地穿过院子,走到我们家门口,探身进屋把盘子一撂,二话不说,又快步走回去了。我们低头一看,是盘儿侉炖小黄鱼,还冒着热乎气儿,看着就好吃。估计是没做胖婶儿家那份儿,这才悄悄地递给我们。
大院里头居住条件虽说不好,可除了时不时顶棚上掉俩臭大姐下来,也没见夏天漏雨冬天灌风的。屋子小,取暖不是问题,再加上那时候也皮实,就算夏天热个几天,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公共厕所也够宽敞,碰见熟人还能唠几句,并不耽误你方便。邻居们也爱聚在一块儿侃大山。夏天晚上吃完饭,一个个就摇着蒲扇,拎着马扎溜达出来。胡同路灯下边靠墙一坐,就天南地北地侃开来。我那几年没少去凑热闹,听他们马海毛、叶利钦、索罗斯的一路侃着,学了不少东西。
其实大院儿里住着,最让人怀念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股热乎劲儿。一个院儿的邻居住得都像亲人。出了院门,整条胡同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碰见谁都会笑嘻嘻地打个招呼,问一句,“您吃了吗?” 家里但凡有点儿什么事儿,邻居间相互搭把手,分分钟就解决了。这时候你要是指望打个长途电话把亲戚叫来,黄花菜都凉了,远亲不如近邻啊。虽说也免不了东家长西家短的,可到哪儿不是这样呢?
住了快三年,我们攒了点儿钱在通州买了房。临走那天大家送到胡同口。妞妞拽着我们不撒手,哭着要把她的蹦蹦杆儿送给我们。胖婶儿和张叔忙着帮忙搬东西,李奶奶不说话,眼圈却红了。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月前回去过一次,快不认识了。胡同还在,院子都拆了,盖起了灰砖的二层小楼。漂亮是漂亮,可紧闭着的院门,透着一股子疏离。往外走到胡同口,迎面过来一辆摩拜,一个姑娘扭着铃铛“丁零零”地骑了过去,帽子下面依稀垂着两条大辫子。我一路望着她远去的身影,好像又看见了妞妞在蹦蹦杆儿上的笑脸,还有她临别时的那汪眼泪。
希望李奶奶、胖婶儿、张叔他们都好,祝你们健康幸福。
“天下,暂时相聚,忽然云散水空流”。
北京似乎留不住我的兄弟朋友。唯有书,常相伴。可是我来北京的时候,只有一本《梵高自传》。还是借大学同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