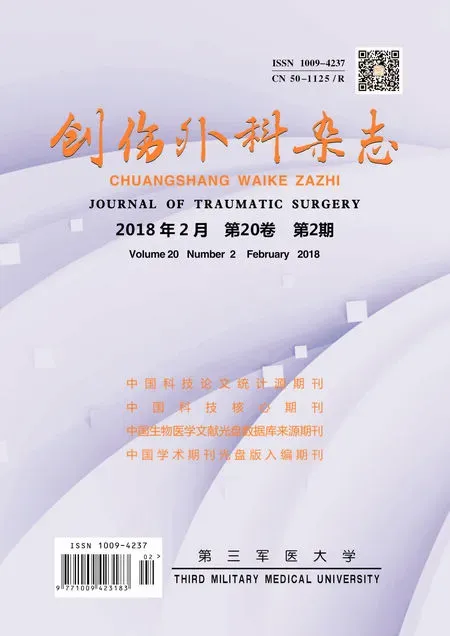严重闭合性胸部创伤患者早期凝血功能变化比较
冀 强,杨丽君,吴 冬
随着交通业和建筑业的迅速发展,胸部创伤患者数量明显增加,尤其是严重胸部创伤多合并其他脏器的损害,病情危急且复杂,病死率较高。Kashuk等[1]曾提到“血液性恶性循环(bloody vicious cycle)”理论,即严重损伤患者的生理状态呈螺旋状恶性循环,低体温、凝血障碍和代谢性酸中毒是其主要特征,结果为机体生理耗竭,难以耐受传统手术的打击。本研究通过分析严重闭合性胸部创伤患者的多种凝血功能相关临床指标变化,揭示导致其死亡的危险因素,为临床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临床资料
1 研究对象
依据多发伤的诊断标准,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2016年6月成都大学附属医院急救科、ICU、胸外科临床资料完整的严重闭合性胸部创伤患者228例。纳入标准:(1)伤后直接入院且24h内无外院治疗史;(2)根据简明损伤分级90版(AIS-90),严重胸部创伤AIS≥3分。排除标准:(1)近期服用华法林或阿司匹林等抗凝药物;(2)中途放弃治疗或自动出院;(3)开放性胸部创伤或锐器伤患者;(4)酗酒史;(5)既往慢性心血管疾病、血液系统疾病、慢性肝肾功能不全;(6)24h内输血量>1 000mL。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2 研究方法
按患者预后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根据评分标准,计算其入院后24h内解剖学ISS和GCS评分;以是否输血、是否为单纯性严重闭合性胸部创伤(以下简称单纯创伤组)、是否ISS>25分及是否GCS<9分组,比较入院24h内常规PT、FIB、D-D及FDP等指标变化差异。
2.1解剖学评分方法:ISS依据AIS-90,从6个部位分区(头/颈、面、胸、腹/盆腔、四肢/骨盆、体表)中取3个最大AIS值求得平方和。ISS均依据24h内CT及手术探查进行评分,较为客观和准确[2]。
2.2采血时间及检验方法:采集伤后24h内静脉血,如患者有失血性休克症状出现,均为扩容和输血纠正休克后静脉血。标本均由笔者医院检验科测定,正常参考值:常规凝血:PT 10.2~15.0s,FIB 2.0~4.0g/L,DD<1.0mg/L,FDP<5mg/L。
3 统计学方法
结 果
本组男性160例,女性68例;平均年龄(49.04±15.17)岁。15例死亡患者中合并颅脑损伤12例,死于颅脑损伤9例,脓毒性休克1例,失血性休克2例,颈髓损伤2例,肺栓塞1例。见表1。
对纳入的228例严重闭合性胸部创伤患者的4项凝血指标PT、FIB、D-D及FDP进行统计学比较分析,结果显示非大量输血情况下,FIB、D-D聚体和FDP含量虽有明显变化,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进一步分析发现,PT、D-D和FDP含量在多发伤组和ISS>25分组中变化明显(P<0.05),见表3、4;在GCS≥9分和GCS<9分组中,血液中D-D和FDP含量比较差异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表1 胸部创伤患者临床基础资料比较

表2 严重闭合性胸部创伤患者是否输血对凝血影响的观察比较

表3 严重闭合性胸部创伤患者是否伴多发伤观察比较

表4 严重闭合性胸部创伤患者是否ISS>25分观察比较

表5 严重闭合性胸部创伤患者是否GCS<9分观察比较
讨 论
大多数胸部创伤患者都需接受多学科评估和稳定病情的处理,能快速、准确和规范地评估伤情及判断预后,对严重胸部创伤合并多发伤患者的诊断、救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认为多种机制共同作用影响严重创伤患者预后,其早期容易发生凝血功能障碍,加重出血,进一步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病死率和并发症发生率增加[3]。Floccard等[4]发现25%~35%的患者在到达急诊室时就出现凝血功能障碍,严重的创伤性死亡患者凝血功能明显高于正常者。在凝血指标中,D-D是纤维蛋白单体经活化因子XIII交联后,再经纤溶酶水解所产生的一种特异性降解产物;FDP是在纤溶亢进时产生的纤溶酶的作用下,纤维蛋白或纤维蛋白原被分解后产生的降解产物的总称,FDP和D-D水平的升高反映继发性纤溶活性的增强,反映凝血和纤溶的理想指标,在临床上已视为体内高凝状态和纤溶功能亢进的分子标志物[5]。
对于大多数的闭合性胸部创伤患者,胸部创伤常常提示患者遭受过高能量损伤,与高病死率有显著的相关性,且早期凝血指标易受到治疗措施的影响,尤其接受大量输血后波动较大[6]。故先排除24h内大量输血患者后,分析本研究输血患者8例,24h输血量400~1 000mL,非大量输血,并以是否输血为标准进行分组,比较凝血指标变化,发现输血组PT值明显延长(t=2.523,P<0.05),结果不仅与输血组创伤较未输血组严重有关,更受本身大量输血及补液影响,而FIB、D-D和FDP含量虽有明显变化,但在非大量输血情况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国内的一些研究结果相似[7]。因此本研究后期探讨仍具有实际意义。
已知闭合性胸部创伤与开放性胸部创伤比较,闭合伤的ISS都显著高于开放伤,表明闭合伤患者的全身多发伤发生率高,病情危重复杂,重伤和多发伤是其重要特点[8]。有研究显示,D-D与创伤患者创伤严重程度及预后密切相关,ISS评分越高患者D-D水平越高[9]。陈影秋和郭峰[10]研究也认为严重创伤患者死亡组中D-D水平显著高于存活组。王诚和张洪金[11]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指出,创伤患者入院后12~48h血浆D-D水平与急诊创伤休克患者死亡呈正相关,并对创伤性休克患者预后具有一定临床价值。本研究显示,在严重闭合性胸部创伤患者中,D-D和FDP含量在多发伤组均高于单纯胸部创伤组(t=7.817,P<0.01和t=7.293,P<0.01),在ISS>25分组均高于低评分组(t=60.77,P<0.01和t=59.43,P<0.01),其总体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上述研究相符。可以认为,ISS>25分的患者几乎都伴有其他部位损伤,因此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合理性。虽然很多文献提示,D-D和FDP升高也说明深静脉血栓形成可能[12-13],但并不是只要升高就表明有血栓性疾病。在调查所有严重胸部创伤患者中,超声发现深静脉血栓的比率较低,结合临床表现,也排除血栓的可能。进一步研究发现,很多严重单纯胸部创伤和低ISS评分的患者体内D-D和FDP也会轻度升高。因此,D-D和FDP含量升高明显,提示病情危重复杂,血栓形成可能性较大,应动态继续监测,及时干预。
胸部创伤常伴随头部损伤,一项研究显示,有25%被诊断为连枷胸的患者存在头部损伤[14]。目前针对颅脑损伤凝血功能障碍研究较多,据统计,创伤性颅脑损伤引起的凝血功能紊乱往往有着不良预后,其住院病死率可高达50%[15]。GCS分值越低,发生凝血功能的可能性越高,当GCS<4分时,几乎所有患者都合并凝血功能障碍。因此,笔者将所有纳入患者进行GCS评分,发现死亡组GCS平均评分明显低于存活组,GCS<9分组中D-D和FDP含量明显升高,虽具有统计学差异,但因与GCS≥9分组样本量差距较大,存在假阳性可能,需今后进一步改进研究。笔者也发现,死亡组和GCS<9分组中伴发颅脑损伤患者占比较大,因此不除外颅脑损伤是严重闭合性胸部创伤患者凝血功能异常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一般认为,其机制是急性创伤后人体处于应激状态,除了释放凝血活酶激活了外源性凝血系统,颅脑损伤会引起大小血管及微血管的损伤,使血管内皮细胞释放大量组织因子促发内源性凝血系统[16]。内外源凝血系统的共同作用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防止颅脑损伤等继续出血。
另外,笔者发现PT凝血指标在多发伤组和ISS>25分组有显著增高,具有统计学差异(t=6.289,P=0.013和t=24.40,P<0.01),但在GCS<9分组(t=1.628,P=0.203)无明显差异。PT是外源性凝血系统常见化验指标,在机体遭受严重创伤时,大量失血导致外源性凝血因子丢失及消耗,导致PT延长,故严重闭合性胸部创伤伴随多发伤和高ISS评分,PT会出现反应性增多。但在GCS<9分或伴严重颅脑损伤患者中,脑组织血管较为丰富,损伤时主要以血管内皮细胞释放大量组织因子促发内源性凝血系统为主,故PT升高较其他失血性休克患者变化显著性不高;且本研究PT受输血影响,因此其特异性不如D-D和FDP强,结果与刘小玲等[17]研究结果相似。在本研究中,各组之间FIB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严重闭合性胸部创伤患者中不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本研究为单中心的回顾性观察研究,未完全纳入所有可能影响因素,如24h内大量输血扩容等抢救,凝血功能如何变化仍需进一步讨论,而且个别组间比较样本量差距较大、许多因素无法进行分层和分组分析,故有待于下一步将研究细化,并希望纳入多中心大宗病例研究。但在各类严重胸部创伤患者受伤早期,D-D和FDP是临床甄别其严重程度,并指导进行早期干预的重要指标。
[1] Kashuk JL,Moore EE,Sawyer M,et al.Postinjury coagulopathy management: goal directed resuscitation via POC thrombelastography[J].Ann Surg,2010,251(4):604-614.
[2] 张连阳.规范应用AIS-ISS(2005)提高多发伤诊断水平[J].创伤外科杂志,2009,11(6):572-573.
[3] Tieu BH,Holcomb JB,Schreiber MA.Coagulopathy: its pathophysiology and treatment in the injured patient[J].World J Surg,2007,31(5):1055-1064.
[4] Floccard B,Rugeri L,Faure A,et al.Early coagulopathy in trauma patients: an on-scene and hospital admission study[J].Injury,2012,43(1):26-32.
[5] 谢辉,刘会敏,马宏伟.D二聚体及FDP检测在骨折患者的应用价值[J].河南医学研究,2012,21(3):302-303.
[6] 席朝运,于洋,陈麟凤,等.1766例创伤患者的临床用血调查分析[J].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2015,23(1):228-233.
[7] 王艳. 输血前后患者凝血功能改变及相关因素的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5,(1):179,180.
[8] 李可可,宋庆青,刘文峰,等.胸部创伤损伤严重度评估及死亡原因分析[J].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2008,15(6):428-431.
[9] 邓燕玲.血浆D-二聚体水平与骨科创伤患者创伤程度的相关性研究[J].中华全科医学,2013,11(5):789-797.
[10] 陈影秋,郭峰.D-二聚体对严重创伤的诊断价值[J].浙江创伤外科,2014,(5):731-732.
[11] 王诚,张红金. 血浆D-二聚体及C反应蛋白测定对急诊创伤性休克患者预后评估的临床意义[J].浙江创伤外科,2015,20(5):864-866.
[12] Niikura T,Sakai Y,Lee S Y,et al.D-dimer levels to screen for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patients with fractures caused by high-energy injuries[J].J Orthop Sci,2015,20(4):682-688.
[13] 王伦善,贾建安,黄其峰,等.FDP和D-二聚体在急性脑梗塞和深静脉血栓中的诊断价值[J].临床输血与检验,2016,18(2):133-136.
[14] Athanassiadi K,Theakos N,Kalantzi N,et al.Prognostic factors in flail-chest patients[J].Eur J Cardiothorac Surg,2010,38(4):466-471.
[15] Epstein DS,Mitra B,O’Reilly G,et al.Acute traumatic coagulopathy in the setting of isolat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Injury,2014,45(5):819-824.
[16] 袁方,丁军,郭衍,等.脑外伤后颅内进展性出血的早期预测[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12,32(4):478-484.
[17] 刘小玲,郭惠,蒋姝婷.严重创伤性患者中D-二聚体与凝血功能的探讨[J].血栓与止血学,2011,17(4):158-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