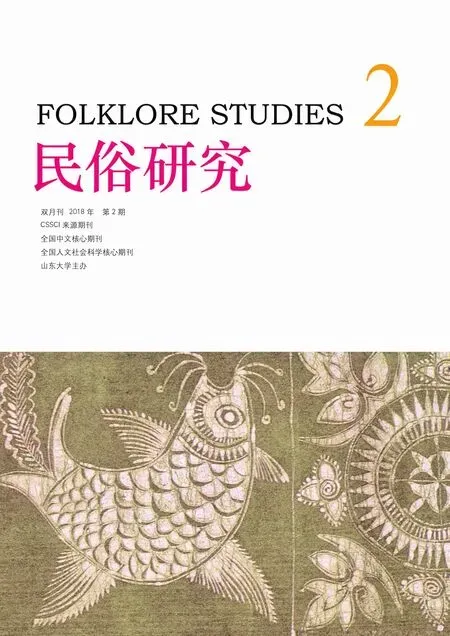袭旧与更新:近代经济变迁中的民间祭祀组织
——以杭州湾南岸地区为例
蒋宏达
一、引 言
1947年,北大前校长蒋梦麟(1886-1964)曾在他那部著名的自传《西潮》(TidesfromtheWest)里回忆起故乡的迎神赛会,娓娓叙述了当时的热闹场景:
迎神赛会很普遍,普通有好几百人参加,沿途围观的则有几千人。这些场合通常总带点宗教色彩,有时是一位神佛出巡各村庄。神像坐在一乘木雕的装饰华丽的轿子里,前面由旌旗华盖、猛龙怪兽、吹鼓手、踩高跷的人等等开道前导。迎神行列经过时,掉狮舞龙就在各村的广场上举行。踩高跷的人,在街头扮演戏剧中的各种角色。一面一面绣着龙虎狮子的巨幅旗帜,由十来个人举着游行,前前后后则由绳索围起来。这样的行列在旷野的大路上移动时,看起来真威风呀!*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第27-28页。《西潮》原著为Monlin Chiang, Tides from the West: A Chinese Autobiograp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7.
蒋梦麟原籍浙江余姚,出生在杭州湾南岸一个名叫“蒋村”的小村子里。引文描述的正是他儿时的乡居见闻。与同时代的很多知识精英相比,蒋梦麟对各种民间仪式活动抱着相对宽容和温和的态度。他在自传中用了一整章的篇幅记录下蒋村乡民的祖先崇拜、神明信仰以及各种年节祭祀活动,饶有兴味地描绘出宗族审判、招魂解禳、神佛治病的童年趣事。不过,这一切都被置于“西风东渐”的背景之下。他相信,自己的童年生活环境“已经很快地成为历史陈迹”,“这个转变首由外国品的输入启其端,继而西方思想和兵舰的入侵加速其进程;终将由现代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化,完毕其全程”。*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第28页。
在蒋梦麟看来,童年所见的祖先祭祀、神佛信仰活动无疑都属于那个行将逝去的时代,它们与源自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思想文化难以相容而并存,终将在滚滚西潮的冲击下湮灭。尽管他对包括迎神赛会在内的民间仪式活动不乏温情与眷念,但其内心秉持的仍然是一种启蒙主义的文化观念。这种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自清末以来百余年里蔚为主流。在这一观念的审视下,基层民众的信仰和仪式活动被抽空了实践内涵,蜕变成一具具空洞的历史遗骸。
观念上的负面定位很快就转化成实际的政治效应。近代以来,随着国家合法性来源和意识形态基础的变动,城乡社会流行的宗教和宗族活动日益成为新派人物和新兴政治势力攻击的对象。特别是进入民国后,此类活动多被贴上“迷信”的标签,屡遭官方压制和禁毁。一系列研究已经表明,近代国家对“迷信”话语的操弄和世俗化宗教政策的推行,严重削弱了民间祭祀组织的统合作用,加剧了政治与宗教、国家与社会间的疏离和对抗。*Prasenjit Duara,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Campaigns Against Popular Relig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0, No. 1 (1991), pp. 75-80; Vincent Goosaert and David A. Palmer,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pp. 43-66; 陈熙远:《宗教——一个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关键词》,(台湾)《新史学》第13卷第4期,2002年。
目前有关民间祭祀组织的研究大都将论述重点放在祭祀活动所蕴涵的“国家-社会”的纵向联系上,致力于揭示现代国家力量与民间仪式活动之间的复杂互动。*海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清末新政时期的“毁庙兴学”和国民政府时期的“反迷信”运动的讨论,如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18-157; Rebecca Nedostup, Superstitious Regimes: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Shuk-wah Poon, Negotiating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State and Common People in Guangzhou, 1900-1937,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日]三谷孝:《秘密结社与中国社会》,李恩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9-207页;黎志添:《民国时期广州市“喃呒道馆”的历史考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7期,2002年;沈洁:《反迷信与社区信仰空间的现代历程——以1934年苏州的求雨仪式为例》,《史林》2007年第2期;沙青青:《信仰与权争:1931年高邮“打城隍”风潮之研究》,《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法]高万桑:《晚清及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迎神赛会》,张安琪、胡学丞译,康豹、高万桑主编:《改变中国宗教的五十年:1898-194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第75-99页。由于偏重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讨论,这些研究对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力量日渐侵入地域市场,区域和跨区域的商贸活动日渐勃兴的背景下,祭祀组织为应对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变动、协调社区内部人群关系而经历的结构性演变甚少涉及。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因受后现代或后殖民思潮影响,开始反思启蒙主义的立场,对民间信仰和仪式活动抱以相当的同情和理解,但多数研究仍然牢固地以“国家-社会”关系(“现代国家-传统社会”)为主轴展开论述。*见前揭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张倩雯(Rebecca Nedostup)和潘淑华(Shuk-wah Poon)等人的著作。在这些研究中,民间祭祀组织的主体性往往隐没不显,只有在与现代国家政治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才能显示其自身的存在。
本文以蒋梦麟的故乡——杭州湾南岸地区为例,对清末民初民间祭祀组织所处的贸易网络的变迁,它们所植根的地方性财产管理制度的演化,以及由这些变化促发的祭祀组织内部的结构调整等问题加以探讨。尽管无法充分展开对这些组织的参与者内在世界的讨论,笔者还是倾向于将他们的仪式和信仰活动视作一种独特的环境和心性的体现,是因应近代经济政治变迁的策略选择和利益表达。*E. P. Thompson,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3, pp. 1-2.本文通过个案剖析试图表明,近代以来,民间祭祀组织呈现出日渐活跃的趋向,但这并非传统濒死的回光返照,而是传统承袭过程中的更新和再造。
二、棉花贸易与地域经济的拓展
杭州湾南岸地区,即今天浙江省慈溪市和余姚市北部沿海一带,处在杭州湾喇叭口南缘,在明清时期属于绍兴府的余姚、宁波府的慈谿和镇海三县北境。这是一片扇形的海积平原,面积约为一千平方公里,大部分土地是元末明初以后从海湾中陆续淤涨出来的。在这一长程的沧桑变迁中,南部居民逐渐向北垦拓、迁徙,在新开发的土地上建立村落,并逐渐发展出市镇。清初以前,当地市镇主要分布在南部宋元海塘沿线及沿山平原一带,清中叶以后,市镇网络渐次向北延伸,至清末已经推进至滨海渔盐地界。*李国祁:《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1796-1911)》,《中山学术文化集刊》第27集,1981年,第325-328页;乐承耀:《明清宁波集市的变迁及其原因》,《浙江学刊》1996年第2期。
杭州湾南岸的开发历程正好呼应着宁波沿海商贸发展的节奏。在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宁波一直是南、北洋商路和财货交汇的贸易枢纽。*[日]斯波義信:《港市論:寧波港と日中海事史》,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 3 (海上の道)》,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第13-29页。清初开放海禁后,宁波商人的活动范围迅速拓展。到了乾嘉时期,本地商人与外地客商以江浙为中心,构筑起南通闽广、北至辽东的沿海贸易路线与东起江南、西达四川的沿江贸易路线。*张守广:《明清时期宁波商人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作为宁波的经济腹地,杭州湾南岸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商人参与到沿海、沿江商贸活动中去,将本地经济生活与区域市场及更广阔的跨区域贸易网络联结起来。*如余姚北部的周巷桑氏和潮塘张氏都曾于乾隆、嘉庆年间开始从事南北洋土货贸易,成为当地颇具实力的商人。见戴尧宏:《宁波帮先驱桑孔斋》,《慈溪史志》2007年第3期;方东编著:《三百年的辉煌:追踪慈溪潮塘张氏家族》,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59-60、80页。
在当地的商贸活动中,棉花贸易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嘉靖《余姚县志》中,已经出现“木绵产海壖,以为絮,或纺之作布,民之大利之”的记载。*嘉靖《余姚县志》卷六《物产》,上海图书馆藏清末抄本。及至清代中叶,当地植棉业更为兴盛,沿海乡民的生计极大地依赖植棉收入,“邑民资是以生者,十之六七”*戴廷沐:《修助海侯庙记》(乾隆六十年),光绪《余姚县志》卷十一《典祀》。。在热络的贸易活动中,大批经营棉花、土布的商人活跃于区域和跨域的市场中。他们浮海南下转输棉花至台州、温州、福州、厦门等地,然后从当地装载木材、砂糖、桂圆等土产回宁绍地区销售。家资饶裕的商人开始积极介入地方事务,变成支配地方社会的新兴势力,并逐渐代替科举士绅成为把控宗族事务的中坚力量。*《余姚孝义傅氏宗谱》卷二《国赉公传》,永锡堂民国二十五年木活字本,第16-17页;《余姚孝义劳氏宗谱》卷三《昭盛公传》,申锡堂民国二十五年木活字本,第23页;《余姚沙墅施氏宗谱》卷首《迪功郎天照公传》《登仕郎小塘公传》,奉先堂民国二十年木活字本,无页码。
19世纪中期通商开埠以后,宁波蜕变为上海的重要支线港口和经济腹地。以宁波和上海为中介,杭州湾南岸的经济与沿海、沿江(长江)的通商口岸市场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当地棉花的生产、销售愈益受到远地市场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1861年4月至1865年4月间,由于美国爆发内战,北美棉花出口拥滞,国际市场出现巨大的原棉供应缺口,英、印等国开始转向中国进口棉花。*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从棉纺织工业史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316页。1862年,浙海关的棉花出口量从前一年的5,849担激增至19,648担,至1863年更跃升到史无前例的125,155担,1864年稍有回落,但仍保持10万担以上的高位(战后急降至3万余担的水平)。面对这一突然变故,杭州湾南岸地区棉农反应热烈,“纷纷弃粮而从棉矣”*《同治八年(1869年)浙海关贸易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
如果说这一短暂的棉业景气缘于战争等偶发因素,那么1890年代初至1920年代末长达30年的原棉出口高峰则建立在市场需求和生产体制的结构性转变的基础上。其关键在于日本和中国国内机器棉纺织工业的扩展。*在此期间,除因天灾、战乱等偶发因素造成棉花减产、出口阻滞外,浙海关的棉花输出量呈现出一条快速增长的曲线。1900年以后,在正常年景下,棉花输出量均维持在不低于10万担的水平,从1907年开始进一步攀升至15万担以上。浙海关税务司佘德(F. Schjoth)在当时的海关报告中提到:“原棉出口的突飞猛进,是在前十年期间本口岸贸易的主要特色之一。在过去年代,棉花出口每年平均仅有12,000担,而现在平均达到8万担……对棉花的不寻常的需求,当然是上海和日本已经建立大量棉纺厂的自然结果。”税务司墨贤理(H. F. Merrill)也在1893年的贸易报告中提出:“目前,日本国内对华棉之需要量与年俱增,而且在那个国家里最近还建立了许多棉纺厂,同时也促进和扩大了宁波地区之棉花种植业。”《浙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光绪十九年(1893年)宁波口华洋贸易情形略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第45、283页。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作为其骨干产业的棉纺织业获得长足发展。*[日]西川俊作、阿部武司编:《日本经济史4:产业化的时代(上)》,杨宁一、曹杰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75页。由于日本本国棉花价格高昂,中国迅速成为主要的原料供应地。据当时的海关贸易报告,1902至1911年间,原棉已经成为宁波最大宗的出口货物,平均每年出口12.7万担,其中约有八成经由上海运往日本。*《浙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2页。紧随日本之后,中国国内的机器棉纺织业也迅速发展起来。甲午战争后的两三年内,上海已经出现“纱厂林立,所用工人日夕赶作”的繁荣场面。*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411页。宁波绅商则于1895年在宁波创建通久源纱厂,杭州于1897年创立通益公纱厂,萧山于1899年设通惠公纱厂,各场纱锭均在万枚以上。1905年后,宁波又先后增设和丰纱厂一厂和二厂。*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中国实业志:浙江省》,(上海)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第13(庚)-14(庚)页。诸厂虽时有兴废,但工业扩张之势已不可挡。
日本、上海及浙江本地机器棉纺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市场对原棉的需求,直接促成棉花收购行业和市镇的勃兴。*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65-173页。清末以来,杭州湾南岸市镇,包括泗门、周巷、天元、浒山、坎墩、逍路头、观海卫、师桥、范市、龙山等在内,纷纷开设花庄、花号,成为远近乡村的棉花集散中心。*许棣香:《昔日棉花业浅谈》,《慈溪工商经济资料》(《慈溪文史资料》第9辑),慈溪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0年,第51页。如泗门最大的花庄宝泰祥号创设于同治年间,光绪后期改为和丰四庄,专为宁波和丰纱厂收购棉花。*杨福堂:《泗门花庄布行的兴衰》,《余姚文史资料》第9辑,余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余姚市政协泗门集镇小组编印,1991年,第96、98页。又如周巷在民初已发展出十余家花行,“在棉花旺收季节,周巷镇内以及农村要道,有不少临时商贩,收购籽棉(俗称水花),转手贩售给花行”。*诸源祥:《周巷商业概况》,《慈溪工商经济资料》,慈溪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0年,第35页。同一时期的天元市也开设了不少花庄,它们“向棉农收购棉花后转运上海、宁波一带牟利。”*朱可淦:《天元工商业沿革》,《慈溪工商经济资料》,慈溪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0年,第46页。浒山一带则出现了以陈震泰、陈茂泰、裘复盛、杨玉兴等“四大家”为首的大批兼营棉花收购和加工的花行,它们同时收购籽棉和皮棉,并使用新式机器绞花脱籽,加工后的棉花直接雇船运至宁波,通过当地花庄的中介,出售给本埠与上海的纱厂。*陈曙华:《解放前的浒山镇工商业》,《慈溪工商经济资料》,慈溪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0年,第27页。至民国十七年(1928),整个杭州湾南岸地区有记录的轧花庄店号总数已多达115家。*《余姚棉花产销状况》,《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21号,1929年;浙江省立棉业改良场编:《余姚各镇花庄调查一览》,郑成林选编:《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汇编》第1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115-122页。
棉市的升腾极大地促进了杭州湾南岸植棉用地的扩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杭州湾南岸的沙盐地带已发展成为浙江最重要的植棉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占全省半数以上。这一时期的棉地扩张不再局限于1860年代“弃粮从棉”式的作物耕种模式调整,而是转向滨海沙涂的大规模围垦。正如1892-1901年的十年海关报告书中提到的那样:“近几年来,本省棉花种植已大为扩展。有大量土地不能种水稻,没有水渠灌溉以及近年来镇海以西面对海湾的沿海土地(即杭州湾南岸地区——引按)大块被开垦,现在到处用来种植棉花。”*佘德:《浙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页。棉田的大规模垦辟使得滨海沙田的开发和控制成为这一时期地方社会的核心议题,由此也引发了基层社会组织的结构调整。
三、宗族组织的结构转型
清末以来,国际和国内市场对棉花需求的增长,特别是由新兴棉纺织工业化引起的滨海棉田扩张趋势,对杭州湾南岸社会造成了巨大扰动。可观的植棉收益促使南部居民蜂拥向北筑塘围垦。由于滨海沙涂的土地边界和地权归属极不明晰,不同人群之间为争夺新生沙涂陆续爆发争端。进入光绪朝后,因植棉用地需求激增,滨海田土争夺更呈白热化状态。*曾广锺:《余姚沙地应行清丈理由书》,绍属余姚沙地清丈委员会宣统三年铅印本,第3页。为了应对长期的械斗和诉讼,当地原本松散的宗族组织不断强化内部整合,使得以大规模沙涂开发和经营为基本活动的控产宗族迅速崛起。
滨海沙盐地带由于缺乏统一的田土管理制度,其地权秩序往往需要通过经年累月的诉讼和械斗才能确立起来。当地争夺沙田的冲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本地灶户宗族势力之间为划分土地界限而产生的争端,文献中多称为“邻界之争”;另一种则是发生在土著灶户与客籍沙民之间的冲突,亦即“主客之争”。*民国《余姚六仓志》八8《盐法》,民国九年铅印本。
邻界之争在当地所在多有,清末民国时期编修的族谱常常连篇累牍地记述不同宗族之间——有时是同一宗族内部不同支派之间——围绕滨海田土的各种纠纷。*《姚江熊氏宗谱》卷一《友于堂公立碑记》,孝友堂民国二年木活字本,无页码;《姚江三门墙张氏宗谱》卷六《子涂小引》,树德堂民国五年木活字本,第4-5页;曹仰钦:《复斋先生传》,《余姚司前桑氏宗谱》卷一《家传》,一本堂民国六年木活字本,第3-6页;周其梧:《柴涂纪略》,《姚北周氏宗谱》卷一,顺德堂民国八年木活字本,无页码;蔡仁标:《西房助地记》,《余姚蔡氏宗谱》卷末,萃先堂民国十年木活字本,第12-13页。如孝义周氏宗祠从道光年间开始围垦沙田,陆续圩筑三丘土地。民国初,周氏着手圩筑第四丘,“不谓工作告成而邻界之争乃起”,毗邻的陈、邵、吴等姓怀疑周氏在勘定土地经界时动了手脚,群起交涉,由此开启了数姓之间反复丈量、诉讼和调解的过程。此案拖延十余年,最终经当地乡绅多方调停,周氏同意将边界所争之地助为本乡教育公产,才得以平息。*周干济:《筑圩始末记》,《姚江孝义周氏宗谱》卷首,雍睦堂民国二十二年木活字本,第1-5页。又如开元周氏在光绪年间与邻界的谢、杨二姓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诉讼才确保对利济塘以北沙涂的占有。*《钦加五品衔赏戴花翎特授余姚县正堂加六级纪录十二次高为出示晓谕勒石永禁事》,《余姚开元周氏宗谱》卷十,大本堂民国十五年木活字本,无页码。与之相仿,慈谿师桥沈氏也在光绪后期经历了漫长的诉讼纷争才将北部新涨的数千亩海地纳入宗祠管理。*这一场诉讼的详细档案保存于沈嘉瑲:《慈谿沈师桥沙涂纪事》,宣统元年印本,第23-67页。
在这些纠纷中,有关孝义五姓争端的记载最为翔实,展示了诸姓之间从冲突到调解、再到合作的完整过程。孝义五姓包括劳、傅、褚、严、陈五大姓氏,他们在姚北平王庙界下毗连而居。五姓之中以劳、傅二姓实力最强,冲突最为激烈。劳、傅之间在道光年间已爆发邻界争端,进入光绪朝后愈演愈烈,并数次对簿公堂。旷日持久的诉讼对双方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一位参与诉讼的劳氏族人曾这样描述应诉的惨境:“傅姓费至一二千贯,而我族费始百数,尚可支持。后则上控府、道,县、场会勘,伤安添砌,火耗烦多。傅姓固祠产尽毁,而我族亦不堪言矣!”*劳梦鲤:《丁涂丈分记事》,《余姚孝义劳氏宗谱》卷四《祠录汇编》,申锡堂民国二十五年木活字本,第2-3页。为了应对延宕不决的讼事,他们不得不先后采取“派丁捐资”“标立钱会”等方法来募集讼费,左支右绌,景况艰难。正当劳、傅二姓为讼事焦头烂额之际,毗连的其他姓氏乘虚而入,大肆“侵占”沙涂。在几方夹攻之下,劳氏率先不支,退而寻求妥协。他们联合褚、严、陈等姓制定了一套“统丈公分”的方法,合力对经界混乱的沙涂进行丈量,为每姓的丁地确定界址和弓数,并绘制成图,呈交给县衙决断。此举得到官府赞赏,经知县和乡绅斡旋,傅姓最终同各姓言和,加入“统丈公分”的行列。*劳梦鲤:《丁涂丈分记事》,《余姚孝义劳氏宗谱》卷四《祠录汇编》,第2-3页。此后,五姓又在此基础上订立“五姓合同议据”,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协调机制,将因沙涂分配而引发的冲突降至低点。*《余姚孝义傅氏宗谱》卷一《圩地记》,永锡堂民国二十五年木活字本,第4-5页。
相比于邻界之争,主客冲突更为激烈,难以调和。大约在乾隆、嘉庆之际,杭州湾南岸一带沙民(“盐户”“卤民”)势力开始展露端倪,并逐渐显示出让官府不安的能量。*汪辉祖:《梦痕余录》,《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第386-387页。这些沙民大都是沿海破产、失地的盐民或农民。他们多半受雇于南部灶户地主、盐商,或在北部海涂开荒植棉,或在海滨从事制盐活动。太平天国动乱后,大量沙民从绍兴、上虞一带涌入姚北,与灶户之间的田土争夺日趋激烈。*民国《余姚六仓志》卷八《盐法》。1880年4月间,上海《申报》以“盐枭滋事”为题报道了姚北泗门一带沙民“霸夺”沙地的情形。*《盐枭滋事》,《申报》1880年4月30日。同年8月间,又传出“灶民被害”事件,本地灶民二人被沙民戳死,数人受伤,而沙民居所则被大量焚毁。*《灶民被害》,《申报》1880年8月7日。民国初,一位同情沙民的余姚盐场官员曾在一份公文中这样描述沙民的景况:“卤民吁请无门,往往迫而出于械斗,然则终以势力悬殊,众寡不敌,虽械斗亦卒归效甚微。至地内房屋、器具、卤缸、漏碗、泥垛等,悉数铲毁,无异兵燹。”*转引自慈溪市盐务管理局、慈溪盐政志编纂委员会编:《慈溪盐政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203页。
光绪后期,前述孝义五姓也因沙涂围垦之事与北部的沙民爆发激烈械斗,致使“五姓子弟咸奋不能平,农夫相约荷锄往垦。沙民即群起斗殴,而诬我以命火重案”*劳尔选:《筑新圩记》,《余姚孝义劳氏宗谱》卷四《祠录汇编》,第11-12页。。这场官司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一直持续到宣统二年(1910)才告平息。劳、傅等姓为此靡费巨万、精疲力竭。*劳尔选:《筑新圩记》,《余姚孝义劳氏宗谱》卷四《祠录汇编》,第13页。
激烈的主客冲突不但引致灶户宗族间的联合,而且强化了宗族内部的整合。孝义劳氏为此制定出详尽的“丁签章程”,用以将南北近十个劳氏村落的壮丁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同沙民的械斗。其中提到:
宗祠丁签重在丁力……以备公事也。公事非他,即祠产内海地圩涂每有筑塘掘沟、保守疆界等役必须人力为之,非壮且近者不能为助。兹特集宗房董事公议,作竹签五百余根,仿五人为伍之法,择一犹壮者为丁首。小事发丁首,大事统发。鸣锣为号,闻锣即各带耜头、铁耙、匾(扁)担、青柴棍等物赴宗祠,听宗房长、董事谋议,踊跃前往,同心协力以相与有成……自明年庚辰起,凡住居本村与平王街、小劳村、傅村、义让路、驿亭路、三塘头、四塘头、劳家埭等处,年自十七岁至五十九岁者俱得灯宵(即元宵灯会——引按)给饼钱,临事给饭钱……倘发丁日,族有闻风来助之壮丁,亦给饭钱,但以报名面给执照为凭,空言难信。*《余姚孝义劳氏宗谱》卷一《章程》,第1-2页。
从章程规定中不难看出,凡接受祠堂公钱的劳姓子弟均有强制参与“公事”义务,否则将面临严处。对此,章程规定,凡接受饼钱之家,在宗祠有事发丁之际,或因早出远门,或因偶乏气力,无法前往者,必须立即向房长上交现钱二百文,另雇异姓壮丁替代。如若临时退缩不前,即罚现钱二百文,以补贴宗祠公费。“此二项若靳不肯出,定于簿内记过,扣除每年饼钱,终身不给,决勿徇情!”*《余姚孝义劳氏宗谱》卷一《章程》,第2页。所谓终身扣发饼钱,就是剥夺祠堂享胙的权利,是极为严厉的处罚。
与劳氏相仿,各大宗族普遍加强了对其成员的控制。大量族谱资料显示,当时宗族组织大规模修订族规章程,对宗族祭祀礼仪、族产管理机构、公产出纳乃至宗族成员的行为举止做出严格规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各姓宗祠开始尝试建立严格的宗族丁口登记制度。如前述开元周氏在新订章程中规定:“祠下添丁在一年期限内,务须开具生年月日,来祠报明。倘因住居远地不能前来,亦须按时函报,以便本祠登载报丁簿,稽核查明,至十六岁可以给发丁钱。”*《贻榖简章》,《余姚开元周氏宗谱》卷十,无页码。四门谢氏二房规定“自今添置添丁、庙见册各一,每岁生子、娶妇者,于清明、十二月二十五日两季,报明名氏、生年月日,备登于册”*《序说》,《四门谢氏二房谱》卷一,阁老第民国七年木活字本,第44页。。师桥沈氏则要求“族内凡有生卒,续于元旦会拜时报名,记其年月日时,婚配亦须注册”*沈嘉瑲:《翻印宗谱刍言》,《师桥沈氏宗谱》卷一,民国二年铅印本,无页码。。此外,其他各姓制定的诸如“分丁簿”“年庚簿”“登丁册”“庙见簿”等各色名头的丁口簿册不胜枚举。
邻界和主客冲突的经历不断迫使杭州湾南岸的宗族加强内部整合。在清末以前,当地各姓宗族大都结构松散,公产相当有限。经过长期的诉讼及械斗实践,成千亩乃至上万亩的庞大地产被划为祠堂公产,实力强大的控产宗族日渐成为当地最显著的社会组织。
至迟在明末清初,宗族组织已在杭州湾南岸地区普及开来,不过近代繁荣的商业经济引发其内部结构的演化,使得这一传统的社会组织内部萌发出新的时代特质。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部分控产宗族的管理方式开始突破房支结构的限制,其内部出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态势。
一个鲜明的例证来自聚居在扇形平原西部水阁周一带的开元周氏。如前文所述,周氏在光绪后期通过长达十年的邻界争端才将两千多亩濒海沙涂纳为宗族公产。为了有效管理这些土地,其族人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宗祠控产制度。光绪十二年(1886),他们向余姚知县申请了一道“谕禁”,其中详细记录了周氏宗祠的祠产安排:
计开:
一、周祠盈、仄、拱、平、建、端各字号民田四十亩零,及利济官塘下周姓直塘西首第一、二、三丘零星各块熟地二百亩零拨入“大宗祭”。
又,东首第三丘除祠内护塘沙计熟地四百亩零,内二百亩拨入“公赋祭”,余拨入“豫备祭”。
又,第四丘熟地三百亩零拨入“培文祭”。
又,第五丘熟地二百亩零,及西首第四丘现熟地七十余亩、其下未熟毛涂约八百亩零拨入“矜恤祭”。*《钦加五品衔赏戴花翎特授余姚县正堂加六级纪录十二次高为出示晓谕勒石永禁事》,《余姚开元周氏宗谱》卷十《谕禁》,无页码。
“谕禁”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祭”的设置。如引文所示,周氏在光绪年间共设置了五个“祭”,分别为大宗祭、公赋祭、豫备祭、培文祭和矜恤祭。到了民国年间,随着沙涂的进一步垦拓,他们又增设贻榖祭,并将新围垦的第六、七、八、九丘1,800余亩土地拨入其中。自此,全族3,800百余亩祠产全部分拨入祭,形成“六大祭”的格局。各祭各司其职:“大宗祭以重祀典,公赋祭以完国课,培文祭以兴教育,矜恤祭以济贫苦,豫备祭以裕岁修。规模宏远,秩序井然。近年,又复筑丁地数丘,增立贻榖一祭,专司阖族丁口,分给每岁丁钱。”*周世凤:《余姚开元周氏续修宗谱序》(1926年),《余姚开元周氏宗谱》卷首,第3页。这里所谓的“祭”实际上是控产宗族内部不同的职能部门。尽管“祭”的名称是用宗族祭祀语言表述出来的,但“祭”本身并不是宗族房支,也不是从宗族房支结构中衍生出来的下位组织。“祭”的运作有其独立的组织架构,有别于传统上习见的按房轮值的公产管理方式。*有关传统时期公产管理制度的讨论见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18-232.
民国十五年(1926),周氏族房绅董为“六大祭”订立严格的章程,在丁产管理中融入选举、董事和监事等现代管理元素。*周世凤:《余姚开元周氏续修宗谱序》,第3-4页。他们在每祭单独的规例之外,统设“六祭总则”。据总则规定,六祭由族人各举董事一人,分管各祭事务,“惟贤达子孙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俱有当选资格”;六祭董事各自雇请司账员一名,管理该祭逐日流水、总清及租账等各项簿据,“每年视事之繁简作为标准,给予薪金若干”;在六祭董事之上,族内公推总董事一人,以监察六祭全年各项进出账目;总董事雇请总司账员一名,以统管汇核各祭收付账目,每年亦发给年俸若干。总董事和各祭董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总董事具有监管各祭的权力,但不掌握财权,每年各祭所收租息公款“悉由各董事分储殷实外姓商店生息,存折归各祭董事收执”,总董事“不得总揽银钱实权,执掌存折”。此外,总则还对各祭之间的公款挪借作了严格限制,“设有通借,亦当年终各归各祭划清界限,不得过解混淆”。*《余姚开元周氏宗谱》卷十《六祭总则》,无页码。在六祭规章程的基础上,周氏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族产经理层。尽管这个经理层中的董事、总董事等人是由阖族“公举”的族人,但他们不需要对他们各自的房派负责,因而独立于宗族房支结构之外。
开元周氏并不是控产组织结构转变的一个孤例。我们在平原东部另一个大族——师桥沈氏那里发现了类似的动向。在清末大规模沙涂开发以前,师桥沈氏并无可观的族产。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三十一年(1895-1905),沈氏宗族经过十年的诉讼纷争将北部3,500余亩沙涂收归宗祠。在这片土地中,除最南部的700余亩划归大宗祠统管外,余下2,800亩土地被平均分成14股,合称“十四丁甲”。*沈嘉瑲:《沙涂纪事略》,《慈谿沈师桥沙涂纪事》,第16页。与开元周氏相似,师桥沈氏对“十四丁甲”的管理也不采取习见的各房轮值的办法。尽管名义上宗族的土地分授给了族内各房管业,但真正经营土地的并不是各个房支本身,而是族内推举的宗祠总经办和各房帮办。*事实上,“十四丁甲”中有两个丁甲归属于沈氏之外的罗、郑二姓。余下的12个丁甲虽在名义上归属于沈氏本族的12个房派,但这12个房派并不是沈氏宗族自身结构演化的结果,而是为应对清末的沙涂开发和管理而临时归并出来的。换言之,这些丁甲并不对应其现实的房支,而更接近于人为划分的土地管理单元。总经办和帮办的职权独立于宗长和房长之外,甚至常常凌驾于后者之上。*沈嘉瑲:《沈氏接涨沙涂报告册》,清宣统三年印本。
在宗族以外,清代后期形成的沙涂地产也有不少以“义庄”名义组织起来。*民国《余姚六仓志》共记录了十所义庄,其中九所由当地的富室巨商建立,并置于各姓宗族的管理之下。见《余姚六仓志》卷十六《义举》,第1-6页。其中,位于扇形平原中部的杜家团三管义社便是一个地缘性的控产组织。三管义社始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由余、蔡、毛、洪、陈等姓公同创立,合力奉祀余姚先贤王阳明。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义塾设立收支簿,“据册管地,按籍征租”,逐渐发展成杜家团沿海沙涂的控制机构。此后,随着海涂加速外涨,义塾控制的地产规模不断扩大。到了民国初期,其公产总计已达1,500余亩。*杨积芳:《杜家团三管义社记》(约民国八年),民国《余姚六仓志》卷十六《义举》,第4-5页。与前述周氏和沈氏相仿,三管义社的田产管理同样实行专门的董事制度,财权与事权相分离。
在财产控制和经营功能之外,这些控产组织日渐扮演起地方市政机关的角色,它们为新的政治关系网络的运行提供了组织基础。如开元周氏的“六大祭”不仅要负责本族公事,而且要处理各种跨族姓的社区事务。其中,大宗祭除管理大宗祠祭祀外,还要负责对地方保护神仁功侯叶恒的祭祀;矜恤祭除了要为族内孤寡老人、孤儿、残疾无依者提供救济外,还要管理“祠下三社为阖族及全村救灾而设”的消防组织“水龙潜吉会”,并督理义冢事务,另外还肩负着向“本村异姓男女身死无力成殓者”施给棺木的职责;培文祭除了向本族学子发给科考费用和肄业奖励外,还须负责义塾的运作。*《余姚开元周氏宗谱》卷十《大宗祭规例》《培文祭规例》《矜恤祭规例》《六祭总则》,无页码;邹松寿、杨志荣:《话说泗门庙会》,《余姚文史资料》第9辑,第136-137页。同样,沈氏宗族也承担起多种社区职能。它建立了兴善局和储材公所,为师桥一带的贫民提供施棺殓葬的服务。它还担负当地的禁赌工作、向沈氏及罗郑二姓内部“极穷绝食及鳏寡孤独之人”给发米薪钱文的救济工作、宗祠义塾的经费措置工作、每年元旦拜会时的丁口登记工作、中元节海滨祀孤放焰活动的组织工作,以至在濒海山头点天灯为渔船导航的工作。*《公议条约》,沈嘉瑲:《沈氏接涨沙涂报告册》,第10-13页。在清末民初的慈谿北乡自治运动中,沈氏宗族还插手当地的权力中枢——慈北水利公所的事务。*沈嘉瑲:《慈溪沈师桥第一次万安统沙涂报告册》,民国四年印本,第2-8页。三管义社在光绪中期以后职能也不断拓展,“在义塾,则科举给以膏火之资,学校辅以经常之费;在水利,则累次凿浦建闸,土木之费辄数千金;在祭祀,则褅以五月十六日,尝以九月十六日,俎豆馨香,致燔散胙”。在地方自治运动中,它又进一步兼管杜家团水利公所,成为当地的实际管理机构。*杨积芳:《杜家团三管义社记》,民国《余姚六仓志》卷十六《义举》,第5页。这些民间祭祀组织并非与近代政治文化处于截然对立的位置,而是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动不断进行自我调适,从而表现出相当的能动性。
四、神会组织:平等与阶序
激烈的邻界和主客冲突同样强化了当地的神会组织,各种建立在地缘和宗族网络上的神会活动蓬勃发展起来,以协调由宗族控产活动所引发的种种矛盾纠葛。当地的神会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分别为“礼拜”和“赛会”。不同的神会形式体现出不同的人群关系和秩序状态。宗族控产的需求强化了不同区位神会组织的不同发展路径。
“礼拜”又称“行会”,是姚北乡间以庵庙为中心的结社祈神活动。乡民们在不同的庵庙下结成礼拜社,一个礼拜社往往代表着团聚在一个庵庙下的特定社群,多以同姓、同族人为主体。*不同庵庙下的礼拜社数目存在差别,或一庙一社,或一庙多社,视乎庙宇的实力而定。每个礼拜社有若干柱首、执事董理本社事务,下设各种分类会脚,分担行会期间的仪仗和表演职能。*姚鹏飞、鲁水平主编:《姚江风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礼拜活动突出的特点在于,行礼拜时,中心庙宇的神明——通常是观音——在庙坐宫接受下属礼拜社信众的参拜。部分礼拜活动规模很大,如以芦城庙为中心的二月礼拜“其范围之广,东至洋浦社,西至化龙堰白龙社,南至横河大清社,北至海滨”,涉及其下十六个庵庙、四十八个礼拜社。*邹松寿:《余姚庙会调查》,《浙江民俗》1987年第2期。
与礼拜不同,赛会的主体活动是游神,届时信众舁神出庙,巡行四境。如孝义乡的劳、傅、褚、严、陈等姓结成“天医胜会”(平王庙),隔年举办日会和夜会,“巡迎范围西至朗霞、泗门、湖堤;东至沙黄、驿亭路、悦来市、长河市等地”*邹松寿:《余姚庙会调查》,《浙江民俗》1987年第2期。。又如周巷、朗霞、泗门和临山等地盛行东岳赛会,其巡迎范围东起周巷、朗霞,西至泗门汝仇湖堤,南至天华、东蒲、沿山一线,北至海滨,覆盖整个余姚西北地方。*邹松寿、杨志荣:《话说泗门庙会》,《余姚文史资料》第9辑,第132页。开篇所引蒋梦麟自传,描述的正是平原西部乡民赛会的场景。在东部的慈北和镇北地区也存在名目繁多的神会巡游活动。如观海卫东北东山头一带有“都神会”(都神殿),由居住在卫城东部和南部的方姓联合东山附近的林、吴、徐三姓及卫城西南部的韩、蒋二姓组成。慈北一带极具影响力的师桥“高台阁会”(新浦庙)则由沈氏宗族主导,联合罗、郑二姓举行,其巡迎范围覆盖大古塘以南整个鸣鹤乡境。又如鸣鹤东部古窑浦一带有洋山会(洋山殿),由附近戎、厉、柴、裘、陈、叶等六姓居民轮流主理,巡行六姓村落一周。此外,慈北和镇北还流行蚕花会、药王会、大旗会、城隍会、海祭会等多种形式的赛会活动。*方东主编:《快船江风情》,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46-278页。
杭州湾南岸地区的礼拜和赛会活动的分布具有明确的地域界限(见下图)。礼拜活动分布在洋浦以西、化龙堰以东,即扇形平原的中部地区,而赛会活动则流行于扇形平原的东西两翼。这一分布态势与当地的海涂成陆状况和土地开发进程紧密相关。

图1 杭州湾南岸地区神会活动分布示意图(注:虚线框代表礼拜或赛会的范围,虚线箭头代表礼拜行会或巡会游神的方向)
由于西侧受钱塘江来水冲击,东侧受外海潮汐顶蚀,平原中部的成陆速度远快于东西两翼。*在明代以来大约600年时间里,扇形平原最宽处的浒山—庵东断面总计外涨30余里,平均每20年涨出1里,其淤涨速度向东西两侧呈递减趋势。陈吉余、恽才兴、虞志英:《杭州湾的动力地貌》,陈吉余等:《中国海岸发育过程和演变规律》,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第81-96页。这一地理特质使得中部与两翼的聚落结构呈现出明显差异。平原中部地区自明初开始,随着海涂淤涨,居民不断北迁,南部村落(母村)陆续向北分迁出一连串分支村落(子村),从而形成南北子母村落成串分布的格局。*在田野调查中,当地人曾形象地将这种南北成串出现的村落描述为“爹爹村”和“儿子村”,或者“爷爷村”“爹爹村”和“孙子村”,认为它们是“一个生一个”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聚落结构还与当地的社庙系统相适应。*这些社庙大部分属于多姓联合供奉的香火庙,即乡村中管理死后亡灵世界的庙宇。庙宇的管理由各姓宗族按柱轮值,其费用多由宗祠公产拨付。见《余姚上林周氏宗谱》卷首《祭则》,敦伦堂光绪二十七年木活字本,无页码。当地人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社庙,一旦有人过世,鬼差们就会把魂灵押解到相应的社庙里去。每座社庙都有自己特定的“庙界”,亦即庙宇管辖范围。*有关庙界的讨论见王健:《明清以来江南民间信仰中的庙界:以苏、松为中心》,《史林》2008年第6期。一般而言,只有大古塘附近的母村才有这种社庙。这些庙宇的庙界范围从塘南的母村开始一直延伸到海际,子村村民的灵魂也归属于母村的社庙。哪怕经历数次分迁,移居至离母村数十公里远的地方,那些乡民死后其亡灵仍由母村的社庙派鬼差押解审判。礼拜会的中心庙宇通常都是位于南部母村附近的大型社庙,故礼拜的形式主要是北迁出去的子村居民结成礼拜社向南部主庙神明参拜。这种主庙神明在庙坐宫接受村社朝拜的形式体现出一种处于下位的村社(子村)向处于上位的村社(母村)表达恭敬与顺服的状态,彰显了南部村落对北部村落的支配地位。由于南北母—子村落之间常有同姓血缘关系,礼拜活动也内含着联合宗支的意味。
平原两翼因水沙动力条件的限制,土地淤涨幅度有限,较少出现南北子母村落连贯分布的现象。与沟通南北宗支村落的礼拜不同,两翼的赛会活动主要处理东西向不同族姓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赛会巡迎多个神灵,不同神灵之间结成类似兄弟的平行关系。如东山头都神会(都神殿)巡迎的五都大帝是具有“白、蓝、黑、红、黄”脸谱的五座神像,当地人认为他们是明初的五位开国将领。洋山会(洋山殿)巡迎的洋山大帝则是洋山殿内三座同样大小的神像,据说是海上三山之神。西部朗霞、泗门一带的将军会巡迎的刘猛将也有大、小兄弟之分,而泗门新岳殿岳帝会则同时巡迎本庙东岳神、朝北庙天医尊神和络芦庵关帝圣君。尽管这些神明之间的实力存在强弱差别,正如兄弟神灵间也存在排行大小和出巡顺序先后一样,但彼此间仍然维持着相对平等的地位。这与礼拜活动内含的南北向的阶序关系形成对比。*本文对礼拜和赛会中隐含的权力关系的讨论受有关港台天后信仰研究的启发。见廖迪生:《香港天后崇拜》,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第30-31页;Kristofer Schipper, The Taoist Bo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23, 29.
杭州湾南岸的赛会和礼拜往往场面盛大,随之而来的则是巨大的开销。神会活动的花费除小部分来自各个庵庙的庙产或礼拜社的会产外,大部分由控制社庙的各姓宗族承担。*事实上,当地庙产和会产规模有限,大都不过三五亩土地的租息,甚至只有几分几厘地,无法支持大规模的神会活动。如上林周、丁、徐、岑四姓宗族合力支持着樟树庙神会。据《余姚上林周氏宗谱》卷首《祭则》:
吾里樟树庙,七月间向有龙、刘二神会,我周氏与丁、徐、岑四姓共分六柱。周氏一柱,丁氏一柱,徐氏一柱,岑氏三柱,永年以六柱挨次值祭、演戏。我周氏每于辰、戌两年值之。值祭之年,宗祠开销祭费、戏钱约十贯左右,宗长、各房长、各董事前往祭奠,永以为例。*《余姚上林周氏宗谱》卷首《祭则》,敦伦堂光绪二十七年木活字版。
又如开元周氏就在宗族公产中划出部分沙涂资助芦山庙大王会、皇封桥庙判会和莲风庵刘猛将军会,并于“大宗祭”规例中开列各会田土字号、亩分。*“大王会:三坵秋字号 地念三亩三分三厘二毫;判会:四坵蒸字号 地十五亩三分八厘,五坵尝字号 地十亩零七厘;将军会:三坵百字号 地十四亩零七厘。”见《余姚开元周氏宗谱》卷十《大宗祭规例》,无页码。孝义傅氏则在宗谱凡例中规定:“平王庙,吾族在其庙下也。庙内凡有公事、公款应预闻与科派者,每岁九月二十三日演戏、祀神费项……其资由本祠公项发给。”*《余姚孝义傅氏宗谱》卷首《凡例》,第6页。所谓“本祠公项”无疑都来自植棉沙涂的租金所得。
最为显著的例子来自师桥沈氏。1932年底,沈氏主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高台阁会。此次赛会历时三天,“远近往观者达数十万人”*《迎赛高抬阁:宁波三北人之豪兴》,《时代》第3卷第8期,1932年。。据当时报章报道:“此次浙江三北举行高台阁会,靡费之巨,实足惊人。据云,高台阁出行时,上下左右,所占面积极广,故事先拆屋、铺路,耗费约在一百万元左右;而各地赴会之人,难以计数,所耗旅费,亦在一百万元以上。”*《痛心之事》,《商报画刊》第12卷第11期,1932年。所谓靡费百万或有夸张,但巡会开销巨大则是事实。高台阁会的费用主要来自清末以来围垦的沙涂公产,余下部分则由宗族向沈氏殷商筹集。早在赛会前一年,师桥沈氏宗长已特意在上海的一家高档饭店里租下包间,协同各房房长宴请有财势的旅沪族人,共同商讨筹款事宜。为了使身在上海的族人可以如期与会,据说他们还敦请宁波商人领袖虞洽卿出面,照会上海各店号、企业,准许沈氏族裔届期放假,回乡参会。
杭州湾南岸州县至迟在明末已经普遍出现普通乡民的结社巡会活动,沿海沙盐地带系统的神会活动应该形成于清代中叶以后。*万历《新修余姚县志》卷五《风俗》,第14页;光绪《余姚县志》卷五《风俗》,第2页。清末以来,控产宗族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神会的发展。显然,不同神会形式与宗族的控产活动密切相关。礼拜活动中由北向南的参拜活动有助于南部母村宗族统合北部子村的宗族支系,而赛会活动中神灵之间兄弟般的平等关系则因应着东西向不同族姓聚落的协商与联盟。在棉花贸易中勃然兴起的控产宗族,为神会活动注入了庞大资金,推动后者向着“靡费钜万”“如醉如狂”的状态发展。*叶影:《姚北的礼拜会》,《时事公报》1947年3月15日。
五、结 语
从清代中叶开始,杭州湾南岸地区已经形成重层的市场网络,食盐、棉花、米粮、海货等商品以市镇为节点,经各路商人之手流通于各处。特别是棉花和土布等大宗土产的运销,使本地市场通过宁波港的中介作用与闽粤、吴楚等跨区域的沿海、沿江贸易网络联系起来。五口通商以后,这一地区进一步卷入以宁波和上海为中心的通商口岸经济圈中。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日本和中国国内机器棉纺业的相继兴起,域内外原棉需求急剧扩张,并长期呈现高涨态势。为因应宏观市场环境的变化,杭州湾南岸沙盐地带棉田不断扩大,迅速成为浙江最大的棉花种植和原棉输出地。地方市场开始与世界经济体系直接对接,使得沿海、沿江口岸地区和国际市场的经济变动愈益成为本地市场变化的牵引力量。
清末以来,棉业的勃兴推动沿海沙地的大规模围垦,在邻界之争和主客之争的双重压力下,一大批宗族转化为控产宗族。在宗族资金的支持下,地方神会活动也随之兴盛起来。这些神会活动配合着宗族的控产活动。分布于平原中部地区以主神坐宫接受北村社朝拜为特点的礼拜活动,和分布于东西两翼以主神巡行四境为特点的赛会活动,分别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权力关系,即南部旧有聚落控制北部新生聚落的阶序关系与邻界聚落之间彼此统合的对等关系。与此同时,杭州湾南岸地区祭祀组织的控产结构也发生了变动,专门化的董事经理层开始出现,从而引发控产组织内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态势。这一结构性的变化正好顺应了清末民初新政改革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新兴的控产组织为当时的政治社会变动提供了组织基础。
蒋梦麟在描绘近代“西风东渐”过程中中国所面临的危局时,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他说,当时西方的商业势力在兵舰的护卫下犹如章鱼一样盘踞在通商口岸,而章鱼的触须已经延伸到中国内地的富庶省份。不过,令他担忧的是,大部分中国人对此却反应迟钝,“亿万人民依旧悠然自得地过着日子,像过去一样过他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生活,从没有想到在现代的工作上下功夫”*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第14页。。蒋氏故乡的情形表明,他的视野存在一片盲区。他未曾意识到,正是那些在他眼里最具传统意味的民间祭祀组织的活动里,已经蕴涵着民众为应对近代商业势力延伸过来的“章鱼触须”而付出的努力。尽管这不能全然等同于“在现代的工作上下功夫”,但人们并非总对“现代的工作”加以拒斥。蒋梦麟所津津乐道的迎神赛会里,不止有历史的孑遗,还有因应近代经济变迁的社会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