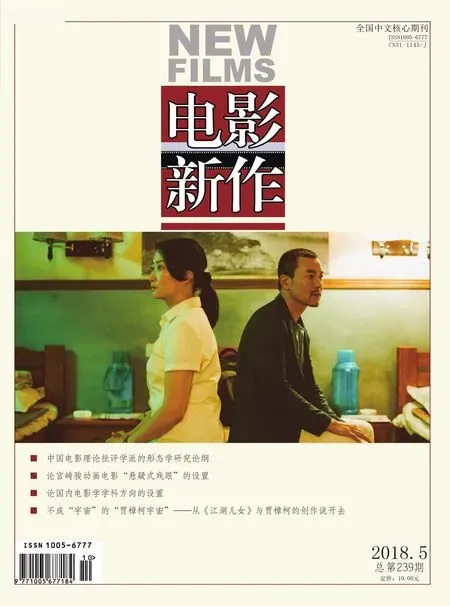迈克尔·度德威特动画电影诗化叙事研究
彭 俊
迈克尔·度德威特出生于1953年,于1992年制作了环保主题艺术短片《清洁工汤姆》,该片以简洁故事传递深刻含义的叙事方式,确定了度德威特的创作风格。创作于1994年的《和尚与飞鱼》饱含对东方传统哲学精神的思辨,并荣获欧洲金动画奖。2000年,讲述离别与等候的《父与女》问世,该片不仅斩获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英国电影学院奖,还在安纳西、萨格拉布和广岛的国际动画电影节上折桂。《红海龟》是度德威特执导的第一部动画长片,也是吉卜力工作室与国外导演合作的首部作品。该片先后荣获2016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特别奖和2017年安妮奖最佳独立动画长片奖。
商业电影在创作上会刻意迎合大众欣赏口味,倚重跌宕起伏的故事和模式化的叙事手法。艺术电影往往强调创作者的个性表达,反对程式化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刻画。度德威特动画作品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对白,选取简单平淡的故事,运用诗化的叙事结构与叙事手法,着力于诗意的渲染和意义的挖掘,用简洁、唯美、细腻的视听语言赋予动画隽永的哲理和强烈的情感。《和尚与飞鱼》《父与女》《红海龟》等影片获得的巨大成功,让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这种诗意的创作手法是如何成功挑战经典叙事法则,取得如此大的艺术魅力的?这种动人的诗意又是如何被作者建构出来的?下文试从影片的剧作结构和叙事策略等方面作出解答。
一、诗化的剧作结构
悉德·菲尔德说:“结构就是把故事按照一定位置安排好的东西。”罗伯特·麦基进一步认为:“结构是对人物生活故事中一系列事件的选择,这种选择将事件组合成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序列,以激发特定而具体的情感,并表达一种特定而具体的人生观。”就观众而言,这种结构序列并非直观可见的对象,人们看到的只是人物形象、情节事件等影片外在的血肉,而影片的叙事结构才是构成影片的内在骨骼,对其进行梳理和探究是我们研究导演风格和叙事手法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早期的电影从戏剧中学到了按照戏剧冲突规律来构建剧本的方法,发展出经典的戏剧式结构模式,其美学特色是以复杂曲折、环环相扣的故事来传达审美意图和艺术观念,因此最容易获得电影观众的认同。好莱坞的动画电影以及宫崎骏的作品大都采用这种结构。《千与千寻》以千寻一家闯入神秘小镇,父母变成猪,千寻被夺去名字为开端,一系列互为因果的情节和事件循序渐进,随着矛盾冲突的产生、悬置、加剧和解除,最后千寻找回了自己的名字并救出了父母,影片也顺利地达到了掌控观众观赏心理和释放情感需求的目的。
不过,度德威特没有采用戏剧式结构,而是选择了以人物的心理或情绪变化作为基本叙事线索、淡化情节、强调抒情的诗化结构。如果说戏剧式结构是受戏剧的影响,那么诗化结构则来自于对诗的学习。诗最富于作者的主观感情,正如华兹华斯所说,“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并且,“在这些诗中,是情感给予动作和情节以重要性,而不是动作和情节给予情感以重要性”。诗化叙事结构首先承继了诗的这一特色,它不靠情节的因果逻辑,而是靠人物情感的累积、变化来推动叙事。例如费穆导的《小城之春》就是完全以女主角周玉纹的自白和旁白为叙事线索,以主要人物心理、情感的变化来推动故事发展。影片情景交融,充满诗意地展现了个人情感与伦理道德、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
迈克尔·度德威特的作品基本都是以情感的发展变化来结构故事。比如《和尚与飞鱼》中,故事的主线就是僧人从费尽心机抓鱼到放下执念“鱼我两忘”的态度转变,人物的心理变化赋予故事情节本身所没有的抒情意味。《父与女》的叙事线索则是女儿对父亲的思念之情。影片中,寒来暑往,时间飞逝,随着女儿年龄的逐渐增大,我们看到她每次到堤岸边停留等候的时间越来越长,对父亲的思念虽经岁月侵蚀却变得愈加强烈。这一情感线索贯穿始终,伴随着片中含义深刻的视觉意象、细腻生动的情节设计和朴素委婉的镜头语言,将既美丽又痛苦的情感勾画得诗意盎然,感人至深。《红海龟》更加明显,影片用人一生中所要经历的各种情愫串起了一个“荒岛余生”的故事,身陷险境时的恐惧、夜深人静时的孤独、看到希望时的喜悦、遇见爱情时的心动、家人欢聚时的满足、遭遇灾难时的绝望、生离死别时的哀伤,平淡的故事情节似乎在呈现着观众自己的亲身经历,充满引人遐想的哲理空间。

图1.电影《父与女》
诗化剧作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不重情节,重细节。它不强调故事情节的因果关系,而是对生活中稀松平常的小事、小情乃至一个小动作格外重视。以《那山那人那狗》为例,父子两人在送信途中曾遇到一条小溪,儿子执意要背父亲过溪。父亲在儿子的背上忆起从前,流下泪来。上岸后,父亲连忙避开儿子的视线,偷偷擦掉脸上的泪痕。这段自然、真切的生活细节,完成了人物感情和人物关系的细微变化。在背父亲过溪的过程中,两人的距离和隔膜消失了。在《小城之春》中,玉纹初次去找志忱,与朝思暮想的旧情人同处一室,却始终背对着志忱,说话时也低头望向别处,故意躲避他的目光。这些细微的动作,勾勒出一个传统女人的羞涩与矜持,也透露了一个寂寞人妇的摇摆与挣扎。
在《父与女》中,类似富有深意的细节也俯拾皆是。在描写人与自行车的关系时,看似简单枯燥的骑车动作,被作者赋予了动人的细节魅力。小女孩骑车时的得意洋洋,中年人骑车时的不紧不慢,老妇人骑车时的摇摇晃晃,逆风时的费力,顺风时的轻松,都显得真实生动而富有诗意。另外,女儿第一次骑车来到岸边时,是随手将车放倒在路边的,而当年迈的她最后一次来到岸边时,同样“年迈”的自行车自己倒了下来。耐人寻味的细节刻画加深了观众对影片丰富内涵的思考。
再看《红海龟》,其故事情节大致可以分为七个段落:
1.主人公流落岛上后探索和熟悉小岛;
2.三次建造竹筏逃离均被红海龟阻扰;
3.与红海龟变成的女人结合、生子;
4.三口之家的岛上生活,儿子逐渐长大;
5.岛上突发海啸,主人公死里逃生;
6.儿子向往远方,夫妻不舍地送别儿子离去;
7.主人公老死岛上,红海龟游向大海。
除第2段落、第5段落具有一定的戏剧冲突外,其余段落均是由平凡的生活事件构成,这些场面共同连缀起流落小岛的男主人公从单身到为人夫、为人父,最终年老故去的一生,一步步展现出主人公细微的情感变化,也传达出作者对爱与孤独、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切感悟。

图2.电影《红海龟》
当然,我们将度德威特的作品称之为诗化动画,不是仅仅因为它们采用了以情感为主线,注重细节渲染的诗化剧作结构,更关键的是因为影片在叙事策略上的“有意为之”。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动画电影,如《千与千寻》里面不少情节场面也是极富诗意的,但却不能称之为诗化动画,一方面是因为其叙事结构并非以人物情感的变化为主导来创造诗的氛围与意境;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故事情节的曲折跌宕,使这些诗意的画面往往成为紧张剧情间隙的一种放松,难以让观众在观影的当下自觉地产生对影片所反映的意蕴的主动思考。
二、简化的叙事内容
厄尔·迈纳在研究诗的时候,将符码的表现归结为:简洁和减少人物的活动。如《诗经·国风·周南·芣苡》便是一首极其简洁朴素的诗。从简单的一句“采采芣苡,薄言采之”发展成三章六句的诗,在三章中只换了六个字。首章写开始采,第二章写采的方式,第三章写采的收获,描绘出一群田家妇女在风和日丽时一边采集,一边歌唱的欢乐景象。

图3.电影《千与千寻》
B·史克罗夫斯基在《电影诗学》的论文集中写道:“没有情节的电影,就是诗的电影。”换言之,电影叙事中诗意的产生,首先需要尽可能地减少信息冲突,这样做可以避免观众沉浸在纷繁多变的叙事素材和环环相扣的因果事件之中无法自拔,为观众腾出审美情绪去参与的时间和空间。在电影《小城之春》中,影片并没有交代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所谓的小城里除去几个片中人物外就再无他人,好像是与世隔绝的一个封闭世界。几个人物在一间破败的房屋里发生的几件小事,让观众对于爱情、希望和责任产生了一种似有所悟又难以说清的感受。
再来看度德威特的作品。《清洁工汤姆》短小精悍,只有一个清洁工、一个垃圾桶和一群来来往往乱扔垃圾的行人。留白的背景仿佛告诉观众,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和尚与飞鱼》的情节也极为简单:和尚发现了鱼,于是想方设法捉鱼,每次都失败的和尚最后与鱼一起飞向天际。简单的故事中,和尚对鱼的态度从执著到豁然的转变令人深思。在《父与女》中,父亲为什么要离开女儿,父亲离开后女儿与谁一起生活,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这些观众会感兴趣的叙事内容都被作者省略了。唯一的故事情节就是离别之后女儿一次又一次来到岸边的等候,唯一的叙事场景就是父女分别的堤岸。度德威特曾在该片的首尾——分离和重逢时刻分别设计了父与女拥抱后跳华尔兹的情节,后来去掉了,因为他觉得“简单的拥抱能传达更强烈的感情”。片尾还有一组20秒的海鸟镜头也被删去了,按照作者的解释,“这样会转移观众对故事主线的注意力。其实,创作的过程就是简化的过程。”简化至极的故事情节留给观众无限的诗意遐想空间。
动画长片《红海龟》也是如此,所有故事都在那个荒凉的小岛上展开,男主人是如何遭遇海难,以及他的身份背景一概被作者回避,红海龟的身份以及她为什么要阻止男人离开小岛,她为什么会变成女人也被略过。我们看到的只是男女主人公相识后相爱、生子、老去、离别的生命过程。少之又少的人物,纯粹、简单的故事构造,让观众的情绪被不自主地引进了对影片丰富意蕴的思索之中。片中诸多故事细节也都采取了简化的策略,如表现男女主人公相爱的场面:他们相对跪坐在洲头,女人捡起并吃掉一个贻贝,递给男人一个,男人缓慢地接过,放进嘴里,两人相对而视。男人想起自己对红海龟的伤害,露出愧疚的表情,女人用手轻抚他的脸颊,起身离去,男人跟随而去,一起跑进竹林。作者以最为简单平和的方式让他们相爱,毫无戏剧性的手法,却令观者心生感动。从这个片段我们可以看出,“信息的衰减在流畅的叙事中造成了信息层面上的‘孔洞’,但是当这些因为丧失信息而形成的‘孔洞’被欣赏主体的情绪填充时,我们便能获得诗意。”
除了人物、故事情节、
场景的简化外,度德威特将影片中的镜头景别和声音也尽量简化了。在其所有影片中,除了极少量的中景和特写,全都采用了远景和全景的景别,这样的景别设置不光营造出一种不掺入个人意见的叙事氛围,令观者以为作者仅在“直言其事耳”,更让影片的画面构成变得单纯而简约。对电影声音元素的简化亦然。声音元素的加入,是电影艺术发展的必然,它与影像造型一起成为叙事的重要构成手段。度德威特却将声音的使用压缩到了最低限度。不光没有人物对白,音乐的使用也相当克制。我们所能听到的所有声音无非是虫鸣、鸟叫、风雨声、人的呼吸和叫喊,以及适时出现的用来烘托情绪、营造诗意的配乐。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曾说,电影音乐的职能是消除观众对音乐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这种需要,音乐要使观众听而不闻,让他们的感官全部集中于电影镜头上。可以说,度德威特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三、象征的叙事手法
对于重在抒情的影片而言,在叙述上往往更需要运用非叙事性元素,如画面的视觉张力、象征、隐喻等来构筑影片结构。度德威特作品中的画面张力是有目共睹的,他把动画片中的造型和视觉构成看成是动感因素,他在谈到《父与女》的创作时表示:“风景中表现力度的线条、人物的动作、风景切换时产生的动感、画面变化时的动态效果,这些因素让影片变得富有诗意,当然,也使叙事变得更加清晰。”确实如此,影片中动与静、疏与密、方与圆,以及点线面的搭配与对比显示出了作者深厚的影像叙事功力。河堤上成排的大树、被风吹动如层层波浪的毛草、浅滩上形单影只的水鸟、秋风中漫天飞舞的落叶,没有一处不给人以一种如诗如画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象征与隐喻的注入能使影像画面的视觉张力进一步提升并激起观众的情感回应。正如马拉美所说:“诗歌不应说教,而应暗示和启发;不应直呼其名,而应创造氛围。”即要善用象征、比喻等手法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如《诗经·国风·邶风·凯风》。诗中第一二章以“凯风”喻母爱,以“棘心”和“棘薪”喻年幼的儿女和成年的儿女。第三四章又以在地下流淌,滋养浚人的“寒泉”象征母爱,以黄鸟尚且可以发出悦耳动听的鸣叫来比拟七个儿子不能抚慰母亲劳苦的心。诗中虽然没有实写母亲如何辛劳,但那些有声有色的意象却将一个伟大的母亲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
我们看到众多诗化电影或电影的诗意段落中,都有大量的象征与隐喻存在。世界电影史上最为经典的“隐喻”之一在《战舰波将金号》中,爱森斯坦把三个雕像——躺着的石狮子、抬起头来的石狮子、跃起的石狮子与沙皇军队的血腥屠杀、人民群众的愤怒觉醒等镜头剪接在一起,体现了人民奋起抗击罪恶与暴力的那种崇高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影片中最具“诗意”的形象。再如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影片通过浊浪滚滚的黄河、贫瘠广阔的黄土地、壮观的腰鼓阵、鼓乐齐鸣的迎亲队伍、虔诚的求雨仪式等一系列富有象征意味的造型与场景,营造出厚重的诗意氛围,抒发了创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中华民族的深沉情感。
度德威特的作品中同样充满了象征与隐喻的意象。比如《和尚与飞鱼》中,和尚求之不得的鱼不只是鱼,它象征人的欲望,正是这种可供读解的符号化象征赋予影片“诗以言志”的气质。在《父与女》中,变换的沧海桑田和反复出现的车轮特写,象征了生命的循环不息,烘托了影片主旨。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红海龟》,俨然一篇由无数象征符号编织而成的抒情诗。比如男主人公初至荒岛,海上飘来的木桶象征着男主角求生的希望,空空的木桶的碎裂则象征他希望的破灭,也暗示他终老于岛上的结局;初生的小海龟们义无反顾地奔向大海象征着生命的力量,也给了男主人公活下去的勇气;儿子捡到的漂流瓶象征外面的世界,也暗示了儿子的最终离去;月缺月圆的更替和候鸟的来回迁徙象征岁月的静静流逝;夭折的小海龟被螃蟹吃掉,螃蟹被海鸟叼走,死去的海狮被苍蝇围绕,苍蝇又被蜘蛛猎食的情节暗含了大自然亘古不变的循环法则;而突如其来的海啸瞬间摧毁郁郁葱葱的竹林,螃蟹、百足虫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则告诉观众人生的变幻无常和大自然足以吞没一切的伟大力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男主角的三次梦境分别是对他三次心理变化的隐喻:梦见竹桥揭示了他想离开荒岛的急切心情;梦见乐队则表明他对往日自在生活的不舍之情、梦见红海龟腾空而起则代表他内心对红海龟之死的愧疚之情。
当我们向人复述《红海龟》的故事情节时,必定是索然无味的,因为那样全然丧失了片中象征意象在客体接受过程中所产生的情绪与诗意。正如苏珊·朗格所说:“当人们试图对诗进行意译的时候,诗本身便在这种复述中消失了。很明显,当一个诗人创造一首诗的时候,他创造出的诗句并不单纯是为了告诉人们一件什么事情,而是想用某种特殊的方式去谈论这件事情。”
四、反复的情节与意象
重章叠句是诗中常常采用的艺术手法,其目的不是为了说得少,而是为了说得更强烈,使艺术形象更鲜明,意境更深远。《诗经》中许多的诗都使用了反复、重叠的表现手法,在第二章第三章重复第一章的句子,仅在个别字词上加以改变。如前文提到的《芣苡》《凯风》两首诗皆是如此。《芣苡》全是重章叠句,将“采采芣苡,薄言采之”六次重复,每次换一字,反复地描写采集的过程,采集成果的由少至多也因此表达出来,全诗未用一个“乐”字,却充满了欢乐的情调。《凯风》中第一二章“凯风自南”诗句的重复,强调母亲像和暖春风般把子女从幼年抚养到成人的深恩;第三四章“有子七人”诗句的重复,则以养育子女之多来突显母亲的长年辛劳。读后令人印象深刻、心灵震撼,不由得反省自身。
在电影中,“反复”也是减少有效信息、创造诗情画意的一种有效手段,因为注重诗化叙事的影片所依赖的不是情节,而是情绪,反复或者说场面的叠加能使情绪层层积累,从而创造出诗的意境。爱森斯坦认为,要使作品具有结构上的稳定性和完整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复,并说:“音乐作品中的某个主题,每隔一定时间就会以不同的变奏形式重复出现于整个音乐材料中。在诗里面,某个统一的形象,某种韵律形式,情节或音调的某个因素,也都经过变形或不变形的方式,重复出现于作品中。”对于电影而言,银幕形象总是一晃而过的,创作者必须通过不断地重复,以使观众维持清晰的条理,来对导演着意表达的内涵和情感保持持久的认识。比如《城南旧事》中看似互不相关的三个平凡故事,其实是对于“离别”的三次反复,这种离别情绪的累积与叠化,在影片末尾构成了一个情绪的高潮,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而陈凯歌的《黄土地》中黄河、黄土地等意象的反复出现,正是要表达自己对黄河、黄土地所象征的民族特性和农民命运的思考。
我们不难发现,度德威特正是通过故事情节和象征意象的“反复”来将诗意与影片主题传递给观众的。首先是具体情节的反复。这里的重复,包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陈述和对显示出相似性的不同事件的陈述。《清洁工汤姆》中男女老少、各色人等挨个登场,却重复着同样的行为——对硕大的垃圾桶视若无睹,将垃圾随手乱扔。轻松的画面包含了对人类文明与恶习的思考。《父与女》中女儿年复一年骑着自行车到岸边等候父亲,并且每一次都与一个与她有强烈反差的路人擦肩而过,这些反复出现的情节对应并强化着“生命周而复始,唯有真爱永恒”的主题。《和尚与飞鱼》的反复情节是和尚一次又一次尝试捉住池中的鱼,一次又一次地铩羽而归,对应着舍与得、执著与放下的哲学命题。
其次是象征意象的反复出现。《父与女》是将季节变换的画面和不停转动的车轮特写贯穿全片,来渲染沧海桑田、光阴荏苒的意境。《红海龟》表现时间流逝、生命轮回并反复出现的意象有:候鸟——飞去飞回,海滩——潮涨潮落,月亮——月缺月圆,昼夜——不断交替,竹林——毁坏与重生,螃蟹——死亡与繁衍等。值得一提的是,该片中出镜率颇高的几只螃蟹看似毫不起眼,却意蕴丰富、引人深思。螃蟹的第一次出现是钻入男主角的裤腿将他从昏迷中叫醒,这个有趣的动作仿佛在告诉观众,这个小岛并非一个充满了可怕和危险的所在。螃蟹作为岛上的“原住民”被作者赋予了沉默的温情,它一会儿目送男主角推竹筏下海,一会儿偷偷爬上竹筏想和男主角一起逃离小岛。其后,螃蟹吃掉死去的小海龟以及被海鸥叼走、螃蟹关于海啸的镜头则显示了大自然的残酷法则。不过,在影片末尾送别儿子的场面中,又一群可爱的小螃蟹出现在海滩上,它们嬉戏玩闹着开始了新的生命旅程。螃蟹的反复出现传达出作者对自然和生命的深深敬畏。
度德威特影片的主题往往是多义的,不同的观众可能会读解出诸如对生命轮回的思考、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对人的孤独的拷问、对两性关系的诠释等思想内涵。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观众对这些主题意蕴的强烈感受很大程度上源于作者对故事情节和审美意象的反复强调。
结语
作为一位受到世界认可的欧洲动画导演,度德威特作品中的线条和笔触都是欧式的,但是他作品中的宁静、含蓄和深远的意境却又透露着东方文化的精髓。在中国动画史上,曾出现过《牧笛》《山水情》这样注重情感表达和诗情画意的诗化结构作品,近些年来,此类作品极少出现在中国观众的视野中。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类影片要传达的,更多的是对某种意念、某种激情、某种哲理或思想的触动与反思,往往要求接受主体具有更高的电影素养和审美追求,市场风险颇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动画创作缺少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审视与观照,在艺术创新上裹足不前,这将阻碍中国民族动画的复兴。
迈克尔·度德威特作品中朴素的审美倾向和诗化的叙事风格,是对当代社会信息过剩和商业电影过度刺激的一种对抗,是对人类向往精神家园和探寻人生意义的一种回应。那些仅仅注重故事性的影片往往只能引起观众短暂的兴奋,度德威特的动画却经得起反复观看与回味。这正是杰出动画作品应该达到的高度。以此而论,度德威特的“诗化叙事”可以作为中国动画创作者们打开创作思路、探索创作路径的一种借鉴。
【注释】
1[美]悉德·菲尔德.电影剧本写作基础[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9.
2[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39.
3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5.
4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6.
5厄尔·迈纳.比较诗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51.
6转引自[苏]多宾.电影艺术诗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4:38.
7[法]奥利维耶·科特.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幕后·手记[M].吉林:吉林美术出版社,2009:229.
8[法]奥利维耶·科特.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幕后·手记[M].吉林:吉林美术出版社,2009:229.
9聂欣如.电影的语言[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340.
10转引自贾磊磊.影像的传播[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25.
11[法]奥利维耶·科特.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幕后·手记[M].吉林:吉林美术出版社,2009:231.
12转引自弗雷德里克·R·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主权1885-1925[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96.
13[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40.
14[苏]杜甫仁科等.论电影剧作[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