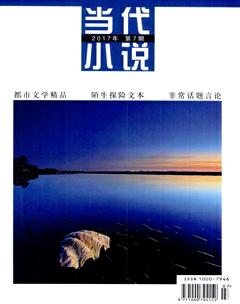苏堤和白堤(短篇小说)
张维肖
“千载兴亡莫浪愁,那个汉家功业亦荒丘……”我带您听的这一段《虞草记》,也许是太涩了一点。您先熟悉熟悉昆味的京腔——在甩不脱的侬语中,您可以听出两个戏班的女苗子正踱上台来。
苏堤和白堤是黄龙戏台最后一批收进的弟子中,并不拔尖儿的两个女娃娃。梨园行,熬得长,成材难,青春饭。除非打小决定一门心儿地往鼻子上涂抹白浆、腮边粘粒老痣向丑角儿婆娘发展,梨园子里没有哪个姑娘不想当个角儿的。
黄龙戏台是余杭乃至江南最古老著名的台子。
这地本是昆曲多些,罕见专门的京剧班子,熬到皇帝被推倒,北方四大名旦盛兴,黄龙戏台才在最末一批弟子中捡起被淡忘的那俩京戏苗儿。苏堤和白堤赶了好时候,在她们十五岁的时候,黄龙戏台终于同意她们挂牌上台,说是要排出梅兰芳的《一缕麻》。
那么問题来了,《一缕麻》,可只能给一个角儿啊。
苏堤和白堤本就都不拔尖才被双双当京剧角儿教习,虽说是愈发热了后俩丫头都使了吃奶的劲儿弥补,但还是脱不掉那娘胎的毛病。论模样,带了妆的白堤一等一的漂亮,汪润的杏眼,横波的眉尖,六角的脸盘,流水的身段,随手拿一个兰花指恰就能捏出迷人的香气,苏堤呢,有点地包天,盗汗吃妆;可这论腔调,苏堤又是当仁不让的珠圆玉润,甩个高腔,座儿们的掌声都能没了最后的唱词,不疾不徐,回味和清河坊的茶香一样悠长,相比下的白堤,气短、腔浮,拿不出手。
一座八方台,三面玲珑座。结果这《一缕麻》,座儿还是捧了,而且捧得它一炮而红!也不知是谁的妙主意,竟让这头五天的戏由白堤出扮相,苏堤配腔调配出双簧来填座儿的胃口。说起那会儿,师父把清早练功两人叫来宣知台主的意思,白堤本也对这个安排无可大非议,说到底苏堤更委屈些,而苏堤顺着细细的眼,瞧了瞧白堤,瞧了瞧师父,又瞧了瞧白堤。
师父摁一只手在苏堤的肩膀上:“过了头五,立马轮着你出扮相,白丫头唱!”
苏堤吊起了嘴角勉强笑:“噢,嗨。”
到了第六天,恐怖的噩梦降临了,前五日她俩完美的结合让黄龙戏台的第一出京剧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座儿。可现下,苏堤台前一亮相,白堤幕后一开口,座儿们本向前倾的坐姿瞬间明显地松懈了些。演到一半,座儿已是疲懒地靠在了椅子背上。再过一晌,任苏堤认真卖力地躺在榻上捻起一缕麻作出痛苦的情状,还是听着背后白堤的唱腔越来越不安,那难过的神色真切又不对头——出戏!底下的座儿骚动得越来越大。
终于,一个小高潮,苏堤按照自己的吊腔节奏端的好表情,咿咿呀呀地晃着脑,身后的通声口却早绝了声响,只有丝竹!只有丝竹!
双簧,断了!
苏堤哪还敢晃!愣了。
“嘎什么东西的!”
“怎么不瞧见前几日的角儿?我还是专又带着家母来捧的!”
“这六儿,黄龙哄我呢!退座!退座!”
可怜的苏堤摊上了最坏的局面:她的面儿凑了白堤的声儿,简直是灾难!彻骨的尴尬灭顶袭来。
或许挪到五天前演也不会显得这么糟,可是现在……
苏堤几乎是挣扎着“唱”完了最后一段词,定定地立在台中央,看着底下唏嘘喝倒彩的人和空了东一片西一片的座儿,瞪出来的眼泪都是汪着血丝的。或许,这就是师父故意想让她看清的?抑或,白堤唱成这般是故意的!这是她第一次登台!她才十六岁,或许这是她最重要的机会!可现在呢,她的脸都丢光了!她好恨、她好恨,她好恨!
谢了幕转到后台,师父早叹息着步入跨院儿不见了人,而白堤就不言不语地靠在一个特制的通声口旁,端着一杯香片,微驼着背透过小口在看外面散戏的场。
苏堤扭开了戏服下巴颏的第一颗盘扣,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妆粉气。白堤偷觑被抓个现行吓了一跳,冲她微笑了一笑,亏欠地,带怯地。苏堤劈手夺过那杯香片,咕咚咕咚灌下一口,烫茶呛得她一阵咳嗽。
“该给师父说的,”苏堤低头看着那杯香片,“你该给师父说的!轮到我根本……根本就,根本就不用给我配唱!”
白堤别过头:“对唔住。”
“我根本不用你给我配唱!”苏堤压低了声音,死死地盯住茶水里白堤漂亮的左脸的倒影。
“对唔住。”左脸稍稍转了回来。
“明天,以后,也都不用替我唱!我也不想替你唱!”苏堤的手抽了力气,慢慢倾斜,胳膊由左到右划出水平线,把瓷杯里还盛着的香片缓缓倒在了两人之间的地上,滚烫带白气的水印横在两人之间仿佛楚河汉界,溅到两人裙摆,割开两人的交情。
“对唔住,我想也是的。”白堤被烫得缩脚,许久,才提起正眼瞧着苏堤慢慢吐出一口气,“我不替你唱,也不要你替我唱了。”
此后苏堤再也不理白堤了,白堤也在躲着苏堤。
泼皮些的苏堤亮出话来:没有她的腔,量她白堤是神妃仙子也甭想在台上撑过一炷香!
敦厚些的白堤听后笑笑:余杭的台又不是无盐岛。
这算是宣了战了!
她俩本就话少,以前是暗里较劲,现在,所有人都见不到黄龙戏台上有京剧《一缕麻》,也都见不到她俩同时出现了。师父想再劝苏堤出声白堤出面,谁知两人齐齐不肯。
偏又是这时候,一位自称亚美利加外交大员的找上了黄龙戏台,称看过《一缕麻》首演告捷,故诚邀班子漂洋过海去亚美利加,为他们演出,旅费自然是外交馆付,包他们红遍东海岸。
这个可是大喜事!除了伶界新宠大王梅兰芳,还没有谁能再出了海演戏!
只是,人家亚美利加不兴双簧,大员只带一名演员走。无论去了哪个,以后的光景都是可想而知的好。当个角儿刚挂牌就能混到这般,何等光荣!
台主给这白发碧眼的洋鬼唬的!
整个班子给这白发碧眼的洋鬼唬的!
苏堤白堤给这白发碧眼的洋鬼唬的!
苏堤开始格外关注自己的那脸那身子,她清早不吊嗓了,摸着黑好几趟拍开胡庆余堂的门儿,又是求瘦身息肌的方子,又是每晚偷偷浸在廉价的石膏汤里,每次上妆,都得重整他好几遍。更有甚者,她裁了一缕羔羊皮碾成绳子,带住她稍稍“地包天”的下排牙,绑在后脑勺,每天躲在没人的地方,一下一下抬头,以求能拽得它靠后些。endprint
白堤呢,为了多个吊嗓的空儿,起得更早了,每日每日地缩缩在墙角对着竹丛,咿咿咿呀呀呀。两个眼窝子和吸了大烟的人一样青黑,妙手再捏兰花指就和被啃干净的糟凤爪一样,让人瞧了都心悸。奈何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白堤排演时不是哑了嗓子就是晕了过去,忙喊了郎中来瞧,也只是叫人将冰糖或罗汉往她口里塞。
三两月下来,人们都说,苏堤盘靓了很多,白堤嗓亮了一点。亚美利加的那位大员总来探排练的班,更夸奖苏堤。也对,男人哪有不爱俏的。如今他眼中,白堤是不如首演时候的俊了,而苏堤,倒是又积极又招摇。曲目也定下来了,这令人不快的《一缕麻》就让它见鬼去罢,黄龙戏台决定排《虞草记》,那是园里教习苏堤和白堤的第一出戏,也是个苦女丧郎的悲剧,只消出一个青衣角儿。
说到底,这京剧唱、念、做、打,唱字还是当头。定了厚厚的妆,洋鬼子哪看得见你们扮相的差别?而这亚美利加也是有歌剧的呀,一亮嗓,饶他听不懂词,还听不出你吊花腔么!亚美利加大员曾请苏堤白堤一起去别家戏馆看过戏,又看过上海滩那块儿传过来的电影,他总是和苏堤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的。后来,大员又送鲜花到戏台,给白堤的是白玫瑰,送苏堤的是红玫瑰。这也就算了,花束里却还有洋文的字条。虽说苏堤看不懂,杭州城也没谁能看懂,但所有人都看出来,苏堤最终渐占了上风。
话说这黄龙戏台后是班子们的住所,茅房和浴房在一起组成净堂,挺大的。
再后来,班子里总有人说,净堂闹鬼呢。三更里总有鬼喘气儿和磨牙的声音。而最近,班子几个闲里人——小生吴山养的金丝雀儿、台主太太的黄鹂、弁老太的鹦哥接二连三丢了,找遍园子不见最后都在净堂的马桶里看见几根毛。人道可能是招了鬼了,也可能是招了夜猫了。
白堤苏堤各自的小厢房都很靠近净堂。苏堤胆子素大,照样觉觉到天明。
入了夏,天气热了起来,黄龙当初与亚美利加大员约定的最后选角的日子就在明天了。
不知是晚饭后贪喝了几碗绿豆水还是心绪紧张的苏堤起夜解手,说起也怪,最近总不再见大员来探班,好些日子了,差人去提醒大员,亚美利加公馆也只白了差人说是大员忙,记着了。纵平白受了好多“恭喜”,看不见大员最后关头的态度,苏堤还是不能心安。
路过了白堤的厢房,里面还有勤奋的豆灯燃着。苏堤不免堵得撇嘴,“充什么能的!”心里堵的女人永远会对添堵的人产生无法抗拒的好奇,苏堤猫着腰来到白堤的西窗下,小心地抬起手臂,又小心地伸出带有长长指甲的小拇指向那层薄薄的窗户纸悄悄捅去。透过去看,什么都没有,人都不在。
苏堤没趣,闷闷地走进净堂随便掀了一个门帘,闪身进去,一屁股坐在木头马桶上。夏日上茅房,不想在里头被熏死,就要讲究速战速决。
这时,她听见了——听见了闹鬼的声音!
是了,旁边的茅房隔间!霍霍,霍霍,不仅像磨牙、不仅像磨牙呢——还像磨着刀!呼——哧——呼——哧……这又是什么,鬼的喘息吗?
苏堤溺尿到一半儿,惊得都不敢继续了,她哆嗦着手捉住另一只手,嘴里念叨着鬼神莫怪鬼神莫怪定神。再一会儿,她觉着这鬼……喘得蹊跷。哪有鬼喘气的时候,仿佛凫水的人换气呢?
苏堤大着胆子拨开她一点点旁边的丝绒门帘:晦暗的月光下,披头散发的人正襟危坐在木头马桶上双手捧着些什么作弄,裤子没脱,腮鼓得大而实,像是憋着气,喉咙里有蚊吟般的“呜……嗯”。
是白堤!
苏堤忙把帘子放了下来,两只手按住狂跳的心脏。白堤何时这样吓人了!
白堤根本没发觉她,隔壁诡秘的声响源源不断地刺挠着苏堤的耳膜。苏堤鼓足了劲,再次横拨开一点丝绒门帘往那头瞧,夏日里马桶的袭人浊气直往她保养良久的玉面上扑过来。她皱紧了眉头,赶紧缩了手指横堵在鼻孔下,下牙扯紧了上唇不敢出声惊了里面亦人亦鬼的白堤。
白堤未曾发觉隔壁的苏堤,苏堤看清了她是在一下一下地转着捣药杵,聚精会神地碾着钵中的东西,产生了那霍霍的响儿。
苏堤又把帘子掀得厉害了点,马桶的恶臭令她强遏住呼吸。粪便,血腥,腐坏的饭菜,沤烂的生命!
而白堤恰就在恣意欢快地享受利用这恶臭一样,她深深地吸进一口气,然后将这口气死死锁在口鼻,憋住——同时碾呀转呀手中的捣药杵——直到把脸憋硬,眼珠子凸凸着,喉咙里发出那蚊吟般的“呜……嗯”渐渐强了起来,她才长长地舒松了下巴,放那口恶气出来。
苏堤一阵反胃,黑暗中看不清白堤的表情——该是怎样难过狠绝!以臭气逼着练气量……原来白堤用这手段练私功!不知道是不是就在鲍鱼之肆不闻其臭,白堤甚至吸气的时候越来越凑近了马桶!
被当头一记闷棍打得苏堤不知作何反应才好,五官手脚心里口里都乱了套了。眼看着白堤还要埋到粪土里吗!
在这个封闭的又柔软的,恶心的又清静的,挺大的又拥挤的一方空间里:白堤就这样重复着她的动作,忘了时间;苏堤就看她重复,忘了时间。
大概二更了,白堤才端着细细磨好的药钵缓缓从马桶上起身,撩起丝绒门帘,小步,小步向自己的厢房走去。苏堤方如梦初醒,皱眉揉了揉坐麻的腿脚,撒了一泡憋了许久的紧张的尿。她拽着门帘一点点尝试着站起来。
出了净堂,白堤的屋里还是亮着,苏堤不死心,犹豫了一下,还是悄悄来到西窗下,正好透过一个时辰前指甲戳的小洞朝里看。
这一看!看了个清楚,那如豆的灯光足够满足早已适应黑暗窥探的眼!白堤临西窗的桌台上的,是近日班子消失的鸟雀们!没了毛的,紫红紫红。每个鸟雀身首异处,脖子一小段早被白堤仔细整齐切了下来,带着凝固的血,扔进钵里。估计同被扔进钵里的还有那旁边凌乱散放的滑石、罗汉、薄荷、枇杷……
苏堤早就被镇得失去了大叫的能力,白堤好像也惫懒收拾这些东西,倒开始一丝不挂地化起了妆。
拍彩,拍红,定散粉,掃三庭,扫红,元宝嘴,画眉眼,勒头带,梳头,贴片子,戴大柳,线帘子,戴头面,着戏装。早扮三光,晚扮三慌,白堤比苏堤更懂行。endprint
足足到了三更,白堤才完工。
苏堤呢,看痴了!忘了走,忘了叫,忘了动,天都开始蒙蒙亮,前堂已经有了其他伶人练功和师父台主张罗摆台的动静,她终于看懂了自己的黯淡,白堤就是白堤,定了妆明艳得不可方物的白堤。
“苏堤啊……”白堤理着戏服的袖口,端着碎步到窗前。窗外的苏堤猛一哆嗦,但是白堤垂着眼皮瞧都没瞧她,语气仿佛梦呓,又好似自言自语:“苏堤妹妹,你我打小同门,咱俩谁红不是红呢?为何,这次非要和我过不去呢?”言罢轻轻叹了一口气,拿出一个小银勺轻轻地刮着药钵钵。
“我也知道,原也不是你和我过不去,只是……”白堤刮一下。
“角儿就是角儿,角儿只有一个。”白堤刮两下,将小勺刮下的暗红浆糊空到一粗瓷碗里,再启开一只瓷瓮,里面也是一样的糊。
“你都不知道,为了压过你一个呀,我有多辛苦。”白堤把瓮中的糊也同样小心翼翼地全部刮在粗瓷碗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嚓!”
“啊——”
一只精巧的匕首刺透了窗纸木棂,精准地刺破了苏堤包裹着喉咙的皮。
苏堤惊恐万状地后退,摔下厢房的台阶仰倒在地,她尖叫着,还麻着的左腿或吓软了的右腿令她根本无法爬起来。房门吱呀开了,白堤右手端着那粗瓷碗施施然走了出来,左手中是那把匕首,上面还流着苏堤的血,像融化的鸽子红宝石。
“这是我好不容易调的百凤散呢……罗汉一枚,薄荷五钱,滑石半两,吴山的金丝雀儿,台嬷的黄鹂,弁老儿的鹦哥……它们的嗓子呀……以形补形啊,都在里面呢……”白堤笑了,“苏堤妹妹,你要尝尝么?”
“你、你疯了!”苏堤听得一阵作呕,脖子的痛痒却让她做不出吐的动作。
“你真的不要尝尝吗?你喝了,唱得准更好听。”白堤把嘴凑到瓷碗边,一仰脖子灌了一口,再抬手拭了一下嘴角,身段漂亮得像在演贵妃醉酒的选段,随后,她露出一个微笑,上排贝齿都染成了丑陋的暗红色,“这还不够呢,挖不出你的嗓子来配,就这些杂毛怎能称得上‘百凤?”
白堤微笑着在苏堤面前蹲下,一只手平端着粗瓷碗,一只手抵在苏堤的喉咙。
“你疯了!你疯了!”刀子渐渐逼近,苏堤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挣脱了白堤,爬起来,几个踉跄,向前堂跌跌撞撞奔去。
“白堤疯了!白堤疯了!”苏堤跑过连廊,疼得哭。
“白堤疯了!白堤疯了!”苏堤路过跨院,哭着笑,“哈,哈哈哈……”
“哈哈哈!角儿是我的……你们知道吗!角儿是我的!大员来了没有?白堤她疯了她……”苏堤又哭又笑地扑进了前堂。
“啪——”两个民国衙门条子模样的人手脚利索地抓住了她,一记巡棒扇到她背上,苏堤立仆。头被摁在地上,动弹不得。
“你们是哪的瘪三!放开我!今天是我的大日子!我是要去亚美利加的角儿。”苏堤被摁得恼火,摁得莫名其妙,而这莫名其妙在此刻就凑成了她的冲天怒火。
“我们是奉命前来纠察缉拿苏共国际间谍找的下线,你就是那个要赴美的细作吧,跟我们走一趟吧,共匪。”
“放了我!我不知道什么苏共!我要等亚美利加的大员,我没有问题,我是要去上台子!”苏堤拼命地扭动身体想要挣开桎梏,挣扎间才看见黄龙戏台的前堂满满的都是条子和衙狗,班子里其他人都已经被五花大绑起来。
亚美利加的大员呢!今天是约好的日子!他怎么不在,他怎么能不在!她还要亲口听他说要带她去亚美利加,去上台子!
“臭娘们,哪有什么大员,什么台子,贱戏子再装,再装就撕了你衣裳。”
什么纠察?什么下线?什么细作?她不过就是个戏子!哪知道什么苏共国际,哪知道什么共匪!黄龙出啥事了?出啥事与她何干!今天是她的大日子:白堤疯了!白堤完了!角儿是她的,角儿是她的!
可现在呢,他说大员是假的?他们说亚美利加的台子要没了?
不可能的!她的角儿!
“你们找的到底是谁!”苏堤被反剪的双手反扯住攫取她胳膊的官府条子,十个长长的指甲几乎要撕碎条子的的确良衣裳,“谁!”
“这就得看哪个是角儿了,我们当差的也是听上头吩咐,逮那个和共匪勾结的细作!”
“角儿!角儿当然是我!……不、不是我,大哥你听俺白了……我们还没选呢——大员选了的话也是——也是——”
“哟,亚美利加大员?哈哈哈——”条子和衙狗一起冷笑着彼此指点,“那你还是胡汉民了!你是孙大科!我还是汪精卫了!”
“臭娘们,留着你这细皮嫩肉的给司令‘白去吧!走!带走!”
“千载兴亡莫浪愁……”
《虞草记》!
苏堤拼死了抬头。
是白堤。
是那个疯子!
疯子白堤!为什么!她不能演,她不能!她是疯了的!
“……功业亦荒丘空余原上虞姬草舞尽春风未肯休……”
当然是白堤,果然是白堤。
“滚啊!疯子!滚!”苏堤目眦尽裂,冲着那出戏的方向叫喊。
缓缓步入前堂,又缓缓登上戏台,再缓缓定在台中央亮相的,是定了妆的白堤,着云裙的白堤,抛水袖的白堤,捏兰花的白堤,翻碎步的白堤,匀润腔的白堤,甩高腔的白堤,念白段的白堤,款深福的白堤……一个一个,一字一句,都是白堤,都是白堤。好听的白堤,好看的白堤!
竟然是那样好的腔调!竟然是那样好的身段!
竟然有那样好的戏子,竟然有那样好的戏!
当真担得起“风华倾城”四个字!
台主盯着白堤的牙惊惧,师父不愿理会地阖目,四下戏子被制住的脖子竖起耳朵来使劲地听,没被制住脖子的拿眼睛可劲地瞧着。头脸被按在地上的苏堤,拼死了劲,用肩膀支起来脑袋,抬头又听又看,撕裂了下巴,剥开了嗓子,嘴张大。
刚刚凝固的脖子的皮,又在地板上磨出了血。
……
……
“……衰草不青不堪记,时光哥,来也复去……”
黄龙戏台就走了一个人,以后恢复了平靜,开始只排昆曲,关于他们曾经有过京剧角儿这档子事,谁都不再提了。
官差放开了苏堤。
责任编辑:王方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