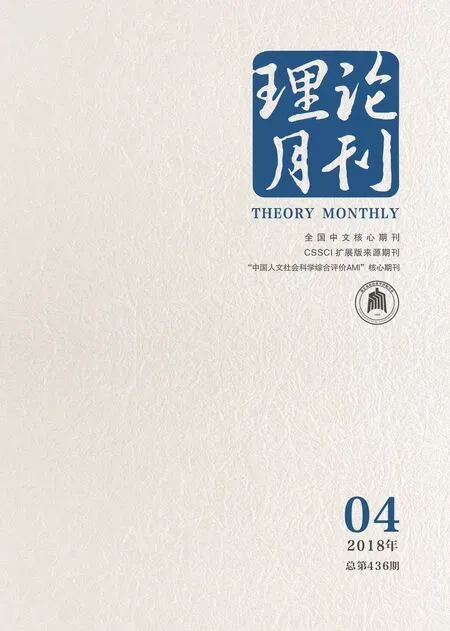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现代启示
——以李陈玉的息讼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 朱声敏
(1.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2.广西财经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3)
在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习近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解读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了“礼法合治,德主刑辅”这一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精髓要旨。他指出,这些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作为“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乐礼善学、尚中贵和”等传统思想的集中体现,“无讼”是古代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而息讼则是官员们实现这一理想境界的重要策略。笔者拟以明末李陈玉的《退思堂集》为基本素材,考察其在浙江嘉善知县任上息讼活动的具体实践,深入分析古代地方官员息讼的基本方式及其背后原因,以期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特有的司法文化基因和价值理念,发掘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现代意义。
一、李陈玉及其《退思堂集》
李陈玉,字石守,号谦庵,江西吉水人,崇祯甲戌进士,官至南明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崇祯七年至十三年,李陈玉任浙江嘉善知县,颇有建树,史称其“知嘉善县,为民兴利除弊,多异政”[1](p358)。时值明末,天灾频仍,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社会秩序混乱,官方的控制力严重削弱。尽管如此,李陈玉仍然赴任,勇担责任。其自律甚严,每日退堂,如无特殊情由,即将所思所想记录于册,以供自省,后将这些文章结集刊刻,名曰《退思堂集》。
众所周知,明代实行中央、布政使司、府、州县三级行政管理模式,州县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时有“天下治权始乎州县”之说。州县长官,责任重大,一人之贤愚,关系千万百姓之休戚,故学界对州县官的研究经久不衰,成果丰富。然而可惜的是,目前学界对于《退思堂集》的研究非常有限①详见范金民:《嘉善县事:明末知县李陈玉的县政实践》,《江海学刊》2016年第1期。。而在这本笔记之中,李陈玉述及的讼案、收集的判牍共数百例(份),有的事件记载详尽,有些事件虽然陈述简单,甚至仅寥寥数语,尽管如此,也足以令人管中窥豹,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司法实践运作和社会经济状况留下了珍贵的材料。所以,研究《退思堂集》和李陈玉的治政实践,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古代地方社会实况及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特色,可以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二、李陈玉的息讼实践
中国古代诸子百家,都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和谐”思想不仅是“儒家的最高价值标准”,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2](p210)。儒家、道家都对人间无争无讼、和睦相处的社会理想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孔子曰:“听讼,吾尤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此短促而有力的寥寥数语成为中国古代“无讼”理想的权威描述。先贤的哲学阐发以及历代政府有意识地利用,以一种神秘、恐怖的气氛笼罩之,使得“无讼”意识逐渐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的基本文化观念之一。英国汉学泰斗李约瑟认为,“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3](p338)。“无讼”即为这一理想在司法领域的经典抽象。
然而,几千年的历史证明,“无讼”始终是一种理想,在农业文化背景下的现实生活中,无一日无争,无一日无讼。根据日本学者夫马进的看法,中国至少在宋代以后,诉讼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他还据此提出了中国古代“诉讼社会”[4](p1)的概念。既然讼争无可避免,为了稳定统治秩序、尽力达成儒家“大同”社会理想,“息讼”便成为官员们为实现“无讼”而采取的策略。总结起来,李陈玉的息讼之道具体有如下特征:
(一)限制或拒绝接受词讼
为人父母,总希望子女友爱团结、和睦融洽。在家国同构的古代,为民父母的地方官员,自然也希望治下百姓谨守规矩,清净本分。他们往往将民间词讼视为“人心不古”的表现,视兴讼之人为刁顽不灵、好事斗狠之徒,倍加反感,他们往往下车伊始便会发出告示,告诫百姓安守本分,休要轻易兴讼。如“圣人”王守仁在江西时就发布《告谕》曰:“庐陵文献之地,而以健讼称,甚为吾民足羞之……县中父老谨厚知礼法者,其以吾言归告子弟,务在息争兴让。”[5](p375-376)若百姓意欲提起诉讼,地方官员往往会对其加以种种限制或干脆拒绝受理。
官员们限制诉讼,一个重要原因是讼案多“诈伪不实”。李陈玉在笔记中透露,其初到嘉善,每日收到词牒近百份,后来这个数量增加到三百份[6](p34)。而海瑞的说法简直耸人听闻,其云:“江南民风刁伪,每放告日,状动以三四千计。”[7](p237)可想而知,面对如此众多的词牒,官员们很难一一细阅、斟酌,其时间、精力也不允许一一处理完毕,他们只能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挑选其中比较紧要的进行审理。如上述三四千份状词中,海瑞“所准行二十分中之一而已”[7](p237)。于是,投牒之人便千方百计“打”动官员,在词牒中虚张声势、添油加醋便成了不得已的策略,这种情况甚为官员所厌恶。李陈玉刚到嘉善不久,考察民情,便认识到“禾俗赖诈成风,一夫病死,奇货可居;一纸冤情,富家立破。甚而无赖之辈,服溷沉渊,雉经自刎。子利父死,兄戕弟生。无干势棍认为家仆者,更有认为姻亲子女者。”[6](p12-13)在指出上述诸多赖诈现象的同时,他也发布文告,禁止滥兴词讼,文告曰:“本县劝讼,非不谆谆,而民间扰扰,比前较甚。……中间诈伪不实,岂但可已,兼亦可恨。”他在文告中详细列举了“诈伪”的诸多具体表现,并跟民众约法,今后“告状不实者反坐,续状大多者究讼师,不诉而告者不勾摄原告。排邻查实非邻,逐一加责。总甲报事不实,枷号示众。乞照乞示,一概不准。请销者,坐以诬告之罪。告免前官赎银者,责原差”[6](p38-39)。
设置“放告日”来限制诉讼,这是明代官员普遍的做法。早在汉代,已经有“务限”之说[8](p349),即官府对于户婚田土等民间细故限定时间进行受理。该办法既有防止百姓因诉讼而耽误农时的考虑,也是“息讼”价值取向使然。到了明代,尽管朝廷没有统一规定“放告日”(或称“听诉日”),但地方官员都明确规定受理诉讼的时间,多为每月三日[9](p125)。尽管明朝有“告状不受理”之律,规范官员受理案件的行为,其中“斗殴、婚姻、田宅等事不受理者,各减犯人罪二等,并罪止杖八十”[10](p175),然考诸史册,笔者未见官员因不受理此类案件而遭受惩处的记载。或许,官方律文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差距本身就体现了官方的态度:即默认官员在斗殴、婚姻、田宅等方面享有决定是否受理案件的权力。当然,对于如杀伤、奸淫、抢盗等重大案件,当事人可以随时提起,官员随时受理。
在《退思堂集》中,笔者找不到李陈玉受理讼案的具体日期,但文集中有“每遇放期,动盈百纸”[6](p31)“(沈鹤)父死兄丧,妻乞于市。每遇告期,则鹤妻仍系于家”[6](p58)等表述,我们可以推测,其受理讼案也是指定了具体日期的。
(二)感化教育
将词讼拒之门外或对其数量加以限制,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策略。倘若官员将所有纠纷都拒之门外,必将加深涉案各方的矛盾,影响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在受理诉讼之时,对涉案各方进行感化教育才是一种更具效果的息讼方式。在明代,别说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官员深谙此道,就连马上打天下的太祖皇帝都了然于心。明初,太平府有两兄弟相互攻讦,地方官受理后,将案件提交刑部。太祖得知后,曰:“兄弟骨肉至亲,岂有讦告之理?此因一时愚昧,或私妻子,争长竞短,怒气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至泯灭,姑系之狱,待其忿息,善心复萌,必将自悔。”[11](p81)次日,兄弟二人果然哀求改过,太祖遂释之,让兄弟和好如初。到了李陈玉这里,其经常对诉讼各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父以慈为本,劝子以孝为先,“小事则教诲解散,大事则轻重处分,使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而好事者渐稀矣”[12](p15)。
经济算账是地方官员劝民息讼的常见策略。古代涉讼,两造动辄被拘系、被刑讯。为了使自己得到好一点的待遇,两造往往会遂官吏之愿,任其上下其手、大肆榨取。著名的《忍讼歌》就告诫人们:“世宜忍耐莫经官,人也安然己也安然。听人挑唆到衙门,告也要钱诉也要钱……听人诉讼官司缠,田也卖完屋也卖完。”[13](p229)有官员指出:“民间词讼,情弊万端,官府问理则人被久禁,吏典受赃,颠倒是非,多有破家荡产者。”[14](p286)所以,诉讼给当事人带来的经济灾难到了令人谈虎色变的程度。经济灾难也就成为地方官员堵塞百姓诉讼之路的常用伎俩。如李陈玉曾在《息讼示》中提及“本县严肃极意爱民,然安知无照管不到处!尔辈之屈,抑反甚乎!尔乡有田一十五亩便充粮长,假令结讼一岁,此十五亩者,何异浇雪?馁妻子而饱他人,他人又不任恩,非计之得也!况并无一十五亩者乎!若其家富,一年一讼,不及十年,田宅必空。”[6](p32)审判实践中,有两家相争,诉讼近十年,到了李陈玉面前,其劝曰:“以十年讼费买田,何止所争数亩?以十年精神作家,何必开口求人?两父相争已登鬼录,又遗两子修理旧时葛藤,所谓继志述事如此,政不须也。”[15](p4)此案中,面对“必求昭雪事”,知县不去探究讼争的原因,更不去思考如何判决以求得实体上的公正,代之以苦口婆心的教育感化,让两造自愿息讼。
俗云“清官难断家务事”,既因家人同居屋檐下,朝夕相处,事端千头万绪,难以理清,也因今日断其旧事,恐不能彻底平息仇怨,反为他日祸事埋下根源。故地方官员处理家庭、家族内部的讼争往往慎之又慎。倘若家庭、家族内部有词讼发生,官员们往往会将实体问题撇在一边,积极教化,以情感人,以理讽人,既使其息讼,维持家族的和谐。李陈玉堪称此行中的“高手”。他“到任数月,察视民情,一意教化,躬先德行。凡父子兄弟相讼者,必为导以天性,嘘以至诚。令其悔泣而后已”[12](p16)。当时另一名吏祁彪佳在这方面也有上佳表现。蒲阳生员陈一翰先娶妻林氏,生二子公奭、公尚,继妻丘氏无所出。丘氏随嫁之婢林氏生一子,名咬奇。陈一翰故去,母徐氏尚在。丘氏、林氏与公奭、公尚矛盾日趋尖锐,丘氏遂兴讼。时任推官的祁彪佳对一干人等进行了一番劝解,“为媳者而奉其亲姑,为子者而事其继母,为兄者而育其幼弟,岂不一堂顺聚哉?丘氏乃借咬奇以起釁,何为乎?背姑则为不孝,告子则为不慈”。祁彪佳还让族众替丘氏等处分了家产,继而再教育之,曰:“继母丘氏有赡,妾林氏有赡,使老依长孙,另分咬奇以己赀婚娶,他产三子均而得焉。可谓经理明,而争端杜矣,徐氏风烛之年亦可以自慰矣。此后丘氏不得昵妾子以仇前子,公奭等不得以异母而并疏孤弟,以守亲父之业,以安祖母之心,天伦骨肉不亦两无憾哉?”[16](p12-13)此案中,继母与继子起衅,家人反目,地方官员不是寻根究底从而作出公正的判决,而是本着“以德化人”之心,耐心劝谕,终使众人感悟“天伦骨肉”之情,心悦诚服地平息了纷争。
正因为“无讼”是朝廷和地方官员追求的境界,责任心强的官员往往会自认为百姓兴讼系因自己教化不行、教化不当所致。而一旦经过教化之后,两造“幡然悔悟”,自愿息讼,官员就会认为自己教化业已然有效,两造已诚心向善,不会再胡作非为、架词涉讼。于是官员往往会网开一面,对本该刑罚之人从轻发落。例如,明律确立了“诬告反坐”的原则,明律规定“强奸者,绞;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10](p212)。据此,若诬告强奸,罪应绞或流。明末广州府的吴姓一族有吴良和吴仲高,二人素有芥蒂。吴良有子吴达,吴达有养女亚丙。一日,吴仲高之子吴举贤调戏了亚丙,吴良父子借机捏禀巡司,张皇其事。吴仲高反诉吴达捏奸摆陷。地方官员奉宪拘审,经耐心教育,令双方都“哀吁悔息”。最后地方官员虑及双方“原无次骨不解之仇,一时相激”且已经悔悟,仅仅以“轻率渎宪”杖责而已,而没有深究[17](p226)。
(三)推行教化,移风易俗
明代是一个很重视“教化”的朝代。明初,太祖朱元璋即发布了《正礼仪风俗诏》,诏书痛陈当时民风之劣,“道理未臻,民不见化,市井乡间,尚然元俗”[18](p1258),由此宣告了官方自上而下的教化活动在全国展开。此后,“治国以教化为先”[19](p1681)成为大明的基本方针政策。明代中期,时人赞曰:“国朝文教四被,风俗还淳,百余年来民熙如也。”[20](p482)然而,明代后期,伴随着商业发展、市镇兴起,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官僚腐败、宦官作乱,政治黑暗。于是,逐利之风盛行,奢靡之气弥漫,整个社会陷入普遍的道德危机。这也正是词讼频繁的重要原因。于是,不少知识分子纷纷奋起有为,力倡教化,拯救世风。就连小说家冯梦龙都在其小说序言中开宗明义其教化的创作目的,曰:“夫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21](p1)
李陈玉也认识到“夫无讼者,尚教化”[6](p64)。他还说:“上讼法堂,听断治于已然之后。乡约化导,治于未然之先。……使民知兴起节义而乐行善也。”[12](p16)在他看来,官员在裁断讼争时要进行周密的考虑,不但考量双方直接的利害关系,还扩而广之到讼争之外的广泛社会关系,诲人不倦,要取得社会教化意义。
古云“教民之要,不外劝、惩二端”[22](p304)。高明的官员,善于在劝中惩,在惩中劝。李陈玉即是如此,其借判案之机,积极推行教化,导民向善。他在给上司的述职报告中提到自己“职任数月,察视民情,一意教化,躬先德行。凡父子兄弟相讼者,必为导以天性,嘘以至诚。令其悔泣而后已”[12](p19-20)。比如,两户人家因数亩田地讼争,两家父亲去世之后,两位儿子还是互不相让,让讼争延绵了十年之久。李陈玉的日记中并未载明其如何判断此案,仅记录了其批词。词曰:“以十年讼费买田,何止所争数亩?以十年精神作家,何必开口求人?两父相争已登鬼录,又遗两子修理旧时葛藤,所谓继志述事如此,政不须也。”[23](p4)其以经济核算的方式,讽刺了两家相争十年的愚蠢,以“中立”的态度劝人息讼。又如,李陈玉审理了父子兄弟为娼优争风吃醋一案,借机下令逐娼优以防淫盗,并公告全县:“移风易俗,长吏之责也。……驱娼颇严,亦为民间除父兄之忧,清争夺之源。……未至歌舞之声盈于狱讼也。”[12](p23)这则公告不但陈述利害,还明显带有宗法伦理的痕迹。
再如一则赌博案,李陈玉批词曰:“犯者不赦,则效尤者稀。为之导以生业,谕以务实,拘其父兄而晓之,株其朋党以戒之。”[12](p22)一件嫁祸于人的案件,李陈玉的批词曰:“此中民情甚痴,只谓本县可骗,岂知斧凿有痕,缝补有迹,狡兔虽狡,人正从狡处得之。”[23](p39)一件匿名告人案件,李陈玉的批词曰:“此地不逞之民,匿名暗揭,以为日用饮食。风俗薄恶,习与性成。然究竟败露。即不败露,亦未必遂能害人。凡天下之至奸至诡者,天下之至蠢至拙人也。不容无惩以创魑魅。”[23](p64)上述批词,知县大人将案件扩而广之,苦口婆心地对民众进行开导教育,其审判的道德教化色彩甚为浓烈。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当事人,让当事人道德愧疚的同时,伸张正义,教育民众。
移风易俗,自当除恶扬善,激浊扬清。李陈玉访知“此地不逞之民,匿名暗揭,以为日用饮食。风俗薄恶,习与性成。然究竟败露。即不败露,亦未必遂能害人。凡天下之至奸至诡者,天下之至蠢至拙人也,不容无惩以创魑魅”。于是他命令众衙役:“一干人犯,三日内即行差的当衙役拘齐,连招解报。”[23](p61)很坚决地铲除地方恶势力,为地方培养良好风气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四)严格控制吏胥
明代州县政府,除州县官和少数佐贰、首领官之外,便是大批的吏胥,这种组织结构决定了州县官在司法过程中不得不依靠吏胥。然而吏胥因为在政治上升迁之途已被堵死,故往往“破罐破摔”,营私舞弊、借案生财。明初开科取士,朱元璋即“以吏员心术已坏,不许入试”[24](p3367)。有明一代,吏胥“多不畏法,惟图贿赂,颠倒是非,出入罪名”[25](p3817)。吏胥欺公卖法、借案生财,衙门已然成为罪恶的渊薮,这严重影响了政府权威,且既不利于旧案的解决,也容易滋生新案。李陈玉越来越认识到“令事之难,以簿书繁多而难稽也,吏胥狡诡而难察也,豪猾梗结而难治也,佐属驽劣而难驭也”[26](p20)。所以,他知道要实现政清民和,达到息讼的目标,必须对吏胥实行有效的控制,防止其上下其手、为非作歹。
当时的嘉善,吏胥众多。单说衙役,“有一役而数人共者,有一人而经数房者,有已革而改名换姓溷入者,有作恶谄天幸未败露尤然在役者”[6](p40)。“役色之冗,莫如嘉邑。一皂也而分河分徭,一捕也而名应名盗,有健步又有长差。……前官已革而后复入,往事已惩而后恶又作,一人常兼数役,一役常容数人”[6](p43)。所以,要加强对吏胥的控制,其一,就要裁撤衙役。他先是颁发公告,要求各衙役填报考核单,单上写明自己籍贯、年纪、外貌,进入衙门的年月以及工作履历,甚至还要交代清楚平时与哪些吏胥交往较好,更要将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受到的惩罚一一详细禀明。为了督促衙役如实填写,他还特别表示“有不遵依注明,查出责革,仍此欺蔽论罪”,并实行五人连坐之法[6](p40-41)。
其二,为进一步控制吏胥,李陈玉创设了鸳鸯签制度。其签宽约二指,长约七寸,自中间对开为二,“仍合书本役姓名,腰尾用二铜管束之。实钉右半,其左半可出入”。每次派员出差,官员、吏胥各执其一。因为原先的一张竹签,人为劈为两半,故名“鸳鸯签”。待事件完日,两半吻合,方能销差。如出差吏胥久不赴销,则官员只要查到在笥的半片竹签便可了然。而且,因为半片竹签是由官员藏于匣笥,不同以往用簿册登记可以让人轻易涂抹删改,在此情况下,吏胥欲“匿则其半在笥,不能匿也”,“欲私上其半,亦无从出,并可以革白役假签之弊”[6](p44-45)。如此,则吏胥难以再偷奸耍滑。
其三,尽量减少衙役出差机会。李陈玉他认为:“积渐而无,莫妙于省。省差、省符、省笞、省锾,一切俱省乃底本于平。勾摄之役四出如虎,民未得直则先得扰,故省差所以防扰也。”[26](p61-65)其自己尽可能躬亲讼案,凡事不用或少用差役,纵然非用不可,也不会专用某人,避免此人以“亲信”“心腹”的身份攫取不当利益。他向民众颁布告示,曰:“本县左右决无一私人,吏不过供看印,书不过供算写,门子不过供衣服,皂隶不过供传呼。”[6](p29-30)他特别提醒人们不要受什么“心腹”“亲信”的欺骗,“若有一人在外招揽词讼、讬言访事者,许人指名呈告。若有过客自言乡里亲戚、平昔知厚者,一概勿听,驱逐出境。”[6](p30)
三、李陈玉息讼之道的形成原因
我们知道,古代地方政府是行政兼司法的“超职权主义”模式①详见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季卫东:《中国司法的思维和文化特征》,载《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季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7—87页。,尤其在明清时代,州县政府有“一人政府”的说法。但这不代表地方官员能为所欲为。无论其行政,抑或司法活动,既有自身素质的主观原因,同时又均受制于政治、文化环境,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探析李陈玉息讼实践背后的缘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学说的熏陶和节约司法成本的考虑是其息讼实践的两种主要成因。
(一)儒家文化的熏陶
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司法文化以和谐为价值追求目标,且试图在施政实践中用一种“无讼”状态彰显这种价值追求。儒家所谓“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是反对争讼的[13](p341)。在他们看来,道德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工具,以德礼治国,方能实现理想的无诉讼社会。至少可以说,在创造和谐社会的作用上来看,他们认为德礼更重要与法律。西汉“独尊儒术”,引礼入律,推崇教化。当时大儒荀悦认为“不教而杀”是虐政,认为“教化之废,推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途”[27](p10)。唐代礼法合一,法律的伦理色彩更加浓重。历代统治者无不倡行教化,鼓吹仁政,以争取民心,稳定社会。李世民就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28](p158)就连夺取侄儿皇位的明成祖朱棣,其登基后也曾下一道《谕勉臣僚恤民诏》,曰:“治天下,以得民为本;保民,以爱恤为先。爱恤之道,不过使其衣食之有余,无冻馁之患。则礼让可成,斗争不作;教化兴则习俗美矣。”[29](p136)
儒家主张仁政,心怀仁慈、刑宽狱简向来是人们对官员的理想要求,亦是清官循吏们的自我期许。从古代“父母官”与“子民”的对应关系我们也可以看出,社会要求官员在裁断狱讼当中不能简单机械地以纸面上的律法来进行,而是要像父母斥责犯错误的子女,调停子女间的争执一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抱着仁慈之心,明德慎罚,借机教化百姓,让司法活动取得更大的社会意义。
在儒家学说的熏陶之下,李陈玉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断案理念:“职本以平心,察以隐情,持以公理,熏以和气,与父言慈,与子言孝,与朋友姻亲言敦睦。小事则教诲解散,大事则轻重处分,使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而好事者渐稀矣。”[12](p14)“催科不扰,是催科中抚字;刑罚无差,是刑罚中教化。此二语良为名言。然欲得不扰,惟有催而不催、不催而催之法;欲得无差,惟有刑期于无刑、罚期于无罚之意。”[26](p6)
也是受儒家学说的熏陶,李陈玉谳狱有个明显的特点,即“宽”“恤”。《尚书·大传》曰“哀矜折狱”,即按儒家的说法,审断案件必须谨慎,且须抱着“仁恕”的准则,“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李陈玉在日记中写道:“为政者贵宽体而严用。以宽为体则一切出于爱恤,自然不苛。小不阴刻至大之极久,而不乖至诚之极久而相谅。严为用者,人始不欺,奸始不蒙也。息诈止恶,省事安人,莫要于此。……故治道贵酌乎中则宽体而严用,百不失一焉。子产孔明俱其人也。”[26](p15)其在给上司的述职材料中还说:史称“活人多,厥后昌……余临狱,每做此想,匪敢失出。盖念牧民者生民者也,时用巧心于仓卒之外,贯朴心于精详之内,日积月累,豁释颇多,不足记者”[12](p54)。李陈玉“省赎以养民财,省笞以教民和。本忠厚与正直,乃熏蒸而孔多”[30](p66)。他在日记中写道:“汉人有言:‘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此语何其切至!宋人有言:‘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两无憾矣。’此语何其真笃!余每临断,大息于汉狱而取法于宋人。”[26](p14-15)其理念的核心即是“宽”“恤”,这与传统的“哀矜折狱”异曲同工。
(二)节约司法成本的考虑
早在宣德年间,江南地区讼牒纷繁,时任松江知府的赵豫就“患民俗多讼”[19](p7213)。明代中期,江南便有民谣“种肥田不如告瘦状”[7](p237)。据海瑞说,“江南民风刁伪,每放告日,状动以三四千计”[7](p237)。明末风雨飘摇之际,东南富庶之地也是盗贼四起,“浙西水乡一带,盗贼出没,白日为梗”[31](p84)。根据李陈玉自述,“善邑诉繁,自来苦之。职下车时,每日投牒凡以数百计”[12](p13)。纵然李陈玉披星戴月,也罕有闲暇。他在另一封给友人的书信中说嘉善一县的簿书可能堪称“海内至繁”,自己“晨出暮入,戴星鞅掌,两臂欲断,双眸不交”。原先的吟诗作赋、游戏山水以及与朋友交游的兴趣爱好,不得不统统放弃。比起知县生涯,李陈玉觉得昔日之雅致“皆似隔世生活矣”[31](p62)。他曾在给朝中内阁官员的一封书信中提到自己“复承乏大邑,朝夕簿书,身在苦海”[31](p63)。尽管如此,他对于听讼断狱一直是慎之又慎,因为讼案事关他人生死、家庭存亡,“一事未严,滥觞此起,一字未核,窦弊潜生”[26](p33)。
李陈玉上任时是崇祯七年,嘉善有大盗袁珠寿为“七郡巨魁,白日入村落民家,或索千金,或数百金,少不遂意则缚其人去,必如数以赎,乃归”[12](p52),百姓深受其害。故而铲除大盗,维护地方安宁,成为李陈玉当务之急。从李陈玉的记录看来,其搜捕、剿灭以袁珠寿为首的窝盗历时约为一年,费尽周折[12](p54)。其他盗贼,如祁峰、陈君甫、沈凤等,“盖不止数十党也”,尽管“诸盗或以嘉善为畏途矣”[12](p11),但可想而知,李陈玉在缉盗问题上付出的努力何其多哉!
必须指出的是,抚字催科与缉盗安民虽同为地方官员两大任务,但似乎明代地方官的考课主要在于钱粮赋税,故其通常会将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催赋征税,能够用于讼案的时间本就不多。而这不多的时间,又主要用于缉拿大盗,故地方官对于讼案只能采取一种“抓大放小”的策略:办案的力量,办案的精力和时间用于处理大案、要案,对于民间细故,只要其不严重危及社会稳定、不妨碍官员考成,就尽可能调处息讼,尽快解决问题,恢复和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避免自己“以有限之时日,供无情之案牍”[6](p64)。
而且,衙门内吏胥有限,诚实可靠、干才显著,能让地方官放心任用之辈更是寥寥。如在缉拿大盗袁珠寿时,诸衙役明知袁珠寿经常来往之处却不能擒之,初来乍到的李陈玉就明白了衙役当中有袁珠寿的内线。于是,他不动声色地访查衙役之中正直善良之辈,令其密访,本以为很快会得大盗之踪迹,不料三月过后,竟一无所获。后来,他又廉访暗查,得知二巨盗妻妾之居所,委一衙役将之拘来。然而,其人却在次日空手返回。经李陈玉严厉督责,该衙役方将二巨盗的妻妾拘至。可见,非常有限的人力资源已经使得地方官员在行政、司法活动中凸显捉襟见肘的尴尬。这促使地方官员面对繁多的词讼不得不采取“清静无为”的消极态度予以应对,正如李陈玉所说那样,“夫无讼者,尚教化。教化非一日之故也。积渐而无,莫妙于省。省差、省符、省笞、省锾,一切俱省乃底本于平。……小事听其去来,大事速为判结。案无迟留,狱无反覆,则请托无所干,隶胥无所示,奸伪无所利,而民之力常宽矣。……吏道贵清净。”[6](p64-65)透过这些墨迹,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其“清净”背后的无奈与苦衷吧。
四、余论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纵使是明末乱世,李陈玉等地方官员仍然秉持“无讼”的理想追求,通过限制或拒绝接受词讼、感化教育、推行教化移风易俗、严格驾驭吏胥等措施化解民间纷争,试图通过息讼达到“无讼”的境界,其目的不仅仅在于个案的裁决,更着眼于社会整体和谐关系的恢复和维持,力争实现“事理而民安,政平而讼简”[29](p61)的目标。究其缘由,既因李陈玉等官员深受儒家“无讼”学说的熏陶,自觉地抱着仁慈之心,哀矜折狱,明德慎罚,借息讼之机教化百姓,激浊扬清,让司法活动取得更大的社会意义,也因为政务繁多,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地方官员精力、能力难以胜任众多讼案的裁断,不得不节约司法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李陈玉在嘉善知县任上,采取了包括息讼在内的众多治理措施,实现了“政刑修明”[30](p63)的治理目标,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其离任后有人作去思碑,赞颂李陈玉治下“国无逋税,野无追呼,胥史刀笔文无害”[32](p28),身殁后被列入名宦祠,可见嘉善百姓对于李陈玉是相当认可的。这就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其息讼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谓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思想文化,而儒家思想文化的终极追求在于建立一个“不争”“无讼”的社会,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地方官员以息讼为宗旨的调处成为古代最常见的司法形式。这种司法形式,直指伦理道德,以高姿态的说教促使当事人平息纷争,恢复和谐关系,“既降低了当事人的成本开销,又节约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无论是对国家、政府,还是对社会、民众,都传递了较大的正能量”[33](p23)。尽管这种形式往往置实体权益于不顾,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个体权益,但个体让渡出部分权益,可能会保持整体权益的完整,有利于更多人的权益得到满足。有学者总结道:“中国传统司法观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核心,其主要表现是:仁道司法观、中道司法观与和谐司法观”[34](p26)。如果此言不差,则贯穿于仁道、中道、和谐三观中的“息讼”可谓中国传统司法观最为直接的外在表征,是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最集中的体现,其内涵值得我们挖掘。黄宗智比较中西法律发展,就提出中国未来法律不一定要像西方那样,依权利为运作核心,而是可以同时适当兼顾中国古代传统,从人际关系出发,依道德准则来指导法律[35](p736)。
总之,古代地方官员的“息讼”实践与艺术是我们认识与理解古代司法文化的共同话语,在当前“法律体系不完善,社会各阶层境况迥异,法官释法能力尚显粗疏、机械的现实情况下”[36](p151),作为一种具有“综合化作用”的处理方式,调处息讼包涵的和谐价值文化理念是我们今天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本土司法资源,我们对于这种资源应予以充分重视并利用之。
参考文献:
[1](嘉庆)大清一统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张岱年.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0.
[3][英]李约瑟.李约瑟文集[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4][日]夫马进.中国诉讼社会史概论[M]//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第六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5]王守仁.公移告谕五种[M]//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甲编第二册.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2006.
[6]李陈玉.退思堂集:卷四[M].崇祯刊本.
[7]海瑞.海瑞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胡旭晟.狱与讼: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9]朱声敏.明代州县官司法渎职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
[10]怀效锋,点校.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1]余继登.典故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李陈玉.退思堂集:卷三[M].崇祯刊本.
[13]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14]汪天锡.官箴集要[M]//官箴书集成:第一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
[15]李陈玉.退思堂集:卷五[M].崇祯刊本.
[16]祁彪佳.蒲阳谳牍[M]//杨一凡,徐立志.历代判例判牍:第五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7]颜俊彦.盟水斋存牍[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8]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史语所影印本,1962.
[19]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0](嘉靖)沛县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影印,1990.
[21]冯梦龙.警世通言.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22]汪辉祖.学治续说[M]//官箴书集成.合肥:黄山书社,1997.
[23]李陈玉.退思堂集:卷六[M].崇祯刊本.
[24]朱国祯.涌幢小品[M]//明代笔记小说大观[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5]明英宗实录[M].台北:中央史语所影印本,1962.
[26]李陈玉.退思堂集:卷一[M].崇祯刊本.
[27]荀悦.申鉴[M]//吴道传,校.诸子集成:第七册.上海:世界书局,1935.
[28]吴兢.贞观政要[M].谢宝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
[29]傅凤祥.皇明诏令[M]//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三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30]李陈玉.退思堂集:卷十二[M].崇祯刊本.
[31]李陈玉.退思堂集:卷十[M].崇祯刊本.
[32](康熙)嘉善县志[M].光绪刻本.
[33]张仁善.传统“息讼”宣教的现代性启迪[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5).
[34]崔永东.对中国传统司法观的理性分析[J].现代法学,2011(3).
[35]黄宗智.中西法律如何融合?道德、权利与实用[J].中外法学,2010(5).
[36]白晓东.和谐司法中的本土资源借力与转化[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