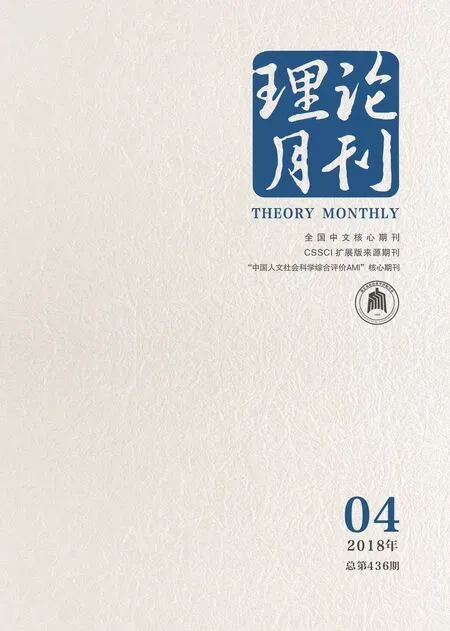《史记》战争叙事的三种笔法
□王俊杰
(河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24)
司马迁以如椽巨笔,在中国历史的宏伟画卷中挥毫泼墨,绘就了中国上古三千年全景式的战争画卷。《史记》战争场面描写运用了不少文学笔法[1](p92-95),然而,《史记》虽是文学巨著,但它首先还是历史巨著,司马迁虽是文学家,但他首先还是历史家。因此,司马迁叙战用得最多的还是史家笔法,史家惯用的叙战手法被他所承继,以言叙战、以文存史、载录军功简牍是《史记》战争叙事中的三种史家笔法。司马迁的战争叙事,具有鲜明的史家做派。
一、以言叙战:滔滔说辞代作喉舌
《史记》中的语言,按其功能可分为:叙事语言、人物语言、抒情语言、议论语言,而人物语言在四者之中所占比例是惊人的。据可永雪先生以王伯祥选注的《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为样本进行的统计分析:人物语言在全篇所占比例最高的竟达71.4%(《范雎蔡泽列传》),低的也占10.8%,平均起来也有42.7%,如果除掉论赞,只以对话与叙事之比算,则几乎接近一比一[2](p366-367)。人物语言又可分为:独白(一人自语)、问答(二人对话)、会话(众人交谈),在三者中问答所占的比重最大。而在“问答”中,所问较短,所答则较长,有的甚至滔滔数百言,乃至上千言。长篇说辞在《史记》中所占分量是很大的,涉及战争的篇目中的长篇说辞有:《仲尼弟子列传》中子贡受孔子之命为救鲁先后游说齐、赵、吴、晋诸国,《苏秦列传》苏秦分别游说六国合纵,《张仪列传》张仪分别游说六国连横以及司马错与张仪廷辩伐蜀抑或伐韩,《范睢蔡泽列传》范睢向秦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以及蔡泽说范睢以取其相位而代之,《平原君虞卿列传》毛遂说楚王与赵合纵以及虞卿说赵王不事秦,《鲁仲连邹阳列传》鲁仲连说赵义不帝秦,《张耳陈余列传》蒯通说范阳令和武信君不战而下三十余城,《淮阴侯列传》韩信登台拜将时发表的“汉中对”,广武君向韩信献策以定燕赵,以及武涉、蒯通分别说韩信叛汉以自立,《黥布列传》随何劝黥布弃楚而投汉,《郦生陆贾列传》郦生说齐王降汉以及陆贾使南越说赵佗归汉,《张释之冯唐列传》冯唐为汉文帝言用将,《匈奴列传》中行说与汉使言匈奴风俗。这些长篇说辞的主体有些是谋臣良将,而绝大部分则是纵横策士,这些策士有的生于合纵连横的战国时代,有的则是驰骋于纵横遗风依然很盛的秦汉之际。这些长篇说辞或高屋建瓴纵论天下大势,或合纵或连横控导国际关系于股掌之间,或兵不血刃而占城陷地,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人归附。这些说辞,气势凌人,纵横捭阖,充分显示了策士们的才智,正所谓: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兵;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
司马迁这么津津有味地铺排大量长篇说辞,有其深刻的原因。
其一,以言叙史的史学传统的影响。中国史学早有记言的传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虽然二者说法不一,其说也未必完全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言与行确实是古代史家记录的主要对象。《左传》记录了许多大夫向国君的谏说之辞以及外交辞令,它们简洁精炼,婉而有致。《国语》以“语”名书,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语言生动活泼,文采斐然。《战国策》以纵横策士为表现对象,纵横家们的游说之辞,铺张扬厉,辩丽横肆。先秦史书确立了以言叙史的传统,这种传统浸染着司马迁。另外先秦诸子散文,大多是语录体,以滔滔雄辩互相辩难为能事,它们积累的记言的艺术经验对司马迁也不无影响。
其二,所取史料使然。其实这与第一个原因就像硬币的两面,上面讲的是记言的史学传统及艺术经验对《史记》的规范作用,这里说的则是《史记》以先秦记言的典籍为史料,司马迁转录其中的长篇说辞也就在所难免了。《苏秦列传》《张仪列传》《范睢蔡泽列传》是三篇表现纵横家的篇目,其资料主要来源于《战国策》,此三篇列传基本由大段长篇说辞串联而成,而这些说辞又几乎完全袭用《战国策》,司马迁只是在联缀时增加了中间的过渡转换,因而它们仍然保持了《战国策》纵横恣肆、犀利明快的特色。对司马迁贯穿长篇说辞的本领,可永雪啧啧赞道:“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是如何从一篇篇分散的、各自独立的说词里,发现和找到它们的内在联系,经过揣度推详,把说词背后的一些东西给想象补充起来,把产生说词的前因后果给贯穿起来,把当日进说的情境场面、主客双方的心理以至动态表情都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一句话,从几篇说词‘复原’出了人,‘复原’出了真实的人物和场面,使千载之下的读者都有幸领略到策士进说是个什么情景,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创作天才!”[2](p406-407)司马迁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本领,对有些看似“犯重”的篇章的处理才能做到游刃有余,如吴见思曰:“苏、张是一时人、一流人,俱游说六国,便有六篇文章,接连写此两传,岂不费力!乃苏传滔滔滚滚,数千言,张仪传滔滔滚滚,又数千言,各尽其致。游说一纵一横,文法亦一纵一横,吾何以测之哉!”[3](p43)苏秦、张仪两传都以长篇说辞为骨架,经司马迁生花妙笔的点化,两篇文章一纵一横,“重”又“不重”,各具风姿。
其三,代作喉舌,借人物之口叙写形势、兵略。通过剧中人物的语言以交代剧情并推动情节向前发展,这是戏剧惯用的叙事手法,这种方法推而广之对整个叙事文学也是适用的。《史记》是史传,自然也属叙事文学之列,让人物代作喉舌以叙写天下形势及克敌制胜的谋略,就成为司马迁叙写战争的一种特殊方式。如司马迁借苏秦、张仪、范睢之口,纵论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的军事外交战略,各诸侯国在此战略格局中分别占据的位置,以及各国或合纵或连横的利弊得失。《淮阴侯列传》中韩信的“汉中对”,纵论刘、项之得失,预见两大军事集团力量的此消彼长,对楚汉相争的发展大势不言而自明。同是该传,借武涉与蒯通之口,指出当时形势:楚汉相争的最终结局,悬于韩信之手,韩信向汉则汉胜,向楚则楚胜,当时确实存在楚、汉、齐三分天下的可能。对天下这些大势,司马迁自己不说一句话,却句句都是他说的话,让历史人物做自己的“传声筒”代已说话,这就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对史传代言、拟言的特点,钱钟书先生早有高论: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4](p166)。
钱钟书隔岸观火,如酷吏断狱,字字见血,句句要命。在这一点上,钱钟书要比章学诚高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中说:“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5](p167)章氏不知,不仅叙事之文作者能够做主,就是记言之文,作者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能做得了主。钱钟书的那段话是针对《左传》而言,其实同样也适用于《史记》《战国策》《国语》等史书。《史记》中的长篇说辞有的是司马迁直接捉刀去“拟言”,有的则是采录《战国策》等先秦典籍,司马迁虽然没有直接操刀,但《战国策》等的作者何尝不也“拟言”呢?另外,司马迁拟录说辞还有一层用意,就是假历史人物喉舌,表明自家对历史人物的态度。如《淮阴侯列传》用武涉、蒯通说韩信叛汉自立来表明韩信以谋反罪被诛实为千古奇冤,姚永概说得好:“《淮阴侯列传》武涉、蒯通二段,反复曲尽,不厌其详,所以见信不反于此时,则后之反乃妄致之辞耳。”[6](p535)从某种意义上讲,司马迁在让武涉、蒯通二人大声替韩信喊冤,这也是司马迁用的一种“曲笔”。
其四,让策士自言心声,展现其价值追求及性格命运。言为心声,让人物自己开口自我表现,这是揭示人物性格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些策士特别是纵横家有其共同的性格特征,他们纵横捭阖,时而连横,时而合纵,没有固定的政治信仰。他们审时度势,崇尚谋略,追求个人的富贵利禄与功名显达是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内在驱动力。他们能说会道,善于揣情摩态,具有高超的语言艺术。对形势的分析既有合乎实际的一面,又有夸大其辞、虚张声势的一面。讲寓言、打比方,是他们惯用的技巧,如苏厉以养由基善射而不知止劝说白起勿伐梁(《周本纪》),陈轸以“画蛇添足”说楚将昭阳勿伐齐(《楚世家》),陈轸以“两虎相斗”说秦惠王不要参与韩魏相攻而要坐收渔利(《张仪列传》)。一般而言,策士们的长篇说辞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声情并茂,即使同一个人物在不同场合的说辞,也是一篇一个模样,各尽其妙。如《苏秦列传》中苏秦分别说六国合纵,“说燕简,而说赵详,燕非纵主,赵为纵主也。说韩、魏虽同,言割地事秦之弊,而辞旨则一主器械,一主地势也。说齐,则羞其以大国而事秦;说楚,则言其纵利而横害。国有大小,地有远近,故不能不异其主张也。有排山倒海之势,并不是一泻无余;有风雨离合之致,并不是散漫无归。”[3](p160)司马迁用这些说辞不仅展现了策士的共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每个策士的个性,这也是《史记》超出其他正史的重要方面。“正史的人物语言以理性化见长,而个性化程度较低。历史著作的这一特征表达了史家的一种人文立场:历史著作的职能是经由对事实的记叙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智慧。对人物语言的记叙也必须服务于这一职能,那些个性化的生活语言在这一取舍原则的支配下往往被忽略和省略。”[7](p188-201)然而,司马迁却不为这种“约定俗成”所牢笼,在人物语言个性化方面,他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在他笔下,苏秦的个性是图强发愤,张仪是机巧诡诈,范睢是幽险倾危,蔡泽是坦荡雍容,鲁仲连是识远义高,毛遂是胆壮辞犀,郦食其是倨傲放狂,此外子贡、甘茂、甘罗、蒯通、随何等人,也是各有各的声口,各有各的风采。
二、以文存史:转录军用文书以叙战
采录军用文书以叙战,是《史记》战争叙事的又一特殊形态。如《夏本纪》采《尚书·甘誓》叙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殷本纪》采《尚书·汤誓》叙商汤伐夏桀的鸣条之战,《周本纪》采《尚书·太誓》叙周武王盟津观兵,《周本纪》采《尚书·牧誓》叙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秦本纪》采《尚书·秦誓》叙秦穆公封尸崤中,《秦始皇本纪》采贾谊《过秦论》作为论赞(今本《秦始皇本纪》录《过秦论》下、上、中三篇为论赞,而梁玉绳、泷川资言等学者认为司马迁只用了下篇,上篇与中篇为后人所妄加)。《陈涉世家》采贾谊《过秦论》上篇作为论赞,《乐毅列传》录乐毅报遗燕惠王书,《鲁仲连邹阳列传》录鲁仲连遗燕将书,《吴王濞列传》录七国之乱时刘濞起兵檄文,《平津侯主父列传》录主父偃谏伐匈奴疏,并录徐乐、严安二人之上书,《卫将军骠骑列传》录汉武帝封赏霍去病的诏书。《史记》中所录文书远不止这些,那些不与战争相关的文书就不列举了。司马迁所录的与军事相关的文书,体裁不一,有盟誓、书信、檄文、表疏、诏书,司马迁录用这些文书时,往往对文字有所改动。
司马迁之所以大量采录已有的军用文书以叙写战事,也是事出有因:
其一,以文存史的史学传统的影响。《尚书》作为上古史书,它的记史就是通过汇辑历史文献的方式来完成的,《尚书》最先确立了中国史学“以文存史”的传统。《尚书》所收文献,共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类,其中与战争联系最为紧密的是誓。所谓誓,是君王诸侯在征伐交战前率领军队的誓师之词,《尚书》中的《甘誓》《汤誓》《泰誓》《牧誓》等誓词都为《史记》所采录。《史记》所录之文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它们本身就蕴含着大量宝贵的历史信息,并且以文来存史简单易行,这也是后代正史采录文书不绝如缕的重要原因。司马迁的高明还在于,他能够根据叙述历史的实际需要,恰如其分地安排历史文献的位置,使它们与前后文水乳交融,与所叙述的历史浑然一体。
其二,司马迁作为“文章家”对奇文的偏爱。古人早就以“文章家”目史迁,如班固在《公孙弘卜式倪宽列传》盛赞武帝时代人才之盛时就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西汉文章两司马因此而得名。风行文坛千年的“古文”,更是以《史记》为范本,司马迁作为文章宗师是有着“文统”意味的。司马迁作为横空出世的一代“文章家”,惺惺惜惺惺,对于他认可的好文章,更是不厌其烦地加以收录。《司马相如列传》实开正史文苑传先河,为司马相如立传也表明司马迁对文章家历史地位的重视。司马相如以辞赋见称于世,本传所收司马相如辞赋达八篇之多,分别是《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书谏猎》《哀二世赋》《大人赋》《封禅文》,该篇也因此成为《史记》收录文章最多的篇目。邹阳不论从历史地位还是从其性格上,都是不足以立传的,然而就因为史迁对邹阳那篇《狱中上梁王书》情有独钟,故把他与鲁仲连合传,诚如茅坤所言:“邹阳本不足传,太史公特爱其书之文词颇足观览,故采入为传。”[8](p4512)吴见思亦云:“鲁仲连、邹阳二传,绝无连贯,止为鲁仲连有聊城一书,邹阳有狱中一书,词气瑰奇,足以相比,遂合为一传耳。观赞语可知。”[3](p50-51)司马迁由于喜欢汉武帝册封其三个儿子的诏令,便为他们专设一世家,并全文照录这三篇诏令,这一点司马迁在《自序》里说得很明白:“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9](p3312)这种做法未免偏激,但也表明对好文章格外关注是司马迁写《史记》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也是太史公“好奇”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即好奇文。司马迁所录的军用文书中,确有一些是难得的好文章,如《乐毅列传》所录乐毅报燕惠王书,感人至深,洞见肺腑,实为诸葛亮《出师表》之蓝本。泷川云:“六国将相有儒生气象者,惟望诸君一人。其《答燕王书》,义理明正,当世第一文字。诸葛孔明以管乐自比,而其《出师表》实得力于此文尤多……彼此对看,必知其风貌气骨有相通者。”[8](p4420)又如《吴王濞列传》所录刘濞起兵时的檄文,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先说汉有贼臣离间刘氏骨肉,次说自己被迫起兵以诛奸佞,极言己方之声势,大有大兵一出天下可定的架势,最后说有功必赏,号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这篇文字作为檄文是很合乎文体规范的,它文辞犀利,语意倾人,富有煽动性,堪称好文章。作为大汉朝的史官,修本朝历史时居然将反叛者的檄文照单全录,这要放在后代正史中是不可思议的,在朝廷看来,这不是在替造反者张目吗?司马迁对刘濞并没有多大好感,之所以全文录用其檄文,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
其三,以文代叙,借他人文章明自家观点。司马迁引录贾谊《过秦论》作为《秦始皇本纪》和《陈涉世家》的论赞,最能说明这一点。论赞本是司马迁直接站出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明对历史的看法,而《秦始皇本纪》和《陈涉世家》偏用贾谊数千言的文章代作论赞,也确是太史公的一大发明。贾谊《过秦论》论述透彻,见识高超,文辞华美,实乃千古好文章,也是汉初总结“秦何以亡汉何以兴”的第一等文字,司马迁把《过秦论》拆开来分别作为二传之论赞,实在是知文而善用,量体而裁衣。《秦始皇本纪》录《过秦论》下篇,以说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9](p278)《陈涉世家》论赞用《过秦论》上篇以说明“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9](p1965)司马迁“偷梁换柱”,借贾谊之文表明自己的看法,这种功夫算是练到了家。再有《平津侯主父列传》录主父偃《谏伐匈奴书》以及徐乐、严安二人上书,也是此意。主父偃是狡猾奸险之人,司马迁却不以人废文,这是因为《谏伐匈奴书》与司马迁反对对匈奴动武的原则立场相一致。让主父偃为己代言反对汉匈开战,这就是史公转录该文字之最用意处。还有《卫将军骠骑列传》引汉武帝嘉奖霍去病军功的四道诏书,也是典型的以文代叙。对霍去病的军功,司马迁不用正笔实写,而是借诏书去虚写,目的是表明霍去病在汉武帝眼中是怎样的大红大紫,正像姚苎田指出的那样:“于去病之功,悉削之不书,而唯以诏书代叙事,则炙手之势,偏引重于王言。”[10](p247)司马迁引录诏书来写卫青、霍去病二人之遭际,一个幽清冷落,一个炙手可热,史迁对此情形不著一字,但此中用意尽现纸背。
三、军功简牍:撮叙功状,不载方略
《史记》战争叙事还有一套笔仗,这就是熔铸军功档案,而不载录方略谋划,它在形式上很像公牍文字,这在《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傅靳蒯成列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曹相国世家》将曹参分做两截写,后半部分写他为相清静无为,前半截则写他为将时的攻城野战之功,下面是《曹相国世家》所叙曹参早期部分军功:
高祖为沛公而初起也,参以中涓从。将击胡陵、方与,攻秦监公军,大破之。东下薛,击泗水军薛郭西。复攻胡陵,取之。徒守方与。方与反为魏,击之。丰反为魏,攻之,赐爵七大夫。击秦司马展军砀东,破之,取砀、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章邯车骑。攻爰威及亢父,先登,迁为五大夫。北救阿,击章邯军,陷陈,追至濮阳。攻定陶,取临济。南救雍丘。击李由军,破之,杀李由,虏秦侯一人[9](p2021)。
杨慎曰:“此与《绛侯世家》及《樊郦滕灌列传》叙战功处同一凡例,纪律严整,盖当时吏牍功载之文如此,可为叙载战功之法。”[6](p432)以上诸篇的传主都是以攻城野战而著称的将军,他们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大都是以勇猛闻名,却不长于谋略,所以司马迁写这类战争人物时,就用另一套笔法,撮叙功状,不载方略。诚如吴汝纶评《樊郦滕灌列传》所云:“此篇以四人战功为主,与叙曹参、周勃战事略同,皆撮叙功状,不载方略,此太史公所以为峻洁也。”[6](p538)这种战争叙事别具一格,自成一体,也为后世正史叙战功树立了榜样。它形似文牍简册,却是条贯缕析、不枝不蔓,甚得“峻洁”之妙,是叙战又一变体。
司马迁撮叙功状,看似简单,实则仍有关窍,他写功状能够紧贴各人身份,文法同中有异。《樊郦滕灌列传》写了四个出身卑微因跟随刘邦立军功而拜将封侯的人物,在司马迁看来,他们之所以成功是跟对了人,所谓“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9](p2673)因为附着于良马的尾巴上,所以能随之一日而致千里。这四人都是因人成事,故此篇多用“从”字,樊哙十九、郦商七,夏侯婴十四,灌婴十四,从字凡五十四见,这是四传之同。司马迁连写四传,其笔法同中又有异,这就是紧贴各人身份,一篇一个模样。因为夏侯婴是太仆(为王者赶车的官),所以司马迁写夏侯婴种种战功时就紧紧围绕“太仆”和“车”做文章。班固依据《史记》再为夏侯婴作传时,裁剪掉不少“太仆”“车”这些字样,传记简则简矣,文章却顿失神采。李景星有高论:“樊、郦、滕、灌以身份相同合传。樊以屠狗为事,郦聚少年而东西略人,滕为沛厩司御,灌在睢阳贩缯,其出身微贱同。樊传曰‘复常从’,郦传曰‘以将军为太上皇卫’,滕传屡书‘为太仆’,灌传曰‘从中涓从’,其被亲幸亦同,是以太史公合而传之。传之妙处在以一样笔法连写四篇,而每篇又各自一样。樊哙是亲臣,故叙其战功以‘从’字冠首,附战级、赐爵而不再编年月;郦商传虽以年月纪事,而却以官名提纲、属战功于其下;滕公夏侯婴本是车将,故节节提‘奉车’字样;灌婴是骑将,故曰‘长于用骑’,曰‘破其骑’,曰‘斩骑将’,曰‘击破楚将’,曰‘虏骑将’,曰‘破胡骑’,曰‘受诏并将燕、赵、梁、楚车骑’,处处以‘骑’字关合,较上三传尤有色泽。”[11](p87)李景星的评语鞭辟入里,深得史公文法之三昧。
司马迁叙写战将功状,多用短句,给人造成一种短兵相接、紧张激烈的感觉。司马迁既善于构造长句,又长于运用短句,短句多用于战争、行刺(如荆轲刺秦王)、劫盟(如曹沫劫齐桓公)等篇章。短句就句子成分而言,它们突出主干,剥离枝叶,显得简净利落,短句与短句相接,如热锅爆豆,又似爆竹投火,噼噼啪啪,声声响脆。司马迁用短句写趣攻战疾,营造出一种令人心惊的近身肉搏的战场氛围,语言形式与所写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司马迁是语言大师,遣词用语的功夫臻乎化境,这种功夫的养成显然也得益于对“春秋笔法”中的“以一字为褒贬”的自觉师承。《史记》叙写战争特别是叙写战将军功时,措辞很有讲究,对此前人多有评述。茅坤评《樊郦滕灌列传》记战功时说:“太史公详次樊、郦、滕、灌战功,大略与曹参、周勃等相似,然并从,未尝专将也。其间书法,曰‘攻’、曰‘下’、曰‘破’、曰‘定’、曰‘屠’、曰‘残’、曰‘先登’、曰‘却敌’、曰‘陷阵’、曰‘最’、曰‘疾战’、曰‘斩首’、曰‘虏’、曰‘得’,成各有法。又如曰‘身生虏’,曰‘所将卒斩’曰‘别将’,此各以书其战阵之绩,有不可紊乱所授也。”[7](p4977-4988)可永雪也指出:“汉初战将纪功,仿《春秋》书法,创为历叙体,用‘攻’‘击’‘ 破’‘追’‘围’‘救’‘下’等字序其事;又用‘定’‘得’‘取’‘守’‘虏’‘斩’等字序其功;并以或‘陷阵’‘先登’,或攻城掠战中常‘最’或‘疾斗’‘战疾力’‘以兵车趣攻战疾’表其人的个性特点,行文以简捷、简劲取胜。”[2](p345-346)司马迁撮叙功状,用不同词语以区别不同的战绩,这些词语生动准确,简劲的字词中包蕴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微妙的情感向度。
司马迁作史充分利用了汉代的官府档案,上述诸篇典型地体现出《史记》取材军功档案的特色。刘邦打天下时,有严格的记录军功的制度,正因为如此,将士们才会奋不顾身、浴血沙场。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是读过这些军功簿的,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他说:“余读高祖侯功臣”[9](p877),就说明他作年表时依据了当年的军功档案。太史公既是史官,又是“档案管理员”,可以说,司马迁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家,与他是一位杰出的档案工作者密切相关。善于利用档案材料是历史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司马迁虽然大量地运用档案材料写历史,但并不是简单地搞成档案材料汇编,而是化档案材料为历史,把档案材料用活,写成信史。”[12](p137-141)司马迁据档案作史,军功自然准确严密,其叙战则别开生面,自成气象。熔铸军功档案而不载录方略谋划,它形式上很像公牍文字,实际上是叙战的一种变体,文章也因此呈现出一种古朴厚拙之美。
参考文献:
[1]王俊杰.论《史记》中的战争场面描写[J].佳木斯大学学报,2013(1).
[2]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说[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3]吴见思,李景星.史记论文·史记评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6]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史记集评[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7]陈文新,王炜.传、记辞章化:从中国叙事传统看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2).
[8]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姚苎田.史记菁华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1]李景星.四史评议[M].长沙:岳麓书社,1986.
[12]施丁.谈司马迁运用档案撰写历史[J].学习与探索,19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