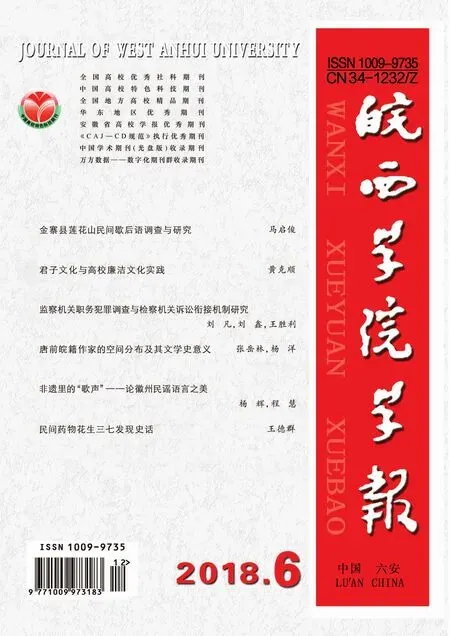雍正时期惩贪治吏的思想措施探析
代鹏芳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清朝自1644年入关以来,不断进行统一战争,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康熙中期。自此,中国又一次走向统一,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经过数十年的平稳发展,到了康熙末年,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加之康熙后期“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的方式治理国家[1](P436),奉行“宽仁为尚”的原则,以致吏治败坏,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到了雍正继位之时,已经亟须变革。
一、雍正朝的吏治情况
吏治问题在雍正为藩王时已经注意到,他对此有着深刻的认知和强烈的反感[2](P86),尤其是对官吏中存在的贪腐现象深恶痛绝,“数十年来,日积月累,亏空婪赃之案,不可胜数,朕若不加惩治,仍容此等贪官污吏拥厚资以长子孙,则将来天下有司皆以侵课纳贿为得计,其流弊何所底止!”表达了对吏治问题突出的不安和担忧。相较于康熙,雍正虽自谦事皆不如其父,但“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者,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远过之。”[3](P798)再加上其本身果断坚毅的性格特征,形成了雍正皇帝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所以在继位之后,他便着手整顿吏治。
综合的说,雍正时期的吏治大致存在这几个问题:其一,最突出、最敏感的就是朋党问题,既包括由储君问题产生的各皇子党派,也包括朝中满汉大臣之间的立场斗争。雍正是储君斗争的亲历者,他深知朋党斗争对社稷的影响,所以对朋党问题态度坚决;其二,贪腐现象常态化,加速腐蚀着整个官僚阶层。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耗羡银。所谓耗羡银,就是指政府在征税的时候附加的银两熔铸损耗费。耗羡银是一种附加税,一般由地方政府支配,不统归中央。由于清代地方官员合法俸禄普遍较低,难以维持高额的日常开支和节日孝敬之费,所以通过征收“耗羡银”开拓财源成为很多地方的通例。冯尔康先生在其著作《雍正传》中根据现存的资料整理出了清朝康熙后期全国各省的火耗加征率表(表1)[2](P83)。
可以看出,各省的火耗征收普遍比较高,康熙后期对耗羡银的监管进一步放松,这就助长了部分地方官员随意加收和挪用耗羡银的不良风气,加剧了官场的腐化程度。
雍正明确表示要“移风易俗,跻斯世于熙皞之盛”[4](P280),力求革除康熙以来的种种弊病,以使国家政治焕然一新。他深知,康熙朝以来在吏治上所造成的问题,不仅是朝夕所成,更是数百年来的积累形成的痼疾。兴利除弊,就必须追根溯源,“澄清吏治”就要“于公私毁誉之间,分别极其明晰,晓谕不惮烦劳,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5](P1205)雍正一改其父坚持的“宽仁”治国的策略,主张“当宽则宽,当严则严”[6](P2995),天下承平有年,世人“玩愒已久”,社会“百弊丛生”[6](P2995),这种情况下再以“宽仁”治国必将导致社会矛盾的爆发,这体现出了雍正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与时俱进的治国思想。
雍正首先做的就是剪除影响他推行改革或者对其造成一定威胁的潜在势力,他通过分化、瓦解,清除了允禩、允禵集团,继而又对诸如年羹尧、隆科多痛下杀手。通过打击朋党,他基本上肃清了政治障碍。在此背景下,雍正通过政治、经济等诸多手段,一扫康熙后期以来的“颓风”,整顿吏治初见成效,故而时人有“雍正改元,政治一新”之说[7](P158)。因篇幅有限,这里仅从思想文化领域作一探析,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指正。
二、利用儒家端正道统,以儒理治世
统一后,由于清人没有足够的统治经验,大多采取野蛮武力和思想控制,加剧了民众和新政权之间的矛盾。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新政权的基础日益稳固,便逐渐采取怀柔的方式处理满汉问题,推崇文教,将科举考试作为拉拢汉人特别是士人归心的重要方式。康熙亲政以后,开设博学鸿词科,汉族士子反应积极,这样,清政府对待儒学和汉族士人的态度才算真正确定[7](P158)。
(一)雍正的儒理治世方针:尊孔以崇儒
作为继承人,雍正延续并贯彻了康熙的这一既定方针;同时,作为完全成长在儒学文化环境中的皇帝,他不仅完全认可儒学,也对儒学有深刻的理解,他认识到儒学中的某些观点对加强君主专制的作用,也可以成为其整顿吏治的一种手段,为己所用,所以雍正大力推崇儒学。推崇儒学,雍正最先做的就是尊孔。孔子历来被视为儒家的创始人,一直受到整个社会的推崇,所以尊孔就是释放国家重视士人的信号,这样既能使天下学人归心,又借此达到教化的政治目的。可以说,雍正对孔子的尊崇无出其右者。首先抬高孔子的地位,不过彼时孔子早已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已至最崇,所以雍正便决定追封孔子先人五代为王,以示尊荣[8](P118);之后的十几年里,雍正通过改“幸学”为“诣学”①[9](P227)、指派工部重修曲阜孔庙、要求全国避孔子名讳等方式来表示对孔子的尊敬。
雍正尊孔,不仅仅因为出于自己内心对儒学的热爱,而更具有实际目的性,他直言:
至圣先师孔子以仁义道德启迪万世之人心,而三纲以正,五伦以明,后之继天御宇兼君师之任者有所则效,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10](P572)。
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序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见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11](P905-906)。
他毫不隐晦地说尊孔能够“正三纲,明五伦”,“为益于帝王也甚宏”,所以要“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同时指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对纲纪人心、君臣伦理有重要的约束和规范作用,这些对于为君之人是受益最大的。崇敬孔子以及推崇儒学还可以表明新朝承继前明,具有正统地位,这样雍正利用儒理治世便显得顺理成章。他将孔子视为己师,掌握着儒家道统的话语权,在尊孔崇儒时特意放大了正纲明伦和阐明君臣义礼、尊卑有别的部分,名之曰“教化”。为了达到理想效果,雍正将重点放在了学校教育和科举,因为这两个部分是国家选拔人才、任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这就是从官员选拔的源头向国家的储备人才强调忠君、正己、奉公、廉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颁布《圣谕广训》和《庭训格言》
为了达到“教化”的目的,他颁布《圣谕广训》、《庭训格言》并广泛传谕,要求庠序之所遍习。这两部著作藉忠孝之名却处处将君臣比作父子,以孝言忠。《圣谕广训》实际上是对康熙 “圣谕十六条”进一步解释而成的书。康熙九年,以上谕的形式发布“圣谕十六条”,七言对仗,谕文如下: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穆;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弥盗贼,解雠忿以重身命。
可以看出,其核心就是儒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要求世人要重人伦秩序、讲求节俭、务本守法。在雍正看来,“圣谕”“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本末精粗,公私巨细”[12](P266),这些对普通民众有教化作用,还可以被用来教育官吏。为了让“圣谕”能够最大范围的普及,雍正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圣谕十六条”逐一解释、扩充,“寻绎其义,推衍其文”[12](P266),最终形成十七篇文章,包括一篇序文和十六篇释文,洋洋数万字,以《圣谕广训》名之。雍正对“圣谕”的解释,实际上是寄托自己对天下百姓、大小臣工的期望,比如解释“圣谕”第一条时就联系到儒家“宗圣”的话:“居处不庄非孝,事君不忠非孝,莅官不敬非孝……皆孝子分内之事也。”[13](P593)根据皇帝的要求,《圣谕广训》成为科举考试的项目。
此外,雍正又不遗余力地亲自撰写《庭训格言》一书。此书成于雍正八年,共一卷二百四十六条,所记载的主要是康熙晚年对诸皇子教导的话,包括治国为政、统御臣下等为君之道和诸多日常琐语,是根据雍正的回忆收辑编纂而成的,这些内容是实录之类所没有记载的。雍正在《庭训格言序》中说道:
皇考圣祖仁皇帝性秉生安,道参化育,临御悠久,宇宙清宁六十载,圣德神功超越万古,凡为史臣所记注,黎献所见闻者,固已备编于实录……天颜怡悦倍切,恩勤提命谆详,巨细悉举。其大者如对越天祖之精诚,侍养两宫之纯孝,主敬存诚之奥义,任人敷政之宏猷,慎刑重谷之深仁,行师治河之上略,图书经史礼乐文章之渊博,天象地舆历律步算之精深,以及治内治外,养性养身,御射方药,诸家百氏之论说,莫不随时示训[14](P613-614)。
“庭训”,取自《论语·季氏篇》中所载陈亢和伯鱼的对话,伯鱼回忆自己“趋而过庭”时其父仲尼对自己的谆谆教诲,后人将此称之为“过庭之训”或“庭训”[15](P176)。所以,《庭训格言》这本书的含义就是将康熙对自己的教诲当作准则一样传授下去。
他于《庭训格言序》中说自己:“四十年来,祇聆默识,夙夜凛遵,仰荷攒承,益图继述。”[14](P614)以此来证明自己从小就受到康熙皇帝的耳提面命,表明统治的合法性,同时“益图继述”也表明了其“格循祖训”,继承和坚持其父的施政方针并发扬光大的意志。正如书名一样,雍正有意不提政治,抛去“皇帝”的光环,而是以一个普通儿子的身份来记述父亲生前对自己的“叮咛告诫之言”,这是对康熙的一种夸大式的褒扬,实际上也是雍正对自己的一种鞭策——继承圣人遗志,再造一个圣人。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本书表达了整顿吏治的决心,故曰:“司马迁有‘百称皇帝,其文不雅驯’之说,盖其识不足以知圣人,故所述不尽合本旨也。是编以圣人之笔,记圣人之言,传述既得精微,又以圣人亲闻于圣人,援受尤为亲切。垂诸万世,固当典谟训诰共昭法守矣。”[14](P637)
这种用文化进行吏治教育的方法的确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如果单纯依靠文本教育来整顿吏治恐怕是不够的。雍正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大力宣传儒家忠君敬业、廉政爱民的思想之外,他还极力宣传“清官”,鼓励臣民以他们为榜样。这种更为直接的教育方式,与文本教育互为呼应,相互补充。
三、宣传“清官”的政治榜样,进行政治教化
雍正借助乃父“清官”之风留下来的政治遗产,以“清官”作为政治榜样,实行政治教化。然而,雍正对于什么是清官、清官的性质、清官的作用等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从具体的分析阐述中可窥见一斑。
(一)“清官”含义及其演变
所谓“清官”,与“贪官”有着相对立的含义,指为官清正廉洁的人。但实际上,“清官”的概念一开始并非如此。中国古代典籍里最早出现“清官”的说法是《三国志·虞翻传》[16](P1317)。不过在《三国志》中,“清官”的含义仅与“浊官”相反,意指“清贵简便之官”。[17]人们在表达理想中的为官者时往往用“贤”。《说文解字》曰:“贤,多才也,从贝臤声。”[18](P204)如孔丘之“见贤思齐”,又如诸葛氏之“亲贤臣,远小人”之类。到了两宋时期,市民阶层的崛起带动了通俗市民文化的发展,如宋话本等。在这些民间文化中,人们为了表达对吏治的理想,始以“清官”这一词为载体,将其赋予了“清正廉洁、办事干练”的意义,大概类似于古之“贤”。至此,“清官”得以今义开始流传。
因为人的个体差异和环境所限,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很难求得道德和能力的双赢。统治者们在人才选拔中总结经验,探索对选拔官吏时“德”和“才”之间如何权衡。如北宋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就认为,“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即人们通常将“德”和“才”混淆在一起,这导致了人才选拔的失误。而他将人分为四种:“圣人”“愚人”“君子”“小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19](P15)明末的李卓吾就按照这种人才鉴别的思想认为被一些史学家所称道的海瑞也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清官”。他说:“世有清洁之士,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如世之万年青草,何其滔滔也!”[20](P162)他认为海瑞洁己却能力欠缺,故而可以称其有“德”而不能说其有“才”,所以不能称之为“清官”。
(二)清朝的“清官”及康雍任人比较
“清官”一词真正被官方和民间普遍使用要到清康熙以后[9]。此时,“清官”已经渐趋偏离了宋以来的含义,以“德”而非“才”论之,正是因为这样,康熙以来被人称道的“清官”才被很多学者诟病。如前李卓吾所云,“贪官之害,但及于百姓,清官之害并及于儿孙”[20](P162)。这里已经很明确地对“清官”做出了批评。而雍正正是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将自己对“清官”的偏见表现得淋漓尽致。雍正对人才选拔很是注重,称“从古帝王之治天下,皆言理财、用人,朕思用人之关系,更在理财之上。果任用得人,何患财之不理,事之不办乎?”[21](P685)更言“治天下唯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支叶事耳”[22](P708)。他如此重视用人,是为其政治改革服务。康熙以“德”为首,所以用人取才皆以道德论高低,忽视了对官员行政能力的考察,所以康熙朝多“清官”,却难见办实事的人。雍正深以为弊,故其用人并不援例其父,反而更加看重才能,并多次在公开场合中表达对部分“清官”的不满,认为这些人不是自守清高而无所作为,就是沽名钓誉、表里不一,故曰“节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23](P51),所以他“宁用操守平常之能吏,不用因循误事之清官”[24]。不过,以才任人往往带来人事的频繁变动,他自己解释道:“事无一定,又不可拘执……是故或一缺而屡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后顿异,盖朕随时转移,以求其当者,亦出乎不得已。”[25](P481)又言“缘目击官常懈弛,吏治因循,专以积累为劳,坐废濯磨之志,不得不大示鼓舞,以振作群工委靡之气。”[26](P806)但是,这种唯才是举的方式因为缺少对“德”的考察,造成了一定的政治风险。雍正虽夸口“朕意虽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何惧之有?……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省力,唯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操纵”[22](708)。这种做法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冲突,而雍正宣称以儒理治世,要在二者之间加以权衡,他依旧像中国传统帝王一样,把三国魏末司马昭所谓的“清慎勤”作为选官的标准②,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审时度势,更加强调能力优先[2](P527)。
(三)雍正以“清官”为范,教化臣工
面对这种非常规的官场秩序,雍正巧妙地利用“清官”这一群体,深化其思想教育的策略。实际上,雍正并没有对“清官”全面否定,他也一直强调“操守清廉乃居官之大本”[26](P806),“清官”之所以能够被百姓所爱戴,是因为他们“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27](P690),即便能力欠佳,只要用心上进,亦可留用,以观后效。雍正深知“清官”背后所代表的道德对治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塑造“教育模范”这一政治角色来鼓励官员廉洁自律,达到治吏的目的。这一做法是和他所采用的以才论人策略相互。要兴补充的。兴利除弊,从制度上加以补救是必需的,但是制度的推行在于其威严,只能使人心生畏惧被动遵守,要使人主动约束自我,道德上的制约也是必不可少的。雍正从这两种途径双管齐下,通过给予“清官”口头上或物质上优厚的政治待遇,树立政治榜样。在不重用“清官”的前提下却号召向他们学习,这实际上就是把“清官”群体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给臣下参照,既要求洁己,又要以清官平庸的行政能力为戒鞭策自己。
比如雍正时期著名的“清官”魏廷珍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魏廷珍,直隶景州人,康熙五十二年探花,初为编修,以后历任侍讲、日讲起居注官、侍读等,入直南书房。康熙皇帝也一直重用他,康熙五十八年命其祭告中岳及济淮两渎,次年又充任正考官,并擢为詹事、迁内阁学士。此后,魏廷珍逐渐被委以实权,经手地方财政大事。康熙六十一年,办理两淮盐政;雍正元年,授湖南巡抚,成为封疆大吏。雍正称其“为人清正和平,朕所悉知”,“为人老成,学问操守俱好,是以用为湖南巡抚”[28](P1092)。但是其实际政治能力又如何呢?我们可以看看他出任地方大员后的一些为政表现。雍正二年二月,在湖南巡抚任上处理辰溪县革生黄先文故杀一案、辰溪县谭子寿等奸毙三命案量刑失当,“均经部驳”,被斥为“草率朦混”,并交部议处,最后降三级调用;次年在安徽巡抚任上,因审查地方假印私收钱粮一案不力又被上谕训斥,此后又因督办清厘钱粮、清查亏空致受罚者过多而罢……雍正起初对其抱有信心,还勉励他要“处事贵刚果严厉,不宜因循退缩。地方利弊之应革应兴,属员贤否之应举应错,须尽力振作一番,方冀可收成效”[28](P1092)。但其实际表现却让雍正大为失望,说他“自到任以来,甚乏理番治剧之才,凡料理一切刑名钱谷,非过则不及,率多罢较糊涂”、“于相省事务漫不关心……甚属疏忽怠玩”,并把魏廷珍作为反例,“以为封疆大臣忽视地方利弊者戒!”[28](P1094)而魏廷珍在经历种种挫折之后上疏乞求“内补修书之地”,却被雍正斥责道:“惟务洁己自好,于民生国计毫无补益,而遽望内转清要,安闲适志,以保禄全名。如是,则为臣不易之语谬矣,汝其勉之!”[28](P1094)但即使这样,魏廷珍却被加以优遇,虽遭降职留用,寻又升迁高位,包括盛京工部侍郎,湖南、安徽、湖北巡抚,礼部尚书、漕运总督、两江总督、兵部尚书、皇清文颖馆副总裁等要职。乾隆初年,皇上还亲赐匾额、御制诗,恩荫子孙,死后“赐祭葬如例”,并赐谥号“文简”。可以看出,魏廷珍在政治上的建树并不突出,不过雍正依旧重用他,其目的就是以其“学问操守甚好”来树立政治榜样,激励其他臣工学习以魏廷珍为代表的这类“清官”的品行,从而达到惩贪除弊、整顿吏治的目的。
纵观整个雍正朝的政治状况,实际上以“清官”为政治教化的措施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到了雍正后期,这种策略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已经让人忧虑[24]。究其根本,是对道德和能力的理解错位,雍正似乎过高地预估了自己御下之术和人性的自控力,一旦失去了道德约束,很容易从“能吏”变为“酷吏”。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言:“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危害岂不多哉!”[19](P15)
四、融合儒佛道三教,利用宗教控制士民
雍正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宗教氛围浓郁,佛道之教大兴,其背后是雍正试图利用宗教管束臣民,从思想文化方面对吏治加以控制。这从他对佛道两教的具体方式中可以窥见。
雍正身居藩邸之时就与佛教有了密切的接触,比如雇人替自己出家,名曰“替僧”,经常和高僧坐而论佛,接受指点,从佛教中汲取为臣为君之道。他继位之后更加尊崇佛教,还多次称自己是和尚、野僧。他在一首名为《自疑》的诗中说道:
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
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29](P938)。
他不仅称自己是和尚,甚至还把自己看作“释主”,即佛教教主之意。《雍正朝起居注》雍正五年正月,“北萨克喀尔喀尼鲁特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折奏黄河澄清恭请诵经祈福”,雍正准允了这一请求,并在致贝勒贝子的祝福中称“朕亦即是释主”[30](P938),这样一来,他就通过自封成为佛教的精神领袖,将佛教纳入到自己的政治管理之下,为己所用。他对佛教事务的干预超过很多皇帝,主要表现在赐予佛徒封号,任命寺院主持,扩建、修缮梵宫等。他还热衷于辩论佛教理论,“辨明思想,既要以符合自己意见的观念作为指导思想,不仅要把它贯彻在俗民中,还要统治方外世界”[2](P517),最终掌握对佛教的解释权,让自己能够对佛教理论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解释。
雍正将自己变成政教合一的总领袖,实际上是想借助佛教的力量整顿吏治。雍正时期的佛教高僧——文觉禅师,就长期供养于紫禁城中。雍正视其为自己的智囊,允许其参与朝廷机要,许多政治事件的处理都是咨询他的意见,包括允禩集团案、年羹尧案等。此外,雍正自称“释主”之后,便在宫中举办聚会,聚众论法。他甚至收徒讲学,有门徒十四人,包括允禄、弘历、鄂尔泰及张廷玉等亲近心腹之人。每当君臣以讲授佛法之名会面时,实际上就是一次政治会议,所讨论的更多的还是实际的政治事务。
除了佛教,雍正还尊崇道家。他对道教的态度和对佛教是一样的,都是本着为世俗政治服务,他在一首名为《碧霞祠题宝旙步虚词》的诗中表达了他的这种意思:“常将天福人间锡,奖孝褒忠佑乃方。”[31](P465)就是希望道士们心存济世救民之心,宣传忠孝,协助君王的治理。他继位之后对道士宠渥尤甚。不仅经常和道士往来,还将一批道士养于宫中,坐而论道。当然他自己对道教的思想理论并没有什么兴趣,用意在于以道教的相关理念能够在民间和朝廷传播,成为他治理国家的思想工具。
作为统治阶级推崇的社会意识形态,雍正看到了儒佛道在政治领域的共通性,他将儒释道融合为一体,“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32](P465),能起到“致君泽民”的作用。他将佛道二教融合,称“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33](P137),既收佛教弟子,又纳道教真人,混淆佛道的界限。同时利用儒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帮助抬高佛教和道教的地位。不过,雍正对宗教的态度一贯是利用而不是沉溺其中。他将自己凌驾于宗教之上,以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的双重身份,自觉地将宗教宣扬的“忠孝”带入到世俗中去,始终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也避免了重演历史上宗教乱国的悲剧。
雍正在思想文化上整顿吏治的措施,相当多的只能起到治标的作用,又因为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短时间内很难看出明显效果,所以雍正短短十三年的统治是为乾隆作了基础。雍正以才论人的措施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行为,不管是任用能吏还是惩罚贪官,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一旦嗅到了政治环境的变化,又会是另一番情况。他的这些改革很难触及根本,所以他也不可能挽救“颓势”,改变的只是暂时的效果。但是,我们还应看到,雍正敢于改变、革新,他所采取的这些思想文化措施部分顺应了民众的诉求,对团结汉族士人,调节满汉关系,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有一定作用。他所倡导的这些,固然有其个人因素需要商榷,但考虑时代的局限,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① 中国古代皇帝去学宫祭祀孔子时称“幸学”。“幸”者,“巡幸”也,是“臣下尊君之词”;雍正认为用“幸学”使“朕心所未安”,所以凡后则将“幸”改为“诣”,“以伸崇敬”。
② 《三国志》卷18《魏书·李通传》裴松之注引王引《晋书》:“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36页。
—— 陈廷敬
—— 陈廷敬
——于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