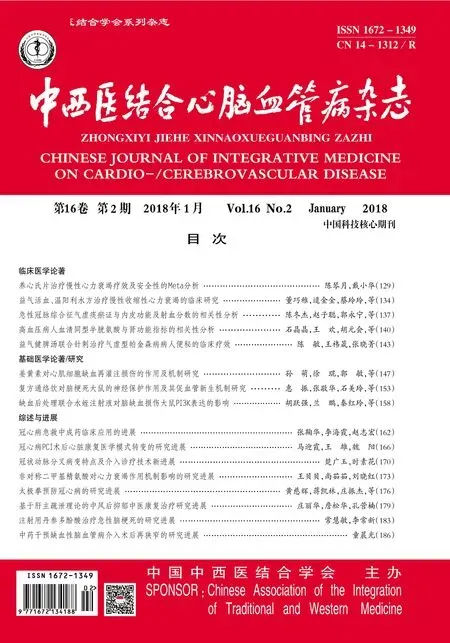急性冠脉综合征气虚痰瘀证与内皮功能及射血分数的相关性分析
,,,,,, , ,
心血管疾病具有发病率高、致死率高、致残率高特点,已成为我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致死、致残的首要原因,严重影响我国居民的健康,同时对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负担[1]。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 dromes,ACS)是由于冠状动脉堵塞,发生急性、持续性缺血缺氧引起的心肌坏死,主要临床表现为剧烈而持久的胸骨后疼痛,呈压榨感,经休息或扩血管药后不能完全缓解,伴有心肌损伤标志物增高和心电图改变的急危重症,常合并恶性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急性心力衰竭等严重并发症[2-4]。ACS的发生发展与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密切相关,血浆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内皮素-1(endothelin-1,ET-1)、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on willebrand factor,vWF)是重要的血浆内皮功能标志物,三者水平异常是ACS的病理机制[5]。ACS属于中医学“真心痛”“胸痹”等范畴,属于本虚标实之病,本虚为气虚,标实为痰浊、瘀血,气虚是内在基础,贯穿疾病始终,痰浊、瘀血是病理产物,三者互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其证素以气虚、痰浊、血瘀为主[6-7]。目前关于ACS中医证型和内皮功能研究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ACS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开展。本研究探讨ACS气虚痰瘀证与NO、ET-1、vWF、左室射血分数(LVEF)的相关性,为中医药防治ACS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研究对象 纳入2015年1月—2015年12月广东省中医院收治的ACS病人60例,根据中医证候量表分为气虚痰瘀证组及非气虚痰瘀证组,各30例。气虚痰瘀证组男16例,女14例,年龄65.9岁±6.3岁;非气虚痰瘀证组男15例,女15例,年龄66.1岁±6.9岁。两组病人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1.2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2007年美国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脏协会关于ACS的相关诊断标准[8],中医辨证参照1991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学会颁布的《冠心病中医辨证标准》[9]中的气虚痰瘀证辨证标准和2002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中关于冠心病的辨证标准[10]。
1.1.3 纳入标准 符合西医ACS标准;符合气虚痰瘀证和非气虚痰瘀证的诊断标准;年龄30岁~75岁。
1.1.4 排除标准 合并严重脑血管病、消化道出血、严重糖尿病并发症、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血友病、严重血小板减少、凝血功能异常者;合并恶性肿瘤者;精神病病人;服用华法林者;合并其他心脏疾病如心脏瓣膜病、心肌病、肺心病等疾病者。
1.2 研究方法
1.2.1 实验室指标测定 所有病人均在空腹状态下,抽取肘静脉血6 mL,离心后分离血浆,立即冻存于-45 ℃低温冰箱中备测。采用ELISA等方法检测血浆ET-1、vWF;硝酸还原酶法检测NO水平。上述检测由金域检验公司完成,按照试剂盒实验步骤进行操作。
1.2.2 LVEF 应用GE Logig 7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1.5 MHz~4 MHz),病人处于左侧卧位,进行胸骨左缘探测,于胸骨左缘长轴切面、心尖四腔心与五腔心切面进行检测。

2 结 果
2.1 两组病人内皮功能和LVEF比较 气虚痰瘀证组血浆vWF、ET-1水平明显高于非气虚痰瘀证组,血浆NO水平明显低于非气虚痰瘀证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病人LVEF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组别nNO(μmol/L)vWF(ng/L)ET1(ng/L)LVEF(%)气虚痰瘀证组 3038.45±5.10130.70±4.18229.10±15.1347.43±3.62非气虚痰瘀证组3053.46±3.62125.74±3.06208.39±7.3748.83±4.45t值-13.145.346.74-1.34P 0.000.000.00 0.19
2.2 ACS气虚痰瘀证与NO、ET-1、vWF、LVEF的相关性分析 由于ACS气虚痰瘀证与非气虚痰瘀证为二分类变量,ACS非气虚痰瘀证为0,ACS气虚痰瘀证为1,对ACS气虚痰瘀证与内皮功能(NO、ET-1、vWF)及LVEF行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ACS气虚痰瘀证与ET-1、vWF呈正相关性(r值分别为0.766、0.555,P<0.05),与NO呈负相关性(r=-0.8400,P<0.05),与LVEF无相关性(r=-0.132,P>0.05)。
3 讨 论
ACS属于中医学“真心痛”“胸痹”“厥心痛”等范畴,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心血管急症。正如《灵枢·厥病》言“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ACS属本虚标实之病,本虚是气虚,标实是痰浊、血瘀。气虚是冠心病发病的根本前提和内在基础,贯穿疾病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痰浊、血瘀是气阴亏虚的重要病理产物,是中心病理环节,二者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病程缠绵,因此气虚痰瘀为主要病机。
现代医学认为,ACS是冠心病中一种危重的类型,主要发生机制是冠状动脉易损斑块破裂或糜烂,激活血小板及凝血酶,导致斑块表面血栓形成和/或远端血管栓塞,造成相应冠状动脉完全或不完全闭塞,最后引起心肌缺血甚至坏死为特征的一组疾病综合征。ACS的病理基础是动脉粥样硬化,而内皮损伤反应学说[11]是目前广泛认可的动脉粥样硬化发病机制,这种假说的关键是内皮损伤,而“损伤”发生于动脉壁上特殊解剖部位内皮细胞[12]。
血管内皮细胞在维持血管张力和血流调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内皮细胞可阻止血小板和白细胞的激活,因此完整的内皮系统在维持血管稳定和防止血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这种血管的稳定性及血栓的形成是ACS发生的病理基础。血管内皮细胞是人体最大的自分泌、旁分泌和内分泌器官,主要通过合成和释放血管活性因子,影响血管张力和调节血管壁内外环境动态平衡。NO和ET-1是主要的两种血管活性因子,NO具有舒张血管、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抑制平滑肌细胞过度增殖作用,若NO释放减少,则促进血栓形成[13];ET-1引起血管收缩,激活巨噬细胞,促进平滑肌细胞增殖和迁移。vWF是由血管内皮细胞和巨噬细胞合成分泌的糖蛋白,具有收缩血管作用;NO生成减少、ET-1和VWF合成增多,即内皮依赖性收缩因子与舒张因子失衡,引起血管痉挛,平滑肌细胞增殖,血栓聚集,加重斑块硬化进程[14]。NO、ET-1、vWF是反映内皮细胞损伤的敏感指标,因此检测血浆ET-1、NO和vWF对判断血栓形成风险、病情轻重及预后具有重要意义[15]。
中医传统理论认为,心主血脉,其中心气推动和调控心脏的搏动及脉管的舒缩,维持脉道通利。气虚心气不足,无力推动,气为血之帅,血行不畅,壅滞血脉化瘀;气虚机体运化失常,水湿内生,聚而成痰,痰阻经络,加重气虚。“痰”是人体水液代谢障碍形成的病理性产物,与脏腑气血关联;“瘀”指体内因血行滞缓或血液停积形成的病理性产物,其产生与中医的气机、脏腑之气如心、肺、脾、肝、肾密切相关,“瘀”既是病理产物,又在一定条件下也可成为某些病的致病因素。痰瘀二者同源异质,并可互相转化而促进,气化失司则生痰,气虚则痰生,痰生则血瘀。有研究表明,痰证与脂质代谢异常密切关联,瘀证与血流动力学、血液流变学指标密切相关,脂质代谢异常可影响血液的黏稠度和血液流变学,导致微循环障碍,组织缺氧等,因此认为痰与瘀之间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转化的过程[16]。
本研究观察ACS气虚痰瘀证与非气虚痰瘀证病人血液NO、ET-1、vWF水平,分析ACS气虚痰瘀证与血管内皮功能的相关性。本研究发现,气虚痰瘀证组病人血浆NO水平较非气虚痰瘀证组降低(P<0.05),而ET-1、vWF水平较非气虚痰瘀证组升高(P<0.05);两组LVEF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ACS气虚痰瘀证与ET-1、vWF呈正相关性(P<0.05),与NO呈负相关性(P<0.05),与LVEF无相关性(P>0.05)。提示ACS气虚痰瘀证病人存在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和血管收缩、舒张障碍,血浆NO分泌减少,vWF和ET-1水平分泌增加,导致血管舒张降低,血管收缩增强,血栓形成风险高于非气虚痰瘀证病人[17],与近年来研究[18-19]发现冠心病血瘀证存在高凝血结论一致。中医认为“血凝而不行”“凝血蕴里不散”,均说明血在脉中不能“如水之流”,存在血液流变性异常,推测冠心病气虚痰瘀证病人内皮细胞损伤严重,存在明显血液循环和微循环障碍。
综上所述,ACS不同中医证型病人存在不同的内皮功能损伤,vWF、ET-1与气虚痰瘀证呈正相关,NO与气虚痰瘀证呈负相关。内皮功能与证型二者相互结合,可在系统、细胞、分子水平上为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广泛和精确的依据。
[1] 陈伟伟,高润霖,刘力生,等.《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4》概要[J].中国循环杂志,2015,31(7):617-622.
[2] 沈卫峰,张奇,张瑞岩.2015年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诊断和治疗指南解析[J].国际心血管病杂志,2015,42(4):217-219.
[3] 高润霖.急性心肌梗死诊断和治疗指南[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1,29(12):9-24.
[4] 袁晋青,宋莹.《2015年中国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诊断及治疗指南》——更新要点解读[J].中国循环杂志,2016,31(4):318-320.
[5] 马礼刊,顾统元.内皮功能异常与冠状动脉疾病[J].心血管病学进展,2000,21(6):339- 342.
[6] 王东生,袁肇凯,李建玲,等.冠心病痰瘀病理临床研究[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27(2):109-111.
[7] 李俊哲,赵清武.广东地区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中医证候特征分析[J].中医学报.2014,29(8):1202-1204.
[8] Anderson JL,Adams CD,Antman EM,et al.ACC/AHA 2007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unstable angina/non-ST-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a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Task Force on Practice Guidelines (Committee on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Unstable Angina)[J].Jam Coll Cardiol,2007,50(7):e15-e17.
[9]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学会.冠心病中医辨证标准[J].中西医结合杂志,1991,11(5):257-259.
[10] 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281-285.
[11] Ross R.Atherosclerosis-an inflammatory disease[J].N Engl J Med,1999,340(2):115.
[12] Rider PM,Hennekens CH,Roitman-johnson B,et al.Plasma concentration of soluble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 1 and risks of futur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apparently healthy men[J].Lancet,1998,351(9096):88.
[13] Thomas H,Isabel O,Katharina K.Platelet glycoproteinⅡb /Ⅲa receptor blockade improves vascular nitric oxide bioavail 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J].Circulation,2003,108(5):536.
[14] Nakaki T,Nakayma M,Yamamoto R,et al.Endotheline mediated stimulation of DNA synthesis in vascular smooth muscle[J].Biochen Biophy Res Commum,2001,89(2):168.
[15] Hamilton CA,Brosnan MJ,McIntyre M,et al.Super-oxide excess in hypertension and aging:a common cause of endothelial dysfunction[J].Hypertension,2001,37(2):529-534.
[16] 王乐平,付海英.痰瘀与冠心病的关系探析及思考[J].中医药学刊,2006,24(1):41-42.
[17] 张继东,乔云,武传龙,等.冠心病患者胰岛素抵抗与中医辨证分型及纤溶系统活性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4,24(5):408-410.
[18] 王晓岚,于之敬,王晓洛,等.血小板α颗粒蛋白140与血瘀证[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9,5(5):27-28.
[19] 陈可冀,张之南,梁子钧,等.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368-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