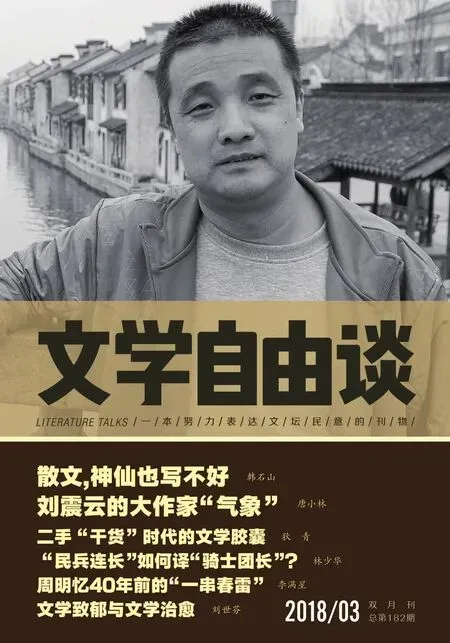我读《根河之恋》
李 更
大约10年前,我和一帮人去桂林。因为去过好多次,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阳朔泡西街,又因为不能喝酒,显得和周围格格不入。听说附近有个挺有名的地方叫龙脊梯田,颇为壮观,便自己找了去。
原来这里还是一处景点,只是更农家乐。旅游大巴只能到山底,当地为了赚钱,有专门的小巴送人上去。一层层转上去,梯田以前也看过不少,不觉得有什么新奇,一路打瞌睡。
到得山顶,还有山路,那时还没有痛风,一鼓作气,那些层层叠叠用木头石头搭建起来的房屋便让我欢喜。我特别喜欢这种完全是木头拼接的房屋,各种木头的气味,睡眠好了许多。
手机已经没有了信号,整个山寨安静得如世外桃源,只有一台老旧的电脑可以上网,而且速度极慢,所有上网者都像在排队等着出恭似地煎熬着。
那些占据了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老外,坐在窗口处淡定地看书,半天头也不抬。
让我惊异的是晚上。深一脚浅一脚,总是躲避不了那些狗屎牛粪,想去有灯光的地方找点消夜。忽然抬头,漫天的星星像天花一样向我洒落。“疑是银河落九天”,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有多久没有看见星星了?儿时的感觉一下出来了。下山来马上联系朋友,你多久没有看见星星了?对方一时也反应不过来,很久了吧。
原来中国的城市已经很难发现天空的星星了,尤其是大城市。城市的灯光,灿烂的夜景,已经把星星湮没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有多久没有进行纸媒阅读了,智能手机这几年已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我的阅读习惯。更有朋友直接说,手机已经让他们彻底告别了纸媒阅读。
除了对眼睛的伤害,那种碎片化、快餐化的手机阅读甚至快要改变我的思维能力。我好像已经习惯了段子式的接受,如果开头没有几句吸引人的噱头,我可能立刻就放弃此文的阅读,因为还有更加大量的文章需要我去消化。
不说中长篇小说,就是短篇小说我也有十几年没看了——如果说有看,那只是职业性地阅读。因为我还是个副刊编辑,味同嚼蜡的阅读是我的工作。
为了保护锐减的视力,我决定让阅读回到书本。
真是瞌睡遇到枕头,《根河之恋》出版了,给我带来轻松而享受的阅读。
回到书本阅读我是有条件的:一,熟人;二,大家;三,散文。
这本书居然都符合。作者叶梅不仅是我的老大姐,早在上世纪80年代,她就是湖北文坛的“大家姐”——大姐级的人物。大量的各种文体的写作,也早已让她成为文坛大家,至少是让我服气的大家。同时,她还是我文学青年时代仰慕的——按照今天的说法是——美女作家。
我在翻开这本书的第一时间,感觉就像看见星星。
果然是一本散文。在阅读之前我就知道,作为本书其中一篇的《根河之恋》,在2017年成为北京市高考试题。
我一直认为,文章成为教材是最好的传承方式,成为高考试题更加是放之天下而皆准的。在早年的机械性记忆中,课本无疑是一个民族语文最佳的示范,而且,孩童时期的记忆才是最有效最深刻最持久的。我喜欢类比,我学生时期记忆最鲜明的散文大家,就是课本提供的,杨朔、徐迟、碧野。读叶梅的散文,自然而然就想到这三位大家。
正能量,这是没说的。三位大家中,杨朔似乎更加根正苗红,散文中的红色经典的创造者。他的散文起承转合已经格式化,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套路”。这恰好是他发明的一个文本。中国人讲究仪式感,文本就是文章的仪式。不是谁都可以创造新的文本的。当年韩少功急于创造文本,还引发了一场官司。
在逐句逐篇的阅读中,我非常固执地觉得,叶梅的散文是对新中国散文传统最好的继承。她没有受到今天网络式杂乱无章的文字的任何影响,没有像博客、段子那样炫耀机巧,而是非常朴实,用最简单的文字词句去说明、描述,接地气。
同时,她也不拘于一种文本,没有字数限制,甚至,在散文里也有小说语言。有一段时间,为了在博客上吸引读者,我曾经研究了很久文章字数的问题,甚至得出“800字是考验读者阅读耐心的节点”的结论。但看了叶梅的散文,才觉得自己有些教条,随意、随心,才是为文之道。
最近几年,因为参加的笔会多了,和道友一起讨论最多的问题,居然是:采风后的文债怎么还?
大家都有这个让人头痛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一位诗人去北京开会,第一次坐上飞机,才发现云上世界那么美妙,他甚至因为看了两个小时的云,就写了一篇关于云的散文,居然被收入许多选本。他后来几乎成为专业的散文作家,其代表作就是那篇关于云的散文。
今天不可能再有这种事情了,如果有,一定会成为段子手的笑话。新鲜感,往往是启发文章的成因。后来这位散文作家真的走到哪写到哪。有诗人不服气,他们可以见什么就写什么,看见钢笔写钢笔,看见火柴写火柴,以此类推,没有什么不能写的,就像那些吃货,没有忌口。有诗人每天都可以写一首诗甚至几首诗。
但是真正要写得好,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湖北是个散文大省,湖北文坛,几乎人人都可以写散文,而且水平都不错。我一直是徐迟散文的粉丝,当年就是读他的散文来认识他去过的云南、巴黎等地方;后来经济条件容许,我甚至沿着他散文的描述去旅游。一直到高龄,徐迟也保持着对所到地方的高度新鲜感。在他写到的地方,出现一大批因他的写作而成长的作家群体,比如云南。他把云南的土地写得发烫,以至于有人读了他的散文后,云南就成为非去不可的地方。
那年鲁彦周来珠海度假,到寒舍写毛笔字,我就请教过他:那么多大家中,他的这种散文怎么特别少?要知道,在经常出访的作家中,他比别人更加方便,因为他还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领导,出访机会更多。他说,不是不想写,而是来不及消化,经常是前脚刚刚走完一个国家,想安静地写一篇,结果后脚又接到任务,马上去下一个国家。时间长了,就麻木了。
有一段时间,我专门在一些报刊上研究那些参加笔会的兄弟们怎么写出不同的感受。同时去一个地方,同时写一个地方,这就像读同一本书,然后写心得体会——命题作文啊!没有经过中国应试教育,没有经过科班培训,就是相当的大师,也叫苦不迭。
然则,课后作业也不能不做。当然有应付的,肯定也有认真的。我觉得这关乎一个文人的心态,更是一种做人准则。首先,不能有考试的恐惧,要预热,事前了解很重要,当然不是要你抄袭导游图。在过去,电影电视都不发达,你写散文可以从某地东经多少西经多少开始,光是描述性文字就可以单独成篇了,让没有去过的人随着你事无巨细的描写仿佛身临其境。现在微博微信什么都有了,你还敢抄导游图?
所以“走读类散文”最重要的是思想和语言。不骗你,我真的遇到不少陈奂生式的读后感,有人问他,《西游记》里面最厉害的是谁?孙悟空。为什么呢?妖怪都是他打死的!
没错啊,你能说陈奂生有什么问题吗?
许多去采风的作家,其实都是陈奂生。
你首先要有兴趣吧?然后,还应该感恩吧?要不,你去干什么啊?
就是体谅人的,也只不过是当二道贩子,就是剪刀加浆糊那种,拼拼凑凑完事。
珠海的横琴开发区曾经拿出重金,央某国家级杂志组织名家采访出专号。结果,大爷们吃了玩了拿了,然后拍拍屁股走了,许多人没有留下一个字,留下的也多是应付。当地作协只有找我这样的救场,可我至今没有喝到他们一口水。
其实我也能够理解,他们走马观花,能写什么东西呢?首先应该让作家们热爱去采访的地方,所以选择非常重要,不仅是地方选作家,作家也应该选地方。先小人后君子比先君子后小人礼貌得多。
但是,确实也有命题以后出了好文章的,比如任芙康,比如叶梅、赵玫。文坛中,“任说”,是一种专有名词,他的看法甚至流行基层,影响上层。他的说法,蕴含在其精劲短小的篇幅中,同样的采访,同样的地方,任芙康就是与众不同,甚至他的幽默,甚至他的谋篇造句。
读叶梅的散文,会觉得她是那种会一手女红的女子,细腻,真挚,她是会和你促膝谈心的。这一点,得缘于她曾经的农村基层工作。这是我特别敬佩的,因为有不少从家乡走出去的作家再也回不到自己的故乡。叶梅是真正从大山里走出去的作家,从恩施到武汉,从武汉到北京,走得越远,心贴故乡越近。她从来不否认自己来自哪里,从来不回避对家乡父老的帮助。年纪越大,越挂念自己的乡亲自己的民族。
这些年,她有意识地重访旧地,寻访新境,开始收脚印之作。她做得极其细致,极其耐心,每到之处,不仅进行资料收集整理,还有滋有味深入农家屋舍,在街边与当地人攀谈,直接询问了解土风民情,像一个邻家大姐。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叶梅的水墨画也十分到位,往往删繁就简,便春机盎然。我在工作室里挂了一幅。和那些专业画家、名家的作品比起来,诸多美术专业人士居然没有发现她的业余,说明她的水墨花鸟已经可圈可点了。散文里面,我更看重有美术美学功底的作品。叶梅的散文,文中有画面感,如果把那些段落拆开,会发现有的就是连句的诗。
其实读画也好,读文章也好,我从来不相信那些所谓专业的理论。那大多数恐怕是职业评论家的中药铺吧,他们随便抓几把,可以放进任何作品评论的罐子,顶多,就是多几次排列组合,多几个甲乙丙丁。
我觉得,好的绘画,就是你看了,自己也想画;好的文章,就是你读了,自己也想写。
读完《根河之恋》,我忽然发现,对以前去过的地方,也可以像叶梅大姐那样,把那些地方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