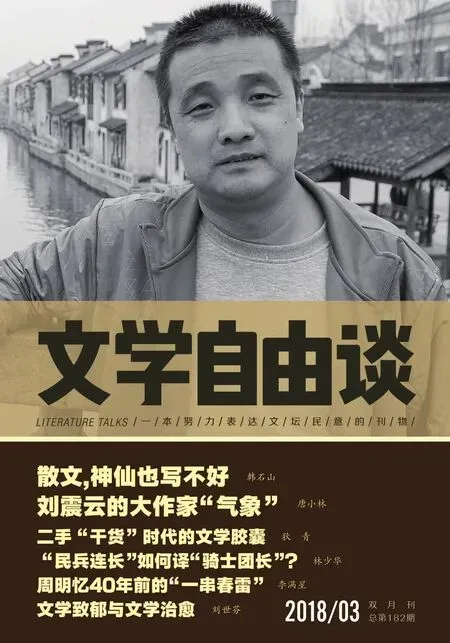忧乐斋随笔(四题)
耿春元
高 汤
少年时,喜读有“学问”的书。如果那书让我不住地查字典,那学问便大了。遇上些姿态炫耀、奇巧绚丽的句子,往往如私塾里的蒙童般摇头晃脑地咏读,还常常整段整段地抄录在本子上,放在枕边随时温习的。
书渐渐读得多了,才知道“中国文字的繁花似锦,最易迷惑勾引初学者”的。
鄙人所藏书籍数千册,如今能够放枕边温习的,算来不过三五本而已。其中便有一本汪曾祺先生的书。浅淡天真得儿童都能读的书,已经在枕边放了有许多年了。随手翻开哪一页,无论读过多少次的句子,再读依然有一种令人回味不尽的意味——
雨真大。下得屋顶上起烟,大雨点落在天井的积水里,砸出一个一个丁字泡。
雨打得荷花缸里的荷花东倒西歪。
一只乌龟,哈,下大雨,它出来了。昂起脑袋看雨,慢慢爬到天井的水里……
这是汪曾祺散文里的句子。
詹大胖子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
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每天还要写一张仿。村里都夸他写得好,很黑。
这是汪曾祺小说里的句子。
贾平凹说,汪是一文狐。王安忆说,汪老小说最好读。我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形容,只感到汪老这等大巧若拙的文字功夫,施展得何等彻底!
汪曾祺自己说:“修短相宜,浓淡适度,就可以无憾了。”
汪曾祺自己不知道,这话就是某些大师们,也不容易达到的高度!“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汪曾祺在引用庄子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很骄傲的。
读汪老,经常让我想起大厨做的高汤来。
高汤有多种。乌鸡甲鱼两样混炖较常见。炖高汤忌放葱姜等佐料的,以防夺味,但是必须加酒,以除荤腥。制做高汤需要许多道工序的,最后熬出来的是一碗明亮见底的清汤!
高汤的味道是极淡的,用“大味必淡”来形容高汤,再合适不过了。
吃高汤如读汪文,不是一般人能品出滋味来的。
那是美食家享有的口福!
孤独的甄如
四五十年前,在青州东关没有不知道甄如的。甄如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人”,老婆和一大堆孩子也都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供应粮,在东关他成了一个苦难的符号。为了养家糊口,甄如什么都干——修脚、掌鞋、骟驴、阉猪、刻字、修表、刻钢笔、卖老鼠药……数都数不过来。那年月做什么买卖都犯法,甄如只能干这等营生,他把智慧转化为一种生存的小技能了。
我年轻时曾在东关住过两三年,跟他一条街,见面就多了。甄如一表人才,即使穷困潦倒,也显得干净、优雅、阳刚、高贵。他的灵魂里没有自卑,像是从人生深处走来,大多数时间都在沉默,在思索。有时他也侃侃而谈,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甄如一街好人缘,却极少搭理我,我也极少搭理他。我们在用心灵交流,他有一种无形的魅力诱惑我,挟持我,让我不得安宁。
寒冬腊月,甄如穿得极单薄,瑟瑟地缩在墙根掌鞋。我站在他旁边很久很久,谁也不理谁。他知道我的存在,我知道他的存在,一街人都消失了,只有我们俩。这世间必然有一种无形的线,幽幽地牵在一个度上,让人互相沟通。总觉着他内心藏有一种精神,像珍珠,在蚌壳里。
他给人刻钢笔,都是毛主席诗词或语录,然后再刻上钢笔主人的名字。那天,我把我的钢笔递给他,他没有看我,匆匆刻上两行字,再用黄色蜡块一擦,送到我手上,是很古意的两行金色隶书。我眼前一亮,念出声来——
不是闲人闲不得
闲人不是等闲人
我看了他一眼,他看了我一眼,彼此心领神会,互相都懂了。然后递上一毛钱,他从容地收下;再找我两分钱,我也从容地收下,并不多说一句话。这时只感到他有一种最深邃的痛楚和难以言喻的隐忍在心里。他是孤独的,我感觉到了他的孤独。
终于有一天,他让整座小城吃了一惊。远方来人费尽周折找到了他,接着风传甄如是“大右派”!是1957年逃避批斗先逃往东北然后再逃回东关老家的。
他妻子毅然丢掉工作陪他一起奔上逃亡之路……她是一个好女人,但是,他值得她这样。如果是我,也会的。
远方来人是给甄如平反来了。这以后,我对东关人一直心存敬意。知根知底的人自然有,大家却守口如瓶:不然,就是逃过了1957年,也逃不过“文革”一劫的。
我想对甄如说,钢笔上的这两行字,我在《小窗幽记》里读到了。甄如会马上补充道:作者是陈继儒。陈继儒,号媚公,明朝人。
但是,很遗憾,甄如平反不久便谢世了。
我泪流满面。
写作秘笈
曾经听过刘知侠的文学讲座。想不到写出《铁道游击队》的著名作家口才却很一般。啰嗦,还有点口吃。也许“文革”后刚刚解放出来的缘故,一些话还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这就更觉无趣。就有一些人没听完便悄悄离去了。我是坚持到底的。因为刘知侠一开始就卖了个关子,说是他有个写作“秘笈”,讲到最后会告诉大家。那时我一心想当作家,听了这话自然高兴极了,说不定一旦得了那“秘笈”,这作家就成了。
听刘知侠讲了一天课。记得是在安丘的一家礼堂里。算起来已有三十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刘知侠的口才不仅不济,还实在没有讲出多少有新意的东西来,充其量是那个时代的老生常谈。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刘知侠。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全国高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指出:“50年代开始,文学中人性与人道主义被作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经过“一连串的批判运动之后,新中国文艺传统成了一片空白”。可想而知,从那个文艺荒漠中走出来的作家,你要求他们讲出点文学真谛,实在是强人所难。刘知侠那部《铁道游击队》,“文革”中在书店里都下了架,对文学,他还能讲些什么呢?令人欣喜的是,最后他果然郑重其事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他的“写作秘笈”——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小本子和一个铅笔头——大家都笑了。我却没有笑。若干年以后,就是这个“秘笈”,竟然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从那以后,我的口袋里也有了一个铅笔头和一个小本子,譬如一闪念的奇思异想、一种思想的突然开悟、一个细节的偶然捕捉、一位不识字的老头或老太的乡言村语……我的许多作品多是来自它们,而且绝少与人雷同。因为,它是生活特有的馈赠。
刘知侠先生是1991年去世的,享年74岁。
见到过许多作家,刘知侠先生格外让人怀念。
读 友
那天文友聚会,陈沛出了个题目:谈谈为什么要写作。大家都谈了,各有各的因由,兴致都很高。剑评最简单,只三个字:我喜欢!我也谈了。鄙人作文追求简约,说话却极啰嗦。说来说去,竟然不外剑评那三个字:我喜欢。首先喜欢读书,然后喜欢上写作的。曾经写过《我是一个发烧友》的小文,说的也不过这意思。
说着写作,不由想起几位读书的朋友来。
写作有文友,饮酒有酒友,旅游有驴友,因读书结交的朋友呢,我称作“读友”。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不幸被我们这辈人摊上了,却偏偏喜欢读书,可读的书却极少,还要冒风险。遇到一本好书,经常是你读完偷偷传给我,我读完偷偷递给他,像地下工作者传递情报。
那时候读书的目的非常纯粹,纯粹得令人感动。
后来有的读友渐渐读得少了,都忙呢,忙家庭,忙生计……不过有了一些书卷打底子,即使清贫,也不会丢了做人的身份的。
却有一位读友始终如一地读。已经大半辈子过去了,不改初衷。后来我的业余时间被写作占去了,就是读些书,多是为写作吸收“营养”的。他却不写。就是写,也是留给自己看的,从不示人。他仍然是纯粹的读书人。读书已是生命中必须的一部分,就像空气和水。
过去是不断见面的,见面自然谈读书。岁数大了,见面也少了,偶尔聚首,竟也不大谈读书了:闲闲地坐着,心已经交流了。
在他面前,经常自惭形秽。他读书,还喜欢旅游,国内国外都去,那游记是写得极好的。我说拿出来发表了吧,明知会被拒绝的,说了就后悔了。他是真正把世事参透了,在浮华人生中,已经望断了名利二字背后的虚无。
腹有万卷诗书,过着庸常人的日子,有着庸常人不可企及的人生境界:白水清风、冰雪聪颖、养性修身、淡泊宁静……说着他,已有阵阵书香袭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