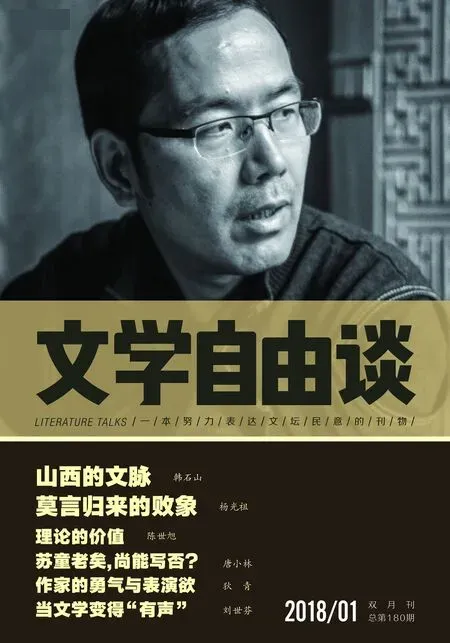《丙申故事集》里的集体“无能感”
宗 城
《丙申故事集》(弋舟著,中信出版集团)收录了《随园》《发声笛》《出警》《巨型鱼缸》《但求杯水》五篇小说,其中,《随园》是水准最高的一篇,也是我重点想谈的。从第一句起,弋舟就进入了自己的节奏,切入熟悉的人物。他擅长写师生关系,但假如全篇只写学院和启蒙,未免过于书斋。庆幸的是,弋舟没有这么做,仅仅过了一段,他就设置了一个陌生化的场景:
入校不久我就开始逃课,常常跑到城外的戈壁滩上眺望皑皑雪山。他从未陪我去过。但却是他告诉我的,“戈壁”原来是蒙古语。他还向我展示过一块白骨,也就一次性打火机那么大,让人难以判断到底出自躯干的哪个部位……
这是弋舟给“随园”开的玩笑。《随园》致敬何者,读者心知肚明,人们本以为:弋舟会写江浙地区才子佳人的事,但他颠倒了这种印象,他的随园建立在荒凉之中,如同一片历史的废墟。
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如今。它包含了一些大词,比如启蒙、历史、死亡等等,如何处理这些大词,这考验一位作者的功力。作者需要呈现出令人信服的现场感,在此基础上,他不能很大地书写,也不能妄下议论,否则即是僭越。弋舟的小说很克制,他切入的点恰到好处,《随园》由此成为一篇庄严的诗化小说。
《随园》是一篇典型的弋舟式小说,作者靠想象力和对词汇的咂摸来营造氛围。弋舟有丰富的生活素材做积累,可以靠强故事性推动小说。但他更多靠想象力。他是博尔赫斯一类的小说家,能够从人们忽略的词汇中打捞出别样滋味。《随园》的题目、用词乃至提及的书目,都有作者的用意,顺着它们,你就读到了《随园》背后的大历史,读到小说的话外之音。
小说的多处地方都有意在画面中建构历史感。比如“我躺着的这块儿地方,是祁连山的洪水冲击出来的”“可我觉得天荒地老,自己是被撂倒在一个亘古的意义上”等,表面上,小说的女主角置身于荒凉的戈壁,实则,她走在历史的废墟里,她自己又无法摆脱历史的逻辑。
弋舟有意提示读者,什么是被湮没的历史,是有待发现的历史。于是,“我”发现:“一部翻开的《子不语》扔在地板上,山风掀动着它黄色的书页。我过去把它捡了起来。结果它的下面还扔着一本《夹边沟记事》。”《夹边沟记事》是杨显惠的作品,书名提及的夹边沟,是甘肃酒泉的一个劳改农场,是共和国历史里一处充满了难言之隐的伤痛之地。弋舟此处绝非闲笔。
与被湮没的历史相对,是目力可见、冠冕堂皇的历史,它又和过去形成一种难堪的 “视而不见”。那个在戈壁滩上将“我”撂倒的尧乎儿,如今成为“真正的县领导”;那些启蒙别人的人,却成了被启蒙的对象;而我,“在本该青春飞扬的时候却迷恋累累的白骨”。
所以,《随园》不仅彰显了弋舟的创作技艺,也是他极具勇气的历史书写。古往今来,历史不仅仅由史家记录,小说家同样能参与到记录历史的过程中,《随园》是一次示范。
和《随园》相比,《出警》的历史感相对轻了一些,如果说《随园》很庄严,那么《出警》关注的则是世俗人物的琐碎生活。
《出警》是一部细致周到的小说,情节密实,转折精彩,应和了弋舟写作生涯的几个常用母题。弋舟对警察口吻的揣摩比较到位,许多对话画面感很强,如果再拓展些,完全可以拍成电影。《出警》值得反复品味的地方在于节奏和对话。和《随园》不同,《出警》靠的不是叙述,也不只是对意境的描摹,而是贴合人物身份的对话。在《出警》里,“重要的是说话本身”。
这篇小说与《丙申故事集》的另外三篇——《巨型鱼缸》《发声笛》和《但求杯水》共同指向了个体的中年危机。这里,有熬成处长的马政,有事业有成的刘奋成、王桐,也有生育后仍身材曼妙的“她”。但他们都郁郁寡欢,因为他们无论再怎么努力,都无法留住逝去的东西,他们最大的敌人是时间。
马政成为处长后更加压抑;刘奋成、王桐离婚收场;“她”通过少年寻找灵与肉的慰藉,却最终决定离开情人。他们仍要面对多数时间里的平庸,与青春和爱渐行渐远,最后走上孤独的方舟。
但是,这些人物孤独而不避世。他们在烟火里无法逃离。这就和人无法逃离自己的土地一样,哪怕肉身迁徙,灵魂仍有所羁绊——人们的一切爱恨悲喜都来源于脚下的土地。
纵观整部《丙申故事集》,小说的人物底色往往具有二重性——知识分子的气派和被“无能感”笼罩的中年人,一明一暗,交织于人物内心。看似书写边缘人,其实,支离破碎的环境里,每个普通人都是边缘人。弋舟在写集体的失落,在写一代人面对时代巨变而来不及调整后的精神危机,而这亦是70后作家普遍要面对的问题。
这些小说中的中年人也往往是“病人”,身体残缺,精神也在失调。弋舟不是医生,他只是感同身受,于是他要去写,写自己有关的“千千万万人”。在他的文本里,失落的人“可以和自己儿子的小提琴教师上床,可以让自己的手下去顶罪,可以利用别人内心的罅隙去布局勒索”。他们背负着一种罪过感。
但是,如果这种失落局限于个人的沉沦,被膨胀的申诉欲裹挟,它就容易变成自我怨艾的私语,而难以形成普世关切,徒留一场修饰明显的“低声哭泣”。庆幸的是,弋舟在《随园》等作品中做出了积极尝试,个人的境况与历史相结合,小说由此达到更广阔的境界。
人到中年,弋舟习惯一种自我审判式的书写。从《刘晓东》开始,他愈发关注“我之罪”,愈发敢于面对个人的懦弱与平庸。王小波曾说:“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凡人总是要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自我拼搏与历史进程的错位、个体意志与集体意志的矛盾,在所有矛盾的时时刻刻,人的无力感由此激起,无论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盖茨比,还是《老人与海》的渔夫,亦或是《随园》的老师与学生、《出警》的警察与犯人等,他们皆被“无能的愤怒”所包围。弋舟的小说看似高深,剑指的却是一个普通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即——认识你的无能。
这种写作转向与作者本人的境况有关。孩子、心脏病、追忆与凭吊、空巢老人等,弋舟开始更多关心死亡、历史、中年人,他曾关注空巢老人,也体察过城市青年的精神困境。在他的作品中,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孤独。他们渴求一份理解,但人间最难的事情就是感同身受。这只是孤独的表面原因,更深的,是这些人物踏在命运之船而无法走下,活在历史的逻辑里,看到灯火后的虚空,于是,他们被孤独感所笼罩。而这些孤独者最终还是要回到琐碎的生活,小说的文本也回到一个古老的命题,那就是生而为人,我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平庸。
弋舟在小说中对上世纪80年代的浪漫建构值得商榷。对知识分子而言,80年代是一个黄金时代,是五四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到了90年代,政治与经济的剧变让80年代的风潮骤然停歇,也让知识分子走向落寞。所以,知识分子对80年代有普遍的怀旧甚至美化情绪。只是,这种浪漫想象容易掩盖问题的复杂性,使小说局限于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
《丙申故事集》还有一些明显的缺憾,这尤其体现在《但求杯水》《发声笛》《巨型鱼缸》中。弋舟的写作如同精密仪器,他在结构和氛围的营造上格外小心,但他过重工笔,小说的人物有时会沦为推动情节的符号。在一些细节上,弋舟没有完全摆脱翻译腔式的拿腔拿调,对人事的形容词尚可斟酌。而在讲述“现实”上,弋舟时而显露的说教反而打破了小说的自然感。他控制过多,结尾过重“规整”,却也在造境上平添刻意,反而使小说少了一点如斑斓蝴蝶般的灵气。
在某种程度上,《丙申故事集》可以说是一位飞行家的例行表演,这还是那个我们熟悉的弋舟,照出他人到中年的写作质感。作为一名半路冒出的作家,他的路还远远没有尽头,假以时日,他可以写出更加精细的作品,而这,想必也是当代文坛希望见证的惊喜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