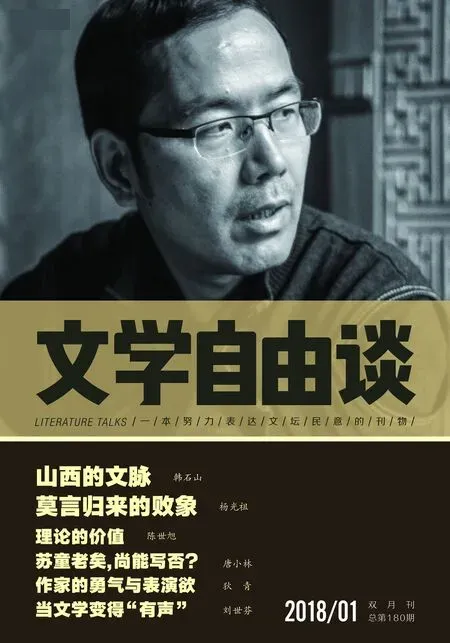当文学变得“有声”
刘世芬
半年来,我在“喜马拉雅”把《红楼梦》“听”了一遍,当即自创一个新词——有声文学。
喜马拉雅!显然,谁也不会OUT到以为我去地球屋脊的那座山峰去“听”《红楼梦》了。不听不知道,一听真奇妙!继阿尔法狗、“情趣”机器人以及各类“智能”之后,我这个自诩还有点儿阅读量的“读书人”,在阅读的缝隙,倏然瞧见一个不同凡响的世界:一夜之间,关于阅读,耳朵对眼睛已然宣战!
认识“喜马拉雅”,经历了一个有趣的过程。偶然的一天,朋友说她正在“听书”,我瞬间想象成听“评书”。她说:“你怎么像刚出土的啊?放眼望去,遍地都是播放器!连你自己的文章都多次进入声音了,还评书呢!”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发来一张图片,是一个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的白色方块儿,我叫不出名字,她告诉我那是飞利浦迷你小音箱,“我已在这上面听完《红楼梦》,正听《三国演义》呢。”我思忖着也要买那个魔幻小盒,她说大可不必,手机上随意下载APP……
我很快走进“喜马拉雅FM”——音频分享平台,顿时惊讶不已:文章除了印在纸上,还能变成声音——读了千年的书,此刻触网,书也能“听”了。传统的手持书卷的阅读画面,正在悄悄改变,小说、散文、诗歌……还能这样“发表”!还有什么比这更新奇的呢。
“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自鸿蒙开启,可怜且浪漫的古代文人,只能在勾栏瓦肆、烟花巷陌“发表”诗文。当然他们的“发表”除了各类“题壁”,口头朗读作为最佳途径成为“有声文学”的鼻祖。到了当代,又曾有评书的风靡,但评书依然古意横生,自出世就打上了“娱乐”的烙印,覆盖范围小得多。且看APP,由“喜马拉雅”,我又“结识”了一大波播放器:荔枝、蜻蜓、酷听、365读书……这些名字 “撩人”吧,只因后面加上了英文字母——FM(频率调制),摇身一变,已成为一款广播电台,像蘑菇般一夜之间冒出来,一下子就漫山遍野了。
自从有了FM,文学似乎再也难以在文化圈内“自娱自乐”,而是随着遍地开花的FM敲击着寻常百姓的耳鼓。客观上讲,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时间花在了交通上,微阅读、屏读热闹了几年,电子书已经深入人心,地铁、公交车、排队等候这些场景造就了几乎清一色的“低头族”。可是眼睛抗议了,车身摇摆不定,头晕目眩,特别是那些以电脑为业的年轻人,下班后眼睛仍不得闲——这就形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并被FM立即满足,先前寂寞的文学转化为“生产力”,一跃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直以为,人类发明的许多事物都有其实用性,但在诸多功用中,有一个是具有共性的——消灭寂寞。即使那些有钱有闲一族,也存在一个消遣问题。1934年,美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声读物,就源自于汽车。汽车文化成为“有声”的始作俑者——地广人稀,一个人上下班开车要走长长的路,“有声”成为最佳陪伴。这给出版商带来前所未有的灵感——以唱片形式出版语言教材,一个新兴产业就这样诞生了。从此,知识、讯息的获取方式变得多元化,新兴的数字化产品不断冲击传统的纸质报刊书籍,直接改变的就是大众的阅读习惯。
“有声”来到中国则是近些年的事。必须承认,“有声”有效整合了当下中国人的碎片时间。文字和视频都需要专门用眼睛看,但是“听”可以发生在眼睛被占用的场景中。于是中国式FM可就不那么“素”了,进入FM的大都经历了筛选、编辑,囊括文化、娱乐、生活、科技、时尚、财经……前不久,我参加一次主题宣讲,选题就是“新时代,新阅读”,一位女官员让我看她手机上自己开发的“主题APP”,并说正应用于本单位的知识竞赛,点击率火爆——实用的典范!事实上更多的FM还不止于“听”,在原来单向订阅、关注、收藏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社交元素:评论、点赞。
还是需求!人口红利嘛。
有一个现象,也是微信和FM的直接结果:许多以前只在纸媒和网络发表的作品,如今在发文字的同时,几乎都有音频同播。《文艺报》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个“今日主播”,分别邀请不同的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我听过蒋方舟、张楚、鲁敏、张莉等作家朗读自己的文章。此前只见过他们的照片,声音让他们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给人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作家本人也“立体”了许多。
随之“立体”的,还有APP本身。随着不断闯入“喜马拉雅”内更多的子频道,我发现里面绝不止一篇篇文章,而是把现实中的图书馆、杂志社、电视台、广播电台,更重要的是广告公司,统统“装”进去!了给我的感觉,文学,没有哪个时代能有眼下的“大繁荣”。
按理说,如此繁荣的文学带给我这么多便利,该心存感激才是。事实也是,我也曾对“有声”抱有“早晨八九点钟太阳”般的热情。可是从某天开始,我忽然觉得情况有点不妙,自己也不再像当初那般热络激动,而是审慎、警惕起来——FM露出的“杂音”,让我感觉不再“那么好”。
请注意上述文字里“有声”后面频繁出现的连缀词——“产业”“产品”。是否有这样的经验,某些事物,特别是文学,一旦“产业”起来,就有了不同的味道?有声文学说到底还是一种录音“产品”,无论何种录音方式,是产品就带有利润的属性。如今,每当打开熟悉的播放界面,耳朵需要承受几秒至十几秒不等的广告才能进入正式内容。飘浮的广告也越来越多,往往进入一个节目频道要跨越无数道广告的拦截。左冲右突地进入了,还要接受频道本身的广告,这重重广告使当初的听书打上深深的商业烙印:作为“行业”,有声文学不得不越来越“商业”。
下面这些本与文学无甚关联的字眼儿:利润、广告、成本、投入、价格走势、目标客户、风险、大数据分析、商业前景、市场发展趋势等经济术语,已经把“有声”重重绑架,成为类似某个房地产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文学,在其中的身份变得扑朔迷离,使人不知不觉间对它们的“感激之情”大打折扣——尽管我明白,灵魂产物与经济搭界,诱惑难免。
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听”到的并非都是美感。在《文艺报》“今日播报”里,并非所有作家的声音都令人愉悦。某些作家的声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嘶哑,怪异,更别提有的带着让人难以听懂的乡音。乡音的场合不对,极易让乡音之下的文字倒胃口,还不如保留点想象的空间。某文学馆要“出新”,将某位诗人的作品让作者本人用方言朗读放在微信公众号上,那声音听上去怪怪的,让好端端的作品变了味,反而伤害了文字本身。但主办者觉得这样就是出新了。
“有声”时代,我们究竟该如何读书?书,到底适合读,还是适合听?
在我“听书”的半年内,还真发现了许多“不适合”。
听书与读书,有着完全不同的心理和生理体验。我的个人经验,听书只能作为补充,真正的“书”是需要读的——特别是“纸质版”的书。纸质书和电子书,都可以控制阅读节奏,由读者决定细读还是浏览。但“听”就做不到了,即使反复听书,一样的语调节奏,会让人无暇思考,继而扼杀想象力。书,本来提供的是视觉,而不是听觉。阅读本就是一种耗费认知资源的事,需要我们把注意力高度集中,接收书里的知识信息,然后动脑加工、吸收。但人类的注意系统并非那么刚强,反复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声音上,催眠的作用就难免了,这也是林青霞把“蒋勋说红楼”当作“半颗安眠药”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阅读,无论是阅读习惯,还是阅读材料,本质上都针对的是视觉。即使视觉缺失,第一替补对象也是同样具有空间性的触觉(如盲文),而非听觉。
这个时代,有些事情往往来得大刀阔斧,有些东西仿佛悍然降临,一夜之间就打翻颜料瓶,改天换地。对于连缀“碎片时间”这件事,我是不太赞成那种“分秒必争”的。时间放在哪里自有其特殊的需要,比如我在健身时就选择什么都不听,运动就是运动,难得尽心融入自然,这时耳朵里不管播放什么声音,都是对这种美好状态的破坏。不知我们是否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误区中耽溺太久,总是害怕浪费时间,久而久之,难免心性散涣,忽略了品味和欣赏,而丧失的是个人的独立精神。余光中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忙出来的,唯独文化艺术是闲出来的。”时间、金钱、效率、生命,只适用于某些特定场合,未必适用于艺术。艺术需要时间的涵育、浸润。君不见,互联网的双刃剑效应就在于,许多观念在扁平世界迅速传播时,世界因而变得扰攘、快餐化。
读书的过程与人脑的劳动有点相似。今天人们对信息的处理,人的头脑与全球数据库连接,有问题上百度、Google成为习惯。云数据让人类彻底改变,跳过了原来的分析阶段,看似方便,实际上失去了头脑的训练过程,这与听书同理。如果过多使用“有声”,会不会导致阅读能力的下降,甚至剥夺阅读的能力?此外,也有专家提醒,过分依赖有声读物,严重的话还会造成一些听觉障碍,如幻听等。
文学的盛宴,只有耳朵是不够的。就像一桌宴席,本来各种维他命齐全,一旦“有声”起来,反而“饥馁”很多,许多对人体有益的营养元素流失,成了只剩脂肪而少营养的简餐。在这个问题上,我倒是希望把“听书”作为读书之余的有效补充。我个人的体会,“听书”比较适合听那些曾经读过的书,听的过程就是在拾漏补缺。就像我听《红楼梦》《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些巨著曾读过,再听一遍又收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文学的FM使文学迅速大众化。
某些时候,文学大众化并不是坏事,但大众化的另一种可能就是文学神圣感的减弱或消失,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就是——庸俗化。有权威统计,2016年最流行的文学FM是推理、惊悚、言情、奇幻小说。有时打开“有声读物”,与之相关联的,竟是一堆不甚洁净的信息:性爱、少女、夫妻等等与色情难脱干系的字眼儿,这更让我对“有声”的蔓延充满警惕。有一段时间,在我居住的小区,电梯口的“分众”屏幕整天打一款广告,那是一款学习点读机。新闻媒体曾披露,许多学习APP内的聊天内容不堪入目,可是,许多这样的学习APP早已“植入”了各类文学FM,它们的目标人群就是中小学生。在手机高度覆盖的今天,孩子们注定难以躲避。
那些远离色情的呢?就说“喜马拉雅”,我平时听的几部书都在这里。有一天,我听完一章,没再像往常那样关闭广告对话框,而是顺着这些广告点下去,发现营利依然是“有声”的第一选择。不仅如此,当我一步步沿着“言情”“悬疑”“都市”“魔幻”“武侠”一路浏览,发现这里应有尽有:儿童家教、相声评书、脱口秀、娱乐、英语、股市、旅游、汽车……如果点开某个链接,里面的细分名目繁多眼花缭乱,更有类似“少妇白洁”“和空姐同居的日子”“人生管理课”“空空道人的股市实战课”以及某大师讲《易经》等混杂其中,给人一种良莠同在、鱼龙混杂的印象。“酱缸”,大概就是这个了。
柏杨曾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名著虽进入“有声”,一些鸡汤式文字也很“励志”,但为了“利润”,大多数文章必须具备大众口味。郭德刚、高晓松、蒋方舟、吴晓波等人的节目,它要让人在学识、实用、启迪之外,再加一个——放松!这至关重要,哲思凝重的人和文章很难进入这里。想想现实,纯文学的愁云惨雾还不够让众人胆颤心惊吗?这时,谁若昂着头“拣遍寒枝不肯栖”,那只能被时代抛弃了。
我们不得不重新打量这个魔方般的世界了。开始时,“公号大咖”虔诚地为文学耕耘,到了后来名气越来越大,商家广告滚滚而来,抵御诱惑实属不易。再后来,文学越来越淡,喧宾夺主的事就难免了,办成了一个“公号托拉斯”。“有声”也越来越公司化,此间的文学,也越来越沦为一支羞答答的玫瑰——文学,真不容易!
纸质与有声之间,虽然都有一个“工业化”过程,但“有声”有其独特的制作流程,有市场的“可行性分析”,有利润预期和前景,很大程度上遵循的是商业原则,一切以市场效益为判断标准,简单地说就是要追求播放率、点击率。相比之下,纸质书刊还是更侧重文学性,至少其方向还是靠近纯文学。在读者选择纸质书时,有更多的自主性,基本上不带世俗功利目的,是一种纯精神性活动。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纸质书刊与有声读物的内在差异性。“有声”一方面提升了写作者的影响力、知名度以及作品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对于社会而言,“有声”又是一把不得不警惕的“双刃剑”,在收获了“市场”的同时极有可能“污染”文学本身。在文化体制、政策尚待完善的情况下,“有声”之后的文学如何保持不会泥沙俱下,是个问题。
2017年是有声文学标志性的一年,更多的人一边“有声”一边工作——“朗读者”真正成为产业,不成都不行。有声书正在变成出版商的大生意,许多出版商向朗读者、作者提供着极具诱惑力的报酬,《哈利·波特》、狄更斯、凡尔纳等作家作品因“有声”而获得另一份意外的版权和稿费收入。岂止作家,这个产业也拉动了一大批人来此就业——从朗读者到音频工程师,即,当机器人纷纷跟人类抢“饭碗”时,天无绝人之路,人类自己会创作更多新的工作机会。
只是,当文学变得“有声”,我们或许要在耳朵和眼睛之间做一番选择。作品被成功“有声”,是作家的荣幸,那么对听众呢?“被听”的感觉并非一律美妙,何况有时是被挟裹着成为“有声”消费者。这一消费过程中,就使得这个世界看上去很精彩,有时还有点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