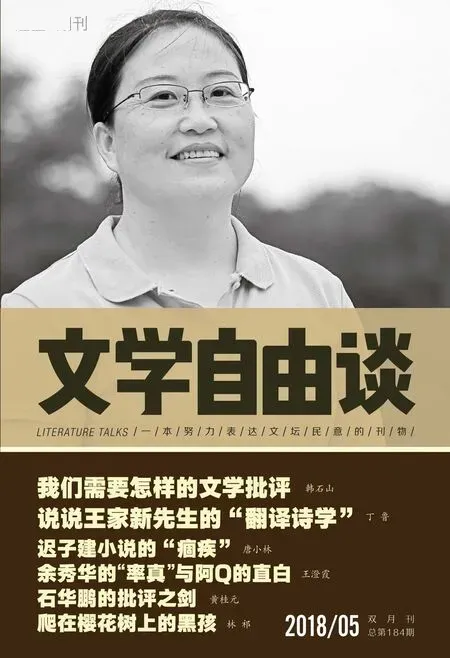女神萧红的“不着调”
侯德云
端木赐香的书,我读过的不下七八本,都读得缓慢且反复回味,唯有手边这本《悲咒如斯:萧红和她的时代》,读得极快,在7℃的高温里,两天半,读完。
读得这么快,有原因。其一,我对萧红非常熟悉。我读过(或精读或浏览)她的全集、十几种传记和三大册 《萧红研究七十年》,大约五百万字的作品。随着阅读的延伸,从2014年6月到015年6月间,我还写过三篇关于萧红的随笔——《萧红的真相》《〈呼兰河传〉:描摹故乡的“工笔画”》和《萧红为什么这样红》,总计四万三千字。因而我对萧红的某些“事迹”,可以匆匆掠过。其二,端木赐香的文字,很家常,像邻居家儿媳妇说话,张三长李四短,都以“人之常情”为游标卡尺去衡量,根除了学院派的晦涩,和以往的意识形态叙事也有本质区别,故而阅读进展迅速。“好诗不过近人情”,说得没错,其实好文章也一样。
我对读过的十几种萧红传记,大多不满意。不满意的所在,不是偶尔的细节失误,而是故意的形象虚构,能染色的地方都尽量染色,弄得该同志浑身上下红彤彤,光芒好几丈的样子。
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有句话:写作就是 “向陈词滥调作战”。我以为,端木赐香这本书的价值就在这里。她遮蔽了“斗争”“压迫”“反抗”等等暴戾视角,把萧红置放在“女儿性”“妻性”“母性”的显微镜下,展示了另一种让人目瞪口呆的事实。
这就好。这就值得砍倒几棵树,做成纸张,把显微镜下的情感萧红、性格萧红以及命运萧红,呈现在读者眼前。
萧红在我心中的地位,自2014年对她进行一番细心的“研究”之后,便一下子滑落谷底。无论是作为人,还是作为女人,用东北话说,我都觉得她特别“不着调”。
这里不妨借用阿·托尔斯泰的语式说句国产“名言”:着调的人都是相似的,不着调的人各有各的不着调。通过端木赐香的显微镜,我们来看看萧红到底不着调到何种程度。
其一,谁宠她谁是好人,反之是敌人。
谁最宠萧红呢?当然是她祖父。童年时代的萧红,是祖父的心头肉,想怎么便怎么。有这张保护伞罩着,萧红很快成长为整个张氏家族的“害虫”。她跟祖母作对,跟父亲作对(竟然说她爹不是亲爹),跟母亲作对,跟继母作对,跟舅舅作对,跟阻碍她任性和神经质的所有人作对。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说:“这世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果然天不怕地不怕。她因私奔以及与男人同居等等事因,弄得整个张氏家族颜面扫地:父亲被黑龙江省教育厅解除秘书一职,贬为巴彦县教育局督学;兄弟姐妹受不了舆论压力,纷纷转校离开呼兰县,到外地求学。
离家出走以后,萧红苦苦寻找人生中的另一位“祖父”。很幸运,还真让她找到了。这位“祖父”名叫鲁迅,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文坛泰斗。该“祖父”主要是在文学上宠着萧红。萧红把作品寄给他,他再推荐给杂志发表。萧红的中篇小说《麦场》,他先是推荐给大型期刊《文学》,审查未获通过;又转给《妇女生活》杂志,也未刊登。最后由他出资并写序,胡风写后记,改名《生死场》,自费出版。萧红的“成名作”就是这样出笼的。你说鲁迅是不是很宠她?
萧红曾经跟老友李洁吾谈论鲁迅。李说鲁迅待她像慈父一样,萧红立即反驳:“不对!应当像祖父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父亲!”
其二,换男人跟换水杯似的。
萧红短短一生中,或者这么说吧,从1930年离家出走到942年1月在香港去世,十一二年时间里,亲密接触过的男人至少四位:表哥陆哲舜,未婚夫汪恩甲,作家萧军,作家端木蕻良。此外还有两位“疑似病例”——老朋友李洁吾和新朋友骆宾基。
关于陆哲舜,以往的叙事都说得委婉,什么同住一院、对外以甥舅相称等等,毕竟当事人萧红没直接承认那啥,大家也都心照不宣地跟她一起委婉。端木赐香却说得果断:私奔加同居。严格说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汪恩甲与萧红的关系颇为复杂,两人经历了以下几个回合的纠葛:订婚,抗婚;同居,闹掰;再同居,又闹掰;再再同居,直到汪永远消失。
萧军和端木蕻良没啥好说,萧红自己都说了又说嘛。
李洁吾这人,据端木赐香考证,早在1930年之前就认识萧红并发生恋情,或者关系更深一步也有可能。
骆宾基很诡异。有迹象表明,他跟萧红的关系非同小可。
此外,萧红对萧军的朋友方未艾有过多次挑逗,还经常“含情”注视聂绀弩。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是萧红的情感生活常态。
是不是有点乱?确实乱。人家奉行五四之后从苏俄进口的爱情“杯水主义”,今朝有情今朝爱,明朝无情便走开。哪个杯子不能喝水啊。
方未艾对“杯水主义”有异议,萧红说他“真封建”!
其三,把抱怨当流行歌曲来唱了。
读萧红的文章和书信,你会读到很多抱怨。不知是谁赋予的权力,反正我们都看得到:萧红可以说“不”。我这个在红旗下长大的乡下人,对她被“黑暗的旧社会”所团团包裹的童年,竟然羡慕得要命:占地七千平方米的大宅,占地两千平方米的后花园,即便在当代乡村,也是土豪级别,加上祖父的溺爱,你萧红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可人家偏偏就是不满意,说什么寂寞啊寂寞,弄得茅盾也跟着说“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
“寂寞”是萧红的口头禅。散文《搬家》:“多么无趣,多么寂寞的家呀!我好像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且隔绝。”散文《他的上唇挂霜了》:“好寂寞的,好荒凉的家呀!”
萧红在日本也寂寞,不光寂寞,连窗外的风雨,室内的一只苍蝇,被蚊子咬一口,都要写信跟萧军抱怨一通。在北京似乎更寂寞。萧红从日本归国不久去了北京,写信给萧军:“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还说什么“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读萧红在日本期间写给萧军的信,读得老夫一阵阵心堵,心说这女人怎么这样啊。我就纳闷,如此这般一堆堆垃圾倒下来,萧军是如何承受的?端木蕻良又是如何承受的?换了我这种凡夫俗子,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大概还承受得下来;要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哼,瞧好吧,非给她一个“胶带”不可。
史料显示,萧红说话语速很快,要是当面跟你吵,“圆形小嘴”(萧军语)整天嘎嘣嘎嘣,无理也要取闹,别说萧军那样匪气十足的男人受不了,就是老夫这样的乡下孬种也绝对受不了。在上海期间萧军揍过她,原因在此。
其四,住谁家谁烦,不住也烦。
在哈尔滨,萧红一度住进《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家里,萧军每天都去看她。两个人,嗨,动手动脚,呼呼嗨嗨,弄得主妇很烦。裴夫人曾经暗示萧红该搬出去了,可萧红就是不走。裴夫人没辙,自己走了。你走俺也不走。裴夫人一横心,把被子褥子都拿走,留给二萧一个光溜溜的土炕。光溜溜就光溜溜,继续动手动脚呼呼嗨嗨。直到萧红生孩子,才不得不离开裴家。
在北京,住李洁吾家,弄得李妻撂了孩子躲出去,两口子间火星子乱灿。
在重庆,住白朗夫妇家。萧红暴躁易怒,常跟白朗发火,跟白朗的婆婆也发火,让白朗好生为难。(之前在上海,白朗罗烽夫妇投奔二萧,在二萧家住过一段时间,后被萧红找借口撵走,加上别的事端,双方几乎绝交。)可笑的是,萧红生完孩子,竟然还想住到白朗家,被拒绝后才回到端木蕻良身边。我以为拒绝是对的,再不拒绝,白朗家的生活秩序必定会遭到进一步破坏。
在上海,倒是没到鲁迅家里住,但在鲁迅生病期间,萧红天天去,无外乎是倾诉她痛苦啊寂寞啊,啊啊啊。许广平既要照顾病人,又要陪她,整天手忙脚乱,曾跟胡风的夫人梅志大倒苦水:没地方去就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除了以上四条,还有没有五六七八呢?当然有。比如不存天理只存私欲,对亲生儿女,一个送人,一个“对于这个婴儿之死的推断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季红真语);比如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用你时千方百计找到你缠住你,不用你就不辞而别;比如擅长使用道德绑架手法,让你觉得不帮她就不是中国人,或者是对不起“作家”称号;再比如胡闹到“脑残”程度,把办丧事用的纸花挂到自家窗口,直到褪色才扔掉,等等。但我已经把自己说得很烦很烦,不想再说了。读者若有兴趣,不妨买一本端木赐香的书来看,各种详细各种精彩都蕴含其中。
抛开萧红的不着调不谈,端木赐香在书中的议论,也常常点亮老夫的眼球。她的“吃左奶右奶论”,一下子打通了我对晚清、民国到如今的思想淤堵,让我兴奋得嘴角湿润。她的“男人进球论”,又让我进而想到,除了职业球员,作为男人,最大的生活智慧应该是学会如何盘球过人,而不是胡乱进球;萧军和端木蕻良就是反面例子。这是历史经验,不可不察。
端木赐香认为,萧红悲剧的终极原因是“心智的不成熟与性格的内在冲突”,并分析说:“在原则问题上,比如婚姻、性爱、男人、读书等重大问题上,她粗枝大叶,不管不顾,任着性子,夜半临深池、盲人骑瞎马一般乱冲乱撞,可是对深池的水温高低、瞎马的毛皮软硬,她又有着极致的要求。”没错没错,是这样,我对这观点和分析,都毫无异议。
纵览全书,我稍稍感到遗憾的是,端木赐香的笔墨没有彰显萧红对端木蕻良的深度伤害,以及端木蕻良对萧红的帮扶层面。在《萧红的真相》一文中,我最大的感叹,便是萧红对端木蕻良的无情。它集中体现在萧红生命中最后四十多天跟骆宾基之间的唧唧咕咕,并经过骆宾基的笔和口,将端木蕻良的“污点”泼得到处都是。有些传记作者据此断言,萧红跟端木蕻良一起生活的那几年,是萧红一生最暗淡的时光。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觉得那是萧红一生中最荣耀的章节。这个把写作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的女人,无论就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来说,这几年都是她最为重要的年份。说萧军是萧红在文学上的第一节梯子,鲁迅是第二节,那么端木蕻良肯定是第三节,也是最重要的一节。仅以在香港的最后两年为例,在端木蕻良的帮扶下,萧红接连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以及散文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被后人称作是萧红“巅峰之作”的《呼兰河传》,先在《星岛日报》连载,后出单行本。长篇小说《马伯乐》第一部出版,第二部在《时代批评》杂志连载。如果真的“最暗淡”,你相信萧红在短时间内会有这么多作品问世么?
作为史学中人,端木赐香刻意回避了对萧红的文学评价。我对这回避持默许态度。而我作为文学中人,对此却不能不正视。还是《萧红的真相》中那段话:“在我看来,萧红只是一个‘很有天赋’却没来得及把天赋完全发挥出来的作家,或者说是‘可以有成就’却没来得及有成就的作家,她永远停留在一个成熟作家的早期作品’阶段。以文学高度论,萧红是一棵小树,是比她自己的身高还要矮一些的小树。”
此外我还想说,一度泛滥成灾的对萧红人与文的“女神”化,以及至今还常常抱团取暖的众多“粉红”的存在,除了当年那些主流话语”的影响、能量巨大的幕后推手、名利心作怪等元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便是鲁迅对孙伏园说过的话:“不满,往往刻画得易近于谴责;同情,又往往描写得易流于推崇。”对,是同情。萧红芳华早逝,催生无数眼泪。这眼泪中有很多都转化为钻石,把萧红打扮得异常炫目。因此我有预感,端木赐香的这本书,很可能会激起“粉红”们的强烈反弹,甚至爆发口水战也说不定。你把人家心中的“女神”给“妖魔化”了,人家不喷你喷谁呢?
我很欣赏端木赐香在《后记》中的内心独白:“对文艺来讲,文艺固是全部,但对人生来讲,文艺只是点心,吃多了心沉。诗和远方固然美丽,但心神不安,诗和远方不外是漂泊。谨望我的这种棒喝,对当下文艺男女的幸福人生能有所启迪。”我的理解,这是一个学术中人对文艺男女的悲悯情怀。这情怀可敬可佩。很多人都知道,萧红的情感、性格和命运,并没有远离尘世驾鹤西游,它们至今还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重播。对于那些活生生的萧红而言,这本书无疑是一座警钟。它似乎来得太晚。但它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