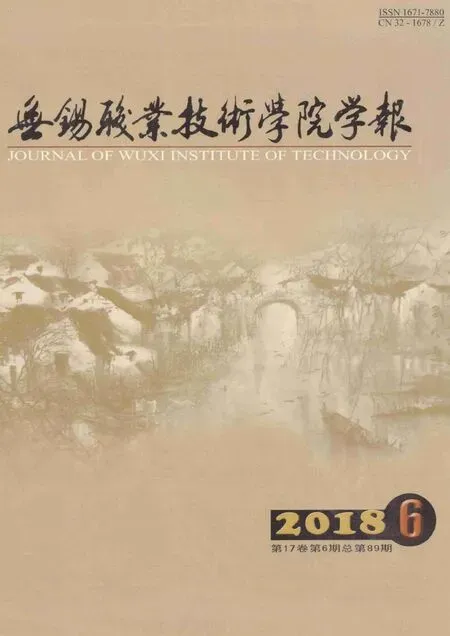诗性与人性的同构: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叙事空间解读
付元红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信息部,山东 济南 250013)
在对一部作品进行叙事学角度的解读时,除了从叙事的语法、叙事时间、叙事情境和叙事的声音外,还会涉及叙事的空间性问题。与时间的一维性相比,空间是三维性的,但对文学作品来讲,作为一种文字艺术,叙事的空间性不是直观的,他其实是作者讲述故事时的及故事文本中的空间地理位置。黄强说:“我们界定的空间感显然并不仅仅包括空间上的知觉,他还综合了想象、记忆、习俗传统培养起来的习惯、特别是生产方式所规定的空间经历而形成的空间体验。”[1]这便是文学中常说的“地域”。涉及作者的身份认同,作者在讲故事时总要受到地域色彩的影响,他总要站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进行叙事,从而形成与他者在其他地域进行叙事时的不同点。另外,文本叙事作为一个故事的讲述过程,总要落实在一定的地域上,使故事有一个发生的环境背景,让故事中的人在这个空间中进行言说,来传达出叙事人的独特的叙事目的。现代作家沈从文在他的小说叙事中,钟情于他所出生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湘西,通过勾画出诗性与人性同构的“湘西世界”,呈现出独特的空间特征。从叙事的空间角度解析,是一种诗性与人性的共同建构,通过对自然美与民俗美的礼赞,来凸显田园牧歌式的诗性特色。
1 诗性:田园牧歌式的空间呈现
运用原型批评的概念来审视沈从文的作品时,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湘西地域作为一种原型和沈从文的叙事乡土世界发生着十分亲密的融合关系。原型(Archetype)在柏拉图那里指事物的理念本原,荣格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其重新阐释与再造,来指隐藏在人们集体无意识之后的思想本原。由于沈从文生于湘西,受中国楚文化的影响极大,某些湘西的民间原型包括文化艺术原型(如传说原型、故事原型、戏曲原型等)、民间的生活原型、风俗原型、信仰原型、环境原型等,都对他的文本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按照自我设定的心灵时空而进行的情感投注,使他的叙事具有特定的空间特征,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沈从文小说叙事空间有时是显性的叙事空间,他成为叙事中的诗意所附着的主要凭借;有时是隐性的叙事空间,他承纳了叙事者的精神依托。通过辨析现实精神气候与小说精神气候的异同,可从中找出其地域性的叙事空间的变化形态。通过从湘西这个乡村社会中剥离出来的沈从文所建构的诗性的理想社会的透视,可体会出这个叙事空间的独特性。在这个空间里,可审视到沈从文叙事时田园牧歌式的诗性世界。“属于沈从文小说的独特诗性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诗性,是生命存在的诗性。”[2]湘西对楚文化的保留是极为完好的,在这里成长起来的沈从文,他的“本我”中充满了楚文化的影响,从而构建了独特的、诗性的叙事空间。
沈从文小说叙事的最突出的成就是他那细腻的笔触、清丽流畅的文字以及蕴涵于其中的真挚情怀。经过他的精心描绘,沅水两岸灵秀的风光和湘西人民独特的世态人情水乳交融,同时具有了一种田园的诗意。作者对湘西地区自然风光的描绘,倾注了作家的整个身心,更增添了对苗民地区美好人性进行赞扬的环境底蕴。“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3]从作者所用的叙事话语来看,他所建构的世界是一种和谐、宁谧的“桃花源”,极具田园特色,充满和缓的诗性与灵动。
在沈从文的叙事作品中所呈现的诗性的空间里,他以对自然的钟爱,使他所描绘的情与景具有一种“纯粹的诗”的“美”。《看虹录》中写道:“百合花颈弱而秀,你的颈肩和它十分相似。长颈托着那个美丽头颅微向后仰。灯光照到那个白白的额部时,正如一朵百合花欲开未开……微笑时你是开放的百合花,有生命在活跃流动。你沉默,在沉默中更见出高贵。你长眉微蹙,无所自主时,在轻颦薄媚中所增加的鲜艳,恰恰如浅碧色百合花带上一个小小黄蕊,一片小墨斑。”[4]“百合花”是一种优雅神情的象征,沈从文在文中赋予了它一种抽象的美,来象征高贵的生命的意义,通过构建自己心中的“人性小庙”与污浊的都市来抗衡,从而达到一种“用理性空间抗衡现实空间”的理想境界。
作为一名出身边地的作家,沈从文毫不隐讳他的写作倾向性,他所倡导的是自然的人性,认同的是自然意义上的人,在他的小说叙事中,他以“艺术性和审美性,装饰着人类心灵千百年”[5]。沈从文笔下的自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神性的存在,是人与大自然的共存、和谐与统一。如在《边城》中,作品整个儿仿佛一幅水墨山水画,来展现这个湘西边陲地带的人情美、人性美、风景美。沈从文的叙事语言如流水般鲜活,以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表述手法描述了这里的自然风景之美,并折射出人物的心理活动。这里的一切都按照自然的方式在发展,翠翠的祖父无名无姓,便直名曰祖父,翠翠之名,也得于自然,不但“翠色逼人”,而且具有人性的善与美,正如那满山的翠绿。在《夫妇》《阿黑小史》《雨后》《月下小景》中反复出现的野花这一意象,也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诠释着生命的鲜活,粗野,枯萎与毁灭。《野店》中的一声野性的呼唤,《渔》中的悄无声息地流动的乌鸡河等,更是贴近这种生命的自然与本真。在这里,叙事人给我们勾勒的,是亦真亦幻的奇美湘西世界和淳良厚朴的本真人性状态,是“人性善的杰作”,是对世外桃源的重构。
沈从文的田园式叙事空间里,颇多对民俗的摹写,通过对湘西地区民俗的重现,来建立作家田园牧歌的支撑点。民俗是各民族和各地区人民文化生活、精神状态、思想品格上的一些共同特征。沈从文的湘西叙事正是反映了这一特征,表现出对湘西地区的独特青睐。民俗作为作家创作的集体无意识和现实创作来源,使得沈从文的湘西叙事的作品有着诗性与人性的合一,从而使沈从文的叙事作品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沈从文从十四岁就开始在沅水流域漂流闯荡,他对湘西的山水草木、风俗人情更是体会颇深,并能够深切认识到湘西地区民俗的特殊性。沈从文在叙事作品中不止一次地称自己是“乡巴佬”,正是这种“乡巴佬”的执著,使湘西沅水的神韵融化在他的血液中,形成了他特有的性格及叙事偏好,正是这种“乡巴佬”的纯情,才使他写出了充满风俗味的作品。
民俗“反映着集体的和社会的人群意愿”[6],也许正因为如此,沈从文对民俗的描写,已经成为他叙事的因子。如在《边城》中作家对湘西端午节赛龙舟的风俗描写,从那些振奋人心的场景,可以看出这里古老而健康的风俗,可以感觉出湘西人民粗犷放达的性格和心理。而小说《雪晴》则给我们描绘了湘西一带的婚嫁民俗,充满了极善、极真与极美,充满了田园式的牧歌情趣。当我们对沈从文叙事的空间特色进行审美观照时,会深切感受到,作为一位来自于湘西民间的作家,沈从文的文学的根是深深扎在湘西这块土壤上的,也是扎根在湘西古老的文化传统中的,其叙事空间环境带有地方特有的色彩与气息。
2 人性:重振民族精神的基点
在湘西这块神秘的土地上,苗蛮民族不惜以血的代价在这样一个封闭落后的边陲之地创造着、生存着,在他们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了楚风中的善良与野蛮、粗犷与彪悍的特点。在这块闭塞的土地上,远离都市文明的侵蚀,独自保留着一份野性。沈从文正是从这块土地上,发现了蒙昧中的人性的闪光点。这里的民风淳朴而野蛮,形成了叙事人独特的叙事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作家发掘出了“人性”这一瑰宝,并将其作为与城市相对抗的堡垒,作家在这里找到了重振民族精神的基点。在这里,有他的童年回忆,有他的苗族乡亲讲述的民间故事,有他在乡下行军途中或江湖漂泊时所遇到过的种种经历,也有街头巷尾的谈话及乡里小儿的对骂等。沈从文正是根据这些湘西生活的素材,给我们刻画出了丰满而生动的形象,并从其中发掘出了美好的人性,独具叙事的个性化色彩。
从某种程度上讲,沈从文的叙事文本中同时具备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叙事语境,体现为他的小说叙事往往设置了一个“无限的传奇时间”[7],引导人们完成对人生的感悟。“现代性语境是从他人身上感知人,而后现代性语境则是从自然身上感知人”,以《边城》为例,其中所描绘的淳朴的民风,就是一种人的自在生命的体现。老船夫一生为人摆渡,过往行人心中感激,要付钱,而老船夫说:“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你这个!”这里的人性之美与人情之美跃然纸上。当我们对沈从文所塑造的时空体进行感知时,会感受到,在那种近乎凝滞的时间下,作家好似用了影视中的定格手法,为我们展现了这里的独特空间特色。
沈从文常常写到乡下人的活动,他的小说中有店老板、船总顺顺等,这都是作家着力刻画的人物。他把这些乡下人写得有声有色,把湘西风光和水上生活精雕细刻,书写了这一叙事空间下醇美的乡土情怀。在沅水这条河流上,沈从文还特意从社会竞争的角度来淡化社会对抗的程度,来突显这一地区尚武的传统本色。他写船民在迎战飞瀑时无所畏惧,写在《边城》中二老傩送的豪情等。总之,沈从文对这里的一人一物,一草一木都投入了浓浓的审美情感。沈从文主张人性即自然,在其湘西世界中,他一直固守着人性的本原。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曾描写这里的山里人常常拿了刀叉火器,用绳网捕捉大蛇,打鼓敲锣来猎杀野猪等等。在湘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我们好像又看见了一幅年代久远的狩猎图,人类还在与虎狼猪豹的搏斗中去争取自己的生存权。这里的水手们也是不论严寒与酷暑,从天明做到天黑,当拉纤时,即使需要爬着行走,也是毫不推辞。这里的人的人生态度总起来说是“不卑不贱,雄强进取”。在沈从文看来,他们的行为“比起风雅人来也实在道德得多”[8]。
沈从文为了给他笔下优美的叙事空间添上一道美丽的人生亮色,他的叙事空间中活动这一位位纯情漂亮而又懵懂的湘西少女,如翠翠、萧萧等,在她们身上,寄托了作家“人性即美”的思想主张,在他的“人性小庙”中增添了一份清纯与柔性。如《长河》里的夭夭对客人说:“你们想吃就吃!口渴了自己爬上树去摘,能吃多少吃多少,不用把钱。你看(夭夭把手由左到右画了个半圆圈),多大一片橘子园,全是我家的。今年结了好多好多!”在这段对话里,夭夭活泼、天真而又善良的性格十分明显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她与橘子园那清爽、静美的景物相对映,可以说是沈从文“诗性与人性世界”的代言人。《边城》中的翠翠也是美丽善良。通过沈从文的叙事文本,我们可以解读出,他把梦想与现实放在同样的立脚点,但由于现实世界的人心隔膜,他只能通过文字来期待与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
沈从文以乡土为题材的创作中,《边城》《长河》《龙朱》《神巫之爱》《月下小景》《阿黑小史》等,这些都组成了沈从文叙事中一种生命神性的庄严,沈从文从中领悟到了“健康雄强的生命跳跃”。《边城》《月下小景》等所展示的都是人的生命的存在状态。“他跳脱出以人为主体去看待世界的范围,用陌生化的眼光,融合自己的感受去发现人们未曾发现的,却已经存在的风景,并重新赋予他们价值。”[9]他的“人性神庙”与自然紧密结合,耐得风雨与寂寞,具有某种永恒的味道。在这里,尽管生存环境恶劣,但生活的激情仍存在于傩舞中,存在于赛龙舟的冲刺中,存在于火辣辣的情歌中……在这个世界中,沈从文建造了一座希腊小庙,来供奉着“美在生命”的人性,并将其作为亚里士多德所言的“撬动地球的支点”,试图重振萎顿的民族精神。
3 位移:都市与乡土的对比与反观
沈从文依托湘西地域所建构的诗性与人性同构的叙事空间,是相对于都市的世外桃源,作家对湘西的吟诵,是一曲悠悠的田园牧歌,是以都市人生作为参照下的对乡村生命形式的探索。他对乡村世界的叙写,全部都是对都市人生思考的反拨。当沈从文进入都市后,当作家经由了由乡村到都市的位移后,便在思想深处进行了都市与乡土的对比与反观,以所描写的空间的诗性与人性来与都市的污浊相抗衡。“这就促使沈从文在创作都市小说时,选择了人性的视角,并且形成了两种鲜明对比的空间——以苗文化为主的湘西世界和以汉文化为主的都市世界。”[10]他的叙事能够一直保持对本真人性的体验,对城市文化有一种独特的反思,从而呈现出独特的叙事时空体模式。沈从文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中,很多都穿插着对都市文明的批判,他笔下的都市生存空间,在整体上也与他笔下的湘西世界对立。沈从文站在乡下人的视角对城市生活的荒谬进行审视,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人性失落的天地。在《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烟斗》《大小阮》等一系列作品中,沈从文以讽刺的笔触,抓住都市上流社会的言行不一、表里不一,从不同侧面揭露都市现代文明的虚伪、自私、怯懦、庸俗,贯穿这些作品的始终如一的线索是人的本质的失落,人性对自然的违反。
当然,作家笔下的边城等湘西地域,仍然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初级社会形态,广大农民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原始而又封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市“现代文明”开展侵入湘西地域,从而造成不同文化状态在湘西这一区域的相互撞击。在《萧萧》《丈夫》等叙事文本中所展示出来的,不仅有这里的人们的善良与纯朴,还有他们主体精神的蒙昧。从《船上岸上》《夫妇》《阿黑小史》等小说中也会清晰地读出其中封闭、保守、愚昧、落后的乡村现实。另外,湘西地域的民族性也有凶狠、野蛮等特点。但是朴素人情美、人性美与自然美使作家总在有意无意中回避现实。沈从文对自己的乡土充满原谅之情,“人生可悯”,作家只能借助湘西这个叙事空间来回避痛苦、强化美好。在作者看来,《凤子》《边城》等小说中描写的勇武好斗等,一旦到了全中国被指认为积弱不振的关头,便会成为一股原始力量,来激活民族的活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沈从文在湘西这块土地上宣扬这些人物,意在认为家乡的希望在这些勇敢而有理想的年轻人身上。沈从文并不把这些人的鲁莽看成暴力,他从中看出的是这些人的生机勃勃的活力,是遇到困难时百折不挠的意志。
历史创痛和现实焦虑使作家胸中充满了沉重的乡土悲悯情怀,也蕴涵着沈从文深长的历史感悟和民族悲悯。这种忧郁和悲悯也从沈从文所营造的意境中幽幽地散发了出来。因而,在沈从文笔下诗性与人性合一的湘西世界也时常透出某种淡淡的忧郁与感伤的气息。与乡土大师鲁迅的冷峻相比,沈从文的个性气质更多包含着自然孕化出的宽厚与从容,他主要从“善”的角度写作,重在对完美人性的颂扬。沈从文在湘西世界中呈现出的独立不群的叙事空间,是乡土特色与牧歌风味的融合,是诗性与人性的同构,是地理位移与文化位移后对都市与乡土的反观,是作家重振民族精神的基点。沈从文的小说世界建构的叙事空间实际上融合了鲁迅风的乡土叙事和废名式田园叙事,拓展出更独特的诗性与人性合一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