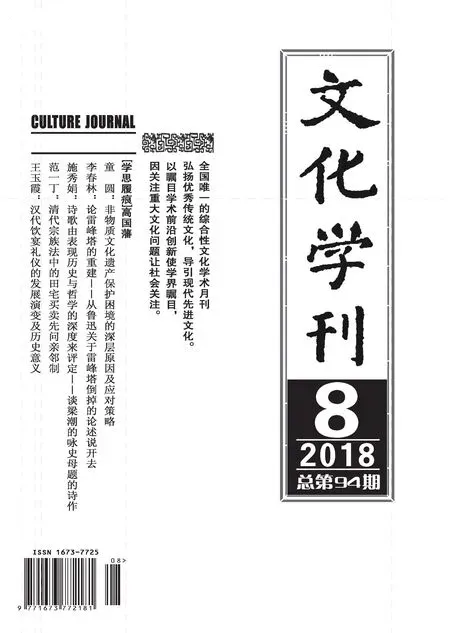魏晋玄学对儒学的继承及发展
于冠琳
(西南大学含弘学院,重庆 400715)
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儒家思想因其对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本质的充分适应而成为最有利于统治阶级推行统治教化的思想[1],其传承和发展在中国哲学源流中从未间断过,在各个时代一脉相承,但都有其针对时代特点的不同表达形式,而在魏晋时期,儒学这一主流正统思想便在一个分支上特化成了糅合道家特质的玄学,并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思想。
一、玄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魏晋玄学家的儒学背景
从汉武帝始,儒学经董仲舒为适应统治阶级需要而改造后成为了官方哲学,并在教化、选官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充分实践,牢固确立了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但儒学在被统治阶级使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僵化,特别表现在名教思想上的僵化。魏晋时期战乱频繁,统治者不断在名教的外衣下做出有悖伦常的事,传统儒家的价值观被当成了统治者掩饰自己对利益追求的工具。[2]
这时出现的玄学家大多具有世家大族的家庭背景,在小农经济中属于地主阶级,为适应魏晋的门阀士族政治,在幼年时期必须接受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因此他们本身具备极高的儒学素养。幼年时期的熏陶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玄学家的价值取向依然具有儒学内核,即作为士人(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结合以上两个方面不难发现,玄学家内心所向往的积极入世为官、建立王道社会的理想与当时混乱的社会现状和统治者的黑暗政治相去甚远,但他们的价值观又迫使他们对现实政治给予关注。为了在乱世中坚定自己的价值取向,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同时又要保全自己和家族,他们出于对自身心灵宁静和家族地位的考虑,委曲求全,选择了用道家思想来丰富传统儒家学说,因此,玄学的出现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
二、玄学思想中对儒家的继承和发展
(一)注经改革:进行理论创新
正始时期,玄学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肯定了“意”的第一性,他认为可以将“言”与“意”适当地分开来看,从而使注经这一基于原有经典进行解释的活动不仅仅局限于用儒家观点来解读儒家传统思想,而给了注经者能够与时俱进、充分发挥的可能性。“言意之辩”直接改革了注经方法,针对当时儒家经学僵化衰落的局面首先做出了理论上的革新,从中能看出王弼希望在乱世中用拓宽注经的方法来重振儒学,一改之前“注不破经”的学术瓶颈。
王弼的“言意之辩”为他自己和之后的玄学家利用道家观点解释儒家经典著作提供了支持与依据,使儒家学说在更广泛的程度上接受、吸收、糅合其他学说的观点,完善了整个儒学理论体系,从而维护了其思想主流地位。因此,玄学也成为了中国哲学史上承上启下的环节,为其之后与佛学的融合及理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二)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
在道家与儒家的辩论中,道家常常用“自然”的观点来反驳儒家的名教与礼法,但传统观点中对立的两方在玄学中走向融合。传统道家认为,“自然”代表宇宙原生,而“名教”是人为创造的,想要达到“任自然”和“逍遥”的境界就必须像挣脱束缚人的枷锁一样抛弃名教,回归宇宙中的大道。但当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赋皇权”学说深入人心后,玄学家们开始思考:宇宙原生的“天”产生了皇权,而“天”和人类社会连接的途径也是皇权,而皇权正是名教、礼法的核心,因此正始时期的玄学家,如何晏、王弼等都认为名教生于自然。[3]而且老子所讲的“万物皆生于无”也是此想法的一个支撑,“万物”中也包含礼法和名教。既然名教出于自然,那么“任其自然”就意味着对礼法和名教的认可,即遵从礼法、名教就可达到“无为而治”,从而用这种方法来使人们更好地遵从儒家礼法。
元康时期的向秀、郭象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又提升了一个层次,他们认为名教即自然,自然与名教完全合一。他们将儒家学说中的“天命”与“自然”相结合,认为“命之所有者,非为也,皆自然耳”,用自然的观点来解释“天命”,来表达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秩序紧密结合的观点,从而使自然社会化,即“儒化”。
(三)儒学在玄学家家族中的传承
考察竹林七贤中阮籍、嵇康的家族以及他们的生平经历不难发现,他们出身于官宦世家,因为在魏晋时期门阀士族政治背景下,只有世家大族的后代才有入朝为官和为人所知的机会。《晋书》中记载阮籍“本有济世志”,少年时曾极为崇尚儒家经典,但当阮籍、嵇康等人转而进入道学领域时,依旧在家族中遵守礼法,并且以儒家道德教育自己的子侄。如嵇康写《家戒》来教育儿子嵇绍为人处世和做官的道理,他希望儿子有远大抱负,能成为忠义道德的君子,而不希望他效仿自己;阮籍也曾在家中严厉地禁止子侄们效仿自己“放达洒脱”。[4]《世说新语》载“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从他们对于子侄的教育上就能看出竹林时期玄学家从内心还是非常信奉正统儒学的。实际上,竹林时期的玄学家反对的并不是儒学,而是当时黑暗社会政治中统治者的“假仁义道德”,他们的放浪形骸实质上是一种自保和保全家族的手段。唐长孺先生也曾指出:“嵇阮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儒家所规定的伦理秩序,只是反对虚伪的名教,他们理想中真率自然之人格仍然与封建道德不可分割。”
三、玄学家的社会定位与自我认知
儒学在魏晋时期的传承主要是通过政治的影响力。不管是在朝为官,还是拒绝做官,玄学家们都无法摆脱门阀士族政治的束缚:他们心中坚持的传统儒家思想要求他们一定要重视家族,是故在乌烟瘴气的乱世中保全家族成为了他们最大的行为约束。究其本质,是玄学家自身的贵族、地主阶级属性使得他们无法直接表达对传统儒学的坚定信仰和对现实政治的批判。那些拒绝为统治者服务的玄学家努力在高压政治下寻求自身和家族的保全,通过结合道家的学说来使自己获得超越感和解放感;而那些在朝中做官的,依旧是为了在门阀士族政治下巩固自己的家族地位,他们用道学观点解释儒家经典,一方面继承和革新了传统儒学,希望通过自己的学说来重塑符合传统儒家价值观的社会伦常秩序,另一方面也对统治者产生了“君主无为,门阀专政”的影响。
综上所述,儒学在玄风劲吹的魏晋时期并没有从哲学史中消失,玄学反而可以被看作传统儒学的翻新和重铸,在社会动荡的魏晋时期保持了一份独特的风骨。玄学家的阶级属性使他们形成了尊儒内核,而政治的压迫又使儒学的传承具有了玄学这样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儒学得以曲折地向前发展,不断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王弼名教思想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