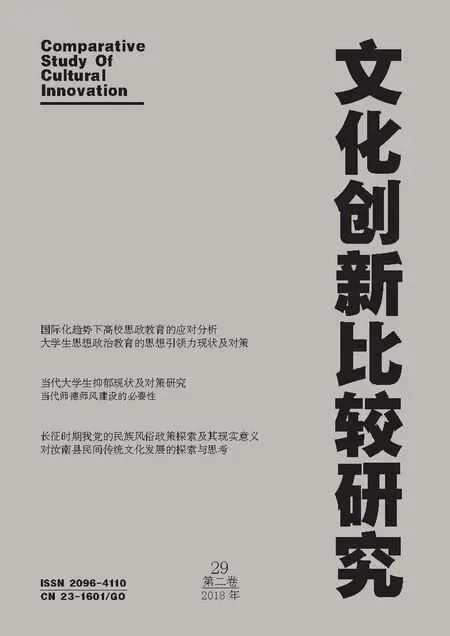从《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看中美历史教育观的不同
张慕颖
(常熟外国语学校,江苏苏州 215500)
《〈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K-12 年级)》,修订于1996年,分两部分:幼儿园K-4年级学生的历史课程标准;5~12年级学生的美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课程标准。美国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有效“参与民主制管理”与能“履行国家民主制”的美国公民,而“历史知识是一个人在政治方面具有明智才能的前提”“没有历史,一个人无法明智地研究社会中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道德问题”“没有历史知识以及它所支持的历史研究,一个人就无法成长为见多识广、独特的公民”。美国相当重视各个年龄段的历史教育,针对各年龄、年级的差异,编制了循序渐进的课程目标。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但对历史教育的重视,并不亚于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研读《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了解美国中小学历史教育理念和历史课程内容,笔者深切感受到中美历史教育理念多层面的不同。
1 贴近生活,遵循个性发展规律层面
从《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中看出,美国历史教育是以学生为中心来安排教学内容,并提出相应教学要求。学生年龄越小,年级越低,越是从学生熟知的角度组织来组织历史学习的内容。如在K-4年级学生的历史标准中,是以“这儿—那儿—那时”“这儿与现在”的模式来让学生先了解此时此地的现实的,然后逐年扩展空间、回溯时间,以学生熟知的生活和社会为中心,逐步扩展到遥远的地方和很久以前的社会,从社区到州,从美国、美洲到世界;从当代追溯到近代、古代;从学生的已知延伸至未知,以已知来引导对未知的兴趣和理解。无疑,这是尊重了学生的年龄和智力发展的特征,尊重学生各年龄段分析、理解历史的能力和特征。
美国课程标准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教育理念,为我们中国在新世纪初期的课改中有所借鉴。比如:初中出现了综合性课程《历史与社会》;高中历史体例由通史转变为专题史等,这很大程度是顺应“以学科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的转变而改变的。但在之后的教育教学实践中,这些新变化或多或少地都出现了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初中的综合课程《历史与社会》弱化了学生的历史学科知识体系,而高中专题史的学习前提是学生必须具备完整的通史知识结构。无疑,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初高中教学衔接中的困难。诚然,美国历史教育贴近学生的生活,从学生身边的人和事出发,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关注人,从“人”的角度来看待和思考历史长河中的人物和事件,人性、个性在历史的脉动中清晰可见。但美国的这一理念,我们中国该如何借鉴,如何同我们教育实际相结合,值得我们商榷和反思。
2 激发想象力,鼓励个性发展层面
美国的史观,强调历史发展的偶然性:“社会中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人们的意图有多么重要,行为方式对结果有何影响,其过程和结果处于何种的混乱之中”。因此,为了培养学生成为“历史叙述的深思型读者”,他们鼓励学生对历史进行臆想,进行假设。美国的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学生 “富有想象力地阅读历史叙述”,如对5~12年级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标准中提出了 “富有想象力地阅读历史叙述,考虑叙述所展示个人和群体的人性,他们可能的价值观、见解、动机、希望、恐惧、性格优点和缺点”,还提出“臆想历史的影响,既包括以往决策的局限性,也包括可能出现的机遇”,甚至,还要求学生“通过举例说明历史的偶然性、不同的选择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挑战历史必然性的各种论点。”通过这一方式,来激发和发展学生的想象力。而我们中国历史教育一直强调:历史,不能假设的,更不可以想象、臆想!我们历史唯物主义观指导下的历史是:历史,是既成的事实,并遵循其客观的规律而发展,历史事件的发生或是湮灭,只有偶然中的必然!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求学生“想象”历史,“挑战”历史的“必然”呢?在美国历史课程标准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或许就是其中的理由之一:“如果学生认识不到历史本来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那他们就会无意中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未来也是必然的或预先确定的,人类和个人行为毫无价值。再没有什么态度能比这个更能够“培养”公民的冷漠感、玩世不恭和弃世的心态了。而这正好是我们希望通过历史学习能够避开的东西。”这段话,使笔者发现:中美国两国思考问题的角度是截然不同的。美国历史教育中,通过引导学生对历史进行想象,对历史事件发展提出各种假设,凸显了历史中人的作用,从而使学生深刻认识到“个体”对“社会”“国家”的价值和作用,通过这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也强调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和影响,但更强调:不管历史人物是怎样的叱咤风云,都必须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才可做出真正的惊天伟业!历史伟人只有承担起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才能青史留名。在这一问题上,中美两国虽然教育目的一致,但思考问题的角度截然不同的,这也凸显中美两国不同的价值观和教育理念。
3 培养质疑精神,尊重个体独立层面
在美国历史教育理念中,要求学生认识到:历史本来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并在历史教育中要“归还历史以本来就有的各种选择权”,并要求学生理解:书面历史只是人们的一种事实构建,很多历史决定都是试探性的、可辩论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是批判性的、延续性的,也可以和其他历史学家进行探讨。基于这样的理念,美国鼓励和要求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对一切进行质疑。
《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提出要求学生整合不同历史作品中的事实,运用他们的历史解释技能,进行历史分析和历史解释,甄别历史文献或历史叙述的作者或资料来源并评价其可信程度。这种对已有历史材料和历史结论的质疑,体现在美国课程标准的字里行间。例如,对于低年级的学生,要求教师在通过历史叙述培养儿童的批判性、分析性思考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逐渐增强他们智力方面的独立性,并帮助学生克服一些思维的偏向”,如“等教师给出提示;寻求唯一的正确答案;毫无意义地把书本上的话当作权威和真实的情况等”;对5~12年级学生的历史研究能力则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能够“通过如下方法向历史资料提出问题:它们出现的社会背景、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考察其可信程度、权威程度、真实程度、内部的一致性和完整性;觉察到冗长叙述、对事实的删减或“自创”所反映的偏见、失真和宣传,并对之进行评价。”从中,我们看到,美国历史教育,不仅支持学生说出自己的观点,甚至是对他们的质疑精神和质疑能力提出了“要求”。这无疑是要学生打破思维定式,用自己的材料来证明,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分析,得出新的结论。这不仅锻炼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还有利于打破 “教科书就是历史”的传统观念,使学生不唯书、唯上。
美国的这一教育理念,笔者未必苟同,但教学方式,值得我们借鉴。2017年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高中学生提出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明确了“史料实证”的要求。在以往的历史教育中,我们更多强调对历史知识的识记,直到21世纪开始的新课程改革,历史教育中对史料的辨伪、历史结论的是非判断,才逐步出现在中学历史课堂中。对于个体成长而言,探讨“为什么”,显而易见,比识记“是什么”更为重要。在目前的初高中历史教育中,历史质疑精神和质疑能力在教育教学中正逐步展开,但相对于美国而言,我们不仅起步晚,在现实的教学实践中的普遍做法也显得肤浅。在学习高压下,学生搜寻、研读史料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获得的史料是狭隘的,教师引导学生所进行的质疑,是微观化的,往往仅仅是对某段文字、某段材料、某个方面、某个角度的质疑,因而,我们的历史质疑,是片段化、具有片面性,而美国学生所质疑的内容,外延更广,内涵更深,角度更全面和宏观。
4 社会伦理道德培养,彰显个性层面
重要历史问题往往会牵涉价值观问题,历史学习活动也为学生提供了评判历史人物行为是否合乎社会伦理道德的机会。比如:在南北战争中,林肯总统在当时是否马上废除南方奴隶制度的问题上,就会面临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两难选择,美国的课程标准中则明确规定:教师不应该用历史事实来论证他们所欣赏的道德戒条。因为他们认为:学生会拒绝特定的伦理说教,他们会有而且也应该有自己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而且,这样的教学方式也无法培养学生获取道德思考和道德推理所需要的复杂技能。但相似的,比如,“岳母刺字”的典故就传达了我们数千年的传统理念“精忠报国”。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就渗透了伦理道德的价值趋取向。中美教育中的这一差异,应该是由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国情造成的。
中美两国国情、价值理念和教育理念的不同,造成了中美两国历史教育观的不同,出现了中美课程标准的差异。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阅读《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有助于我们反思:作为历史教育工作者,该如何从国情出发,培养不盲从,不墨守成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新一代。
——依托《课程标准》的二轮复习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