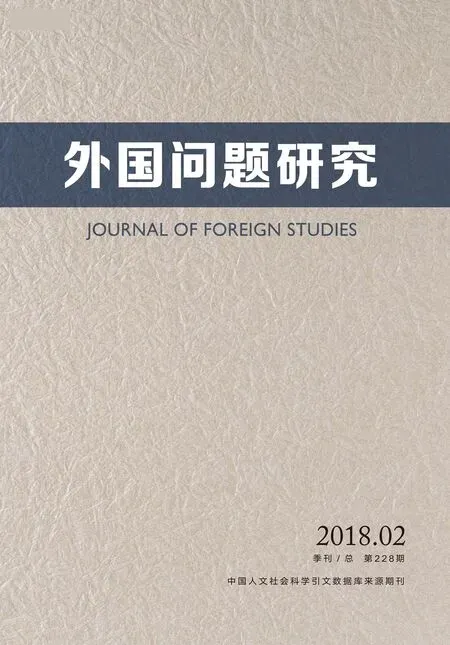国际托管制度视角下的战后琉球地位探讨
李 超
(复旦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200433)
在国内,以琉球学为主体的中琉关系史领域向来是一个研究热点。*国内学界关于中琉关系史的研究现状及成果,可参见赖正维、李郭俊浩:《回顾与展望:中琉关系史研究30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7年第1期。近年来,战后琉球问题在东亚地缘政治上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进展较快,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国内学界近些年来关于琉球的问题意识及研究现状,可参见徐勇、汤重南主编:《琉球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33—340页。琉球这一名词在这里的含义,并非历史上已经灭亡了的古琉球国,而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主要指日本九州岛西南和中国台湾东北之间的琉球群岛(现日本冲绳县的行政管辖区域),包括了奄美群岛、冲绳诸岛以及先岛诸岛等地方。*相关称谓还有“西南群岛”“萨南群岛”和“冲绳群岛”等,这些是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所推广使用的称谓,具有刻意的政治意图。参见刘绍峰、袁家冬:《琉球群岛相关称谓的地理意义与政治属性》,《地理科学》 2012年第4期。此外必须指出的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并不包含在琉球的地理范围内。国内关于琉球的国际法地位探讨,主流学术观点是琉球战后地位至今未定。*近年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罗欢欣的《国际法上的琉球地位与钓鱼岛主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及刘丹的《琉球托管的国际法研究——兼论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12期)和《论近世琉球的历史和法律地位——兼议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海洋法学评论》 2016年第2期)等。简言之,即琉球的主权归属问题至今没有明确,在现代国际法上缺乏明确有效的文本证据。
如所周知,在美日两国为首的大国操弄之下,琉球自战后以来的国际法地位频频发生变迁,当地人民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发言权和自决权,不满和抗议之声蔓延至今,在日本和国际学界上也是一个研究热点问题。基于当下亚太国际秩序重建的新时代背景,该问题在国内学界值得受到进一步关注,相关问题的探讨也有待加强。本文在学界先行研究成果基础上,依托国际托管的研究视角,对战后琉球地位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一些个人粗浅看法恳请学界同仁指正。
一、战后琉球地位国际托管的文本依据
在历史上,琉球自古以来属于本土王朝琉球国的领土。1879年4月,琉球被日本强行设立直辖的冲绳县后,成为日本领土一部分,也宣告琉球国的正式灭亡与被吞并。二战期间琉球惨遭摧残,并被以美军为首的同盟军战时占领,改由同盟军直接统治。但琉球的战后命运变迁仍未消停,有关其领土的战后处置一直是以同盟国为主的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焦点议题。
1951年9月8日,在美国的主导和策划下,48个战胜国与日本在旧金山签署了单方面的媾和条约,即《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以下简称“和约”)。次年4月28日和约生效,在恢复日本国家主权的同时,对相关领土问题也做出了规定。琉球战后地位体现在和约第三条,即置于国际托管制度之下;换言之,琉球应成为托管领土的地位得到法律确认。关于琉球战后地位,该和约条款规定是:“日本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29度以南之南西群岛(包括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墉妇岩岛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鸟与硫磺列岛)及冲之鸟岛与南鸟岛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之任何提议,将予同意。在提出此种建议,并对此种建议采取肯定措施以前,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其君民,包括其领海,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国内关于该条款的翻译有多个版本,对条文原意理解上存有混淆之处,本文采用罗欢欣著作中的译文。关于国内其他译文版本的翻译问题,可参见罗欢欣:《国际法上的琉球地位与钓鱼岛主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16—119页。
可见,通过对上述条款愿意的解读,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点:一是琉球的地位是成为托管领土,纳入托管制度进行管理;二是托管国是美国,而且是唯一的管理当局;三是在成为托管领土之前,由美国施政;四是由美国负责将琉球纳入国际托管制度,对此日本已经同意。显然,成为联合国的托管领土是琉球战后应然地位,而该法律地位之真正实现,则是美国作为暂时施政国和未来托管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
在旧金山和会后,美日两国绕过琉球应然托管地位,彼此展开谈判博弈,私相决定授受琉球的施政权。1969年11月,佐藤荣作和尼克松发表“冲绳返还”共同声明。1971年6月17日,美日正式签订《琉球与大东群岛协定》,俗称“冲绳返还协定”。*该俗称被学界和媒体广为使用,但该条约自始至终未出现有“返还”或“复归”等字眼,关于该地称谓使用的是“琉球”而非“冲绳”,也未涉及“主权”归属问题,故“冲绳返还协定”说法容易令人产生附会或歧义,值得引起注意。1972年5月15日该协定生效,琉球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移交日本。换言之,美国将对琉施政权让渡给日本。日本学者矢吹晋指出,该行为导致琉球战后地位发生了实质变动,日本据此认为将对琉的所谓“剩余主权”变为“完整主权”,号称“冲绳复归”。*矢吹晋:《钓鱼岛冲突的起点:冲绳返还》,张小苑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7页。可以说,美日私相决定授受琉球施政权的“冲绳返还协定”,在现代国际法上存在非法性,不仅违背了托管地位的和约规定,违反了国际社会多边机制处理原则,也是对琉球人民自决原则的侵犯,则应视作无效文件。*关于该文件非法性的研究论证,可参见张毅:《琉球法律地位之国际法分析》,博士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13年,第84—86页;以及罗欢欣:《国际法上的琉球地位与钓鱼岛主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39—155页。所以,琉球战后地位仍应适用1951年和约第三条有关托管地位的规定,将其纳入国际托管制度下,成为联合国的托管领土。
二、国际托管制度的形成与特征
一般认为,联合国成立标志了现代国际法的正式诞生。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生效,宣告联合国正式成立。宪章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联合国在其权力下应设立国际托管制度,以管理和监督战后规定的托管领土。这也意味着国际托管制度成为现代国际法的一项构成内容,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与接受。
(一)委任统治和国际托管
国际托管制度,是将某些领土依照托管协定,置于联合国框架下进行管理的一种制度,而纳入该制度下的领土,即联合国的托管领土。托管领土依托管协议的签订,而成为正式的托管领土。不过,协议内容依各托管地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若托管地是战略防区性质,还应由安理会核准(宪章第八十三条),普通托管地则由联合国大会核准即可(宪章第八十五条)。
关于该制度的宗旨,宪章第七十五条有详细规定:一是促进国际和平及安全;二是增进托管领土居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之进展,并以适合各领土及其人民之特殊情形及关系人民自由表示的愿望为原则,且按照各托管协定的条款,增进其趋向自治或独立逐渐发展;三是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提倡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并激发世界人民互相维系之意识;四是于社会、经济及商业事件上,保证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及其国民的平等待遇,及各该国民于司法裁判上的平等待遇。在很大程度上,上述宗旨体现了联合国解决战后殖民地问题的思路和原则。托管制度自诞生以来,在这些宗旨的基础上也不断有所发展,特别是在现代国际法的理论层面上,被赋予新的内涵。譬如,美国学者查米恩就此提出了神圣信托原则、国际问责制原则、造福世界为目的之管理原则以及殖民地信托临时性原则,即所谓国际托管制度的四大原则。*Charmian Edwards Toussaint,The Trusteeship System of the United Nations,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76,pp.3-18.可见,宗旨第二项内容相当丰富,可以说是该制度的首要宗旨,是托管国对托管地及其人民的根本义务。国际托管制度是依联合国宪章规定而诞生,是现代国际社会为解决殖民地战后领土问题达成共识的新方案。不过,该制度并不是一种崭新事物,其前身是形成于一战后的委任统治制度。
在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凡尔赛和会上,作为战胜国对从战败国分离出来的殖民地等领土的处置方法,委任统治制度被明确规定在国际联盟的盟约中。凡殖民地及领土,在战后不再从属于原宗主国,而对那些尚不便于实行自治的地区则实行委任统治的原则,委任统治制度的目的是要保证将居住在该地区内人民之福利及发展视作文明之神圣任务(第二十二条)。也即,这些委任统治地的领土主权不归属任何国家,而是委托某一或几个国家作为受任国,与国联签订书面协定,代表国联实行统治。
可见在托管制度诞生前,委任统治制度即成为战后处理殖民地等领土问题的一种方案,很大程度上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显然,该制度有别于先占、征服和割让等这些传统国际法中的方式,性质上不是领土的取得或变更,是基于非殖民化的理念,应归属为现代国际法领域的构成内容。
在委任统治制度下,虽然受任国行使统治权,但需同时接受国联之监督。除了每年递交治理报告书外,凡发生涉及委任地法律地位变动的行为,也需事先征得国联之同意。而且,委任地人民并不当然获取受任国的国籍,但在商贸领域需保证其与受任国及国联会员国的国民享有同等权利等。可以说,委任统治制度虽然在一战后并未适用于所有殖民地,主要是用来处理原属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殖民地,存在历史局限性;不过该制度的提出和部分适用,很大程度体现了国际社会处理殖民地领土问题的原则与方式,即非殖民原则和国际化处理方式,客观上也是时代潮流的发展方向。
一战结束后,英国、法国、比利时、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日本被指定为受任国,分别对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共14个委任地实行委任统治。其中,日本作为受任国,负责对赤道以北的太平洋岛屿进行委任统治,具体对象是:马里亚纳、加罗林和马绍尔这三大群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1935年日本退出了国联,但对这些领土的委任统治并未因此而中断,仍定期向国联递交治理报告书,继续以委任统治的名义对这些群岛实行统治。究其原因,以法律视角分析的话,主要在于该制度本身对委任地的类型有所区分。国际联盟将委任地分为甲乙丙三大类型,甲类如伊拉克等,社会发展已经到达独立国程度,乙类如喀麦隆等,社会发展程度比甲类稍欠,而余下的丙类领土,简单理解就是处于未开化的状态。“此外土地,如非洲之西南部及南太平洋之数岛,或因居民稀少,或因幅员不广,或因距文明中心辽远,或因地理上接近受任国之领土,或因其他情形最宜受制于受任国法律之下,作为其领土之一部分,但为土人利益计,受任国应遵行以上所载之保障。”*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第107—108页。据上可知,针对丙类委任地,受任国可以视之为本国领土,并依据本国法律实行统治。虽然在名义上,日本对于南太平洋三大群岛施行的是委任统治,但实质上可以认为是一种赤裸裸的主权统治。但从委任统治制度出发,日本退出国联的行为也意味着脱离出了该制度,自动丧失其委任国的资格,理应由国联重新指定新的委任国对上述群岛实行委任统治。但适逢二战期间,该制度对于法西斯日本无法发生作用,相关问题只好留待战后解决。
1947年2月美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过一份托管协议,同年4月得到安理会的核准。美国据此接管日本委任统治下的南太平洋三大群岛,当时委任统治制度已被托管制度所取代,这三大群岛的法律地位则由委任地变成了托管地,而且属于战略防区托管地,与此相应,其受任国日本也变为了托管国美国。但值得注意的是,琉球的战后托管地位与该协议并无关系,既不是战前日本的所谓前委任统治地,也不在该协议所规定的托管范围内。
(二)国际托管的宗旨及其变质
回溯历史,不论是现代国际法下的托管制度,还是作为其前身的委任统治制度,很大程度上均是在美国的提议下而诞生。一战后针对殖民地处置问题,美国率先提出委任统治这样一种方案,包含在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之中。威尔逊试图通过委任统治制度解决殖民地问题,但出于种种原因,作为首倡者的美国却没有加入国联与该制度之中。
托管制度的提议者也是美国,罗斯福基本延续了威尔逊的非殖民原则,发展为一种反殖民的外交政策,在促使菲律宾实现独立地位外,不断呼吁其他殖民宗主国也能效仿美国,为托管制度之诞生作出了大量贡献。然而,随着战争及国际局势的变化,罗斯福的托管构想逐渐发生了变化,立场趋缓。一方面以同盟国为主的国际社会中,虽然中苏对此表示赞同,却始终遭到老牌殖民国家英法之反对,而且美国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在博弈。
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继任总统的杜鲁门虽然延续了托管制度的上述构想,立场上却更趋向保守。联合国成立,宪章中规定的托管制度已经变味,从“全面托管”逐渐演变为“有限托管”,并衍生出使托管地成为战略防区这样一种完全服务于托管国外交和军事战略的新方案,即所谓“战略托管”。对此,国内学者毕元辉这样指出:“(该制度的演变)使托管制度失去了非殖民原则的光环,美国的殖民主义以战略托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复兴,非殖民原则在战后美国外交实践中逐渐削弱甚至消失,使殖民地人民试图藉美国和联合国摆脱殖民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的梦想破灭。”*毕元辉:《从“非殖民”到“国际托管”:罗斯福政府殖民地政策论析(1941—1945)》,《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科版)》 2014年第2期。
可以认为,托管制度是美国在二战期间推行所谓非殖民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原初构想是将所有附属领土置于国际机构的管理下,通过授权管理当局依照托管协议实行托管统治。但受制于国际形势的变迁及大国政治的演化等诸多因素,该制度在从构想、商议到确定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变化,而且在具体实施中又有一些变质。
杜鲁门就美国对该制度的愿景,曾有过这样的表达:“第一,保持美国的军事和战略权利;第二,为确保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控制;第三,促进从属领地居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册)》,李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42页。而且,后来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证实了美国这般愿景。美国凭借自身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领域的突出优势,刻意通过国际托管的名义,以迅速挤兑旧殖民宗主国的势力,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际相继签署所谓防御条约,在托管地大肆建造军事基地,使该制度服务于国家自身的利益与战略考量。
因此,关于国际托管制度及其前身委任统治制度,虽然在构想和宗旨上是非殖民与反殖民,但其实在殖民主义的清除方面并未起到太多实质作用,受任国和委任地之间,托管国和托管地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本质上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李艳娜:《“委任统治制度”与“国际托管制度”之比较》,《历史教学》 2009年第16期。
三、战后琉球地位国际托管的法律瑕疵
1951年旧金山和会上,琉球地位已为和约第三条明确规定,纳入托管制度下,成为联合国的托管领土。但美日两国刻意绕开这一法律依据,将所谓“剩余主权”论当作彼此谈判、私相授受琉球治权的依据。从托管制度和现代国际法角度出发,实际上琉球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托管状况,而在理论上又有哪些值得国际社会予以重视的因应策略呢?
根据宪章有关托管制度的程序规定,一地是否已经纳入托管制度成为托管领土,有两项外在要件的判断标准:一是签订了正式的托管协议,二是接受联合国的监督管理。对此审视琉球托管可知,美国始终没有签订过琉球托管协议,也没有向联合国递交过琉球治理报告书等文件。换言之,自1952年合约生效至今,作为琉球唯一管理当局的美国未将琉球真正纳入托管制度下,其规定义务的怠于履行,很大程度致使琉球战后的托管状态存在法律瑕疵。
对于该托管状态,国内学者刘丹指出:“琉球战后托管在国际托管制度的程序和实体上均存有法律瑕疵,充其量只能视为一种‘事实托管’。美国以《旧金山和约》作为‘法律依据’对琉球的托管既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又不符合国际托管制度的形式要求。”*刘丹:《琉球托管的国际法研究——兼论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太平洋学报》 2012年第12期。另一方面,前文已述托管制度的最终落地,表面上是国际社会在委任统治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改良,用以解决殖民地战后处置问题的新方案,但实质上也可视作美国等大国试图实现全球霸权政治的一个幌子。在琉球战后托管上,和约第三条的托管规定对于美国的实际意义,只不过是据此获取了可以继续统治琉球之合法性或曰正义名分。
事实上,不仅琉球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托管,即便是所谓“剩余主权”论的政治构想,在后来美日的互相谈判和博弈过程中,也逐渐陷入空洞化之境地。对此,日本学者河野康子也这样指出:“美国借此摆脱了对琉球殖民主义统治的嫌疑,终于可以继续军事占有并统治琉球。”*河野康子:《平和条約以後の沖縄と日本》,《外交資料館報》 2016年第29号。
可以说,战后美国的琉球政策,不仅无视中国等直接关系国,还严重侵犯了琉球当地人民的权益,有意绕过将托管制度落实于琉球的必要程序,任意决定和改变琉球的战后地位。尤其是美日在旧金山和约之外又签订了所谓“安保条约”,私相又为琉球地位问题设置法律障碍,使该地位困境进一步加剧,甚至可以说在其军事化过程中,逐渐演变成美日的双重殖民地。*加文·麦考马克、乘松聪子:《冲绳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争》,董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9页。不过有必要注意的是,施政权不是主权,虽然琉球接受美国单独统治,但主权并不会由此归属美国,其主权自战后初期被规定脱离出日本后,归属问题始终不明朗;而成为托管领土的地位规定也无法确认其主权归属的对象。因此无论托管地位之实现与否,均改变不了主权归属未定的状态。
1945年10月24日宪章生效、联合国成立,托管制度自此成为现代国际法一项重要内容,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同时也被广泛适用。战后许多领土据此被纳入到了托管制度中,成为联合国的托管领土,主要是前身委任统治制度下的领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或将自敌国割离的领土;以及负管理责任之国家自愿置于该制度下的领土等。战后初期琉球从日本版图中脱离出来,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领土,在旧金山和约第三条中也明确规定其作为托管领土的法律地位,却迟迟未真正得到兑现。
到1950年,已纳入托管制度的领土共有11个。到1976年,在这些托管领土中,除了前文提及的美国从日本手上接管过来的南太平洋三大群岛外,其余托管领土均先后实现了独立或与邻国联合变成独立国家。经过长期谈判,美国最终结束对这些群岛的托管,联合国也决议终止适用上述群岛的托管协议。一般认为,随着1993年12月独立国家帕劳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托管制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该结局表明了托管地人民追求平等、争取独立的力量,也是各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国际化合作解决国际问题所取得的成就。
关于琉球战后托管问题及其法律瑕疵之解决,托管制度的程序及其宗旨有必要得到国际社会的重新正视。而托管制度是现代国际法下诞生的新制度,依宪章规定是联合国在其权力下设立而成,针对琉球战后托管的解决路径,依据宪章及现代国际法相关内容及原则,提出以下三点思考。
第一,托管是专门的法律概念,在赋予受托人权力的同时也有所限制。托管制度规定于宪章,其适用原则也应符合该法律概念本身的含义。由此,作为琉球唯一管理当局的美国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利益考量,也无论琉球纳入托管前还是托管后,均改变不了美国和琉球之间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委托与被委托的法律关系,这也是该制度应有性质及宗旨的体现。
第二,托管协议有必要得到签订或补充。某地被纳入托管制度的根本标志即托管协议之签订,历数上述战后托管地,均无一例外签订有正式的托管协议,并且协议均规定管理当局应促进自由政治制度在托管领土的发展,也就是使当地人民逐渐获得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帮助托管地在政治上未来可能实现自治或独立。而在托管协定的解释和适用上,若管理当局和联合国另一会员国之间发生争执,在无法以谈判或其他方式解决的情形下,应提交国际法院予以裁决。
可以看出托管协议的条款拟定、正式签订与积极履行,是托管正常运作的法律保障。以此审视琉球战后地位,那么缺失的托管协议,则是国际社会解决托管状态法律瑕疵需重新思考与面对的一项议题。
第三,决定托管领土地位的权力应归属联合国。在托管制度下,托管国的地位是托管地的管理当局,绝非托管地主权的拥有者。可以简单理解为,管理当局地位的取得,是依据联合国的授权,若出现违背托管协议规定,以及托管国退出了联合国或被除名等情形下,在理论上联合国是可以将托管领土转交其他国家进行托管,即变更管理当局。可见托管地的最终责任,在于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管理当局每年向大会递交治理报告书,其实是联合国对托管制度行使监督权的体现。所以说,非经联合国核准,管理当局美国无权处置作为托管领土的琉球,也无权以任何方式擅自改变琉球战后的法律地位。
结 语
综上可知,如果我们从国际托管制度这一视角出发,审视战后琉球的国际法地位及其存在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么不难发现,战后琉球的应然法律地位,应是以旧金山和约第三条作为确认地位的文本依据,即明确规定将其纳入国际托管制度并成为联合国的托管领土。但是事与愿违的是,美国当时作为琉球指定的唯一管理当局,出于自身利益和战略上的考量,仅仅是凭借该条款规定,看似合法地获取了可以继续单独统治琉球的国际名义,旨在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国际社会对其在琉球驻军及建设军事基地,甚至进一步施行变相军事殖民主义统治的谴责之声。
就战后琉球地位,对于国际托管制度而言,无论是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可以认为美国均没有真正遵照相关规定及最初宗旨,正式签订过应有的托管协议,积极履行国际法义务,将琉球纳入国际托管制度以成为联合国托管领土。非但如此,美国还转而与日本一道,在所谓“剩余主权”的法理框架下进行政治交易与战略博弈,最终私相授受琉球所谓行政管理权,即对琉施政权。台湾学者陈荔彤这样写道:“美国对琉球问题的处理显与联合国宪章的托管制度未尽相符,以政治手段操弄一切。”*陈荔彤:《琉球群岛主权归属——历史角度与国际法》,《东吴大学法学研究》 2005年第22号。
以现代国际法角度视之,美日两国关于战后琉球地位的种种行为及其签署的相关文件,不仅是对国际托管制度程序及宗旨的不履行,还是对现代国际法原则和法理的违背,可以说与战后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时代浪潮倒行逆施。正如国内学者罗欢欣写道:“(琉球)最终地位应该在联合国框架下集体处理或通过行使民族自决权来实现……日本目前对琉球的‘施政’缺乏合法依据。”*罗欢欣:《国际法上的琉球地位与钓鱼岛主权》,第197页。
最后,还需要指出对琉施政权不等同于琉球主权。虽然战后琉球的托管地位没有能够真正实现,所谓施政权从美国转移到了日本手上,目前仍在日本实际有效控制下;但基于现代国际法和托管制度的视角,可知即使其托管地位真正得以实现,也不必然意味着其主权归属对象随之明确。无论如何,国际托管是战后现代国际法的重要部分之一,在反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上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在战后琉球地位上,该制度本身应得到国际社会的重新探讨,美日两国与该制度有关的行为及法律瑕疵应得到国际社会进一步审视,而当下琉球人民的政治诉求也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