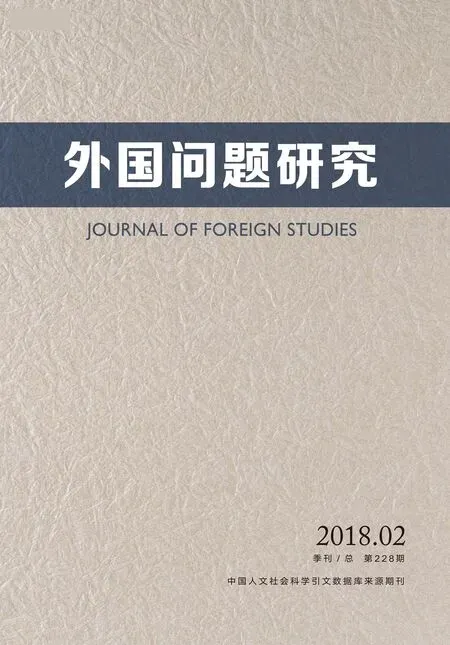叙利亚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研究
王新刚 张文涛
(1.西北大学 叙利亚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9;2.西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9)
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是现代化进程中引人关注的政治发展问题。叙利亚政党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是如何适应叙利亚独特的社会政治生态,以及对叙利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现代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是有研究和探讨意义的。
第一,政治稳定不仅是目前叙利亚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核心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稳定始终是政治发展的前提,而政党制度对一国的政治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帅:《阿萨德体制下叙利亚的政治稳定研究》,硕士论文,西北大学,2015年。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页。因此,动荡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经济与社会的变革,而政党制度又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2页。亨廷顿从政党制度的适应性出发,认为在那些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多党制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稳定并不相容,一党制反而因其历史起源而更加稳定。*张弘:《政党政治与政治稳定——乌克兰案例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年第1期。本文将在相关理论基础上,从叙利亚政党制度发展历程的角度分析其对叙利亚政治稳定的影响。
第二,叙利亚是中东地区的政治大国,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沿线国家,研究其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具有现实启示意义。历史与现实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性,将现实问题上升至历史的高度予以观察与思考,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在叙利亚持续动荡的今天,平息内乱的路径和前景迄今仍是人们不得其解的难题。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皆是历史演变的必然产物,今日叙利亚的政治乱象,根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矛盾,尤其是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复杂互动与结构失调。*马帅:《阿萨德体制下叙利亚的政治稳定研究》。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在于长时段的动态分析,纵观现代叙利亚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的历时关系,有助于我们拨开历史迷雾正确认识叙利亚危机,为政治稳定重构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党建设寻求启示。
一、叙利亚一党独大政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亨廷顿认为,国家欲摆脱社会动荡与政治衰朽的局面,必须依靠缔造一个强大政党并巩固其统治地位来建立强大政府,树立政权威信。叙利亚自独立后国家深陷军人干政的“普力夺社会”,激烈的党派斗争与频繁的内阁更迭造成政府效能低下,国家的政治生活实际上陷入缺乏权威的衰朽状态。同时,经济矛盾、阶级矛盾、宗教矛盾、地区矛盾等相互交织、贯穿于叙利亚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中,现代化进程深陷派系斗争与军人干政的泥淖中止步不前。*马帅:《阿萨德体制下叙利亚的政治稳定研究》。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复兴党作为一支具备鲜明完整的意识形态纲领和健全的组织机构的政党,成立以来很快获得各阶层的支持和拥护,有着较强的政治动员能力。复兴党从掌权之日起,就牢牢地控制着政治、军事等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同时,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也大大增强,以往涣散分裂的社会被整合进国家机器,为其统治奠定了稳固的基础。*马帅:《阿萨德体制下叙利亚的政治稳定研究》。叙利亚一党威权的政党制度是在国内亟须政治稳定的背景下产生的,并与本国的政治发展相契合。叙利亚一党威权体制给叙利亚创造了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奇迹,将一个动荡涣散的蕞尔小国改造成相对稳定的地区强国。
(一)叙利亚复兴党的创立与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登上叙利亚政治舞台时,一个默默无闻的、主要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运动——“阿拉伯复兴运动”开始兴起。它的创建人是一位名叫米切尔·阿弗拉克的阿拉伯基督徒和一位名叫萨拉赫·丁·比塔尔的逊尼派穆斯林。1941年初,阿弗拉克和比塔尔开始以“阿拉伯复兴运动”名义从事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活动。1943年7月,阿弗拉克第一次将“阿拉伯复兴运动”称作“党”,并提出党的口号为“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具有不朽的使命”。 1947年4月4—6日,复兴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复兴党成立。党纲强调“阿拉伯祖国是政治经济不可分割的整体”,复兴党正在领导“一个争取阿拉伯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的人民民族革命运动。”至此,复兴党以“阿拉伯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三大目标为中心的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系统,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阿拉伯复兴运动”正式以政党形式登上历史舞台。*王新刚,于晓冬:《叙利亚复兴社会党的历史沿革》,《认识伊斯兰》,和讯网,2015年11月,http://opinion.hexun.com/2015-11-11/180499469.html.
20世纪50年代复兴党迅速发展。复兴党高举阿拉伯统一、维护阿拉伯民族权益的大旗,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广大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其主张逐步在阿拉伯国家得到传播,党组织也得到发展。1950年,复兴党已相继在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建立分支机构。1953年,复兴党同阿拉伯社会党合并,改称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但仍沿用阿拉伯复兴党的口号和主张。合并前复兴党是一个以逊尼派穆斯林和希腊东正教教徒为主体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同时在农村低层中有一定的影响,并且与青年学生及年轻的军校士官生联系密切。由于阿拉伯社会党重视土地和农民问题,合并后复兴党在农民阶层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由此,复兴党成为穆斯林和基督徒不同教派的、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体现超越传统家族势力、地区利益和教派分歧之狭隘界限的民众性政党。
1954年6月,复兴党第二次民族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中央设立“民族委员会”,领导阿拉伯世界的复兴党;在每个阿拉伯国家设立一个地区委员会,领导本国复兴党日常工作,从此复兴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泛阿拉伯政党。
(二)叙利亚复兴党的分裂与重生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复兴党极力鼓吹与埃及合并。1958年2月,叙、埃两国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然而令复兴党始料不及的是,叙、埃两国的合并却使复兴党蒙受了严重的挫折,复兴党发生了自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叙、埃合并后, 阿联总统纳赛尔发布命令,解散叙利亚所有政党。同年,复兴党在黎巴嫩受挫。1959年伊拉克复兴党也遭到政府镇压。复兴党在叙、伊、黎等地相继受挫使党的组织一片混乱。同年8月底,复兴党非常代表大会在贝鲁特召开。大会虽然决定采取措施重整党组织等,但并未平息党内对纳赛尔的不满情绪。1961年9月,叙利亚右翼军人集团发动政变,宣布中止与埃及的合并。10月,部分党派及穆斯林兄弟会等发表声明,支持政变军人。但以阿弗拉克等人为首的部分复兴党领导成员对上述声明表示异议,复兴党的一些派别组织不同意阿弗拉克等人的主张,复兴党内部分歧逐步公开化。1962年5月,复兴党在霍姆斯召开“民族五大”时,胡拉尼及其支持者拒绝与会,复兴党发生严重分裂。而此前,坚持反对脱离“阿联”的亲纳赛尔分子萨米·苏凡及其支持者已经脱离复兴党另组纳赛尔主义组织——社会主义联盟运动。*王新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及其理论与实践》,《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4期。
60年代初,复兴党经历了重大考验,但却为登台执政积累了经验。从这一时期开始,党内老一代领导人影响力下降,复兴党“军事委员会”为主的少壮派影响逐步扩大。1963年3月8日,复兴党“军事委员会”成员参与了由齐亚德·哈里里少校发动的政变,以少壮派为首的复兴党逐渐成为实际的执政者。1966年2月23日,复兴党少壮派贾迪德和阿萨德等人再次发动政变,推翻阿明·哈菲兹政府,并夺取复兴党民族领导机构和地区领导机构领导权。9月,复兴党“民族九大”,决定开除阿弗拉克、比塔尔等元老派。至此,复兴党不仅在“三·八”革命后再度崛起,而且完成了新老两代领导人的交替,并在此前后构筑起的党政合一政治体制下,成为延续至今的执政党。
1967年“六·五”战争后,新复兴党人内部逐渐产生了以贾迪德为首的激进派和以阿萨德为首的务实军人派的两个派别,并在对内对外政策主张等方面发生严重分歧,甚至出现了以民族领导机构和以地区领导机构为背景的两个权力中心。*王新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及其理论与实践》,《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4期。激进派将老一代领导人排挤出局,开始在国内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严重冲击了传统大地主和城市工商业阶层的利益。同时,激进的计划经济政策也使经济发展面临困境,加之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惨败对政权的沉重打击,复兴党再次面临政治危机。
20世纪60年代末,阿萨德与贾迪德的权力斗争从最初的个人竞争演变为军队与党之间的角逐。阿萨德虽然在党内资历与地位处于劣势,但军队是在他的直接控制与指挥之下。贾迪德在阿拉伯世界的政策失误以及在对抗以色列问题上的软弱为阿萨德推翻其政权提供了借口。阿萨德1970年11月13—16日发动不流血军事政变。政变被阿萨德描述成“响应我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而发动的“纠正运动”。为了巩固其统治,阿萨德甫一上台,全面改组和重建各省党部,加强对党政军的控制,同时重构国家体制,不断清洗和排斥反对势力,标榜民主政治,塑造政权合法性,确立个人统治威权。
(三)一党独大政治格局的最终形成
1970年11月阿萨德发动所谓“纠正运动”,从此开启了叙利亚阿萨德时代,直至2000年6月阿萨德去世。阿萨德时代,复兴党对叙利亚国家政治体制即此前初步形成的一党执政、党政合一的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首先,于1971年2月宣布建立人民议会,并通过修改1969年临时宪法,将总理内阁制改变为总统共和制,3月阿萨德当选总统。其次,1972年3月,宣布建立复兴党领导下的“全国进步阵线”,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阿拉伯社会主义运动、叙利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统一运动等组织纳入到复兴党主导的政治体制内。第三,1973年1—3月,在复兴党的组织领导下制订并通过叙利亚永久宪法,在宪法中正式确认复兴党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党”。至此,在阿萨德领导下,复兴党完成了对国家政治体制的重构,使叙利亚成为复兴党领导下的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总统共和制国家。
1971年召开的复兴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章程,修改复兴党中央机构的选举方式和集体领导制度,明确规定阿萨德在复兴党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强化复兴党自上而下的政治原则。在之后的历次复兴党民族与地区代表大会上,阿萨德连任总书记。在阿萨德30年执掌国家政权的过程中,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拥有为数众多的党员及其群众基础,党的纲领成为国家的主导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党的组织机构发挥着凝聚精英、调控权力、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政府、军队的要害部门均由复兴党要员领导,主要的社会团体如工会、商会、妇联、各类行业联合会及高等院校的负责人也均由复兴党党员出任。入党成为民众进入权力体系的唯一通道,所有精英的选拔,任何人才的招募,均通过党组织进行。尽管在阿萨德执政期间复兴党也曾发生内乱,但在阿萨德的领导下,复兴党政权及其统治基础基本稳固。2000年6月10日阿萨德去世后,其子巴沙尔·阿萨德在接过国家最高权力的同时,也接任了复兴党民族及地区领导机构的总书记职务。
(四)复兴党长期一党执政的原因
复兴党在叙利亚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复兴党称得上是阿拉伯世界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政党,具有鲜明完整的思想纲领。复兴党“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三大目标,以及复兴党党纲在宗教、自由、妇女解放、社会经济、教育政策等方面系统明确的立场,不仅来源十分广泛,而且有极强的号召力。复兴党纲领体现了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政治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双重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时值泛阿拉伯主义思潮迅速上升,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颇感失望之际,复兴党系统而鲜明的政治纲领无疑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吸引了各个阶层和不同宗派的民众。
第二,复兴党有着健全的党组织。复兴党在建党初期,党员人数较少,组织结构单一。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组织机构也很快健全起来。1954年第二届复兴党民族代表大会,确立了“民族”(阿拉伯世界)、地区(各个阿拉伯国家)、分部、支部、分支部等五级组织建制。各级组织中,“民族委员会”是复兴党中央最高执行机关,是最高决策机构,并负责复兴党在阿拉伯世界的日常事务。其下是“地区委员会”,分别负责各主要阿拉伯国家的党务工作,拥有很大的实权。不管从组织机构、机构职能,还是组织原则、活动程序上讲,复兴党都堪称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党。
第三,复兴党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较强的政治动员能力。在建党初期,复兴党在大学及中学,甚至军事院校等开展工作,与教师和学生联系密切。1953年复兴党与阿拉伯社会党合并后,复兴党的影响很快渗透到农民、城市平民,而且在上层统治阶层中也开始产生影响。特别是在农村和城市中下阶层中,复兴党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当这些学生步入社会或国家机构,成为职员、公务员、军官,并代表新兴中产阶级利益之时,其本身也就成为复兴党最稳固的社会基础。在农村,复兴党通过有农村背景的骨干分子积极展开宣传,号召消灭剥削和贫困,进行土改,并广泛建立基层组织,通过议会斗争、群众运动等多种形式,发动组织农民,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政治热情。在城市,复兴党注重加强同工人、城市平民以及各种工会和职业联合会的联系,并着手领导了一系列旨在捍卫工人和民众权利的罢工和示威活动。与此同时复兴党还非常重视在国家机构内部,尤其是在国家职员和青年军官中进行宣传,因为这些人不仅代表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往往具有农村和宗教少数派背景,并拥有相当大的政治实力。事实证明,复兴党登上政治舞台,最终夺取权力主要就是依靠这个阶层。
第四,1973年颁布的永久宪法明确规定:复兴党是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党。特别是在阿萨德时代,作为阿萨德政权三大支柱之一,复兴党是现政权权力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首先,精英选拔和权力调控。任何一个希望进入国家权力结构的人,无论是文职还是军职,都必须是复兴党成员。其次,复兴党发挥着意识形态宣传、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的作用。阿萨德上台后,复兴党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但作为现代意义的政党,其意识形态宣传作用、利益诉求和意见汇集机制以及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功能,仍然是其他国家机构难以取代的。再次,进行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协助政策实施。依靠强大的组织力量,复兴党在各级国家机关、大中型国有企业和社会团体中,普遍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机构,通过人事任命和政治指导,将影响力渗透到各个社会团体职能部门,从而加强了政权的政治和社会控制力。因此,复兴党也成为阿萨德政权依赖的重要支柱而受到权力核心的重视。
第五,复兴党与军队结盟,相互倚重,是复兴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条件。1958年复兴党军事委员会成立。1963年3月8日军事政变,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参与其中。此后,复兴党逐步控制了军队,特别是新复兴党人军人背景日渐浓厚。至阿萨德时代,阿萨德不仅本人军人出身,而且以他为首的权力核心完全控制了军队,进而使军队在阿萨德时代的权力结构中成为与复兴党组织机构、行政官僚体系并立的三大支柱之一。
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阿萨德凭借其个人的超凡魅力,在集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及民族进步阵线主席于一身的同时,其个人权威不断上升,进而超越了党政军各个国家权力或强力机构;而相对阿萨德个人权威的上升,复兴党等政治作用和地位相应下降、削弱了。更为严重的是阿萨德超凡的“克里斯玛式”领袖人物生命的有限性,预示着政党、国家及军队等领导力、凝聚力的不确定性。
二、叙利亚一党制总统威权体制与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政治学范畴。但是,政治稳定或政治失稳的因素,却存在于错综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中。”*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页。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伴随着经济发展与转型,催生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往往滞后于经济改革则是许多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复兴党一党独大的叙利亚也不例外。同时,叙利亚的政治稳定问题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宗教少数派统治多数派的现实使教派矛盾成为政治稳定的严重威胁,而内部夺权、继承人问题及全球化则消解着体制的合法性与认同感,由此,叙利亚一党制总统威权体制下政治稳定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控制与政治权威的构建(20世纪70年代)
1971年2月16日,阿萨德政府宣布建立人民议会。3月12日,阿萨德在只有一个候选人的选举中,以99.2%的支持率当选总统。同年5月和9月先后召开了叙利亚复兴党地区委员会“五大”和民族委员会“十一大”,重新组成复兴党民族和地区委员会,阿萨德当选为复兴党总书记。这两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阿萨德上台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即树立了自己对党的绝对权威。为了进一步确保他对党的控制,阿萨德不断清除异己,将大多数老资格的复兴党领导人投入监狱或流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自己的前任上司贾迪德投入监狱,并且于1972年命人暗杀逃亡黎巴嫩的乌姆兰。阿萨德的举动使与贾迪德、乌姆兰有教派关系的阿拉维人十分不满,一些亲贾迪德和乌姆兰的官员结成秘密组织,在伊拉克政权的帮助下,试图推翻阿萨德。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1972年12月,贾迪德的堂兄伊札尔·贾迪德发动政变遭到镇压,大约200人被逮捕。*Malcolm H.Kerr,“Hafiz Asad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Syrian Politics,” InternationalJournal,Vol.28,No.4(Autumn 1973),p.703.面对这类规模有限但却强有力的反叛活动,阿萨德恩威并施成功控制了政权。一方面他将正规部队和后备役军队中的几十位难以驯服的顽固派军官逮捕、清除或处决,其中包括七名高级军官。另一方面,他对部分亲贾迪德和乌姆兰的阿拉维官员采取了安抚政策,通过政权使他们获得既得经济利益进而换取他们对政权的支持。在赢得了阿拉维宗教领袖的支持后,阿萨德几乎成为全体阿拉维人政治上的最高代表、经济利益的保护人,甚至成为本民族的化身。1973年,42名军官被控计划谋杀阿萨德,而遭到处决。事实上是阿萨德偏好军中的阿拉维派,借机铲除军中逊尼派军官罢了。*周煦:《叙利亚史——以阿和平的关键国》,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第131页。大多数阿拉维人都承认阿萨德政权对他们的切身利益是至关重要,一旦政权丧失,阿拉维人的利益将面临严重威胁。
1975年4月,叙利亚复兴党地区委员会召开“六大”前夕,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再度凸现,党内元老派及贾迪德派欲参加竞选,企图重新挤入地区领导班子。而逊尼派和阿拉维派之间的宿怨也导致两派在“六大”期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权斗争,结果阿拉维派的地位得到巩固,逊尼派力量被削弱。在之后的历次复兴党民族委员会与地区委员会代表大会上,阿萨德都成功连任总书记,并且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事实上是阿萨德控制和内定的,选举的结果也由阿萨德预先决定。为了赢得城市逊尼派的支持与体现政权代表绝大多数民众的合法性,阿萨德坚持在地区领导机构中提高逊尼派成员的比例。“1970—1980年间,地区领导机构中有70%的逊尼派穆斯林,21%的阿拉维人、4%的德鲁兹人和5%的基督教派。”*摩西·马奥茨:《阿萨德传》,殷罡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82页。
政治权威作为一种让人们信从的政治威望与政治力量,它可能集中在某个个人或少数人身上,但实际上它还依赖政治、经济、组织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的配合与支持。*聂运麟:《政治现代化与政治稳定》,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通过政治清洗,阿萨德将个人权威最大化,上升为国家与民族最高权威的代表,同时又进行社会整合,将政治权威转化为政权合法性。叙利亚作为一个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国家内部存在着以地域、教派、部族甚至血缘为基础的多元认同,国家认同深陷多元认同交织的漩涡。*刘中民:《民族与宗教的互动: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312页。而只有当民众的认同对象集中在主权国家本身时,政权才可能最大程度上动员民众,从而实现国家与人民的有机融合。*田文林:《阿拉伯世界权力更替的内在逻辑》,《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7期。阿萨德掌权后就努力通过社会整合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谋求政治上的团结。
阿萨德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把来自不同地区、部族、宗派和阶层的民众和社会团体尽可能多地动员起来,接受复兴党的领导。大批阿拉维人、德鲁兹人、基督教徒和伊斯梅利人被吸纳进复兴党,同时,他对人口众多的逊尼派穆斯林给予特别注意,尤其是那些没有特权的下层民众,这些群体的加入使复兴党增色不少,用阿萨德的话讲,它表明复兴党是“劳苦大众的党”。据报道,大约1/3的逊尼派穆斯林农民在阿萨德掌权以后,被吸引到复兴党周围或纳入复兴党。队伍的扩大意义深远,说明阿萨德政权下唯一政党代表着全体叙利亚人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一个少数人的团体。这突出了阿萨德政权的民众性和文官性质,向叙利亚人民和全世界表明,阿萨德政权是最大限度的“人民民主”政权,而不是阿拉维的军事专权。为了进一步整合社会成员,阿萨德有意在政府机关及国有企业中实行超额雇佣。由于公有部门的福利待遇与社会地位都远高于其他单位,使得人们对此趋之若鹜。“政府的官僚机构与军事情报机构迅速膨胀,将数万叙利亚人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纳入阿萨德国家机器直接控制范围。1970年公共部门的雇员包括军事安全机构成员只有236000人,到1980年总数增长三倍达到757000人。”*Alan George,Syria:Neither Bread Nor Freedom, London: Zed Books Ltd,2003,p.10.同时,政府努力培养工会干部对党和政府的忠诚,通过对工会、各类行业组织达成对整个社会成员的控制。
社会整合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前提,而政治认同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看,亚非拉国家在建国后势必进行社会整合,其目的是在全体国民中间创造出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和公共文化,以及全体国民的归属感和政治认同,从而创造出维持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凝聚力。”*黄民兴:《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析当代中东国家的社会整合》,《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阿萨德通过复兴党的社会整合扩大了国家的权威及治理能力,提高了民众的归属感和政治认同,国家相对于教派、部落、族裔等,其地位得到大幅度提高,创造了维持政权所必需的凝聚力。
(二)失衡与政治稳定的挫折(20世纪80年代)
1980年,叙利亚全国14个省中有8个省发生动乱。*刘竞:《中东手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0页。“如同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叙利亚的20世纪80年代也将被铭记为‘错失发展的十年’。”*Volker Perthes,“The Syrian Economy in the 1980s,” Middle East Journal,Vol.46,No.1(Winter 1992),p.37.经济危机、教派冲突和高层夺权一度使叙利亚面临政治动荡的严峻威胁,总统阿萨德依托个人威权与经济改革扭转局面,重新巩固政治稳定。80年代叙利亚政治稳定虽然遭遇严重挫折,但依然没有动摇阿萨德一党执政体制的权力根基,这一统治模式继续沿着“纠正运动”以来既定的轨道发展,*王新刚:《20世纪叙利亚——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嬗变》,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但这些失衡的表现以及问题的凸显也充分说明阿萨德一党执政体制的弊病。
在之前的十年中,叙利亚人民已然习惯了可观的经济增长与虽不对等但大体上升的生活水平,但在80年代,人口的不断增长,购买力的下降,经济的停滞不前,这些经济而非政治问题使阿萨德政权面临上台以来的第一次合法性危机。*Volker Perthes,“The Syrian Economy in the 1980s,” Middle East Journal,Vol.46,No.1(Winter 1992),p.37.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稳定在所难免受到经济问题的影响。
80年代开始,叙利亚经济危机症候开始凸显。经济增长与衰退之间的转折点出现在1979—1983年间,通货膨胀率上升,在史无前例的30%波动,导致大多数人生活极度困窘。直至1982—1983年,阿拉伯世界相对充裕的经济援助掩盖了至少一半的贸易逆差。*Volker Perthes,“TheSyrianEconomyinthe1980s,” p.39.然而,好景不长,伴随西方经济危机,石油市场供过于求,国际油价下跌,使阿拉伯产油国的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对外援助锐减。此外,叙利亚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朗的立场也招致阿拉伯世界的孤立,海湾产油国对其资本输出及叙利亚劳工的侨汇收入都明显减少。由于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军事干涉以及谋求与以色列的军事平衡战略,军费开支大幅增加,“1984年国防开支比1978年增加了3倍,占1984年叙利亚经常性开支预算的56%和全部政府预算的30%。”*摩西·马奥茨:《阿萨德传》,第183页。庞大的军事开支加剧了国库紧张,造成经济建设缺乏必要的资金保障,使得政府债台高筑,外汇储备告罄。而农业部门发展迟缓,由于政府重点发展工业战略以及严重的旱灾等自然灾害频繁,致使农业歉收,无力满足人口增长与工业发展需求,国家不得不耗费大量本已十分短缺的外汇储备购买食品。工业领域也不容乐观,尽管阿萨德放宽对私营经济限制,国营经济依然居主导地位,政府对国有部门统管过死,管理不善导致工业产量不高,效益低下,“据估计,在1983年单就一家国营工厂损失了20亿叙镑。”*Steven Plaut,“The Collapsing Syrian Economy,” Middle East Quarterly,Vol.6,No.3(September 1999),http://www.meforum.org/476/the-collapsing-syrian-economy.叙利亚宏观经济形势全面恶化,“80年代的经济衰退已成定局,连续8年国家财政预算赤字猛增。官方估算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自1982年至1987年间下降了15%,生活水平指数(由官方消费者物价指数折算人均私人消费量来衡量)下降了灾难性的37%。”*Eliyahu Kanovsky,“Syria’sTroubled EconomicFuture,” Middle East Quarterly,Vol.4,No.2(June 1997),p.25.
严重的经济问题常常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社会问题的凸显,高出生率、高失业率以及高贫困率已成为普遍问题。贫富两极分化,国内矛盾丛生,阿萨德政权受到激烈批评,统治基础动摇,威胁政治稳定。急剧的通货膨胀使工人以及中下层国家雇员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他们无力应对不断攀升的物价带来的生活负担。而为数众多的农民处于失业状态,城市化进程使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涌入城市谋生,但他们的生活境况十分困窘,贫穷而没有保障,大多朝不保夕。“1965—1980年间,大马士革人口翻了一倍,从678,000增长到1,327,000人。城市人口激增导致首都有增无减的住房危机。飞速的城市化遍及全国,1960年总人口中只有37.5%居住在城市,到80年代初期已经超过一半,城市化将来自农村的贫困人口集中在一个区域,更加剧了贫困。严重贫富分化导致人们的政治认同危机”。*Alasdair Drysdale,“The Asad Regime and Its Troubles,” MERIP Reports,No.110,November/December1982,p.6.
伴随经济危机与国内局势的动荡,叙利亚政坛又因阿萨德健康状况恶化而爆发了权力之争,几乎引发内战。在阿萨德患病期间,他的胞弟里法特向总统的权杖发起挑战。1984年2月,里法特将他控制下的部队开进大马士革市内和郊外各个要点,准备发动军事政变接管权力。但他的图谋遭到大多数“贾马阿”成员与其他元老的强烈反对,他们依然效忠于阿萨德,同时也害怕里法特威胁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政权延续。双方展开武装对抗,内战一触即发。阿萨德虽身处病榻,但对外界的消息却了如指掌。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当机立断,强撑病体只身前往里法特的驻地,面对面盯着弟弟呵斥道:“你要推翻国家吗?我就站在你的面前,我就是国家!阿萨德就是叙利亚!”*Patrick Seale, Asad:the Struggle for the Middle East,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433.里法特不知所措,更不敢轻举妄动。阿萨德平息了胞弟的夺权行动,随后重新改组政府,史无前例地任命了包括里法特在内的三位副总统,但他们并没有实权,更多的是相互之间的权力制衡,阿萨德不动声色地解除了里法特的兵权。同时,阿萨德在军队中进行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对参与里法特反叛的将领绝不姑息,进行了严厉惩处。“里法特与阿萨德之间长期的权力斗争最终在1985年1月5日至20日的复兴党地区委员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画上句号,里法特形式上被重新选入叙利亚地区委员会,但事实上被孤立,很快被流放到欧洲。”*Nikolaos Van Dam,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Syria: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Asad and the Ba’th Party,I.B.Tauris,2011,pp.121-122同时,在“八大”上阿萨德对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对党、政部门的控制进一步加强,政局趋于稳定。在1985年2月的总统选举中,阿萨德作为唯一候选人以99.97%的支持率再次当选。*Derek Hopwood,Syria 1945-1986: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Unwin Hyman Ltd,1988,p.71.
80年代后期,民众对经济状况不满情绪愈演愈烈,演化为公开批评,政府显然无力应对危机。*Volker Perthes,“The Syrian Economy in the 1980s,”Middle East Journal,Vol.46,No.1(Winter 1992),p.37.1987年11月,阿萨德大刀阔斧地对政府进行改组,任命祖阿比担任总理,组建了新一届内阁。新政府奉阿萨德总统指示,通过渐进的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在大力发展农业和石油支柱产业的同时,鼓励非石油和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同时,进一步放宽私营经济,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最终扭转了经济困局。在1987年的改革之后,国内生产总值回升,年增长率不断提高,基本达到了4%,90年代初期,甚至高达8%。*王新刚:《20世纪叙利亚——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嬗变》,第190页。经济形势的好转对扭转动荡的政治局面起到了助推作用,国内政治日趋稳定。
(三)转型与政治稳定的隐患(20世纪90年代)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20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复兴党政权奉行的复兴社会主义面临挑战,国内民众对复兴党意识形态产生怀疑,同时政府的腐败专制加重了这种怀疑。在大马士革的街头巷尾,出现了打倒专制的口号和标语,一些要求推行西方民主自由的政治主张也出现在私下议论和传单中。但是,阿萨德鉴于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认为,任何政治上的改革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害关系,有可能导致整个统治秩序的瓦解。*Eyal Zisser, Asad’s Legacy:Syriain Transiti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1,p.181.而且,90年代阿萨德政权处于权力换代的关键期,此时一旦放开所谓自由民主,仅占总人口12%的阿拉维派是无法掌控政权的,多数派将重返权力中心。 “阿萨德和他的军政府深知在政治开放的方向上迈进一步,都有可能将他、他的家人和整个阿拉维族群扔进‘历史的垃圾堆’。”*Steven Plaut,“The Collapsing Syrian Economy,” Middle East Quarterly,Vol.6,No.3(September 1999),http://www.meforum.org/476/the-collapsing-syrian-economy.关于民主,阿萨德重申:“叙利亚实行的民主制度是无法依靠强行嫁接某些国家的模式得来,它不是僵化、固定的理论架构,而是深深植根于叙利亚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土壤中。”*Eyal Zisser,Asad’s Legacy:Syriain Transition, p.182.基于这样的理念,阿萨德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表现得比经济自由化更加小心翼翼。
为了应对民主化浪潮和国内改革压力,阿萨德政权不得不摆出改革的姿态,开始营造政治民主化氛围。这在1990年的议会选举中得到体现,这届议会议席由195增至250,其中三分之一是独立人士,他们代表了新兴阶层或以前与复兴党政权较为疏远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包括部落领袖、土地主、城市职业者、学者、商人,特别是新的商业资产阶级和私营企业代表。“叙利亚的议会改革,可以理解为一个‘社团主义’的策略,以应对既要满足政治参与需求又要组织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技术要求。”*Volke Perthes,“Syria’s Parliamentary Elections:Remodeling Asad’s Political Base,” MiddleEast Report,Vol.22,No.174(February 1992),p.18.虽然不能说是“民主化”,但可能意味着阿萨德所依赖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政治基础逐步重塑。*Volke Perthes,“Syria’s Parliamentary Elections:Remodeling Asad’s Political Base,” p.16.另外,1991年12月开始启动通过公民投票选举总统的程序,这一年政府大赦2814名政治犯,到1995年大约有5000多名政治犯获释。但是原定接班人巴西勒的意外死亡使阿萨德再度紧张起来,为了避免高层争权,他将一批元老级官员解职,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控制,有限的政治改革便止步不前。
在阿萨德一党执政体制下,叙利亚国家精英阶层分为两部分:通过控制军队和安全机构来掌握政治权力的阿拉维军官,与占据经济权力中心的逊尼派城市商人阶层。阿萨德在过去运用政治经济大权将两方精英力量联合成为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和拥护者,然而90年代,伴随国内外局势的变迁,三个核心问题侵蚀着精英集团的凝聚力。“第一,新的经济自由化计划正在塑造新的受益者和失利者,正在弱化维持政权稳定的政治结构。第二,大马士革的为独裁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消退,不断产生对政治自由化的呼声。第三,由于当局答应对区域和平负责,大马士革将不得不重构它和黎巴嫩的关系,有可能丧失支撑叙利亚政权的关键来源。”*Glenn E. Robinson,“Elite Cohesion,RegimeSuccession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Syria”,Middle East Policy, Volume 5,Issue 4,1998,pp.159-160.三个问题导致两个精英集团利益的分歧:一方面,逊尼派在重大的市场变革、真正的政治自由化和削弱与黎巴嫩的关系三个方面具有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阿拉维军事精英的利益存在于限制市场改革、维持一个独裁主义政权体系和继续控制黎巴嫩三个方面。精英凝聚力的分化加剧了叙利亚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离心倾向,成为政治稳定的巨大隐患。
作为长期执掌叙利亚党政军大权的阿萨德深知,在他苦心经营的威权主义权力结构中,任何其他力量的单独崛起都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坍塌。“当他死后,一些元老级人物将为权力展开角逐。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极有可能造成阿萨德整个政治体制的崩溃。然后叙利亚政治将复辟到之前派系增殖、军人干政、政治动荡的历史困境中。”*Daniel Pipes,“Syria after Asad,” World and I,February 1987,http://www.meforum.org/pipes/177/syria-after-asad.此外,由于阿萨德体制是宗教少数派阿拉维派占据权力中心的政治体制,他们的统治秩序长期招致逊尼派穆斯林的不满与仇视。阿萨德去世后,“奇里斯玛式”威权的缺失而引发政权危机,极可能导致逊尼派卷土重来,进而造成叙利亚政治的转型和阿拉维部族的衰落。“阿拉维派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一旦他们失去了权力,很可能会有一个大清洗。”*Daniel Pipes,“Syria after Asad,” World and I, February 1987,http://www.meforum.org/pipes/177/syria-after-asad.因此,从维护国家政局稳定和家族利益的立场上考虑,只有“子承父业”的家族世袭制才能保证政权交替的有序性。
阿萨德长子巴西勒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是最理想的接班人。巴西勒长期伴随其父左右,阿萨德倾注了全部心血扶持巴西勒树立其在党政军中的威信。然而,1994年一场车祸夺取了巴西勒的生命,也使阿萨德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接班人计划遭遇严重挫折。巴西勒死后,阿萨德精神上虽然受到巨大打击,但依然没有改变其子承父业的权力交接初衷,阿萨德力排众议,竭力培养次子巴沙尔接班。他曾对周围的亲信说:“继任者除了巴沙尔,别无他人。”然而巴沙尔并无从政意愿,他于1992年远赴英国攻读医学学位,在国家政坛和军界毫无影响力。*Steven A.Cook,“On the Road:In Asad’s Damascus,” Middle East Journal,Vol.3,No.4(December 1996),p.41.阿萨德明白,若想确保毫无根基的巴沙尔在自己身后顺利登上权力巅峰,必须帮他争取到党政军的支持以及叙利亚民众的拥戴。但前提是,巴沙尔要首先证明自己有领导国家的能力。于是,在阿萨德的精心安排下,巴沙尔开始了政治资本的积累过程。他首先被送进叙利亚霍姆斯军事学院受训,5年之后晋升为上校军衔,让他获得在军队供职的经验;授权他负责黎巴嫩事务,以证明叙利亚的战略利益在他的手中完全可以放心;让他负责信息技术工作,支持使用因特网,意在使他得到迅速增多的叙利亚青年一代的拥护。*彭树智:《阿拉伯国家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5页。在叙利亚国内,巴沙尔和阿萨德的画像经常并排悬挂,有的地方还与其父及兄长的画像并排悬挂,利用媒体和舆论提高巴沙尔的影响力。*时延春:《中东风云人物》,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25页。阿萨德利用他的绝对权威,将有野心的老臣逐一排除,为巴沙尔接班铺路。90年代末,叙利亚政坛高层变更频繁,副总统里法特、总参谋长谢哈比、情报部门主管纳贾尔等一批年长的领导人被解职,一些阿拉维派年轻人得到提拔。经精心培养和铺路清障后,巴沙尔最终子承父业,叙利亚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
但是,依据1973年宪法,叙利亚作为共和制国家,实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组织形式,总统需经选举产生。因此,任何指定继承人的做法都是违宪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阿拉伯新生代政治家》,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83页。子承父业的“世袭制”权力交接模式无疑造成严重的政权继承危机,所谓“继承危机”反映的是权力交接的不确定性,是强人政治不可避免的问题,根本原因是最高权威代表变更与政治合法性的衰减。*陈德成:《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08页。阿萨德作为“奇里斯玛式”领袖,政权合法性是以对某个人特有的非凡神圣性、英雄气概或模范性格的忠诚为基础的。*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90页。这种建立在“人治”模式上的合法性没有足够的制度保障,继承性较差,是无法延续到其指定的接班人身上。因此,不管阿萨德如何的精心布置,世袭制必然带来政权合法性的衰减。“尽管阿萨德正在帮这个34岁的儿子继位,并且已经清除了军队和政界的潜在对手,但是巴沙尔还没有经验与资历来独自维持统治威权,并且可能与大马士革复兴党政权关系网的元老们分享权杖。”*IISS, “Syria after Assad,” Strategic Comments,Volume 5,Issue 7(September 1999),p.1.而且,由于老一代的统治者在维护个人权威、家族利益的前提下,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阶层矛盾。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民众将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继任者就不太可能拥有其前任们那样多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已无法为新生代的领导者提供持续有效的政治资源,因此其必然面临严峻改革挑战。
(四)改革与政治稳定的重建(21世纪前10年)
2000年6月10日老阿萨德突发心脏病逝世。7月,巴沙尔·阿萨德子承父业,以97%的高票当选总统。为使年仅34岁的巴沙尔·阿萨德合法继任总统,人民议会临时修改宪法第83条,将总统任职年龄从40岁调整为34岁,并选举巴沙尔为复兴党总书记,晋升陆军大将,担任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巴沙尔执政后在政治上推行有限的民主化,强调实行复兴党领导的、通过全国进步阵线完成的政治多元化;巴沙尔认为叙利亚必须“在正常的地区过一种正常的生活。”*Barry M. Rubin,The Tragedy of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2002,p.112.巴沙尔在就职演说中曾提出,将“考虑民主问题”、“改革政治机构”和“提高政治公开性”。“我们急需要建设性的批评,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客观地思考和考察每个问题。”*Barry M. Rubin,The Tragedy of the Middle East, p.108.他宣布实施政治和经济改革,释放政治犯,推进反腐运动,减少军费开支等等,外界普遍认为叙利亚出现了“大马士革之春”的民主气象。
巴沙尔政府主要举措之一是赋予人民议会更多的权利。多年来,人民议会一直决策乏力,只是政治多元化的象征,仅仅是给复兴党政权涂上了民主色彩。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民议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逐步凸显,对政治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1990年5月2日的人民议会选举中,代表席位由195人扩大到250人,其中包括对复兴党政权持批评意见的独立人士和不同政见者。2005年6月,复兴党叙利亚地区委员会召开第10届代表大会,这是巴沙尔执政后5年来复兴党首次召开地区委员会代表大会。巴沙尔在大会上宣称,改革将取得“巨大的进步”。*罗宾·休斯、倪海宁:《改革陷入困境,外部压力推动军力建设:叙利亚安全形势透析》,《国际展望》2006年第3期。在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下,叙利亚国内政治、经济论坛等大量涌现,引起更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向政府呼吁给予社会更多自由以及承认政治多元化。然而,因库尔德民权运动等活动高涨,各类政治论坛的活动及言论逐渐超越了政府容忍的底线。察觉到叙利亚国内局势存在失控风险后,巴沙尔政府逐渐放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雄心,开始抨击逾越雷池的“改良主义者”,加强对社会的控制。2001年9月叙利亚政府逮捕了“公民社会运动”中最著名的活动家们,“大马士革之春”随即也昙花一现地宣告落幕。
此后,巴沙尔将叙利亚国家体制改革的目标由政治、社会转向经济领域,大力吸引外资、鼓励并扶持私企,进一步采取经济开放政策,目的是鼓励经济活动,将经济精英和逊尼派城市中产阶级整合到国家经济体系中。这一政策使城市商业精英富裕的同时,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新问题,即两极分化。昔日政权的支持者低层社会、工人、农民和城市市民逐渐边缘化、贫困化。据官方报道,2006年叙利亚的失业率大约是20%~25%,实际数据可能远高于官方报道。据政府估计,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十年内创造300万个就业岗位,每年提供30万个。而2009年叙利亚财政赤字达1930亿叙镑(约合41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4%。*高兴福:《叙利亚投资市场分析》,《西亚非洲》 2009年第10期。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意识形态上的宣传以及国家安全的考量,复兴党政府经济政策仍在国营与私有、计划与市场的两难中徘徊,这无疑影响了政府的经济决策和民众热情,造成经济发展的迟缓。复兴党政府经济上的改革由于受政治约束,不仅收效甚微,而且无力剪除经济中的结构性弊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将叙利亚说成是“博物馆里的收藏品”——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还保留着1965年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新华社联合国2000年6月18日英文电。政府不能实行完全的经济自由化,叙利亚复兴党也不愿意看到国家对经济失去控制。
巴沙尔时期叙利亚复兴党在私有化方面踌躇不前,也有其自身的难题。政权的主要支柱阿拉维派,由于受政府保护,在商业、政府和军事等部门都居于优势地位。出于政治安全考量,叙利亚政府并不想大刀阔斧地改革,因为私有化真正的受益者将会是对现政权心怀不满的逊尼派穆斯林。因此,一旦经济发展和政治诉求产生矛盾时,当权者往往会牺牲前者。现代化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进程,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必然引发政治的变化。没有政治的协调发展,经济和社会也是不可能发生变革的。政治意愿、政治权威和政治技巧是保证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而这正是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国家经济现代化所缺乏的。
(五)危机与政治稳定的困境(2011年至今)
2011年3月,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反政府浪潮开始波及叙利亚,使其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从最初的民间示威抗议,发展为有组织的反政府武装行动,叙利亚危机愈演愈烈,政府面临极度困境,国内陷入内战深渊,成为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重灾区。然而,当其他阿拉伯国家出现政权倒台乃至开启新一轮政治重建之时,叙利亚国内仍硝烟弥漫、枪声不断,以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为首的复兴党政权与各路反对派及宗教极端组织陷入残酷的缠斗,政权面临严峻挑战。
叙利亚自2011年3月15日发生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以来,政治多元化一直是反对派和示威者最主要诉求之一。随着示威抗议活动与暴力冲突此起彼伏、相互交织以及伤亡人数增加,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内忧外患日益严重。2011年上半年,巴沙尔总统采取改组政府、释放政治犯、取消《紧急状态法》等一系列措施,并授命以萨法尔为总理的新政府制订涉及政治、安全、司法、经济、社会和行政改革等诸多领域的全面改革计划,成立《选举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参照其他国家相关法律,制定“与当今世界现行法律接轨”的新大选法草案。8月4日,巴沙尔政府颁布允许多党制政体的政党法,作为推动政治改革、回应反对派和反政府示威者核心诉求的一项举措。政党法允许成立新政党,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同发挥作用。同时,巴沙尔政府也积极推进改革,宣布废除“紧急状态法”和国家安全法庭、释放政治犯、放松对媒体控制、开展民族对话、实行多党制、提高库尔德人地位、改善民众生活等。2011年7月,巴沙尔政权重新控制了中部和南部的主要城市。以上举措使局势暂时得到平息,但并未根本解决国内政治危机。2011年12月,叙利亚在乱局中举行地方选举,该次选举取消了民族进步阵线必须取得50%以上席位的规定。尽管如此,政治多元化未能阻止叙利亚的乱局,叙利亚境内的反对派迅速兴起,构成威胁巴沙尔政权的主要力量。2012年以后,叙利亚内战局势日趋白热化。一方面,反对派逐渐夺取政府控制的阿勒颇等重要据点,政府军在内战中的压倒性优势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反对派内部的矛盾凸显,作为反对派军事协调组织的叙利亚自由军影响力有限,各反对派武装独立性加强。反对派武装与政府军,以及反对派武装之间在叙利亚全国范围展开激烈混战。宗教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势力迅速膨胀。2013年至2015年,叙利亚政府逐渐丧失主导权,内战陷入僵持,“伊斯兰国”在内战中迅速坐大,发展成为叙利亚、中东地区乃至世界性重大安全威胁,国际社会也开始深度介入进行联合反恐。2014年叙利亚内战期间举行的大选中,巴沙尔以83%的得票率第三次蝉联总统,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巴沙尔多次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外部干涉,并做好与国家共存亡的准备。2015年9月俄罗斯正式军事介入叙利亚,大批俄罗斯军机进驻叙利亚。2016年1月,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叙利亚政府军对外宣布,已将反对派武装彻底逐出拉塔基亚省。*Syria Conflict: Major Rebel Town ‘Seized’ in Boost for Assad, BBC, 24 January, 2016.随后,叙利亚政府军在南方完全控制了德拉省的战略重镇马斯卡因,*Barry Temmo, Update 4-Army Establishes Full Control over al-Sheikh Miskeen in Daraa and a Village in Aleppo, Syrian Army Seizes Strategic Town in Deraa Province: Monitor Reuters, 25 January,2016.并且成功挫败“伊斯兰国”对代尔祖尔省叙政府控制区域的进攻。2017年11月20日,巴沙尔总统飞抵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国元首共同对外宣布已战胜“伊斯兰国”,并声称正式开启国内政治和解进程。至于这一进程前景究竟如何,仍有待后续观察。不过可以预期的是,叙利亚国内局势虽有好转,但许多关键性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特别是各派势力在短期内达成和解的可能几乎为零。
在俄国等干预下,巴沙尔政权维系至今,叙利亚政党政治和政府政治均处于非正常的运行状态。尽管未来叙利亚政治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是复兴党独掌大权的局面将被打破。叙利亚社会也将沿着民族和教派的界线发生裂变,没有一股力量有能力成为主导统治力量。民族和教派冲突将成为叙利亚的政治标签,后者也可能变成下一个伊拉克。如同其他的后冲突国家一样,叙利亚也将由复兴党统治下的“强国家”变为“弱国家”。叙利亚的未来不仅决定于叙利亚能否创制出适合国情的制度文明和实现民族和解,更决定于国际社会的作用。
三、叙利亚政党制度矛盾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当前叙利亚的政治矛盾主要集中在复兴党政府和怀有不同诉求的各反对派之间,其实质是长期执政的复兴党与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的各社会政治阶层之间的冲突。叙利亚复兴党一党独大政治格局演变具有浓重的军人夺权、个人专权、家族统治、教派纷争的色彩,该政权几乎集中东威权政治国家众多不同特点于一身,因而是所谓“茉莉花革命”的直接对象。阿拉伯世界政治的动荡以及外部干预固然是导致叙利亚复兴党陷入执政危机的重要原因,但危机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其政党政治发展滞后与民族国家建构失败的结果,特别是在于其未能妥善处理政治认同、体制改革、意识形态、社会整合、经济发展、教派民族以及对外交往等社会政治问题。内战作为其执政危机的总体呈现,是各种致危因素相互碰撞而产生的政治合力的必然结果。
(一)精英阶层分化与权力高度垄断的矛盾
在阿萨德家族统治下,叙利亚国家精英阶层分为两部分:通过控制军队和安全机构掌握政治权力的阿拉维军官,与占据经济权力中心的逊尼派城市商人阶级。老阿萨德在过去运用政治经济大权将两方精英力量联合起来并成为政权的既得利益拥护者。然而,如前所述,90年代伴随国内外局势的变迁,三个核心问题消解着精英集团的凝聚力。精英凝聚力的分化加剧了叙利亚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离心力,成为政治稳定的巨大隐患。以色列学者埃亚尔·齐塞尔(Eyal Zisser)认为,在阿萨德统治的最后十年,叙利亚已经陷入绝境。更糟的是,它还面临着很多紧迫的问题,如政权的继承、社会经济危机、全球化、黎巴嫩的动荡,以及与以色列的关系。总之,老阿萨德留给儿子的是一个衰败中的国家。并质疑巴沙尔是否能够控制复兴党,因为他缺乏其父的刚强果敢。*Eyal Zisser, “Will Bashar-Asad Last?” Vol. 7,Issue 3(Sep. 2000), p.3.
巴沙尔上台后,继承其父的政治遗产,无可避免地也面临精英阶层凝聚力分化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垄断和控制,以巩固其统治,巴沙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通过迫使复兴党内“元老”退休,以培植亲信、强化个人的权力和消除改革的阻力。2005年,复兴党叙利亚地区委员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阿萨德时期的实权人物被迫辞职。据估计,巴沙尔上台后,各级政府、复兴党组织及其议会中60%的官员陆续退休。*Shmuel Bar,“Bashar’s Syria:The Regime and Its Strategic Worldview,” Comparative Strategy,Vol.25,Issue 5,2006,p.371.巴沙尔将那些忠于自己、具有改革精神和专业素质的青年官员安插到政府和军队的各部门。巴沙尔的弟弟马赫尔(Maheral Assad)和姐夫阿瑟夫(Assef Shawkat)*阿瑟夫属逊尼派,2011年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在2012年7月18日发生的袭击中身亡。分别被任命为共和国卫队和军事情报部门的领导人。巴沙尔通过上述举措控制了复兴党,加强了个人权力,但是却严重削弱了复兴党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复兴党在高级官员选拔和制定内外政策中的作用逐渐丧失。*Raymond A.Hinnebusch,“The Ba’th Party in Post-Ba’thist Syria: President,Party and the Struggle for ‘Reform’,” Middle East Critique,Vol.20,No.2,2011,p.124.此外,尽管巴沙尔提拔的年轻官员大多是阿拉维派,但他们出生于城市,接受西式教育,与阿拉维派部落联系并不紧密,而且也缺乏政治和军事历练和治国经验。因此,巴沙尔在打击复兴党内异己力量的同时也削弱了复兴党的执政能力。2010年,巴沙尔辞退了一大批复兴党的基层和中层干部,这些人本来在控制社会和调解族群、部落与宗教冲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Dawn Chatty,“The Bedouin in Contemporary Syria∶The Persistence of Tribal Authority and Control,” The Middle East Journal,Vol.64,No.1,2010,pp.29-49.结果复兴党出现了“空心化”趋势。巴沙尔对军方一直心存芥蒂,废除了军人的司法豁免权,并且禁止军方通过商品走私等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由于军人正式的官方收入相对较低,这一措施引发了军方不满。总之,巴沙尔个人权力的加强是以打破老阿萨德所建立的以复兴党为基础的政治体系为代价的,巴沙尔个人权力只能建立在阿萨德家族和阿拉维派的小圈子之上,由此造成了巴沙尔政权统治基础变窄,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减弱。
另一方面,巴沙尔政治改革的骤然停滞与叙利亚社会对政治变革和现代化日益强烈的诉求之间形成矛盾。巴沙尔执政之初,新政权面临着新形势下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双重挑战,巴沙尔曾以工具理性原则在叙利亚推行大规模的政治自由化改革,强调实行复兴党领导的、通过全国进步阵线完成的政治多元化。他宣称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等,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叙利亚的公民意识,并使他们对现政权产生了较大的期待。然而,在察觉到叙利亚政治局面逐渐出现失控危险后,巴沙尔又迅疾终止了绝大部分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自由化实践。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政治姿态,直接导致叙利亚社会对巴沙尔政权的信任、忠诚度的急速下降,并引发了人们对现行威权体制合法性的普遍质疑。随着叙利亚经济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及转型,这种质疑声日益强烈,并最终引爆了变革上层建筑的强大民意。
(二)社会结构碎片化与政治认同缺失的矛盾
叙利亚历史上长期遭受外族统治,从而形成了多民族、多宗教、多教派的社会结构,“马赛克”式的族群和碎片化的教派结构是政治生态的基本态势。从民族结构来看,叙利亚1843万总人口中,*https://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SY.阿拉伯人占80%以上,另有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等。从宗教文化认同看,叙利亚处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的重要影响地区。现代叙利亚民族国家诞生后,呈现多种宗教和文化共生的现象。主要包括伊斯兰教逊尼派、阿拉维、德鲁兹、伊斯玛仪、基督教马龙派、亚述教派以及雅兹迪异教派等。由于存在多种教派和族群,不同的教派和族群在国内有不同的地位和发展空间,宗教矛盾还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国内教派摩擦不断,族群矛盾重重,这是影响叙利亚局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叙利亚的政治体制是宗教少数派阿拉维派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体制,他们的统治秩序长期深受逊尼派穆斯林的不满甚至仇视。巴沙尔政府曾试图通过强调当代叙利亚与倭马亚王朝、抗击十字军的萨拉丁和抗击蒙古人的拜伯尔斯,甚至与罗马帝国的历史联系,强调叙利亚历史文化发展的独特性,以便强化民众对于历史和领土的认同,从而强化民族国家的认同。但是,巴沙尔的这些努力非但没有弥合叙利亚社会的裂痕,反而被严酷的政治现实撕裂。其一,巴沙尔政权仍然由阿拉维派掌控。尽管巴沙尔在公众面前一直强调自身的阿拉伯属性,淡化宗教上的差异,但其权力基础仍然是阿拉维派,特别是阿萨德家族所属的卡拉比亚部落(al-Kalabiyya)。国家高级军官中90%来自阿拉维派,他们控制了主要政府部门。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哈马血案”后,逊尼派中下层和阿拉维派相互仇视在巴沙尔时期并未缓解。其二,复兴党社会主义破产。巴沙尔削弱了复兴党的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复兴党社会主义。*Raymond A.Hinnebusch,“Syria:from Authoritarian Upgrading to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8,No.1,2012,p.98.经济改革及其造成的社会问题,也使复兴党一贯倡导的“均贫富”观念被遗弃。在对外交往方面,2005年叙利亚被迫从黎巴嫩撤军并与以色列进行谈判。这与巴沙尔一直坚持的反以反美的阿拉伯主义相矛盾,曾经统一和团结民众的复兴党社会主义全面瓦解,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在这种背景下,伊斯兰主义和自由主义日趋填补了认同的空白。也就是说,巴沙尔打破了叙利亚旧的国家认同,但并没有建立起新的认同。在叙利亚,复兴社会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和自由主义具有竞争性。这三种意识形态往往又和家族、部落、族群和教派认同相互交织,伊斯兰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反对阿拉维派独占权力的思想表达,成为政治反对派的主要精神力量。
叙利亚危机本质上是民族建构失败的表现。老阿萨德通过国家政权的复兴党化、复兴党和安全部门的阿拉维化、国家权力的个人化和家族化等措施实现了国家的稳定,但他并没有能够解决民族国家建构的根本问题,即如何在具有多样性民族和教派结构的分裂型社会实现权力的相对均衡和有效分配,以及如何建构具有全民性的国家认同。而这些问题在巴沙尔时期仍未得到解决,这是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
(三)政治改革有限性与腐败问题严重的矛盾
在叙利亚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推行的是政治稳定优先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为了给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有序的政治社会环境,不给或少给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独立自主的“自由权利”,或者在法律上给了,而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很难行使,政府加以种种限制直至完全取消。在推进经济迅猛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政治变革却没有取得相应的进展,民主体系无法形成,政治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紧张。国家内部不断衍生诸多令民众深恶痛绝的痼疾:个人专断的猖獗、权力运行不透明;政府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当权者疯狂聚敛钱财、官宦腐败成风。这些问题最终都转化为诱发社会剧烈动荡的酵母和催化剂。“高层官员利用职务之便竭力营私,攫取国家财产,掌控就业渠道,监管进出口和私营部门的投资许可,负责政府采购合同,特别是在进口贸易和建筑领域。不容分说,这一群体利用贿赂盗窃国家财富。”*Volker Perthes,“The Bourgeoisie and the Baath:A Look at Syria’s Upper Class,” Middle East Report, Vol.21(May/June 1991),pp.33-34.极权统治为家族利益和新生的阿拉维权贵服务,政治腐败的滋长蔓延一方面对政权合法性造成严重威胁,瓦解政治稳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阿拉维派成为“暴发户”的事实更加招致逊尼派商业阶层的不满。
巴沙尔执政后,通过大力发展经济维护政权合法性,开始尝试经济自由化改革。2005年,他提出建立“社会的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即在保持一定程度的国有经济部门的同时,扩大私营经济的比重,放松对外资和金融业的管制,这些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叙利亚的经济发展,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自由化改革的主要手段是私有化,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私有经济比重很快超过国有经济。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与巴沙尔政权有密切联系的阿拉维派大商人和官僚。他们垄断了国家主要私有经济部门,形成官僚资本。例如,巴沙尔的表兄拉米·马克鲁夫(Rami Makhlouf)控制了包括通信、石化、金融、零售业和航空在内的几乎60%的经济部门。*Michael Peel,“Assad’s Family Picked up by the West’s Radar,” Financial Times,April 27,2011.改革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和贪污腐败现象。5%的人占有50%的国家财富。*Omar S Dahi,Yasser Munif,“Revolts in Syria:Tracking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Authoritarianism and Neoliberalism,”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Vo.47,No.4,2011,p.328.随着20世纪8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步入劳动力市场,*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以来,叙利亚的人口翻了一倍。参见Anna Borshchevskaya,“Sponsored Corruption and Neglected Reform in Syria,” Middle East Quarterly,Vol.17,No.3,2010,pp.43-44.青年人的失业率不断攀升。2011年失业率为30%,*Jihad Yazigi,“Syrian Unemployment at Twice Previously Estimated Level,” Syria Report,December 19,2011.其中男女青年的失业率分别高达67%和53%,大学毕业生通常在毕业4年后才能找到第一份工作。*James L.Gelvin,The Arab Uprisings: What Everyone Need to Kno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08.与此同时,政府却大量削减对教育、住房、医疗、食品、燃油和养老等公共部门的投入,导致社会下层的生活水平下降,接近50%的民众居住在贫民窟,在大马士革更是高达70%。*Robert Goulden,“Housing,Inequality and Economic Change in Syria,”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38,No.2,2011,pp.188,201.
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滞后,加之经济自由化改革缺乏渐进的、总体的战略,腐败在政府机构和国有部门迅速扩张,财富大多被最高领导人的亲朋属从、官僚和权贵瓜分。而且,有限的改革不仅无法缓和社会矛盾,反而破坏了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脱节,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民众与统治阶层的严重对抗,最终削弱了政权的社会基础。
(四)地缘政治复杂性与个人威权式微的矛盾
叙利亚地处中东的“心脏”,既是西方国家觊觎的对象,也是中东地区什叶派和逊尼派争夺的焦点。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叙利亚视为“无赖国家”。伊拉克战争后,美国陆续通过了多项制裁法案,对叙利亚进出口、外国投资和金融部门进行制裁,*Jeremy M.Sharp,“Unrest in Syria and U.S.Sanctions Against the Asad Regime,” CRS Report for Congress,RL33487,August 9,2011,pp.24-30.并且公开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美国试图借此颠覆复兴党政权,使叙利亚成为其“大中东计划”的另一块拼图。另一方面,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激化,叙利亚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而叙利亚在西方国家打压下,日益加强与伊朗的联系,成为伊朗在黎巴嫩扩展影响的中介,出现了所谓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因此,叙利亚与海湾君主国的关系恶化,后者试图孤立叙利亚,剪除伊朗的“羽翼”。*Frederic Wehrey,Saudi-Iranian Relations since the Fall of Saddam, RAND Corporation,2009,p.89.此外,叙利亚与土耳其关系也充满变数。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在中东推行“零问题”外交,叙土关系逐渐摆脱之前亚历山大勒塔争端及库尔德人问题的阴影,两国关系得到改善。然而,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动荡为土耳其扩大在中东影响力,乃至填补中东权力真空带来契机。因此,土耳其开始支持叙利亚的伊斯兰主义反对派,以强化“土耳其模式”在中东的影响力。
老阿萨德是中东国际舞台上的政治雄狮和外交强人,他领导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精明老到的外交谋略使叙利亚在中东地区树立起政治、军事和外交大国的形象。但是,阿萨德去世后,“奇里斯玛式”威权的缺失,其子巴沙尔虽然继承其政治遗产,却无法继承其政治权威。因此,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和沙特、土耳其等邻国积极插手叙利亚事务,不遗余力地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主要为逊尼派),力促巴沙尔下台。与其他经历动荡的阿拉伯国家相比,叙利亚问题不仅具有更为复杂的历史根源,而且还与外部因素紧密交织。
结 语
一国的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之间的联系是动态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通常总有一种政治体制是特别适合于时代要求的。*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24页。叙利亚自独立后国家深陷军人干政的“普力夺社会”,激烈的党派斗争与频繁的内阁更迭造成政府效力低下,整个政治生活实际上陷入一种缺乏权威的衰朽状态。复兴党的崛起重构叙利亚的政治生态,与本国的政治发展相契合,并通过与军人集团的联合建立起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阿萨德上台后,凭借一党制总统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保持了叙利亚30年的政治基本稳定,同时,叙利亚的社会经济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一个虚弱涣散的国家变成一个具备相当实力的中东地区强国。然而,从叙利亚复兴党政党政治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叙利亚政治生态纷繁复杂,矛盾重重,政治发展相对滞后与经济秩序剧烈变动的矛盾构成了叙利亚政治不稳定的基本矛盾,同时,经济、阶级、教派、地区等矛盾相互交织,贯穿于叙利亚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中。今日叙利亚危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本质上是叙利亚政治发展和国家建构双重失败的结果。尤其是阿萨德父子既没有在宗教及教派结构分裂型社会中实现权力的相对均衡和有效分配,也没有建构起全民性的政治认同,人民不断增长的政治参与热情以及社会凝聚力的分化必然导致严重的改革压力与合法性危机。因此,要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就必须破解危机的根源,推进叙利亚有关各方的政治对话,加快政治改革,使人们对变革和发展的意愿得以表达、诉求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