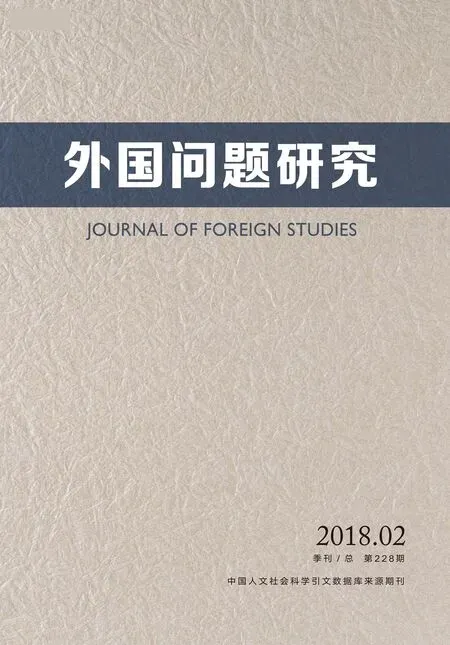拉铁摩尔边疆理论视域下的慕容政权“边缘农耕社会”
李 路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模式,拉铁摩尔对中国历史上“边疆”问题的核心理念在于,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统一性的达成,是多元力量的作用,既来源于相对南方的汉族文化,也来自于相对北方的游牧文化,是农耕社会与草原社会达成互补共生关系之后的结果,所谓的“中国”,是一个“互动过程”。*黄达远:《边疆、民族与国家:对拉铁摩尔“中国边疆观”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这一理念缘起于拉铁摩尔对中国长城的认识,在对亚洲大陆进行整体观照的过程中,他发现“对于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地带,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7页。他并没有像中国传统“中原中心”观那样,将长城视为民族或国家的“边界”,而是将之视为一个以长城为中心的边缘地带或“过渡地区”,他认为:“边疆……成了草原部落团结与分裂循环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朝代兴亡循环的一个因素。草原民族不能完全征服中国,因为长期侵入中国后,终将变成汉族,留在后面的才继续保持草原生活。同样的,汉族侵入草原太远时,也会脱离中国,加入草原社会,而留在中国的则继续发展中国的生活。只有在他们中间,在两种生活都能存在而不完全丧失其本来性质的过渡地区,这两个势力才能接触融合。所以,只有边境的混合文化,才能较远地伸入中国及草原。”*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98页。在这一思考的基础上,拉铁摩尔将以长城为中心的中国北部边疆进行了整体分类,即东北地区(“满洲”)、蒙古地区、新疆地区与青藏地区,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藩属分类方法。这种观念既有别于西方近代历史观中的“民族国家”理论,也不同于中国传统历史观中的“汉族中心”理论,而是重视长城南北的汉族社会与游牧民族社会两大社会实体的长期“华夷互动”与“共生”,*贾宁:《美国史学界关于清代早期边疆研究的新发展》,《清史研究》 1995年第2期。环境、社会与历史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拉铁摩尔思考的重点。
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东西方学界的认可,如巴菲尔德、*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巴菲尔德在该书中认为,当中原王朝稳定强大时,草原游牧政权倾向于松散联合,反之,东北的游牧部落则倾向于进入中原,建立具备自身特色并与中原传统相结合的政权。狄宇宙、*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狄宇宙在该书中在阐释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进程时,极为重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互动关系,将游牧文化视为与农耕文化平等重要的中国古代文化参与力量,显受拉铁摩尔影响。王明珂*参见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王明珂在本书中,重视各种游牧人群体与汉人农耕社会的关系互动。等人对东亚地区游牧民族的关注都承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而来,西方学界“内亚史”“新清史”的研究也都深受拉铁摩尔的影响。但目前东西方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蒙古、女真、满清以及拓跋鲜卑与北魏等形成长期政治影响力的民族或政权上,而对影响力相对次要的民族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慕容政权即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纵观慕容政权发展史,其与拉铁摩尔边疆分类中的蒙古地区和东北地区都有着深厚的联系,其在三至四世纪的活动区域也长期围绕东北地区的长城一线分布,其更具有“从东北地区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游牧民族”这一特征,从而使其迁徙与社会转型问题具备了在拉铁摩尔理论体系框架内进行进一步分析的价值。
一、慕容政权迁徙活动与“边缘农耕社会”的形成
在拉铁摩尔对长城的认识中,长城沿线作为“过渡地带”,农耕与草原两种类型的社会实体始终围绕长城进行密集的互动与发展,这一地带既处于草原社会的边缘,也处于农耕社会的边缘。在这种过渡地带内,越靠近长城一线,两种文化互动共生所形成的混合文化表现就愈加明显,反之,越远离长城一线,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的独特表现就愈加明显。在这一理论架构内,拉铁摩尔更为关注草原社会一侧的影响,如其认为当在“过渡地带”的人类群体深入草原后,就会“从边缘游牧制度转变到完全游牧制度……许多不同的游牧民族,在草原的不同边缘发展了游牧技术,然后逐渐进入草原中部,建立了一个不再是边缘性质的草原社会,而且能在较大的地理范围内发展”。*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10页。这种的“边缘游牧社会”主要表现出两个特征。第一,“边缘游牧社会”诞生于农耕社会与草原社会过渡地区的草原一侧,即草原边缘。第二,这种社会的“边缘性质”,体现在形成“边缘游牧社会”的社会实体,其社会主要生产方式在以长城沿线为中心的过渡地区与游牧生产相结合,进而成为以游牧生产为主的“混合社会。”如拉铁摩尔援引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观点认为,西伯利亚、乌梁海及阿尔泰边缘的北方蒙古人的起源与森林狩猎民族有关,还认为西伯利亚森林中以狩猎和驯鹿为生的民族,“可以在草原边缘上把放牧驯鹿,发展为大量放牧其他动物,使他们自己转变为真正的游牧民族……其他部落也可以同样地在东北森林和东蒙古及东北西部草原的边缘上发展形成。”*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10—311页。他敏锐地注意到了边缘地带对游牧社会的改造作用,但对这一理论的另一侧面,即“边缘农耕制度转变到完全农耕制度”这一问题论述的并不多。而历史上慕容政权的迁徙活动,其前后的社会表现是呈现出这一特征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辽西地区建立的“边缘农耕社会”。
慕容政权,曾为汉代檀石槐鲜卑联盟之一部。慕容氏其先本居住于大兴安岭东南侧浅山区,*佟冬等:《中国东北史》第一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455页。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遂退保鲜卑山*刘晓东等点校:《十六国春秋辑补》卷23《前燕录一》,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174页。深入蒙古草原腹地。东汉时期南迁至“西拉木伦河的上游”,*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又于曹魏初年在莫护跋率领下再次向东南方向迁移至幽州辖区,居于大棘城(今辽宁省锦州市义县附近)之北。
值得注意的是,慕容政权的这一迁徙活动,是一次由长城以北向长城以南的逐渐迁徙过程。曹魏时期的辽西长城,基本上仍为先秦时期修筑的燕北长城。从大的走向来看,燕北长城共分南、北两道,南道长城可称之为“内线长城”,而北道长城可称之为“外线长城”。*冯永谦:《东北古代长城考辨》,《东北亚历史与文化》,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内线长城又分东、西两段,其中的西段,就是《史记·匈奴传》中记载的“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这一段长城。*阎忠:《燕北长城考》,《社会科学战线》 1995年第2期。该段长城由造阳起,至襄平止。造阳,原属上谷郡斗辟县,大体位于今河北省独石口至滦河源一带。*李文信:《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上)》,《社会科学辑刊》 1979年第1期。襄平,即今辽宁省辽阳市古城。结合考古资料,该段长城的西段起于今河北省独石口北滦河源南的大滩,后东北行,经丰宁县北部,进入今围场县境内,又东行进入内蒙古赤峰南部,经今昭盟喀喇沁旗、赤峰县南境、建平县北境、敖汉旗中部,穿老哈河、蹦河、孟克河、教来河继续向东进入今辽宁省境内。*项春松:《昭乌达盟燕秦长城遗址调查报告》,《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7—8页。向东南又经辽宁省北票县北部、阜新市北部,又东行穿过辽河,最后止于辽阳市古城。慕容政权在东汉时期所居的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大致位于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附近,位于赤峰南线长城以北。而其南迁所居住的大棘城,即今锦州市义县一带,则位于朝阳、阜新一线长城以南,因此,这毫无疑问是一次穿越长城一线的由北至南的迁徙活动。
依据拉铁摩尔的理论,从慕容政权的迁徙路径来看,其在东汉时期从蒙古草原深处迁徙至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实际上标志着其从完全草原社会迁徙至东北这一草原社会与农耕社会的过渡地带,并位于草原倾向区。而其又在曹魏时期越过长城南迁至今辽宁义县一带,又标志着其进入了这一过渡地带中的农耕倾向区。在这一过程中,慕容政权迁徙前后的社会文化表现形式必然会出现变化。
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莫护跋率领部族迁入辽西之时,游牧生产显然是其社会中的主要生产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辽宁省朝阳市十二台营子乡砖厂曾陆续发掘出一批鲜卑墓地,这一批墓葬,当为莫护跋、木延、涉归时期的遗存,始于曹魏初年,止于公元289年。从随葬品的内容来看,基本只有生活日用陶器、简单的生产工具、装饰品、兵器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墓葬中发现了很多与游牧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用具,但并无农业生产工具。*田立坤:《三燕文化墓葬的类型与分期》,《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15页。如1988年发掘的88M1墓,该墓地共计出土遗物300余件,其中有骑装一套,马具如当卢、銮铃、马镫、马鞍等多件,以铜、铁质地居多,另有骨质、陶制生活器具多种,反映出慕容鲜卑迁居辽西时“保留本民族的传统较多……社会发展还处于较低阶段”。*张克举、田立坤、孙国平:《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11期。在其他类型陪葬品零散琐碎的情况下却有完整的骑装出土,说明游牧生产是这一时期慕容政权的主要社会生产方式。另外,从这批随葬品的形制与种类上看,与今内蒙古哲盟科左后旗舍根发现的鲜卑墓基本保持一致,表明慕容氏迁居辽西前后在社会主要经济模式上并无变化,仍然保持着其居住于长城以北时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在慕容政权的从蒙古草原迁徙至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又迁至辽西的过程中,其社会文化并无根本改变,属于典型的草原文化类型。西拉木伦河,秦汉时称饶乐水,其上游地区地处蒙古高原向辽河平原的过渡地带,位于华北平原北端,又位于蒙古草原南端,比邻科尔沁沙地,属干旱——半干旱区,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古代北方游牧区,慕容政权长期保持这种草原社会状态自然不足为奇。
而慕容政权在辽西地区居住一段时间并迁居大棘城之后,此种情况即发生了改变。大棘城,一般认为当位于今辽宁省朝阳市、义县、北票县一带,*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4页;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年,第90页;田立坤:《棘城新考》,《辽海文物学刊》 1996年第2期;林林等:《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 2013年第2期。据《晋书·慕容廆载记》:“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房玄龄:《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04页。其地东临医巫闾山,西部平原广被,位于大凌河中游,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在适宜游牧业发展的同时也具备了定居农业发展的优良自然环境,属于半农半牧区,具备形成游牧——农耕混合文化区的条件。这种情况忠实地反应在此一时期慕容鲜卑的墓葬遗存之中。例如,今辽宁省北票县喇嘛洞遗址“其时代可定为三燕文化中期的棘城、龙城时期,即公元289年起到350年”,*田立坤:《关于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的几个问题》,《辽宁考古文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63页。亦即慕容廆至前燕慕容儁时期,其中喇嘛洞M3、M4、M5、M6、M7、M8、M9可定为棘城时期,*田立坤:《三燕文化墓葬的类型与分期》,《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17页。即慕容氏迁居大棘城至慕容皝迁都龙城之间时段。就生产工具而言,喇嘛洞遗址中发现的类型十分丰富,除慕容氏传统的甲骑具装及各类型金属马具之外,还发现了大量铁质农业生产工具,数目多达70余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考古》2004年第2期。形制上皆为魏晋时北方习见农耕用具。此外,同为棘城时期的北票仓粮窖墓,房身M1、M2、M3,朝阳甜草沟M2等墓,龙城时期的奉车都尉墓、甜草沟M1、八宝M1、袁台子壁画墓等鲜卑遗存,皆与喇嘛洞遗址的情况类似,铁质农具和骑装马具都有大量出土,说明棘城、龙城时期的慕容政权已经形成农耕生产与游牧生产并存的混合文化。另据针对喇嘛洞遗址中人骨进行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喇嘛洞遗址居民的日常主食为糜子、粟米等谷类作物,与内蒙扎赉诺尔地区及其他鲜卑遗存中主食为肉类的情况已大为不同,进而说明鲜卑社会的“粮食生产已能基本满足食物需求,农业生产已成为鲜卑主要的生活方式”。*董豫等:《辽宁北票喇嘛洞遗址出土人骨稳定同位素分析》,《人类学学报》 2007年第1期。尽管根据针对喇嘛洞遗址中人骨遗骸进行的研究,其中发现有数十个贫血个体,男女老幼皆有,反映了喇嘛洞居民普遍性营养不良的状况,*陈山:《喇嘛洞墓地三燕文化居民人骨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6—137页。似可从侧面说明早期慕容氏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尚未能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慕容氏在迁居棘城前后的墓葬内容差别如此之大,仍可以充分说明慕容氏在迁居大棘城之后已经迅速地在其社会中建立起农业——游牧业混合共存的生产秩序,并且农耕生产已经成为其社会生产的主导。
值得注意的是,慕容政权这种混合生产模式中的游牧生产成分并非与其传统游牧生产完全一致,而是因地制宜地产生了变化。如咸康七年(341),慕容皝即下令“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房玄龄:《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22—2823页。此条史料证明,棘城、龙城时期的慕容政权社会中存在由官方设置的牧场,并进行有统一规划的牧业生产。放牧业除了可以作为主要肉食来源之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还具备不可替代的军事意义,因此对于慕容政权来说,放牧生产活动有其存在的必然需求。*郑小容:《慕容鲜卑汉化过程中所保留的本民族文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5年第2期。但是,由国家或官方统一设置牧场,说明慕容鲜卑此时的放牧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在固定区域内从事的、具有显著计划性与目的性的、由国家整体规划的经济活动,这就与以部落为单位的、四处游走式的且具备相当随意性的传统游牧生产已经有了本质不同。此种转变,恰是在游牧——农耕这一混合经济模式社会中,在长城以南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整体环境中,放牧业随之做出自我调整的表现。
拉铁摩尔的“边缘游牧社会”理论,表现的是某一社会群体在边缘地带的草原一侧所产生的社会转型。从慕容鲜卑迁徙过程及其前后的社会变化来看,恰是拉铁摩尔着重论述的这种“边缘游牧社会”的镜像表现,即“边缘农耕社会”。其“边缘性质”主要表现在:第一,慕容政权是由东北地区的长城以北迁徙至长城以南,亦即,其社会形态的变化主要发生于边缘地区的农耕一侧,即农耕社会边缘。第二,慕容政权在辽西地区的社会形态改变,主要表现为社会生产的农耕化,农耕生产极大程度地替代了游牧生产的作用,并成为社会主要生产方式,游牧生产随之进行了自我调适,二者共生形成了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农耕——游牧混合社会,也就是拉铁摩尔并未详加论述的“边缘农耕社会”。
二、“边缘农耕社会”与辽西地区的“贮存地”性质
“贮存地”,即“Reservoir”,*拉铁摩尔最初是在《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32)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国内学界一般将之译为“蓄水池”。而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拉铁摩尔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虽用词未变,但国内学界一般将之译为“贮存地”。在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体系中,是建立在“长城边疆”理论上的调节草原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矛盾的一个缓冲地带。在《满洲:冲突的摇篮》一书中,他说:“这个‘贮存地’地区,不管是野蛮人占优势时期还是中国人占优势时期,都被认为是中国北方——通常是全部中国统治权的一把钥匙。因此,就有一个地域的重要性问题,这一问题超越种族及其文化的重要性。然而,获胜的北部地区就会扩张其中国的权力,中国人口就必然地会涌入贮存地地区,乃至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现在就可以掌握全部中国事务,并进而去占领北方蛮族的领土。”*Owen Lattimore, 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 p.41在拉铁摩尔看来,“贮存地”地区存在的地缘张力,使其成为草原社会与农耕社会势力消长的首先反应地带,一旦各自存在发展需要,最先得到改变的就是“贮存地”地区。当草原社会强大时,其南下的过程必然要首先改变“贮存地”的混合文化面貌,使其倾向于“游牧化”;反之,当农耕社会实力增长时,北上扩张的农耕社会也要首先使其倾向于“农耕化”,进而继续向更北扩张。对于拉铁摩尔来说,“贮存地”的历史意义在于,由于在中国北部以长城沿线为核心的边疆地带实际上是草原社会与农耕社会的长期拉锯地带,因此“贮存地”的存在始终左右着中原和游牧社会之间的平衡关系,决定了传统中国在内陆亚洲的统治限度,*Owen Lattimore,“Origins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A Frontier Concep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p.116“它不仅是黄河流域,也是全中国统治权的关键。在中国强盛之时,它是中国政治和文化势力向外延伸的最有效的地区,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是入侵者侵入中国的始发线。”*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62页。尽管拉铁摩尔在后期主要将蒙古地区视为主要的“贮存地”地区,但东北地区也毫无疑问地被包括在内。
他认为,历史上的东北游牧民族想要成功南下,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首先控制东北这块区域。东北地区由于其自然环境的多样性与多民族长期杂居的历史,使其往往形成多元化的生产方式与文化类型,这其中当然包括草原社会与农耕社会的长期互动共存(尤其是辽西地区)。而东北地区又恰好位于中国长城东段的“过渡地区”,且南距中原不远,从而使东北游牧民族往往需要在这里对南下后的文化与社会环境进行先期适应——只有在妥善经营东北区域的基础上,才能将其统治势力进一步向南扩展。有趣的是,他对“贮存地”这一概念的最初理解,恰是在其对东北地区大量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展开的。
从慕容政权在辽西地区的发展态势来看,辽西地区已经具备了拉铁摩尔“贮存地”理论的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慕容政权的“边缘农耕社会”,是农耕社会与草原社会在辽西地区达到平衡的结果。在慕容政权进入之前的辽西地区,以长城一线为界,长城以南的辽西地区,自燕秦以来即被纳入中原王朝郡县体系,是中原王朝的直辖统治区,是典型的农耕社会。自秦汉至西晋,经历代王朝的经略,农耕社会在这里长期占据优势,慕容政权初至辽西之时也是如此。因此,来到辽西之后慕容鲜卑社会的转型,更多地表现为农耕社会对草原社会的改造,即以农业文明逐步替代游牧文明,二者逐渐形成平衡态势,进而促使其社会形态转型成为“边缘农耕社会”。秦汉以来,辽西地区成为了汉族社会向东北边疆区域延伸的直接影响区,因此这种“边缘农耕社会”是以农耕为主、游牧为辅的方式呈现的,慕容政权是在辽西地区度过了与农耕文明的相互适应过程,他们是在这里逐步完成了向农耕化社会的转型,其草原文化传统也是在这里开始被逐步消解。
其次,慕容政权的“边缘农耕社会”,事实上改造了辽西地区的社会生态。慕容政权的飞速发展,是在西晋“八王之乱”之后。随着“八王之乱”从内部瓦解了晋王朝的统治机能,其开始逐步失去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力,慕容政权趁势而起,征服周边大小部族,成为东北地区最为强大的政治势力。这一时期恰为农耕社会在辽西地区的衰弱期,也是以慕容政权为代表的草原社会强势期。慕容政权虽然经历了农耕化进程,但其社会内部的胡汉分治、族内通婚、习讲鲜卑语、保留部落、大批量蓄养牛马等不同于传统农耕社会的文化表现,也事实上改变了辽西地区的社会生态,使原本的汉族社会遭受了冲击,慕容政权的“边缘农耕社会”在其经略辽西的过程中实际上取代了这一地区原有的社会生态。
最后,从后续的历史发展来看,辽西地区在慕容政权的长期经营下,成为其对外扩张的稳固后方,是其南下“入侵”中原的跳板,也是其从东北这一“边疆”进入中原这一“中心”的始发地。慕容儁建立前燕后,随着慕容鲜卑的持续南下,前燕政权的疆域已经“南至汝、颖,东尽青、齐,西抵崤、黾,北守云中”,*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历代州域形势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4页。从而据有今北京、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苏、辽宁等地,与前秦呈平分黄河、中原之势。如果说从蒙古草原地区迁徙至辽西,是由草原文化区向以长城为中心的边缘混合文化区的迁徙,那么慕容政权逐渐南据中原这一汉民族核心政治与文化腹地,则是由东北地区这一边疆过渡地带向核心农耕文化区的迁徙。如果说前一种迁移过程是慕容政权社会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逐渐共生的过程,那么后一种则表现为一种逐渐以农耕文化为主、以游牧文化为辅的过程,是一种逐渐远离东北这一“过渡地区”的过程。而这也就意味着,慕容政权在向中原地区扩张的同时,也在逐步摆脱着自身的“边缘性质”。
综合以上三点,辽西地区对慕容政权而言的“贮存地”性质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慕容政权构建其“边缘农耕社会”的过程是在辽西地区完成的,慕容政权也实现了对辽西地区的长期稳定控制,辽西地区也成为了他们南下中原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慕容政权在辽西地区经历了这一区域由农耕社会强势期向草原社会强势期转变的完整过程,这就使慕容政权的“边缘农耕社会”、辽西地区作为“贮存地”,都经历了拉铁摩尔理论框架内完整的发展、变化与转型经历,从而具备了典型性。
从过往的研究来看,我们对慕容政权这种社会转型进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慕容政权“汉化”问题的研究方面,并普遍认为是一个高度“汉化”了的由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专著,目前仅见李海叶:《慕容鲜卑的汉化与五燕政权——十六国少数民族发展史的个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一部,其余以赵红梅、郑小容、罗新等为代表的学者相关研究已经多层次、多角度地对慕容政权的“汉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大多皆涉及了慕容政权在南下中原过程中的社会文化转型问题。但与拉铁摩尔边疆理论不同的是,这些学者的相关探讨,更多关注中原文化、汉民族文化对慕容政权的影响作用,且很多讨论是在社会意识形态层级展开的。但更多是从中原文化或汉文化对慕容鲜卑的影响角度进行考察,而往往对慕容政权本身对汉族社会的改造有所忽略,同样也对辽西这一“贮存地”对慕容政权发展影响的关注有所欠缺。而拉铁摩尔的理论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应该更多关注慕容鲜卑与汉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拉力、多元文化对区域社会生态改造的合力,以及类似于“贮存地”一类边疆地带对中国古代社会构建的作用。毕竟,慕容鲜卑社会虽然经历了高度“汉化”的过程,但并非完全“汉化”,辽西地区的传统农耕社会也并非在慕容政权的影响下完全没有改变,而隐含在慕容政权南下中原过程中的“贮存地”文化向中原地区扩展的历史进程也往往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三、拉铁摩尔边疆理论在慕容政权社会转型问题上的局限
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拉铁摩尔边疆理论在分析慕容政权社会转型问题时有其适用性,并且能为我们提供更为新颖的视角,但仍然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尽管存在区别,但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与西方“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仍然关系密切,并没有脱离西方近代史学界的“国家本位”思想,这就为我们分析类似于慕容政权一样的“边缘农耕社会”性质时带来了一些问题。正如毕敬、赵志辉所论述的那样,拉铁摩尔对“边疆”或“过渡地带”的概念阐释,“是以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为参照系而构建出的”,并在具体论述中“大量使用‘帝国’的概念来描述传统中国的边疆治理模式……但这一‘帝国’本质上仍是对西方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帝国主义的概念演绎。”*毕敬、赵志辉:《中国历史的空间枢纽——欧文·拉铁摩尔边疆范式中的“贮存地”剖析》,《浙江学刊》 2018年第1期。但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中,所谓“民族”,是在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与他者存在明显区分的人类群体,是伴随着欧洲民族国家诞生而产生的种群区隔理念,国家首先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其产生前提是民族自决与自治。但在古代中国,区分群类的标准从来不是历史、语言、文化的不同,而是华夏中心主义思想下的“文野分际”理念,意即,“非我族类”的族群,在完成其文明的华夏化后,即可融入华夏族群,而这一标准往往是宽泛的。因此,在古代中国,几乎从来都不存在一个完全西方意义上的民族自决“国家”,自然也就不存在一个“汉族自决”的帝国,也不存在在“民族国家”理念上构建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一类的国家观念。
在“民族国家”语境中,拉铁摩尔的草原社会与农耕社会往往呈现出绝对的种群对立,所谓的“过渡地带”或“贮存地”实际上是处理这种对立态势的缓冲区。但他忽视的是,这一缓冲区的存在,却使草原社会与农耕社会、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之间在古代中国并不存在一个“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绝对边界,二者很少是完全泾渭分明的。具体到慕容政权所构建的这一“边缘农耕社会”中,虽然其内部存在出于保留传统考虑而设置的人为族群界限,但至少在辽西地区,我们很难明确地划分出慕容鲜卑族群与华夏族群事实上的界限与居地,正如拉铁摩尔自己也认为,“边疆混合社会不可能迅速归属‘严格’的草原社会或‘严格’的汉族社会”。*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72页。但这却无法解释他本身“帝国”化的中国阐释,也很难解释慕容政权与晋王朝的关系以及慕容政权南下后所建立的中原政权性质,从而出现理论上的自体矛盾。
第二,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过于注重自然地理环境对边疆社会的影响,而对人文环境尤其是“汉族文化”影响的关注并不足够。我们依据拉铁摩尔的理论框架来对慕容政权的迁徙活动进行分析,自然就会如前文一样以地域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作为慕容政权“边缘农耕社会”形成的根本依据。但实际上,如慕容政权这种从长城北至南的迁徙活动,意味着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区,当地相对稳固的农耕社会产生的人文环境很难不对这种“混合社会”的形成施加影响。慕容政权社会农耕化转型的背后,除了地域因素外,还体现着历代慕容政权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如慕容廆以招募汉人流民为核心手段,对鲜卑部众“教以农桑”*房玄龄:《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4页。蓄意引导,慕容皝亦“躬巡郡县,劝课农桑”,*房玄龄:《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22页。使农耕文化在其社会中打下了坚固的根基,慕容皝“君以黎元为国,黎元以谷为命。然则农者,国之本也”*房玄龄:《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第2825页。一语,亦可代表着慕容鲜卑统治阶层对农业生产作用的清醒认识。这当然是“汉族社会”农业观传入的结果,而并非仅仅是自然环境变化所导致。事实上,慕容政权一直都是一个注重学习汉族文化的政权,一方面,在传统中国“华夷观”框架下,他们一直试图脱夷入夏,谋求华夏正统;另一方面,他们也一直注重吸纳汉族知识分子,推行汉化政策,使其社会一度“路有颂声,礼让兴矣”,*房玄龄:《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第2806页。中原后世官修史书也不得不评其“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郊天祭地,肆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魏收:《魏书》卷108《礼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45页。这种文化转型现象的产生,实际上是慕容政权本身的主观能动性与中原文化在东亚地区事实存在的辐射与传播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而拉铁摩尔显然对此方面关注不够,他的“混合社会”理论模型也就因缺少人文因素而充满了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