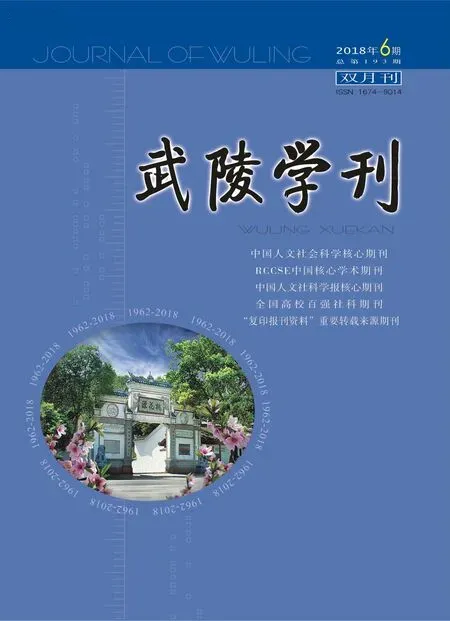庄子幸福实践的个人当为思考
许建良
(东南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6)
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状态和质量的因素也越发活跃地表现出来,诸如能源枯竭、生态破坏、人际关系疏离等三大危机冲击波就是这种威胁的直接反映。因此,2012年4月联合国在不丹举行了有关幸福指数的讨论大会,大会公布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是全球首份幸福指数报告,数据涉及2005—2011年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从此,幸福问题成为地球村居民普遍关注的焦点,从中国古代思想宝库中发掘幸福思想的资源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学界关于庄子幸福思想的研究成果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1]。本文无意于关注庄子幸福思想的内容和价值等问题,主要聚焦其幸福实践途径中的个人当为问题,通过分析幸福的主体是个人、个人幸福要靠自身生命来展示和演绎、死生是生命的主旋律、修身以尽年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展示庄子幸福实践中对个人当为的思考①。
一、幸福的主体是个人
从根本上说,幸福是个人的事,幸福的主体永远只能是个人;离开个人幸福无所谓独立的社会幸福,正是在这个层面完全可以说,社会幸福是一个虚空的概念。换言之,提高社会幸福指数的目标只能在保障个人幸福实现的基础上来达成。前面提到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也明确地昭示了这一点。不仅它的形成是以个人为调查对象的,而且其指标体系中涉及的9大领域包括教育、健康、环境、管理、时间、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社区活力、内心幸福感、生活水平等,最核心的是“内心幸福感”,而这恰恰是指个人内心的幸福感。
因此,个人幸福既是个人生活历程的终极目标,也是生命价值的意义所在。庄子对幸福的重视主要侧重在对幸福的追求上。虽然说幸福是生活的伴侣,但幸福仍然需要个人努力追求而不能坐享其成。众所周知,庄子虽然不主张刻意地追求幸福,但他并没有否定幸福追求本身。他认为“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逍遥游》),“数数然”是急切追求的样子。也就是说,庄子对急切追求幸福的做法是否定的,但他并不否定获得幸福以及获得幸福的实践。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致福”的主体是列子即个人。由此可见,庄子对幸福问题的重视完全在个人的频道上。
与幸福相联系的还有快乐。同样,庄子也是从个人出发来思考快乐问题的。他说:
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
(《大宗师》)
这段话的意思是:把船藏在山谷里,把山藏在深泽里,可谓牢固了;但自然力大无比且始终处在变化迁移之中,昏昧者却不知这些道理;藏小、大即使可以达到相对的适宜,但仍有一定的亡失,因为宇宙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适宜只是相对暂时的,不是绝对永恒的;如果把天下藏于天下就不存在亡失的问题,这本来就是万物所处的日常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万物之真情可以自由显露;人们仅获得形体就欣然自喜,如果知道人的形体千变万化而未曾有穷尽,那么这种快乐岂可胜计!这里的“乐”即快乐的主体无疑也是个人。
显然,庄子所谓“致福”“乐”的主体不是社会,而是个人。因此可以说,在庄子的视野里,不存在社会幸福的问题。当然,这不是说个人幸福与社会没有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文探讨)。幸福永远是个人追求的对象,正如冯友兰所说:“只需要顺乎人自身内在的自然本性,就得到这样的相对幸福。这是每个人能够做到的。”[2]幸福的主体是个人。另外,“庄子认为,人是单个的自然人,他对这个封建宗法社会团体没有义务,他追求的是个人的幸福”[3],两者阐明的道理也是一样的②。
二、个人幸福展示和演绎的域场是生命
“致福”的主体是个人。可是,个人“致福”的域场又是什么呢?这也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不然,“致福”就显得笼统模糊。综观庄子思想,可以说,生命是个人“致福”的域场。
(一)生命的基质在“命”
庄子的“命”虽然有多种意思,但其中之一就是性命。在庄子看来,在万物自身的系统里,就存在着“命”。庄子说: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
(《人间世》)
文中的“大戒”是大法的意思。庄子认为“命”和“义”是最值得注意的两个大法。它们一内一外,织成一个整体,是个人无法回避的。就内在方面而言,“子之爱亲,命也”的“命”是性命的意思;就人的性命情愫而言,包含着“爱亲”的因子,这是无法释怀于心的。换言之,爱亲尽孝离不开真心真意,不能有丝毫懈怠,而且这些都是无条件的,即“不择地而安之”。由于“不可解于心”,所以在具体实践上应该从“心”开始,即“自事其心”,这样的话,人就不会为哀乐所左右。庄子这里强调了自然性,“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幸能正生,以正众生”(《德充符》)中的“命”,指的正是个物之所以为个物的性命情感要素,它来自于天地自然。在外在的方面,“臣之事君,义也”,可以说是义命,这里的“义”同“仪”,是外在的仪制和规定。“不择事而安之”,指的是无论任何事情都安然处之,这是尽忠的极点。
显然,在庄子那里,生命的域场包含着内外两个方面,内在的方面是个人的性命,这是一个人生存的基质和最重要的方面。庄子关于“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的运思中,“保身”“尽年”强调的就是性命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庄子虽然追求精神自由和灵魂平安,但都无法离开客观现实。日本汉学家中岛隆藏认为庄子是“在俗中超俗”③,这是非常精当的视点。同样,庄子在生命问题上,也展示了外在方面的因素,这就是外在的“义”即义命,主要指对人的职分的规定,人通过遵守履行职分规定,达到与外在社会整体的协调一致,这是一个人基本生活的需要。这里指的虽然仅限于政治上的“事君”,但整体上与庄子关于“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内直者,与天为徒。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人间世》)的思想是吻合一致的。对个人而言,人的内在本性基因是独特而不可复制的,而且万物皆然。所以,个人在与外在他者相处时,必须秉持“外曲”的规则,这是尊重他者的需要。换言之,也就是“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德充符》),这一行为也即“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大宗师》),可谓个人幸福的最高状态。因为,在最终的意义上,个人幸福获得了“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的哲学支持。
(二)生命历程的演绎域场在宇宙万物
众所周知,庄子逍遥游的理论基础是万物齐同的价值理念。在大千世界,任何物的价值只具有相对性意义,没有被绝对化的理由。由此审视庄子所追求的自由和心灵平安,也只能在相对的层面赋予其价值意义。
基于相对性的视野来审视庄子关于生命的内涵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庄子虽然强调自由,但其视野仍然没有离开世俗社会。庄子重视外在的义,这与他的宇宙视野是一致的。正如他在《齐物论》中所说:
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奚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置其滑涽,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钝,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
庄子这里想言说也是希望别人静听的内容,他在言及圣人的特性时提到了“宇宙”。由于在内篇里仅此一处谈到“宇宙”一词,为了尽可能准确理解它的意义,必须在全面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来进行。庄子这段话的意思是:与日月并明,怀抱宇宙,与万物互相吻合,殽乱混杂则随而任之,一于贵贱;众人熙熙攘攘于现实是非名利,圣人素朴安然,领悟于历史事实而保持精纯不杂。万物就这样以此相互包涵。虽然众人与圣人的行为之方相异,但都是万物之一的存在。庄子希望众人能在圣人的行为之方中得到启示,在整体上,庄子表达的正是万物齐同的理念。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庄子“宇宙”的内涵④,但可以与下文的“万物”联系起来理解;或者说,宇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万物,对此,我们可以参考美国汉学家安乐哲的评述:“事实上,道家将‘宇宙’(cosmos)理解为‘万物’(ten thousand things),这意味着,道家哲学根本就没有‘cosmos’这一概念。因为,就‘cosmos’这个概念所体现的统一、单一秩序的世界来说,它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封闭和限定了的。就此而言,道家哲学家基本上应算是‘非宇宙论’思想家。”[4]
在庄子这里,万物之所以齐同,就在于万物是一体的,在动态的层面它是通过整体联系来共作互存的,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换言之,个人生命的具体演绎域场就是整个宇宙,个体无法离开其他万物来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庄子个人幸福演绎的生命历程,就牢牢地驻足在大千世界了。
三、死生是生命的主旋律
生命定位和演绎在宇宙万物的世界里,它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死生。
现代语言中的生死,在庄子那里就是“死生”,这是对生死概念的较早表达。众所周知,现代日语使用的汉字至今还有约3 000个,其保留的汉字,表达的基本上都是它的最为原始的意思,譬如,“私”在日语中表示的是自己、我,所以日本人在作自我介绍时用的就是私は×××です,这是“私”较为原始的意思,表示“我”的意思。《老子》中有3个“私”的用例,即“少私寡欲”“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用的正是这个意思。关于生死的概念,日本人也习惯于称之为死生。
毋庸置疑,生死与死生的价值取向是相异的。就死生而言,《庄子》内篇有8个死生的用例,没有生死的用例;死生的起始点是死,虽是痛苦的,但终点是生,充满着希望和活力,对人是一种积极激励,蕴含先苦后甜、崇尚生命活力的价值追求。在死生的过程里,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生以及如何提高生存的质量和生活价值。
(一)死生,命也
庄子认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死生是生命本有的自然课题,就如有白天、黑夜的常态是天道自然一样。庄子把对自由的追求与个人的内在德性素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在强调逍遥游和齐物的同时,尤其强调个人才性的涵育,其“才全”概念的提出就是明证。“哀公曰:何谓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这些都是事物变化的具体样式,是生命及其境遇发展演绎的行迹。这里的“死生”与“死生,命也”的“命”的意思是一样的。
对“命”一词,笔者也曾以“命运”作解释[5]。这一理解也是基于成玄英对《德充符》“夫二仪虽大,万物虽多,人生所遇,适在于是。故前之八对,并是事物之变化,天命之流行,而留之不停,推之不去,安排任化”的注疏。现在看来,从生命以及其演绎的境遇来理解似乎更符合庄子的原意。因为,其中的“饥渴寒暑”等明显与命运无关。
总之,死生是生命本有的自然课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
死生是一件极大的事情,庄子说:“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死生影响不到王骀,因为宇宙万物处在整体联系的有待的境遇之中,他能谨慎地对待无待即“无假”,而不轻易地与外物迁变,但能顺任物事的变化而执守其宗本。《庄子》内篇里虽然没有使用“生死”的概念,但是,他在具体界定死生时,并不是从“死”开始,而是从“生”开始的,这与他企图体现生命活力的价值取向相一致。
子来曰:“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大宗师》)
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
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
(《人间世》)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生命是自然的馈赠。子女对于父母,无论去往东西南北,都会听从父母的吩咐。自然对于人,无异于父母对于子女;它要我死而我不听从,我就蛮横违逆了,自然有什么罪过呢?大自然给我形体,以生使我勤劳,以老使我轻松逸乐,以死使我安息。生是人不断变老的过程,而死则是人安逸休息的一种方式。由于生使人勤劳,在具体的劳动实践中会遇到艰辛和挑战,对待这种境遇,最有效的方法是遗忘它;人应该喜爱并良善地对待生,正如喜爱并良善地对待死一样,不应该“悦生而恶死”,而应该客观地面对死。
把死亡看成是回归大自然的一种人生态度。但就人生旅途而言,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困难重重,所以不仅要“忘其身”,而且要“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即物我两忘而与“道”融合为一体,以“道”为人生的路标,唯“道”是从,这才是心灵的最高境界。在这个境界里,道化的人和人的道化,人与“道”在本质上交融;生是“道”的价值的体现,死是向“道”的回归。
(二)齐同死生
在庄子的视域里,生是艰辛的,人得以安逸致老,最后抵达安息的处所却仅仅是一生一次的死亡。人如何平衡情感,增强善待生活的原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庄子的解答是等同死生。他说: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俄而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曰:“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其心闲而无事,跰□而鉴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恶之乎?”曰:“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
(《大宗师》)
在死生存亡是否一体的问题上,子祀等四人持有相同的观点。一次,子舆病得很重,子祀去探视他,问他是否厌恶自己“曲偻发背”的样子。子舆说没有什么可以厌恶的,因为,对人来说,生是适时,失生(死亡)是顺应,人只有“安时而处顺”,才不会被哀乐所困扰,自然能平静地应对死生而不恶死。
死生作为个人生命的课题,二者具有同等的地位,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齐物论》),生意味着死,反之亦然。所以,人应该乐观自然地对待死。庄子说:
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子贡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临尸而歌,颜色不变,无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大宗师》)
在世俗的眼光里,死是悲哀的事情,人们表达悲哀的方法一般是放声痛哭。但子桑户死后的情形却是另一番景象:“编曲”“鼓琴”“相和而歌”,这些都是与世俗相异的做法,所以,子贡认为这违背了礼仪。孔子得知后,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疽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大宗师》)也就是说,人与天地合一,生命就是气的聚合,如身上的赘瘤一般;死就像气的消散,如脓包溃破一般,根本没有死生先后的分别⑤。
齐同万物和齐同死生二者的对象是相异的。万物是外在于自己的,自己是万物之一的存在,故自己与他者同;齐同生死的对象都是自身,因此,对人而言齐同生死并非易事,但也并非不可能。“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神人就能冷峻地对待死生。
四、养亲尽年
在个人追求幸福即“致福”的实践中,庄子虽然聚焦了内在性命和外在义命,但它们都必须在自然的轨道上运行。对个人而言,不仅需要齐同他物,而且必须齐同死生,这是实现个人幸福的枢机,这就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告诉我们的道理。由此可见,庄子对基于人自身臆想的善恶行为都是否定的,强调要因循自然而为,这是实现个体幸福的关键。汤川秀树认为庄子论证了“脱离了自然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6]观点,可谓是对庄子思想的最好诠释。
庄子还明确提出“养亲”的问题。“养”就是修养,他的《养生主》告诉了我们养生的真谛。在内在方面,要“因其固然”(《养生主》),即按照万物的本有规律和特性来进行;在外在方面,则要“依乎天理”(同上),做到“安时而处顺”(《养生主》)。两方面结合,就能真正实现“内直而外曲”。由此可见,庄子并没有否定个人在实现幸福征程上的努力,而是他努力的方法独具一格罢了。
(一)常因自然
自然是道家的标志性概念⑥,虽然在《逍遥游》《齐物论》中没有提出自然的概念,但反映其自然思想的相关论述却不难找到。庄子在谈到“天籁”时说:“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齐物论》)这里的“自己”“自取”实际上都是自然的意思。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郭象对这两个概念的注释:
此天籁也。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
(《齐物论注》)
物皆自得之耳,谁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籁也。
(《齐物论注》)
郭象正是以“自然”来解释“自己”、以“自得”来解释“自取”的,而自得就是自然而得。
显然,重视自然是庄子的一贯主张。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实践中,他提出要因循自然,即“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符》);因循自然,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根据自然的本性来行为,为此,“坐忘”是最为重要的。
“忘”在庄子的思想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诸如“忘年忘义,振于无竟”(《齐物论》),就是具体的说明。“忘年”即玄同生死,“忘义”即贯通是非善恶,不为世俗所左右,这样就可进入无穷尽的境界。不仅如此,庄子还提出了著名的“坐忘”的概念: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大宗师》)
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
(《德充符》)
简单来说,坐忘就是“离形去知”。“堕肢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大宗师》)是“离形”的方面,“黜聪明”就是“去知”,属于忘神的方面,具体包含仁义礼乐等。对人来说,“德有所长”是“所不忘”,如能忘的话,就是真正的忘,即“诚忘”“坐忘”,从而到达“大通”的境界而不为世俗之礼所囿,即“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大宗师》),抵达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是,一般人往往遗忘的是内在的、代表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性特征的东西。换言之,就是忽视自身的内在素质而对外在形体方面本该遗忘的东西无法遗忘不是真正的忘。坐忘则是内外两忘,完全听从自然的声音来生活。
(二)顺物自然
在外在的方面,个人幸福的实践,最关键的是因循他者的自然本性与他人相处,即“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无容私”就是不要融进自己的臆想。庄子认为,人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他说: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齐物论》)
意思是说,言论与风是相异的,因为前者是人为的,后者是自然的,所以每个人的言论没有客观的标准即“特未定”。基于这种情况,就很难判断言论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社会的发展,使道和言论失去本有的效用而产生真伪、是非的分辩,其原因是道被人的小成所隐蔽,言论在浮躁的言辞中黯然失色。这就像儒家墨家那样各自肯定对方所非而否定对方所是。因此,庄子主张以空明的心境来观照万物本有的状态。
人的局限性就在于容易从主观出发来评判周围的物事。人与人的差距正如大鹏与斥鴳,大鹏“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和斥鴳“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差距之大是客观存在的。斥鴳的问题就在于以自己的是非为标准来审视世界万物。“明”是庄子的一个独特概念,其本质精神与“虚”一致。一个人获得了“明”就能实现“顺物自然而无容私”,换言之,“明”是人克服自身局限性的关键,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基础。为此,庄子提出了“心斋”的方法。
在庄子的视野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如果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就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知识是根于人心的认识,他否定刻意用心的行为,即“常季曰:彼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哉”[7],以知得心、以心得常心,都是有意而为,不是自得。他强调“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人间世》),即外于心知。外于心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有限生命中播种幸福的种子,为此,庄子提出了“心斋”的概念:
仲尼曰:“斋,吾将语若!有〔心〕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暤天不宜。”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夫子曰:“尽矣。吾语若!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
(《人间世》)
有心为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以为容易就不合自然的道理了。“心斋”不同于“祭祀之斋”,因为“祭祀之斋”只要吃素就可以了,这是有形可寻的。“心斋”是依靠心灵的气化来推动的,它不是心知。在与万物的关系里,气处在“虚而待物”的状态,虚就是心斋。《尔雅》曰:“虚,空也。”“空”就是不实,就是有空隙,即在心中留有一定的位置。对个人而言,要做到“虚”,就要把自己内心世界的空间留出来,而不要让它被自己的欲望占满。因此,处在“心斋”状态的人,是没有思虑的,心灵的一切活动“听之以气”,顺其自然,完全摒弃了世俗的观念,不为名利所累,完全处于忘我的境界。
其实,因循自然也就是因循道,因为道是虚的整合即“唯道集虚”。对个体来说,无我的状态,即是“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在与外物的关系上,是“虚而待物”而不用强,即“入则鸣,不入则止”。在庄子看来,价值坐标的中心是他人,自己内心的“虚”是为外在他人的“实”创设的前提条件。
(三)个人幸福的具象——真人
在因循自身和万物本性的前提下,能否真正做到对自己“不益生”、对他者“无容私”呢?这是需要考虑的。如果不能实现“不益生”“无容私”,其思想也就失去了意义。其实,在庄子那里,这完全是可行的,这就是他的“真人”的价值所在。
1.与道相合。庄子说:“古之真人……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大宗师》)他在这里讨论的主要是真人在天人关系上的态度。“天人合一”观点的立足点在天道自然上,天人不合一观点的立足点则在人道上。但不管是“一”还是“不一”,他们都是合一的,天人互相协调一致即“天与人不相胜”,真人客观地看到了天、人的作用。荀子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⑦)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真人正视天、人的存在,真人和道在一定程度上相融相通。那么,什么是真人?“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大宗师》),就是具体的回答。人类的真知是通过真人来传递的,真人既因顺寡少,又不自恃成功,不谋虑行事;对过错、得当的事情都能泰然处之。
2.不悦生恶死。生死是生命的主要课题,是个人幸福无法回避的问题。“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大宗师》)这段话说的是:真人不悦生恶死,自然对待生死而做到无拘无束,不忘记自己从何处来,不追求往何处去,欣然接受生命历程中发生的事情,忘却死生而任其复返自然,这就叫做不以自己的心知害道,不以人为辅助天然。
3.与万物相宜。在与万物的关系上,真人“其心忘⑧,其容寂,其颡頮;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大宗师》)意思是说,真人心胸宽广,容貌静寂安闲,额头宽大恢弘,冷峻如秋,温暖似春,喜怒自然,与万物相适宜,使人难以得知其极限。其中的“宜”也是庄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与今天我们使用的“幸福指数”的意思相同。“与物有宜”是实现外在幸福的需要,也是外在幸福的体现。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真人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前两方面是指“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后一方面是指“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外在的幸福都是因循自然的结果,在本质上是齐同万物的产物,即“庄子的人生哲学以因循主义为一贯;其次,其基础是万物齐同的哲学,万物齐同哲学主要认为,作为存于差别现象深处的并对此贯穿的同一性,是要注目的绝对的理法;立于这理法即道的中心——道枢之时,才会洞察明了一切无差别无对立的真实之相。作为人的生存之方,必须停止追求现象层面的相对价值,仅置身于绝对的‘自然’道理而行事,只有这样才是因循主义”[8]。
综上所述,庄子追求“致福”的实践,把个人生命历程看成幸福演绎的域场,通过等同死生来实现全生、尽年;在全生、尽年的过程中推重因循自然的方法,具体通过坐忘、心斋等途径来确保“不益生”“无容私”的实现,真正实现内外幸福,最终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庄子崇尚逍遥自由,但并不否定个人的责任,他始终把个人置于宇宙万物之中,强调个人在因循万物自然中的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与他强调的“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应帝王》)互相呼应。“使物自喜”是个人履行自己责任实现幸福的结果,这是我们应该重视的。
注 释:
①论文认同《庄子》内篇代表庄子本人思想的观点,故本文仅以《庄子》内篇为研究对象;文中所引文献以郭庆藩辑《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为准。
②关于庄子“人是单个自然人”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③日本著名汉学家中岛隆藏认为,庄子不过是在俗中超俗,没有与世俗彻底割断,其实,彻底割断也是不可能的。参照中岛隆藏著《庄子——在俗中超俗》,日本集英社1984年12月版。
④《庄子》外、杂篇里不仅有4个“宇宙”的用例,而且还有对宇宙的专门界定,即:“出无本,入无窍。有实而无乎处,有长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庚桑楚》)
⑤庄子后学发展了庄子的思想,直接把生死界定为气的聚散,即“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知北游》)
⑥参见许建良著《先秦道家的道德世界》第1—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⑦参见王先谦著《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⑧王叔岷注:“赵以夫云:‘其心志’,志当作忘……案志为忘字之形误。”参见王叔岷撰《庄子校诠》第212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