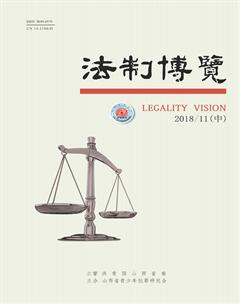我国让与担保制度浅谈
摘要:虽然让与担保在实践中已较为普遍地存在,法学界对于让与担保制度的研究也颇多分歧。但基于我国为成文法国家及让与担保自有的缺陷,在立法未正式确立该项制度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不应随意突破物权法定原则和流质契约无效的限制。最高法最新判例引用《民法总则》相关条文作为裁判依据,对各级法院认定让与担保效力提供了指引。
关键词:让与担保;理论研究;司法实践;裁判依据;指引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8)32-0216-02
作者简介:李继辉(1972-),男,四川营山人,硕士,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法治理论与实践。
让与担保(或称非典型性担保)目前并未被我国立法所确立,但在实践中却已广泛存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让与担保的裁决并不一致,极大地损害了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法学理论界对于让与担保的效力也颇多分歧。本文拟从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两方面对让与担保问题作一浅议。一、基于最高法判例的司法实践情况分析(一)最高法判例梳理
截止目前,经中国裁判文书网全文分别检索“让与担保”“非典型性担保”,最高法共7起判例涉及“让与担保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问题。其中,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的判例1例([2011]民提字第344号);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判例4例([2013]民提字第135号、[2016]最高法民再113号、[2017]最高法民申3248号、[2017]最高法民再154号);未直接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效力,但认定“无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的判例2例([2015]民申字第3051号、[2016]最高法民终52号)。
(二)最高法判例认定让与担保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裁判理由
1.违反禁止流押强制性规定和物权法定原则
(2013)民提字第135号民事判决书观点:双方当事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行为成立一种非典型的担保关系。既然属于担保,就应遵循物权法有关禁止流质的原则。(2013)民提字第135号民事判决一定意义上催生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7)最高法民再154号民事判决书观点:根据《补充协议》安排,双方系以在借款到期前以让与房屋所有权及保有回购权的方式为借款提供担保。基于物权法定原则,因双方没有按照法定担保方式设立担保物权,双方合同约定内容不能产生物权效力。在债务不能清偿的情形下直接由债权人取得担保物所有权的约定,系我国法律明确禁止的应认定为无效的流押情形。
2.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真实意思,虚假意思表示行为无效
(2016)最高法民再113号民事判决书观点:《民法总则》143条第二项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民法总则》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买卖店面的约定本身是当事人之间的虚伪意思表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以案涉店面担保借款债务的履行,当事人间达成一致的真实意思即隐匿行为是将案涉店面作为借款合同的担保。根据《民法总则》146之规定,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本身作为伪装行为无效。
(2017)最高法民申3248号判决书观点:因双方系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形式为借款提供担保,也即名为商品房买卖实为担保,双方并不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的意思表示,因此双方以虚假意思表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属无效。
最高法2017年12月的二判例中,均是以同样的理由闡释让与担保房屋买卖合同效力。(2016)最高法民再113号裁判文书则是直接明确引用了《民法总则》146条,(2017)最高法民申3248号裁判文书虽没有直接引用该法条,但实际上是该法条的应用。(三)最高法判例的指引意义
1.最高法司法判例关于让与担保房屋买卖合同效力认定的主流观点是无效说。
2.最高法司法判例否定让与担保买卖合同效力的裁判理由引入了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新规则。
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基本以物权法定原则和流质契约无效否定让与担保,最高法2017年的二判例引用《民法总则》146条确立了认定让与担保买卖合同效力的新规则。
3.《民法总则》146条确定了从“意思表示”角度认定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新规则。
(1)《民法通则》关于“意思表示”对民事行为的效力认定。因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第58条)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的行为为无效(第58条);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行为(第59条)为可变更或可撤销。
(2)《民法总则》关于“意思表示”对民事行为的效力认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第146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第154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第147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可撤销(第148条);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149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150条)。
对比二者可知,《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从“意思表示”要件认定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则有了较大变化。《民法总则》将《民法通则》中“可变更或撤销”统一归为“可撤销”,而取消了“可变更”。《民法总则》146条则是从“意思表示”要件确立了认定民事法律无效的新规则,此处的“意思表示”不真实是双方通谋而为,与可撤销情形下的一方意思表示不真实属于不同情形。
4.通谋而为虚假意思表示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可能性。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关系中,当事人可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掩盖借贷中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利息。
5.从立法层面追索,《民法总则》被认为是我国对《德国民法典》117条的法律移植:须以他人为相对人而做出的意思表示,系与相对人通谋而只是虚伪地做出的,无效。另一法律行为被虚伪行为隐藏的,适用关于被隐藏的法律行为的规定。我国台湾民法典第87条也是源于德国民法典: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伪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无效。但不得以其对抗善意第三人。虚伪意思表示,隐藏他项法律行为者,适用于该项法律行为之规定。
结合最高法判例和《民法总则》146条,各级法院认定让与买卖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既有司法实践判例指引,亦有明确的裁判依据。二、法学理论界主要观点梳理(一)肯定说
代表学者有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杨立新教授。杨立新教授将房屋买卖合同作为担保称为“后让与担保”,认为应当肯定其效力,其性质是物的担保,不是传统的物权担保,而是非典型性担保①。肯定说者基于让与担保在现实中的广泛存在而提出应突破物权法定原則,认可让与担保这种新型担保形式。(二)否定说
代表学者有中国人民大学王利民教授等。否定说者提出,让与担保违反了禁止流质契约的规定。房屋买卖让与担保本质上就是未来物上的抵押权,并非一种新型物权②。否定说基于物权法定原则对让与担保予以否定。因此,司法实践中,持此观点者以流质契约无效而否定让与担保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三)部分肯定部分否定说
部分研究论者提出,应肯定担保效力,否定合同之效力,或者应肯定合同之效力,而否定担保之效力。
(四)让与担保制度在我国《物权法》立法过程中始立终弃,说明让与担保并未为法学界主流理论认可
总之,我国为成文法国家,虽然让与担保在各领域的法律实践中已经普遍存在,法院裁决还是应以现行立法为准绳,而不宜随意突破物权法定原则和禁止流押之规定。《民法总则》生效后已可为让与担保效力认定提供裁判依据,最高法裁判文书也已经明确引用《民法总则》146条为裁决依据,各级法院应当遵循。[注释]
①杨立新.后让与担保:一个正在形成的习惯法担保物权[J].中国法学,2013(3).
②董学立.也论“后让与担保”——与杨立新教授商榷.中国法学,2014(3).(上接第218页)
如果该禁止规定的实施,不仅不能达到保护特定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反而会给特定相对人造成不利后果,在这种情形下,执意执行该禁止规定很明显违背了立法的初衷,也违背了相对人的意愿,相对人应有权拒绝“被保护”。在上述案件中,如果没有《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禁止性规定的约束,陈某完全可以与A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顺利拿到其应得的33万多元的经济补偿金。正因为有了《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使A公司维持与陈某的劳动关系符合法律的规定,并得到劳动仲裁委及各级法院的一致认可和支持,但同时也令陈某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为比陈某晚入职A公司的几位老员工,已经各自拿到几十万元经济补偿金离开了A公司,陈某成为被动“被保护”的对象。
“被保护”应是陈某的权利,对于该权利,陈某本应享有行使或放弃行使该权利的选择权,也就是说,陈某有权选择放弃该“受保护”的权利。然而,基于现有的法律规定,若发生与陈某案情类似的案件,相同的裁决、判决、裁定将会再现,除非对《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进行立法修订,才能避免劳动者再次“被保护”。
四、对《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的修订建议
为了更加精准地保护需要保护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使需要保护的劳动者获得应有的保护,不需要保护的劳动者避免“被保护”,需要赋予劳动者选择权,让劳动者在被保护前享有表达并决定是否需要被保护的权利。故此,作者建议将《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中规定的“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修改为“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同意被解除劳动合同的除外”。[参考文献]
[1]张在范.论劳动法的直接目的与终极目的[J].河南社会科学,2009(1):91-94.
[2]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穗劳人仲案[2014]2650号仲裁裁决书.
[3]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4)穗荔法民一初字第1599号民事判决书.
[4]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423号民事判决书.
[5]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