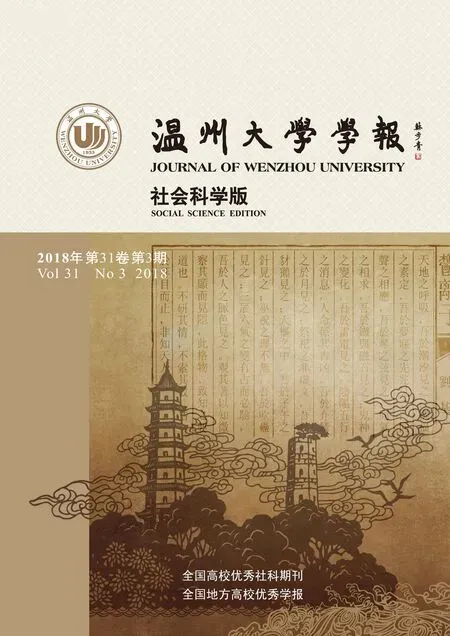晚明世风变异与屠隆戏曲的宗教教化思想
—— 以《昙花记》为中心
蓝 青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珠海 519082)
相较风情剧、历史剧、社会家庭剧等,神佛剧自古以来不太受评论家青睐。如清初朴斋主人批评明末宗教剧曰:“近来牛鬼蛇神之剧充塞宇内,使庆贺宴集之家终日见鬼见怪,谓非此不足以悚夫观听。”[1]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玉掌记》曰:“一涉仙人荒诞之事,便无好境趣。”[2]75不仅古人对宗教剧普遍评价不高,当今学术界对宗教剧亦存在一定偏见,往往将其视为“封建迷信思想的宣传工具”[3],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宗教剧内涵与价值的探索。实际上,明清时期不少宗教剧有着丰富的社会生活蕴涵与深刻的思想内容,颇值得深入探讨。屠隆的《昙花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昙花记》成书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描写唐朝定兴王木清泰受僧道点化,勘破酒色财气,弃家求道,历游阴曹地府与西方净土世界,经过诸多考验磨难,最终证道登仙的历程。该剧因宗教色彩浓厚,内容驳杂,情节漫衍,历来评价不高。如吕天成评曰:“《昙花》以仙佛牵合,殊恨庞杂也。”[4]385祁彪佳评其“阐仙、释之宗,穷天罄地,出古入今。……学问堆垛,当作一部类书观”[2]20。吴梅评其“通本结构,又似《西游》取经,贪袭仙佛语,致有晦涩不明处,实非词家正则”[5]。《昙花记》虽以宣扬佛禅信仰为宗旨,然其思想与内涵远超出了宗教范围。剧作对晚明世风变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试图借助宗教思想来恢复传统的道德、社会秩序,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故本文拟从晚明社会风气与士人心态入手,考察《昙花记》的创作意图与思想内涵,揭示其作为宗教剧所蕴涵的独特艺术价值,以期对晚明戏曲研究尤其是宗教剧研究有所助益。
一、晚明世风变异
晚明商品经济的繁荣对传统的社会、道德及文化秩序产生了强烈冲击,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金钱的地位与影响力凸显,拜金逐利之风炽盛,冲击着传统的道德秩序;二是尊身、适己之学兴起,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强烈冲击,士人信仰出现危机。
先来分析晚明逐利之风。明代前期经济结构以自然经济为主导,与之相应,社会风气较为淳朴,“人尚齿序,礼先官长,婚姻略财,丧祭如制,重本而轻末,贱释而贵儒士,绝市肆之饮,民乐赋役之输”[6]。民安其业,恪守礼制,社会秩序井然。进入正德以后,随着商品经济日益繁荣,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渐趋瓦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金钱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整个社会陷入到狂热的金钱崇拜之中,“穷日夜之力,以逐锱铢之利,而遂忘日夜之疲瘁也”[7]。金钱甚至取代礼法,成为衡量一切社会价值的标准,如冯梦龙曰:“父非此不云慈,子非此不云孝,生非此不遂,名非此不立。虽大圣达贤,大英雄到此,只得唤它做没奈何也。”[8]逐利之风强烈地侵蚀着传统的社会礼义道德秩序,德信礼义逐渐被浮糜奢侈的享乐主义所取代,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社会秩序渐趋失控。屠隆批评道[9]第7册:199-200:
闾阎之间,厚妻子而薄父母,狎淫朋而疏兄弟,笑贫贱而轻廉耻,鲜退让而尚争斗,薄本业而尚冶游。家无担石之储,而身披罗绮之服。出则纵饮博之乐,而入不问瓮餐之需。闻一道德方正之事,则以为无味,而置之不道;闻一淫纵破义之事,则投袂而起,喜谈传颂而不已。……此庶民之俗坏也。
由此可见,在拜金主义思潮影响下,封建纲常伦理的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世风渐漓其真,不复明前期淳厚之貌。金钱显示出强大的诱惑力,整个社会趋之若鹜,士人阶层亦不例外。如屠隆称万历时期“士束发授书,日夜垂涎富贵,望一旦得志,而高堂广厦,堆金积玉,妖姬娈童,清歌艳舞,绝不以怀仁负义、济时行道为念。……此士子之俗坏也。”[9]第7册:199不少士人为逐利变得虚伪不真,口谈道德而心同商贾,表面上仁义道德,内心实为图谋私利[9]第7册:179:
人之好附而趋利也!……当途好道学,则争宽衣博带,绳趋尺步,聚徒结社,高谈性命以进;当途好佛老,则争言泥洹羽化,虚无空寂,机锋玄解,饰有道气象以进;当途好功名,则争谭黄石《素书》、五兵《三略》,攘臂请缨,东征夷,北讨虏,作英雄面孔以进;当途好简朴,则争敝车羸马、粗衣粝食,内或多欲,外示清真以进;当途好辞赋,则争夸雕龙绣虎,人怀寸珠,家藏片玉,握管函牍亦进。
屠隆对这种心口不一、言行相悖的虚伪浮巧士风深恶痛绝。《昙花记》虽系写唐代,然其所描写的各种社会不良风气与虚伪奸诈之徒,恰是对晚明世风的批判。时人亦发现了这一点,如臧懋循评《昙花记》曰:“长卿颇有伤时之意。”[10]543屠隆对晚明士风的不满在第三十三出“遍游地狱”体现得尤为明显,“只因近日士大夫迷真逐假,矫饰欺人,一切道学气节,诗文仙佛,往往多是作假的”[10]280,故阎罗在十八层地狱之外新设“假地狱”,以惩罚那些表里不一的作伪士人。
再来看晚明士人的信仰危机。晚明逐利之风使政治日趋黑暗,法纪日颓,政以贿成,“有廉直自持、任劳任怨者,或被屈抑;贪墨无耻、浮躁饰非者,附和结纳,以致是非淆乱,纲纪日颓,士风日坏;又有等不循法守,专挟制人之术,嘱托营私,甚废公直”[11]。政风的败坏使不少士人失去了政治热情,袁中道曰:“天下多事,有锋颖者先受其祸,吾辈惟嘿惟谦可以有容。”[12]中册:978陈继儒曰:“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于今之世矣。”[13]儒家的功业精神逐渐被退隐保身所取代,加之商业的繁荣与奢靡风气的炽盛,尊生、自适思想颇为流行。如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即赋予身体极高的地位:“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14]李贽曰:“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适,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糠。”[15]享乐、自适成为众多士人的人生追求。如袁宏道曰:“人生贵适意,胡乃自局促。欢娱极欢娱,声色穷情欲。”[12]上册:63-64梅国桢曰:“人生自适耳。依凭轨迹,外张名教,酷非所屑。”[12]下册:711
自适之学对传统的儒家思想产生了强烈冲击,明代中后期士风渐趋淫靡,社会上“不以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16],不少士人竭意声色,放佚浪荡。如屠隆生活放荡,自称“朝从博徒饮,暮向娼家眠”[9]第1册:36,“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17];袁中道亦有青娥之癖,坦言少年时常流连于“浮冶之场,倡家桃李之蹊”[12]中册:954;袁宏道自称“生平浓习无过粉黛”[18]1232,并放言“死而等为灰尘,何若贪荣竞利,作世间酒色场中大快活人乎”[18]1225,将恣意纵情、追求感官刺激的晚明风气展现得淋漓尽致。
士人在极度纵欲之后往往会产生空虚之感,如洪自诚曰:“宾朋云集,剧饮淋漓,乐矣。俄而漏尽烛残,香销茗冷,不觉反成呕咽,令人索然无味。天下事率类此,奈何不早回头也。”[19]屠隆曰:“及罢官,放逸稍游乎酒人。然每至酒阑客散,愧悔欲死。比明旦天青日朗,宾友来集,意念暂宽,兴趣复发,至夜复愧,悔如初今。”[9]第10册:1108而此时儒家的三不朽思想亦无法填补这份失落感,士人频频陷入精神焦虑。《昙花记》中木清泰身上即反映了晚明士人精神上的焦虑。木清泰自幼从军,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被封为定兴王,“鬼帽金貂,东朝赐第,衮衣玉带,南面称孤,富贵爵赏极矣”,于是“陈歌舞,钿钗绣袄,行乐且当年”[10]16。然而宴饮游乐并未带给他持久的乐趣,反而生出迷茫、空虚之感,“妆阁陈歌舞,叹风流一往,都无深趣”[10]10,“明说道好筵席定散,欢乐过转未殃。梦甫觉邯郸一觉熟黄粱,瞥然回首悟无常”[10]75。木清泰德行、功业、声名皆备,堪称儒家道德理想的典范,然仍不免陷入焦虑:“我木清泰世间奇男子,济世爱民,扶危定难,忠勋不小,爵位已高,青史许我标名,红妆可以送老,世事到此足矣。只是我这一点灵性,无处追寻;一副骨头,没有下落。”[10]58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人的社会价值,其三不朽理想已无法满足士人对于个人终极价值的追求,晚明士人亟需新的价值观念作为精神寄托。
二、《昙花记》的宗教教化思想
面对世风变异以及士人信仰危机,不少文人士大夫转向宗教寻求解决办法。明代中后期,士大夫阶层兴起一股佛老之风。进入万历时期,此风愈加盛行。如张履祥称:“近世士大夫多师沙门,江南为甚。”[20]刘汋称:“学者盛谈玄虚,遍天下皆禅学。”[21]士人们借助禅净理论以及因果报应思想,以恢复传统的社会秩序,而戏曲作为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频频被用来宣传宗教劝化思想。如智达作传奇《归元镜》“专在劝人念佛,戒杀茹斋,求生西方”[22];佘翘《锁骨菩萨》“辟度门于戏场,大畅玄风”[23];叶宪祖《北邙说法》阐扬净土思想,“妙谛不减风幡,令曹溪汗下”[24]。屠隆对戏曲的教化作用有着清晰的认识,《昙花记》即“以戏文为佛事”[10]549。屠隆尝自序此剧曰:“世人好歌舞,余随顺其欲而潜导之彻,其所谓导欲增悲者,而易以仙佛善恶,因果报应之说,拔起赵帜插汉帜,众人不知也。投其所好,则众所必往也。以传奇语阐佛理,理奥词显,则听者解也。导其所好,则机易入也。往而解,解而人,入省则改,千百人中有一人焉,功也。”[10]549《凡例》亦云:“此记广谭三教,极陈因果,专为劝化世人,不止供耳目娱玩。”[10]549可见,《昙花记》以教化民众、挽救世风为宗旨,虽系宗教剧,然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张琦评曰:“《昙花》一记,愤懑凄爽,寓言立教,具见婆心。”[25]以下分别从极陈因果、广谭三教、弘扬忠孝三个方面分析屠隆的救世思想。
(一)极陈因果以警戒世人
业报观是释、道理论的重要内容,宣扬天理昭彰,奖惩分明。《太上感应篇》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因果报应对民众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与震慑力,有时甚至可以“补王法之所未及”[26]。“世道不古,人心浇漓,礼教不能劝化,刑罚不能禁止。惟感应二字,可以动其从善去恶之良心。人即不畏王法,未有不畏鬼神者”[27],故因果理论常常被用来劝化世人尤其是下层市民,如《蕉窗十则》曰:“遇上等人说性理,遇下等人说因果。”[28]
屠隆认为世人之所以敢为恶多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惩罚不力。“神”的缺席使世人肆无忌惮,《昙花记》中奸臣卢杞的一段说白道出了古今不少作恶者的心理:“有人说:功名富贵,天命安排。暗室阴谋,神灵监察。这个也不管他。天道难明,神灵谁见?”[10]114为彰显“善恶到头终有报,皇天上帝眼分明”[10]271,挽回世道人心,《昙花记》不仅设置天王使者下界暗访,逐一考察人间众生之罪,“若是清心寡欲,正直慈悲,重重功德,悉记善曹,以须赏激;假饶浊乱贪污,奸回残忍,重重恶愆,直书恶簿,听候行诛”[10]109;而且借鉴地狱观念,设置冥司断案情节,“世人造业 ,不论广众大庭、暗室屋漏,不论施为行事、动念举心,这里幽隐悉知,毫发毕照”[10]286,以增强震慑力量。屠隆在剧中极陈果报不爽,第三十六出《众生业报》更是历数古今奸邪之士死后业报:伯嚭因“生前专一谗谤忠良,陷害伍子胥”,被阎罗天子罚作杜鹃鸟儿,“口中终日流血”;司马懿因“平生为人奸险幽暗,深藏不测”,被罚作癞黑蟆,“终日只躲在泥坑里,好生气闷”;杨再思因“生平为人谄佞”,被罚作叩头虫,“逢人便叩”……以示因与果“到头难避,无漏无差毫与厘”,从而“劝世人及早回头策厉”[10]301-302。屠隆在描写报应时流露出鲜明的现实批判意识,如第三十二出《阎君勘罪》令伏后边鞭打曹操边叱其罪状:“一手掌河山,挟风雷指顾间,诛锄义士把各雄剪。神机鬼关,难逃老奸,阴谋昼夜无停算”,“你流毒遍,多少忠良命早捐,谁不思为主分忧除国难”[10]269。如此不留情面的嘲讽,当然不只是对曹操的激愤,而是对现实中所有奸佞之徒的严正声讨,正如祁彪佳评其:“唾骂奸雄,直以消其块垒。”[2]20
(二)广谭三教以挽救士风
为恢复传统的社会秩序,屠隆不仅借助因果报应思想对世人尤其是下层市民进行外在约束,亦通过禅净思想来加强士人内在修持,以挽救士人精神危机。在他看来,传统的儒家功业思想已无法满足士人对于人生终极价值的追求,“英雄翕张簸弄,其所建树非不伟,然为不闻道故多所粘滞,多所留滞,全少洒脱自在意思。天下或蒙恩泽,而自己却无受用”[9]第6册:409,“我们只知道古来圣贤豪杰立三不朽,垂千百年。那修道德的俎豆宫墙,干功业的姓名麟阁,做文章的藏草名山,这便是豪杰的极则了,那里知道别有一种出世的大道”[9]第11册:469,故倡导三教合一,借佛老以化解士人精神焦虑,“夫儒者在世之法也,释者道者出世之法也。……儒者其道治世,修明人伦,建立纪纲,法精网密,人待以为命。然而世法荣华,易生健羡;世法无常,易生得失;世法束缚,易生厌苦;世法勤劳,易生烦躁。至于释道贵寂寞而去荣华,重性灵而轻得失,离束缚而尚摆落,舍烦躁而就凄凉。……故三教并立不可废也”[9]第8册:599-600。屠隆虽主张三教合一,但儒、释相较,仍以释为高,故木清泰欲求自我生命的解脱,辞家远游,去云水间寻求出世大道。
具体到修行上,屠隆主张禅净兼修,《昙花记》对此多有陈述。如第五十出祖师称:“禅与净土,虽分两途,其实修禅须兼净土”,“禅兼净土,两修持应无错途。论生时非佛非凡,究真诠即心即土”,“往生之路,只在一心。既要守如来之戒,亦须知观想之方”[10]437。屠隆特别强调修行的坚定性,“修行之事,理虽顿悟,功必渐修。要炼身心,须历境界”[10]81,第十二出《群魔历试》令雷神、巨蟒、猛虎、凶鬼等诸魔沓来,轮番骚扰,以试木清泰心性;而后更是令其在僧道指引下遍阅阴府泥犁与西方净土大千世界,“磨炼身心”[10]67。屠隆的宗教思想受云栖袾宏影响颇深。屠隆尝拜袾宏为师,万历二十四年(1596)春末入南屏寺屏居三个月,期间持戒静修,日与袾宏“参订出世大道”[9]第10册:1109。袾宏主张三教合一、禅净合流,屠隆早年一意修禅,其晚年转向净土、严守戒律修持,与袾宏有着密切关系。
(三)弘扬忠孝以扶危匡世
屠隆广谭三教,虽以释为高,然并未忽略儒家思想的根基作用。在他看来,儒学乃立世之根基,在维护社会秩序与世道人心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尧、舜、周、孔为世立法,乃世界砥柱、人生命脉。自有生以来,固诚不可一日而少废”[9]第9册:755,“儒者譬则嘉食也,释道譬则浆饮也。以释道治世,若以浆济饥,固无所用之;欲存儒而去释道,若食谷而不饮浆,如烦渴何”[29],“用儒道以匡时立教、治国修身,用佛道以理性归真、出尘超劫”[9]第6册:476。屠隆始终未放弃入世救世之心,他认为“本菩萨之心,行豪杰之事,致君于尧舜而,世莫窥其作用。横出竖出,总是真如;顺行逆行,无非佛事”[9]第9册:766。如果说木清泰出世求道代表了士人功成后的解脱之道,木清泰之子木龙驹“寻亲靖难、忠孝两全”[10]474则体现了屠隆对未经仕途的青年后辈的期许。《昙花记》中木龙驹见父亲证道成仙,欲效仿其弃家云游,却被阻止:“情关父子心自苦,且回家列职承茅土。愿你精忠报主,努力起雄图。父拥幢幡趋紫府,儿荣冠盖昌朱户”[10]156,“令郎根器不凡,将来亦必入道。今日且立功根主,先奉人伦耳”[10]462。于是木龙驹“志立功名”[10]431,沙场讨叛,克复神京,立下赫赫战功。木清泰虽已遁入空门,然亦未绝救世之念,路遇身遭冤屈、家贫如洗的黄氏父女,即施财修书以助,尽显侠肝道肠。
《昙花记》中体现出的救世精神正是屠隆现实心态的真实反映。屠隆早年以儒家进取思想为主,怀抱兼济天下的宏伟理想:“我昔雄心出寥泬,许身管乐倾豪杰。长思只手擘风云,数梦骑龙扶日月。中年作吏出专城,江淮吴越称神明。严霜烈日砭肌骨,凄风苦雨怀精诚。东南千里待举火,布衣贤豪倒屣迎。妻子饥寒都不问,要与天壤加峥嵘。”[9]第5册:21即使罢官后亦未忘情世事,自称:“隆业已屏居物外,称黄冠道民,学摄心炼性之妙法,而世事方艰,隐忧时起,雄心未死,侠骨尚存”[9]第7册:144,“东教以如伤为爱,西方以平等为慈。学道人即息景蒲团,那得便秦越众生,了不关念”[9]第10册:1313。万历十五年,浙江水旱严重,死者无数,屠隆虽削籍闲居,然“睹记时事,有慨于中”,遂察民病之缓急、酌时势之变通作《荒政考》,以期“为当事者采而行之”[30]。万历二十年,倭犯朝鲜,明朝军队入平壤战倭失败,屠隆作《南北备倭策》,欲向兵部尚书献策。可见,屠隆虽隐居学道,然“复以人世疾苦挂诸胸怀”[9]第10册:1313,终未弃忧国忧民之心。
三、《昙花记》的艺术特色
戏曲作品大多以叙事或抒情为主,而《昙花记》目的“专为劝化世人,不止供耳目娱玩”[10]550,以说理为主。说理性使《昙花记》对传奇文体的传统体例多有逾越,正如屠隆《昙花记·凡例》所言此剧“多创新意,并不用俗套”[10]550。以下分别从结构排场、人物形象塑造、曲白比重三个方面分析《昙花记》的艺术特色。
(一)结构松散化
王国维称戏曲“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31],情节作为戏曲的要素之一,在戏曲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元、明戏曲家对情节结构颇为重视,剧本大多有着精彩的故事情节与清晰的叙述脉络。《昙花记》意在“讲说仙宗佛法”[10]550,该剧以说理而不是情节作为结构线索,故全剧结构颇为松散,情节不连贯,戏剧冲突淡化。《昙花记》开场称“会撒手的定兴王木清泰金精铁炼,早回头的卫夫人玉洁冰清,建功业的大小侯麒麟并画”[10]10,《昙花记》即以木清泰辞家云游、妻妾居家修行、儿子木龙驹外出寻父后沙场建功为主要线索,其中尤以木清泰一脉为主。《昙花记》试图以木清泰的上游仙界、下游地府绾系全剧,然不少出目却游离于该线索之外。木清泰的空场戏实有十出之多,如《奸相造谋》《士女私奔》《仇邪设谤》皆为阐述众生作恶及报应不爽而设,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卓锡地府》《阎君勘罪》《冥司断案》三出叙木清泰游地狱观阎王审案,阎王成为主角,而木清泰仅为串连情节的线索人物。《昙花记》打破了戏曲“一人一事”的结构传统,大部分出目颇为独立,不少人物亦仅为说理而设,如昙花一现,来去匆匆。评论家常批评《昙花记》系众多碎片的堆砌凑合,缺乏一以贯之的情节结构。如吕天成评其“说世情极醒,但律以传奇局,则漫衍乏节奏耳”[4]255;徐复祚评其“肥肠满脑,莽莽滔滔”[32];臧懋循嫌“头绪太多”[10]541,故其改定本对《昙花记》进行了大量删节。
(二)人物形象概念化
人物形象塑造是戏曲作品的重要内容,传统戏曲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多具有较为鲜明的性格特征与典型意义。《昙花记》中有姓名的出场人物虽高达70余位,然几乎没有多少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这与该剧“以传奇语阐佛理”[10]549的宗旨有着直接关系。屠隆塑造人物并不在于人物形象本身,而在于其背后传达的教化思想。如第十五出《士女私奔》演书生顾雕龙与比邻佳人陈木难的情爱故事,然作者用意显然并不在风情,而是借此惩戒私奔行为,以示人间恶事天庭皆晓。顾雕龙、陈木难形象皆为说理而设,故十分苍白。《昙花记》中的人物形象或为反映现实中某种现象,或为阐述某种理念,皆属教化思想的承载体。例如卢杞形象,实际上就是现实生活中一切专事谗言毁谤的奸臣的化身。卢杞的形象不仅是现在的,亦是过去与未来的所有奸臣的象征,正如卢杞自述“王莽之后,又有曹操;司马懿之后,又有桓温;李林甫之后,又有我卢杞。……只怕从此以后,骂我卢杞的不少,做我卢杞的还多”,“地狱苦难自支,史书骂没了期,谁知依旧多卢杞”[10]407。而宾头卢与山玄卿分别为佛、道人物的代表,均属教化思想的传声筒。其他如王戎代表“一生贪吝”者,李林甫代表“心肠太毒”者,张昌宗代表“淫秽宫禁”者[10]301,具有明显的概念化特征。即使全剧最重要的角色木清泰形象亦过于简单化,主要作为士人幡然悔悟、证道成佛的典范,并无多少性格体现。《昙花记》人物大多系说理之需所设,故明显体现出概念化、平面化,缺乏立体性与变化性,这使其与同时期传奇作品大为异趣。
(三)说白比重增大
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唱曲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故戏曲剧本大多遵循以曲为主、曲多白少的创作惯例,这与传统戏曲大多以抒情为主有关。《昙花记》意在教化,出于说理的需要,屠隆采用说白演绎情节,直接阐述宗教教义,如同僧人开坛讲经,这使全剧中曲的分量极大减弱。如第三出《祖师说法》由外扮西天祖师宾头卢阐说禅宗顿悟之理,长达千余字的说白全系一人陈说,无一句唱词,如同一篇佛理骈文;第七出《仙佛同途》由外扮宾头卢与末扮山玄卿二人讨论佛老同途,整出戏一白到底,二人完全是作为佛理道法的陈述者出现。《昙花记》共计五十五出,纯用说白的出目竟高达八出,即《祖师说法》《仙佛同途》《天曹采访》《冥官迓圣》《卓锡地府》《遍游地狱》《冥司断案》《阴府凡情》,且其中有两出戏相连,皆有白无曲,这种形式在明代传奇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说白比重的增加使戏剧的抒情性大为削弱,亦影响了人物性格的塑造。此种体例常为评论家病垢,如臧懋循评其:“终折无曲,几于冷淡。”[10]541李调元曰:“屠长卿《昙花记》白终折无一曲,……其谬弥甚。”[33]然而,《昙花记》毕竟突破了戏曲重曲轻白的传统,在明代传奇史上应占有一席地位。
综上,《昙花记》虽系宗教剧,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批判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明社会秩序以及士人心态的变异,有着超越文学之外的重要社会意义。《昙花记》体现了晚明士人利用三教合一、因果报应等宗教教化思想为恢复传统的道德秩序所做出的努力。该剧一反以叙事或抒情为主的戏曲传统,为较好地实现说理劝化目的,对传奇文体的传统体例多有改变。无论是思想方面还是文学方面,《昙花记》的地位与意义都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朴斋主人.风筝误总评[M]// 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378.
[2]祁彪佳.远山堂曲品[M]//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6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3]周妙中.清代戏曲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29.
[4]吕天成.曲品校注[M].吴书荫,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
[5]吴梅.吴梅全集·理论卷:中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834.
[6]郑相修,黄虎臣纂.(嘉靖)夏邑县志:卷1[M].明嘉靖刻本.成都:四川大学图书馆.
[7]张瀚著.松窗梦语:卷4[M].盛冬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80.
[8]冯梦龙.古今谭概:微词部第三十[M].栾保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393.
[9]屠隆.屠隆集[M].汪超宏,主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10]屠隆.昙花记评注[M].田同旭,评注 // 黄竹三,冯俊杰.六十种曲评注:第22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11]南炳文,吴彦玲.辑校万历起居注:第3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1293.
[12]袁中道, 珂雪斋集[M].钱伯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3]郑元勋.媚幽阁文娱:卷首[M]//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辑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2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2.
[14]王艮.答问补遗[M]// 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主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33.
[15]李贽.答周二鲁[M]// 李贽.焚书:增补一.陈仁仁,校释.长沙:岳麓书社,2011:442.
[1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 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83.
[1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445.
[18]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下册[M].钱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9]洪应明.菜根谭[M].李伟,注译.武汉:崇文书局,2012:201.
[20]张履祥.愿学记二[M]//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中册卷27.北京:中华书局,2002:748.
[21]刘汋.先君子蕺山先生年谱[M]// 刘宗周.刘子年谱:卷40.董玚,编次.清道光四年吴氏刻本.济南:山东大学图书馆.
[22]智达.归元镜规约[M]// 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卷11.济南:齐鲁书社,1989:1419.
[23]祁彪佳.远山堂剧品[M].明末祁氏远山堂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
[24]叶宪祖.北邙说法[M]// 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清代编):第4集.合肥:黄山书社,2008:253.
[25]张琦.衡曲麈谭[M]//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70.
[26]游子安.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5:210.
[27]王砚堂.太上感应篇注[M]// 胡道静,陈耀庭,段文桂,等.藏外道书:第1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270.
[28]闵鋐.焦窗十则注解:卷下[M]// 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第4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24.
[29]屠隆.冥寥子游: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12.
[30]屠隆.荒政考[M]// 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1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195.
[3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8.
[32]徐复祚.曲论[M]//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40.
[33]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