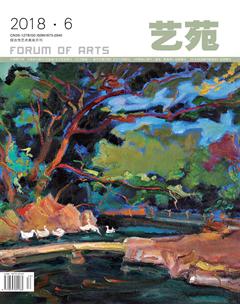禁忌与凝视
赵亮
【摘要】 厦门大学“中文有戏”毕业电影板块向来是厦大校园影像实践的重地,2018年厦门大学“中文有戏”演出季毕业电影板块的主要内容是以“身体”为主题、以《吾栖之躯》为名的短片合集。笔者担任了其中短片《之间》的编剧与导演,也与另外三部短片《相拥而眠》《红舞鞋》及《风吹不进的房间》的导演有过深入的探讨与交流。本文通过介绍此次毕业电影中各短片导演创作构思与校园电影实践中多重维度的碰撞,对各部作品的题材和视听上关于禁忌、凝视与身体的种种进行了思考与分析。
【关键词】 中文有戏;校园电影实践;身体;凝视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自2008级毕业电影《厦大,我爱你》伊始,厦门大学“中文有戏”演出季的毕业电影板块就成为了校园电影创作与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个板块当中,自时间纵线而下,诞生了无数充满自由想象与先锋创作的短片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无论类型还是题材,都彰显了厦大校园电影实践的巨大创作空间。
此次毕业电影创作从一开始便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为了更好地统合毕业电影各短片之间的种种联系,2018年的毕业电影自剧本征集起便设立了“身体”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从电影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发散而来,讨论主题之时正值社会种种女性性骚扰、性侵的新闻爆发,女性主义也是作为这个时代的电影创作者一直以来重视的方向。但经过种种讨论,我们决定不将主题设限在某一个“主义”或是某一个视域之中,于是我们将思考不断向更内化的角度进展,由此衍生出“身体”的主题背景。于是顺着“身体”这一主题而来,“禁忌”就变成了不得不讨论的一个客体。一方面是题材上,由此主题生发的题材鲜少被纳入主流题材,首先极易被纳入思考的便是各种各样关于“性”的讨论。“性”作为(尤其华语世界)受避讳的一个话题,尽管被临床医学、精神分析到后现代哲学长久地贯穿在历史当中,但对其的讨论始终处于一种被压制的状态。关乎生殖、宗族、宗教等领域的种种禁忌,“性”作为一个伦理问题始终与禁忌和权力话语伴生,更作为圆心,延展到以身体为媒介时个体到个体在不同权力话语之间的关系。这点在《吾栖之躯》中张超导演作品《相拥而眠》、金洋导演作品《红舞鞋》中做出了一些讨论的尝试。另一方面,身体作为人存在的载体和有形表征,也是感性认知的一种方法,常常同自我认同相互勾连,在权力运作(规训)和“被观看”(消费)之中形成个体与社会关系之间的不同运作模式。其中一些运作模式往往是个体对社会关系之压迫的挑战,同样也形成一种相对于权力话语的“禁忌”,在一些场景中相对于大多数的少数族群就成为了这些“禁忌”的载体,诸如跨性别者亦或是(中国)少数族裔就承载着社会观念与政策机制的“禁忌”。以这样的“禁忌”为主体的讨论在笔者执导的《之间》和张义导演的作品《风吹不进的房间》亦有所体现。由此可见,《吾栖之躯》在实践之初——題材创作上,便由“身体”而生发,在相对的“禁忌”之中探讨了不同方向的问题。这些问题同长久以来社会运作的权力机制息息相关,同时又落地到了一些社会图景下的现实主义关怀。
以上种种创作与实践的梳理源于更宏观的社会叙事背景,又同“中文有戏”毕业电影创作这个场景紧密相连。校园电影创作给予学习者和创作者更多的空间,又与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无比靠近,在没有审查机制与资本控制的创作背景下,从一些细微的社会场景便可以衍生出既有深度讨论又有现实关怀的艺术作品。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校园电影从实践和创作上仍然受才华、经验、技术与潜在的自我审查机制等所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无所谓审查机制与资本运作的背景,但这些“禁忌”仍然在创作者的自我审查、同观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学校这个仍然存在部分审查机制的场景中存在。如笔者创作的《之间》是一部讲述跨性别者认同的、传统意义上的“酷儿电影”。之所以用“传统意义上”进行形容,也是因为这部短片的内容相对“规整”,也是当代影坛上一个典型的、逐渐失去所谓“前卫性”的酷儿类型题材。其所探讨的问题、探索的尺度与行进的叙事也都被相对的控制在一个自我能把握、观者也能接受的范畴内。例如一些原本构思里的肌肤赤裸、更突显性意识和性别意识的身体姿态与故事舞台(原本的同志酒吧场景被删去),在最终呈现中其实都未呈现出来。尽管如此,笔者并不认为这些被留白和未展现的“赤裸”是一种遗憾,反而正是凸显了在校园这个场景下进行创作时所有内外交织的“困境”(在整体呈现上也许反而更“有益”),或者放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下来说,也是权力话语在运作时的昭显。
从校园电影实践的这些创作场景,我们可以一窥此次毕业电影诞生与最终呈现的种种缘由。而就《吾栖之躯》的内容本身而言,四部短片各不相同又彼此勾连,在各自的文本和结构上都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相拥而眠》《红舞鞋》《之间》与《风吹不进的房间》四部短片,使用各自的视听语言,携带着各自的意象,在各自的叙事当中做出了丰富的表达。
张超导演、胡方麒编剧的《相拥而眠》讲述了齐与红在时空中相遇,通过耳垂和后脑的身体抚摸为彼此带来睡眠和安全感,结束时发现红不过是齐的一重幻影,齐继续独自生活,独自找寻安全感。导演和编剧的阐释中,《相拥而眠》来自于对失眠、睡眠带来的安全感的若即若离,从身体触感出发,进而讨论人作为单一的个体在城市、人际空间中孤独感与安全感来源。当我们处于和其他人相处或是自我意识里不再“单一”的状态之时,我们将主体附着在对他者的依恋之上,这和对他者的“凝视”之中获得混杂性的主体建设有些异曲同工。但进一步处理的,是这样“凝视”的不稳定。区别于西方东方,男性女性这样宏大的讨论,“凝视”的权力运作机制在落到个体之时的含混并不能维持一个稳定动态,而常常是“脆弱”的。微小的个体与个体在城市空间当中,彼此观看、凝视,尽管在欲望驱动下权力是含混交叠的,但权力能够运作的空间是极小的,因而对他者的欲望往往最后落在借他人的观看去凝视自己,这样他者和自我之间的震荡增加了“凝视”与“反凝视”机制下彼此主体建设这个过程的脆弱性。《相拥而眠》中展现的结果,尽管有一个向外部的趋向去疏解这样的欲望求而不得,但男主角齐最后的状态是孤立的。整部电影最能产生共振的地方是齐在红走之后,自己在床上对耳垂和后脑的抚摸。笔者看来,这种“自慰”也是在视听上对“禁忌”的规避之后对性意识的一种呈现。主体经历一个惯常的“迷失-探寻”的叙事逻辑,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相拥而眠到“自慰”看似是一种对影片伊始枯燥生活的回归,其实是主体发掘主体性的结果。尽管我们不能据此下结论说主体建构完成,但重塑主体的过程仍然是影片深刻核心的呈现。此外,影片中出现的夜晚和凌晨的城市大楼、非常少的人群(全片除结尾只有主角“二人”)、靠海的车行大道,这些城市空间的呈现也让其背景呼之欲出。尽管并未多做讨论,但在疏离的城市当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似与特殊也是影片留白的巨大空间。
金洋导演的《红舞鞋》以一双红舞鞋串起前史与当下的纠葛。林鸿、赵静和沈安是从前同窗,沈安死后几年,赵静来到林鸿的城市参加了林鸿的剧团,排演话剧《玩偶之家》。红舞鞋既作为线索串联故事,也代表了沈安,笼罩在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头上。电影中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导演使用了两个空间联结人物,将排演《玩偶之家》、赵静饰演娜拉的困难以及电影另外的女性角色高晴放置于剧场空间之中,排演的过程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场景。而在排练之外则全部为赵静和林鸿在沈安阴影笼罩下的生活点滴。高晴作为与赵静争夺“娜拉”的角色却与赵、沈和林三人合照中沈安的形象完全一致(同一演员饰演),这也是金洋导演在电影留下的人物形象互文。高晴在排演中跳起了赵静无法跳出来的舞蹈,也作为沈安角色的现实呈现被放置到故事之中。这两重空间伴随着林鸿的刚愎自用和赵静的懦弱渐渐互相瓦解、融合,故事的核心至此回到了对于“沈安”的阴影的放下与摆脱。值得一提的是,《红舞鞋》在最终剪辑过程中改了许多版本,从一个单一线性叙事改为倒叙、插叙并行的叙事。在《吾栖之躯》其他三部短片当中也都打破了时间线性的叙事结构,或试图制造悬念,或试图将叙事多线铺陈以增添厚重感。这与学生为主的校园创作优势、困境都暗含关联,笔者在此不多做赘述。
如前文所提及的,笔者的《之间》是一部以跨性别认同过程中的个体为核心呈现对象的短片。故事的主人公高中生陈良渐渐发觉自己的跨性别意识,同时性别的流转伴随着哥哥陈正失意归乡、女同学杨青的暗诉衷情、男同学林森的人际拉扯。在经历了跨性别认同在陈正的隐隐规训、杨青表白失败后的举报、对林森诉衷肠后的背叛之后,陈良开始摇摆不定,他在各方之间,最终以女性外表呈现,却并未给出答案。故事的构思难免还是要从创作谈起。笔者本人是一个顺性别者,在创作和拍摄时悬在头上的剑便是去试图“凝视”跨性别者的这个动作趋势。尽管对于酷儿理论有所研读,但在创作时难免会陷入一些猎奇的想象窠臼,跨性别者在顺性别者的视线之中会自然地变成“他者”。于是在剧本创作的中期,笔者联系到了厦门大学里一位致力于跨性别群体公益的跨性别女性,向她咨询了许多关于跨性别者、跨性别认同的现实问题,也对剧本做了数处修改。必须要承认的是,其后执导、拍摄之时(包括顺性别者演员的出演),对于跨性别者作为他者的凝视是无法避免的,在创作与拍摄的起初这是笔者无法走出的困境。但在整个制作过程中,笔者逐渐反思的是,是不是一定要剔除掉“我”在视听基础上的政治性。这样的权力话语先定诞生,但对于创作者的主体建构的反作用力、对“凝视”的“反凝视”以及在影像虚构中“动机”的先天不纯,这些种种缘由渐渐形成了一个模糊的、试图稳定于阈限的趋势与动力,也最终变成了这部短片本身。在这样的动力驱动之下,人物设置上,笔者多数选择重叠的、镜像式的人物关系。例如陈良和杨青,两人实则都向往一种“女性形象”,却胆怯,陈良是因为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对立,而杨青则是因为男权中心权力运作下对于女性气质的贬低与女性自我身体呈现的失语。两人所承受的权力压迫本质上是同源的,而两人所追求的根本也属同宗。尽管我们可以从后现代的批评中承认这两个角色所追求的一种女性气质都从属于社会的建构,甚至在视觉呈现上也可能正如劳拉·穆尔维所言那样来自于男性中心的“凝视”;但如果加入现实主义的、更放大每一个个体复杂含混的场景的视角,如何运用这样的被权力话语所建构女性气质下真正呈现自己的主体,往往才是一个实在的、更具关怀的目标。在影片的前半部分里,有一个来自陈良的主观视角的镜头,是扫过杨青的面庞,视线落在杨青的胸部上。这个镜头的呈现尽管在客观上就是占据整个屏幕的女性胸部,但并不是要呈现女性的身体,如果强调动机的反凝视的话,似乎也就规避了劳拉穆尔维式的批判。这个镜头更多昭示的是陈良对女性的身体的渴望,也就在这里开启了跨性别意识的萌动。而杨青在最后亲吻了穿着女性服装、化上女性妆容的陈良,这也是对前一部分陈良观看杨青身体的镜头的回应。陈良第二次试图变装时与杨青的蒙太奇更是直接昭显人物的镜像关系。陈良和陈正这对兄弟关系,则相对更为简单一点。陈正在陈良第一次变装后的规劝来自于陈正自身的家庭、社会压力,而非单纯的家庭式、宗族式的二元对立压迫。陈正从城市失意归来,承担社会、家庭的“失败者”话语,转而对陈良的规劝和期待也就倾向于保守。短片后半段的剧情重要转折,一个长镜头的设置,一方面是从陈良、陈正、杨青、林森几个单独个体之间的互相交叠扩大到“学校”作社会场景的压迫;另一方面其实也是陈正在此刻从承认压迫的顺从、规训到认同陈良的解放和反抗的过程。林森这个角色意涵更为丰富,也更为含混一些。作为偶然的被倾诉者,事不关己的林森很轻松地呈现了包容、接纳的姿态,但最后凝视的目光也投向他之时,他也自然地呈现出了逃避、顺从的姿态。很难用二元的目光辨析林森是权力话语中的上层还是下层,但置于这样的场景之时,恰好成为了一种可能的状态——权力的“糖衣”,这也似乎是复杂语境里大多数人的现实境况。此外,在短片中笔者设置了一些日常物件作为意象和人物的投射。频繁出现在片中的柚子是女性生殖的视觉表征,同时柚子的干瘪、丰盈也是分阶段去表现陈良当时跨性别认同的摇摆;陈良在路边见到的女性假人模特从倒在地上到被陈良扶起、给“她”戴上假发也是一个意识觉醒的展现;陈良在家中所临摹的席勒速写(填充颜色)也有性别的暗指。但总体来说笔者没有给予主角陈良一个确定的意识或认同,而是尽可能地埋藏在一些日常圖景的变化当中。在短片中陈良也并未呈现清晰的情感取向,也许最后在剧作上他仅仅是从“模糊”达到了“不那么模糊”的状态,但这样也是我给更复杂的语境、更真实的关怀以填充空间的一个举措。
张义导演的《风吹不进的房间》是《吾栖之躯》中唯一的一部毕业作品,也是笔者认为的四部短片当中具有相对艺术高度的作品。《风吹不进的房间》在《吾栖之躯》四部短片中相对最为诗化,同时也最具现实主义关怀,讲述的是维吾尔族青年K在半虚构的城市冬门租房未果,寻求非法中介租房,又因中介的种种问题麻烦缠身最终被迫搬回宿舍。其间穿插着家庭的境况,弟弟打架,父亲进医院;还有与为凑钱租房做导游认识的女孩之间发生的故事。这些用租房中介的追债人对K的审问串联起来,将故事的叙述打散,用一个非线性的叙事搭建了一个相对诗化的影像空间。维吾尔族青年的租房问题是一个源于社会现实的截面,K的遭遇非常普遍,也并不“严重”,但其间关于少数民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位置变换,关于异乡与家庭的内外交错,都延展到了更为宏大的命题。一方面是社会现实,在这个事件当中,隐藏在整个社会结构的无可厚非之下的是关乎中国城市经济政治变迁大背景。正规租房中介的欲言又止交代了不可言说的潜台词,一件租房的事成为了一种大众视野的共识“禁忌”,这不光是普通汉族对少数民族以殖民化的视角进行“凝视”的结果,更多是作为整个宏大背景下的命运共同体被驯服成为了规避“禁忌”的主体。另一方面是精神欲望,在K的信仰和欲念中间横亘家乡与城市的隔断,与女孩橘子同床共枕,大风让窗帘四起,但K的世界在这一刻是沉闷的、无风的。在和张义导演的交流中得知,原本的剧本长度比现在所呈现的要长一倍,其中的大风四起的阳台上铺设软垫的镜头是为了之后一场中的做礼拜准备的,但在后来的考量中删除了这个场景,而把关乎信仰的、精神的更多埋藏在更诗化的视觉呈现当中。例如多次出现的洗澡镜头、主观视角的花洒与顺着浴室下水道蔓延墨色水迹,这似乎与一些关乎穆斯林信仰的禁忌相对应。相对的,一些欲望的呈现被安置在城市的描摹当中,隧道的穿梭、高大的地标式建筑自下及上的镜头竖移以及钞票的特写同租住楼房的叠画等。这些欲望的表征不一定是K的欲望,而更多对于个体而言,城市空间同消费、资本与性占有变成了同位的名词。此外,短片中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异乡人,维吾尔族的K、东北口音的租房中介阿飞、西北口音的K的朋友,乃至审问K的追债人都操着贵州口音,在“冬门”一座靠海的城市里,海风常常发作,但所有人都在一个“风吹不进的房间”里,个体命运同城市空间隔着一座陌生化的桥梁,无一例外都是被整个城市空间的特定权力结构囊括的、“凝视”的。短片的神来之笔是一处偶得的镜头,K在帮助“黑中介”收留他的朋友之后,独自站在高处平台上,背后一架直升飞机不断地向它的后方平移。这样的镜头平添了一份魔幻现实的诗意,与张义本人喜欢的塔可夫斯基(影片中直接播放了他的电影)产生了遥远的相似性。这也是电影实践里不可预测又充满魅力的所在之处。
总而言之,《吾栖之躯》是一次校园导演们个体与校园这个创作场景的碰撞,即使会生成一些结构性下权力运作的“禁忌”,但对创作、实践和学习而言,校园所支撑的仍然是一个自由、开放与培植灵感的平台。校园电影实践对学生而言是一次自我的成长与历练,对于学校而言也拥有了各种各样的话语和场景,所呈现的更包容和多样场域也为一代代学生创作者提供土壤。而就此次《吾栖之躯》的电影文本而言,朝外部的,有各种人群和城市空间的呈现与关怀;朝内部的,也有关乎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他者的以及内部主体建构的思考。虽然在经验、才能和技术上的瑕疵还有很多,但“中文有戏”毕业电影《吾栖之躯》仍是一份对自己、对学校都相对满意的答卷。这不仅是一次中国电影产业人才的培养储备,也是学校对于学生精神建设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