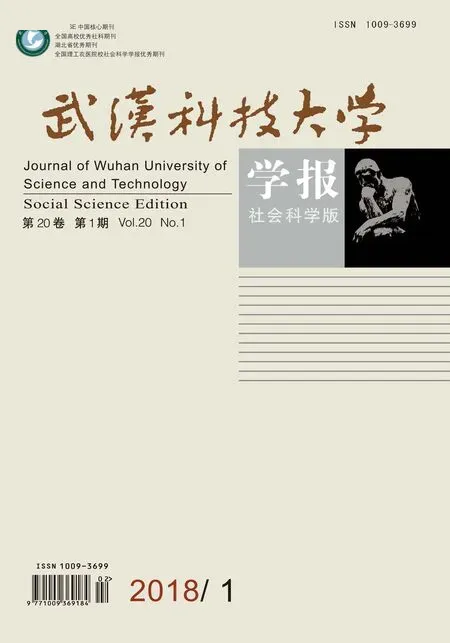论阳明“四句教”的工夫路径困难
王 帅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学术思想概括性论述,其内容如下:“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257从它诞生之日起,众多学者乃至王门后学对其所蕴含的哲学意义和价值争论不休。公元1527年,王阳明在越城天泉桥与其弟子钱德洪、王畿详细阐发四句宗旨,史称“天泉证道”。在这场天泉问答中共有三种意见:王畿主张“四无”说,即“心无善无恶,意无善无恶,知无善无恶,物无善无恶”;钱德洪则主张“四有”说,即“至善无恶者心,有善有恶者意,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阳明居中调和,主张“四句教”是“彻上彻下”工夫,要二者打并为一,“有”“无”合一。
王畿认为,心与意、知、物是体用关系,心既然是无善无恶,意、知、物就都应该是无善无恶,因此“四句教”后三句所说似乎就不恰当,他主张:“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即一种“四无”立场。而钱德洪则不赞成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认为心意知物都不是无善无恶。德洪认为,“‘为善去恶是格物’是最基本的复性工夫,否定了意念有善恶,并否定了在意念上下为善去恶的工夫,那就根本取消了‘工夫’”[2]200。对于两人的分歧,阳明采取调和立场,指出王畿的看法是接引上根人的,德洪的看法是接引下根人的,但两种看法各有局限,应“相资为用”,不可偏废。从工夫上讲,德洪坚持以意念上的为善去恶为工夫;王畿主张从彻悟心体的无善无恶入手;阳明则认为,上根之人悟透心之本体无善无恶,一了百当,下根之人在意念上为善去恶,循序渐进,即上根人入道以“悟”为工夫,下根人入道则要渐修“致良知”,顿悟之学是“从无处立根基”的工夫,渐修之学则“从有上立根基”的工夫。
一、“四句教”工夫路径的困境
《传习录》中,阳明对王畿的教法是“一悟本体,即是功夫”,对钱德洪的教法则是“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王阳明年谱》也做相同区分:“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以及“初学用此,循循有入”;《天泉证道纪》亦是如此格局。
牟宗三先生曾对此提出一个问题:“四有”“四无”都要求必须对良知本体先有所悟,上根之人尚且好说,可以一悟而知本体,“如果‘四有’句是属于中根以下之人,则如果他们‘未尝悟得本体’,则他们如何能致得良知?”[3]279-280
牟先生自己的解释是“四有”“四无”皆须悟得本体,差别在于对治工夫的有无:
上根之人顿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基,一体而化,无所对治。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中根以下之人虽亦悟得本体,然因有所对治,不免在有善有恶上著眼或下手,因而在有上立根即立足,是以心与知物皆从有生。[3]280
但这似乎不合龙溪记载的阳明“本意”:
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1]259
阳明所谓上根人直接悟入本源,其次用工夫渐渐入悟,正和《坛经》“迷即渐劝,悟人顿修”说相符,并不是说在悟本体后,尚有对治工夫的存废。
同时,德洪主张知善知恶、为善去恶是对恶的对治,则有其工夫相,如《传习录》中言学知利行、困知勉行者,尚未能依良知而行,故需多下工夫,时时省觉。那么,依此而言,根器的不同,也只表现在对治工夫的多寡,并不体现为心体上的差异。
上述问题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上根之人一悟即本体,即无需对治工夫;中下根之人不悟本体,工夫则无从确立对治方向。依德洪“四有”思路的对治功夫所达到的本体,必然是“纯善无恶”的良知,此种形态的良知对于保证道德的内在根据而言已然足够,那么似乎就没有再强调心体“无善无恶”的理由。
我们知道,阳明认为良知即心之本体,也即强调心体作为道德主体的意义,如“至善者心之本体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这个心体或良知的形态是至善无恶的。但“四句教”首句心体的形态则是无善无恶的。那么,这里的疑问是,该当如何理解良知的“至善无恶”和“无善无恶”?
阳明的调和立场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了“四有”“四无”的“本体-工夫”困难,是本文想要澄清的事情。若要厘清上述困惑,关键要明确“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含义。
二、良知的“无滞性”与“不动心”
《传习录》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於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1]66这里将“无善无恶”与“至善”划等号,从字面上理解,不同于至善,无善无恶是不具有伦理意涵或维度的。但不管怎样,无善无恶要么是超伦理的,要么就具有确定的伦理意义。根据天泉问答,阳明对“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解释是“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钱德洪主撰的《王阳明年谱》也有一段很重要的话:
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饐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4]
这段话与敦煌本《坛经》的一处话题惊人地相似:
何名摩诃?摩诃者,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若空心坐,即落无记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见一切人及非人,恶之与善,恶法善法,尽皆不舍,不可染著,由如虚空,名之为大。此是摩诃。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不思,名之为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少。莫口空说,不修此行,非我弟子。[5]
自性犹如虚空一样能含万法,但该当如何恰当地思考这类问题:什么是“虚空”或“太虚”?其是否要参与善恶的作为?仍然很难说。不过,两段材料对比,虚空有助于自性工夫,太虚有助于心体工夫,在这个“有助于”层面二者说的似乎是一个意思。
阳明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并不与伦理的善恶相关,而是在强调心本来具有的一种不粘着的状态,陈来先生称之为“无滞性”:人心就其本然状态来说,具有如同太虚一样的纯粹的无滞性。实际上,阳明自己用“廓然大公”言心体原无一物,就是对这种心灵上无滞的描述。对于这种无滞的境界,阳明有时也用另外一些词来说,如“廓然大公”和“不动心”等。让我们具体来看:
问“有所忿懥”一条。先生曰:“忿懥几件,人心怎能无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懥,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过当,非廓然大公之体了。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如今于凡忿懥等件,只是个物来顺应,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体廓然大公,得其本体之正了。且如出外见人相斗,其不是者,我心亦怒;然虽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动些子气,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才是正。”[1]204
先生曰:孟子不动心与告子不动心,所异旨在毫厘间。告子只在不动心上著功,孟子便直从此心原不动处分晓。心之本体原是不动的;只为所行有不合义,便动了。孟子不论心之动与不动,只是“集义”,所行无不是义,此心自然无可动处,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动,便是把捉此心,将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挠了,此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孟子“集义”工夫,自是养得充满,并无馁歉,自是纵横自在,活泼泼地,此便是浩然之气。[1]229
但人们似乎可以在多种意义上谈论“不动心”,比如:a.指是一个人经历人生变故后所形成的一种沉着稳定的心理性格;b.指通过强制限制意识活动的方法求“不动心”,这是一种超道德的境界;c.此“不动心”之境不是平常心,而是基于道德意识培养上的“一种特别的生理心理体验”和“一种强烈的内在充实的感受”[2]309-310。
那么,a之“不动心”并不“有助于”我们的自性工夫,甚至它很可能败坏我们的工夫修养;而b之“不动心”则根本上否定了道德工夫修养的意义;c之“不动心”,是由孟子所谓的“集义”所达至的一种结果,“集义”本身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不动心”不是预设的目的而是“集义”自然达成的结果。
对心体或良知的这种“廓然大公”或“不动心”之境界的效验,来自于阳明自述其军旅生涯。阳明曾说其良知学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是自己“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的经验之谈。但一种“以义制心而不动”的境界毕竟是有其工夫相,亦即以“集义”为头脑,那么,对于良知的“无”的这一面相,除了阳明本人的人生经历为这种境界作担保外,将“太虚”解释为“不滞性”与“不动心”之间并非完全没有张力:如何调和心灵的无滞与心灵滞留于“集义”的关系呢?或者说,如何消除无滞留的中立立场与“集义”的择善固执之的非中立立场的张力呢?除了阳明自身阅历的经验担保之外,一种执着于善的确定的伦理工夫如何达到“四句教”首句心体“无善无恶”之“太虚”的超伦理状态,至少是不清晰的。
据以上分析可以确定的是:凡一切本来具有的,就是能够通过努力达至的。心之本体即心的本然状态既然是“太虚”或“不滞性”,那么不仅是阳明,经验世界中同样具有七情六欲的任何人也能达到这种“不滞性”。并且,一切情感、念虑对于这个“心之体”而言都是异在的,因为心之体在意向性结构上没有任何“执著”,听凭情感、念虑往来出没而不滞不留,这个心体是相对于七情而言,因而不是指纯粹意识的主体,而是纯粹情感的主体。这是一种存有论的本体论视角。
三、良知本体的两种形态
根据目前所得,似乎使我们倾向于在这种意义上去理解“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含义:这里的心之体的“体”并非指某种本质或伦理原则,而是一种本然的心理状态,而且这种先验的心理状态的特征是无滞性。就此而言,阳明至少是在两个层面谈论“心体”,亦即是说,具有两种形态的良知:道德形态的良知和非道德形态的良知。
陈来先生说,阳明使良知“一心开二门”,成为一个互补的先验结构:良知本体至善无恶,是伦理内容的基础和根据,具有知善知恶的先验能力;良知本体又与“太虚”同体,其作为本体亦指心的本然状态,具有“不著意思”的先验品性。在此结构中,至善代表了结构的内容方面,无滞代表了结构的形式方面,阳明以“有”为体,以“无”为用,以“有”合“无”,实现“有”“无”合一的境界[2]218。
本体是工夫的内在依据,工夫是本体的实现方式,根据这种“以有合无”论,在为善去恶之外,另有一超越善恶的工夫,即前一节阳明所谓通过“集义”而达到心体的“太虚”或“廓然大公”或“不动心”的工夫,这个工夫最终指向一种“有”“无”合一的境界。“有”是指承认世界的实在和价值的实有,而“无”的境界可以使好善恶恶的实践因不著意思而更加便于发挥出主体的全部潜能,用“不染世累”促进儒者“尽性至命”目的的实现。
在这种阐释框架下,在工夫上就有两个层面的修行要求:一是要确认自心道德形态的良知本体的实在性,即明吾心之天理本具,不假外求;二是要将现实心理还原到其非道德形态良知的那种本然之心的状态。
天理吾心本具,所谓“万物皆备于我”,这不难理解,从而可以确立自己的良知本体的纯善无恶。但工夫对治毕竟要求“彻上彻下”的打通环节,要求将现实心理还原为具有“太虚”或“廓然大公”的超善恶特质的非道德形态的本然之心。该当如何正确地理解所谓“无滞性”或者说良知“无”的那方面?其工夫路径又是怎样打通的?两种形态的良知是否可以很好地结合在同一心体中,以及在工夫一截上,不滞的超道德境界是如何更有助于好善恶恶的道德实践的?这些问题指向均很模糊。
四、良知作为现象之本体的困境
上面论述的迟疑可简略地归结为一句话,即如何对待“四句教”中首句“无善无恶”与后三句“有善有恶”、“知善知恶”以及“为善去恶”之间的张力?根据字面意思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一种对善恶的不执著似乎是对“好善恶恶”的善恶二元价值对立的相对中立态度,以及在行动上对“为善去恶”的不执著和不计较。
如前所述,“廓然大公”只是阳明解释良知的一个面向,阳明还以“廓然太虚”为譬,而有“良知无物不有”“良知为造化的精灵”“无一物在良知之外”等诸多明确之说。根据这些说法,可以得到一个“良知作为万物的本体或本质”的本体论版本。
这是一个强立场。良知本体要负责的不只是道德的根源问题,还包含对天地万物、一切存有的说明。在这种解释下,“盖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1]41,本体即是现象,现象只是本体流行,那么一切现象都是良知本体的展开。单就此层面而言,现象世界中存在的经验事实都一定在本体良知那里找到依据。
但现象界毕竟仍有善恶相之区分,必待善恶相之泯除,乃能即本体即现象,否则本体现象就不是彻上彻下,体用分而为二。就此而言,德洪的“四有”要进至龙溪的“四无”,工夫就不落在为善去恶上,而是在于绝诸分别,达至不动心。换言之,“四无”即本体即工夫,其实就是即本体即现象。而阳明也提过“本体即流行”的观点:
问:“知譬日,欲譬云,云虽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气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象可辩,亦是日光不灭处,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然才有著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此处能堪得破,方是简易透彻功夫。”[1]240
阳明以七情乃是“人心合有”,如顺其自然之流行,即是良知之用,即良知流行的呈现;反之,如有所著,则为良知之蔽。良知的流行表现在耳目口鼻等乃至于任何知觉作用中,质言之,本体流行不异,本体现象不二。
但问题是,这种存有形态的良知如何对付经验的恶呢?经验的恶作为一种实在的现象,难道也是此本体良知的展现吗?通过上面的大致考察,阳明对现实之恶大致有两种态度:一是为善去恶的工夫对治;一是无执著于善恶的一体浑化。在道德形态中,良知本体并不负责恶的由来,良知负责的是善的可能,旨在证成心即理、心外无理,不需要对现实之恶作出说明;然而,现象中又必须承认恶的存在,那么经验中的恶作为一种现象,在阳明这里就必须得到合理的解释。
具体来说,这一理论困难是这样呈现的:在“四句教”中,以“无善无恶心之体”发而为“有善有恶意之动”,则无论是何种形态的良知,“心之体”都需要为“意之动”负责。道德形态的良知作为道德的根据并不需要对恶作出解释说明,因为本体的善与经验的恶并没有直接的直线关联;但作为非道德形态即存有形态的良知本体,不但是善的根源,发之而有善恶之意,又是所有现象的本质,而现象则是此良知本体的流行展开。但既然体用不二,形上的本体的纯善就需要对这流行展开之中的形下层面的现象之恶负责,那么,“以有合无”论在何种程度上是成立的,就需要得到进一步说明。
五、恶的来源问题使良知异化
良知心体,本来纯善,但经验之恶又不容否认。依照格物“正其不正以归于正”的思路,其工夫在于以先天之善正后天之恶,那么恶似乎就与良知无关。对于恶的来源说明,阳明除了答之以“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外,还有著名的“拔本塞源”说: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仇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1]113-114
人们知行不一或不能依天理而行的原因,在于“私欲”,因“有我之私”,而“人各有心”。阳明大概认为,恶根自于“私欲”“习心”和“气质”,通过对此三者的一个大致的梳理和界说就可以看出,对内在的良知与外在的恶的关系,阳明的说明仍未能究明。因为,恶如果是因气质形躯而来,则经验世界中,人们终不能离于气质而存,则经验对治的断恶修善,在工夫论的层面就行不通,即便是有所向善,又不断为气质形躯所沾染,岂有终日[6]。
本体现象二分的格局下,把恶交给外来的气禀或私欲负责,以解释知行不能合一的问题,是方便之计。但如果现象与本体并非截然二分,甚至现象是本体的流行,则原本外在的障蔽就不可能源自于外在,因为如果现象的一切皆不能外于良知,俱是良知的展现,那么会使人们背离良知的,就不能归咎于外来。但如果是良知自己生出了异于自己的东西,这岂不是又与佛家“自性清净而有染污”的悖论同出一辙了吗?诚然,阳明的良知担保道德行为,也担保宇宙万有,兼具道德本体与存有本体的意涵。但在存有本体的本体到现象的发动层面,阳明并未明确说明一元本体如何生出兼具善恶的二元现象。
一种可能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把意识视作心体发动的现象,意识本身虽有善有恶,但恶意是心体感物而动才出现的,那么往上推,就很容易得到心体也有善有恶,只不过在未与物感之前,善恶未现罢了。亦即是说,心体只是善恶潜在的状态,本身非善非恶,没有现实善恶可言。但这种阐发的问题是,如果心体本身潜藏恶之种,我们就没有理由为善去恶,人们将从根本上丧失为善去恶的根据。更何况,良知心体作为人们道德实践可能的根据,岂能只是被动地去等待物感而发。这种解决方案仍不能令人满意。
六、结语
如果良知是一切的本体,就必须对经验现象的善恶分明作出合理的说明。经验世界是善恶二元的,在二元现象界中存善去恶以归于一元,这不存在解释上的困难;但一元的本体是如何向下建立二元的现象结构的,这里就存在理论上的困难。阳明对良知在存有层面的确立开启了这一困难,把善念恶念交由形下的“意”负责,再把形下的“意”解释成是本体良知的呈现或流行。与其同样划分形上、形下的二元界限但并不负责去交代一种由上而下的关系的本体工夫的道德形态相比,非道德形态的本体现象一元论则需要解释恶的根源,尽管这在理论形态上更为“彻底”,但似乎仍待进一步说明。
阳明阐发良知的无善无恶的形态,旨在反对理障,反对胶着于存善念。单独理解这一点并没有难处。实际上,对两个形态的良知分别加以理解,都不会很困难,但不清楚的是,专就良知的“无”的面向而言,一种无著于善恶的境界如何可以与阳明格致的肯定工夫相契合,以及这同一良知的两种形态本身如何能够融洽无间地统一于心体。两重困境都根本性地体现为其在工夫一截上的困难,也就是,一种达到无善无恶境界的工夫与一种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的工夫终究是有差别的,而前者何以更能够有助于后者是不清晰的。尽管这种分析并非主张阳明应该放弃二者之一,但其工夫理论上的可能性在何却似乎仍有待究明。
[1] 王阳明 撰,邓艾民 注.传习录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M].台北:学生书局,1990.
[4]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306.
[5] 慧能 著,郭朋 校释.坛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49-50.
[6] 许朝阳.阳明良知学的两种型态及其对恶的处理[J].周易研究,2013(4):8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