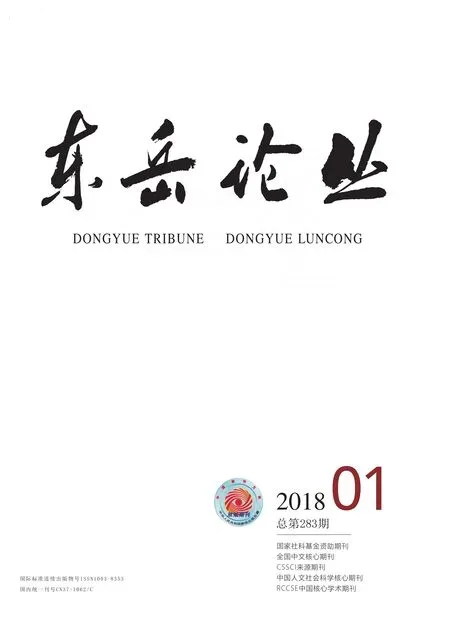“人间戏场”:刘云若小说对城市消费娱乐空间的书写
乔以钢,张 斌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刘云若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通俗文学大家。他一生创作长篇小说50余部。其作品以言情为经,以社会为纬,全面展现了近代中国都市(主要是北方重镇天津)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在当时的通俗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时人有“南张(张恨水)北刘”之称,新文学大家郑振铎甚至认为:“他的造诣之深,远出张恨水之上”①徐铸成:《旧闻杂忆》(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1页。。本文主要探讨刘云若小说中有关城市消费娱乐空间的形象化书写,考察其文化内涵和价值。
一、舞台化的市井生活
民国时期,天津的城市消费娱乐极其繁盛,不仅西方娱乐方式不断由租界向华人社会扩大影响,而且传统消遣形式也在不断更新、发展②周俊旗:《民国天津社会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第203-209页。。刘云若笔下庚子之后天津的“繁华”③《小扬州志》的开篇楔子从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这个时间界点切入,以诗话形式怀古,以鼓楼钟声消逝的寓言形式讽今。今古对照之下,揭橥了近代以来天津的城市物体形象、精神空间和文化肌理的深刻转变,也描绘了庚子之后天津都市“繁华梦”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心态。“繁华”一词不仅是包括《小扬州志》在内刘氏作品中的高频词汇,“繁华梦”更成为刘云若小说创作不绝的社会文化资源。气象,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歌舞管弦、日夜笙歌的城市消费娱乐,或者说市民文化中放纵不羁的逸乐性来表现的。戏曲、曲艺在民国时期天津市民的娱乐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京剧成为天津最具影响力的娱乐形式,平剧、河北梆子等地方剧种也在天津成熟起来。同时,天津更是北方曲艺说唱艺术的集散地④周俊旗:《民国天津社会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第203-209页。。
勾栏瓦肆是刘云若小说描述最为细致全面的城市消费空间之一。它不仅再现了当时天津戏园、茶楼之多,看戏、听曲之盛的艺海繁荣场景,以及艺人台前幕后的生活细节和生命传奇,更有意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舞台化,从而制造出一种人生如戏的虚幻感。或者说,刘云若笔下的近代天津是一座建构在舞台上的城市——戏与人生的边界是模糊的,就像以京剧女伶为主人公之一的小说《粉墨筝琶》在开篇楔子中以“人间戏场”对作品寓意的表述:
戏台上的对联,向来传述很多,不过好的很少……最好的一联,我忘了是见于什么笔记上面,联文是“何人解洗琵琶陋,若辈能逃粉墨难”,可谓寄托高远,感喟遥深。所以本书为描写最近动荡时代中的人间戏场,就摘取了联中四个字作名字,用意也不过记载一班难逃粉墨之人,净洗近年琵琶之陋……*刘云若:《粉墨筝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作品将沦陷后的天津喻为戏场,透视社会波折与世间离乱,沧桑之感溢于言表。其实,不仅《粉墨筝琶》一书如此,在戏剧化的市井人生舞台这一意义上,“人间戏场”可以作为刘云若小说创作内涵的概括之一。人生如戏的虚幻与无常,几乎总是笼罩着他笔下这座逸乐、繁华的都市,构成了作品的整体性氛围。
戏园、茶楼,是刘云若小说中一道浮华的城市娱乐消费景观,也是其最直观的空间形象表征。在他笔下的故事情节中,不断出现看戏、看杂耍、“听玩艺儿”*“玩艺儿”即曲艺。民国时期,曲艺在市民眼中只是消遣取乐、地位低下的“杂耍”“玩艺儿”。曲艺作为一个艺术概念是1949年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吴文科:《中国曲艺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的日常休闲场景,小说人物的无聊闲逛也往往离不开戏园、茶馆。比如,《粉墨筝琶》中翥青酒后闲游中央大戏院,《旧巷斜阳》中赵静存借酒消愁后无意识地到杂耍场闲坐,同一作品中张柳塘闲逛之所多是酒肆茶楼,《小扬州志》中虎士夜游夜花园的杂耍场已成习惯,如此等等,仿佛这些闲人都走顺了腿,又好像勾栏瓦肆是这座城市所有道路的尽头。由此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城市如同一家大戏场、一个大舞台,牵连着各类人士的日常生活,也消解着生活带给他们的烦恼和压力。在这之中,刘氏小说涉及的戏种、曲种极多。他写台前幕后之细致,展示剧情之准确,评戏论曲之专业,尽显行家手笔,更衬托了城市娱乐文化的俚俗特征。或者说,那鼓楼钟声消失后沉酣不醒的都市“繁华梦”,很大程度上正是凭借“人间戏场”的歌舞梦、消遣梦、逸乐梦所铸就。
在这样的“人间戏场”里,艺人特别是女艺人往往唱大轴。刘云若发表于1925年的《鼓娘小传》,歌咏了十余位优妓参半的女性。此文虽非小说,但已可见出沽上曲艺氛围之浓厚。1930年开始连载的《春风回梦记》延续了《鼓娘小传》的风格,女主人公亦出身曲海。该作开启了作者以艺海窥人生的小说创作模式。此后,《冰弦弹月记》《小扬州志》等作品皆摄取鼓曲女艺人的命运遭际,将其作为重要的情节脉络之一,而《粉墨筝琶》《酒眼灯唇录》等小说同样都有以京剧女伶的生命体验反映世事浮沉的内容线索。作为小说配角的碧莹(《酒眼灯唇录》)之类着墨不多的底层艺人,在刘氏小说中更比比皆是。与大红大紫的舞台人物相比,她们难以为继的艺海生涯反映了“人间戏场”真实、悲苦的另一面向。如果说当红艺人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近代都市轻薄的文化质感,那么底层艺人则透露出它浮华表象之下沉重的痛感。需要强调的是,此类作品所塑造的如莲(《春风回梦记》)、青青(《小扬州志》)这类传统歌姬式人物虽然珍贵,但这只是刘氏笔下消费娱乐空间的个别现象。他描写更多的,还是当时曲山艺海中普遍存在的包银主义、师徒暧昧、同行冤家、半优半妓等情态,“人间戏场”也因此而散发出真实的市井社会的烟火气味。
置身“人间戏场”,艺海之外的人物同样难逃粉墨。有学者指出,刘云若善于借鉴京剧“三小戏”的程式化人物塑造方式,即以小生、小旦、小丑三种角色为主线,形成其小说人物关系的基本格局*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此论道出了刘氏小说人物的戏场底色。其实,这种戏曲化人物的造型在人物取名上就已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虎士”“惊寰”“翥青”等“正面”男性取名通常取义高远,“散德行”(《粉墨筝琶》)、“谢杜芝”(《小扬州志》)*“散德行”在天津方言中有丢人现眼之意,而“谢杜芝”在故事中即“泻肚子”的谐音。等丑角的名字则多以谐音寓意讽刺。值得注意的是,刘氏笔下多次出现男性为女性改名的细节。虎士为妻子雪蓉改名学蓉,翥青将妻子凤云的名字改为绮琴,从中不仅流露出男性偏好闺秀的传统心理,也反映了作者在小说人物取名上的用心。实际上,人物取名的类型化是人物形象气质类型化的外在包装。翥青的清秀斯文,散德行的肥头矮胖,与他们的名字形成严格的对应。虽然这些人物未被施以“极善极恶”*刘云若:《自序》,见《春风回梦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的简单化处理,但名字作为一种标签,正像戏曲舞台上的脸谱,鲜明地标示出粉墨人物的形象特色。
在刘云若笔下,舞台与人生的界限是模糊的,台上台下皆是戏。一方面,前台表演是现实化的,不断参与故事人物命运和小说情节的进展。《小扬州志》中,李美云与黎小霞在郭宅堂会借《虹霓关》的情节掩护相互调情以至假戏做真,台上的调情演绎成了台下的奸情。《春风回梦记》中,如莲借《活捉三郎》《雪艳刺汤》等鼓词向惊寰传递消息、表达不满,同样是作品刻意打破故事中舞台间隔的重要细节。通过戏中戏的情节设计,舞台表演避免了成为风俗知识的简单展示,而是构成了人物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从而具有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的叙事功能,也造成一种生活与演戏难分难辨的错觉。另一方面,台下的场景又是舞台化的,生活的情景时常以“戏”的形式展现。《粉墨筝琶》反复强调,翥青与大巧看凤云唱戏本身就是一场“戏”。按照作品的表述,梁泽民是“幕后导演”,翥青、大巧是“唱戏演员”,他们看戏时穿的衣服“等于唱戏的行头”——这场戏的要件是相当齐备的。他们通过在台下“演戏”刺激台上唱戏的凤云,使之回心转意,与翥青破镜重圆。正因为台上台下的戏相互交织,共同推动情节发展,翥青才得以通过凤云接近汉奸蔡文仲来执行暗杀锄奸的爱国行动。
更重要的是,故事中弥漫着强烈的人生如戏的生命感受。一方面,作者将这种感受借小说人物君奇(《酒眼灯唇录》)之口道出,让他在看戏时发出“百年后,他们(台下看戏的达官贵人)也要变为戏中人物”*刘云若:《酒眼灯唇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的感叹,其中不无在宏大时空视阈中看透、看淡生活的达观,却也混杂着一定的消极意绪。另一方面,所谓人生如戏更来自社会上的小人物难以把握自身命运的无力感,以及对此的自我解嘲、自我安慰。《粉墨筝琶》中,陆凤云最初对翥青情深义重,结婚后逐渐离心背德,最终弃夫而去,回归戏场。对这段生活历程,翥青反复强调有一种“演戏”的感受。这种类似于“戏剧本能”*[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北京: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的心理甚至成为他逃避抗争命运的借口。他总是将其实主要源自其个性的颓败人生与天津沦陷这一民族灾难的历史大戏联系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便于将客观环境拉来做自身缺陷的挡箭牌,人生如戏的精神信念也便才能真正起到麻痹和解脱自我的作用。
与此同时,作品的形式也不断强化这种市井社会普遍存在的宿命感。有研究者认为,通俗小说的常规套路在“刘云若手里才神奇起来”*张元卿:《津门社会言情小说史论》,见《民国通俗小说论丛》,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实际上,这种精心安排的悬念、冲突、巧合、误会在激发读者阅读期待的同时,也通过消解日常凡俗与戏剧冲突(人间与戏场)的界线,营造了生命无常的戏剧化气氛。更为精妙的是,说话人的声音*对于刘云若小说的叙述人,学者们各执一词。有论者如赵孝萱持批评态度,认为“叙述者以采用古代说书人凌驾一切的权威口吻叙述”。(见赵孝萱:《世情小说传统的承继与转化:张恨水小说新论》,台北:台湾学生出版社,2002年版,第399页)张元卿则认为刘氏小说的说话人“消解晚清以来对小说社会作用的夸大,同时否定了‘说话人’作为史官、‘道德化身’的权威形象,把‘说话人’界定为现世中一个活生生的有个性的人,完全恢复其世俗的一面”,由此“拉近了‘说话人’与读者的心理距离”,同时“刘云若小说中的说话人却因刘氏的改造而具有故事亲历者或者不参与实践的无处不在的同谋的意味,这无疑强化了‘说话人’的叙事功能”。(张元卿:《在章回体中“起舞”的现代性——刘云若论》,见王之望主编《天津作家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68-69页)不时打断故事的进程,造成小说自圆其说的完整性和真实感遭到挑战,由此产生了一种虚实交锋的张力。也就是说,说话人不断提醒看客:故事情节再紧张,人物命运再跌宕都不过是在做戏(虚构)。于是,舞台与人生的关系更加暧昧。
生活的舞台化还是一种社会思维方式的折射。或者说,“人间戏场”是戏曲、曲艺与地方生活水乳交融的文化场域。在这一场域中,戏文曲典不仅是风俗化的地域知识,更是人物表情达意、判断是非、解读人生的观念资源。首先,艺人从小坐科学艺,读书大多有限,深受行规行风和舞台故事影响。《春风回梦记》关于如莲情感经验主要来自鼓词的表述,凤云以戏词“大丈夫难免妻淫子不肖”判断太太出毛病不算事的细节,都透露出艺人的思想底色。其次,普通市民深受戏曲、曲艺文化熏染,曲词戏典也是他们体察生活的重要参照。翥青以秦琼卖马等戏典自况窘状,雅琴以梅兰芳的扮相称赞巧儿的貌美,过铁以《朱砂痣》里中年员外对比璞玉幼子的懂事……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到,舞台故事对观众而言已超越“叙事”层面,成为真实可信、提供经验的历史或身边事。再次,叙事人也时常借用戏典、曲词。例如,凤云与大巧争夺爱情的局势扭转,《粉墨筝琶》借戏词点评:“莫道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作了姨太太的雅琴衣着华贵,《旧巷斜阳》以《四郎探母》戏中的公主相比;《酒眼灯唇录》将发生打斗的舞场比作戏台,形容这场面是唱上了《艳阳楼》,等等。小说人物及叙事人对戏词曲典的大量运用,不仅呈现了曲风戏风浸透市井,同时也彰显了天津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以“去雅向俗”为主调的城市文化基因。
艺人的明星化趋势,意味着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和社会阶层展露雏形,“人间戏场”的氛围也因此更浓。民国时期,京剧成为国粹,“玩艺儿”、蹦蹦(平戏)等低级表演形式也开始登堂入室。艺人的地位大有改观,当红者更是广受追捧。刘云若小说描述了大量捧角家,虽然多为贪婪、小气、庸俗、好色等偏于负面的男性形象,或是以女学生为代表专捧青年伶人的肤浅行为,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京剧艺人的影响力。作品挖苦捧角家以进入后台攀交艺人为荣的“后瘾”以及窥探艺人私生活的“八卦”现象,透露出艺人明星化的趋势。艺人成为明星,更得益于作为“印出来的社区之家的日记”*[美]帕克:《报纸形成的历史》,见帕克等著:《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的报纸将都市联结为紧密的生活共同体,并为大众精神共振的明星效应之形成提供了平台。
刘云若笔下的捧角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卢先生、祝矮子(《酒眼灯唇录》)这类小报记者、三流文人。这些人物在市井之中与“戏忙子”“狗腿子”并称,地位不高、水平有限,甚至因其为稻粱谋而遭尽红伶白眼。然而,正是他们的“一阵乱捧”,才使嫁人后复出的黄柳莺(《酒眼灯唇录》)“轰动九城,流传万口”。《粉墨筝琶》指出,伶人生病的新闻传播甚至快于时政要人的消息。显然,这些低等文人“油腔滑调”的文字不再是传统社会精致的无用之物,而是有着制造艺人声望和曝光度的实用功能。深谙“在这种时代,非仗着宣传联络,不能成功”的红伶黄柳莺,因此网罗了一批三流文人在报纸上宣传造势。黄柳莺等艺人的明星之路,就如同近代上海小报记者与名妓联手构建城市娱乐文化的一个翻版*[美]叶凯蒂:《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39》,杨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14-218页。。可以说,报纸媒体通过建构新的城市娱乐文化和社会阶层,以旧酒新瓶的形式更新了大众对传统娱乐想象和参与方式,由此也强化了“人间戏场”的浮华气象。
二、欲望化的娱乐空间
刘云若笔下的“人间戏场”不仅是舞台化的,它更是一个欲望充斥的游戏场。作者以名士眼光观察城市,青楼妓馆自然成为其笔下市井图卷的核心构图之一。作为欲望空间的表征,妓业、妓女的大量描述还只是表象,更为关键的是刘云若小说对娼业变迁的实录。从青楼文化到身体交易的妓业下降趋势,到新生业态对传统娼业的补充,都反映了都市消费娱乐领域浮华的肉欲氛围和物化的城市痛感。
消费娱乐的欲望化首先体现为娼业空间、北里人物在刘云若小说中的大量呈现。老报人左笑鸿谈到刘云若时曾说:“他的旧文学有些根柢,但生活相当散漫,因而对娼妓的情况很熟悉,所以小说中有不少写到妓女的,而这一部分也是他的拿手。”*左笑鸿:《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六十五)刘云若》,见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596页。此语切中刘云若熟悉北里情态并善于付诸笔端的特点。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即以曲中人物如莲的爱情故事和人生遭遇为主要内容,莺春院、忆琴楼等妓院构成了小说主要的故事场景。其后,他的社会言情小说创作延续了这种狭邪传统。《冰弦弹月记》虽“重于社会方面,和《春风回梦记》专主言情取径迥异”*刘云若:《冰弦弹月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但却是鼓姬出身的妓女生命故事的旧题重作。《小扬州志》全书肇始于虎士流连北里而遭家败,但他浮华逸乐的青楼梦魇从未真正驱除,各类妓院、班子、娼窑在他无所事事地闲逛于城市街巷时总是不期而遇。《旧巷斜阳》不仅表现了三玲书寓等高等班子情状,还通过赵家窑、横街子等下等娼窑聚处的景象,呈现了底层娼业空间的真实状态。即使在《红杏出墙记》这种描写新式青年恋爱故事的作品中,妓女柳如眉所混迹的高等妓院也占了不少篇幅。可以说,妓院不仅是刘云若小说重要的故事场景,也是他借以凸显近代城市娱乐空间乃至整个都市的欲望气息和浮华气氛的重要载体。
更有历史变迁意味的是,刘云若的小说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娼业从青楼文化传统转向肉体交易的“向下运动”*[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第24页。。在刘氏早期创作的《春风回梦记》中,尚能看到理想化的传统青楼爱情的影子。小说男女主人公如莲与惊寰之间的情感不仅无关肉体交易,且如莲还刻意保持着两人关系的纯洁性。这个女子清丽脱俗的外在形象,忠贞不渝的爱情追求,淡薄金钱、不畏权势的超凡品性,擅长濒临绝迹的子弟书技艺,以及居所悬挂名士楹联的文化点缀,都有着传统名妓的风流余韵。然而,如莲又并非典型意义上的传统名妓——她不仅不通诗书,甚至并不识字。这种德才貌不平衡的微妙信息透露出“融姿色、气质、才艺、修养为一体”*柳素萍:《晚明名妓文化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第157页。的名妓文化的衰落。此外,小说收尾处,写到若愚在前往墓地纪念如莲后,道出了松风楼已改作西餐厅的变化。这看似漫不经心的一笔,恰与如莲之死一道,共同构成了青楼文化行将终结的隐喻。故事中,松风楼不只是如莲作为鼓曲艺人时期赖以生存的演出场所,更是使她得以一入红尘便高于其他从业者的名气积累之地。在这样的意义上,松风楼象征着培育名妓的文化土壤,关联着如莲的特定身份。松风楼的欲望化空间意象因而得以与莺春院、忆琴楼一脉相承,其文化意义与如莲的名妓身份互为映照。松风楼的变迁与名妓亡故这两个象征性事件也由此而相互指涉,共同透露出名妓文化穷途末路的时代嬗变讯息。
《春风回梦记》之后,刘云若同类题材小说中所写的大多是追求金钱、以色悦人的妓女形象,极少再有传统名妓式人物。虽然从饭局、牌局、叫条子、打茶围等班子体制、规矩中约略可以看出传统青楼的怡情法则,但蕙质兰心的传统名妓形象已经更多地被物质化的摩登“名妓”、贪得无厌的俗妓和苦不堪言的底层妓女所替代。孟韵秋(《小扬州志》)、柳如眉(《红杏出墙记》)等人虽然仍享有“名妓”的头衔,但已不再是历史上那种受过教育甚至经过精心培养的高级妓女的继承者。妓与客之间很少文化、情感的互动。孟韵秋自任班主的孟寓与《旧巷斜阳》中的三玲书寓以及《冰弦弹月记》中也被称作书寓的眉月楼一样,不再具有19世纪中后期以坤书表演为主要内容的上海书寓的实际意义⑤[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第24页。,而不过是环境较好的高等班子而已。《旧巷斜阳》写到一个专做洋人生意、聘有白俄妓女的西式妓院。其细节透露出的虐恋式游戏规则和淫乱、暴力的气息,与风流薮泽中斯文雅致的文化情趣和“心灵上相互慰藉、依存”⑥柳素萍:《晚明名妓文化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第157页。的情感诉求相去甚远。凡此种种,都显示出妓业的“向下运动”,即“一种使高级妓女的服务更加‘情欲化’的趋势”*[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第109页。。高等妓院如此,下等娼窑则更讲究现实利益。正如《旧巷斜阳》中评论,“固然自古说青楼非言情之地。上等地方,或者还能发现情字的影子;到这下等地方,完全是商业性质,贪婪心情,把游客当作仇敌看待。”*刘云若:《旧巷斜阳》,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页。质言之,刘云若小说以妓业从传统青楼到性服务业的“向下运动”,揭示了近代都市繁华的肉化与物化性质。
肉欲化的“人间戏场”不仅体现在娼业空间,其他消费娱乐行业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情色化倾向,最典型的是梨园行和曲艺界。虽然民国时期艺人有明星化趋势,《酒眼灯唇录》中戏院启示“黄柳莺艺员”的称谓也体现出某种程度上的职业体面,但刘云若小说中与妓女的行业血缘最为亲密的仍属女优,“优妓之间形象的差异”*张远:《近代平津沪的城市京剧女演员:1900—1937》,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第46页。依旧模糊。一方面,青楼文化、名妓时代正在远去,高雅的诗书趣味在娼界踪迹难觅,取而代之的是皮黄、鼓曲等通俗技艺,甚至如莲、月琴所擅长的子弟书已属俗中雅音。《小扬州志》描写腊月二十五落子馆封台仪式,妓女们纷纷登台献艺,就是一次对妓/艺关系的象征性的集中展示。另一方面,艺人在兼顾本业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从事卖身行为。李美云(《小扬州志》)、陆凤云(《粉墨筝琶》)等女艺人都曾为富贵荣华而辗转于不同男性的床榻,即使黄柳莺这样的红伶也追逐“某种交易的报酬”。大巧骂陆凤云“你这种唱戏的,跟窑姐儿一样”,陆凤云也亲口承认作为变相的“高级妓女”的“苦处”——“女人唱戏,不应酬是不成的”,“只陪人吃饭也不成的”,“身上好像沾满了臭泥”。曲艺女艺人于此更甚。《旧巷斜阳》以女招待卖茶、卖笑、卖饭的“三卖事业”与莲花落的“四卖”对比,其意味不言自明。《酒眼灯唇录》也提到:“打鼓妞儿在卖唱上挣不多钱,必须别营副业,以供衣食,也就暗地流入风流行当”。这些关于艺海俗态的书写无不反映了艺与妓、优与娼的难剥难离。此外,艺人出身的如莲、月琴等女性由于种种因素入班为妓,脱离北里的孟韵秋、下海挑班的韩家潭名妓程玉娟拜为名伶姚梅生的入室弟子(《小扬州志》),则反映了“女伶与妓女时相变化”*佚名:《女伶之黑幕》,《上海黑幕一千种》,广文书局,1980年版,第1页。的行业生态。正如有的历史研究者所述,“……当时的女演员中许多曾为妓女,或被迫转而为娼,除此之外,女演员也常兼营妓业以维持生活……二者之间的界线常被模糊”⑤张远:《近代平津沪的城市京剧女演员:1900—1937》,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第46页。。可以说,在凭借演戏做艺能够获得有尊严的社会地位之前,情色化是现代消费市场促使传统演艺行当固有病态愈加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此同时,刘云若小说对随着西式消费娱乐出现的舞女、女招待等女性服务人员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法国学者安克强将随着西式消费娱乐出现的这类群体视作近现代上海“卖淫的补充形式”⑥[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第109页。。这些产生于新业态的人物时或有其标新立异的一面。比如,《旧巷斜阳》中借春楼饭庄和电影院的双料女招待梁玉珍,操着流行的标准国语,约略映现出近代都市女招待试图追求新潮流的群体性特征。按照小说中纨绔子弟周蔚青的理论,跳舞比嫖班子高尚;女招待是职业女子,比舞女地位更高。而实际上,她们与女伶一样,在兼顾本业的前提下同样时有暗操副业者。梁玉珍的职业就被表述为“变相的卖淫”。作品中月宫饭店的雅座几乎是小雏鸡等女招待暗地拉客的私密空间,女招待也因此成了食客眼中“变相的妓女”。“改业为娼”作为离业女招待为数不多的出路更显露出淫业意味。于是,月宫饭店带有了隐匿的妓院性质,对传统道德伦理在近代城市生活中的地位构成了强烈冲击。假名士季八老婆大闹借春楼、痛打女招待的闹剧,中学生朱景琦迷恋梁玉珍,以偷盗进奉而进监狱的悲剧,以及韩巧儿因作女招待遭大杂院邻居嫉妒、排挤、侮辱(《旧巷斜阳》),如此等等,都是道德风波的具体呈现。富家小姐梁意琴之所以一度很不愿意与追求者吕性扬到月宫饭店约会,也正是因为,若以正统道德观念视之,女招待与妓女、聘用女招待的休闲场所与妓院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彼时的舞厅同样是与公序良俗相悖的城市空间。《酒眼灯唇录》中描写在仙游舞场表演草裙舞的舞女鹿呦呦:“真是好一只大鹿,身体高大,曲线美丽,身上只有中间一节草裙,乳房处一副乳罩,脚下一双舞鞋,以外绝无遮掩。那光洁的玉璧,抖动的肌肉,已经炫目动人,尤其是一双丰满圆润,十分肉感的大腿,更有绝大的诱惑力,人人都心旌摇摇地,发生抱粗腿的希望。”*刘云若:《酒眼灯唇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虽然从“抱粗腿”的讽刺语调和小说叙事人自道“冷眼观察”的风格来看,这些描写与“新感觉派”小说全情投入地营造舞场迷情氛围的特色其趣颇异,但舞场性诱惑的肉欲气息同样扑面而来。更为讽刺的是,当女伶黄柳莺与舞女姜姗姗这对情敌相互攻击时,都试图以指认对方暗操卖淫副业来证明自己的贞洁。而实际上,她们互相侮辱得越露骨,其与妓女之间的相似性就越被强化。
三、等级化的消费领域
有论者指出,近代以来“租界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城市文化的等级构成,商业化成为城市文化近代演进的推动力,最终形成以市民文化为主流的近代城市文化”;然而,“传统等级文化向近代市民文化的演变”*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演变》,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页。并不意味着以商业化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消费娱乐会自然地成为一种去等级化的平民文化。恰恰相反,“消费领域是一个富有结构的社会领域”*[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现代消费社会建构起自身的等级制度和等级文化。在刘云若的文学城市中,虽然这种近代消费娱乐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的活力,但更为突出的是,它所强化的新等级文化不仅体现为消费层级的壁垒和消费人群的区隔,与此同时,作者还不时地利用叙事技巧,透视城市消费娱乐的繁华表象下“人间戏场”的真相。
城市消费领域的等级化最直接地体现为刘云若小说对消费人口阶层化现象的呈现。尽管租界促进了城市文化由传统等级文化向近代市民文化演变,然而商业只是有限度地调节和重组了等级结构。它不但无力消除、反却是在制造着城市新的阶层壁垒。消费大众化的假象背后,是资本占有不均所导致的等级分化。小说《旧巷斜阳》中老财主张柳塘和洋车夫丁二羊在同一消费空间内截然不同的经历,对此体现得十分充分。张、丁同以打探谢璞玉下落为目的,造访高等妓院三玲书寓。前者不仅受到老鸨远接高迎的礼遇,而且作为张柳塘风尘故人的老鸨还担负起帮助他赎买璞玉的中间人角色;后者则连三玲书寓的门都进不去,甚至他的洋车停放在门口都不被允许。这些细节所折映的,并不仅仅是世故的市井心态,更还有繁华都市表象背后消费领域的权力壁垒。张、丁二人在西餐厅这一新式消费空间的经历同样有一定的代表性。张柳塘心仪女招待雪蓉而流连于月宫饭店。一次他为雪蓉解了流氓之围,从此月宫上下对其视若家主。而丁二羊受璞玉所托到月宫给雪蓉送信求救,先是被女招待钱自贞侮辱为“讨饭的”,后又被小雏鸡揶揄取笑,其遭遇与张柳塘的派头形成鲜明对比,形象地呈现出消费世界所存在的“量化的身份等级制度”*[英]罗杰克:《名流:一个关于名人现象的文化研究》,李立玮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都市繁华表象下秩序的冰冷从中可见一斑——原有的阶级壁垒尚未松动之际,伴随新的资本要素的注入,又出现了更为错综的社会情态。被平民文化所粉饰的,并非一个平等的世界。
作品中从业者的悬殊境遇,同样反映了近现代城市消费娱乐业的等级机制。《旧巷斜阳》中,南市的借春楼饭庄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消费空间,这里的女招待按各自的条件被安置到分工和地位的差序之中。作品如此描述:
这饭庄共有三层楼,楼下是散座,二楼是分成鸽子笼的单间雅座,三楼却是通连的两间大厅,专备请大客用的。楼中的女招待,也随着高下而分出等次。楼下的散座,用着六、七、八号三个女招待,多是年长貌陋,由三等妓女改造的劣等货色;二楼较高一等,三、四、五号都是二十岁以下的少年,容貌也都看得下去,只是未曾出名,但虽屈在下僚,却时时有着升腾的希望;至于三楼专预备和富人贵客打交道的一、二号,那就非同小可,大有来头,是招待界中久享大名,经饭庄精挑妙选,三请四聘才得到的台柱角色,是举足轻重、关乎饭庄成败的。*刘云若:《旧巷斜阳》,第18页,第342页。
这里可以通过借春楼的空间格局看到消费本身的层级化,而其背后更为本质的是人的等级化。根据女招待的形貌、身份进行编号,来对应不同档次的消费服务的分工操作,有点类似于妓院中姐妹排行的家庭式游戏规则。小说中时常提到的作为分工依据或标准的“叫座”,其实是对茶楼、戏园里衡量艺人演出上座率的行业术语的借用和模仿。这种消费娱乐新空间对传统消费娱乐行业游戏规则的移花接木表明,在消费领域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过程中有一点始终不变,即营销活动与人的“量化的身份等级制度”的重要关联,区别只是在于,借春楼的排序规则来得更为直接和坦白。实际上,不同业态女招待的地位也不尽相同,正像作品中小雏鸡对柳塘所说:“虽然一笔写不出两样儿女招待来,可是女招待还分三六九等哪!你别把我们跟那些小饭馆和一角钱电影院的女招待,来个一锅熬啊!”小说人物自以为是的优越感,透露了不同业态之间的微妙差别。
比之女招待,妓女和艺人的三六九等之划分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妓院的姐妹排行与借春楼的编号形式相比更具人情味,但实际上妓业门第等级的存在更为严酷。《粉墨筝琶》中,大翠云历经南市班子、三等、四等、西头永套子和落马湖等娼业纵向结构的全过程,既反映了“下坠”的女性生命轨迹,也呈现了细化到令人咋舌的妓业层级。在三般九格的妓业结构中,妓女生存状态的差异是迥然的。《小扬州志》中,南市低等窑子里十二三岁的雏妓“由幼孩一跃就成为小老婆”的惨状,令人读来揪心。相比而言,故事中自任班主的孟韵秋不仅生活优裕,而且想要脱离风月场也毫无障碍。又如,同班妓女的地位、待遇也大不相同。《春风回梦记》中的如莲在选择客人和决定歇业等方面都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而同为莺春院的妓女喜子、小凤不仅毫无人身自由可言,而且遭尽毒打、虐待。这一方面是住家、包帐或讨人等*[美]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0-72页。身份差异的娼业机制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与“叫座”相仿的“红”字起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江湖艺人与此相仿。《酒眼灯唇录》中,曾经同台的柳莺与碧莹再度相逢时命运却已是天差地别,除了造化弄人,再就是一个“红”字作祟。《粉墨筝琶》中,复出唱戏的陆凤云不愿意给人“打补丁”“挂并牌”;《小扬州志》中,李美云受邀唱堂会格外计较大轴出场的地位,相关人物尽力周旋、平衡她与黎小霞的演出顺序和节目搭配,无不反映等级化的行业机制对艺人虚荣心和实际利益的影响。总而言之,在商业消费模式下,艺人尤其女艺人无论多“红”、多“叫座”,都难逃本质上作为“物”的商品性质,她们之间的层级分化其实正是其作为“商品”的物化差异。因此,《粉墨筝琶》中,齐聚怀仁堂献艺的平津名伶被表述为“真好似商店的活动橱窗中货品大拍卖”*刘云若:《粉墨筝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饭局上被安排在达官贵人身边落座的女伶被称之为“货”,而陆凤云甚至直接充当了礼品,名字赫然出现在礼贴之上。
刘云若小说时常以叙事视角的巧妙设置凸显城市消费娱乐空间的级差。据时人回忆,天津最典型的低级娼窑聚集区“以落马湖和城西南角的赵家窑历史比较悠久”*刘炎臣:《旧天津老城厢妓院概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七十六辑(《天津老城忆旧》)。。正是这两个底层娼业空间成为小说中反观城市消费娱乐浮华气象的幽暗参照系。不同之处在于,赵家窑是情节层面的,而落马湖是意象层面的。《旧巷斜阳》中,张柳塘乔装成下人到“车夫小贩花钱的地方”⑤刘云若:《旧巷斜阳》,第18页,第342页。的赵家窑营救璞玉,用他自己的话说,另一目的是“看看眼界”。这也暗示了作品以上流社会的“陌生化”视角体验底层世界的用意。因此赵家窑的情状、风俗被作为“地域知识”展示得格外细致,它们带给张柳塘的惊诧感也被描述得格外生动。作品通过“陌生化”视角凸显张柳塘“看看眼界”的惊奇体验,其实就是调动人物关于月宫饭店等上等消费空间的已有经验,建构空间反差。或者说,上流人物对底层社会猎奇式的“观看”视角,恰恰反映了底层人物在消费主义主导下的人群分化中处于被观看的“他者”位置。相比而言,落马湖比赵家窑更具神秘感和威慑感。从马五(《粉墨筝琶》)与大翠云这对妓、客二十年间“门当户对”的不断下降的霉运,到《旧巷斜阳》中掌班对“六等地方”落马湖妓女惨状的描述,都可清晰地看到落马湖深处繁复的娼业结构底部和它“火坑”般的空间意味。
然而,作为底层社会真实写照的落马湖却从未充当过故事发展的空间载体,从不与作品产生情节性关系。落马湖在《粉墨筝琶》中是通过马五的讲述来呈现的,在《旧巷斜阳》中是透过璞玉听掌班与过铁姘妇的议论勾勒出来的,总之始终处在故事主线之外。这种传说化的表现方式不仅拉远了落马湖与故事中心的空间距离,也制造了它与日常生活的距离,从而使这一空间神秘色彩倍增,其恐怖意味也由此更甚。与此同时,在大翠云坠落于妓业垂直结构的过程中,落马湖又实实在在地与故事前台的浮华情景产生了某种联系。似乎传说化的神秘空间又具有了一种似非而是的真实力量,为小说中俯拾即是的繁华景观祛魅。耐人寻味的是,刘云若小说描述赵家窑常以诙谐笔法为之,而每当涉及落马湖,幽默之箭便按住不发,仿佛刻意以隐于幕后的落马湖来表达远离“繁华”气象而又真实存在的城市黑洞的严肃寓意。
如果说情节层面的赵家窑和意象层面的落马湖是刘云若小说中消费娱乐空间的潜在参照系,那么作品中的南市则是一个多级消费空间的典型缩影。刘云若小说所写的茶楼、戏院、饭馆、妓院、旅馆大都出自南市。然而,南市不仅是租界之外集聚效应明显的城市娱乐消费中心,更是一个层级分化鲜明的休闲空间。在《小扬州志》第六回,虎士以德赛都所谓的地面行走的视角穿过整个南市,“把行动转换成可读的东西”*[法]米歇尔·德赛都:《走在城市里》,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即南市的地理情状和空间政治。虎士最先步入南市的平康曲巷,这里是旧家少爷出身的他家财败尽的旧游之地,属于高等消费区域。之后他出巷向南跨过一条臭水沟,就到了“下等娱乐”所在的东兴市场。以上两个区域相互比邻,但无论在空间形象还是在消费档次上都差别巨大。在东兴市场的内部,“还分有贵族、平民两派”*刘云若:《小扬州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25页,第470页。。市场内的小商店、室内坤书场是“贵族区域”,而市场西边是露天卖艺的“低级娱乐”空间。比东兴市场内部反差更大的是“繁华的南市”这条下等娼窑聚集的长巷。这条崎岖肮脏的巷子给虎士的印象比“暑天中的公共厕所还比较臭得正道些”③刘云若:《小扬州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25页,第470页。。穿巷而过时,虎士也遇到了与张柳塘探险赵家窑相似的低等妓女强行拉客的骇人场景。可以看到,区域不大的南市,不仅空间形态杂乱无章,消费层级也是千差万别。
总之,在刘云若笔下的“繁华”都市中,近代城市文化是逸乐性的。这种逸乐文化浸透于市井生活的骨髓和肌理——消费娱乐不仅是市民的生活方式,更渗入了近代城市的文化精神。于是,城市呈现为立体化的“人间戏场”。繁华的消费娱乐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经济社会活力,而另一方面,“人间戏场”的生动描绘也生动形象地揭示了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某些特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刘云若小说的城市书写具有特定的历史蕴含和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