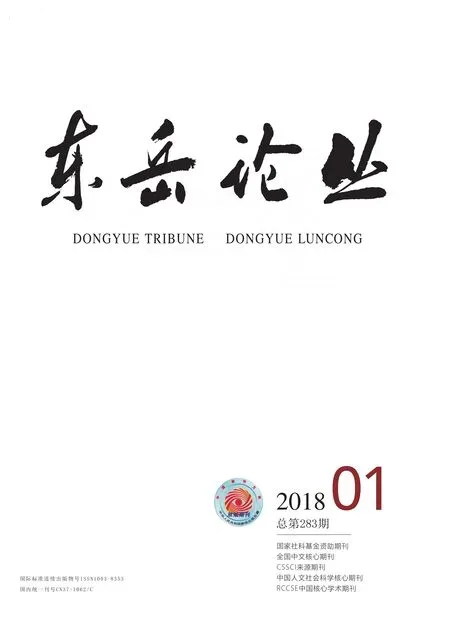人口发展与家、国生育目标比较
——基于制度的分析
王跃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国人口发展、演变深受各种制度的影响,而这些制度又集中体现在生育行为上。不同时期,“家”“国”之间形成各自的生育目标。“家”“国”生育目标既有相同也有差异。国家或政府往往通过不同形式的制度对民众与官方相一致的生育行为实施鼓励,抑制不一致的做法。本文拟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对“家”“国”生育目标类型与制度进行考察,探讨不同类型生育目标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对社会转型时期家、国生育目标进行理性分析,促使兼顾家、国两方面利益的政策出台,从而更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研究说明
(一)几个重要概念的辨析
本文主要从“家”“国”两个角度考察民众和政府的生育目标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生育行为具有引导和约束性的制度。这里首先要弄清以下几个概念。
1.“家”“国”之义
“家”,一般来说,指由具有血缘、姻缘和收养关系成员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生活单位或组织。若将“家”与生育目标结合起来,“家”成员的生育目标的形成基于夫妇的理性认识,夫妇是生育行为的直接担当者或承载体。中国社会中,在“家”中还存在对夫妇生育目标起作用的其他成员。它可扩大至直系尊亲,主要是父母,甚至祖父母,这些亲属可能通过观念意识和直接帮扶行为对子孙的生育目标和选择(生育时间、数量和性别)产生影响。在乡土社会中,这一点最突出。因而,本文中的“家”有两层含义:一是生育行为的担当之人,可谓直接行为者;二是对夫妇生育行为具有影响的直系“家”人,特别是尊亲。
生育目标中的“国”指对民众生育行为具有干预和影响作用的政府及其所掌握的各级公权力量。具体来说,“国”既指国家,也指主导法律制定、行政决策事务的中央机构。在帝制时代主要指皇权及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中央机构。民国时期则主要指国民政府及行政、立法、司法等机构。当代则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等具有决策、行政和立法权力的机构。同时需要指出,在中国不同时期,中央之下的各级政权机构秉承或受命中央政令、法律等制度精神行事,并制定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规则、政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地方政府也是“国”的代表力量。概括言之,本文的“国”是中央及其所属各级公共权力机构。
2.生育目标
一般来说,生育目标是“家”“国”对生育数量和性别构成的期望。家庭的生育目标是指育龄夫妇及其主要家庭成员对生育子女数量和性别构成的计划和追求;国家的生育目标指政府为了推动人口增长或使人口总量减少而希望民众生育的数量水平。
3.生育行为
生育行为可分为狭义生育行为和广义生育行为。狭义生育行为指妇女的孕育、分娩过程,自然属性较突出;而广义生育行为则为在一定观念和外部制度约束下妇女或夫妇对生育时的年龄、生育子女的数量和性别的选择,是社会属性的体现。实际上,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产生家庭后,生育行为是社会属性很强的一种行为。本文的研究重点针对后一种行为。
4.生育制度
生育制度指对民众生育行为具有约束和引导作用的各种规则。
基于“家”的制度主要有地方性惯习、宗规族训等。它们或直接或间接影响民众生育行为,浸润于日常生活之中。而“国”的制度主要有政策、法律等。这一类型的制度有的直接鼓励或限制民众的生育数量,或矫正民众的性别偏好。
(二)相关研究
就既有文献来看,将家、国生育目标和制度进行分别考察的论著相对较多。如从家的研究方面,主要是育龄夫妇生育意愿和行为的研究*顾宝昌:《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人口研究》,2011年第2期。*陈卫,靳永爱:《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人口学刊》,2011年第2期。*宋健,陈芳:《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与行为的背离及其影响因素——来自4个城市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5期。;从国家视角的研究,主要分析生育控制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及其在人口数量控制中所起作用,不少研究还对该政策实施的副作用进行分析。
相对来说,将家、国生育目标结合起来的研究比较少。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提出这样一种认识:在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需要从家庭、妇女的角度考虑政策取向。尽管家庭生育数量的变化和差别仅在于一个或两个孩子之间,但公共政策应重视家庭需求,有利于家庭有计划地安排生育*郑真真:《从家庭和妇女的视角看生育和计划生育》,《中国人口科学》,2015年第2期。。这可视为具有家、国生育目标意识的一种观点,但并非这方面的具体研究。笔者曾探讨过制度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指出:从家庭和国家角度看,民众生育行为受到外在和内在两种制度的作用,由此,家、国之间的这两种制度既有一致之处,也有矛盾和冲突之处,这需要相互调适,寻求最佳结合点*王跃生:《制度与中国当代生育行为关系分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就总体而言,现有的人口发展研究缺少对家、国生育目标进行比较分析,至于就不同时期家、国生育目标及相关制度的比较分析较为少见,理论探讨尚显薄弱。本文力图将生育目标置于家、国两个相对并立的语境下,采用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家、国之间在不同人口发展阶段所形成的生育目标类型及相关制度。
二、“家”“国”生育目标一致及其制度
“家”“国”在生育目标上的一致性,在我们看来,它可分为多育目标一致和少育目标一致两种。民众与政府有基本相同的生育目标,并在制度上体现出来。
(一)“家”“国”多育目标一致或相似及其制度
“家”“国”多育目标的一致主要发生在近代之前农耕社会为主导时期。中国自战国以来直至近代的农业生产组织多以家庭为单位,耕作方式以人力、畜力为主(富裕家庭有相对多的畜力投入),家庭对劳动人手的再生产——生育子女有较强的期望。家庭劳动力多少和强弱直接决定着家庭经济水平和家庭成员的生存条件。与此同时,在这一阶段,政府主导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所覆盖的人群范围很小,仅限于对极少数孤寡老人的救助。在绝大多数家庭,子女是父母年老后主要甚至唯一的赡养、照料依靠者。一定数量的子女存活下来,长大成人,家庭的养老安排才能落实。而生育目标受到当时高出生、高死亡和低增长人口发展模式的制约。只有增加生育数量,才能保有家庭世代更替、延续所需人口。从国家角度看,家庭人丁是国家徭役、赋税的征派和落实对象,故多数时代政府希望辖区民众提高生育水平,藉此增加人口。家、国生育目标具有了共同性。
1.民众中的多育目标和行为
传统时代,夫妇理想的子女数量是多少?我在冀南农村调查中发现当地的习俗中有以“5男2女7子团圆”为荣耀*河北省成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成安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759页。之说。湖北黄陂一带民众将“5男2女”视为理想结构*胡燕鸣主编:《平峰村的文化转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可见,在民间社会这一观念不限于个别地区。显然,这里的“5男2女”并非仅指生育,而是实际长大成人的子女数量和性别构成。在人口死亡率较高的传统时代,这一子女数量和性别构成目标大部分家庭是不可能实现的。笔者在冀南农村的调查中发现当地民国时期多数民众理想的生育结构是“3男2女”*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0页。。要达到这一目标,则需夫妇在育龄阶段不断生育。由此,我们认为,现代之前,人口转变(高死亡率、低增长率转变为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发生之前总体上多数民众以多育为基本生育目标。
2.多育时代政府对生育家庭的帮扶措施
近代之前政府的做法:近代之前的多育时代,家庭是生育成本(怀孕后和生产时需人照料,同时子女年幼时是净消费者)的主要承担者,若生育成本超出家庭的承受能力,则会抑制民众的生育行为。因而一些朝代的政府会给予生育家庭一些帮扶措施。
(1)减免生育家庭的赋役。它最早实行于西汉。西汉初年,承秦末大乱,全国户口减半。繁衍人口、增加劳动人手成为恢复国力不可缺少的一环。刘邦于七年(前200年)下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汉书》卷1,高帝纪)。即免除生育家庭原本应服役者两年的徭役。这一政策后世多有效仿者。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下诏: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按照汉代量制,1斛为10斗,1斗为10升。斛与石相通。汉代1石=2市斗,1市斗=13.5斤,1石=27市斤粟,三斛为81斤粟。见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史》(上),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后汉书》卷3,章帝纪)。它可能是成为东汉初年以来一项重要惠民政策。所谓“勿事二岁”、“勿事三岁”或“复其夫”,主要是免除生孩子家庭父亲或孕妇丈夫所应承担的徭役。而勿算三岁或一岁,则是免除产妇三年或一年的算赋(汉代有人口税,即算赋,15-56岁,人出120钱)。南朝齐武帝永明七年(489年)的政策继承了汉朝的做法:“若产子者,复其父”(《南史》卷4,齐本纪)。但所免徭役的年限未予说明,至少应为一年。建武四年(497年)明帝又下诏:“民产子者,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南史》卷6,梁本纪)。这一规定的免役期限明确,而且“调”(实际是赋)也在优免范围。南朝梁天监十六年(517年),武帝下诏:“若民产子,即依格优蠲”(朱铭盘编:《南朝齐会要》,民政)。“依格”表明当时有条文规定的照顾规则,非临时动议。这些政策的核心目的是促使人口增长。如果说,南朝齐明帝的做法中,除了蠲免产子家庭父母调役、赐米之外,还有一条为”新婚者,蠲夫役一年”(《南齐书》卷6,明帝纪)。该项政策显然是为新婚夫妇的生育创造条件。
(2)对生育家庭赐赏粮食等生活资料。近代之前由于粮食作物亩产量低,加之农业生产具有“靠天”特征,因水旱频发,家庭食物资料不足具有一定普遍性。为此,有些王朝将食物赐赏作为鼓励民众生育的一种手段。前述东汉章帝所定“胎养令”即属食物帮助之举。南朝一些政权对生育家庭有固定的赐赏。齐建武四年(497年)明帝下诏:“民产子者赐米十斛”(朱铭盘编:《南朝齐会要》,民政)。这个标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已不算低。另外,对灾民中生子家庭还有特别优待。南朝宋文帝令官员在赈济时,注意对生育家庭实施救助:“民有生子者,口赐米一斗”(《宋书》卷63,沈演之传)。南宋时也制定有胎养令,即从官仓中支出粮食发予孕妇家庭。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下诏:“诸路提举司置广惠仓,修胎养令”(嵇璜等撰:《续文献通考》卷32,国用考)。光宗时,福州知州赵汝愚将无主、绝户之田收益资助有生育家庭,其方式是:召佃输租,仍发籴本建仓,收储租米。遇受孕五月以上者,则书于籍,逮免乳日,人给米一石三斗”(嵇璜等撰:《续文献通考》卷32,国用考)。
(3)救助经济困难的生育家庭。东汉政府通过对婴儿家庭的救助来达到鼓励生育的目的。东汉元和三年(86年)章帝下诏:“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廪给如律”(《后汉书》卷3,章帝纪)。南宋政府对贫穷百姓中的生子家庭予以适当照顾。绍兴八年(1138年)规定: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省(嵇璜等撰:《文献通考》卷11,户口考)。绍兴十五年(1145年),高宗命贫民产子赐义仓米一斛(《宋史》卷30,高宗纪)。以此作为其鼓励人口增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孝宗于乾道五年(1169年)下诏:“福建路贫民生子,官给钱米”(嵇璜等撰:《续文献通考》卷32,国用考)。这显然也是经济困难所导致的弃养行为。上述政策,特别是免除生育家庭父母的赋役举措多实行于汉朝至南北朝之间。这与当时的赋役征派以人口、特别是成年人口为对象(非后世以土地为基础或人财并重、最终在清朝中期实行摊丁入亩之制)有关。国家通过减免生育家庭的赋税、徭役和给予必要资助,使其生育压力有所降低,进而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从政策的颁布方式上看,该时期不少政权在优待生育家庭方面有相对固定的条令,非偶然行之。这些政策中,一年及以上的赋役免除对生育者家庭生存压力的减轻有实质性帮助。“胎养”谷赐赏也有助于提高孕妇的营养水平。有些赐赏仅为象征性做法,不过其鼓励生育的导向意义由此体现出来。
当代的做法:中国当代是否存在家、国均将多育作为目标的时期?在我看来,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生育4胎(2男2女)以上的多育目标在多数民众中是存在的。当然,在政府方面,至少50年代前期,政策导向并非完全一致,对多育虽未明确鼓励,但却有扶持性做法。其后,在城市低工资和农村集体经济制度下,一些家庭因多育生活压力增大,他们往往成为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救助对象。另外,集体经济时代的粮食等生活资料分配方式,也具有向多育家庭倾斜的特征,至少在北方农村有此表现*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27-431页。。多子女家庭的生存压力由此得以缓解。
(二)“家”“国”在节育目标上形成共识
节育是指家庭或夫妇减少生育数量的行为。客观上讲,近代之前一些生育多、家境困难的民众即有此意识,但当时却无有效避孕方法可以借助。因而,真正的节育是现代避孕方式发明之后的产物。
中国电影资料馆策展人沙丹在《今日影评》说:因为黄觉戴上了眼镜,带着大家一块戴上眼镜,这个动作是跟电影中人物达到相同的一个过程,营造出一个3D沉浸式梦幻的体验。如果没有这个3D效果,《地球最后的夜晚》这部电影,尤其最后长达一小时的长镜头,跟男女主角的步履行进时,可能达不到一个真切、曼妙的感觉。
当代家庭节育目标形成的逻辑是,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出生人口死亡率大幅度降低,多数出生子女都能存活下来并长大成人。若不采取限制措施,以自然方式生育,家庭抚育压力增大。这种感受在城市民众中,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中相对强烈,故此有减少生育数量的愿望。政府因人口增长快、人口规模大给社会发展(就业、教育、医疗等)和民众基本生存(食物资料供给、住房等)带来压力,希望育龄夫妇减少生育。由此,家、国之间在节育问题上共识增大,政府推行生育控制政策的阻力较少。这是当代“家”“国”之间在减少生育问题上所表现出的一致性。而当时已经出现的避孕药物和节育手术等为家庭实施节育、政府推行节育提供了可能。
具体来说,解放后,中央政府的节育意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1956年9月总理周恩来所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适当地节制生育。要求卫生部门协同有关方面对于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中国人口年鉴》(198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第14页。。按照1957年政府草拟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60年第13期。。这一时期,政府对节制生育的提法比较谨慎,要求民众“适当地”节制生育是主调。或许这是因为当时多数民众还有多育愿望,不希望外部限制力量过大。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的节育意识增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地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③《中国人口年鉴》(198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第14页。。此后,具体的措施制订出来。1964年国务院发布文件要求对城乡居民群众施行男女绝育手术、放取节育环或人工流产的全部手术费实行减免*王维志:《计划生育和人口政策》,见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8页。。
(三)“家”“国”在少育目标上趋向一致
就当代而言,家、国少育目标是节育目标的进一步推进。从政府角度看,少育一般是指二胎及以下的生育,或者说将生育子女数量降至两个即属于少育。相比只是泛泛减少子女生育的节育做法,少育目标则有了具体的数量标准。应该说,当代全国范围内比较明确的少育目标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1973年12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强调推行“晚稀少”的做法,即男25周岁,女23周岁始得结婚,两胎间隔四年左右,每对夫妇最多生两个孩子*王跃生:《制度与人口——以中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分析》(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0页。。
从家庭和夫妇角度看,由于有前一阶段的节育宣传并予鼓励的工作基础,城市多数民众对生育两个子女的政策接受度较高。不过,应承认,在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民众对少育目标的接受度相对较低。
综合以上,“家”“国”的生育目标在现代之前农耕社会为主导的时代具有多育目标上的一致,而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特别是60年代之后,则逐渐在节育和少育问题上形成共识,在当时的城市居民中尤其如此。一般来说,当“家”“国”生育目标一致时,官方制度和民间制度会形成合力,政策落实中的冲突较少,目标实施的效果较好。这一经验是值得总结的。
三、“家”“国”不同生育目标下的制度与行为
“家”“国”生育目标不同,民众愿望和官方意志出现错位,它会有多种表现。家庭希望适度多育(如生育4个左右的子女,政府限制多育(以不超过2个为目标);家庭希望少育(生育2个子女),政府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庭采取性别选择性溺婴或流产做法,政府加以限制。家、国生育目标不同,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会引发官民冲突,民众抵触情绪大。
(一)“家”“国”在生育数量目标上的不一致
1.家庭多育与政府推行少育目标的不一致
当代计划生育工作中,一般将三胎及以上生育称为多育,这里我们采用这一划分标准。
如前所述,政府为实现人口数量控制目标而限制民众多育,这种做法主要表现在当代社会。当政府推行晚、稀、少政策之时,城市居民的接受度较高;农村居民对节育尚能接受,但若将生育数量控制在两个以内,这与其生育目标存在较大距离。因此,政府的少育政策在农村的落实效果不佳,至少在政策实施初期如此。
2.家庭少育与政府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所产生的家、国目标冲突
当婴幼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且养育成本提高之后,民众多育目标开始发生改变并能够接受或形成只生育两个子女的“少育”目标,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的城市出现这种状况。然而,政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人口生育控制力度,如80年代初推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对此,多数民众难以接受,但城市企事业单位、机关从业者受到外部政策的强大制约,不得不做出让步。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农村,尽管有制度约束,但政府可以实施的惩戒手段有限,违规者不在少数,政府不得不对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如多数农村地区独生子女政策被调整为,头胎是女儿者间隔四年可以生育二胎;山区和西部农村间隔四年普遍可以生育二胎;部分地区允许生育三胎。
(二)民众非法减少子女数量,政府实施限制
这种做法传统时代和当代均存在,但它只是一部分民众的做法。
1.生存困难民众采取溺婴等方式减少子女数量,政府和其他公共力量予以限制
在现代避孕技术产生之前,民众因家庭经济困难,抚育能力不足,有将新生婴儿溺弃的做法。这完全是家庭或夫妇的行为,但它与当时社会所提倡的道德和伦理相违背,故政府及社会组织多予限制。从现有文献看,汉朝以来至南北朝时期抑制民众溺婴、杀子的措施基本上出自地方官员之手,尚未形成全国性制度。它或许说明,这只是个别地方官员所实施的“惠政”。其他地方这种现象或许不严重,因而不被地方官所重视。宋代以来,中央开始制定全国性的政策抑制溺婴行为。宋朝有“故杀子孙徒二年”的律条(苏轼:《苏东坡全集》前集卷30,与朱鄂州书一首)。南宋高宗下诏重申荆湖、福建士民不举子之禁,“令保伍更相觉察”(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3)。“杀子之家,父母、邻保与收生之人,皆徒刑编置”(杨士奇等撰:《历代名臣奏议》卷108,仁民)。开禧元年(1205年),政府“严民间生子弃杀之禁”(嵇璜等撰:《续文献通考》卷12,户口)。明朝永乐八年(1410年),针对“京师愚民有厌子息,多生辄弃之不育”行为,政府令“严禁之,再有犯者并两邻加罪”(吕本等辑:《皇明宝训》仁宗卷,卷2,正风化)。清朝康熙十二年(1673年)政府规定:“凡旗民有贫穷不能抚养其子者,许送育养婴儿之处,听其抚养;如有轻弃道途,致伤生命,及家主逼勒奴仆抛弃者,令五城司坊官严行禁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36,禁止遗弃婴孩)。在全国,清政府在乾隆年间也采取过制止性措施,史载当时将溺婴者以“故杀子孙律治罪”,“例禁綦严”(《清穆宗实录》卷169)。解放以后,法律中仍有禁止溺婴、弃婴的规定。1950年《婚姻法》第四章第十三条:溺婴或其他类似的犯罪行为,严加禁止;1980年《婚姻法》第三章第十五条: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虽然近代之前各个时期政府多有禁止溺婴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做法,却不可能将其彻底消除。当时溺婴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无非是贫困。溺婴做法的根本性减少是在解放以后。生存条件的改善提高了家庭养育子女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之后,避孕措施和药物、手术流产技术逐渐普及,育龄夫妇得以减少超出抚养能力的子女出生。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即解放后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和城市单位制度下,妇女多在不同形式的集体组织中就业,其孕育行为处于组织或众人的视野之中,“私生”、生下来随意处置的空间被挤压。当代城乡绝大多数孕妇在医院生产,由此溺婴发生的可能性被降至最低(非婚生育另当别论)。
2.家庭溺弃女婴、选择性流产与政府的抑制
生育中的性别偏好,特别是男孩偏好可谓自古迄今一直存在。这主要是子、女在家庭中的功能差异所导致,其中与子女在家系传承中的功能不同关系密切。传统时期男女婚姻被视为“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嗣续传承实际是儿子的责任,他通过娶妻、生子来完成。这成为乡土社会民众重视男嗣的最主要原因。另外,女孩婚后嫁出,不能成为家庭的劳动力和照料老年父母的人手,对亲代的回报功能低于男孩。这一观念和行为主要表现在传统社会,当代社会基于此种认识而歧视女孩的行为并未彻底消除,农村特别是西部和南方农村该观念一定程度上保持着。
(1)溺弃女婴及其限制。近代之前,夫妇养育子女的能力不足时,溺弃女婴往往是首选。它可谓源远流长。战国时韩非子指出: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韩非子·六反》)。韩非子的这一表述显得有些极端,父母即使有溺杀女婴行为也应在至少生育一个女儿之后,而非生女即弃养。当然,他要说明的是当时民间对女儿有严重的歧视行为。就已有官方文献所见,唐宋之前育龄夫妇及其家庭虽也有溺婴行为,但没有将女婴作为主要溺弃对象。当时的文献中记载民间有“杀子”“不举子”等行为,需要说明的是,先秦和秦汉及以后的一些时期,“子”并非仅指儿子,而是子女。元代之后,生育政策中的子女分别才较为明确。元朝及其后的王朝将溺女婴的处罚纳入法律之中,说明这一现象有增多之势。根据《元史·刑法志》:“诸生女溺死者,没其家财之半以劳军;首者(举报者)为奴,即以为良;有司失举者罪之”(《元史》卷103,刑法)。明朝宪宗曾下令:“所产女子如仍溺死者,许邻里举首,发戍远方”(吕本等辑:《皇明宝训》宪宗卷,卷2,正风化)。清朝康熙中期因都城溺女“相习成风”,三十六年(1697年)政府下令:“五城司坊官严行禁止,违者照律治罪”(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36,禁止遗弃婴孩)。民国时期,一些地方政府的政令中包含溺婴内容。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广西改良风俗规则第三十二条:堕胎、溺女者依法惩处(民国二十九年《平乐县志》卷2,风俗)。正如前言,解放后的法律中《婚姻法》都有禁止溺婴规定,它所针对的主要是溺女婴现象。计划生育政策实行时期一些地区出现遗弃女婴做法,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章第二十二条专门规定:禁止歧视、虐待、遗弃女婴。需要指出,近代之前,南方一些地区如湖南、江西等溺女婴行为相对较盛,原因是当地流行厚妆奁之俗。女儿长大成人后不但不能给家庭带来财富增值,而且出嫁时还需家长花费财力为其置办嫁妆,以致成为一种负担。所以民众试图通过溺女婴减少后顾之忧;有的则通过溺女婴减少抚育投入,加速下一个生育过程的到来,达到生育男婴的目的。而这种做法也是解放后才基本上消除。
(2)性别选择性流产及其抑制。它主要是当代计划生育时代才出现的现象。在少生政策约束之下,若通过自然方式生育,一些家庭难以实现儿女双全的目标,特别是头胎生育女儿的夫妇,寄希望于生育二胎达到有子目的。由于担心二胎所生仍为女儿,故怀孕女性及其家人让一些机构(以私人机构为主)利用现代技术手段(B超)鉴别胎儿性别,若仍是女性,则中止妊娠、实施流产措施。为此,政府部门对鉴定胎儿性别的机构或医生进行惩处,没收私人B超设备等。这种做法虽有抑制作用,但却难以从根本上杜绝此类行为。中国当代出生婴儿性别比上升与之有很大关系。
(三)民众少育、晚育甚至不育与政府适度鼓励生育
在当代社会,民众已经形成少育习惯,人口总量明显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有鉴于劳动力短缺,养老负担加重,政府采取措施鼓励民众多育。政府针对民众少育行为实行鼓励生育政策在国外和境外发达国家已有所表现,中国内地尚未进入这一阶段。
(四)“家”“国”不同目标下的制度作用特征
我们认为,若就当代而言,少育和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之下,制度的效果会有两种:一是在政策高度约束和强有力引导之下,一部分民众的生育行为由多育转变为少育,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后,城市居民的生育行为就是由此发生转变的;二是一部分民众难以接受独生子女政策,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追求自己的生育目标,违规生育二胎和三胎,躲避生育,隐匿不报所生子女,由此引发官民矛盾。政府为缓解冲突,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时也应看到,在政策的约束之下,农村多数民众基本上接受了2个及以下的少育要求。应该承认,家、国生育目标不一致而政府又想干预时,改变、矫正民众生育行为的政策成本往往较高。
四、“家”“国”无相对应的生育目标
我们上面对不同人口发展环境下家、国生育目标和相关制度进行了梳理。实际上,在近代之前或现代的一些时期,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形,家、国之间并无相对应的生育目标。
(一)民众追求自己的生育目标,政府既不扶持,也不抑制
我认为,在中国近代之前,这种状况是存在的,甚至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做法。其表现为,家庭或夫妇在生育问题上有自己的数量目标;生下来的子女,能养活者尽其所能抚育,家境困难者则可能将超出抚育能力的子女送人,灾荒年份会将无力养活的年幼子女卖与他人。
政府视生育为民众家庭事务,既不鼓励也不抑制。就中国历史时期来看,隋唐之前尚有直接鼓励生育的措施,而宋元以后,除了一产三男等特殊生育现象会获到政府资助外(官方视此为祥瑞之兆),绝大多数民众的生育行为得不到政府的直接帮助,亦即政府没有具体的生育鼓励措施。它与当时的赋役制度变化有一定关系,隋唐之前,人口、人丁是政府赋役征派的重要对象,宋之后家庭财产数量或财富水平等级在征派赋役中的作用增大,至清代中期实行“摊丁入亩”,家庭人丁、人口多少与徭役征派脱离了关系,因而相应政策也无实施必要了。宋以后,政府没有与民众生育目标相对应的措施,特别是没有规范性制度措施予以帮扶,其原因还在于,政府财力有限,赋税收入更多地用于国家政治、军事系统建设及其人员消费,无力对有生育行为或因生育子女多而困难的民众予以资助。
(二)政府感受到人口增长的压力,但并无控制措施
历史上,一旦战乱结束,社会秩序恢复,民众安居乐业,生存条件改善,出生人口死亡率降低,人口数量上升,并在局部地区出现“人满”现象,进而出现食物资料短缺问题。但在当时社会,政府控制民众生育或倡导节育的认识无从产生,更不会制定降低人口数量的政策目标。客观上,当时社会政府没有质量可靠的避孕和流产方法予以推行,政府解决人口压力的基本思路是鼓励“人满”地区民众寻找尚未开垦的荒地,以此为生存困难民众提供一线生机。清代中期政府的做法就具有这种特征。雍正帝于元年(1723年)指出:“今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在其看来,解决之道“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故此他要求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七年(1729年)再次谕令户部,“国家承平日久,户口日繁,凡属闲旷未耕之地,皆宜及时开垦,以裕养育万民之计,是以频颁谕旨,劝民垦种”(《清世宗实录》卷680)。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高宗针对四川总督周人骥奏请各省流寓民人入川者甚多,请设法限制一折提出批评:“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小民自量本籍生计难以自资,不得不就他处营生糊口。此乃情理之常,岂有自舍其乡里田庐而乐为远徙者。地方官本无庸强为限制”(《清高宗实录》卷604)。可见,近代之前农耕为主的传统社会中,政府不会从人口自身再生产中寻求解决办法,而将扩大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区域或空间视为缓解人口压力的主要途径。
五、社会转型时代“家”“国”生育目标特征及其制度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进入空前的社会转型时代,传统农耕为主的社会彻底转变为非农业劳动力、城市人口为主的社会。社会转型是一个过程,目前尚处于社会转型的初期。中国城乡“二元”社会并未从根本上改观。这一人口发展环境中,夫妇生育目标的多样性比较突出。政府在进行生育政策调整时,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现状。
(一)社会转型阶段的民众生育目标
社会转型初期城乡育龄夫妇的生育目标具有多元表现,形成少部分人不生、多数人少生(2个及以下)、一部人多生(3个及以上)的格局。整体看,第二种类型将是最大群体。当然城乡和地区之间会有不同,中东部农村地区和中小城市育龄夫妇将形成少育(2个为主)、3个为辅的格局;西部地区农村多育行为仍有潜力;而大城市将可能出现只生一个、生育二个和少数不生三种主要形式。
当代育龄夫妇生育行为整体弱化及城乡民众表现出的生育目标差异与代际关系功能变化有很大关系。在城市,子女的家系传承功能弱化;农村尚有保持。城市成年子女对父母的养老保障(经济供养)功能基本丧失,农村还不同程度存在。城市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照顾功能虽然保持但已有替代做法,农村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父母仍主要依赖子女照料。与此同时,城市养育子女成本上升,特别是教育投入持续增大,子女,特别是儿子结婚时仍需父母提供住房,花费不菲。我们认为,这是城市夫妇生育意愿和行为维持在较低水平的主要原因。不过,在城市亲子之间的另一项功能情感关系依然被看重,甚至可以说,当物质性功能关系弱化之后,情感关系更受重视。还有夫妇结婚所组成的家庭,也是财产单位,多数人仍希望自己的财产由直系亲属来继承。由此,当代城市文化影响下的夫妇生育目标表现为既不愿多生,又不会放弃生育,当然这是就主体而言。
我们认为,城乡夫妇生育目标的差异并非观念的“先进”与“落后”使然,而有很强的功能考虑。当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传统乡土社会嗣续传承观念改变,夫妇的生育目标和行为既会出现“趋同”性变化,也会因地区惯习和养育子女成本不同而出现差异。
(二)当代基本人口形势及政府政策选择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即进入低生育水平维持阶段,之后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由此中国人口总量增势得到控制。2015年底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被中止。城乡育龄夫妇均可生育两个孩子。
在城市,放开二胎生育似乎有“遇冷”的表现。这种状况也属正常现象。除了上面所说的代际功能关系整体弱化外,还有一些具体因素,即城市目前的育龄夫妇主体是独生子女,他们多数人接受了中专以上的教育,对自身发展有较高追求。生育两个子女可能会影响个人事业发展。加之城市养育子女成本较高,多生育一个孩子会对其现有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从政府角度看,当放开二胎若干年后仍不能提升妇女总和生育率,那么首先须采取的不是鼓励二胎生育,而是尝试放开生育控制,使“家庭计划”得到落实。不过,在正式实施之前,应在适当时候和范围内进行试点。这样做的理由有三:一是适应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多元生育目标逐渐形成的要求,多元生育目标下,出生人口总量的大幅度增长空间有限;二是广大农村二胎生育具有普遍性,若政府仅在城市采取鼓励二胎生育措施会有新的不公平感,若普遍实施具有补贴性质的鼓励政策成本较高;三是通过实施减少对家庭生育数量直接干预的政策,为民众自己决定生育行为的“家庭计划”环境形成创造条件,现有以生育数量控制为目标的人口管理成本也将大大降低。
当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逐渐取代家庭养老保障做法时,同家庭养老保障需要家内成员代际接续一样,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维系也离不开具有一定规模、且结构相对平衡的不同代际成员进行支撑。若老年人口增长过快、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降低,将会对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维系产生削弱作用。
六、结语与讨论
中国历史和现实表明,家、国之间在生育目标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表现。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认识:
近代之前农业社会为主导的时期,医疗卫生水平低,生活资料相对短缺,高出生、高死亡和低增长为人口发展的基本模式。家庭为了保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和老年赡养人力资源,进而维系家系传承,多育成为普遍追求。在当时社会,家庭的多育目标与国家以人口、人丁为赋役征派对象的做法相一致,故此政府采取了鼓励生育的制度。在这一主导模式之下,民众中也有非主流做法。生育子女过多导致家庭生存资料不足,因无有效避孕、流产等手段,故出现溺弃婴儿等做法,特别是对女婴溺弃相对较多。政府将其视为违法之举加以抑制。
解放以后,随着医疗卫生水平提高和生存条件改善,出生婴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家庭成年子女数量增多,城市受教育水平高的育龄夫妇节育和少育意识产生,并希望借助现代避孕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因人口增长快,就业安排和教育、医疗机构建设压力大,粮食供给不足,故开始推行节育、少育政策,以减少人口总量。由此,家、国目标形成新的一致。值得注意的是,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初并未成为城市多数民众的生育目标,一定程度上讲它是靠严格的外部政策约束加以推行的。而在农村,少育,特别是只生一个子女均非多数民众的目标,因此落实难度大,政府不得不对此进行调整。
也应看到,近代之前,特别是在宋代以来,政府较少为生育、特别是多育民众提供直接帮助。民众多根据自己的养育能力选择生育子女的数量。因无有效节育方法,对超出抚育能力的子女,往往在生育后或溺弃或送人。当人口增长较快、人口压力增大、民生出现困难时,政府所能采取的措施是鼓励民众垦荒,或将“人满”地区民众迁移至荒地较多之处,而不曾制定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就中国当代而言,城市多数民众的生育目标为“少育”(不超过2个),其中大城市以只生一个孩子为目标的夫妇占一定比例。在农村,少育目标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民众中所占比例相对较高,而西部地区、南方沿海省份农村以多育为目标者非个别现象。政府希望适龄夫妇积极生育二胎,担心他们不生或只生一个孩子。总体上,目前家、国在少育目标上一致性较高。现实状况是,一些民众因抚育子女成本高而放弃生育二胎,这可能使政府希望增大二胎生育比例来改变人口结构的初衷难以实现。究竟出台鼓励二胎生育的措施还是放开生育限制,使民众的多元生育行为得到体现?这成为一个新的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总的来说,“家”“国”生育目标具有很强的功能性,且因时而变,不同形式的制度在其中起着很大的维护或抑制作用。我们应从家、国两个视角来认识生育目标和人口发展目标,兼顾家、国利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官方政策等制度才更有针对性和可行性;还应注意使官方制度与民间惯习等制度相互衔接,从而减少政策实施中的“家”“国”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