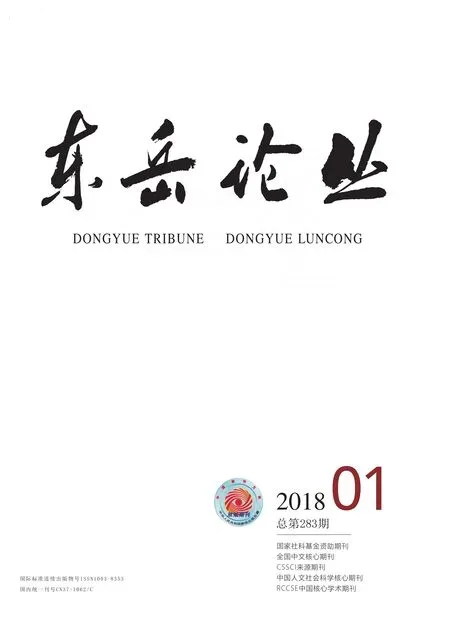《西游记》中经文的“物质性”与“空”的形而上学
安汝杰
(东南大学 哲学与科学系,江苏 南京 211189)
《西游记》第九十八回的关键时刻,唐僧师徒到达了西天大雷音寺,最终取到了他们苦苦盼望了十四年的佛经。但是,当他们离开时,灾难降临了。一阵剧烈的香风吹走了他们手中的经卷,经卷毁的毁、破的破,纸片遍地。四位取经者发现这些佛教宝典只是一些不写一字、空空如也的经卷:“沙僧接了抱着的散经,打开看时,原来雪白,并无半点字迹,慌忙递与三藏道:‘师父,这一卷没字。’行者又打开一卷看时,也无字。八戒打开一卷,也无字。三藏叫:‘通打开来看看。’卷卷俱是白纸。长老短叹长吁的道:‘我东土人果是没福!似这般无字的空本,取去何用?怎么敢见唐王!诳君之罪,诚不容诛也!’”①(明)吴承恩著,陈先行等校点,《西游记:李卓吾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3页。唐僧师徒四人怀疑阿傩、伽叶密谋欺骗他们,四人匆忙赶回雷音寺。出于对师徒四人的同情,佛祖发了慈悲,将有字真经,点够同样的卷数(5048卷),赠予四人。此时,师徒四人已经在路上渡过了5040天。这有字真经的数目恰好弥补了他们耽误在路上的时日,他们的生命和经书、路途及果报于此达到平衡。
一方面,这种不露声色地进行的经典调换作为一个笑话而存在,强调了小官员的吝啬和佛祖玩世不恭的慷慨大方。然而,这种恶作剧式的授权(赠予佛经)——用无字佛经换取有字真经——从人事上讲正如佛祖自己现身说法,即这段插曲提供了理解佛教空无思想的更深层次的信息。考虑到《心经》在《西游记》小说中的特殊意味,通过文本的“空性”来说明“空”的思想是有意义的。《心经》最重要的一句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当我们把经卷的白纸视为“色”,把字迹全无看做“空”,那么这段插曲就很好地说明了《心经》的悖论,因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种解释让我们了解了佛祖为什么说有字经文和无字经文是可以互换的。经卷的“空性”因此成为佛教教义“空”的物质载体,同时它也指向一种符号——这种符号本身是用否定方法所得的、不可言喻的最高实在的本质象征。
取经僧徒的灾难并没有在此结束。在下一回中,观音菩萨审查他们的行程,一一列出唐僧师徒经历的八十次灾难,她发现还差一次——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算是功德圆满。于是,最后一难上演了:渡过通天河。就在此时,他们之前见过的一只白色大龟帮忙渡河。但是这只龟想到在雷音寺僧徒四人忘记了问自己的阳寿(大限)而心生怨恨,于是就抖动躯体将师徒四人、白龙马和经书抛入水中。唐僧师徒四人不得不从水中捞出湿漉漉的经卷在阳光下晾晒。结果几卷佛陀传记粘在石头上,这直接导致《心经》的结尾有一部分遭到损坏。这就是今天《佛本行经》不是一个完整文本的原因,同时那个晾晒《佛本行经》的鹅卵石依然遗留了一些经文的痕迹。当三藏抱怨他们不够细心时,孙悟空立即答道:“这经原是全全的,全沾破了,乃是应不全之奥妙也。”*(明)吴承恩著,陈先行等校点,《西游记:李卓吾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7页。这就是说,经文的落水是对不完美之理的极好诠释。
从字面上看,这两个插曲只不过是僧徒四人取经途中必经的一对苦难,算不了什么。然而,它们出现在小说的末尾,讲述的是文本(经卷)的遭遇,一个关于字词的消失,另一个关于经卷的分裂,这表明它们有着深刻的寓言意义。经卷落水的插曲很可能就是受到真实的玄奘传记的启发,玄奘在传记中曾经落水,在回来的途中也丢失了一些经卷。然而,对于一个如此频繁地把历史事件演绎成宗教寓言的小说来讲,故事一定有着深刻的寓意。毕竟,当悟空自己解释说经卷文本的不完整是佛教“不完美秘密”思想的一种隐喻时,这种寓意是显而易见的。无字文本和“空”的形而上学相联系,支离破碎的文本和铭文的物质性与保存相联系;前者关涉消失的能指,后者关涉这种能指的受损载体。把这两个插曲捆绑在一起的口头线索是字迹的副本,表明经文脚本的不在场、被忘却和消失:僧徒四人看到的只是“没有字迹的白纸”和“残留一些字迹”的鹅卵石。小说的最后一章深入和反复地反映了文本的物质性和形而上学。这两个插曲强调了小说的元叙事特征,因此,《西游记》显然是一个寻找“文本”的文本。
这些无字经卷的意义,虽然已经被指出,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Anthony C.Yu在他的《西游记》翻译修订版的引言中指出,小说第九十八回的故事是禅宗语言哲学的“指月之手”,但是他没有深入分析这一“手势”*Anthony C.Yu,The Journey to the West, rev.ed.,4 vol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p.65.。Andrew Plaks在他的《明代小说四大名著》中,把讲《西游记》的一章名称定为“空的超越”,他奇怪地驳斥了这个插曲的深刻寓意:“最后讽刺的无字经卷明显的是一个赤裸裸的玩笑,除非我们选择去强调中国哲学话语中‘空’的经文传达出的众所周知的愿望,其中真经的最后复原本身进一步消解了追求的终极意义。”*Andrew H.Plaks,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Perio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243.Francisca Cho Bantly对此的回应是:“取经者取得的无字经文不含有讽刺意味。这正如佛教救世哲学所讨论的那样,觉悟不离自身,因此它不能成为获得的对象……结果……可以被简单地视为一种最终和不可抗拒的语言之‘空’。”*Francisca Cho Bantly,“Buddhist Allegory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8.3(1989):p.520.中国学者最近提供了对于无字真经主题的语言学解释成果*陈宏:《略论无字真经与小说〈西游记〉的关系》,《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6),第643-654页。。Ling Hon Lam以心学为中介或通过研究“心”提出了另外的“空”义解析,他认为“无字真经”当然是一种关于不通过语言直接自证真理的陈词滥调*Ling Hon Lam,“Cannibalizing the Heart:The Politics of Allegory and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in Literature,Religion,and East/West Comparison:C.Yu,ed.Eric Ziolkowskit ,Newark,DE: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2005,p.164.。
考虑到这些论文无一例外地强调语言之“空”的浅层含义,我认为佛祖的玩笑比起这些先前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解释,因为他们忽视了经卷的“物质性”。取经者最后带着一批经文离开,视它们为需要保护的宝贝。就此而论,恰如其分的解读不仅强调“空”作为精神原则的重要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易理解的东西——而且作为经文的物质载体——还没有得到批判性的讨论。“真经”的最后复原没有减少取经者的功德成就,相反,它承保和满足了朝圣者的目的。
《西游记》最后一章应该被解释为《心经》的寓言与扩展。经文之“空”的“形而上学”和散落经文的“物质性”恰好对应于《心经》中“空”与“色”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最终消解于佛学悖论的通过语言手段表达的非二元性,这一点被佛祖的说法、悟空的言论和叙事者的叙述所证实。《西游记》乃至于整个佛学无不表明所有的文本——不论是经文还是小说——在追求终极真理方面是必要而远远不够的。文本只是工具性的,一旦到了觉悟之河的彼岸,借以到此的木筏就应该舍弃。
《西游记》具有高度的整合性;《西游记》宽广的、充溢的想象无所不包,它的佛学研究的“来世”也正在生成。经文的“物质性”和“空性”的观点在亚洲佛教思想中是基本性的,遍及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佛典中,我们必须广泛地考察才能弄清楚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在促成佛教学术讨论方面的独特意义。
一、“空手”与残缺的经文
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中,阿傩、伽叶问唐僧师徒要“人事”的情节是该回叙事出现“波澜”的标志:“‘却说那宝阁上有一尊燃灯古佛,他在阁上,暗暗的听着那传经之事,心中甚明,原来是阿傩、伽叶将无字之经传去,却自笑云:东土众生愚迷,不识无字之经,却不枉费了圣僧这场跋涉?’”*(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1页,第722页,第684页,第729页,第729页。燃灯古佛的笑是意味深长的,他的笑潜藏着深刻的哲理。愚迷众生认为无字经文一文不值,而觉悟者视之为无价之宝——这可比拟于龙树曾经宣称的:慧根浅者误解空,犹如蛇皮难称身。孙行者把阿傩、伽叶传无字经卷之事向佛祖“申辩”。“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②(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1页,第722页,第684页,第729页,第729页。如来佛祖开玩笑似地把取经者的“空手”与“无字经文”等同了起来。
然而,《西游记》是一部寓意丰富的小说,“空手”有多重反讽意味,揭开它的寓意就能理解这一细节的深刻之处。“空手”象征着取经僧徒的不名一文;他们拥有的只是一个钵盂和一件袈裟。正如之前引文所说的那样,经文对于三藏的重要性正如衣服之于其他神职人员。玄奘说:“《般若心经》是我随身衣钵。”③(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1页,第722页,第684页,第729页,第729页。钵盂是盛饭的容器,它像僧徒四众的双手一样是“空”的,它的存在的价值在于它的“纯粹形式”,它的“空性”与容受能力。《道德经》第十一章有言:“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此外,“空手”意味着取经者不能够在他们经过的外国土地上像芸芸众生那样进行“财物交易”,不管是赠予还是索取。实际上,小说中的大部分情况是当取经人空手而来他乡做客时,许多“当家人”都觉得不舒服。总之,这还不是最窘迫的,取经者在西天大雷音寺无法提供礼物不仅使该寺掌经者不悦,也使他们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当他们经历曲折取得真经时,他们的身份也随之来一个大转弯:他们成为永恒文本的捐赠者,而不是可朽食物的乞讨者。
经文营养心灵,钵盂盛物饱人——这些物质性的东西供给尘世之用:一个武装思想,一个维持躯体。一旦取经者摆脱了世俗的欲望,这些器具就会变得多余。《金刚经》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金刚经·第六品·正信希有分》)在小说第一百回中,大唐皇帝为取经僧徒举行宴会,僧徒四人并不觉得饥饿。当一个人觉悟成佛时,他不再需要经卷和食物。
至于经文的有字/无字,回到第九十九回《九九数完魔灭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经文散失一地的这一片段。首先,读者看到的是经卷被一阵风吹散,紧接着这些有字经卷被浸泡在水中,经受着风力、电闪、雷鸣和云雾等自然力参与的一系列化学变化:“真个是:一体纯阳喜向阳,阴魔不敢逞强梁。须知水胜真经伏,不怕风雷闪雾光。”④(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1页,第722页,第684页,第729页,第729页。中国宇宙论中的五行——纸中之木,水中之水,光中之火和石中之金、土——共同作用以造成不受天摧地腐的永恒经文。有字经文在一种佛教式的“浸礼”中经受净水的“洗礼”和普照万物的阳光的温润。有了光的温润,“自此清平归正觉,从今安泰到仙乡。”⑤(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1页,第722页,第684页,第729页,第729页。
然而师徒四人想不到的是“晒经石上留踪迹”。“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经粘住了几卷,遂将经尾沾破了,所以至今本行经不全,晒经石上犹有字迹。”*(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9页,第729页,第729页,第729页。见此光景,“三藏懊悔道:‘是我们怠慢了,不曾看顾得!’”②(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9页,第729页,第729页,第729页。悟空深得其味:“行者笑道:‘不在此!不在此!盖天地不全,这经原是全全的,今沾破了,乃是应不全之奥妙也,岂人力所能与耶!’”③(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9页,第729页,第729页,第729页。在其他场合,悟空也同样开导唐僧:文本的残缺仅仅是经文的物质材料的损失,这在精神上去有着“不全之奥妙”。这不是因为“语言逐渐成了概念的符号,日益趋向空壳化”*周裕锴,《痛感的审美:韩愈诗歌的身体书写》,《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60页。,而是因为语言本身就是“空”的,相应地,承载语言的经卷也呈现出不全之貌。在此之前,玄奘没有意识到空的经文的完满之处,而此时悟空为他解说了不全经文的妙蕴深义。
除了经卷解释了不完满义之外,这一片段对作为风景的残缺经文进行了生动描写,“晒经石上留踪迹,千古无魔到此方。”⑤(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9页,第729页,第729页,第729页。这一描写绝非“神来之笔”,它受到古代石上刻经传统的启发*详见Robert E.Harrist,The Landscape of Words:Stone Inscriptions from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8.。可谓:丝竹易朽,铁石难损;石上刻经,可传百代。事实上,以这种方式保存的经卷是般若智的显象。虽然《西游记》小说中的经文是肉眼可见的,但刻在石头上的经文因其字体较小往往不易被全部辨认。“神圣文字”刻入地理风貌的纹理,满载经文的石崖碑刻给原初的自然景观添加了些许人工痕迹,石崖碑刻因此增添“依存美”的美质。“神圣景观”与“神圣写作”之间密切相关:“山是钢刷;海洋是墨。天和地是盛载经卷的墨盒;一笔一划映照宇宙万川。”*Fabio Rambelli,Buddhist Materiality:A Cultural History of Objects in Japanese Buddhism,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18.虽然,悟空认为,残缺的经卷映现了“不全之奥妙”,此非人力所能为,但晒经石上的经文痕迹表明了保留经文的秘密——经卷的力量不仅能够穿透脆弱的纸张,也能刻入坚硬的岩石由此感动山石,度化人心。
二、文本的“空性”
百回本《西游记》中,“空”随处可见,《心经》也被多次称引,以至于美国学者夏志清在论到《西游记》时认为,“(吴承恩)力图要把整部作品变成对《多心经》哲学上的评论”*[美]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胡益民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第十四回《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回首诗”即说:“非色非空非不空,不来不向不回向。”*(明)吴承恩著,陈先行等校点,《西游记:李卓吾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第251页,第417页,第861页,第953页。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一回中,乌巢禅师说西天大雷音寺很远,但言:“路途虽远,终须有到之日,却只是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乌巢禅师口诵《多心经》,传给三藏,“此时唐朝法师本有根源,耳闻一遍《多心经》,即能记忆,至今传世。此乃修真之总经,作佛之会门也。”⑩(明)吴承恩著,陈先行等校点,《西游记:李卓吾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第251页,第417页,第861页,第953页。《心经》在根本上具有助人“内省”的作用,也可以外用“辟邪”。第三十二回《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一回中,玄奘问“逐逐烟波重叠叠,几时能够此身闲”时,“行者闻说,笑呵呵道:‘师要身闲,有何难事?若功成之后,万缘都罢,诸法皆空。那时节自然而然,却不是身闲也?’”(明)吴承恩著,陈先行等校点,《西游记:李卓吾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第251页,第417页,第861页,第953页。第六十四回《荆棘岭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谈诗》中,三藏为木仙庵“四老”讲禅法道:“菩提者,不死不生,无余无欠,空色包罗,圣凡俱遣。”(明)吴承恩著,陈先行等校点,《西游记:李卓吾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第251页,第417页,第861页,第953页。第七十一回《行者假名降怪犼 观音现象伏妖王》“回首诗”云:“色即空兮自古,空言是色如然。”(明)吴承恩著,陈先行等校点,《西游记:李卓吾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第251页,第417页,第861页,第953页。
《西游记》第五十八回《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寂灭》中,如来佛祖开示了“色”“空”的“了义”。真假行者“斗法”,飞云奔雾,径往西天灵鹫仙山雷音寺。此时,四大菩萨、八大金刚等正听如来说法,“那如来正讲到这:不有中有,不无中无。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为有,非无为无。非色为色,非空为空。空即是空,色即是色。色无定色,色即是空。空无定空,空即是色。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为照了,始达妙音。”*(明)吴承恩著,陈先行等校点,《西游记:李卓吾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81页,第1320页,第1057-1058页。如来佛祖“色”与“空”的说法解决了区分真假悟空引起的分辨“身份-在-二元性”和“二元性-在-身份”二者的困境。
“空”作为一个概念的重要性在孙悟空的名字中也得到了强调,即悟“空”。这正如《西游记》的一些早期评论家所认为的,孙悟空名字中的“悟空”二字和用不同的方式理解“空”有着直接的关系。另外,猴王的早期名号“齐天大圣”也包含着许多讽刺意味。“齐天大圣”的名号为天界管理者所授,其含义是“空的名号”“没有职权”,天庭授予猴王此封号的目的是平息他那超乎想象的野心。猴王的最终任务就是要觉知一切存在的“空性”。他师父的名字“三藏”的字面意思就是“三个篮子”——“三藏”指的是南传佛教的三类经典。小说的末尾,三藏被授予“三藏经”,以“超脱苦恼,解释灾愆”。“三藏:有法一藏,谈天;有论一藏,说地;有经一藏,度鬼。”②(明)吴承恩著,陈先行等校点,《西游记:李卓吾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81页,第1320页,第1057-1058页。悟空和三藏的名字合起来就是“空”与“经文”的“异文合成本”。这正如如来佛祖所说:“名和实一致并相互阐发时,正是妙音始达时。”
在小说《西游记》的最后章节中,三藏和猴子名字的意义通过他们取走的经卷得以阐明。太宗皇帝为玄奘举行的官方致谢典礼记录了这样的事实:玄奘早年就意识到三种“空”的形式的价值——空,无相,无原。该引用出现在这样一个后期的文本中意在强调“空”这一教义不仅启动也终结了三藏的取经旅程。小说第七十八回《比丘怜子遣阴神 金殿识魔谈道德》,三藏为“国丈”道士讲述“空”的义理一节值得注意。“三藏闻言,急合掌应道:‘为僧者,万缘都罢;了性者,诸法皆空。大智闲闲,淡泊在不生之内;真机默默,逍遥于寂灭之中。三界空而百端治,六根净而千种穷。若乃坚诚知觉,须当识心:心净则孤明独照,心存则万境皆清。真容无欠亦无余,生前可见;幻相有形终有坏,分外何求?行功打坐,乃为入定之原;布惠施恩,诚是修行之本。大巧若拙,还知事事无为;善计非筹,必须头头放下。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若云采阴补阳,诚为谬语,服饵长寿,实乃虚词。只要尘尘缘总弃,物物色皆空。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享寿永无穷。’”③(明)吴承恩著,陈先行等校点,《西游记:李卓吾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81页,第1320页,第1057-1058页。玄奘的说法紧密契合中观学派的思想。印顺法师在《中观今论》中说:“依缘起相依相待、相凌相夺的观法,随顺胜义的中道而倾向于胜义——‘一切法趣空’的观慧。观慧虽也观察不到离言的中道胜义,而依此缘起观,却能深入本性空寂,成为深入中道的不二法门。中道离一切相,但即为成立缘起的特性,中道即缘起的中道;缘起的因果生灭,当下显示这空寂的真理。……从缘起法以观察中道,也即是如此。文字(即总摄一切名相分别)性空即解脱相,趣入离言是不能离弃名言的。所以说:‘言不是义,而因言显第一义。’”*释印顺著:《中观今论》,北京: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8-39页。中观学派标举“中道”,此说否定肉眼所见的凡俗世界和证悟终极真实的虚无(空)。在中观学说乃至于所有的佛教教义中,“空”的佛理超越一切感官、因果和机缘。当玄奘看到经卷是空本时,他的反应是:“把这无字的空本带回去有何益处!我怎么面对唐朝皇帝?”在这一情节中,玄奘陷入窘境中,他对于无字经文的失望表明,他依然心系世俗,他的首要任务是为大唐皇帝负责,也因此不能悟得终极真理。文字是经验现象的记录和象征,经验本身是空的,真经也只能是空的。文字引发了五蕴之苦,因之必须超越。若要了悟成佛,修行者必须将色(物质)搁置一边,包括文本,只需信奉佛陀开示的“终极智慧”。无字经文恰恰就是取经者十四年奔波的结晶。因此,佛祖说:“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2页。
三、语言、文字的实/空的悖论
佛祖轻视有字经文意在消除取经者对于文本的偶像式的崇拜。如若经文真的没有意义,为什么佛祖还会授予他们呢?这正如Jay L.Garfield所分析的:“根据很多中观学者的说法,在修行的开始阶段,语言是不能丢弃的;尽管有着自身的局限性,语言并不是无用的或者十足的误导人的认知工具。”*Jay L.Garfield,“Sounds of Silence,” in Empty Words:Buddhist Philosophy and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71.毕竟,佛祖自己一生中也有大量的文字存世。语言足以传递世俗真理(世俗谛),它是庸常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系统。东土众生“愚昧无知”,他们需要所能得到的一切帮助,以明佛法真义。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功用是证入佛理的“方便”门径,所以佛祖慈悲为怀,恩赐取经者有文字的经卷。
这个有字经文与无字经文之间的有趣矛盾实际上是“空”之本性的深刻话语。吊诡的是,只有通过讨论“空”,人们才能够把“空”作为“沉默”来认识。终极真理非语言能够表诠,同时它不否定一般的、可以解说的真理。毋宁说,终极真理完善可以解说的真理。空海这位活跃于八世纪的日本僧人曾于长安青龙寺学习密宗,他认为:“佛教的道理不是语言能够言说的,但是离开语言就不能揭示佛理。”*Fabio Rambelli,Buddhist Materiality:A Cultural History of Objects in Japanese Buddhism,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24.语言是不足以传达真理的,因为语言的基本指谓功能词“是”和“否”往往落于二边。所指不明的以符号方式运作的语言陷入了“是”与“非是”的囚牢,因此不能捕捉到终极真理的灵光。
理解“空”的最好方式就是保持沉默。这一点在《维摩诘经》*《维摩诘经》是一部影响巨大的大乘佛教经典,该经广泛流传于中亚和东亚,玄奘法师于公元650年左右将其译为汉文。的第九章有详细的解释。菩萨在《维摩诘经》中聚在一起详细讨论“不落二边”的原则,以消除诸如“生与灭”“罪与福”“有为与无为”“暗与明”等分别相,以通往终极真理的“坦途”:“时,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赖永海,高永旺译注,《维摩诘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4页。在这里,什么音节、声音和想法都是没有意义的。维摩诘的“沉默”不是任何一般形式的沉默不语——它不是不理解和无知交织在一起的沉默无言。恰恰相反,他的沉默是彻悟之后的沉默,它传达出音节、声音和想法所无法言说的“不二”真义。
“空”是“不存者”,语言把“空”带入“存在”,使它具体化。该文本中的“空”义发微是维摩诘通过沉默的暗示,把一些不存在者显示其身,借助语言使“非存在”变成“现实”。换言之,语言的缺位——沉默——作为“口头铭文”留下遗迹。但是从罗格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来看,文字只是语言(此处指有声的一类)的符码和派生物。书写沉默就是一个双重的悖论,因为经文本身就是无声的不由口头产生的沉默。在本例中,维摩诘的沉默恰好就是言说“色”中之“空”与“空”中之“色”的不二真理。小说第九十三回中唐僧师徒的对话生动描述了语言的悖论:“三藏说:‘猴头!怎又说我不曾解得!你解得么?’行者道:‘我解得,我解得。’自此,三藏、行者再不作声。……三藏道:‘悟能悟净,休要乱说,悟空解得是无言语文字,乃是真解。’”*(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84页。悟空与三藏的沉默和维摩诘的沉默相呼应,悟空的“无言语文字”的说法预示着未来佛祖赠予的无字真经。无字经文指向用否定方法所得的空寂涅槃之境。
四、经文的神圣性
随着佛教的历史从口耳相传到文字传播,佛教徒制定出精致的仪式来保护以物质形态呈现的佛经。如果考虑到佛教徒修行追求的“空”的境界,有观点可能会认为佛经走向物质化是“逆流而动”。事实上,佛子为保存在他们心目中至为神圣的佛经想出了各种办法,尤其是传经及诵经活动的辅助用品——神圣的船只、圣髑盒和令牌——这些是祈愿祭祀活动的必需品。这些极为考究的佛事用具强调了佛教思想的基本悖论——一方面,它坚持一切无常,看空一切的观点;另一方面,它又强调祈福等仪式的豪华阵容,金银珠宝、水晶琉璃和珍贵贝壳等“一样都不能少”。
在《西游记》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中,我们看到这种豪华场面的极力展示,大雷音寺“图书馆”被描写成一个四处散发着珠光宝气的宫殿:“那厢有霞光瑞气,笼罩千重;彩雾祥云,遮漫万道。经柜上,宝箧外,都贴上了红签,楷书着经卷名目。”*(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19页,第723页,第735页。如来佛祖教导唐僧四人供奉苦修得来的经文的仪式,如来道:“此经功德,不可称量,虽为我门之龟鉴,实乃三教之源流。若到你那南瞻部洲,示与一切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宝之重之。”②(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19页,第723页,第735页。
经文崇拜是佛界中的普遍现象。这正如Jinah Kim所指出的,经文崇拜在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的南亚随着坦陀罗深奥教义的出现而极度盛行*Jinah Kim,Receptacle of the Sacred:Illustrated Manuscripts and the Buddhist Book Cult in South As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书写经文的经书是一种神圣的存在,其中遍藏“圣经”和积淀着代代读经朝圣者的“心路历程”。此外,John Kieschnick考察了佛教经卷在中国物质文化中被视为“圣物”而崇拜的历史*John Kieschnick,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89-164.。佛教经书被崇拜是因为它们是佛陀真实踪迹的记载(物质承担者),因此,它们不仅是凡间众生学习的对象,同时也是举行佛教仪式的必备圣物。在中国古典思想中,书籍崇拜(包括经卷)是同样源远流长与根深蒂固的。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墨子曾经写到:“我们知识的来源就是刻在竹简和写在丝织品上的文字,镌于金属器具和石头碑刻上的铭文和碑文,所有这些都要流传于后世,有益于来者。”*The Mozi:A Complete Translation,trans.Ian Johnst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667.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读经和抄经成为中国佛教的“头等大事”。
佛经的崇拜话语在中国较早出现在《妙法莲华经》里。文本是成圣的阶梯:如若一人记忆,背诵,抄写和出版佛经,他将获得福报。带着神圣的光环,物质性的佛经和文物、图标和护身符获得众生同等程度的崇拜,是礼拜仪式的工具和佛陀的化身。从某种意义上讲,佛经甚至比佛陀的文物更重要,文物只是物质性的存在,而佛经是佛陀思想的结晶,是明心见性的必由之路。以物质形态呈现的文物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一个华丽的“圣髑盒”的精神象征意义。在《大般若经》中,佛祖向一位至为虔诚的弟子说道:“是故,阿难,有志觉醒者,有志于成为无所不知的伟大圣人者,须习《大般若经》。这部经须保存、背诵、掌握、宣称、散发,……阿难,这就是我们的教导。”阿难在佛祖的众多弟子中素以“佛法的守护者”远近闻名,因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西游记》这部小说中,阿难的形象是级别很低的普通保卫者“啊难”,他吝啬又贪婪的个性遭到其他菩萨尊者们的嘲笑。
正如普通人造物也有机会被人们赋予神奇的力量一样(例如普通瓶子可以具有无边法力),佛经不仅仅是阐释佛陀话语的工具,同时也是妙乐世界的精彩一隅。通过对佛经文本物质性的强调,我们可以理解小说最后一回精心展示佛经的合理性所在——这超过了Plaks和其他批评家的预期:佛经是沟通世俗和精神王国,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的桥梁。
小说的最后一页把取经四众神圣化了:“长老捧几卷登台,方欲讽诵,忽闻得香风缭绕,半空中有八大金刚现身高叫道:‘诵经的,放下经卷,跟我回西去也。’这底下行者三人,连白马平地而起,长老亦将经卷丢下,也从台上起于九霄,相随腾空而去,慌得那太宗与多官望空下拜。”⑥(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19页,第723页,第735页。“讽诵”之“讽”和“香风”之“风”的语音双关使这一阵风意味深长。八大金刚声称,僧徒四人应“而今迈步从头越”,四众被风卷离“水陆大会”是他们走完漫漫西天取经路的标志,也因此不再需要祈祷的工具——经卷了。僧徒四人从口中呼出的“气”消融在把它们带入天国的那一阵风里——同样是这一阵风,曾卷走他们的无字经文(第九十八回),也曾从西天净土把它们平安送回东土大唐(第九十九回)。玄奘在凡间的最后留影正应了《瑜伽经》的那句话:“重而又重的唱诵感动神圣心灵”。这里的奇迹是,玄奘还没来得及重复唱诵咒语就已经感动了神圣心灵,他和他的徒弟们也因此得以度脱。
按照读经传统,祷文(即咒语)应该以唱诵、宣讲、默念、耳语等方式进行供养。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梵语和巴利语佛教咒语通常被音译为同音汉字,这种译文基本上没有语义学上的意义。但是,即便音译也能使读经者从“幻想式”的解读中解放出来,翻译上的这种处理反而更增添了咒语的吸引力。在佛教仪式中,这种被抽空了语义学意义的近乎“原生态”的咒语更为有效,因为它打开了一扇仅仅借助于听觉就能顺利沟通神圣净界的窗口。“至于咒的运用,小说中亦有相关的描述,如玄奘以‘紧箍咒’约束孙悟空,观音用‘金箍儿咒’收伏红孩儿及用真言降服黑熊怪等,这都说明咒的神秘力量不可思议。”*李小荣:《〈西游记〉〈心经〉关系之略论》,《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以此看来,念咒本身作为神圣的“显象”,是一种先于和超越语言的“讲说”。咒语(佛经)的这种“声波作品”超越了凡间语音,它的袅袅余音成为了纯粹声音,以至于它能够和宇宙的振动合拍同调。
正如Andre Padoux所认为的,“咒语是声音,是音位,至少可以认为它本质上不是能够写出的字词。”*Andre Padoux,“Mantras—What Are They?” in Understanding Mantras,ed.Harvey P.Alper,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9,p.297.但是,这不妨碍出现在小说结尾部分的咒语为书写出的文字。小说中“诵经”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的情节出现在最后三回的佛祖点清经卷名称和卷数等处:佛祖颁给玄奘四人的三十五部经被清点了两次(第九十八回);观音菩萨查检师徒四人一路上经历的灾愆患难(第九十九回);一连列出六十三名的佛、菩萨尊号(第一百回)。单调的列表可能使阅读过程乏味难耐,但正是由于这种机械列表才避免了歪曲理解的出现,换来的正是听者内心的宁静平和。“西方的列表、目录——目的是编写百科全书,编制独立的目录、清单等归档工作的目的是引导人们了知宇宙本质的浩渺无限性。”*Robert E.Buswell Jr.And Donald S.Lopez,Jr.,The Princeton Dictionary of Buddhi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1065-1102.与此相类似,数不尽的经卷和目录也是佛教经典的重要特征之一。列举佛、菩萨名号与佛经名录卷次不仅使《西游记》这部小说的文化身份完成从取经故事的讲述者到咒语化身的转变,同时也使这部小说的哲学意蕴从形而下的具体的物质性文本上升为一种声音的形而上学。小说文本的最后几个字是“摩诃般若波罗密”,其深意在于重新发明《心经》结尾处的“劝导语”——“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因此,小说最后的词句可以说不是它自己独创的,它是《心经》结尾处的劝导语的重复。
五、世界作为文本
《西游记》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无文字”的,作为“景观”和作为“声音”的文本。问题在于,这一世界怎样告诉我们它是作为文本而存在的?中国十一世纪的学者尤侗(1618-1704)注意到,《西游记》可以被看做《华严经》的外篇(尤侗《西游真诠序》)*见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58-559页。。《华严经》是经中国僧人及学者修订的关于西方庄严净土的经典,它是一部影响巨大的大乘经典,讲述关于宇宙的无限和相互包含的世界之间的玄理。基于对《华严经》这种微观-宏观宇宙模式的分析,我们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部经文,反之一部经文也囊括整个宇宙。基督教的寓言可以类比《希伯来圣经》的末世论,“诸天必团在一起滚动”。在《华严经》中,整个宇宙被设想为一个巨大的文本系统,每一微粒和尘埃无不包含着整个世界:好像有一部经卷在滚动,它大如这到处塞满经文的三千大千世界;同时,这部大千世界无一遗漏地承载着无情草木和有情众生,“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这一大千世界包括在每一微尘中,每一微尘同样地支撑着这一卷轴的转动,是故唐僧教导孙行者“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赶走蟊贼勿伤命”。
这就是“世界作为文本”和“文本作为世界”的转化机制。这一设想描述了大千世界中万物相互混入、融化的内在机理:佛陀的启示内在于有情众生;一微尘孕育三千大千世界(整个宇宙)。该种宇宙观不同于西方的罗格斯中心主义,在这里思维(理论)与存在(现实)融合为一:文字的重要性不逊于讲说;确切地说,文字优越于或者至少与讲经说法一道传播着佛法。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不是三千大千世界的精致模仿,“世界之诗”也不是如柏拉图所声称的是理念的拙劣模仿,“和真实的事物(理念)隔了三层”*邓晓芒著:《西方美学史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文本也不是指向一种“超验”的差异性的“幕后显示器”;文本本身就统摄着佛祖智慧的无形王国。因此,佛经是以较小的文本载录三千大千世界的“韵文”,可谓是体小而量大,一粒沙映照七彩世界:一笔一划蕴无穷妙韵;一勾一点证至真佛理;一唱一念显至诚真心。
在《西游记》小说中,取经者得到的只是全部佛经的一部分,“这已经足够好,没有比这更好的了”*Cheshire Calhoun,“On Being Content with Perfectioon,” Ethics127.2(2017),p.333.,这部分佛经的目录也被清点了两次。第一次清点后,取经者放到包裹里的是三十五部经计一万五千一百零五卷。之后,经过与吝啬的“守门人”(阿傩、伽叶)的一段遭遇,佛祖问阿傩、伽叶传了多少经卷,要求一一报数。所授经卷再次被清点,然而数目却与第一次相比大为减少:“在藏总经,共三十五部,各部中检出五千零四十八卷,与东土圣僧传流在唐。”*(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3页,第724页。(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
这时,取经者在路上渡过的天数和得到的经卷数目还不能划上一个等号。“旁又闪上观世音菩萨合掌启佛祖道:‘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之人,今已成功,共计得一十四年,乃五千零四十日,还少八日,不合藏数。望我世尊,早赐圣僧回东转西,须在八日之内,庶完藏数,准弟子缴还金旨。’”④(明)吴承恩著,(明)李卓吾评,《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3页,第724页。(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这样,加上往返东西所需的八日,取经者取得的经文卷数才得与取经途中耗费的时日相抵。
以此看来,僧徒四人的取经征程的“回报”只是佛祖原定答应传授经文的一部分。这种“不完美”正好暗合了学者在学习佛经时的感悟,学者所学到的只是难晓其奥的经文深意的一个概要。而但就这“摘要”来看,它不折不扣的就是宇宙大全缩略而成的“造化之文”。
那么,在何种方式上,作为小说文本的《西游记》符合“宇宙作为文本”的解释范式呢?这一文本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原则)又在何种方式上契合佛教教义呢?根据《华严经》的说法,大千世界中的一粒微尘就在其自身内包含着“宇宙文本”的全部奥秘,长达一百回的《西游记》文本不也同样如此吗?至少《西游记》早期的批评者刘一明(1734-1820)是持这种观点的。与其说“《西游记》‘取经’故事本身所取之‘经’就是佛经”*赵凤翔:《〈西游记〉宇宙体系的解构与探究》,《明清小说研究》,2017年第1期。,倒不如说《西游记》文本的“神圣”地位应不逊色于佛经:“唐僧师徒四人西行求取真经故事本身的深层意义就是他们取得了《西游记》这部真经,即是说只有《西游记》才能称得上四人念念不忘的‘真经’(除《西游记》外,别无真经可取)。正是基于此,《西游记》正是通过佛陀所说经的广泛流布而深入人心的。进一步讲,如果读者能真的读懂了《西游记》,那么他就会发现三藏经文就在它的文本之中。”*参见Liu I-ming,“How to Read The Original Intent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trans.Anthony C.Yu,in 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ed.David L.Rolst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303.
刘一明把取经者明心见性的过程与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心路历程等同了起来。整部小说就是全部佛经的一个提喻,包括佛经的目录、引用和其他信息。刘一明把《西游记》这部小说——它的文本和文本中的精神启示——视为佛经本身,这与神谕的精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无论这本书在何处,天上的神就会在暗中保护着它;同时对于该书“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因为“在心理层面,经典内容成为无需证明的神圣对象”*杨剑霄:《论佛教经典信仰的形成及其功能》,《江海学刊》,2017年第1期。,并且佛经作为经典“不仅是思想文本生成的起点,亦是思想内容评判的准绳”②杨剑霄:《论佛教经典信仰的形成及其功能》,《江海学刊》,2017年第1期。。
玄奘、悟空和悟能等不再需要借助佛经明心见性,因为在他们取经征途的最后阶段他们本身就是佛经的精神象征或者说是佛经的“可见肉身”。经卷不是为他们服务的而是利益东土大唐众生的。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师徒四人成了文本,更确切地说,他们已经成为佛教经文本身。那么读者呢?读者在走完了一百回的小说阅读过程后也会有同样的感受(美的体验、经验)。如果用唐僧师徒四人跋涉千山万水来比喻读者在阅读《西游记》中的点滴思考,那么读者的《西游记》诠释学建构就是见到如来、证得佛法的过程。不仅如此,《西游记》“每一次磨难都可以被讲述成相对独立的小故事,而它们的结构大致相似”*朱刚:《百回本〈西游记〉的文本层次》,《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的叙述特点,使读者更容易进入这一文本世界,与唐僧师徒“心腹相托”“患难与共”。这一小说类型也可被称为“明心见性”的神魔小说。
西天取经接近尾声,那阵吹散经文的“香风”也把取经者的身体吹离了文本世界。在印刷而成的小说文本中,映入读者眼帘的是佛、菩萨的引人入胜的冗长名字,这拓展了读者的辨认能力(审美能力),抬高了读者的“审美临界点”。从整体上看,这部小说作为一种宗教文学成功地理清了现实(文本)和它的象征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世界确实把自己浓缩在一部小说中吗?书本的真正目的是使人们脱离书本吗?不管怎么说,考虑到当今东方和西方的人们仍然“愚顽不化”,我们需要更多数目如同浩繁经卷之巨的《西游记》小说或类《西游记》小说来度化陷入苦难的芸芸众生。
六、余论
四众西行拜佛取经,肩负着大唐国朝廷与黎民百姓的希望和僧众人等的寄托,如来佛祖的“无字空本”何以打发跋涉千里、历时十四年之久到达西天大雷音寺的唐僧师徒?“无字之经乃真经”,佛祖开玩笑似地说:“只因你东土民众愚昧,不识无字真经的妙处,这有字真经也是好的。”当我们把经卷的白纸视为“色”,把字迹全无看做“空”,那么“用无字佛经换取有字真经”的情节就很好地说明了《心经》的悖论,因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种解释让我们了解了佛祖为什么说有字经文和无字经文是可以互换的。《心经》全文出现在《西游记》第十九回“浮屠山玄奘受心经”一节中,此后唐僧逢灾遇难就会心中念叨它,可见《心经》在取经途中的重要性。清人张书绅用儒家经典《大学》来阐释解读《西游记》,认为《西游记》为为学之书,“学为西游之总纲”,但通观百回“西游故事”可知《心经》是取经朝圣者的“精神支撑”。《西游记》最后一章应该被解释为《心经》的寓言与扩展。经文之“空”的“形而上学”和散落经文的“物质性”恰好对应于《心经》中“空”与“色”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最终消解于佛学悖论的通过语言手段表达的非二元性,这一点被佛祖的说法、悟空的言论和叙事者的叙述所证实。最终,玄奘、悟空和悟能等不再需要借助佛经明心见性,因为在他们取经征途的最后阶段他们本身就是佛经的精神象征或者说是佛经的“可见肉身”,同时,如来佛祖在造“三藏真经”之时,已经给定了这样的预设——取经者、经文及其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文本依赖性的关系,这也可能是世界作为文本以及历代学者乐于解此文本的奥秘所在,同时这一文本也为有志于基于“中国言说方式”的立场,以实证的、动态的,而不是印象的、静止的方式解读《西游记》的研究者提供一展身手与各抒己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