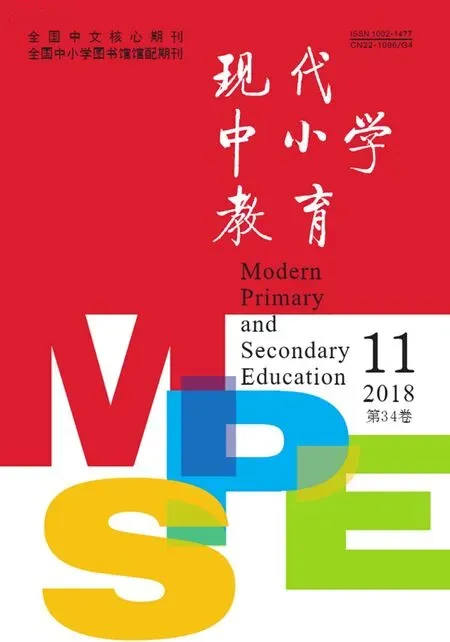澳大利亚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资助制度改革
赵 顺 彩
(喀什大学南疆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新疆 喀什 844000)
一、改革背景
1.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的发展
澳大利亚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Early Child Education and Care)是针对0~5岁幼儿提供的一系列教育和保育服务[1]。2009年7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颁布《儿童早期教育和保育国家质量框架》(National Quality Framework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简称《国家质量框架》),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首次针对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的全国性质量标准[2]。为切实实施《国家质量框架》并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早期教育,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COAG)于2009年10月颁布了《归属、存在和形成:澳大利亚早期学习框架》(Belong,Being and Becoming:The Early Years Learning Framework for Australian,简称《早期学习框架》)。主要内容包括:支持和提高0~5岁婴幼儿学习的关键性原则、实践方法以及成果表现;儿童保育机构向学校过渡事宜;强调以游戏为基础的学习及交流的重要性[1]。以上两个政策文本的颁布和实施,推动着澳大利亚早期教育与保育的不断发展。
2.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资助的探索
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开始为幼儿保育提供公共财政支持。此后的几十年间,幼儿保教机构从由政府直接设立,逐渐转变成由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设立;政府机构提供财政支持也随之增加对非政府机构运作经费补贴,以此促进儿童保育的发展[3]。20世纪9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政府开始以向家长提供资金的方式,支持幼儿保育事业的发展。
2007年,澳大利亚拉德(Rudd)工党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将提高儿童早期教育和保育质量作为改革的重点之一,并为之提供资助[4]。2009年,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签署了首个全国性早期教育宏观指导战略《国家早期教育发展战略:投资在早期》(National Early Educ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Investing in Early),宣布“联邦和州以及地方政府联合,确保到2020年所有儿童都享有最好的早期教育,以便为自身和国家创造更好的未来”[5]。2010年5月,澳大利亚教育、就业、劳资关系部和社会团结部联合(Australia Ministry of Education,Employment and Labor Relations,Social Solidarity)颁布“2010—2011技能和基础设施预算(2010—2011 Skills and Infrastructure Budgets)”方案,提出要加大对教育投入,尤其是儿童早期的教育投入,以抓住未来可能发展的机遇。
近年来,为进一步确保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的质量,及资金的切实和正确使用,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改革和完善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的经费保障制度[6]。
二、改革的内容
2014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的颁布,规范早期教育与保育资助经费的使用,强调诚信原则,强化管理制度,并切实落实,从而实现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早期教育与保育服务。
1.规范诚信
随着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费用的不断上涨,许多家庭难以支付高额的费用,为此,2014年12月4日,澳大利亚教育与培训部(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出台了《儿童保育支付合规方案战略》(Child Care Payments Compliance Programme Strategy,以下简称《方案战略》),明确了联邦政府对儿童保育机构的资助数额,规定了保育机构的责任,确保其诚信,从而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保育服务[7]。
《方案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1)明确资助数额。在未来四年,澳大利亚政府将投资400亿美元左右支持儿童保育,其中《家庭儿童保育工作条例》(Job for Families Child Care Package)实施增加30亿美元,并在两年之内再增加8.43亿美元,以确保所有澳大利亚儿童在接受正规教育前有机会获得一年的学前教育计划。(2)对保育机构的责任提出要求。有的保育机构虽然知道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却没有遵守;有的保育人员意识到法律对自身技能和知识的要求,但仍不达标。针对以上情况,《方案战略》要求保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要具备必要的技能,并不断更新保育知识;若联邦此后对保育工作人员的技能和知识有新的要求时,保育机构应及时回应。(3)对不遵守法律的处罚。如果保育机构故意不遵守法律要求,对政府存在欺骗行为,以及故意犯错,政府将取消保育机构的资助,终止相关的资金协议;如果保育机构进行自我评估,主动说明自身不合规行为,交待资助钱款不合理使用的地方,政府将会考虑恢复资金的提供。
《方案战略》的实施,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使超过120万个家庭能负担得起更高质量的保育;同时,对保育机构提出要求有助于提高保育工作者的技能和知识;对于不遵守法律的保育机构给予明确的处罚,可以确保公共资金的合理和负责的使用。以上均有助于确保保育机构的诚信,为高质量的保育服务提供保障。
2.加强管理
因《方案战略》只明确了保育资助费用的资助总额,而没有规定详细的预算项目,为保证资金合理的分配和有效使用,联邦政府于2016年2月8日修改《方案战略》,生成《儿童保育和早期学习合规框架》(Child Care and Early Learning Compliance Framework,以下简称《框架》)。
主要内容包括:(1)处罚。2016年引进《家庭儿童保育工作条列》,新的条列将加强政府力量对于不合法行为的处罚,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还加强对需要重新评估的儿童保育机构的管理,重新审核获准资格,这个规定会在2016年7月1日起生效。(2)监控。《框架》将支持新的ICT系统,该系统可以提供改进报告和监测功能。尽量减少政府的监管负担,新的ICT检测系统发挥应有的功能,及时监督不合法行为。为确保资金的正确使用,重要的是要有适当的问责制,且提供保育费用资助到位的机制,切实做到提供资金资助保育。(3)数据。《框架》中对保育机构进行随机抽样,以便确认数据中提交的家庭是否真正受到保育资助费用的援助,这将有助于确保依法管理联邦资助的家庭。且加强执法,惩罚和制裁不守法的保育机构,使得保育机构能在法律规定之下为儿童和家庭服务[8]。
《框架》加强执法、惩罚和处罚,确保资金的使用,有助于促使保育机构切实做到保护政府声誉,避免发生损害政府声誉的行为;确保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保育;确保政府资助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的资金要公平地使用在儿童身上;也让家庭和社区为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担负起应有的责任。
3.切实落实
由于之前资金的使用没有真正地支付给需要资助的家庭和儿童,儿童没有受到高质量的保育服务,且造成资金流失。为此,联邦政府于2016年10月10日修改了《家庭援助法》,规定新的儿童保育支付标准。明确给出需要改变的具体支付内容,确保达到对家庭而言高质量的、灵活的、可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
新的《家庭援助法》对不再支付的项目和保育者的义务做了如下规定[9]:
(1)儿童保育资助费用在下列情况下不予支付。儿童保育服务不是在政府规定的范畴不予支付;在保育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费也不是主要的支付内容。家庭保育日(Family Day Care,FDC)在儿童自己家里,或者父母就是保育提供者,不予支付保育费用。在家里保育(In-Home Care,IHC),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就是儿童保育提供者,这类情况联邦政府不再支付儿童保育费用,这样可以确保父母将儿童送到有保育资格的机构中接受儿童保育服务。
(2)最低义务要求。出现情况时,保育机构应向联邦政府报告,寻求解决措施。对于保育关键人员的规定,包括:职员、家庭日托保育者、一日教育者或者在家保育者,这类人员都对儿童保育负有法律责任。当保育机构被人控告或者有严重到可以起诉罪行时,保育机构可能会面临破产,不能再提供服务,宣布停止运营。
(3)新的适宜性标准应用于相关人员,包括申请服务的批准、认可服务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人。
《家庭援助法》对于保育的支付条件做出明确的改变,使得资金切实落到儿童身上和家庭上,而不是主要用于支付交通费用。必须把儿童送到被认可的保育机构,接受专业的保育服务。明确儿童保育服务中的关键人员,使保育工作者知道自己是儿童保育的主要责任人,而不是推卸责任。对涉及的相关人员有明确规定,更加规范儿童保育服务机构的行为,相对于《方案战略》和《框架》而言,《家庭援助法》规定的儿童保育费用支付的范围更明确和具体,更能具有操作性。
三、思考与启示
1.思考
(1)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经费资助制度以现实发展需求为基础。从《方案战略》规范保育机构诚信,到《框架》对保育机构有效监管,再到《家庭援助法》改变保育支付标准,经历了政府提供资金的总额到具体规定支付依据的过程。这使得资金使用有明确的依据标准,确保资金真正用于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上,从而为儿童受到高质量的保育服务提供基础。政策文本出台都会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局限,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新问题,因此政策文本及时修改、生成新的政策文本,正是积极应对现实发展的需求,澳大利亚的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资助制度更好地推动了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的发展和改革。
(2)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经费资助制度指向提升儿童教育与保育服务质量。为达到对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机构的有效监管,提升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质量,澳大利亚儿童教育和保育质量监管局(Australian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Care Quality Authority,ACECQA)成为全国性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全国儿童教育和保育。对于不符合质量的保育机构,质量监管局负责整治,提出反馈意见。对于已经获批的保育机构,通过定期考察,不仅给予合格与不合格的评估结果,而且会依据评估结果采取资金增加、减少、暂停发放等措施,鼓励或督促保育机构不断地提高质量,从而为家庭和儿童提供高质量的保育服务。
(3)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经费资助制度有助于提升教育公平。2014年以来澳大利亚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经费资助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均指向为儿童和家庭提供高质量的、方便的、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服务,确保儿童在保育阶段就有平等接受保育的机会,为其他阶段的教育公平奠定了基础。此前,儿童保育政策使家庭承受了高额的儿童保育费用,致使家庭负担过重,儿童不能接受高质量的保育服务。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高质量、方便、可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服务大量增加,这有助于提升教育公平。
2.启示
澳大利亚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资助制度改革中,为规范保育机构的诚信,明确资助数额,对保育机构提出要求,对于不遵守法律的保育机构实施处罚;为加强管理,引进新的工作条例、新的监控系统,随机抽查保育机构;为切实实施资助,改变支付标准,规定最低义务要求,提出新的适用标准。所有的改革都致力于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资助经费的切实落实和有效使用,从而为儿童提供高质量的保育服务提供了基础,体现了联邦政府对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的重视。澳大利亚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资助制度改革对我国有以下启示:
(1)加大资金投入,为学前教育发展提供保障。自2001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增长明显。2001年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60.28亿元,2009年244.78亿元,2010年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728.01亿元,2011年突破1 000亿元,对学前教育的资金投入不断加大[10]。虽然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在增加,但是占教育经费的比重较低,特别是较其他阶段的教育而言。在保证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同时,如能提高占总教育经费的比重,将会为学前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另外,在经费分配过程中,城市和农村存在很大的差距,若在经费的分配中适当向农村倾斜,将会更好地促进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
(2)健全学前教育法规制定。目前我国针对学前教育的立法包括《幼儿园指导纲要》《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管理条列》,且这三个法规是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的部门规章,随着学前教育的发展,内容已不能完全满足当下要求。为保障学前教育的地位,应不断修改已有法规,且要出台更高层次的法律法规,保障学前教育的发展。另外,在健全法规方面应有监督机构、评价体系、经费使用及分配法规,从而使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学前教育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3)促进教育公平。《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改革和规划纲要(2010—2020)》(简称《纲要》)中提出我国要普及学前教育、并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随着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学前教育入园率在提高,2013年全国共有幼儿园19.86万所,在园幼儿(包括附设班)3 894.69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学率为65.7%[11]。但是,还有部分适龄儿童没有机会参加学前教育,因此,提高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增加幼儿园数量,是提升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