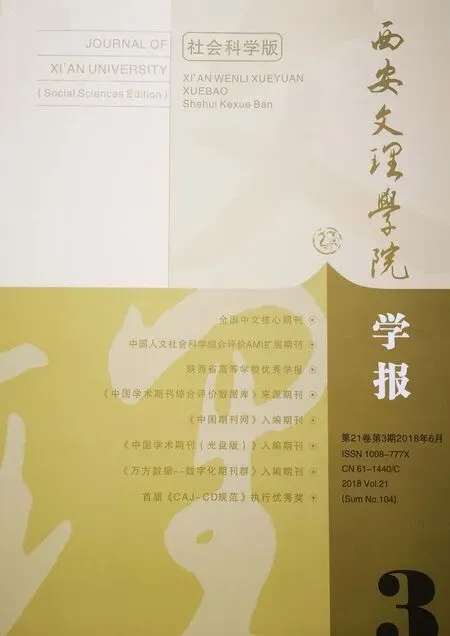唐五代批评视野中的韩柳并称
刘 城
(广西教育学院 文学院,南宁 530023)
当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及散文史著作都视韩愈和柳宗元二人为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领袖。但考察唐五代典籍及唐人的批评可知,这种观点实际上不太符合唐代的事实。中唐时期,韩、柳二人在当时并未同时被世人看作是文风改革的领袖。韩愈在中唐已逐渐确立“文宗”的地位,而柳宗元的影响远不及韩愈。韩柳文并称在晚唐才出现,而韩柳并称以及二人同被世人视为文坛领袖的观点则是在北宋以后才逐渐流行并定型。
一、韩愈“文宗”地位在中唐的确立
韩愈于唐代文名极盛,时人虽对其文颇有微词,但其道德、文章常称颂于世人之口,一代宗师的地位亦是不易撼动的。此不仅见于韩愈生前,亦被传于身后。
首先,唐五代人盛赞韩愈继承古之圣人的道统及卫道之功。这种激赏更见于韩愈的好友及门生的文章中。
张籍《上韩昌黎书》就认为,在孔子殁后,唯一能继孟子、扬雄而“言圣人之道者”,唯韩愈一人,且更是力劝其弃“绝博塞之好,弃无实之谈”,努力“嗣孟子、扬雄之作,辨杨墨、老释之说,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可见张籍对韩愈继承道统的期许。[1]卷684李翱《与陆傪书》亦谓“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斯者”[2]。赵德《昌黎文录序》明确韩愈所履之道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轲、扬雄”[1]卷622之道。晚唐的皮日休在《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亦有类似论述。
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并序)》就激赏其捍卫儒家之道的精神与勇力。其云:
先生七岁好学,言岀成文。及冠,恣为书以传圣人之道,人始未信。既发不掩,声震业光,众方惊爆,而萃排之。乘危将颠,不懈益张,卒大信于天下。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跋邪抵异,以扶孔氏,存皇之极。知与罪,非我计。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呜呼极矣,后人无以加之矣,姬氏已来,一人而已矣。[3]221
生动描绘了韩愈于中唐儒学衰微之际力挺圣人之道,其学终为天下信之艰难过程。张籍《祭退之》:
呜呼吏部公,其道诚巍昂。生为大贤姿,天使光我唐。德义动鬼神,鉴用不可详。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4]
“独得”二字既显出韩愈之寂寞,更衬托其力振儒学之功。这种不顾时俗、力倡儒学之精神,在晚唐也常为人所道,如皮日休《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谓韩愈,“吾唐以来,一人而已”[5]22,此“一人”即与张籍的“独得”遥相呼应,其又有《原化》云:
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杨、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岳其基,而溟其源,乱于杨、墨也甚矣。如是为士,则孰有孟子哉!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之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5]88
与皇甫湜之描述无异。
其次,韩愈不仅倡儒学,更是以儒学作为为文之根基,力辟当时浮华文风,宣扬儒家教义。李汉《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讳愈文集序》说韩愈:
比壮,经书通念,晓析酷排,释氏诸史百子,皆搜抉无隐,汗澜卓踔,渊泫澄深,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铿然而韶钧发。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洞视万古,悯恻当世,遂大振颓风,教人自为。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坚,其终,人亦翕然而随。乌乎!先生于文,摧陷郭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1]卷744
此论亦见于晚唐牛希济的《文章论》,其云:
古人之道,殆以中绝,赖韩吏部独正之于千载之下,使圣人之旨复新。[1]卷845
于世风日下、儒学衰颓之际,以一己之力独振儒家之学,成就了“儒者”韩愈。他勇于卫道之精神在当时倾倒了不少士子,林简言《上韩吏部书》即云:
去夫子千有余载,孟轲、扬雄死,今得圣人之旨,能传说圣人之道,阁下耳。今人睎阁下之门,孟轲、扬雄之门也。小子幸儒其业,与阁下同代而生,阁下无限其门,俾小子不得闻其道,为异代惜焉。[1]卷790
除明韩愈之道统外,还强烈地表达了欲追随韩愈“儒其业”。这种愿以弟子师之的情况更是出现于文学领域。郭绍虞先生指出:“韩氏之教不外传道、授业二者而已。实则传道是后世道学家的事,授业者正是当时古文家的事。所以韩愈于此二者虽是并重,而比较言之,则韩愈于道的方面所窥尚浅,于文的方面所得实深。故韩门弟子与其谓之学道,不如谓之学文。”[6]
韩愈文宗之地位,在唐代已成为共识。刘禹锡《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就曾透露当时韩愈与李翱为文坛盟主,其《祭韩吏部文》亦云:“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7]1537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自贞元末以至于兹,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7]1537王定保《唐摭言》卷六亦谓韩愈“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8]63。
这种名声,使得士子多以之为师,且形成一定的声势,对当时文坛颇有影响。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曾云:
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9]57
唐人赵璘撰《因话录》卷三亦云:
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10]82
韩愈自己也勇于为师,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进。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曾云:
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10]82
元稹《赠韩愈父仲卿尚书吏部侍郎》说韩愈“雄文奥学,秉笔者师之”[11]。唐人康骈的《剧谈录》、佚名的《灌畦暇语》及五代时王定保的《唐摭言》亦多有记载。这种勇于为师、奖掖后进的做法,不仅能使更多士子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且能扩大自己的学说及创作理念,陈寅恪先生曾说:“退之同辈胜流如元微之、白乐天,其著作传播之广,在当日尚过于退之。退之官又低于元,寿复短于白,而身殁之后,继续其文其学者不绝于世,元白之遗风虽或尚流传,不至断绝,若与退之相较,诚不可同年而语矣。退之所以得致此者,盖亦由其平生奖掖后进,开启来学,为其他诸古文运动家所不为,或偶为之而不甚专意者,故‘韩门’遂因此而建立,‘韩学’亦更缘此而流传也。”[12]故学者所称李翱传其道、皇甫湜续其文即谓此。
韩愈一代宗师的地位也使得世人极关注其文,评论亦颇多。王建《寄上韩愈侍郎》就说:
重登太学领儒流,学浪词锋压九州岛。不以雄名殊集作疏野贱,唯将直气折王侯。……序述异篇经总核集作别,鞭驱险句物先投。碑文合遣贞魂谢,史笔应令谄骨羞。[13]卷301
张籍《祭退之》云:
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13]卷383
白居易《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云:
大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14]
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云:
深于文章,每以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其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1]卷640
又于《祭韩吏部侍郎文》云:
呜呼!孔氏云远,杨朱恣行。孟轲距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辩之,孔道益明。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俪花斗叶,颠倒相上。及兄之为,思动鬼神。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开合怪骇,驱涛涌云。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学,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1]卷640
皇甫湜《谕业》云:
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飚激浪,汗流不滞,然而施于灌激,或爽于用。[3]103
又于《韩文公神道碑》云:
七岁属文,意语天出。长悦古学,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秀人伟生,多以之游,俗遂化服,炳炳烈烈,为唐之章。[3]211
另外,人们也关注韩愈的某些篇章,孙樵《与王霖秀才书》就论《进学解》曰:
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1]卷974
李商隐《韩碑》谓《平淮西碑》:
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15]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赞《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真良史才也”。
有正面揄扬,也存在不少质疑之声。如针对韩愈作文求“奇”求“怪”以及“以文为戏”的倾向,在朋友圈里就引起过不同的反响。裴度《寄李翱书》就表达过不满:
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1]卷538
而张籍更是连去《上韩昌黎书》《上韩昌黎第二书》二文,殷切希望韩愈“绝博塞之好,弃无实之谈,宏广以接天下士,嗣孟子、扬雄之作,辨杨、墨、老、释之说,使圣人之道”[1]卷684,难怪《唐摭言》卷五云:“韩文公著《毛颖传》,好博簺之戏。张水部以书劝之,凡二书”[8]55。
但柳宗元却对《毛颖传》之文颇多激赏,柳宗元在《与杨诲之书》中担心《毛颖传》“恐世人非之”,故“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16]848,且于《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极力为韩愈争辩:
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世之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16]569
并引经据典来论证古之圣人亦未弃俳,给予韩愈新文风有力的支持。韩愈的这种为文倾向,李肇《唐国史补》亦云:“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9]57可见,元和以后,韩愈的这种创作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响应。
二、唐人批评视野中的柳文
由上述可知,韩愈的文章、道德均为唐人所关注,虽间有异议,但多持肯定之声。反观柳宗元,由于其罪臣的身份及久居贬地,致使其长期远离人们的关注,故而他的影响力远不及韩愈。
现存唐人评柳宗元的资料极少,所论较多的是其文章与文风,好友刘禹锡论之最多亦最详。刘禹锡《天论上》论柳宗元《天说》:“文信美矣。”[7]139《与柳子厚书》论《筝郭师墓志》:“繁休伯之言薛访车子,不能曲尽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闻善音,如见其师。寻文寤事,神骛心得。倘佯伊郁,久而不能平。”[7]228《答柳子厚书》说柳宗元的文章“其词甚约,而味渊然以长,气为干,文为支。跨跞古今,鼓行乘空。附离不以凿枘,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7]266而韩愈赞柳宗元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7]487。皇甫湜《祭柳子厚文》云柳宗元:“肆意文章,秋涛瑞锦。”[3]231赵璘《因话录》卷三商部下云:“柳柳州宗元、李尚书翱、皇甫郎中湜、冯詹事定、祭酒杨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又元和以来,词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刘尚书禹锡及杨公。”[10]82至晚唐,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还对柳宗元之诗歌给予好评:“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探搜之致,亦深远矣。俾其穷而克寿,玩精极思,则固非琐琐者轻可拟议其优劣。”[17]
柳宗元的文章、才华虽然亦赏于时人,但远未如韩愈一般受到世人的多方面关注,更遑论以文宗之尊去扫荡浮靡文风。相反,当时更多的人是以一种怜惜的心态去评论柳宗元其人,哀其人、才、文不为世用。所论基调多悲悯,且均见于朋友之文,范围极小。
韩愈在《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虽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18],但在《祭柳子厚文》也说“子之文章,而不用世”[19]1395,于《柳州罗池庙碑》云柳宗元:“贤而有文章,尝位于朝,光显矣。已而摈不用”[19]2290。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19]2408—2409刘禹锡《祭柳员外》:“呜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从古所悲。”[7]1529刘禹锡《重祭柳员外》:“出人之才,竟无施为。……生有高名,没为众悲。异服同志,异音同欢。……呜呼哀哉!君有遗美,其事多梗。”[7]1531—1532刘禹锡《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孔氏四科,罕能相备。惟公特立秀出,几于全器。才之何丰,运之何否!……变时移,遭罹多故。……痛君未老,美志莫宣。邅回世路,奄忽下泉。”[7]1535—1536吴武陵《遗孟简书》:“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电射,天怒也,不能终朝。圣人在上,安有毕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刘二韩,皆已拔拭,或处大州剧职。独子厚与猿鸟为伍,诚恐雾露所婴,则柳氏无后矣。”[1]卷718
论其文,哀其人,是唐人论柳宗元之核心。亦有赞柳宗元之德的,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即“以柳易播”之事讥讽“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19]2408的世风,大赞柳宗元重友情之义举。此事亦为赵璘《因话录》所载。[10]72韩愈还在《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中盛赞柳宗元治理柳州之德。
与韩愈勇于为师不同,柳宗元则拒为人师。[20]宋人陈善有云:“一代文章,必有一代宗主,然非一代英豪,不足当此责也。韩退之抗颜为师,虽子厚尤有所忌,况他人乎?”[21]这也是柳宗元在当时未能成为文宗的一大原因。对于他人欲变其“不为师之志,而屈己为弟子”之请,他于《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回复云:
仆之所避者名也,所忧者其实也,实不可一日忘。……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若曰仆拒千百人,又非也。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嗔目闭口耶?[16]878-879
他避为人师,是要避其名,但对于士子关于“言道、讲古、穷文辞”的请求,柳宗元则是倾囊相授,故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赞曰:“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19]2408。不过,这种指导多于柳宗元贬谪永州及柳州之后,两地的文化及科举在唐代本来就不发达,如现在可考知的有确切籍贯记载的唐代进士人数为846人[22],湖南中进士者共25名[23],广西则有12人[24]。柳宗元对永州、柳州等地惠泽极厚,为后人所称道,但对于当时而言,影响还是极为有限的。
三、杜牧首标韩柳与《旧唐书》韩柳比较之发端
五代《旧唐书》载史臣语云:
贞元、太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而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前隳素业。故君子群而不党,戒惧慎独,正为此也。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赞曰:天地经纶,无出斯文。愈、翱挥翰,语切典坟。牺鸡断尾,害马败群。僻涂自噬,刘、柳诸君。[25]卷160
五代史臣于此不吝笔墨地称赏柳宗元、刘禹锡为文华美巧丽,文才出众,但却“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前隳素业”。批评柳、刘持道不严、附昵小人的同时,却肯定韩愈、李翱弘道之心及其出自仁义、语切典坟之文。这种论述实开自宋迄清对柳宗元人格进行批评的先河,进而影响到对其文章的客观评价。
在唐五代,人们多已视韩愈为文宗,且把其文章与明圣人之道、复儒学之尊联系起来,并肯定其力振颓风的功绩。但对于柳宗元则从未有如此评价,相反,在《旧唐书》这样官方的叙述中,柳宗元甚至成了对比韩愈的反面例证,虽有文才,但却“蹈道不谨”,自毁前程。不但与韩愈无并称的可能,更遑论与韩愈并提为共振颓风、推尊儒学的人物。
虽说如此,在韩柳逝世之后,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以二者并称。目前可知最早的韩柳并称见于杜牧的《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诗云:
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26]
杜牧于此首次把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四者并称,且把李杜、韩柳分别视为唐代诗歌、文章之典范。
唐及五代的韩柳并称之例几乎是以韩柳文作为论文之典范,兹例如下:
外王父左冯翊太守讳敬之,韩吏部、柳柳州皆伏比贾马。文章气高,面诃卿相豪盛之非,盖不得为达官。[27]
杨公(杨敬之)朝廷旧德,为文有凌轹韩柳意。[28]
(柳仲郢)撰《尚书二十四司箴》,韩愈、柳宗元深赏之。[25]卷165
时无韩柳道难穷,也觉天公不至公。[13]卷677
来鹄,豫章人也,师韩柳为文。[8]113
刘轲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文章与韩柳齐名。[8]120
这些例子多在论述他人文章时独标韩柳之文,无疑是把其当成评判的标杆。这也表明韩愈、柳宗元逝世后不久,人们已开始关注二人的文章,且有意识地把韩柳文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整合、并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并称几乎专指文章而言,这也是韩柳文研究史上最初颇具意义的发明。成书于公元945年左右的官方史书《旧唐书》却忽视了这一现象,且在极为重要的史臣论赞中把韩、柳之文加以对立,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这也表明韩柳并称的观念于唐五代还不十分普遍。
总览唐代典籍和唐人的文学批评可知,韩柳并称在唐代并不是批评的主流,二人在当时并未同时被世人看作是文风改革的领袖。
韩愈在中唐已逐渐确立“文宗”的地位,其道德、文章常称颂于时人之口,一代宗师的地位亦是不易撼动,其求奇求新之文风具有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引起极大争议。而柳宗元的影响则相对微弱得多,他的文章、才华虽然亦赏于时人,但远未如韩愈一般受到世人的多方面关注,更遑论以文宗之尊去扫荡浮靡文风。而柳宗元由于其罪臣的身份及久居贬地,致使其长期远离人们之关注,加上他不愿为人师的性格,导致他的影响力远不及韩愈。
韩柳文并称在晚唐才出现,但韩柳并称的态势发展并不稳定。《旧唐书》就因政治与儒学的关系,把柳宗元置于韩愈的对立面。真正意义上的韩柳并称以及二人同被世人视为文坛领袖则是在北宋以后才逐渐流行并定型。关于此,笔者有专文阐释,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