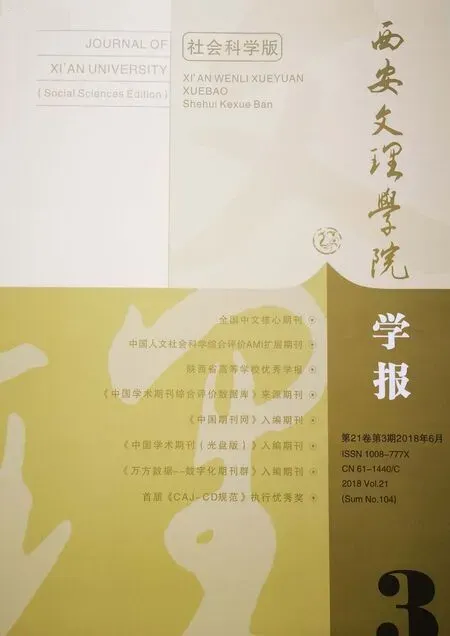唐代传奇小说对《史记》论赞的继承与发展
李 娟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论赞是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应是其正式起源。作者采用“君子曰”“君子谓”“君子以是知”这三种形式,在部分历史事件的描述之后,引用先贤或当世智者的话语来论证自己对某一事件的观点,具有“就事论事”的特征。直至《史记》的产生,史书论赞的模式才正式确立。司马迁通过“太史公曰”的论断形式,在每篇传记的文末直笔表达了作者对前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褒贬态度,具有鲜明的个人情感色彩。这种史评形式受到后世史学家的推崇,并成为史书评论的固定模式。刘知几的《史通》对此有较为详细的总结:“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常璩曰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1]
《史记》论赞不仅影响了后世史书的评论模式,对唐代传奇小说也有较大影响。许多唐传奇作品沿袭了《史记》的纪传体体裁,同时在文章的末尾添加一小部分与文中故事相关的评论,体现出作者对故事情节和人物的褒贬。这种“卒章显志”的议论手法,正是对《史记》论赞的继承和发展。
一、对论赞形式的继承与发展
《史记》又称《太史公书》,多数学者认为“太史公”即是司马迁本人的自称。《史记》的论赞主要出现在每篇人物传记的文末,以“太史公曰”作为开头是其典型形式。例如《殷本纪赞》:“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2]52司马迁在客观叙述历史人物故事之后,于文章的末尾发表与人物或故事相关的评价,而“太史公曰”则直接点明评论者的身份。唐传奇作品沿袭了这种以“某某曰”为开头的自述自评的议论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开拓和发展。
(一)沿袭“某某曰”的议论形式
唐传奇的文末议论在形式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对“太史公曰”等论赞形式的直接模仿,即采用“某某曰”的形式引出作者议论。这种议论方式较为常见,在唐传奇作品中共出现26次。例如李琪的《田布尚书传》:
梁相国李公琪传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负一女子之债,死且如是,而况于负国之大债乎?窃君之禄而不报,盗君之柄而不忠,岂其未得闻于斯论耶?而崔相国出入将相殆三十年,宜哉!”[3]2831
作者采用自述的方式在篇末点明身份,并从旁观者的角度对故事中的人物进行道德层面的评价,这与“太史公曰”的论赞方式别无二致。还有的传奇作者则借用他人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见解,例如《谢小娥传》:
君子曰:“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3]803
无论是作者自述式的直接点评,还是假借他人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唐传奇中以“某某曰”作结的评论方式均是对《史记》论赞形式的直接模仿。这种评论方式在中晚唐时期的文言小说集中比较常见,比如皇甫枚的《三水小牍》往往以“三水人曰”引出一段议论,高彦休的《唐阙史》也常在每篇传奇小说的文末加上一段以“参寥子曰”开头的文字,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所述故事的见解。
(二)新模式的开拓与发展
除了通过”某某曰”的形式来表达作者观点以外,另一种文末议论的方式则是以语气词为引导,通过直接点评的方式来表达作者的好恶。在这一类作品中,作者往往会在完整的故事情节之后,以“噫”“嗟乎”“呜呼”等语气词开头来体现对故事和人物的褒贬态度,如《宣州昭亭山梓华君神祠记》:
嗟乎!鬼神之事,闻见于经籍,杂出于传闻,其为昭昭,断可知矣。然而圣人不语者,惧庸人之舍人事而媚于神也。吴越之俗尚鬼,民有病者,不谒医而祷神。余惧郡人闻余感梦之事,而为巫觋之所张大,遂悉纪其事,与祝神之文,刊之于石。因欲以权道化黎甿,使其知神虽福人,终假医然后能愈其疾耳。[3]880
作者以“嗟乎”开头,感叹鬼神之说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于结尾处解释了自己记录上文故事的目的,是典型的凭借感叹词来引起评论的议论方式。此外,有的作者则不借用任何语气词,直接在文章的篇末进行评论,例如《杨娼传》《李岳州》等。
无论是沿袭“某某曰”的史评论赞形式,还是采用在篇末处直接议论的形式,唐传奇这种“先故事,后评论”的议论方法都是对史书论赞形式的继承和发展,并由此进入模式化状态。同时,唐传奇于篇末处议论的写作模式也影响了后世文言小说的发展,篇末议论成为《聊斋志异》等短篇文言小说作品集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二、对论赞内容的沿袭与发展
《史记》的论赞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论赞内容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或阐述创作目的,如《五帝本纪赞》讲述司马迁将黄帝、尧、舜作为《史记》开篇人物的原因;或点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如《孝文本纪赞》表达了作者对汉文帝的歌颂以及对汉武帝政治统治的讽刺。此外,《夏本纪》《周本纪》等篇目则于文末论赞中增添了与前文有关的历史事件的阐述,补充了文章史料。同时,丰富的议论内容也展示出司马迁鲜明的个人情感色彩,抒情意味十分浓厚。唐传奇沿袭了这种多元化的论赞内容,与之相比,论赞的抒情性更强。
(一)多元化的议论内容
唐传奇篇末议论的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阐明作品的立篇旨意和创作动机,这在唐传奇小说中比较常见。例如《三水小牍·殷保晦妻封氏马贼死》的篇末议论:“渤海之媛,汝阴之嫔,贞烈规仪,永广于彤管矣。辛丑岁。遐构兄出自雍,话兹事,以余有《春秋》学,命笔削以备史官之阙。”[3]2395作者阐述了故事的写作缘起,认为自己记录封夫人临危守节的故事是为了避免其高贵品格湮没于历史之中。
第二类则是直接展示作者对前文故事情节或人物的评判,借此表达作者的主观思想。与《史记》论赞点评人物和事件的内容相比,唐传奇的篇末议论则展示出更为丰富的思想倾向。例如《搜神记·焦华得瓜》:“故语云:‘仲冬思瓜告焦华,父得食之。’凡人须有善心,孝者天自吉之。事出《史记》。”[3]2991作者从传统道德观念出发,赞颂了主人公焦华的孝义精神,同时告诫世人理当心存善念。还有《玄怪录·裴谌》《枕中记》等传奇作品的篇末议论则通过评论前文故事和人物,进而总结出人生哲理、表达作者对人生短暂和命运无常的感慨。而一些与宗教有关的唐传奇小说,除了在篇末议论中表达出作者对故事情节和人物的评价之外,也展现了作者对于某种宗教思想的个人观念,如《玄怪录·张宠奴》《太平广记·杨真》等。
第三类将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故事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以此佐证作者的记录并非凭空虚构。例如陈玄祐在《离魂记》中说:“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规堂叔祖,而说极备悉,故记之。”[3]665作者指出前文故事的讲述者是莱芜县令张仲规,而故事的主人公正是其直系亲眷。因此,与民间流传的其他版本相比,自己的记录显然更贴近真相。作者也正是借此来强调故事的真实性。
(二)议论抒情化的增强
强调议论的抒情性是《史记》论赞较为突出的特点。张大可在《史记研究》中说道:“司马迁的杰出贡献更表现在他既实录史实,而又表达了强烈的思想感情倾向,反映了古代庶民的喜怒情绪,这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精华。”[4]因此,司马迁在记录历史时强调其客观性,而文末论赞时则往往选择直抒胸臆,凸显出鲜明的个性色彩。例如,司马迁在《孔子世家赞》中表达了他对孔子的极度钦佩和敬仰;在《绛侯周勃世家赞》中表现出对周勃父子的无限同情;在《平津侯主父列传赞》中表达出对世态炎凉的感慨。而其他论赞,或表赞美,或表谴责,均寄托着作者个人强烈的情感。
唐传奇小说篇末议论不仅效仿了《史记》论赞的模式,对其议论的抒情性也有所继承。但与《史记》论赞相比,唐传奇小说议论的抒情性更强烈。究其缘由,与作者的写作目的有很大的关系。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到自己著书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1808,而论赞的抒情性也是由于历史人物的遭遇让作者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故而借助议论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但其最终目的仍在于记史,因此更强调历史的实录精神,情感方面的表达相对内敛。而唐传奇强调故事的趣味性和作品的娱乐性,其写作目的在于记述奇人异事,并借此彰显作者才华,获取世人关注。所以,篇末议论中作者情感的表达与《史记》相比更加直接和浓烈,以便于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正如胡应麟所言:“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5]虽然有少数传奇小说作者在其作品中点明自己“补充史料”的目的,如沈亚之、李公佐等人。但纵观唐传奇作品,多数作者仍是以记事为由来表达个人情感,例如韩愈《毛颖传》的篇末议论:
太史公曰: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谓鲁、卫、毛、聃者也。战国时有毛公、毛遂。独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春秋》之成,见绝于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将军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无闻。颖始以俘见,卒见任使,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3]752
韩愈为毛笔作传,虚构出“毛颖”这一人物形象,篇末议论赞扬了毛颖尽其所用的行为,讽刺了秦始皇的薄情寡义。事实上,韩愈借小说中毛颖的经历,在议论中宣泄了自己对现实中帝王薄情、官场混乱现象的不满和愤慨,议论中的抒情色彩极为浓厚。同时,这种通过文章来反映社会现实的笔法,也正符合唐代古文运动中“文以载道”的创作原则。
三、对论赞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尽管是有意为小说,但唐传奇小说仍处于小说文体的早期发展阶段,某种程度上仍未摆脱史书的桎梏,其艺术表现手法深受史家写作手法的影响。唐传奇的篇末议论就继承了《史记》论赞的议论笔法,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一)对史家笔法的继承
《史记》论赞采用的是典型的史家笔法,也可称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是孔子首创的一种文章笔法,左丘明称其为“《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6]。即在写作过程中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微言大义,委婉地表达作者的主观思想,并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进而达到警诫邪恶和褒奖良善的目的。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方法,采用文末论赞的形式,将自己的褒贬态度浓缩于论赞之中,在论赞中斥恶扬善。而唐代传奇小说将作者的见解和对善恶的褒贬都纳入篇末议论之中,借评论故事来彰扬《春秋》大义的写作方法,正是对《史记》论赞中史家笔法的沿袭,同时也实现了史笔与小说议论的完美结合。
唐传奇小说之所以深受史家笔法的影响,与唐代“崇史”的风气有很大的关系,唐代是一个重视历史的时代,史官地位较高。在这种“崇史”观念的影响下,唐代知识分子注重修史的意识十分浓厚,许多文人即便无法在朝堂中担任史官,也会积极进行私人史书的编撰。而唐传奇小说的作者群体多为文人士子,其中曾担任史官或著有史学文论的就有21人,有的作者甚至将其传奇作品作补阙国史之用,皇甫枚就曾直言其传奇小说的创作目的:“笔削以备史官之阙”[3]2395。由此可见,在修史观念盛行的影响下,唐传奇小说作者和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史学思想的影响,其篇末议论也不可避免地运用史家笔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传奇小说作者运用史书笔法也是为了强调其作品具备史书的特性,进一步提高作品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力;同时显示出自己的文才、史才,达到引起读者注意、扬名立万的目的。
此外,中唐古文运动“文以明道”思想的传播,也使创作者们更强调作品的现实意义,以及要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准则和惩恶扬善的要求。唐传奇小说作者不仅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加入个人观点,更于篇末议论中直接表达自己的褒贬态度:或从儒家道德和哲理的角度对故事进行评说、或通过阐明主题来告诫世人,突出文章的教化作用。随着唐代中后期古文运动的愈演愈烈,这种偏重于讽刺时政和强调儒家道德教化的议论内容逐渐增多。至此,唐传奇的篇末议论不再限于“就事论事”式的论说风格,而转变为借评论故事来反映、揭露社会现实状况,或借此来颂扬儒家道德观念的新形式,古文运动中的“文以明道”等思想在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二)对论赞语体的继承与发展
《史记》论赞的语体基本上属于“议论而兼叙述”,写法灵活多变。有的论赞先议论而后叙述,如《陈杞世家论赞》;有的论赞先叙述后议论,如《孝景本纪论赞》;有的论赞则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如《燕召公世家论赞》。唐传奇小说的篇末议论效仿了《史记》论赞议叙结合的语体,并在此基础上更为全面地发展。
唐传奇小说的篇末议论大多篇幅不长,多达百十字,少则几十字。作者在进行议论时,或引经据典,或联系个人经历,往往采取议叙结合的方式对前文故事和人物进行评论,如高彦休的《丁约剑解》。对于字数相对较少的篇末议论,作者通常会采用纯粹议论的语体,直接对人物和事件进行简要点评,借此展现出作者的好恶和褒贬态度,抒情性极为强烈,如白居易的《记异》。但也有少数篇末议论字数长达数百字,则更偏重于使用夹叙夹议的语体,如郭湜的《高力士外传》等。
张新科认为:“唐代传奇是继承前代史传传统及杂传(包括志怪志人小说)成就基础上发展成熟的。”[7]唐传奇小说的篇末议论从议论模式、议论内容及议论方法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史记》的论赞形式,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早期文言小说依附于史传的状况。同时,这种于文言短篇小说文末增添作者个人评论的新型议论方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文言小说的创作。例如宋代刘斧的传奇小说集《青琐高议》,作者就在故事之后以“议曰”或“评曰”为开头进行议论;明代冯梦龙的《情史》也常出现以“情史氏曰”为开头的篇末议论。直到清代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的出现,文言小说进入了发展的新高峰,于篇末处记述作者议论也就此成为短篇文言小说的固定模式。